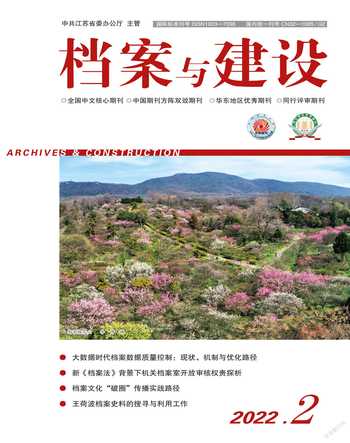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涉华档案简介
田地
摘 要:海外涉华私人档案的搜集与整理越来越受到档案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视,尤其是美国涉华私人档案资料,因其整理规范和两国交往密切,备受研究者青睐。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其手稿部藏有大量涉华私档,系统地记录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变化。这些涉华私档能够与公务档案互证,促进人物史研究不断深入,是研究中美关系史不可或缺的档案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关键词: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私人档案;中美关系史
分类号:G279
A Review of Chinese Collection in the Manuscript Division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Tian Di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East Normal University, Minhang, Shanghai 200241)
Abstract: The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of overseas private files related to China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the disciplines of archives and history, especially the American private files related to China, which are favored by researchers because of their standardized collation and close contact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ibraries in the world, the American Library of Congress has a large number of private files related to China in its manuscript department, which systematically record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Sino-US relations. These private files can prove each other with official archives, 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aracters. They are indispensable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Sino-US relations and have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Keywords: 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 Division; Private Files; History of Sino-US Relations
1 引 言
以归属所有权对档案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公务档案和私人档案。[1]在美国涉华档案资料中,相关研究者对公务档案较为熟悉和重视,而较少涉猎私人档案。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其手稿部藏有全美数量最多的私人档案,且不少与中国相关。[2]鉴于此,本文拟述评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涉华档案资料,以期为研究者利用此部分档案提供便利。
2 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整体情况介绍
1800年,约翰·亚当斯总统批准了国会法案,将国家政府机构从费城搬迁至华盛顿,同时拨款5000美元购置图书供国会使用,这就是国会图书馆的开端。[3]经过200余年的发展,国会图书馆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每个工作日接收到的相关资料平均高达15000件。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馆藏大致可分为三类:综合系列(General Collections)、国际系列(International Collections)和特藏系列(Special Format Collections)。其中,手稿部的资料属于特藏系列。手稿部的档案资料以私人文件为主,辅之以部分组织机构档案,该部所保存的私人手稿数量居全美第一。手稿部中,总统系列文件是学界最为熟知的。该系列包含华盛顿至柯立芝时期23位美国总统的文件,现已全部收录在国会图书馆“数字化典藏”(Digital Collections)数据库中,供研究者阅览和下载。除总统系列文件外,手稿部还藏有政府办公室文件系列、组织文件系列、其他文件系列、特藏文件系列和外语资源系列等。

3 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涉华档案资料介绍
手稿部涉华档案资料基本收藏在与中国交往密切的美国人的私档中。这些人背景不一、身份各异,但都是中美两国“共有历史”的见证人,他们的档案能够从不同角度反映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变化。[4]在手稿部的私档中,以“中国”为主题的相关档案高达115个系列,类型包括电报、会谈记录、备忘录、日记、报纸等多种形式。限于篇幅和研究主题,笔者仅选取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涉华档案加以介绍,主要涉及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援助、冷战时期中美对峙与缓和等内容。
3.1 抗日战争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得远东国际局势发生重大變化。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联和美国的干预。然而,美国一开始却采取消极政策。随着日本不断升级侵华战争,触及美国在华利益,美国远东政策开始转变。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后,中国进入到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积极谋求美国的援助,希望促成中美结盟联合抗日的局面。美国远东政策从“对日姑息”逐渐发展为“援华制日”,并最终在珍珠港事件后,与中国结成战时盟友。关于这一时期的档案资料,手稿部的馆藏相当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中不少人物非常重要,如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Nelson T. Johnson)、亚洲舰队司令哈里·亚内尔(Harry E. Yarnell)、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纽约先驱论坛报》专栏作家艾尔索普兄弟(Joseph Alsop and Stewart Alsop)、《时代》杂志创始人亨利·鲁斯(Henry Luce)和美国政府官员托马斯·科尔克朗(Thomas G. Corcoran)等。
纳尔逊·詹森有着30多年的在华经历,加之长期担任驻华外交官,因而能够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詹森文件绝大部分都与中国相关,内容涉及1922—1923年厦门领事馆文件、1924—1929年中国政治形势变化的报告、1927—1937年有关中美关系的会议备忘录、1927—1928年的南京事件、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美修订新约、1949年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等。[5]
哈里·亚内尔长期在美国海军服役,1936—1939年曾任亚洲舰队司令。他的文件主要包括1936—1939年美国对抗日战争的反应及其军事政策、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有关如何处理中日关系的电报和备忘录、美国从中国撤侨的相关计划、中日两国军队的兵力调动及战况分析、1937年“帕奈号”事件的详细报告、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军方对日本海军军力的评估及其动向预测、蒋介石与亚内尔的往来电报、1942年抗战形势备忘录等。[6]
拉铁摩尔作为中国问题的专家,在二战期间曾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后负责战争信息署太平洋地区事务。拉铁摩尔文件中的战时活动系列值得关注,该系列收录了拉铁摩尔任蒋介石政治顾问期间的相关资料,主要包括拉铁摩尔与国共两党领导人的会谈记录、为蒋介石准备的咨询报告、发回美国国务院的工作报告和美国对华援助资料等。[7]
在艾尔索普兄弟中,约瑟夫·艾尔索普与中国联系紧密。他于1941年作为陈纳德的助手参加飞虎队援华,次年成为美国租借使团驻重庆代表。艾尔索普兄弟文件的时间跨度将近半个世纪(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其中抗战时期的资料主要涉及约瑟夫·艾尔索普 的在华经历、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与援助、史迪威和陈纳德及其飞虎队的相关内容。[8]
美国对华经济援助的资料主要收藏在亨利·鲁斯文件和托马斯·科尔克朗文件中。两人都是抗战期间对华援助的积极倡导者:前者凭借其创办的《时代》和《财富》等杂志,宣传中国为抗战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并筹集资金援助中国抗战;[9]后者在罗斯福政府时期先后任职于财政部和司法部,与国民政府交往甚密。在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成立与运作上,科尔克朗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宋子文与美国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10]两人的档案资料包括中国抗战形象的宣传、中美两国就援华物资问题的交涉、美国援助物资的运输状况、美国援华联合会和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等相关资料。
除上述文件之外,该时期的涉华档案资料还收藏在以下私档中:亚瑟·斯威策文件(Arthur Sweetser Papers)、弗兰克·麦考伊文件(Frank McCoy Papers)、弗兰克·法雷尔文件(Frank Farrell Papers)、卡尔·阿克曼 文件(Carl W. Ackerman Papers)和梅里尔·穆尔文件(Merrill Moore Papers)等。
3.2 “失去的中国”与中美对峙(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
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败局已定,共产党将执政中国,中美关系再次面临着抉择与考验。在冷战国际局势下,美国强烈的反共主义和中美关系神话的幻灭,使得“失去的中国”不可避免。[11]美国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全方位敌视政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遏制中国发展,并借台湾问题等干涉中国内政。
抗战期间一些帮助过中国的“朋友”在冷战时期长期敌视新中国,与台湾方面保持着密切联系,例如美国报业大亨罗伊·霍华德(Roy Wilson Howard)和亨利·鲁斯。霍华德在二战期间借助名下的报社集团,积极宣传中国抗战形象。国民党敗退台湾后,他依旧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等人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霍华德文件的涉华资料主要收录在外交文件系列中,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冷战时期美台关系的演变、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等内容。[12]在鲁斯文件中,也可以找到鲁斯与蒋介石的信件往来以及冷战时期美国的“反共宣传”档案。艾尔索普兄弟文件收录了1946—1956年间《纽约先驱论坛报》事实专栏的相关资料,该专栏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可以反映出冷战前期美国部分精英人士的中国观。
尽管中美关系在这一时期处于敌对状态,但是,依然有一些爱好和平的美方人士与新中国保持密切沟通,例如,社会活动家约翰·亚当斯·金斯伯里(John Adams Kingsbury),他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卫生和福利制度。金斯伯里于1952年访问中国大陆,其私人文件中有对此次访华之行的详细记录。此外,金斯伯里文件还保存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与郭沫若、刘宁一和陈叔通等重要人士的信件往来和备忘录,主要涉及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和世界和平大会等内容。[13]
一些媒体人士的私人文件也有关于该时期中国的资料,例如亨利·夏皮罗(Henry Shapiro)和沃尔特·沙利文(Walter Sullivan)。夏皮罗是合众国际社驻俄罗斯分社的记者,在苏联生活学习长达40年(1933—1973)。他的文件中有关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的资料,包括个人的观察记录和相关新闻报道。[14] 沙利文是《纽约时报》的著名记者,有关中国的资料主要集中于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涉及劳工、贸易、土地政策、军事、教育和台湾等问题。[15]
3.3 缓慢解冻与中美关系正常化(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
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是促成中美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握手言和”的重要因素。尼克松政府上台后,中美接触进入到了“快车道”。1972年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开始,打开了中美关系史的新篇章。然而,由于台湾问题和美苏关系的变化,尼克松访华后至福特政府时期,中美关系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卡特政府时期,美苏矛盾的加剧使得美国政府下定决心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并于1979年1月1日与中国政府正式建交。手稿部关于该时期的资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官员的私人文件,例如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弗朗西斯·瓦莱奥(Francis R. Valeo)和迈克尔·珀楚克(Michael Pertschuk)等,另一类是记者或者社会活动家的私人文件,例如詹姆斯·米切纳(James A. Michener)、理查德·杜德曼(Richard Dudman)和詹姆斯·福尔曼(James Forman)等。
威廉·道格拉斯曾先后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1937—1939)和最高法院助理法官(1939—1975)。在他的私人文件中,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是涉华资料的核心内容。1969年1月24至26日,美日政要围绕对华政策开展了一场高级别会议讨论,参会人员有道格拉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莱特(William Fulbright)等,讨论的议题涉及两国重新评估对华政策、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中日经贸问题和台湾地区问题等。此次会议的详细资料都收录在道格拉斯文件中。除此之外,道格拉斯还于1966年和1974年两次访华,这两次访华的准备工作、与中方的联络交涉、访华行程等文件都收藏在其私档中。[16]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问题上,美国国会的作用不可忽视。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国会改革后,它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明显增强。透过弗朗西斯·瓦莱奥和迈克尔·珀楚克的私人文件,可以看出国会在中美关系上所发挥的作用。瓦莱奥是参议院秘书长(1966—1977)和外交事务顾问,二战期间曾作为美国援华军人参加抗日战争。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访华后,瓦莱奥跟随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Mansfield)等人3次访问中国,在其文件中可以找到大量与之相关的档案资料,包括访华期间与中方的会谈记录、访华报告和备忘录、国会对于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判断和评估、相关电报通讯往来等资料。[17]迈克尔·珀楚克曾长期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任职(1964—1977),后任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1977—1981)。1976年跟随国会代表团访华,并与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等中方官员会晤,此次访华行程的详细资料都收录在他的文件中。[18]
环境外交是学界近些年来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罗素·崔恩(Russell E. Train)是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时期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主要筹划者和实施者。在他的文件中,收录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有关环保问题的交涉,涉及崔恩1975年访华之行和致基辛格等人的备忘录。[19]
理查德·杜德曼是美国著名记者,长期供职于《圣路易斯邮报》(St. Louis post-dispatch)。其个人文件中关于中国的资料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华认知的转变,主要包括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就中国问题所发表的演讲,以及相关媒体人士對中美关系走向的评论和报道;另一部分是卡特政府时期的中美关系,包括万斯访华的备忘录、中美两国对万斯访华的新闻报道以及美方政要呼吁中美两国尽快正式建交的相关资料。[20]
詹姆斯·福尔曼是20世纪60年代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的重要成员,曾担任执行秘书和国际部主任等职务。为了让国际社会支持美国民权运动,福尔曼于1970—1972年访问中国、越南等国,此行的相关资料收录在其个人文件中。此外,福尔曼文件还涉及中国国内政治运动、毛泽东逝世和中美关系等内容。[21]
4 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涉华档案的学术价值
手稿部的涉华私档是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等领域的重要档案资料。但遗憾的是,这些档案未能引起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总体来看,手稿部涉华私档的学术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
4.1 有利于丰富中美关系史等研究领域的史料来源
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务档案由国家各级档案馆整理保存。私人档案则作为 “私有财产”由个人保存处置,一般不会移交档案馆。然而,个人保存档案存在着诸多不便,图书馆通过接受捐赠和购买等途径成为私人档案的主要储存机构。由于私档不易搜寻且整理困难,使得学界在档案利用上形成了“重公轻私”的特点,集中在手稿部的涉华私档就显得弥足珍贵。以美国国会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所起作用为例,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多是参考国会报告记录等文献,存在着史料种类单一、史实还原有限和缺乏个案研究等问题,而手稿部的相关档案则能有效弥补这一缺憾。瓦莱奥和珀楚克等人的私档中藏有大量有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资料,内容涉及多个议员访华前的准备材料、瓦莱奥与中国外事部门的联络信函、国会代表团访华行程见闻、重要会谈记录与备忘录、议员访华行程的总结报告和相关剪报照片等。这些档案为研究美国国会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参考,若能进一步与相关公务档案结合,必将有力推进此问题的深入研究。
4.2 有助于深化涉华相关重要人物研究
私档保留了笔记、信函和回忆录等与个人活动密切相关的文件,这为研究重要人物的个人经历、思想演变和在重大事件上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由此可推进人物史的深入研究。例如,近年来学界注意到托马斯·科尔克朗在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成立和运作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鲜有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相关档案资料的欠缺是掣肘该问题深入研究的重要原因,而手稿部的科尔克朗文件则能有效弥补这一缺陷。科尔克朗文件分9个系列,有关国防供应公司的档案收藏在家庭文件(Family Papers)、综合通信(General Correspondence)和主题文件(Subject File)等系列中,共计20余盒,涉及科尔克朗在国防供应公司筹备和前期运作的种种努力,包括他与宋子文之间的联络以及说服毕范里(Harry B. Price)等美方重要人士加入国防供应公司的相关档案,此外还涉及该公司的组织架构和运作体系等方面的内容。
4.3 促进跨国史和国际史的研究
跨国史和国际史研究要求打破民族国家界限,注重多国多边档案和文化因素的作用,强调“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22]手稿部的涉华私档收录了不少传媒人士的档案资料,他们的视角多从“下层”出发,能够反映中美两国社会与文化方面的交流与互动。通过研究卡尔·阿克曼、亨利·鲁斯、罗伊·霍华德和理查德·杜德曼等人的档案资料,我们可以梳理出不同时期的中国形象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传媒人士在中美关系史上的作用、中国形象的变迁与多元化等问题。
4.4 需要注意的問题
首先,相较于公务档案,私人档案的权威性和准确性都略低一筹,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利用时加以考证。例如,珀楚克文件中收录了一份国会代表团与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的会谈记录,该份文件的时间有明显错误。其次,私人档案形式各异,有的材料缺乏时间和人物等要素,有的材料为手写体,这就加大了研究者识别和利用的难度。最后,由于档案整理方式的差异,无形中增加了私档利用的难度。一般来说,档案馆中的档案严格遵循来源原则加以编目整理,而私档由于其规模不大,材料形式多种多样,很难形成合理统一的整理体系。因此,不同的私档利用的便易程度也不一样。在手稿部中,每个系列的私人文件都配有相关指南供参考利用,但指南编纂的详略程度各不一致,无形中也增加了使用 的难度。
*本文系浙江省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美国对印度核政策研究(1947—1989)”(项目编号:2021RD006)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4.
[2]张仲仁,翁航深.美国档案文件管理[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63.
[3]John Y.Cole.America’s Greatest Library: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M].Washington,DC:The Library of Congress,2017:1.
[4]徐国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1-22.
[5]Nelson T.Johnson Papers: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7-19].https:// 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12/ms012128.pdf.
[6]Harry E.Yarnell Papers :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7-19].https:// 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18/ms018012.pdf.
[7]Owen Lattimore Papers :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7-19].https:// 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03/ms003022.pdf.
[8]Joseph Alsop and Stewart Alsop Papers :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7-19].https://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 mss/2008/ms008095.pdf.
[9]Henry Robinson Luce Papers: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7-19]. https://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03/ ms003045.pdf.
[10]Thomas G.Corcoran Papers: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7-19]. https://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03/ ms003011.pdf.
[11]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03):177-191.
[12]Roy Wilson Howard Papers: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8-30]. https://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10/ ms010299.pdf.
[13]John Adams Kingsbury Paper s: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8-30]. https://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03/ ms003054.pdf.
[14]Henry Shapiro Papers: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8-30]. https://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03/ ms003072.pdf.
[15]Walter Sullivan Papers: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8-30]. https://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18/ ms018010.pdf.
[16]William O.Douglas Papers: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9-15]. https://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02/ ms002011.pdf.
[17]Francis R.Valeo Papers: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9-15]. https://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09/ ms009064.pdf.
[18]Michael Pertschuk Papers: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9-15]. https://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06/ ms006018.pdf.
[19]Russell E.Train Papers: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9-15]. https://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09/ ms009069.pdf.
[20]Richard Dudman Papers: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9-15]. https://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12/ ms012069.pdf.
[21]James Forman Papers: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9-15]. https://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10/ ms010125.pdf.
[22]徐國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国际史研究方法及其应用[J].文史哲,2012(05):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