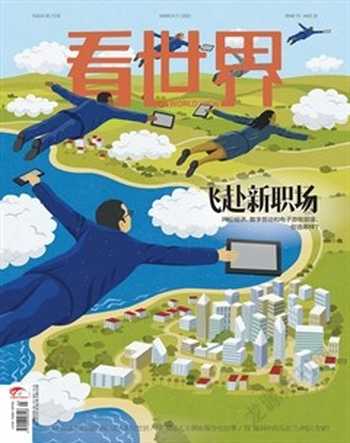“文化混合”之地乌克兰
谢尔希·浦洛基

2014年3月18日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胜利日,此时正是这位61岁的俄罗斯总统的第三个任期。
当天他发表了一篇演说,地点是克里姆林宫中建于沙皇时代的圣乔治大厅—用来会见外国代表团和举行最隆重的国家仪式的地方。这位总统在演说中,请求聚集于此的俄罗斯联邦议会成员通过一条关于将克里米亚纳入联邦的法律。
他的听众们不止一次对演说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样的反应意味着,这条法律无疑会在第一时间通过。三天之后,联邦议会即宣布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俄乌之间各条约和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曾对乌克兰的主权给予了保证。在乌克兰看来,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行动。然而在演说中,弗拉基米尔·普京将这次吞并视为历史正义的胜利。
普京的论证在本质上也的确是历史的和文化的。他将苏联的解体称为对俄罗斯的剥夺,不止一次将克里米亚称为俄罗斯国土,将塞瓦斯托波尔称为俄罗斯城市。他指责乌克兰当局漠视克里米亚人民的利益,并曾在近期试图侵犯克里米亚人的语言和文化权利。普京声称:正如乌克兰有权脱离苏联,克里米亚也同样有权脱离乌克兰。
在乌克兰危机中,历史不止一次成为借口。它不仅被用来对危机参与者进行宣传和鼓动,也被用来为对国际法、人权乃至生命权本身的侵犯行为辩护。尽管俄乌冲突的爆发出乎意料,让许多被波及的人猝不及防,但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丰富的历史指涉。
姑且不论对历史证据的宣传式利用,至少有三种植根于过去的过程如今正在乌克兰同时上演:其一是俄罗斯在17世纪中叶以来莫斯科所取得的帝国范围内重建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的努力;其二是现代民族认同的建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涉及其中(后者往往被地区边界所分割);其三则是基于历史和文化断层的争夺—这些断层使得冲突参与各方将这场冲突想象为东方与西方的竞争,想象为欧洲与俄罗斯世界的竞争。
乌克兰危机,让世界想起18世纪晚期俄国对克里米亚的并吞,以及俄国在南乌克兰所创建的那个没有存在多久的帝国省份“新俄罗斯”。
让关于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扩张记忆浮出水面的,是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的混合战背后的那些理论家——“新俄罗斯”方案的提出者。他们所寻求的,是以帝国征服和在克里米亚鞑靼人、诺盖鞑靼人和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故乡建立俄罗斯统治为基础,发展自己的历史意识形态。
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两个“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以及创立敖德萨共和国和哈尔科夫共和国(这两地也同为设想中的“新俄罗斯”的组成部分)的尝试,同样有其历史根源,可以上溯到苏俄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1918年3月)。当时,布尔什维克们在这些地区创建了多个国家,其中包括克里米亚共和国和顿涅茨克—克里维伊里赫苏维埃共和国—这些共和国自称独立于莫斯科,因此不在条约限制范围之内。
新的顿涅茨克共和国的创建者们,借用了1918年的頓涅茨克—克里维伊里赫共和国的部分符号—与从前那个共和国一样,如果没有莫斯科的资助和支持,他们的这个新“国家”就没有机会兴起或者维持下去。
对俄罗斯帝国历史和革命历史的引用,已经成为为俄罗斯对其周边保持扩张心态提供辩护的史学话语的一部分。然而,这次冲突背后的历史动因,却来自更晚近的时期。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其关于“收回”克里米亚的演说中,曾回忆起苏联迅速而出人意料的解体过程。这场解体才是乌克兰危机最为直接的历史背景。
当下的俄罗斯政府一直声称乌克兰是一个人为创造的国家,而乌克兰的东部领土是苏俄赠送给乌克兰的礼物——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克里米亚一样。根据这种历史叙事,政治体可因血统纯正而拥有历史合法性,就比如早先的俄罗斯帝国和后来的苏联。
今天的俄罗斯,似乎走上了部分前身的老路:哪怕在失去帝国很久之后,它们仍对之依恋不舍。苏联的崩溃,让俄罗斯精英阶层对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切齿痛心,并将这场崩溃想象为一次由西方的恶意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等愚蠢竞逐权力的政客所导致的偶然事件。对苏联解体的这种看法,让他们难以抵挡重写历史的诱惑。
对乌克兰而言,其独立主张则从来都有一种亲西方的色彩。这是乌克兰历史经验的产物:作为一个国家,乌克兰正位于东西方分界线上。这是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界线,是中欧帝国和亚欧大陆帝国的分界线,也是这些帝国的不同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分界线。
这种地处几大文化空间交界地带的状况,让乌克兰成为一个接触区,在这里持不同信念的乌克兰人可以学会共存。这种状况也催生了各种地区分界,使之为当下冲突的参与各方所利用。乌克兰向来以其社会的文化混合性著称,近来更是因为这种混合性而备受推崇。然而,在面临一场“混合战”之际,一个民族在保持统一的前提下,到底能承受多大程度的混合性?这是当下的俄乌冲突将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乌克兰的亲欧革命,发生于冷战结束1/4个世纪之后,却借鉴了冷战时期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该地区其他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共有的对欧洲西方的想象,在某些时候甚至将这种想象变成了一种新的民族宗教。2014年4月,只有1/3的乌克兰人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到了当年11月,这一比例已超过50%。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战争的体验不仅将大多数乌克兰人团结起来,还让这个国家在感情上更倾向于西方。
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在顿巴斯引发战争,并在乌克兰其他地区引发动荡。这不仅在乌克兰,也在整个欧洲造成了一种危险的新局面。无论当下乌克兰危机将走向何方,乌克兰的未来、东欧—西欧(俄罗斯—欧盟)关系的未来,进而至于整个欧洲的未来,都将有赖于危机的解决。
(本文获出版社授权,标题为编者所加)
欢迎各出版社荐书,责任编辑 董可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