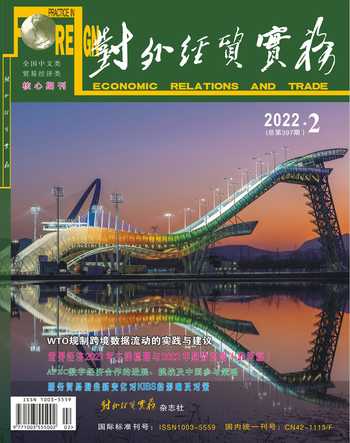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调整与应对

摘 要:美欧发达经济体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相对获益“受损者”角色导致其国内保守主义抬头,而相对剥削感的代际累积性增强又不断酝酿出对全球化不满的民粹力量,二者合力生成了这股反全球化逆流。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局部退潮和经济区域化的持续加深是当前全球化进程调整的双重表现。凝聚多边主义的全球共识、贯彻均衡共享的发展理念、构建层次分明的循环网络和顺应潮流地推动国际经贸体制改革是应对全球化进程调整的争取方向和战略抓手。
关键词:逆全球化;分配驱动;均衡共享
美欧发达地区在近年来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逆流,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法国黄马甲运动以及数个欧洲民粹政党先后上台执政等事件都是这股逆流持续泛滥的直接体现。借助民粹力量获得执政地位的政治精英为回应这股“民意”而出台了一系列逆全球化举措。全球化进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自世界市场形成以来,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三波全球化,国际社会缺乏领导、国家之间以邻为壑和各自为战的历史曾多次上演。曾经的全球化推动者却演变成了现今的反对者,曾经一路高歌猛进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
一、经济全球化及其派生现象
全球化(globalization)實质是在利润最大化目标驱动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进行的优化配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经济全球化定义为“因商品、服务贸易、国际资本流动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而导致世界各国在以经济为主的诸多领域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逆全球化描述了经济全球化由全面开放退回到有条件开放甚至是封闭的过程。而反全球化现象与全球化进程相伴而生,当反全球化力量积累到超越全球化的推动力量之时就被视为逆全球化。这三类经济现象往往繁复交织在一起:就进程而言,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相伴而生,从出现伊始就是一体两面;就结果而言,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则相反相对,二者力量此消彼长;就动力而言,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同根同源,均由分配不均驱动。
比较优势理论为自由贸易贡献了有力的理论注解。不过,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为英国自由贸易政策辩护时却有意忽略该政策所创造的分配效应,即自由贸易会导致不同行业和不同阶层间的收益分配不均。换言之,反全球化逆流由全球化进程所创造的国家间相对获益不均而生成的保守主义和社会财富两极分化而生成的民粹主义两股力量合流所驱动。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间的经济增长不同步会导致相对获益较少者的保守主义抬头,而相对剥削感的代际累积性增强又酝酿着出对全球化不满的民粹力量不断滋长,二者合流并借助政治选举、游行示威等渠道反精英、反建制和反全球化诉求。当然,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自动化和劳动代替也是发达经济体失业率攀升、行业和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晚年也表示当贸易双方都在技术进步,进步快的一方将对慢的一方产生持续性损害,修正了李嘉图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
二、美欧反全球化逆流的生成逻辑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东升西落、南升北降”趋势引发了美欧国内保守主义阵营对既往经济政策的隐忧以及对全球化有关议题的辩论和反思。以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为例,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以及欧盟整体的经济规模均不及2008年。美国2019年的经济虽然相对2008年增长了47%,但GDP全球占比却不及2000年。除美国外的其他发达经济体至少要到2023年前后才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却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群体性崛起。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相较中国、印度和韩国等新兴经济体呈现相对下降趋势,印度和韩国2000年的经济规模仅占美国的10.19%,至2019年提高到了21.08%。疫情背景下的美国经济在2021-2022年相较中国而言下降更为明显。
这股反全球化逆流内生于新自由主义,却也反噬了新自由主义。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倒置的第二意象”强调国际社会是运行在国内社会基础上的国际社会,国家的对外政策植根于国内社会而并非单纯受国际体系的结构约束。这轮反全球化逆流在美欧地区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所有者的经济嗅觉最为敏锐,高技术工作者的经济创造力也更加突出,而普通劳动者往往会沦为由时代浪潮裹挟前进的被动角色。经济全球化成了美欧财富精英的“全球避税化”,普通劳工阶层却成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收益受损方。以美国为例,自1983年以来高收入家庭与中低收入家庭间的财富差距持续扩大。即便在经合(OECD)成员中,美国的贫富差距也相当突出,前10%的家庭占有79.5%的社会总财富,后60%的家庭仅占有2.4%的社会总财富。中下阶层经济状况的不断下滑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和政治激化,滋生了深厚的民粹主义土壤。在特朗普赢得大选前的2015年,美国贫困率比2007年经济衰退最严重时还高1%。美国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危机中的家庭与文化回忆录》(Hillbilly Elegy: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所描述“乡下白人”与孩子们所面临的家庭争吵、暴力、酗酒、精神创伤以及难以摆脱的贫穷困顿,就是对特朗普获选民意基础的生动写照。事实上,欧债危机、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和中东难民危机等背后都有新自由主义的影子。深受现代化理论影响的部分拉美国家深陷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转型困难重重的中东国家难以摆脱“资源诅咒”。“阿拉伯之春”就是新自由主义席卷中东后煽动民粹力量对中东国家政治体系进行的一次结构性“改造”,由此引发的难民危机又成了部分欧洲国家民粹政党上台和英国“脱欧”公投的重要背景。社会中下阶层借助总统大选、“脱欧”公投和游行示威等渠道,释放了一股声势浩大、解构性强的“反全球化-反精英-反建制”力量。
美欧地区的全球化利益受损群体,包括产业转移及业务外包所引发的失业群体、与跨国移民和入境难民竞争工作的当地居民等都是反全球化的代表力量。美欧民粹领袖将其遭遇的困境归咎于既往的经济全球化政策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在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单边主义大行其道。特朗普当选后在国际舞台上“大展拳脚”,修筑隔离墙、发动多起贸易战、逼迫盟友提高军费摊派比例、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一系列多边主义安排以及迫使世贸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停摆等,就是对既往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巨大挑战。
三、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调整与演进趋向
(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调整
世界银行(WB)将世界市场形成以来的全球化划分为三波,即1870-1914年的全球化第一波、1945-1980年的全球化第二波和1980年代至今为全球化第三波。若以主导国和引领思想为标准,又可将其划分成英国主导下的全球化和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英国主导的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与世界银行定义的全球化第一波相重叠,刚刚经历拓荒时代的世界市场建基于帝国-殖民体系之上,以东印度公司为经济载体,实行以英镑为核心的金本位制,而自动的国际收支平衡机制极大限制了各国的货币主权和财政自主性,资本主义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终结了这轮全球化进程。
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又可细分为三个进程。第一程被称为嵌入式自由主義全球化,与世界银行定义的全球化第二波相一致,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关贸总协定(WTO前身)作为协调和管控成员国货币政策、发展资金和贸易分歧的重要平台,修正了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部分弊端,兼顾了各成员国利益和民众福利。冷战终结后,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引领的美式全球化进入2.0时代,大体等价于世界银行定义的全球化第三波。东西方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板块逐渐融合统一,以跨国公司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推动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高度互嵌、深度融合。不过,新自由主义全球化2.0所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所创造的“分配”效应又引发了美欧的民粹力量和右翼势力崛起,美欧发达经济体兴起的这轮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和运动就是当前全球政经格局深刻变革的产物,也预示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事实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也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发展理念和增长动力。当然,经济全球化运转的基础制度架构仍旧以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主导缔造的基本盘为依托,以WTO为核心的全球经贸治理体制正处于改革争论之中,众多地区性经贸安排也层出不穷。作为全球经济的关键引领力量,中美关系势必会深刻塑造全球化第三程的总体样态。拜登执政以来,中美贸易战虽已降温,但美国对华相关领域的头部企业打压力度从未放松,全球产业分工将继续沿着“高端技术产业双轨并行,中低端产业相互融合”的方向演进。
(二)经济全球化的演进趋向
世界经济将沿“全球化速度放缓、经济区域化加深”的趋向演进。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Dani Rodrik)在区分高度和中度全球化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化悖论”和“不可能三角”,即国家无法同时实现民主政治、国家主权和经济全球化。尽管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赋予了成员国兼顾本国利益和民众福利的权利,但仍无法摆脱“不可能三角”诅咒。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国际对外投资(FDI)曾伴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迅速增长,从1970年的123.58亿美元增长至2007年的3.134万亿美元,但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震荡下滑至1.447万亿美元,至2017年才恢复到2.745万亿美元的水平,而2019年又在1.498万亿美元左右。与此同时,以WTO为核心全球多边经贸治理机制也深陷困境。被誉为WTO皇冠上明珠的争端解决机制(DSU)也陷入“停摆”,从2019年12月11日起,WTO上诉机构因两名美国、印度法官到期离任而无法运行。2020年3月,WTO新任总干事的成功选举虽为其改革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但成员国对机构改革的争议不断,全球多边经贸治理机制无法有效满足各方诉求。从奥巴马政府绕开WTO试图分别建立起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的区域经贸协定,到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威胁退出WTO。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前任的贸易政策,并未做出实质性改变。
然而,全球产业链的区块化和经贸治理的区域化水平却显著加深。事实上,美国所发起的多起贸易战都旨在重构全球产业布局,新冠疫情大流行又更加凸显了以医疗器械等为代表的全球供应链之脆弱性,进而加快了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化步伐,与之配套的高标准区域经贸协定层出不穷。自2018年以来,美墨加贸易协定 (USMCA)、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协定(PIIE)、欧盟与日本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EP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等分别覆盖全球各主要区域的高标准经贸协定不断签署或生效。
四、经济全球化阶段调整的应对举措
(一)凝聚多边主义的全球共识
坚决捍卫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与WTO成员加强沟通互信,凝聚多边主义共识,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保证全球化进程不发生根本的方向逆转。尊重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利,抓住机遇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沿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要主动顺应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区块化布局与区域化调整趋势。在加入RCEP基础上,积极表态加入CPTPP等高标准区域自贸协定。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要秉持共商、共建和共享的包容性、开放性合作理念。
(二)贯彻均衡共享的发展理念
新自由主义无法有效回应这股逆流所发起的现实挑战,而强调均衡共享的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则能够有效兼顾社会各阶层需求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成员利益。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借助举国体制大力推进脱贫攻坚,通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来有力回击极端左派思想和民粹思潮的危害。落实“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战略更是中国为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贡献的智慧和解决方案。“市场规模决定分工层次”和“贸易使得人人受益”等自由主义理念虽然揭示了全球化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但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却并未实现南方欠发达国家的利润积累,其在全球发展中的不利地位也没有得到显著改善。中国为此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弊端进行了部分修正,有力回击了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所发起的种种挑战,为人类社会继续推进全球化行稳致远开出了一剂“治病良方”。
(三)构建层次分明的循环网络
中国曾借助美欧所主导国际经贸网络建立起“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的传统国际大循环,但也积累了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伴随着全球产业布局和供应链的区域化调整以及世界经济增长的诸多不确定性增加,要建立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的国内大循环和以推进更高水平开放为目标的国际大循环。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和超大市场规模优势提升了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确定性。实施“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和“区域协调”等发展战略,缩小城乡、产业和区域差距。借助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途径将超大规模市场共享全球,畅通国际和国内双循环网络。美欧国家仍是需要努力争取的重要合作伙伴,联合美欧内部的多边主义力量,确保全球化进程顺利调整。疫情背景下的东盟一度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亚太特别是东亚成为中国构建国际大循环的首要近邻圈层。此外,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形式将国际大循环网络不断拓展和深化。主动承担起大国责任,分享发展红利,提高中国崛起的国际可接受度。
(四)推进顺应潮流的体制改革
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大幅提升也意味着参与塑造国际经济治理规则与机制的能力增强。要积极支持以WTO核心的全球多边经贸体制改革,打破上诉机构的成员遴选僵局,加强对违规行为的约束力度和惩戒机制建设,推进电子商务和跨境数据流动等新议题的多边讨论。加强与WTO成员国之间的沟通协作,形成一份符合大多数成员共识与期待的改革方案,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此外,要推动以RCEP为代表的区域自贸易协定落实,融入高水平自贸协定,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倒逼国内的体制机制改革,加强产权保护、国企改革、劳工权益保障以及绿色标准建设等。
五、结论与启示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以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社会困境。美欧国家的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合流生成了一股强劲的逆全球化潮流,这是对既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内-国际双层“分配效应”的一次内生性反噬,但新自由主义却无法有效回应这轮逆全球化所发起的种种挑战。事实上,更加强调均衡共享的社会主义发展理念为解决全球化所遭遇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可行思路。未来世界经济将沿着全球化速度放缓和经济区域化加深的方向演进。新冠疫情加速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区块化步伐。在国际场合要凝聚多边主义共识确保全球化进程不发生根本逆转,贯彻均衡共享发展理念来缩小贫富差距并增强世界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沿着全球化进程调整的方向构建起层次鲜明的循环网络,确保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积极顺应潮流,推进以WTO为核心的多边经贸治理体制改革,主动融入区域高标准自贸协定,以高水平开放倒逼高水平体制机制改革。
注释:
①本文数据来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Globalization: Threat or Opportunity?”April 12, 2000 (Corrected January 2002); 世界銀行:《世界发展指标》。
参考文献:
[1] Evan E. Hillebrand, “Deglobalization Scenarios: Who Wins? Who Loses?” Global Economy Journal, Vol.10, No.2, 2010, pp. 1–21.
[2]丹尼·罗德里(Dani Rodri).全球化的悖论:什么样的全球经济新秩序才最有意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 戴翔,金碚.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基于全球分工演进视角[J].开放导报,2021(5):49-57.
[作者简介]苏冠英(1996—),男,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