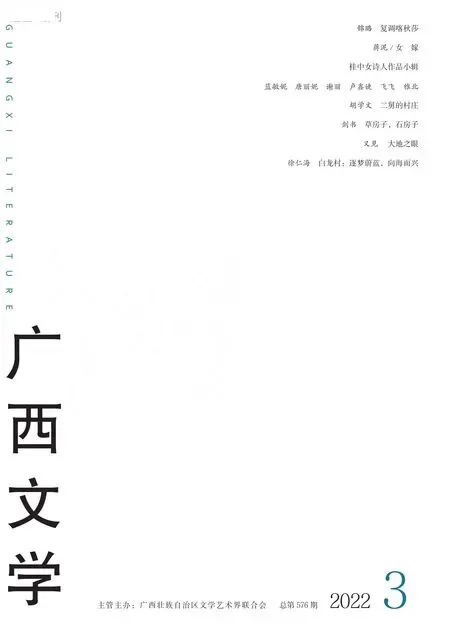恍然书
丁小龙
这是林书海今年第七次梦见大火了,梦见大火烧掉了整个书店。他如临深渊,没有惊慌与惊恐,而大火最终淹没了他的灵魂。梦醒后,他的身上似乎仍带有灰烬的气息。打开手机上的搜索引擎后,他特意查了这个梦的含义。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读:一种说是凶兆,预示着即将而来的灾难;另一种说是吉兆,预示着将会来财。他对着屏幕苦笑,于是打开了蓝牙音箱,整个房间回荡着马勒的《复活交响曲》。多年过去了,这部交响曲仍旧是他最爱的音乐作品。这部关于重生的作品无数次照亮了黑暗中的他。
像往日一样,他骑上电动车,约莫十分钟后到了书店门口。把车子放好后,他便去了不远处的老马家餐馆,点了自己最爱的胡辣汤,搭配黄灿灿的金丝饼。这原本是他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分,如今却带了某种哀伤的乡愁色彩。这个店的胡辣汤,他已经吃了十多年了,却从未厌倦。世界变样了,很多事情也变味了,但这胡辣汤却从来没有变过味,是时间的恒远味道。或许这也是他钟情于这家店的缘故。
店里的老板和他大致上是同岁,每次见到他,都会说同样的话:你来了啊,快到里面坐。临走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话:慢走啊,再来。这两句话仿佛时间的针脚,在他的体内有规律地运转。今天临走时,他对老板说,不知道还能在你们这里吃几次了。老板说,这周末,我们就搬走了。他说,太可惜了,这么多年的老店了,说没就没了。老板说,人也一样,说没就没了,这也是天意吧,之后会开新店的,有机会了来坐坐。他说,是啊,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你的名字。老板笑道,我叫马远航,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我们家就做胡辣汤了,从河南做到了陕西。他也说了自己的名字,之后便离开了这家店,回到了书店。
打开书店门后,光也随之洒了进来,带来夏日的最后温情。天气预报说接下来的半个月都是阴雨天,而他再也不用为接下来的雨季发愁了,因为眼下的书大部分已经有了各自的出路。他打开手机,拍了书店的一角,先后上传到微博与豆瓣,配上了但丁《神曲》中的名句——我看到了全宇宙的四散的书页,完全被收集在那光明的深处,由仁爱装订成完整的一本书卷。他又登录孔夫子旧书网,看到了新接的六个订单,于是去了地下室,把所需要的书一一找出来,摆好在前台。他叫来了快递,按照地址帮顾客把这些书寄走。每次和不同的书告别,他都有某种不舍,毕竟有或深或浅的交情。再过一个月,这个书店就要消失了,而整个幸福堡也将会化为灰烬,从城市中消失。这里将变成新的商业区。
半年前,他就听到了幸福堡将要被拆迁的消息。那时候,他还没有做好离开的准备。毕竟在这里干了十五年了,身体与灵魂已经扎进了这个城中村,仿佛门外繁茂的梧桐树。他用了很长时间才慢慢消化了这个事实,却依旧不敢想象没有了书店的日子。如果没有了这个书店,他可能会再次过上那种被罢黜的漂流生活。他把自己的困惑讲给了好友周洲听,周洲回道,你这个书店也不怎么挣钱,这刚好是个机会,你可以出去谋个事情。他苦笑道,这么多年都不上班了,早都不适应那样的活法了。周洲说,没啥适应不适应的,你当年可是咱们班的大才子啊,要不我在我表哥的公司给你谋个职务。他说,以后再说吧,这种事情也只能说给你听了。和周洲说话,就像与另一个自己交谈。他们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
周洲是他的大学舍友,也是他至今唯一联系的大学同学。大学毕业后,周洲去了县城的政府部门做公务员,三十二岁被调到了市里,三十六岁又被提到了省城,一步步稳扎稳打,如今是处级干部。与周洲的扶摇直上相比,他却平淡无奇,一直都在经营这家旧书店,旱涝保收,没什么大的起伏,是世俗意义上的普通人。周洲每次来找他,什么掏心窝的话都会告诉他,说得最多的是自己枷锁般的生活。自从工作后,周洲几乎就没有了读书的心境,只有与他相处的短暂时间里,才能脱离俗世的束缚,看见自由的幻象。有一次,周洲说自己厌倦了牢笼般的日子,说自己羡慕他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也想把自己心中的苦水倒给对方听,但话都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只能点头苦笑。直到书店面临倒闭,他才把自己的难处告诉了周洲。对于他而言,周洲更像是镜子中的自己。或者说,周洲是自己的另一个分身。
十点半,周洲来到了书店,带来了黄金芽。他说,来就来了,每次来都带茶叶,这么生分的。周洲说,我在你这蹭吃蹭喝,也不能空手来嘛,再说茶叶也是别人送我的。他说,公家的饭不好吃,你可要把碗端平啊。周洲说,我在里面摸爬滚打十几年了,知道其中的分寸。说完话后,周洲自己下了楼,去了地下室,而林书海继续写那篇关于《过于喧嚣的孤独》的书评。编辑已经催过两次了,今天一定要完成这篇约稿。上午来买书的顾客不多,这是最宝贵的写作时光。到了下午,他就会被各种事情分神,只能用零碎的时间来啃噬这些无尽的书。对于像他这样的人而言,这是无言又苦涩的快乐。他已经无法想象没有书的生活了。书,是他的亲密伙伴,也是他的隐蔽恋人。
半晌过后,周洲从地下室走了出来,带着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他问林书海是否读过这本书,林书海点点头说,非常喜欢,我还为这本书写过书评呢。周洲说,太羡慕你了,我已经没心读书了,或者说,我已经被各种烦琐事挖空了心。林书海说,你这是瓤我呢,你们当官才是正道,我们普通人就是混口饭吃。周洲说,你这才是讽刺人哩,对了,剩下这么多的书以后咋办啊?林书海说,能卖就卖了,卖不掉的我就拉回家,再不行就当垃圾处理了。周洲说,那你也很心疼吧。林书海说,我倒是没什么,这些书在很多人眼里连垃圾都不如。周洲没有再说话,而是坐在沙发上,翻读手中的书。
十二点半,他们在对面的饺子馆吃饭,要了半斤韭菜虾仁饺子、半斤猪肉茴香饺子、一盘素拼盘和两瓶干啤。吃饭期间,周洲突然说,哎,告诉你一个事情啊,我估计也快离婚了,我们已经分居三个月了。林书海没有说话,而是看着对方的神情。周洲又说,这次是我的不对,对玲花没感觉了,不知为啥,不想回那个家了,那里就是牢笼。林书海说,哎,都不容易啊,那娃以后咋办?周洲说,玲花要养,就让她养,我每个月给他们生活费,哎,活着有啥意思啊,活着活着,最后连心都没有了。林书海没有再说话,突然发现朋友眼中的星辰坠落了。他在他眼中看见了另外的自己。他总是在他身上瞥见自己的幻影。
吃完饭后,他们又在书店里拉了一些闲话。分别时,周洲再次叮嘱道,书店没了就没了,你可要好好地,心放宽,不要走极端啊。林书海说,你今天看起来有点古怪,是不是有啥话没有告诉我。周洲说,就是之前说的,如果你想上班,我帮你谋个职位,如果不想上班,我帮你找个新书店。他感谢了他,并且要把莫里森的书送给他。周洲摇了摇头,说,你也知道,出了你这个书店,我是不读书的,我们下次再约。
周洲离开后,林书海很快就写完了书评的剩下部分。交给编辑后,他坐在了沙发上,泡了一杯黄金芽。看着在水中舒展的茶叶,他沿着记忆的河流,回溯到了他们的大学时期,回溯到了第一次见到周洲的情景。
1998年的9月,林书海去师范大学中文系报到。有个手续需要交六十元的现金,而他恰好忘记带钱包。正当他准备返回宿舍取钱时,后面有个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这里有零钱啊,你先用上。他转过头,看了看这张陌生的脸,说,谢谢同学,可你不认识我啊。同学说,我是周洲,我们是舍友啊。这个名字突然间涌向了眼前,于是他点点头,从周洲那里借来六十元,现场交了手续费。等忙完所有的事情,他们一起走出了行政楼,绕着秋日的学校散步。那一天,他们说了很多的话,走了很多的路,也由此对学校的各个建筑有了最初印象。这是他来大学后认识的第一个人。让他意外的是,多少年后,周洲成了他大学时代的唯一朋友。
转完圈之后,他们一起回到了宿舍,也由此认识了另外四个舍友——来自广东的安迪、来自福建的胡凯、来自黑龙江的吉庆与来自宁夏的马晓涛。他和周洲来自本省,他是西安本地人,周洲是渭南人。和舍友们寒暄了几句后,宿舍陷入了可怖的沉默,之后便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他从书包里取出一本尼采的书捧着读。周洲喊了他的名字,说,你看我手里是什么书。他转过头,发现周洲拿着的是同一本书。也就是那个瞬间,林书海觉得自己遇见了真正的知己。以前上中学,他从来不敢和任何人提自己读尼采这件事情。父母也禁止他读这位哲学狂人的作品。他们交换读尼采的心得,好像也由此交换了彼此黑暗的心。
后来,周洲就拉着林书海一起加入了本校的文学社团。这个社团每周都有一个主题活动,或是文学讲座、或是读书会、或是创作竞赛、或是观影会。自从创社以来,中文系的领导就特别支持这个文学社团,不仅仅为其提供资金、场地以及人力方面的支持,而且为其办了一个名为《花冠》的文学月刊。尽管只是学校的内部刊物,但《花冠》在学校里拥有很高的知名度,据说师范大学每三个学生中,就有一个是《花冠》的忠实读者。能在上面发表作品,是他们这些文学爱好者的最初梦想。
11月末的某日午后,周洲回到了宿舍,对正在读里尔克诗集的他说,今晚咱们去外面吃火锅吧,我请客。他转头笑道,是不是有啥好事情要分享啊。周洲把书包放在桌子上,拉开拉链,取出了两本《花冠》杂志。他把其中的一本递给他,说,请你从这期杂志中找一找亮点。打开目录后,第一眼便看到了周洲的名字。林书海没有说话,而是直接翻到了这篇名为《夏之旅》的散文。他把这篇文章认真读了一遍,是一篇偶有佳句的旅行散文,记录了作者游玩南京城的所见所闻与所思。读完后,林书海说,祝贺你啊,周同学,文学事业迈出了如此重要的一步。周洲笑道,你可别瓤我了,就是瞎写呢,不过还领了一小笔稿费。林书海的脸上挂着笑容,但心里有点失落,毕竟他也给杂志投过三次稿子了,最终都是落了大海,没了回响。
第一学期很快就结束了,周洲邀请林书海去他的老家玩几天,顺便可以去渭河岸边散散步、谈谈心。林书海刚好也想借此机会出门逛逛,便接受了周洲的邀请。回家的前一天,他们去了学校的图书馆。周洲借了一本托马斯·曼的《魔山》,林书海借的是但丁的《神曲》。看见彼此所借之书之后,他们相视一笑,明白了彼此能成为朋友的真正原因。那个夜晚,林书海陷入但丁构造的地狱世界。他以前只在课本上读过这本书的概括,原本以为是距离自己非常遥远的宗教书籍,如今发现却是但丁的心灵史。但丁所遇到的人生困惑与他的人生困惑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差别。重新发现了但丁,就像重新发现了大海。当然,这本书里也有很多他并不熟悉的历史典故与宗教知识。那个夜晚,他梦见了但丁所看见的黑暗森林,也梦见了那三头野兽。在梦中,他与周洲交换了彼此的身份。
林书海在这个县城待了三天,获得了全新的生活体验。临走前,周洲把一袋椽头馍和一份八宝辣子交给了他,说,这是我妈带给你家的,是我们这里的特产,咱们寒假后再见。林书海上了车,回头和周洲说了再见。虽然只有三天,但林书海觉得自己的内心经历了某种平静的风暴,获得了某种微小的成长。车启动后,他看了看户外的零度风景,随后继续将目光放在手中的《神曲》上。在某个瞬间,他突然意识到但丁的世界与此刻的世界,其实是两个共存的平行世界。
自从周洲有了恋情后,林书海和他相处的时间也变短了。除了日常的课程,林书海将大量时间放在了图书馆,而文学借阅室和社科借阅室成了他的人间天堂。按照图书的序号,他一本接着一本翻,有的书看看简介即可,有的书则需要深入阅读。他会做读书笔记,甚至会为喜爱的书写简短的评论。只有与书相处时,他才能够获得深刻的平静。对于书的上瘾,让他想戒也戒不掉。阅读之外,他开始写日记,只不过是浮光掠影般的记录,却也是内心的真实图景。
5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他在阅览室读纪德的《田园交响曲》,抬眼时瞥见对面有人看着他。他迅速挪开了目光,半边脸燃起了火焰,心中的荒野着火了。他将书放进书包,起身离开了图书馆。图书馆外,他听见有人在背后呼喊他的名字。他转过身,看到了对面的那个女生,于是问道,你好啊,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呢。女生说,你的笔记本上写着你的名字和学院,我也是无意间瞥见的,对了,我也喜欢纪德的书,《窄门》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之后的情节像是很多浪漫小说那样,两个人因书结缘,成为书友,成为朋友,后来成了恋人。
女生名叫杨梅,也是西安人,是同年级的哲学系学生。杨梅也是一个书迷,只不过她并不想成为作家,而是想成为学者。成为恋人后,他们会交换彼此的读书笔记,而他也会把自己的文章拿给她去读。她成了他的第一个读者,也成了他唯一的评论者。大二下半学期,他把杨梅介绍给了周洲和陈舒,当天下午四人便去看了伯格曼的电影《假面》,晚上又一起吃了火锅。回到宿舍后,周洲问他和杨梅发展到了哪种地步。他说,就是牵牵手,也亲过她。周洲说,只有睡过了,才算是真恋人哦,书海君,请继续加油吧。他笑了笑,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打开了手中的黑色笔记本。不知为何,他感觉自己和周洲站在了同一个平台上,又有了更多的生活与艺术的交集。
大三上学期,他去学校对面的书店买了些专业参考书。在一家名为“是梦”的书店里,他很快便找到了所需要的书籍。他又在书店里转悠,打量着书架上的书籍。书店老板对他说,这个同学,你也可以去地下室看看,那里或许有你想要的书。书店老板指了指地下室的方向。他点头感谢了他,于是沿着阶梯一步步往下走,有种下地狱的错觉。地下室仿佛另外的世界,摆放着形形色色的旧书,其间可以闻到时间的尘味。他自认为读过很多书,却在这里迷了路。在书籍森林中,他发现了1990年版本的《神曲》,译者为朱维基,而之前在图书馆所借阅的是王维克的译本。他翻看了其中的前两页,是完全不同的阅读体验,便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本书。回到宿舍后,他把这本书放进了自己的抽屉,时不时会拿出来翻读两三页。他在这本书中发现了更为陌生却更为本真的自己。他没有把这个发现说给任何人。
自此之后,他每隔一些日子便去是梦书店淘书。有时候,他宁愿成为隐身人,因为那里是他的藏身之所。去的次数多了,和老板渐渐也熟络了,从浅到深,从少到多。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书,各种各样的书,多彩多样的思想。老板名叫夏河,五十多岁,以前是国企的车间工人,因为意外事故而导致肋部骨折,出院后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了,于是选择从工厂内退,拿到了一些经济补偿。后来因为各种机缘巧合,在师范大学对面的幸福堡开了这家旧书店,生意不温不火,却也基本上够日常生活的开销。夏河说,自从开了书店后,我才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以前算是白活了。林书海问他为何有这样的想法。他说,以前在工厂,就像机器一样,没有任何精神生活,还以为世界就像自己想的那么大。等熟了之后,林书海也会把心事选择性地讲给这位长者,而夏河的回答总能说进他的心坎。他没有把到是梦书店的事情告诉周洲和杨梅,因为那里是属于他一个人的秘密花园。
转眼间便到了毕业季节。周洲如愿地考上公务员,陈舒则去了南方的某个报业集团做社会新闻记者。他们两个和平分手,并相约做一生的好朋友。林书海通过了教师考试,即将成为西安市某重点中学的语文教师,杨梅则选择继续留在本校攻读哲学硕士学位,两个并没有说分手的事情,但彼此都明白已经不是同路人了。毕业前夕,他们四个人又去了那一家火锅店,吃了散伙饭。那天晚上,周洲喝了很多的酒,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最后林书海和陈舒把他扶回了宿舍。在学校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失眠了,往事像书页般在他眼前翻过,没有留下文字。他想到了第一次住学校的那个夜晚,也是失眠,也是惶恐,只不过心中还有些许期待。四年过去了,期待已经褪去色彩,迎接自己的将是未知的命运。半夜,他听到了周洲的梦话,梦话中出现了杨梅的名字。恍然间,他明白了很多事情,他哭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已经失去的日子。
毕业后,他去了明光中学做语文教师。父母也满意他的这份工作,毕竟是有编制的铁饭碗。他也为自己制定了比较详尽的人生规划——比如说工作之外保持阅读与写作的习惯;比如说寒假的时候去哈尔滨与海南岛,暑假的时候去台北与东京;再比如说去健身、去游泳、去爬山、去看灯塔,等等。然而,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自在,相反,大量与教学无关的事情拖着他、缠着他、磨着他、耗着他,甚至常常以噩梦的形式控制着他。夏至的晚上,他梦见自己死去了,梦见了活着的自己将死去的自己火葬,看见了升入天空的缕缕青烟,最后,活着的自己把骨灰撒进了大海。醒来后,他盯着户外的黑夜,仿佛看见了在海中溺水的自己。如此活着,常常让他有种溺水感。
在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崩溃后,他选择把自己的困境讲给父亲。听完后,父亲说,你这刚进入社会不久,再熬一熬就习惯了。他说,不想熬了,现在看见书,看见字,我就恶心。父亲说,你这就是太矫情了,要是你经历过我们那个时代,你就知道你有多幸运了。他说,你们有你们的痛,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这不是时代的问题,是每个人的问题。父亲说,你就是太脆弱了,多经历些社会的毒打是好事。他看着父亲陌生的脸,没有再说话,而是回到了房间,继续批改那看不到尽头的作业。将近十一点半的时候,他才完成了当天的工作。临睡前,他想翻一翻身边的闲书,却发现自己没有了任何阅读的兴致。关掉灯后,在黑暗中,他觉得自己的灵魂与肉身都被这日常烦琐的事情慢慢掏空了。他开始想念自己的大学生活,想念周洲和杨梅,却发现和他们已经失去了联系。无法入睡,于是打开台灯,敞开笔记本,想要在上面记录心事,却写不出一个字了。眼前的稿纸让他感到害怕,如同步入了黑茫茫的森林。他的心生病了,又找不到医治的方法。看着眼前的《神曲》,他突然想到了那个在旧书店梦游的人。
周末,他去了是梦书店,见到了夏河。自从林书海毕业后,他们有三年多都没有见面了,甚至连电话也没有打过。看到他后,夏河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握着他的手说,你这家伙,还以为你消失了呢。他说,再不见你,我就感觉自己快要死了。他给林书海泡了一杯茶,两个人之间并没有什么生分,开始聊起了各自的生活。夏河说,今年冬天,我就要离开这里去成都了,老两口要去那里帮忙看孙子了。林书海问,那这个书店咋办啊?夏河说,看能不能找到下家,要不就得把书全处理掉,太可惜了,这些书也都是我的命啊。林书海想了半晌,说,其实,我很想接手这个书店,就是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夏河说,这个书店每月盈利还可以,也自在,不看人脸色,就是要常守在这里,比较消耗人,不能和你铁饭碗相比。林书海说,我感觉自己被那里困住了,就像笼子里的鸟,再这样下去我会疯掉的。夏河说,这个你可要好好思索,和家里人好好谈谈,不是所有人都能吃上国家饭。之后,他们又闲谈了其他的事情。临走前,夏河送了他一套博尔赫斯全集,叮嘱他要好好读读这位阿根廷的文学大师。
读完博尔赫斯全集的那个夜晚,他终于可以写出属于自己的文章了,不是散文随笔,不是小说诗歌,而是辞职信。第二天,他把辞职信交给了校长。校长说,小林老师,你可是咱们学校的骨干教师啊,我非常看重你,你再好好想想,要慎重一点,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人辞过职。林书海说,感谢校长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这个决定,我已经想了很久了。校长摇了摇头,没有再说话,而是在辞职信上签了名。之后,他走了离职的正常手续,盖了好几个章子,与学校慢慢地剥清了所有关系。走出大门后,他转过头,给学校摇了摇手,说了声再见。
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之后,想象中的暴风雨并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可怕的平静。晚餐时,父亲突然开口道,哎,不管你做怎样的决定,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都会给你托着底。母亲说,如果我们都不理解你的话,怎么可能会让别人理解你呢。听完父母的话后,眼泪从脸上滚进了汤面里,他没有作声,而是闷头吃完了饭。
和计划中的一样,他从夏河手中接管了这家旧书店。维持旧书店的运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不过在夏河的指导下,他慢慢地掌握了其中的各个环节——如何选书、如何进书、如何摆书、如何售书等,所有的细节最终都化为生活的日常习惯。10月中旬,夏河正式离开了是梦书店。离开前夜,林书海请夏河去湘菜馆吃了晚饭,并相约以后要保持联系。
夏河离开后,他独自来打理这家书店,父母偶尔也会来帮忙照顾。在他二十八岁的时候,父母给他全款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并一再督促他结婚,而他总会找各种理由搪塞过去。毕业后,他先后谈过三次恋爱,最后的结果都是不了了之。所有问题都在自己身上——他对感情很容易就厌倦了,他对恋人缺乏持久的热情,他不懂得挽留,也不会哄人。更可怕的是,当恋人们离开之后,他没有遗憾,没有伤心,也没有愧疚,有的只是摆脱重负后的自由与自在。他觉得自己不适合恋爱,更不适合组建家庭。为了避免更多的伤害,后来的他,几乎不和异性发生微妙的情感纠葛。更可怕的是,他对于书的迷恋,远远超过对于人的迷恋。
有时候,他会睡在地下室,侧着身子看着眼前的书籍。他喜欢被群书环绕,有种踏踏实实的安全感。夜深之时,他甚至能听到从书籍内部发出来的声响。有个夜晚,他梦见周洲从山上跳了下去,以飞翔的姿态。梦醒后,他浑身盗汗,有种不祥的预兆。凌晨三点钟,他拨打了周洲很久之前留下的电话。对方并没有接,自己也只好作罢。清晨八点钟,他接到了周洲的电话:你这家伙,大半夜给我电话,是不是梦见我死了?他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周洲说,我之前也梦见过你死了,是从山上跳下去的,我当时也想给你打电话。他说,我也做了同样的梦,可能太久没有见面了,在彼此心里已经死了。周洲笑道,咱们都好好的,什么死不死的,我这周去西安,到时候一起吃火锅。
从这个梦开始,他更坚信周洲就是另外一个自己,过着自己的另外一种人生。后来读黑塞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突然觉得这本书就是关于他和周洲的另一种现实写照。第二天,他就把这本书寄给了周洲。
2009年春天的某个下午,他打开豆瓣网,收到一条私信,上面写道:林书海先生,您好,我是《青年文艺报》的编辑李曼童,读到了您写的关于库切小说《等待野蛮人》的评论,很喜欢,希望可以在本报刊发,并附有一定的稿费,是否同意,期待您的回复。林书海将这条私信反复读了五六遍,随后回复道:同意,感谢关注。之后,他打开自己的豆瓣读书的页面,发现这几年来已经标注了两千多本书,写过一百多篇书评,总计有五万三千多人的关注。他原本只想将这里作为自己的秘密花园,没想到却开出了可以供人观赏的花朵。无论是他人的赞许或是批评,他都会认真回复每一条网友的留言,这让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一座孤岛。他渴望成为海,而不是成为岛。
自从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后,又有其他编辑通过豆瓣陆陆续续找到了他。他的书评文字变成了报纸上的铅字,这让他有了某种微不足道的成就感。豆瓣上,关注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而他也珍惜每一次表达的机会。后来,他在几家报纸先后开了专栏,把自己喜欢的书籍通过文章传达给更多的人。除了书评,他有时候也会写点散文与诗歌,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与此同时,他也把旧书晒在了豆瓣上,会有网友通过网络来购买这些书籍。有时候,父母也会过来帮他搭把手,看着儿子的精神状况与经济收入都还不错,他们悬着的心才有了一丝丝安慰。
2014年,有个出版公司的编辑表示愿意帮他出一本书评集,问他是否有出版的意向。他很开心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并且与对方签署了出版合同,书名就定为《是梦》。过了一段时间,书便顺利出版了,虽然首印只有八千册,稿费也不多,但对于他而言,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也是生活的新路标。可能因为在豆瓣上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些书不到三个月就告罄了,随后又加印了三次。豆瓣上对这本书的评价也不错,有八点五分,出版社的编辑自然也很满意,表示愿意长期与他合作。他感觉自己打开了那道窄门,看见了新天新地。在经历了地狱和炼狱之后,他仿佛进入了天堂。他又重新读了《神曲》,并尽可能收集《神曲》的各个版本与中文译本。对于他而言,《神曲》就是自己的启示录。他已经写了足够多的书评,但仍旧找不到评论《神曲》的道路。
随着自己在书评圈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是梦书店的声名也跟着水涨船高,很多文学青年会慕名前来,借着买书的名义和他闲谈几句。在好几个中文系男生的身上,他看到了自己当年的模样。有几个常来书店的男生,最后也成了他的朋友。他偶尔也会想到夏河,想到曾经和他深谈的那些个午后。如果没有夏河,自己也许不会走上这条路。从某种意义上讲,夏河就是为自己领路、帮自己穿过地狱之旅的维吉尔。然而,他始终找不到给夏河打电话的理由。
2015年冬天的某个上午,面对着文档,他往上面敲打着文字,是一篇关于斯坦纳《语言与沉默》的书评。写到收尾处,他收到了一条来自夏河的短信,内心有点惊诧。短信上写道:家父夏河先生已于今年十月因病去世,感谢您曾经和他有过交往,人生海海,万事如烟,家父的这个手机号码将于近期注销,再次祝您生活顺遂。林书海不敢相信眼前的话,又反复读了好几遍,才确定这并不是梦。他回复了那条短信:感谢您,夏河先生,我们还会见面的,我也会照顾好是梦书店的。发完短信后,他重新面对着文档,而眼泪已经淹没了眼前的荒野。
又过了几日,雪停了,太阳从阴霾中探出了头,是梦书店的顾客也多了起来。手上的稿子完成了一大半,心情也舒畅了一大半。除了书店的生意,他白天大多数的时间都是用来阅读新到的著作。这里的每一本书,都是他严格意义上的朋友。他珍视与每一本书的情谊。这一天,是梦书店迎来一位独特的顾客。他从声音中听出了她,经过确认后,才喊出了她的名字,杨梅,你怎么来这里了?杨梅转过头,眼神中的疑惑瞬间消散了,笑道,原来是书海啊,这是你开的书店吗?我还以为你一直在中学教书呢。林书海说,早都不教书了,你这些年过得很好吧?杨梅点了点头,说,好着呢,这是我的老公王晨宇,我俩都在师大中文系教书,你媳妇也还好吧?林书海摇了摇头,苦笑道,我还没结婚的。短暂的沉默后,杨梅说,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么爱书,你给我们推荐几本书吧。他原本想把自己的书送给他们,然而转念又把话咽了下去,给他们推荐了几本外国小说。临走前,杨梅和他又交换了手机号码,并邀他下次去他们家吃饭。他点点头,明白那些都是客套话,因为他们早已经不是同一类人了,不可能会再见面了。在她丈夫的眼神中,他已经读出了那种想要掩饰的轻蔑。某个瞬间,他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不过,这样的自问转瞬即逝。他已经厌倦了没有意义的追问,只有真正的行动才能让他体会到深刻的快乐。
临近年关,他带着父母去海南岛过年。那是父母第一次见到大海,他们久久地站在海边,看着一艘轮船起航,慢慢地消融于天海尽头。父亲说,你也大了,我们也陪不了你几年了,我们还是希望你能找个陪你过后半生的人,哎,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母亲说,看着海,人变小了,心却变大了。随后,他们三个人在海边散步,唯有大海知道他们各自的心事。夜间,他听到了海的叹息。
这么多年过去了,是梦书店已经成了他的精神避难所。他在这里读过各种各样的书,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也做过多彩多姿的梦。在这个人间方舟上,他理解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也看清了意义的幻象。如今,幸福堡即将要消失了,书店也跟着要消失了,而他乘着海上虚舟,还没有找到未来的栖息地。然而,他已经不害怕时间了,也不害怕存在了,那些读过的书已经为他建造了坚不可摧的精神王国。
再过三天,他就要离开这个书店了。书店里的书基本上都处理完了,只剩下了最后的三四十本,其中的五本是不同版本的《神曲》。他把这五本《神曲》放进自己的包里,晚上带回了家,与其他三本《神曲》摆在了一起。他打开了笔记本电脑,打开了空白文档,面对眼前的盈盈绿光,再看看眼前的《神曲》。忽然间,他找到了通往这本巨著的道路。在写这篇评论的时候,他仿佛先后又经历了地狱、炼狱与天堂,在敲完最后一个字时,他看见了真正的荣光。写完文章后,已经到了午夜时分,他长时间地凝视窗外的黑暗,恍然间领悟到了生活的奥义,那是无言却又丰沛的永恒沉默。打开其中的一本《神曲》,他重新念出了最初的篇章——就在我们人生旅程的中途,我在一座昏暗的森林之中醒悟过来,因为我在里面迷失了正确的道路。那瞬间,他突然理解了但丁,也突然理解了自己。
他又去吃了老马家胡辣汤,马远航告诉他这是最后一次营业了,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林书海把自己的《是梦》从包里拿了出来,送给了他。马远航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道,你是我们这里好多年的老顾客了,没想到你居然是个作家。林书海说,不,算不上是作家,就是随意写的文章。马远航说,等我们找好新店了,到时候把地址发给你。林书海点了点头,随后便离开了这家店。他站在路口,看着眼前的废墟景象。幸福堡往日的繁华已经不在了,剩下的只是人走店亡后的荒凉。但他的心并不荒芜。要不了多久,这里将成为一片废墟,这里的故事将化为尘土,而我们所有人终将会被时间所掩埋。
最后一天,周洲来书店帮忙。林书海摘掉了书店的牌匾,摸了摸上面的四个字,是时间的触觉,也是梦的触觉。他对周洲说,做了这么多年的梦,也是时候醒过来了。周洲问,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呢?林书海说,好久之前编辑就向我约了书稿,现在我终于知道该写点什么了。周洲问道,写什么呢?林书海说,就写关于这个书店的故事。周洲点了点头,帮他打理好了书店剩下的事情。在关掉书店大门前,他又转过头来看了看这个空荡荡的空间,而他的心却被往事与未来共同填满。他不再害怕任何事情了,包括在梦中出现的那场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