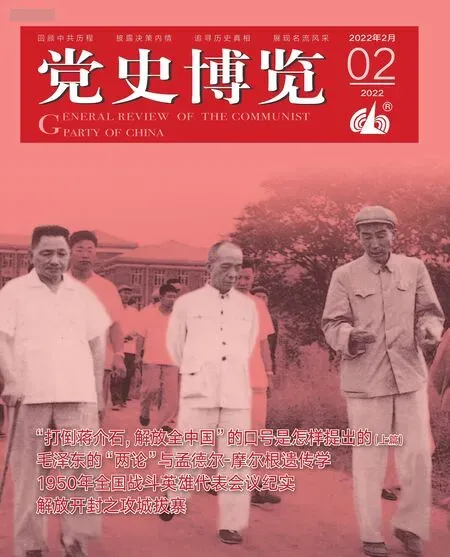博览之窗
毛泽东的“亲书政治”
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 《八一宣言》向全国发表,国共两党随后开始接触谈判。然而,谈判并不顺利,军事对垒仍在,国共通而未通。在此情形下,亲笔书信成为毛泽东沟通国民党政要和社会精英的重要手段之一。
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写的亲笔书信,应以1935年11月26日他致信董英斌为最早。董英斌当时在国民党东北军代理第57军军长,毛泽东给他修书一封,痛陈东北沦丧的历史教训,提出同对方商洽东北军、红军互不攻击等约定。同年12月5日,毛泽东了解到杨虎城与第17路军的情况后,又同彭德怀联名致信杨虎城。
自1935年末对统战对象展开亲书攻势后,毛泽东的相关书信活动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形成了一波高峰。红军东征胜利后,毛泽东于5月25日分别致信阎锡山及其晋绥军部将,晓以共同抗日之民族大义。8月13日,毛泽东又分别致信杜斌丞、杨虎城,敦促对方明确表态。
在敦促西北军负责人积极行动的同时,毛泽东于8月14日一天写了7封信,分别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易礼容。其中,韩、张、刘、傅及宋哲元,皆为国民党当局镇守一方的军政首脑,毛泽东审时度势,尽可能寻觅抗战的同道中人。
(高云摘自 《上观新闻》2020年4月7日,吴海勇文)
中共二大是如何弥补一大“纲领”缺陷的
中共一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与其后历次代表大会所形成的纲领性文件相比,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因为中共一大仅仅完成了建立一个 “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的任务,具体到中国的国情、实际的阶级状况和中国革命的阶段性目标及其政策策略等重要决策,都没有提到。
为什么中共一大解决不了,一年后中共二大就基本解决了联系中国实际这个问题呢?
据胡乔木在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所言,是得益于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共产国际开始在远东具体着手实施列宁主导的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决议”提出的政策主张,是在它发起反对华盛顿太平洋会议运动之后。
通过举办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亲自出面接见国共两党赴会代表,通过酝酿制定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直至下达指令并派代表召集中共领导人加以说服等办法,共产国际一步步说服了中共党内反对的力量,将原本幻想一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早期共产党人,推上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群众性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第一线。
(东方摘自 《史林》2021年第1期,杨奎松文)
中共领导建设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思想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努力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依据经济规律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党的经济发展思想非常丰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明确了新阶段发展任务是根据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解决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对发展理念的分析,明确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对现代化的分析,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及各个领域现代化的内容;对二元结构的分析,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问题,尤其是继消除农民绝对贫困现象后明确了“三农”现代化问题;对经济发展调节机制的分析,明确了推动经济增长并有效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调节机制;对发展格局的分析,从畅通国民经济内循环和外循环的角度明确了我国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这几个方面发展思想是共产党人的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中国成功的发展实践所证实。
(麦农摘自 《管理世界》2021年第4期,洪银兴文)
我国边防武装体制的五次调整和改革
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的边防武装体制经历了五次大的调整和改革。
第一次,1949年1月至1951年12月,是解放军与公安分段防管时期。1951年6月15日,北京第一次边防工作会议决定,与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国家接壤的边疆和远海地区,边防武装警卫任务主要由国防军担任,与社会主义国家接壤的中苏、中朝、中越边防任务由武装警察防管控制。
第二次,1951年12月至1958年7月,是公安防管时期。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全国内卫、边防和地方公安部队于1951年12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1955年7月,国防部将公安部队机关改为公安局,担负国境警卫、边防检查、海上巡逻、边防侦察等任务。1957年9月1日,中央军委撤销公安军番号,总参警备部负责对边防部队的业务指导。这一防管体制一直坚持到1958年7月。
第三次,1958年7月至1966年5月,是公安与解放军分段防管的时期。1958年7月,中央决定除中印、中缅边境外,其余边境的任务由公安部分管,中印、中缅边境仍由军队管辖。1963年12月,中央决定把中苏、中蒙边境地区边防任务移交人民解放军防管,次年将福建公安部队移交福建省军区领导,中朝、中印边境边防任务仍由公安部负责。西藏、海南、新疆由人民解放军防管。
第四次,1966年5月至1973年4月,是解放军防管边防的时期。1966年5月,中央决定撤销公安部队,边防任务完全交解放军担任。1969年将边防站体制改为战斗体制。
第五次,1973年4月至改革开放前,是公安跟解放军分工分管的时期。1973年4月5日,全国陆地边防工作会议决定,边境警戒巡逻执勤任务由解放军负责,边防口岸、雷达站、检疫检验由地方和公安负责。
新中国建立的人民边防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自主的人民边防体制。
(深山摘自 《军事历史》2019年第5期,郑汕文)
任弼时长女任远志回忆与父亲的第一次相见
任弼时长女任远志曾深情回忆自己15岁时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情景。她记得那天是1946年7月11日。当天,任弼时去接从新疆监狱里出来的同志,只有陈琮英一个人来接从湖南老家来延安的女儿。在回去的路上,有一辆吉普车开了过来,母亲指着从车上下来的人对远志说: “你快去,那就是你爸爸,你快去叫他吧。”
远志激动地使劲跑,跑过去很高兴地看着爸爸。任弼时在女儿脸上亲了一下,用手抚摸着远志的头说: “大女儿,你回来了。”
“父亲把我抱上车,车上坐满了人,印象中有三排座,前面坐着朱老总和康克清妈妈,中间坐着父母和我,杨尚昆夫妇坐在后面。我一直盯着父亲看,鼓起勇气突然喊出 ‘爹爹’时,父亲却看也不看我,坐在一旁的朱老总倒爽朗地答应了。我鼓着嘴问: ‘你不是我爹爹,你怎么答应?’当时,满车的人都乐了。那时延安的小孩子都把朱老总叫 ‘爹爹’。”
“我就是叫不出爸爸来,我就搂着爸爸。我就流眼泪了,这是一种幸福的眼泪。我心里在想,这下我不是孤儿了,我也有爸爸,也有妈妈了。”
(冬阳摘自 《同舟共进》2021年第6期,周海滨文)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呈现出从援助到互助再到共融发展的良好态势,这归功于国家、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合力。
民族地区的巡回医疗工作,根据工作重心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49年至1964年,侧重疫病防控与妇幼保健;第二个阶段为1965年至20世纪70年代,旨在缩小城乡差距;第三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重点照顾 “老少边穷”地区。
对口支援是发展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举措。根据受援方的不同,医疗对口支援大致可分为两类,即城乡医疗对口支援和区域医疗对口支援。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是促进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以及解决城乡、区域不平衡问题的重要助力。
民族医药凝聚了各民族的医药知识和疾病应对智慧,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地区医疗卫生领域的独特优势。民族地区的传统医药在临床和产业化方面的优势则在健康中国的战略背景下转化为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并惠及全国甚至全人类。这种合力不仅最终促成了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取得的成就,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和生动体现。
(雅志摘自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方静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