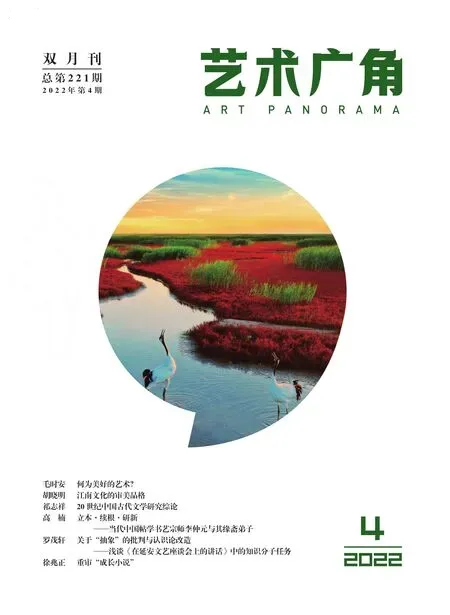立本·续根·研新
——当代中国帖学书艺宗师李仲元与其缘斋弟子
高 楠
几十年来为不少不同门类的艺术家写评论,写鉴赏文章,题序作跋,进行成果评审,授予证书,那是我的工作。但我从未对谁用过“宗师”这个尊号。“宗师”不是职称、不是职业、不是工资级别、不是官职,但它又很是珍贵,是一棵大树,一块丰碑,一个很高的行业标志。“宗师”是一个实至名归的尊称。称李仲元为帖学书艺宗师,当然首先是指他的从艺门类——书法艺术,然后便是对他的书体类分——不是碑艺而是帖艺。帖艺与碑艺之别,是承清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帖学与碑学二分而来,李仲元专攻帖书,又在中国书坛创一家之体,立一门之宗。不过,这里还须强调的是,当下是呼唤“宗师”的时代,也是推出“宗师”的时代。由于各种书人争相登场,商人书法、名人书法、官人书法、闲人书法,一时间书坛混杂,故需要有真正的书法大家来弘扬书界正气,明道度法。以上诸点,本文当展开阐发。
一、开帖艺新宗的精魂起舞
把“精魂起舞”列为本节题目,是由《李仲元自书诗卷》开卷诗的诗句“我诗,心灵之歌也,我书,精魂之舞也。歌世事悲欢之情;舞人生百味之畅”[1]而定。尽管本文不对李仲元诗作进行鉴赏评析,而只是在谈及他书法情韵与笔墨的关系时有所关涉,但“人生百味”“精魂之舞”的说法,正可看作是对李仲元及其弟子书法艺术的点睛之笔。
笔、墨、体、格、韵,这是书艺构成的五个要素,也是最见古代书艺传统的五个方面。中国书艺在这五个要素的综合作用中,道张法明,新风代生。鉴赏与研究李仲元宗师书法,绕不过这五个要素。
李仲元字重缘,号漫叟,室号缘斋,近望九之年,精神矍铄,学气浩然。他学书习字师从其父李文信及魏书行楷立门大师沈延毅。书香门第的濡染,文物考古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使他得天独厚又势在必然地成为自成宗门专攻帖学的书艺大家。
先看“笔”。“笔”即用笔或运笔,包括运笔的方式、笔锋的藏露流转、落笔的轻重断续,以及行笔的疾缓收放等。汉字笔画,横、竖、撇、捺、点、折、弯、钩,处处用笔,处处见笔,而且笔笔有宗,笔笔求法,功夫根底,均挫于笔端。李仲元深究笔法,已炉火纯青,一点一横,一撇一捺,信笔写来,法度规矩尽见其中。他用笔有模铸之妙,模铸,即同一笔划在不同处不同字上写来,基本没有二致,像用模子铸出一般。在此基础上,求笔体墨韵的变化,或笔走龙蛇,或结句布局,就有了万千气象。他的用笔更着重于笔力变化,在轻重舒缓之间追求一种挫顿勾连的运作效果。为此,他在笔锋处理上虽以中锋为运作基形,但又不囿于中锋,而是随力而运,当露锋则露锋,当侧援则侧援。这种发之于力感之以心的笔触运作在他已达到随意而化的程度。如他“石冢神壇屹,大荒猪龙头”这句自书诗,“壇”“屹”的点撇均不藏锋,未见顿挫,轻处落笔,力发于自然,为后面“猪龙”两字的藏锋顿挫预留了后力。李仲元重视用笔,苦练用笔,所以才有自如的笔下功夫。他的四首“戒徒诗”第一首诗的第一句便是“笔不停匀气不华,何来如此大书家”,把运笔停匀的力度变化及心思感应作为书家之首要。书论说的“印泥”“画沙”,就专讲笔锋笔力的处理,李仲元已运用得游刃有余。
次看“墨”。笔无墨不行,用墨的讲究既在于纸,更在于浓淡燥润之分,至于唐代尚有很多禁忌。宋代姜夔《续书谱》的用墨主张,倒是更得书法发展的要领,即浓淡燥润当因体因势而用。李仲元的用墨便极注重合于体势,总体上,即因势而运。就体势说,因他的字体追求方整端和、上下匀平,其势又常求飘逸神骏,古质今研,因此给人一种心正气和,息虑凝神的感受。所以,他的墨法常执于浓淡相间、干湿润和之境,由此写出字来便端庄娴雅、流畅自如,不飘、不滑、不笨、不滞。但也不时会有墨不尽饱、笔不尽开的细毫焦墨,用以勾连转折。苏轼曾以“光”“黑”论墨,“黑”不必多说,“光”即墨的滋润明朗,是水墨相融的适中状态,他称之为“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儿目睛”(苏轼《书怀民所遗墨》),这就又涉及总体的运势了。苏轼这个比喻正可用来体味李仲元的墨趣,即墨润圆柔,因势而化。观当下书法,很多书家却不谙书艺须精熟营造墨境、墨趣的道理,加之古人研墨以求浓淡的习惯早已为墨汁加水所取代,粗放率意难免,因此常见墨气衰败或者余墨溢出的败笔。书乱于调墨不合,用墨无法,已成时下书界时弊。李仲元墨润圆柔因势而化的境界,有匡正时弊之功。
又次看“体”。“体”即见于书法的文字形式,这是汉字元素搭配组合的视觉样式。笔墨有常法,字体无常定,有多少书写者就有多少字体。不过,书法作为以汉字字型为书写对象的艺术,总需要有表现价值与观赏价值,这类价值是具有一定普遍性或共识性的价值,亦即价值标准,它体现为不同时代的代表性书体。如东汉蔡邕、钟繇、卫铄,魏晋王羲之、王献之,唐代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宋代苏轼、张怀瓘等。后来者临习模仿这些代表性书体,就有了诸种书体的延续与创新。当下书界见于书体的乱象即立体失端、创体无准、构体缺范、变体乏由,却又都打着书艺旗号,致使不同程度的丑书横行。在这样的书艺语境中理解与观赏李仲元对于书体的苦心修炼,对于书体代表性范式的深入玩味与体察,进而在传统范式的传承中自立一体,便知这乃是中国书艺在书体乱象中的大胆承担与努力。李仲元临池八十载,专攻帖艺,临习多体,犹以二王、褚遂良、米芾、董其昌为要。李仲元书体形态总体看左侧微轻右侧略重,能见出米芾真书的痕迹,字体轻微左倾,字形右侧时有笔画张出,或勾或撇、或点或捺,因重心适中,便生出一种总体构架自行扶正的倾向,由此便又有了唐虞世南所谓“达性通变,其常不主”的表意灵活性,以及弯弓未发的力度。这里既能见出晋王羲之书体的灵活跌宕,又能感受到褚遂良运笔构形的精致。李仲元很多字对右侧张出的笔触,进行简约处理,捺而不展波折,点而反向拉回,直弯钩变形为曲弯钩、竖弯钩撇笔探压复又折返等,在这类堪称特征的笔触处理中看到的是基于传统的创新。他的《自书诗·佛手柑》中,崴、拔、囊、限、我,戒、最、迎、春、水等字体安排,都很充分地见出这种体势独到的张回折返的势头与力度。
再次看“格”。格即书体排列的格式、格局,又称章法。它赋予书艺以书体连接成篇的形式整体性。书法格局的形式整体性是见于纸上的空间摆布,格局的空间摆布因体、因势、因人而异,这基于书者的形式感。这形式感涉及字体大小相间的安排,字间疏密的摆放,结字横竖的关联,徐缓节律的铺设等。虽然自古以来对于格的空间摆布有多种说法,但总体而言则可概括为以化为功,因势求变。化与势普遍追求的展示境界便是浑然一体。唐张怀瓘《书议》曾专门谈到化与势相互作用的相反相成:“固其发迹多端、触变成态,或分锋各让,或合势交侵,亦犹五常之与五行,虽相克而相生,亦相反而相成”[2],这是传统格局论的精要之见,梁启超则称之为“计白当墨”。以此观赏李仲元书艺格局,不失其正。这种格局既显褚遂良书艺的精致秀雅,又见董其昌格局的天真平淡。以李仲元所书唐代王维《酬张少府》诗为例,其空间布局横平竖直,字体间距匀称齐整,字型大小统一,字与字之间此呼彼应,上引下连。首行“晚年唯好静”,“晚”“静”二字稍大,与中间三字形成微妙的节律变化,又与下两行“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形成提领统带关系;第二行“万”“自”两字与第一行“晚”“静”两字偏大相对比又写得偏小,中间“关心”两字则刻意放大,字行结构顿然活脱起来;其中“长策”“旧林”“解带”“穷通理”“入浦深”等字,在格局处理上,注重间架勾合,以细笔就墨穿针引线,又以撇顿捺折上下接应,通篇看去,娟秀而不失其刚,藕断而内有丝连。以此对比当下一些书法作品在格局处理上的粗糙、率性、缺法、失准,错以为字的大小疏密、间架勾连,不过是随意涂抹,这从书论角度说,便是空间感的混乱,形式感的溃散。
最后说“韵”。“韵”即意趣情调,它在笔墨体格之外,但又因笔墨体格而见,是由笔墨体格向外的生发、向外的舒展、向外的溢出。它常常展现于不经意间,类似于扑面的微风、浮动的云气,因此韵又常与风、气连用,以风、气为喻。韵在书艺中的生成及外溢,与书家对于书艺的理解,对于人生社会的感悟,对于宇宙沧桑变化的深思相关,所以唐张璪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明董其昌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些书艺之外的功夫,倒正成为书艺中韵的生发之由。李仲元书艺在韵上已入高格。安然祥和、娴雅凝重是他的书韵主调。“安然”,即不沉不浮,不疾不徐,不刻意不雕饰,胸有成竹,笔墨自如。这分安然,来于他的饱读诗书、人生百味,确已抵达精魂起舞的境界。“祥和”,是他通过书艺传达的人生态度,他融会贯通于书艺传统,走着一条古质与今研相中和的创新之路。他长于把各种棱角冲突,包括生活中的棱角突出,在深广的襟怀中求得释解与通和。他说:“我写了80年毛笔字,也就是从古人那里汲取营养,一根一根骨骼都取于古人,是综合了多种古人所奔发,所用过的风格。我的书法风格是传统的延续与创新。”“娴雅”,关联着他的品格,简朴为生、勤勉为活、谦和为度。他的平生要事,考古、研典、写文、教书,都是至于静而向于内的经历。这是他运书艺于娴雅的底蕴。“凝重”,得于他的为业与待人。他说“作书写字,主要是作人,作高尚之人,谦谦君子,不用博取功利的手段,否则就会陷入平庸”。“凝重”在美学中属于与优美相对的“崇高”范畴,对人而言则是阳刚之气与负重举物的力量。这正与“娴雅”相左而且互补。他把“凝重”和“娴雅”在书艺中统和起来,并且作为独有的韵味生发于他的书艺作品中。以他自书诗卷《年荷戟人》的“边尘肃靖笑,封刀观海高”为例,这诗句本身就极富阳刚之气,在字体与格局安排上,能体味到他昂然于胸的豪气。前一句笔触右侧上扬,“肃”“笑”“封”“刀”方头顿笔,中锋运行,甚至能感受到魏碑书势的力度。“肃”字左张右收,与其下“靖”字的左收右张正相交互,相挫相展的力量油然生出。竖行结字,在李仲元书格中出现不多见的向右偏斜,产生出《晋书·王羲之传》所说“势如斜而反直”的弓力反弹效果,“高”字以强力的硬钩转折为勾连,更生发出一种内在的张力。两句诗书所演绎出的颉顽之力的组合,综合地生发出一种凝重的力量感受。循字体人,李仲元书作的“凝重”力度,又与他曾经的军旅生涯密切相关。他的弟子们谈到对于老师的一个共识性的感受,即他至老不渝的军旅情怀。他的弟子滕达专门写了一篇《读解李仲元先生诗中之军旅情怀》的文章,文中写道:“1949年9月,他16岁就瞒着家人毅然报名参军。军营是他人生的第一站,部队这个大学校、大熔炉,把一个懵懂的青少年培养成一名战士。”青少年的经验是人生的底色经验,在这样的经验底色中,酝酿了李仲元书艺的“凝重”韵味。
上述五个要点皆以李仲元对于书艺传统的接受与创新为脉络,一方面是要通过这个脉络来体味他书艺深厚的优秀传统根基,一方面则是从他对这五个要点的创新实践,看其书艺的宗师价值。贯穿始终的则是他的明道与度法。
二、志在凌云的缘门弟子规
写书与教书是李仲元几十年如一日的乐业与要业,他引领弟子们徜徉于书艺的历史长廊,并开拓出春意盎然的书艺天地。他在《戒吾徒诗四首》的第二首中写道:“一艺凌云史有声,妍媸清浊许人评。诗书雅韵谁轻取,未必争名便有名。”这是一首励志、劝学、立人的诗,表达着李仲元对弟子的凌云厚望及闻评取诚淡化名利的教诲。李仲元执教甚严,有亲传弟子数十人,最早的弟子收于20世纪70年代末,年龄最大的已过古稀。这里说的亲传不是通常书法班的那种收费讲课,课结人散,而是真正地登堂入室,赐以学名,排以序位,待若骨肉,并授艺树人。他经常把弟子们召集起来,评书论艺,谈古今书势,叙眼下当为。他又常常亲临弟子书室,检查作业、指点迷津,演示教正。几乎每一位弟子的书法都留有他的朱笔圈点,题跋作序,弟子们则把他的圈点指评精心收藏,奉为珍宝。这里氤氲着一种温存的情感,洋溢着一种家庭的氛围,同时又富有彼此切磋的交流互尊。这也是李仲元宗师尊称的名实互映,书而不教,教而无宗者,充其量书者而已,何谈宗师。最令缘门弟子振奋的,当数李仲元率弟子们举办的师生书法作品展,这样的书展2015年10月在辽宁美术馆举办过一次,2021年10月在辽宁美术馆又举办一次。最近这次书展由省市两级书协联合主办,展时5天,规模庄严宏阔,书艺界群贤毕至,书法爱好者络绎不绝,大家都是厚望而来,盛赞而归。各种媒体采访报道助势,使这次书展成为多年少见的省内艺术盛会,这在疫情尚行的情况下几乎可以用难以想象来形容。对这次盛会,李仲元率缘斋弟子发信感谢,更使参展、办展、观展过程以进一步的互动而圆满结束。李仲元在感谢信中说:“展望五天来,展厅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可谓‘云屏诗笔会文邻,致美堂中浩荡春。辛丑秋寒逢雅会,登门俱是艺中人’。”这类联展活动所以令缘门弟子们振奋,不仅是因为大家有了与老师共展书艺的机会,更因为这是缘门群体的一次身份与门风展示。在书艺标准混乱,书法良莠难辨,执笔弄墨商业化的风潮中,如此一个志在凌云、技在传承、艺在高格的师生群体的凝聚突显,自然生出一种标志的力量,它标志出书艺正道,标志出中国书艺阔行于正道的代际传承,也标志出对中国厚重的书艺传承正在守持而且必须守持的那份敬畏之心。这是一种历史责任感的体现。
经过李仲元的悉心指点与传授,他的很多弟子均已达到功成艺就,可以出得“山门”,独闯书艺“江湖”的境界。缘斋弟子书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弟子是对李仲元书艺进行传承研究与实践,潜心模仿李仲元风格与韵味。如佡俊岩,他精习李仲元书,其书形构架已然酷似,加上所事文化工作与其师相近,更多了人生经历的相通,这使他的书法在神韵上也与其师多有相和。其实,佡俊岩习师多年,自然也习得了老师传承且又创新的书法意识,他在精研仲元书体的过程中,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的笔画有自己的宽放,撇捺折点多作舒放圆合处理,在书体上左收右紧,更有自己的严谨。如他所书苏轼《水调歌头》[3],笔势酣畅、高山流水、顺笔运墨,自起波澜,把东坡诗境生动地演绎出来。2021年师生书展,见到他清新雅秀的隶书《苏轼望江南》[4],确然已入上品。白光,1996年师从李仲元,随师习帖二王、褚遂良,对老师书体潜心因袭,已近形神兼备。后遵师嘱经过一段刻苦的创新努力,李仲元评价说,“这个弟子已有所超越。”白光书艺笔法温和流畅,飘逸融通,先后习魏晋、董其昌,行书以魏晋为脉,也见董其昌痕迹,点划间又柔化了得于李仲元书格的“藕断丝连”,书体疏密变化婉转自如。他的书作有以大统小的总体特征,起笔落字不拘于体而发于势,势是笔墨游走的动感,将这种动感融贯到书体中,依势而运,字划的粗细变化便自然流畅,点折收笔又就势带回,格局排列求整饬又有整饬中的变化。
第二类弟子是曾直接研习另外的书法,别有所师。这类弟子不仅在字的笔墨字体格韵上与李仲元有很大不同,而且在气质风格上也多有所异。他收这样的弟子,如他所说,“旨在师生切磋,或对弟子有纤毫之教,也是益事”。李放,先是师从碑书大家孙德州,孙德州则师从东北书界名声鼎然的碑书大师张绪晶。李放遵师嘱写《龙门二十品·始平公造像》,对碑帖已抵通道律法的品级,恩师辞世后投入缘门。他坚持碑帖根底,汲取李仲元帖艺华彩,根据这种风格转型的需要,他又苦练“总百家之体,极众体之妙”的赵孟頫,这是一个融会贯通的过程。张广茂,书画兼功,凝画入书,以书味画,这是他书体风格富于个性的由来。书法方面他取范王羲之,又习清代王铎,并在格韵上汇通李仲元。他书体端庄秀雅,撇捺舒展,横竖粗细转换自然。沈广杰,常年从事书画鉴定及美术史研究,著有《辽宁书画史》专著,他在工作中需要模拟古人的各种体式,这既为他的才艺发挥提供了接送腾挪的广阔天地,又是他的工作为他才艺带来的得天独厚,诸体皆通,诸体皆华,是他突出的书艺特点,他把王铎与米芾相融通,使草书与楷书相渗透,以小篆笔法写大篆,畅汇百家,笔墨腾挪。
第三类弟子是直接学古人书法,深入其中,苦练不辍,情不能拔,师从李仲元,取其才思气韵,于精细微妙处求其画龙点睛式的指导。李仲元对这类学生,信其底蕴、扬其功力、顺势行教、予以赞励。这类弟子最具特点的当属刘秀兰,李仲元评价她“巾帼不让须眉,写《书谱》入化”。她曾习书于书法大家徐炽,又师承仲元,李仲元赞她“精书《书谱》”,这《书谱》即唐孙过庭亲笔用草体抄出自己著作《书谱序》,这是一篇专谈书法见解的精辟之作,由于墨迹得以流传至今,成为此后历代学习草书的范本,孙过庭是强调书法情韵的第一人。刘秀兰专习孙过庭《书谱》,李仲元赞她“写《书谱》入化”。
由李仲元的三类弟子,可见缘门师生彼此研讨交往的情怀,师父承教的严谨,弟子从师的怡乐,也可见李仲元海纳百川的襟怀以及他的“传学”“做人”“从文”弟子规“三要”,此“三要”已然在缘斋弟子的书艺中凝练为众弟子共显的精华。
三、振发书艺的苦求与追索
缘斋弟子的“三要”弟子规,决定了这是一个富于德性的群体,一个在中国书艺领域敢于担当的群体,一个励志于书艺创新的群体,也是一个因此而必然要苦求与追索的群体。李仲元谈到他成就斐然的弟子们很是动情地说:“他们很不容易,书法不能养家糊口,用平生精力专务此业,卖不上钱。很多弟子实际都是业余之为,业余之为又要抵于专业甚至上乘专业水平,靠的是业余时间手不离笔的朝夕努力。”这番言谈,充满师长对于弟子的心疼与关爱,这应该也是李仲元在早已功成名就的情势下,仍要携缘斋弟子互勉前行的动力因由。缘门师生的苦求与追索,已涉入书艺理论的深层问题。
1.书艺美丑之争
很多书界人士都面对一个共识性的现实,即丑书盛行。这与书法各级体制内一些有影响人物的书法导向相关。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又利用很多书法爱好者不谙书艺传统的文化欠缺,别出心裁地制造出一些书法体式、书法格局,其中以此而避功底之浅薄、以短博名的人当然也有之。
这又有两种情况,但这两种情况均为不当,这不当是说它们不合于当下中国书艺基于传统的创新发展大势。第一种情况是行丑书者确有一定的书法根底,但要另外地开宗立门,险处取胜,以求一展。这种情况在中国书艺史上其实并不少见。唐代,被历代书家称为自后汉书艺觉醒后的立法阶段,立法,即立书艺的规矩与标准,有了立法,各种别开生面的破法也便随之而来,于是,一些破既有之法书作便被当时的书界称为“丑书”。对此诚如熊秉明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所说:“唐以前的书在寻找规律;到了唐,规律被确定了,典型的作品完成了,唐以后的书家一方面学习唐法,一方面力求摆脱唐法,反叛唐法。”[5]唐韩愈、颜真卿,宋米芾,明董其昌等,都曾被以丑论之。而这类被称为丑书的书家,其实原本又都是标准中人,其笔墨体格韵均具有承之于古的深厚根基,但基于历史赋予的时代感受,又使他们不甘受这一根基束缚,于是便突破既有标准,刻求书艺创新。这也是那些被称为丑书的书家,此后很快就因其深厚的书艺功底被追随为书艺名家的原因。书法的美丑之争在古代是时代递进的一个标志。但当下中国书艺状况却不同于古,当下中国书艺因20世纪两次大规模的批判传统,又经大众文化及商业化的转型,便出现了一个由小众化向世俗风雅的大众趣味转化的情况,在这样的转化中,既有的书艺标准便陷入混乱,大量书艺爱好者在失序无准中茫然习书。按照书艺的历史发展来说,有准时须破准创新,无准时须立准抱一,不图抱一立准,另谋怪异,这时的丑书便成为无准时的乱上加乱。因此,在这种书势下,丑书肆虐,弊端大矣。这理所当然地会引发守传统之正、创时代之新的缘斋师生的愤然及急欲纠正的冲动。特别是乱上作乱的丑书肆虐,居然在相当程度上与不同级位的体制引导与体制放纵相关联,由此而发的美丑之争,便不仅是美学理论问题,更是我国书艺拨乱反正的历史实践与社会实践问题。丑书两种情况中的第二种情况,当属那些没有书艺根底,但又要装腔作势、虚张声势的人们,这类书者原本也写不出好书,只能以丑示之。其实这样的书,很难称为书,只是写字而已,并非提起毛笔,沾墨写出来的就是书法,充其量这种情况的书法也只能称之为劣书,丑书是谓高抬了。
2.立人立书之辨
立人立书对于缘斋师生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关涉书艺时弊的大问题。缘斋弟子规“传学”“做人”“从文”这三个要点,正是就立人立书而言。立人即务学与树德,这在我国古代既属于知识论又属于道德论,可以溯根于孔孟儒学与宋明理学。而书法则既属于传统文化领域,又属于传统艺术领域,按理说不同领域有不同范式不同尺度,难得一统。但在我国古代二者却天然融合,并无二致,这就是所谓的伦理一元。李仲元把学、人、文三点一线地立于缘斋根基,正是将之把握为一体,并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传教实践。毋庸赘言,书艺的传统属性,决定了它必是随古之道的艺术,也必是归于仁合于德的艺术,承道即合德,立人已在其中。据此推来,它又必须是勤学苦练的艺术,靠急功近利的取巧绝无所成。李仲元已功成名就,视力又不好,仲元体所以有如此起笔布局的体势,如他弟子所说与其眼疾有关,起笔先须找纸,纸既有定,笔墨已起。即使如此,他仍天天临帖作书,励志图新。他的弟子们也都是多年临池劳习苦练,因此才有如此骄人业绩。此外,书艺又是“中和”之艺,“中和”的过程,是平易谦恭的交往过程,这里有“君子”之仪,文质彬彬,不卑不亢,虚怀若谷。前面谈到缘斋师生的关系及缘斋师生对同仁同艺的关系,就是取一个“和”字,和诚为要。再有,就是那承于古、苦于学的书艺,必是游于“艺”且乐于“艺”的,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人生境界。缘斋师生是这个境界的承领者,他们苦在其中又乐在其中。立道、苦学、诚交、游艺,这八个字非立人而无得,非书艺而不现。人书之辨,结于一统,缘斋门风因此而立,缘斋书艺因此而荣。
3.续统研新之思
既然书艺是传统的并且不断地生发于传统,因此从根本说,不续统则无书艺。李仲元灯下闻鸡,临帖不辍,求的就是续统。他的弟子们虽然风采各异,艺境多殊,但又都是殊途同归于续统,也正是在各自的续统中,他们各自精道地处理书艺传统与仲元书艺的融合关系,致使缘斋师生以其风清气洁的作品而彰显书坛。但传统的贵重在于传统,传统的难续也在于传统。传统愈是贵重强大,便愈具有封闭倾向,万绪皆备,万技已功。历史上不少繁极一时的艺术形态及艺术技能,在这道不见痕迹的围墙中一步步地走向衰亡。但就传统的现实状况说,它又具有敞开性。传统既然是历史向现实的延续,是历史的当下化,而现实又是充满活力的,几乎每时每刻都千变万化,抓住现实之变化,并在现实变化中承续传统,转化传统,这又成为续承传统的必然取向。李仲元与其缘门弟子,对此有所深悟。他们每个人都不断地做着自我突破的努力,而他们的自我突破,又不仅是技能技法性的,更是社会实践的交往性的、书法艺术的取向性的,师生之间的切磋性的。因此,他们才能做到续统而不泥于统,研新又不硬折新。已举办的两次缘斋师生艺术展,所以给人以深厚但又清新的印象,就在于李仲元和弟子们的续统与研新之思已凝炼于他们的书艺之作。
4.大艺小艺之论
书艺是我国传统之大艺,也是国宝级的大艺,不然它不会如此源远流长,令人敬畏。上至历代帝王将相,下至各朝文人骚客,尽管成果有异,品第不同,但小觑此艺者几乎没有,甚至有人喻之为“经国大业”。古往今来,真正在书艺上有所成就者,几乎均注重与痴迷于书艺之大。不过,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艺术多出,琴、棋、书、画,礼、乐、书、诗、易、春秋,无处不艺。就此来说,书艺是众艺之一种,众艺为大,书艺就是门类艺术,是小艺了。书艺的大艺与小艺,是辩证关系,因时因地因人而不时变化。如何处理书艺的大小关系,又回到立人树德的大事上来。其实书艺大小之论,本身乃是人品、艺术的关系之论,这也是李仲元与其弟子们不断遇到并不断理论的一个问题。李仲元不断告诫弟子要谨慎为书,要低调为人,这就是要求要摆正书艺大小的关系,不可自大。而李仲元弟子在讨论中提到一种情况,既曾有某位书家责问请他写字的人,不是三五万元一刀的纸,能写字吗?而取来这三五万元一刀的纸,他又如涂鸦于废纸一般一页页地瞬间写完,并以此自得。缘斋弟子对这种作大的架势甚是反感也深感忧虑,因为书界如此者已不时可见。弟子们将此列为书坛乱象,反顾自己师门,他们不无自豪地说:“这样的人本门没有,也不可能有。”这都涉及大艺小艺的分寸尺度以及为人为书的时代大事。
注释:
[1]李仲元:《李仲元自书诗卷》,万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3页。
[2][5]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254页,第38页。
[3][4]张广茂主编:《缘斋雅集——李仲元师生书法展作品集》,万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53页,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