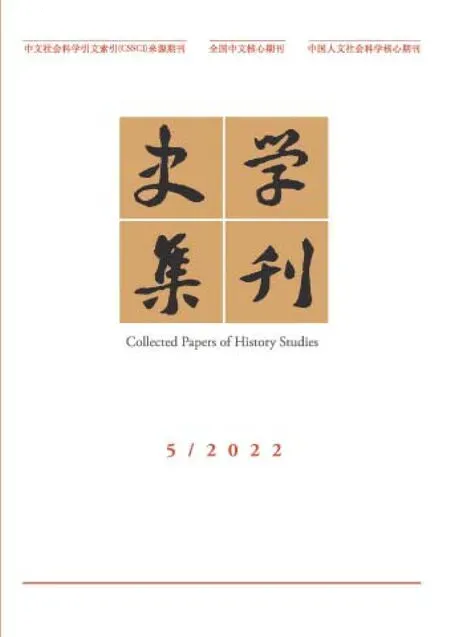南宋明州砂岸买扑制与沿海社会秩序的重构
张宏利
(渤海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南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完成南北大转移,受此影响,东南地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同时,受惠于国家积极开放的海洋政策,宋朝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达到了新的高度。伴随而来的是,沿海地方政府面临着以何种方式管理沿海居民的新问题。彼时,明州(1)庆元元年(1195),宋宁宗将明州升为庆元府。为便于行文,本文主要以“明州”概称,或根据语境而以“庆元府”具称。宋代之时,明州领有鄞县、奉化县、慈溪县、定海县、象山县、昌国县,其域相当于今浙江省宁波市的镇海区、北仑区、江北区、海曙区、鄞州区、奉化区,以及慈溪市、象山县、舟山市。地方官府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所属海滨之地创设砂岸(2)宋代时通行写法为“砂岸”,有时也写作“沙岸”。入元后,通行写法变为“沙岸”,“砂岸”亦在使用。买扑制,以此将海物资源的所有权纳为官有,进以强化对濒海民众的管理。于是,砂岸这一场域汇聚了明州及所属沿海诸县官吏、私占承佃砂岸地方精英、赖砂岸为生的沿海民众三方相关利益主体。他们之间的频繁互动,导致沿海社会秩序处于破坏—重构过程之中。透过砂岸买扑制,不仅能够呈现古代中国海洋资源的所属权变动和海洋管理方式的转变,而且还可以考察南宋及以后朝代沿海地方社会的发展走向。
目前所及,学界尚无以砂岸买扑制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但是,关于砂岸的研究,已有诸多先行研究成果可资参考。就研究主旨而言,大多论著仅是在论述货币地租、学田、海洋捕捞、渔业税等时附带提及,(3)漆侠 :《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367页;顾宏义:《教育政策与宋代两浙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陆敏珍:《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216页;白斌、张伟:《古代浙江海洋渔业税收研究》,崔凤主编:《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徐世康:《宋代沿海渔民日常活动及政府管理》,《中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近来研究有进一步深化的趋势,有学者对其做专题性研究;(4)倪浓水、程继红: 《宋元“砂岸海租”制度考论》,《浙江学刊》,2018年第1期。但以研究视角观之,主要基于经济史视域。
据上述先行研究之检讨可知,学者们主要把砂岸作为海物采捕场所来研究,仅有少数研究者视其为一种海洋租税制度。既有研究虽已注意到砂岸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但未认识到两者皆由砂岸买扑制衍生而来。据此可以讲,现有研究还存在诸多尚需解决的问题,诸如怎样定义砂岸买扑制?砂岸买扑制产生于何时?承佃砂岸地方豪族上户如何凭借砂岸买扑制破坏明州沿海社会秩序?地方官员又是怎样重构明州沿海社会秩序,重构过程中是否遇到阻力,其结果如何?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历史学、社会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解读南宋明州的砂岸买扑制,并回答上述问题。
一、砂岸买扑制释义
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来看,砂岸仅见于明州,且集中载述于地方志中。关于砂岸的含义,宝庆《四明志》称:“所谓砂岸者,即其众其(共)渔业之地也。”(5)(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5页。开庆《四明续志》的记载与此相类,“砂岸者,濒海细民业渔之地也”。(6)(宋)吴潜修,(宋)梅应发、(宋)刘锡等纂:开庆《四明续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715页。对此,学界的解读尚存分歧,主要有两种看法:其一,砂岸即民众近海捕鱼之场所。漆侠、徐世康、白斌、张伟等学者均持此观点。(7)漆侠:《宋代经济史》,第172页;徐世康:《宋代沿海渔民日常活动及政府管理》,《中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白斌、张伟:《古代浙江海洋渔业税收研究》,崔凤主编:《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第170页。其二,砂岸不仅包括渔民近海打鱼之地,而且海岛上的田地、海岛周围的海涂亦属其组成部分。倪浓水、程继红首倡此说。(8)倪浓水、程继红:《宋元“砂岸海租”制度考论》,《浙江学刊》,2018年第1期。两位学者之所以如此定义砂岸,乃是源于他们对“洋山岙隶昌国州(今浙江省舟山市),山七百余亩,地四十九亩三十八步,海滨涨涂不可亩计”的解读。(9)章国庆:《元〈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碑考辨》,《东方博物》,2008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洋山岙与洋山岙砂岸实属两个相异的概念,不可等量观之,此处的山地、海涂地系指洋山岙。另据文献所载“昌国县洋山岙砂岸一所”,“昌国州洋山砂岸系本岙住人丁德诚”所佃,(10)章国庆:《元〈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碑考辨》,《东方博物》,2008年第3期。更是言明洋山岙砂岸为洋山岙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定义砂岸之时,不宜将海岛上的田地、海岛周围的海涂归入砂岸范围。
那么,砂岸是如何变为一个专有名词的呢?在此,我们拟根据地方志的相关记载,勾勒出其大致演变过程。检索文献可知,成书于乾道五年(1169)的《四明图经》尚无砂岸的记载,而撰成于绍定元年(1228)的宝庆《四明志》已经有多处关于砂岸的载述,并详叙砂岸的产生情形。其文称:宋孝宗之子魏惠宪王赵恺判明州时,奏请朝廷将石弄山砂岸拨赐明州州学养士,令其自择砂主,并定其租钱额为5200贯文。(11)(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34-3135页。开庆《四明续志》则将“砂主”称作“砂首”“主砂者”,并记载“以砂首烦扰,复奏请驰以予民”。(12)(宋)吴潜修,(宋)梅应发、(宋)刘锡等纂:开庆《四明续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612、3715页。此处的“砂主”,知庆元府事颜颐仲在奏疏中用其来指代承佃砂岸的地方精英。(13)(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35页。对于“自择”之意,据“浦屿穷民无常产,操网罟资以卒岁,巨室输租于官,官则即其地龙断而征之,或兴或废”,(14)(宋)吴潜修,(宋)梅应发、(宋)刘锡等纂:开庆《四明续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715页。则指称的是招佃。结合上述所载,赵恺此举意在解决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而“令其自择砂主”意指明州州学将石弄山砂岸向当地居民招佃,富家豪民向其缴纳规定额度的租税后,地方政府赋予承佃地方势豪垄断砂岸,并赋予他们向使用砂岸的濒海细民征税的权力。这便是砂岸买扑制的雏形,其法是将通行于宋境的买扑制度移植于海洋经济管理的一种新举措。所谓买扑,系指私人通过类似现代流行的招标竞标的方式,向官府交纳一定数额钱物后,承包或承买官府的商税场、酒坊、田地、盐井等特定时空内的经营权。(15)方宝璋:《略论宋代政府经济管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基于市场性政策工具的视角》,《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3期。因此,知庆元府事吴潜称砂岸买扑制实施的场域为砂岸税场,又称其为团局。(16)(宋)吴潜修,(宋)梅应发、(宋)刘锡等纂:开庆《四明续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715-3717页;(宋)吴潜:《宋特进左丞相许国公奏议》卷三《奏禁私置团场以培植本根消弭盗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政府此举不仅可以节省设务差官的开支,而且能假借豪民之手实得商税,实属有益无弊之举。(17)冷辑林:《略论宋朝的商税网及其管理制度》,《江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细考之,赵恺于淳熙元年(1174)徙判明州,(18)《宋史》卷二四六《赵恺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733页。宋廷于淳熙四年(1177)颁布除罢续置砂岸的诏令,(19)(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573页。因此明州地方政府当于此间创建砂岸买扑制。其后,砂岸数量逐渐增多,故明州新设砂岸局统辖各处砂岸,专门负责砂岸的招佃,并向承佃者收取租税。(20)(宋)吴潜修,(宋)梅应发、(宋)刘锡等纂:开庆《四明续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612页。在此背景下,明州沿海官民逐渐使用“砂岸”一词来指称近海采捕场所。
随着砂岸买扑制的推行,明州地方官府财政收入得到大幅度提升的同时,依海而生的当地民众经济生活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首先,明州地方政府凭借政治权力将海滨人户共渔之地强行纳为官有,进而以强制性手段剥夺了濒海居民共同享有的海物捕捞场域的所有权,由此完成了物产权的转移。其次,沿海细民捕捞海物由免税变为纳税。北宋时期,明州地方政府“以海乡散漫,止产鱼盐,商贾之所不至,故无征禁”,(21)(元)冯福京修,(元)郭荐纂:大德《昌国州图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0册,第4758页。官府此举乃是欲留此利源养赡不耕不蚕的习海之人。(22)(宋)吴潜:《宋特进左丞相许国公奏议》卷三《奏禁私置团场以培植本根消弭盗贼》,第177页。降至南宋,明州地方官府曾短暂向海民捕获鲜鱼、蚶、蛤、虾等征税,不久即以明州乃濒海之地、田业既少、其民兴贩鲜鱼为生理宜优恤的名义,免除了上述税项。(23)(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94页。但是,这种情况在淳熙元年至四年(1174—1177)伴随着砂岸买扑制的实行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其后整个明州沿海地区业海人的采捕活动均被征收租税。明州地方政府向使用砂岸的习海人群征收的赋税,宝庆《四明志》称作砂岸租,有学者称之为“砂岸海租”制度。(24)倪浓水、程继红:《宋元“砂岸海租”制度考论》,《浙江学刊》,2018年第1期。此外,渔船出海捕鱼前后,需要在沿海滩涂晾晒渔网、海产品等,地方政府亦会对占用沿海滩涂的海民进行征税。(25)白斌、张伟:《古代浙江海洋渔业税收研究》,崔凤主编:《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第170页。
综合上述,明州地方官府将海物采捕水域强行纳为官有后,创建砂岸买扑制,通过买扑形式让渡该水域使用权予地方权势之家,濒海人群享有的无偿采捕海物之权随即被剥夺。明州地方政府由此获取巨额砂岸租收入,有效地缓解了地方财政的困窘局面。与此同时,包佃砂岸的地方豪民大族取得了向濒海细民征收海洋渔业税的权力,他们因势而垄断海物资源,致使赖此为生的沿海乡民只有交纳一定赋税方可继续使用砂岸。承佃砂岸的富家大族正是凭借征税之权恣意侵害海滨人户的利益,导致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明州沿海社会秩序因此遭到破坏。
二、承佃砂岸地方势家豪民对沿海社会秩序的破坏
由于明州地方财政日益趋紧,砂岸买扑制得以推广,尤其是在宝庆年间(1225—1227)得到普及。(26)倪浓水、程继红:《宋元“砂岸海租”制度考论》,《浙江学刊》,2018年第1期。因砂岸买扑制引起的明州沿海区域社会关系的变化,成为考察沿海社会秩序破坏—重构的逻辑起点。正所谓权力与所控配置性资源成正比关系,(27)[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8页。强族豪民取得砂岸这一配置性资源后,意味着他们同时获得了官府的授权,堂而皇之地垄断砂岸之利,并能够合法地向海捕人群进行征税。在此情形下,承佃砂岸的地方精英与濒海居民由平等的关系转变为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边海之人因此受到明州地方政府、承佃砂岸地方富民大家的双重剥削。易言之,正是因为明州地方官府强势介入砂岸场域,改变了沿海地方原本利益关联度不强的社会关系,进而生成充满利益纠葛与冲突的新型区域社会关系。
在资源依存性极强的古代社会,海物捕捞场所对于濒海细民生计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砂岸是明州海滨之人的重要生计来源,其民“素无资产,以渔为生”。(28)(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35页。在缺乏利益均衡机制的古代中国,资源配置有利于强者,更易于使强者以侵犯他人利益边界的方式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弱者愈益处于被剥夺的境地。(29)李琼:《冲突的构成及其边界——以湖南省S县某事件研究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05年,第25页。承佃砂岸地方精英正是以垄断砂岸获利,“海乡细民,资砂岸营口腹,龙断者以抱纳微入啖官司,而擅众利”。(30)(宋)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一四三《宝学颜尚书神道碑》,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703页。知庆元府事颜颐仲更是指出:“数十年来,垄断之夫,假抱田(佃)以为名,啖有司以微利,挟趁办官课之说,为渔取细民之谋”,并称承佃砂岸地方豪民对濒海民众横征行为乃是“夺小民衣食之源”。(31)(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35页。史籍虽未明确记载承佃砂岸地方豪民巨族何时借砂岸扰乱濒海生民,但宝庆《四明志》载:“淳熙四年有旨,续置砂岸并除罢。”(32)(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573页。这说明砂岸买扑制创建不久后,租佃砂岸地方豪民巨族欺凌使用砂岸的海滨民众,对明州沿海社会秩序造成了较大的破坏,从而引起宋廷的关注并诏令废除。
然而,宋廷此诏并未能遏制明州砂岸的续置,明州反而不遗余力地续增之,石坛、虾辣、鲎涂、大嵩、双岙、淫口、沙角头、穿山等处均属新置砂岸。(33)(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34-3137页;(宋)吴潜修,(宋)梅应发、(宋)刘锡等纂:开庆《四明续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612页。在此种情势下,官员、地方豪强趁机私占了少部分砂岸,“在外官民户砂岸”,秀山砂岸为徐荣等物产,然其所占比重较少,且砂岸规模亦不大。(34)(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34-3135页。以此之故,承佃砂岸的地方精英一直是剥削濒海细民、破坏沿海社会秩序的主体,私占砂岸者在其中所起作用非常有限。对濒海细民来说,一旦其生存手段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就意味着其生活与过去有了根本的不同。(35)[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随着承佃砂岸势家豪民掠夺幅度的增大,砂岸变为民害的场域,海民因此陷于困苦的境地。文献记载濒海民众为求生存而上诉明州地方官府的情形为,“砂岸之为民害,见于词诉者愈多”,“争佃之讼纷如”,“人又谓主砂者苛征而相吞噬者,则滋讼”,“沿海细民又且词诉迭兴”。(36)(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36页;(宋)吴潜修,(宋)梅应发、(宋)刘锡等纂:开庆《四明续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612、3715-3717页。换言之,承佃砂岸地方大家上户的逐利行为,业已侵害了赖海为生的民众利益,并使他们的生存陷于困境。
逐利属于人的天性,在政府约束力不强的情况下,逐利的天性更是得到彰显。正是由于明州地方官府的纵容,使得砂岸成为包佃砂岸地方精英营私的空间,进而导致砂岸承佃者将征税之权发挥至极致,沿海乡民利益因而被肆意侵害。宝庆《四明志》载述地方势家富民借垄断砂岸之便大肆侵渔濒海细民的行为有如下诸端:
其一,借办课官租,肆意征税于民,为己大肆敛财。垄断砂岸之人,挟趁办官课之说,为渔取细民之谋,名为抽解,实则攫拿。始焉照给文凭,久则视同己业,或立状投献于府第,或立契典卖于豪家。以此倚势作威,恣行刻剥,表现在:一是肆意扩大征税范围,竹木薪炭、豆麦果蔬莫不有征;二是征税名目繁多,有艚头钱、下莆钱、晒地钱等;三是对官府免税的医卜工匠,亦创名色以苛取。(37)(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35页。当然,包佃砂岸地方大族富民的上述行为,既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又因明州诸司不断增多的砂岸租税额压力所迫。唯有更大规模地敛取于民,他们方可完纳官府的课额,进而为己谋利。由此可见,承佃砂岸地方精英的所作所为业已超出了明州地方官府让渡的权力范围。他们为追逐私利、完纳官府砂岸租税而聚敛钱财,对沿海民众进行高强度的经济掠夺,加重了民众负担。
其二,民众生业艰难,民怨归于公。地方富户豪民借砂岸大肆掠夺普通民众,导致后者陷入生存困境,却将民怨引之于官府。时有议者谓:“公家利益甚少,而税场为民害者不赀。”(38)(宋)吴潜修,(宋)梅应发、(宋)刘锡等纂:开庆《四明续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717页。时人对此而叹:“凡海民生生一孔之利,竟不得以自有。输之官者几何,诛之民者无艺。利入私室,怨归公家,已非一日。”(39)(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35页。此段引文说明,涉海民众将其生活艰辛的原因归咎于明州地方官府倡行的砂岸买扑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承佃砂岸地方势家富民正是凭借明州地方政府赋予的征税权力任意盘剥于己,故民众将所怨归于地方官府。
其三,扩充势力,酷虐百姓。承佃砂岸之人不仅在经济上严酷剥掠濒海民户,而且凭借其权势和财富大肆干预地方政务。他们在当地广布爪牙并大张声势,所属砂主、专柜、牙秤、拦脚等数十人结为群,四处为害,具体行径有:一是“邀截冲要,强买物货,挜托私盐,受亡状而诈欺,抑农民而采捕”;二是民众“稍或不从,便行罗织,私置停房,甚于囹圄,拷掠苦楚,非法厉民,含冤吞声,无所赴诉,斗欧(殴)杀伤,时或有之”。(40)(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35-3136页。据此可知,承佃砂岸地方豪强已然成为当地的恶势力,不仅恣意扰乱当地民众的经济活动,对地方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且还任意迫害或残害边海之人,地方政治秩序不断受到冲击。受其影响,明州沿海社会秩序持续地遭受破坏。
在砂岸包佃者持久且愈来愈重的经济盘剥与政治欺压之下,海邦之民最低限度的生存所需越来越难以维系。在这种情况下,濒临生存边缘的沿海民众迫于生计压力转而为盗,用以拓展其生存空间,“比年以来,形势之家私置团场,尽网其利,民不聊生,其间不得已者,未免沦而为盗”,(41)(宋)吴潜:《宋特进左丞相许国公奏议》卷三《奏禁私置团场以培植本根消弭盗贼》,第177页。“近年海寇披猖,如三山、小榭等处,有登岸焚劫之事”。(42)(宋)吴潜修,(宋)梅应发、(宋)刘锡等纂:开庆《四明续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716页。正是由于承佃砂岸地方精英对濒海细民侵剥强度的不断增大,导致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呈现出加剧的态势,由此引发了地方社会的动荡,对沿海社会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部分承佃砂岸地方豪强变作海寇四处劫掠,更是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社会秩序。他们罗织恶少、招纳昔为犯罪之人,揭府第之榜旗,为逋逃之渊薮,操戈挟矢,挝鼓鸣钲,焂方出没于波涛,俄复伏藏于窟穴。其所为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强者日以滋炽,聚而为奸;弱者迫于侵渔,沦而为盗。由此薄人于险而靡所不为:他人之舟,即己之舟;他人之物,即己之物。其强悍的程度,以致兵卒不得而呵、官府不得而诘。(43)(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36页。这说明以地方豪族为首的海盗势力,不仅规模大,而且异常凶悍,以致陆地、海上民众均遭其肆虐,而官府对其亦无可奈何。在上述两股势力的破坏下,沿海社会失序问题渐显并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综合上文,明州地方官府创建砂岸买扑制的目的在于解决日常经费不足的问题,以实际效果来看,明州地方官府经费困乏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但是,宋朝朝廷、明州地方官府未曾预料到的是,承佃砂岸的地方权势之家取得向使用砂岸的沿海民众征税之权后,其所作所为却逐渐摆脱了明州地方官府的控制。承租砂岸的地方精英不仅对沿海居民苛取暴利,而且他们随意干涉地方政事,俨然成为危害一方的恶势力。在此种情形之下讨生活的沿海之人,在承佃砂岸者经济剥削之下,生活业已困苦不堪;在承佃砂岸者插手地方事务后,沿海居民更是时刻面临着失去生命、财货的危险。可以说,砂岸承佃者的弄权行为,不仅加剧了其与涉海群体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引发了明州沿海地方社会的动荡。为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明州有见识的官员以行政命令形式罢除砂岸买扑制,旨在消除造成明州沿海社会动乱的根源,重整沿海社会秩序。
三、地方官员重构沿海社会秩序的努力
承佃砂岸的地方精英侵损濒海民户利益以及破坏沿海社会秩序的行为,已经引起宋廷的重视,并从国家层面发布废除砂岸买扑制的诏命,“淳熙四年(1177)有旨,续置砂岸并除罢”,(44)(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573页。后令近海“众户舟楫往来,纵便渔业,勿有所问,不得容令巨室妄作指占,仍旧勒取租钱”。(45)(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352页。需要强调的是,宋廷仅是下诏要求明州地方政府禁罢砂岸买扑制,而废除砂岸买扑制的实际行动则有赖于明州有作为的官员。鉴于承佃砂岸地方大家上户的行为对滨海居民利益侵损越来越大,并严重影响了沿海社会的稳定,破坏了沿海地方社会秩序,有见识的地方官员屡有废砂岸买扑制之举。宝庆《四明志》对此有详细的描述,“庆元二年(1196),陈景愈于爵溪、赤坎、后陈、东门等处创置税貌。县令赵善与以扰民,白府罢之。提刑李大性摄府,与除免所抱之钱。嘉定二年(1209),杨圭冒置,分布樊益、樊昌等为海次爪牙。郑宥等诉之主簿赵善瀚,历陈其害。五年,守王介申朝廷除罢,毁其五都团屋,版榜示民。宝庆元年(1225),胡逊、柳椿假府第买鱼鲜之名,私置鱼团。郑宥等又有词,仓使齐硕摄府,杖其人而罢之”。(46)(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573页。除此之外,明州沿海制置使司属官胡叔恬亦有劝罢砂岸买扑制之举,“唱言巨室而沙岸为彻局”。(47)(宋)物初大观:《物初剩语》,许红霞:《珍本宋集五种——日藏宋僧诗文集整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62页。尚需注意的是,这些官员罢除砂岸买扑制之举,仅是于一定时期在明州局部地区施行。
因砂岸买扑制造成的恶劣影响日趋严重,最终引起了知庆元府事的重视,并以政治权力强行废罢砂岸买扑制。淳祐六年(1246),知庆元府事颜颐仲到任之初,访闻砂岸买扑制为当地之害,“乃撙节浮费,先措置钱五百(万)余贯,代纳砂岸租钱,而一害先去”,(48)(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204页。并申奏尚书省:“州郡既率先捐以子民,则形势之家亦何忍肆虐以专利。应是砂岸属之府第,豪家者皆日下,听令民户从便渔业,不得妄作名色,复行占据。其有占据年深,腕给不照,或请到承佃榜据,因而立契典卖者,并不许行用。欲乞公朝特为敷奏,颁降指挥,著为定令。或有违戾,许民越诉,不以荫赎,悉坐违制之罪”,宋廷下旨依其所请。(49)(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36页。在颜颐仲的努力下,明州官有及官民私占砂岸一例蠲除。(50)(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35页。颜颐仲此举旨在恢复原本稳定、有序的沿海社会秩序,在吴潜的奏言中已明确言明:“庶几海岛之民可以安生乐业,府第、豪户不得倚势为奸,非唯为圣朝推广惠下之仁,亦不至异日激成为盗之患。”(51)(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36页。然而,砂岸买扑制虽在颜颐仲四年任期内被禁行,但其后又得以复置。
宝祐四年(1256)知庆元府事吴潜到任后,获悉砂岸买扑制为当地民害而奏言:“近幸势家自行住罢团局,听令民间自营生业,小民方有生意”,并称永行禁断砂岸买扑制是培植本根、消弭盗贼之第一义。(52)(宋)吴潜: 《宋特进左丞相许国公奏议》卷三《奏禁私置团场以培植本根消弭盗贼》,第177页。在吴潜的推动之下,曾一度废除砂岸买扑制,但之后“因民之欲而奏复之。越一年,人又谓主砂者苛征而相吞噬者,则滋讼。公知其扰民也,亟奏寝之,或止或行,悉因民欲”。(53)(宋)吴潜修,(宋)梅应发、(宋)刘锡等纂:开庆《四明续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715页。此后的宝祐五年(1257)吴潜奏请将赡学砂岸“复归于学。继而争佃之讼纷如,准制札仍拨归制司,却于砂岸局照元额发钱养士。六年五月,以砂首烦扰,复奏请驰以予民”。(54)(宋)吴潜修,(宋)梅应发、(宋)刘锡等纂:开庆《四明续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612页。在吴潜四年任职期内,砂岸买扑制除罢与复置时或有之的原因,乃是吴潜将沿海盗贼盛行的原因归为罢砂岸买扑制而致砂民无所统率,(55)(宋)吴潜修,(宋)梅应发、(宋)刘锡等纂:开庆《四明续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715页。为维持地方稳定而复置之;其后鉴于复置砂岸买扑制致扰民不息又罢之。这说明,吴潜虽欲根除砂岸买扑制,但受当地实际情形所迫,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
与此同时,为消弭海盗对沿海社会的冲击,颜颐仲、吴潜力推保甲之法,并增加沿海地区的屯兵数量,力图恢复沿海地方的稳定。淳祐六年,颜颐仲已将当地民船团结保伍。(56)(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35页。吴潜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保甲之法。吴潜对该法实行的缘由、具体做法、预期效果等有详尽的阐述,“始者之兴复砂岸税场,不过欲为清海道绝寇攘之计,今已将应干砂岸诸岙并行团结,具有规绳,本土之盗不可藏,往来之盗则可捕”,“则前所谓砂民无所统率而盗贼纵横之事,不必虑矣。又于浃港置立小屯,则前所谓数十里之内官司并无纂节,而莽为盗贼出没之区者,不必虑矣”。(57)(宋)吴潜修,(宋)梅应发、(宋)刘锡等纂:开庆《四明续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716-3717页。庆元府“令当土大家随其地分及砂岸广狭、事力,共团结强壮三千人,仍与各办衣装、器械……置立头目,部勒队伍……以千人合教于郡,三岁周而复始”。(58)(宋)吴潜:《宋特进左丞相许国公奏议》卷四《条奏海道备御六事》,第184页。明州地方政府此举,是以政治手段强力推行保甲制,借此强化对沿海居民的人身控制,进而达到稳定地方社会的目的。应当说,明州以强制性力量弹压沿海群盗的不法行为,仅可暂时实现地方社会的稳定,却无法维持该局面的常态化。因此,地方官府应当构建稳定有序的沿海社会秩序,稳定是外在表象、是初级状态,而有序才是内在的、本质的高层次的理想状态,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根本基础。(59)宋宝安:《论实现社会从稳定到有序的战略抉择》,《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2期。
总的来看,明州自上而下皆有官员竭尽所能除罢砂岸买扑制,确实在一定时期的局部地区或短时期于全境住罢砂岸买扑制,海滨居民因此能够无偿、自由地采捕海物,使得明州沿海社会秩序得以短暂恢复。但是,相对于砂岸买扑制存续时间而言,地方官员维持无砂岸买扑制的时间毕竟为期不长,故其重构沿海社会秩序的努力只能在短期内有效。这足以表明,明州沿海社会秩序的重构遇到了极为强劲的阻力。观其所遭阻力,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明州地方官府;二是私占、承佃砂岸的既得利益集团。
其一,明州地方财政收入窘乏,官府日常经费对砂岸租依赖性极强。明州所在的两浙地区,一直是北宋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60)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伴随着宋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东倾,江南地区步入宋廷重赋征敛时期。(61)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7页。受此影响,两浙地区于北宋后期已屡屡出现财政亏匮情况。(62)(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九》,第7107页;(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七《国用考五》,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95页。迨至南宋时期,明州成为畿辅之地,宋廷对其财赋的索取愈益增重,致使明州出现“税重田轻,终岁所入,且不足以供两税”的现象。(63)(宋)李心传著,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456页。更为严重的是,明州同时进入自然灾害频发期,多个年份发生规模较大的水旱虫灾害,台风、海啸时有发生,甚至出现人食草木之现象。(64)《宋史》卷六七《五行五》,第1463-1477页。因此,朱熹言:“窃见浙东诸州例皆荒歉,台、明号为最熟,亦不能无少损”。(65)(宋)朱熹著,刘永翔、朱幼文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六《奏救荒事宜状》,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62页。不唯如此,明州还需承担日本、高丽使者居留其间费用,对两国漂流人出钱粮施以救济。尤其是开禧用兵后,南宋进入与蒙古军事对抗期,中央财政压力骤增,无疑加重了明州地方财赋的负荷。综合上述,宋廷的重赋索取、自然灾害造成的收入减损以及地方支给增多,共同导致明州地方财政陷于困境。
缘于此,明州地方官府不得不另辟新的财源,以求缓解愈来愈重的财政压力。对边海的明州及所属县来讲,向采捕海物的滨海居民征取赋税成为解决财政困境的重要方式。于是,魏惠宪王赵恺创砂岸买扑制,以解决明州州学经费不足问题。难得的是,文献载述了明州赡学砂岸租税额度的变化情形。从淳熙初年至淳祐六年(1174—1246)的70余年间,明州赡学砂岸就由初始税额的5200贯文猛增至30 779.4贯文,十一年后的宝祐五年(1257)更是达到37 478.75贯文。(66)(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35-3136页;(宋)吴潜修,(宋)梅应发、(宋)刘锡等纂:开庆《四明续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612页。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明州地方政府所定砂岸租额度亦呈现递增之势,某一年岁收砂岸钱共计53 182.6贯文,(67)(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36页。之后更是达到惊人的368 700贯文。(68)(宋)吴潜修,(宋)梅应发、(宋)刘锡等纂:开庆《四明续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715-3716页。深究明州地方政府征收砂岸租额度越来越多的原因,乃是在于所辖诸司以及属县日常支给愈来愈依赖砂岸租所致。明州地方官府征取的砂岸租税,不仅用来拨助昌国县官俸,甚至郡庠养士贴厨、水军将佐供给、新创诸屯与出海巡逴、探望、把港军士生券及庆元府六局衙番盐菜钱之费亦需由其支付。(69)(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35页;(宋)吴潜修,(宋)梅应发、(宋)刘锡等纂:开庆《四明续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715-3716页。
正是基于此,导致砂岸买扑制能够长时间存续。颜颐仲推求砂岸买扑制不能禁绝的原因在于州县财赋收入依赖于砂岸租,为此他建议欲废除砂岸买扑制应先自有司始。(70)(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36页。虽然如此,颜颐仲甫至庆元府即意识到废除砂岸买扑制牵扯多方利益,除罢之事必须慎之又慎,因此他说:“窃计所管课额,散在他司,用度所关,未易除罢。”(71)(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204页。值得一提的是,上述颜颐仲、吴潜虽尽罢砂岸所入课利,但并不意味着明州诸司依赖砂岸租收入的现象立即消失。对于昌国县官俸及养士、饷军之需,他们仅是截拨版帐钱、庆元府醅酒库息钱及翁山等坊、慈溪酒务每岁息钱给予支遣而已。(72)(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35-3137页;(宋)吴潜修,(宋)梅应发、(宋)刘锡等纂:开庆《四明续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716页。由此可见,两位官员所举皆属应急之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明州财赋窘乏的困境,这也导致砂岸买扑制被废除后,复有兴之。更为重要的是,为年入数万缗砂岸租,坐视海民困苦而不救的明州官员甚多。(73)(宋)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一四三《宝学颜尚书神道碑》,第5703页。据此可以讲,明州地方官府所属诸司日常办公经费依赖于砂岸租所得,由此明州地方官府成为住罢砂岸买扑制的主要阻碍力量。
其二,私占、承佃砂岸既得利益集团竭力阻扰废除砂岸买扑制。私占、承佃砂岸者“由其恃有凭依,所以肆无忌惮”,其开抱砂岸者部分为品官与贵势之家,致使奸宄日出、遗祸无穷,从而导致砂岸买扑制屡不能禁。(74)(宋)胡榘修,(宋)方万里、(宋)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第3136页。因此,包佃砂岸的地方豪强凭借明州地方政府让渡的砂岸征税之权以及自身具有的权势、财富,能够统率濒海细民,后者对前者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史籍对此有明确的记载:“人谓砂岸废而民无统,寇职以肆”,“适当海寇披猖之余,遂行考究本末,多谓因沿海砂岸之罢,海民无大家以为之据依”,“皆起于罢砂岸,而砂民无所统率之故”。(75)(宋)吴潜修,(宋)梅应发、(宋)刘锡等纂:开庆《四明续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715-3716页。正是由于承佃砂岸地方形势之家具有的强大势力,他们能够对滨海之民形成威慑之势,从而任意剥掠沿海民众。在这种情势下,吴潜虽强行罢除砂岸买扑制,但仍忧虑地方豪民勾结官府而复之,“一方奸猾之徒垂涎未已,或恐妄行投献府第,借声势以残民,创砂岸以龙断,使小民衣食之源得而复失”。(76)(宋)吴潜:《宋特进左丞相许国公奏议》卷三《奏禁私置团场以培植本根消弭盗贼》,第177页。从文献明确记载迟至咸淳三年(1267)砂岸买扑制得以复置来看,(77)章国庆:《元〈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碑考辨》,《东方博物》,2008年第3期。他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上述事实,充分凸显了明州致力废除砂岸买扑制的官员与私占、承佃砂岸之人博弈过程的复杂性和持久性。
综上可知,明州地方官府日常经费困乏的局面始终未得到实质性改善,故对砂岸租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得以保障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私占、承租砂岸的地方大家上户基于经济利益考量,也希望维持砂岸买扑制,进而获取巨额收入。在这种情形下,明州地方政府与私占、承佃砂岸地方豪强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利益需求,故为实现彼此间的利益最大化,结成了既得利益共同体。地方官府有意容纵承佃砂岸地方精英的不法行为,任由其欺压濒海居民,沿海社会秩序不断遭到破坏。在这种形势下,明州有作为的官员罢除砂岸买扑制、重构沿海社会秩序的努力,虽可短期内取得预期效果,但却难以扭转整个发展态势。值得注意的是,砂岸买扑制并未随着朝代的更迭戛然而止。元代之时,不仅出现官属砂岸被官员、豪民据为己有的新现象,(78)(元)王元恭修,(元)王厚孙纂:至正《四明续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0册,第4614、4628页。而且将其所占官属砂岸转售他人的情况亦有之。(79)章国庆:《元〈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碑考辨》,《东方博物》,2008年第3期。据此可断言,砂岸买扑制产生的破坏力在元朝依旧发挥着作用。降至明代,受官方海洋政策日趋保守的影响,海物采捕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砂岸买扑制最终伴随着明朝的严厉海禁政策不复存在。(80)倪浓水、程继红:《宋元“砂岸海租”制度考论》,《浙江学刊》,2018年第1期。
结 语
明州边海地区有着丰富的海洋物产,这为田业较少的濒海民众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资源。北宋及南宋前期,宋廷、地方财政压力较小,故明州地方官府任由濒海居民无偿采捕海物,沿海民众得以平等地享有海洋捕捞之权。降至南宋中后期,中央政府的财政需求不断增多,对地方财政的索取随之增强,尤其是地处畿内之地的明州成为宋廷重点征取对象。这直接加剧了明州地方政府的财税负荷,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明州地方官府将行之于宋境的买扑制度引入海洋采捕活动中,是为砂岸买扑制。至此,砂岸买扑制作为一种新的机制被创立出来。
明州地方政府通过砂岸买扑制将地方政治权力渗透至海物采捕场域中,剥夺了沿海民众自由和无需交纳租税即可使用海洋资源的权利,并将独占砂岸的权力赋予承佃的地方势家豪民,于是砂岸承佃者与濒海细民之间形成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明州地方官府赋税压力和自身经济利益驱动之下,承佃砂岸地方精英不断突破明州地方政府的规限,肆意扩充税项并任意侵渔沿海民众,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沿海社会秩序受其影响不断被破坏。有鉴于此,明州有识见的官员屡有除罢砂岸买扑制之举,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预期效果,明州沿海社会秩序因此得以重构。然而,由于明州州学养士、屯戍水军所需及部分县官俸禄主要仰给于砂岸租,截拨他处收入支给仅可暂时应之,却无力改变明州地方财政的窘困局面。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明州相关官员欲永久住罢砂岸买扑制,并借此重构沿海社会秩序的努力,势必难以取得一劳永逸的效果。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严重依赖砂岸租的明州诸司,以及私占、承佃砂岸地方势家富民结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明州有作为官员废除砂岸买扑制、重构沿海社会秩序的主要阻力。因此,宋廷、明州地方政府虽皆有罢砂岸买扑制之举,但均遭到赖砂岸租维持日常用度诸司,以及私占、承佃砂岸既得利益集团的百端阻扰,其结果便是由砂岸买扑制引起的沿海社会秩序的破坏活动,终南宋一代未能得到消除。
砂岸买扑制的影响并不限于此,由砂岸买扑引起的承佃砂岸地方势豪破坏明州沿海社会秩序的活动,更是对元明清三朝海洋经营活动产生了影响。虽然,明州地方政府以砂岸买扑制为媒介,将政府力量逐步渗透至沿海居民海物采捕活动中,并不断挤压沿海地方社会的自主空间,意图严格管控涉海群体,进而维持沿海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明州沿海社会的动荡局面并未因此而被有效控制,官员重构沿海社会秩序的努力最终没有成功。受其影响,元明清官府非常忌惮沿海居民的破坏性活动,对滨海民众的防范意识日渐增强,进而不断强化对海邦之民的管理。此举更是直接导致明清官方海洋政策日益保守,对民间海洋活动的限制日趋严格,以致海禁政策屡有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