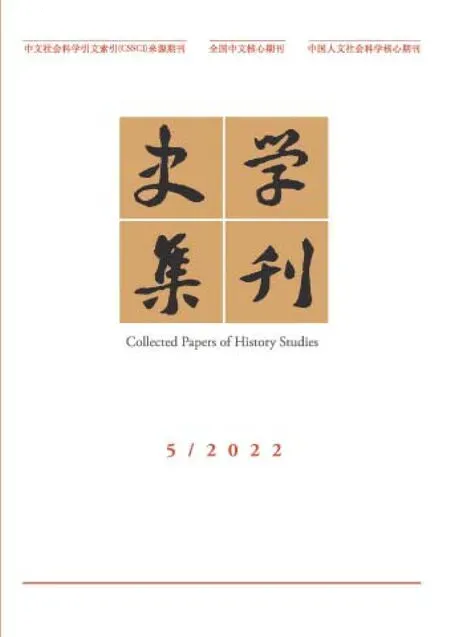清至民国“南明”史概念发生与传播探论
谢贵安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概念是以词汇来表达的,不同的词汇表达不同的概念及其背后的意义。“南明”一词出现较早,但流行较晚。时至今日,由于谢国桢《南明史略》、柳亚子《南明史料》的问世,以及南炳文、顾诚、钱海岳各自的《南明史》的出版,“南明”符号及其指代的那段历史——南明史,已成为明亡后福、唐、鲁、桂四王政权历史的鲜明标志,成为人所共知的流行概念。然而,“南明”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概念,它所指代的南明史也并非一个“顺理成章”的断代史名称,因其隐含抵御外侵的特殊含义而经历了专制压迫。前人对此问题有零星或零散的讨论,但未及做系统的探究。(1)美国学者司徒琳,以及中国学者高小娥、吴航均在其著作中对“南明”一词做了简要的考订和解释,分别见于:[美]司徒琳:《英文版序言》(译文),[美]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严寿校:《南明史(1644—1662)》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高小娥:《“往事南朝一梦中,兴亡转瞬斗秋虫”——有清一代南明研究史》,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第1页;吴航:《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本文拟对清至民国时期“南明”及其指代的南明史概念的发生与传播,进行梳理和论述。
一、“南明”史概念在清前中期的昙花一现
“南明”是指明朝灭亡后,明室后裔在南京、福州、肇庆、安龙、昆明等地建立的福王朱由崧弘光、唐王朱聿键隆武、桂王朱由榔永历以及鲁王朱以海监国等一系列政权。南明各政权都自称“大明”,不会贬自己为“南明”。英国近代化学奠基人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于1671年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得到一本南明时的《大明中兴永历二十五年大统历》,并将其转赠给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此为南明人自称“大明”而非“南明”之铁证。(2)《英国皇家学会与大清国的渊源》,2017年5月11日。https://www.sohu.com/a/139646147_523187(2020-02-23).上述政权灭亡后,“南明”概念反而有了尊崇它们的政治含义。“南明”一词是比附“南宋”而出,而南宋被认为是北宋的正统继承者,“南明”概念的使用亦有此意,蕴含否定清朝的倾向,因此清朝灭掉南明后,为消解南明的正统地位和历史记忆,而大兴文字之狱,严禁撰述南明史和使用南明年号,“南明”一词成为敏感的政治符号被禁止提起。清朝指称上述南明政权及其时代、人民,一般都用“晚明”“故明”“残明”“续明”“明季”“明末”“明余”“明亡”“大明亡国”“南疆”“南天”“南都”“胜国”和“明遗民”等概念,基本上没有人用“南明”一词来指代弘光至永历时的历史,或用“南明”作为史书之名。笔者检索了清修的《明史》和《清实录》,乃至《清朝经世文编》等清朝文献,均未见到专指朝代的“南明”一词的踪影。
然而,仍有极少数人犯禁提出“南明”概念并用做书名,不过只是昙花一现。
“南明”的概念,在清代康熙年间已经出现。江阴人陈鼎(1650—?)在其所撰《东林列传》卷一二《黄道周传》的末尾,以“外史氏”为名发表议论:“嗟乎!明既亡矣,而先生犹狼仓(即踉跄)以图恢复,不亦难乎?假使南渡以来,马、阮即死,而任先生以国,或者李纲、赵鼎庶几再见于南明,而社稷或可苟延于江左。奈何马、阮不死,又欲诛戮东林,期于斩草除根而后快,则先生危矣。至唐王再起,已死之灰,焉能复燃乎?”(3)(清)陈鼎:《东林列传》,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5册,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632页。陈鼎这里称“李纲、赵鼎庶几再见于南明”,显然是比照“南宋”而提出“南明”概念。《东林列传》较早的刊本为康熙五十年(1711)的铁肩书屋刻本,这说明此书当在康熙年间完成。那么,“南明”一词的出现不晚于康熙年间殆无疑义。(4)高小娥:《“往事南朝一梦中,兴亡转瞬斗秋虫”——有清一代南明研究史》,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第1页。不过,直到钱绮之前,清朝无人敢再提起“南明”一词。
19世纪中叶,钱绮(1798—1858)率先用“南明”一词作为书名,撰写了《南明书》。顾颉刚据此认定“南明”一词为钱绮首创:“明、清之际,流传野史极多,但经清政府的禁毁,加以文字狱大兴,留存者极少。嘉、道以后,文禁不如以往的严密,但时间既相隔较远,材料的搜集颇难,故成书极少。惟徐鼒有《小腆纪传》六十五卷、《补遗》五卷。复有《小腆纪年》二十卷,用纲目体,搜集史料略备。又钱绮《南明书》三十六卷,未刊行,傅以礼曾见之;‘南明’一词即为钱绮所首创。戴望对南明史亦曾用力,欲作《续明史》,惜仅成传数篇。”(5)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编《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10页。然据前文所述,“南明”一词显然不是钱绮所首创,而是陈鼎,不过钱绮是最早将之用作书名的人。
钱绮使用“南明”概念撰写《南明书》,是在清朝对南明忌讳有所放松的背景下。道咸以后,“私家学者大都有结撰贯通性、综合性的南明史撰述的学术追求”,钱绮便在这种背景下撰写了《南明书》36卷,但该书“惜其散佚,不存于世”。(6)吴航:《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5页。张星鉴(1819—1877)(7)关于张星鉴的生卒年份,参见蔡德龙:《张星鉴〈仰萧楼文话〉及其骈文学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24页。在《仰萧楼文集》中称钱绮“熟明季遗事,著《南明书》三十六卷……咸丰八年卒,年六十一”。(8)张星鉴:《仰萧楼文集·怀旧记·钱绮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28页。吴航推测,钱绮撰著《南明书》,在道光七年(1827)之后。笔者认为《南明书》成于咸丰八年(1858)以前。
除钱绮之外,夏燮和徐鼒两位史学家也开始突破清朝的忌讳,直接书写南明历史。他们虽然打破清朝禁忌,直书了南明的历史,但均未使用“南明”概念,只有同时代的钱绮直接用“南明”一词作为著作之名。这说明,当时政治环境虽然有所松动,但仍然比较严峻。据钱绮在咸丰七年(1857)自述,道光十二年至道光十六年(1832—1836),他从正谊书院“肄业时”,书院山长、泾县人朱兰坡曾向他“询及时文之外,涉猎何书”?当时“绮方搜罗胜国轶事,遂以阅《明史》对”。(9)(清)钱绮:《左传札记》卷首《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2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297页。钱绮当时搜罗的“胜国轶事”,其实是南明史事,但却回答说是在读《明史》,隐瞒了事实。显然,当时的政治氛围,还不足以松动到可以公开搜集和撰写南明史。因此,除钱绮外,他同时代的人,虽然都在撰写南明史,但没有人敢将自己的著作称作“南明”。
需要指出的是,乾隆时人南沙三余氏编写的《南明野史》虽然用了“南明”一词,但它不是原名,而是后人所改。其原名为《明季五藩实录》(又名《明末五小史》)。(10)《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编者:《弁言》,三余氏:《南明野史》卷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85种,台湾大通书局1960年版,第1页。1929年,王钟麒对此书进行“校补缺文,是正称谓……总颜为‘《南明野史》’”。(11)(清)王钟麒:《跋》,三余氏:《南明野史》卷末,第275页。由此可见,该书是乾隆时的书,但书名则是民国时的书名。谢国桢著录此书为“《五藩实录》八册”,下注“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作《南明野史》”,(12)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56页。可谓一目了然。
由于钱绮《南明书》的出现,使得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人是在此时才提出“南明”概念。美国南明史专家司徒琳称:“众所周知,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学者才使用‘南明’这一称谓。”并说:“南明一词的晚出是可以理解的。此词与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对其他朝代、尤其是对南宋的称谓一样,意味着对某些政权表示尊重,视其为正统。而清朝官方对这些政权的态度尽量予以抹煞。大多数清朝学者提及1644至1662年这段时期,总是称为明末、明季、南疆,或是用前朝亡国的典故以为暗示。”(13)[美]司徒琳:《英文版序言》(译文),[美]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严寿校:《南明史(1644-1662)》卷首,第1页。司徒琳所说的“众所周知”,便是指钱绮撰写《南明书》这件事。显然,她与顾颉刚一样,都未能发现比《南明书》更早的《东林列传》已经使用过“南明”一词。
总之,“南明”一词作为晚明偏安政权的代称,始于康熙时陈鼎的《东林列传》,在中国率先用“南明”作书名的是19世纪中叶钱绮的《南明书》。然而,在中国的东邻朝鲜,乾隆时已有黄景源和成海应二人用“南明”作为书名。
二、朝鲜士人在清中期和清末两度率先用“南明”作书名
用“南明”作史书之名,最先出现在邻邦朝鲜。乾隆年间,朝鲜官员黄景源有感于《明史》不写弘光至永历的帝统,愤然撰写了《南明书》,这是最早以“南明”用作书名的史书。据《李朝实录·正祖实录》记载:“(正祖)十一年丁未(乾隆五十二年)二月癸未,判中枢府事黄景源卒……景源字大卿,号江汉……常以春秋大义自任,见张廷玉《明史》,不与弘光以下三帝统,乃撰《南明书》,三本纪,四十列传,起弘光元年,迄永历十六年。”同时,他“又以崇祯以来,本朝诸臣之为皇朝立节者,作《陪臣传》”。(14)《正祖实录第二》卷二三,《李朝实录》第48册,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6年版,第150页。“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光涛在复述黄景源著作时,一度将书名误写为“《南明史》”,并称原书“不可见”。(15)李光涛:《中韩民族与文化》,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8年版,第116页。
与黄景源几乎同时,成海应(1760—1839)也对张廷玉《明史》未把南明三帝列入本纪表示不满,特撰《〈南明书〉拟稿》以驳之。(16)[朝]成海应:《研经斋外集》第四册《〈南明书〉拟稿义例》,汉城:旿晟社1982年版,第159页。
朝鲜之所以率先用“南明”作书名,是因为当时的朝鲜以“小中华”自居,将自己视为明朝的继承者,故竭力维护明朝及其后继者南明的正统地位,对作为“夷狄”而入主中原的清朝则持排斥的态度。(17)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59页。正如纂修编年体明朝史书《续史略翼笺》的洪奭周(1774—1842)所称,他自己撰写“是书特揭弘光、隆武、永历之号,以续崇祯之后,此非所谓尊正统、攘夷狄、明大义于天下者乎?今天下胥而为戎狄,虽有是书不能广也,然不能广于天下而广之于吾东一国之内,则吾东方之意,岂不益有耀于万世哉!”(18)[朝]洪奭周:《续史略序》,《渊泉先生文集》,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131册,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263-265页。
不仅黄景源的《南明书》不传,成海应《南明书》也只是拟稿,并未成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的政治高压所致。朝鲜虽然处于清朝外围,但作为大清的附属国,仍然感受到清朝排斥“南明”意识的巨大压力。洪奭周称“近世为明史者屡十家,皆迄于崇祯而已”。(19)[朝]洪奭周:《续史略序》,《渊泉先生文集》,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131册,第265页。据孙卫国所列《朝鲜王朝所修中国史书简表》得知,关于明朝史书,没有一个以“南明”为书名的。(20)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第258-261页。事实上,朝鲜王朝所修的明朝史书中,有很多仍将南明历史写了进去。如正祖所撰纲目体《明季提挈》20卷,记录了洪武元年(1368)到永历十六年(1662)之明朝史事;佚名所撰的编年体《明史纪略》,记录了洪武元年到永历十三年(1659)的明朝史实;李玄锡所撰《明史纲目》23卷(1771年刊行),记述了明太祖洪武元年到崇祯十七年的明代历史,同时将南明史实置于补编;南有容所撰纲目体《明书纂要正纲》18卷,意在更正李玄锡之误,强调南明正统,记录了洪武元年到永历十三年的史实;佚名所撰的《明朝殉节诸臣录》11卷,系改编乾隆四十一年(1776)所刊《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而成,废清年号不用,采用南明年号;赵彻永所撰纲目体《续明史》40卷(1839年刊行),以及李宪明所撰《清史提要》3卷,记载了南明与清初的历史,以南明年号为准。然而,以上诸书都未敢直用“南明”之名。因此,乾隆时黄景源《南明书》之不传,成应海《南明书》之不成,盖非无因。
及至清末,反清运动兴起,朝鲜又掀起了反清尊明思潮,已经偃息的“南明”概念再一次兴起。朝鲜人郑乔(1856—1925)于1907年1月29日撰成《南明纲目》,1908年初刊于汉城普文社。全书共5卷,记事自崇祯十七年至永历十六年(1644—1662),书中特重华夷之辨,大书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年号,以南明为正统,黜清朝为僭伪。作者自道“书满洲,即朱紫阳不书契丹,改其国号辽之义也”,表现出强烈的尊明贬清色彩,“从中仍可见其对大明王朝之眷恋与追怀”。(21)秦丽:《20世纪初中韩士人的“排满”思想——以章太炎和郑乔为线索》,《汉学研究》(台湾),2019年第3期。郑乔的《南明纲目》初刊后不久,即赠送给时在日本的章太炎,成为“南明”概念在中国传播的触媒之一。
郑乔的《南明纲目》传入中国后,在民间有一定的收藏。抗日战争时的1943年或稍前,章太炎弟子朱希祖到广州双门底黄忠裕公祠拜访黄佛颐(1880—1946),“乃观其藏书之有关南明者”,发现“其书大抵余已有之,惟苏国祐之《易箦遗言》,及朝鲜人郑乔之《南明纲目》,为余所未有”。于是他“借《南明纲目》抄录一部,其书为五卷,阅读一过,觉其中材料,皆世所恒见。惟间亦有希见者,有朝鲜人所记录者,亦不可不参考之书也”。(22)朱希祖:《广州征访南明史料记》,《中国学报》(重庆),1943年第1期,第32页。郑乔的《南明纲目》也被谢国桢的《史籍考》载录:“《南明纲目》五卷,朝鲜汉城普文社铅印本。朝鲜河南郑乔友向编撰,谷山卢宪容汝章参校,齐安黄翰周鹤汝考订。”(23)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第440页。这证明此书为他所亲阅。此书在中国流传自不待言。
三、中朝“南明”概念及其史书在清末的交汇
在朝鲜关注南明史的同时甚至稍前,中国的部分史籍已开始介绍钱绮的《南明书》。此时,人们不再顾忌清廷的忌讳,公然在史志著作中著录钱绮的《南明书》。始修于同治八年(1869),成书于光绪二年(1876)的《(同治)苏州府志》记载道:“钱绮……《南明书》三十六卷。”(24)(清)冯桂芬等:同治《苏州府志》卷一三七《艺文二》,《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1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8页。1902年成书320卷、1921年(辛酉年)成书400卷的《清朝续文献通考》,也直接记载道:“《南明书》三十六卷。钱绮撰。绮,字映江,号竺生。江苏元和人,诸生。”(25)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六四《经籍考八》,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二集《十通第十种》,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考第10082页。
与朝鲜反清运动相呼应,清末革命党人也兴起了反清运动,开始主动使用“南明”概念,试图撰写南明史。司徒琳指出:“大多数清朝学者提及1644至1662年这段时期,总是称为明末、明季、南疆,或是用前朝亡国的典故以为暗示。但是在二十世纪头十年,清朝推翻,民国肇造,反满情绪随之而起,于是南明一词广泛使用。”(26)[美]司徒琳:《英文版序言》(译文),[美]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严寿校:《南明史(1644-1662)》卷首,第1页。
1904年,同盟会元老、南社领袖柳亚子(1887—1958)可能已使用了“南明”的概念。他自称于民国纪元前八年甲辰(1904)18岁时,“读夏存古、张苍水诸家集,并及全谢山《鲒埼亭文内外集》,为搜讨南明故事之始”。(27)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这段记载是他后来根据回忆写的《自撰年谱》中的文字,但考虑到柳亚子创立“南社”意在“操南音,不忘本”,以与北方清朝相抗衡,因此他使用“南明”概念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另一位同盟会元老、革命党人章太炎(1868—1936),也使用了“南明”概念。这既可能是受钱绮《南明书》的影响,也可能受朝鲜郑乔《南明纲目》的影响。章太炎自称少时十分留心明季史料,热衷表彰明遗民,甚至提出撰写《后明史》的构想。(28)秦丽:《20世纪初中韩士人的“排满”思想——以章太炎和郑乔为线索》,《汉学研究》(台湾),2019年第3期。在这里,章太炎提出的概念是“后明史”,而非“南明史”。在“苏报案”获刑释放后,章太炎东渡日本,在那里得赠《南明纲目》。据章太炎弟子朱希祖(1879—1944)在1934年2月8日回忆时所说:“朝鲜人郑乔所撰《南明纲□》五卷。余于二十七年前留学日本时已在吾师章太炎先生处见之,时初出版,著者所寄赠也。”(29)朱希祖:《跋》,[朝]郑乔:《南明纲目》卷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编:《域外所见中国古史研究资料汇编·朝鲜汉籍篇》第17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90页。章太炎赴日在1908年,则受赠《南明纲目》应在此时或稍后。与章太炎关系密切的刘师培,可能见到了章太炎受赠于郑乔的《南明纲目》,受其刺激,产生了撰述《南明书》的想法,“闻刘师培申叔曾欲作《南明书》,章太炎为之作序,惜未见”。(30)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第478页。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对于“南明”概念已经全然接受。
“南明”概念在晚清的兴起,究竟是源自中国的钱绮,还是源自朝鲜的郑乔,仍值得进一步考订。笔者认为可能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苏州府志》和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均著录了钱绮的《南明书》,章太炎、刘师培通过二书得见钱书名字的可能性很大,而章太炎又直接受赠了郑乔的《南明纲目》,与章太炎过从甚密的刘师培通过章氏接触到郑乔《南明纲目》的可能性也很大。也就是说,在清末反清潮流下,中朝两国的“南明”概念及其背后的思潮已经汇流。
与章太炎在日本得赠《南明纲目》不同,湖北罗田人王葆心(1867—1944)在国内得见朝鲜人所撰之《南明书》。清末,王葆心撰写了《蕲黄四十八砦纪事》。他在该书卷二《鄂砦续篇》按语中称:“吾观朝鲜人所为《南明书》,其中书法实以正朔予安、绍诸帝而外本朝;其书法予夺,均本此义。可见朝鲜人乃以中国正统自居,而以清代为闰位也。”(31)(清)王葆心:《蕲黄四十八砦纪事》卷2,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305册,1972年,第38页。此书的《采用书目》中有“《南明书》(朝鲜人编)”。(32)(清)王葆心:《蕲黄四十八砦纪事》卷末,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305册,第115页。于此可见,《南明书》当时已传入国内,从而为王葆心观阅。王葆心阅读《南明书》后,被谢国桢录入其《晚明史籍考》中:“《南明书》。朝鲜佚名传。按王葆心《蕲黄四十八砦纪事·鄂砦续编》注引《春在堂随笔》云:‘吾观朝鲜人所为《南明书》’云云。”(33)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第477页;谢国桢著,谢小彬、杨璐主编:《谢国桢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478页。谢氏此处疑有误,“吾观朝鲜人所为《南明书》”一句非俞樾《春在堂随笔》原文,实乃王葆心在案语中所说。谢国桢明确指出自己“未见”该书,显系从王葆心的书中转录。那么这部朝鲜人所撰《南明书》,究竟是乾隆年间朝鲜官员黄景源所撰,抑或是其他朝鲜人所撰,不得而知,但朝鲜人的南明史传入中国,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
四、抗战前“南明”史概念在民国的有限传播
民国肇建至抗战之前,虽然“南明”概念因政治禁忌消失而得以松绑,但也因为其反清象征意义的消失而未受到特别重视。当时“南明”概念仍然由那批革命党人及其弟子们坚持使用,如柳亚子和章太炎弟子朱希祖、孟森等人。
柳亚子在民国建立后,仍然坚持使用“南明”概念。1917年他31岁时,于“四月十五日,南社第十六次雅集于上海愚园。六月二十日,为南明杨维斗先生抗虏殉国忌辰,偕邑侯李暾庐及友人沈长公辈诣芦墟祠堂致祭”。(34)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第17页。1918年5月2日,“周芷畦斌招集陶庄之水月庵,南明遗臣陈卧子先生亡命地也”。(35)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第18页。
与柳亚子同一阵线的朱希祖,受老师章太炎的影响也倾向革命。1905年,他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习史,不仅拜当时在日本讲学的章太炎为师,还受到孙中山中国同盟会的影响,立志用南明历史,激扬民族大义。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积极响应,被推为海盐县知事。秉承清末革命党所推崇的“南明”意志,朱希祖在民国建立后,也一直在使用“南明”和“南明史”的概念,并以撰述南明史为己任。1931年,朱希祖发表《编纂南明史计划》,明确提出“南明史计划”并首次界定了“南明”的历史范围:“南明时代,指弘光、隆武、永历三朝而言。自崇祯十七年五月起至永历三十七年八月止(清顺治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44—1683年),约四十年。其间若鲁王监国,郑延平王等事,亦包括在内。”在此文中,他表示:打算以三四年时间,“拟用纪、传、表、志旧法”,编纂成大约六七十卷的南明史。(36)朱希祖:《编纂南明史计划》,朱希祖著,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38、341页。朱偰在《先君逖先先生年谱》中透露,1937年6月,朱希祖始“拟阅南明史,先融其全局史事,以备撰《南明史》,亦作笔记以记心得。时搜集南明史料,已至七百余种,方有意于《南明史》之撰著,而卢沟桥事变亦将作矣”。(37)转引自中华书局:《南明史·出版说明》,钱海岳:《南明史》卷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页。
与朱希祖在北京大学共事(1931—1932年)的孟森,也传播“南明”概念并讲授“南明史”课程。孟森与朱希祖一样,同属于革命党人。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放弃了君主立宪立场,响应革命,被推为共和党干事。他的抗清立场,在揭露《清实录》对相关记载进行粉饰的问题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38)参见谢贵安:《民国学者应用、整理和研究〈清实录〉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因此,与朱希祖一样,孟森也接受了清末革命党人倡导的“南明”概念,并在大学讲堂上大力讲授“南明史”。1931—1937年,孟森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课时,编写了《明史讲义》,其第七章就叫《南明之颠沛》。孟森使用“南明”概念,虽说受到了清末革命党人的影响,但也是他自己深思熟虑后的结果。他指出:“《明史》成于清。清入北都,早正位号,即不以明后为有国家之传统。自古征诛得国,如汉之于秦,明之于元,为民除暴,无须假借于所胜之朝。元之于宋,与清相类,其于宋后,犹列二王于瀛国公之次,附本纪之末,明乎其为宋之君也。清历世为明属,受官借势,并于急难时赐居边内以保存之,其与明,较元之与宋有间。至其修史,乃深没南明,颇为人情所不顺。当《明史稿》成时,南明三主,已援元修《宋史》例,止称三王,然不次于本纪之后,而特于诸王传之外,特辟《三王传》,自为一卷,犹见其与寻常诸王不同。至正史成,而三王各附入其始封之王后,为其嗣王,位置与他嗣王等,则更掩其保明遗统之迹矣。今特矫而正之,叙事虽不能详,名义要不可终晦也。”(39)孟森:《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2页。孟森是最早以“南明”为专题在大学讲课的教授之一。孟森接受“南明”概念,还见于他在1936年7月16日发表的《南明永历帝致吴三桂书跋》一文的题目上,明确使用了“南明”一词。(40)孟森:《南明永历帝致吴三桂书跋》,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57期,1936年7月16日。后收入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6-88页。
受清末革命党借南明以反清的影响,民国学者在宣传南明抗清英雄时,顺理成章地使用了“南明”概念。1926年,陈乃乾、陈洙编成《徐闇公先生年谱》。徐闇公即徐孚远的字,为明末清初松江华亭人,先后跟随南明唐、鲁、桂三王抗清。该年谱后有姚光写的跋语,称徐孚远“刻意光复;昊天不吊,赉志以殁”,考察其生平,“参预义旅、从亡海外,荐绅耆德之避地者,亦皆奉为祭酒,与南明之关系盖不亚于郑延平王及张尚书焉”。又说:“先生往矣,精神自在天壤。百世以下,读者可以想望其风旨,而亦藉以考见南明二十余年之文献矣。”后题:“中华民国十五年(岁次丙寅)孟夏之月,后学金山姚光谨识。”(41)陈乃乾、陈洙编:《徐闇公先生年谱》“附录一”《交行摘稿》姚光跋语,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 :《台湾文献丛刊》第123册,1961年,第87-88页。此跋中两处提到了“南明”概念。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至20世纪30年代,“南明”一词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流行。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直接著录钱绮的《南明书》。1930年,范希曾在为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作补正时,在《杂史第六》之《明季北略》下增补:“元和钱绮《南明书》三十六卷,未刊。”(42)(清)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1933年所修的《吴县志》也著录曰:钱绮“三十以后,按明季事实,著《南明书》三十五卷”。(43)曹允源、李根源纂:民国《吴县志》卷六八下《列传七·钱绮》,《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12册,第10页。谢国桢在1933年问世的《晚明史籍考》中,亦有著录:“《南明书》三十六卷,清元和钱绮映江撰。按绮,字映江,号竺生,元和人,清诸生,熟明季遗事,著《南明书》,咸丰中卒。是书屡为傅以礼等所称,惜未见。”(44)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第477页。虽然钱绮撰写《南明书》是在文网渐宽之时,但仍然触犯时忌,故其书并未流传。民国时期,对此书广加介绍,则反映禁忌无存。第二是广泛使用“南明”概念。1934年刊印的龙顾山人郭则沄所纂的《十朝诗乘》,下面两篇的标题《顾宁人咏南明史事》和《南明二贤士》均使用了“南明”概念。(45)龙顾山人纂,卞孝萱、姚松点校:《十朝诗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2页。第三,后起的学者开始关注南明史籍并撰写南明史。谢国桢(1901—1982)在1933年撰成的《晚明史籍考》中,对南明众多的野史进行了介绍和考订,被柳亚子誉为“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46)柳亚子:《续忆刦灰中的南明史料》,《文学创作》,1943年第4期,第38页。1936年,谢国桢又发表通俗性的《南明史话》一文。(47)谢国桢:《南明史话》,《逸经》(上海),1936年第1期。与此同时,钱海岳(1901—1968)开始从事南明史的撰写。1920年前后,他在北京朝阳大学政治经济科读书,到父亲协修清史的清史馆探视时,与清史馆诸公冯煦、柯劭忞、缪荃孙、吴士鉴、陈伯陶等学者结识。诸公认为《明史》与《清史》都忽视了南明史的撰述,这使钱海岳萌发了编纂南明史的想法。1928年,钱海岳在南京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秘书时,得识南明史学者朱希祖。朱希祖在1913—1915年曾兼任清史馆编修,与钱海岳的父亲是同事。朱希祖将自己搜集到的南明史料借给钱海岳,两人商量南明史的体例和写法。钱海岳自述道:“尝晤朱君希祖,希祖固治南明史而未遑成书者,相与往复,上下其议论,并承假史材,颇窥羽陵、酉阳之秘。”(48)钱海岳:《南明史·义例》,第1页。遇到朱希祖,使钱海岳在南明史编纂事业上得到强大的助力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朱希祖发表的《编纂南明史计划》,“拟用纪、传、表、志旧法”,编纂成大约六七十卷的南明史。后来,钱海岳的《南明史》正是用纪传体撰写的。
“南明”概念的流行,使得南明史开始成为官方认可的研究课题,并成为一门专门的课程和可供研习的断代史专业。1931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的报告中,谈到“历史语言学”时,称设在北平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分三组,其中第一组中“其属于个人研究的”共有九个方面,第九便是“搜访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史料,编纂南明史及南明史的专题研究”。(49)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5页。这是朱希祖研究方向所产生的影响,因为朱希祖就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同年,清华大学开设了南明史课程。据杨凤起所撰《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课程概状(1931)》之“本年新增之课程”中有“南明史,朱希祖,全年四学分”。(50)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 1912-1949》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747页。这是有据可考的中国大学开设南明史课程之始。朱希祖在清华大学开设南明史,比孟森在北京大学讲授明史中“南明之颠沛”,还要专业。1935年5月,新月派后期诗人、徐志摩的学生方玮德于北平病逝,终年27岁。“诗人临终前的一段时间,弃诗而准备攻读南明史了,因此他留存的诗作不多,在中国新诗史的影响不大”。(51)姜德明:《书叶丛话——姜德明书话集》上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看来,南明史的吸引力远大于方玮德对新月派诗的追求。
总之,由于清朝灭亡,“南明”禁忌消失,但借南明以反清的动力亦随之消失,因此“南明”概念虽然仍在流行,甚至在个别学校进入课堂,但并没有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五、抗战引爆“南明”史的研究和史学书写
“南明”史概念迅速被传播并为人们所接受,与抗日战争的爆发有直接的关系。1937年的“七七事变”引爆了南明史家加紧研究和撰述南明史的激情,促进了南明史家队伍的形成。经过南明史家的努力和宣传,“南明”史概念风行中国,一时间成为全国皆知的显学,也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史学史专著开始对南明史学展开历史书写。
抗战前,柳亚子、朱希祖等南明史家,均在推广“南明”概念和南明史,也曾做了一些著书的准备,但都没有大规模地展开研究工作。抗战的爆发激发了他们的斗志,开始加速南明史的研究,因此形成了南明史研究的专业队伍。
南明史研究队伍的排头兵,当推柳亚子。他对“南明”概念进行了界定:“所谓南明的范围,是从公元一六四四年即明历崇祯十七年甲申五月三日弘光帝监国南都起,到公元一六八三年即明历永历三十七年癸亥八月十三日汉奸施琅入东宁,延平幼王朱克塽出降为止,共计四十年。这四十年的历史,正是汉人和鞑子斗争的历史。这四十年间统治汉族的代表者,是南明三帝和延平三王,还有一个旁生侧挺的鲁监国。”同时指出:“南明史料这个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52)柳亚子:《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经过》,《大风半月刊》第82期,1941年1月5日,第2685-2692页。这是继朱希祖之后,又一次较为系统地对“南明”所做的界定。二人都主张南明有四十年的历史。柳亚子有自己的南明史研究计划,坦称自己所辑的《南明史纲》只是未来计划的《南明纪年》的初稿,而编年体的《南明纪年》与纪传体的《南明史》和纪事本末体的《南明纪事本末》这南明史三书,则是自己未来的奋斗目标。(53)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页。他还提出了南明史研究的方法问题,在《致胡朴安》信中坦陈自己用的是旧方法,是准备为“将来用新方法研究南明历史之人”提供方便。(54)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第210页。柳亚子从1939年开始在上海整理南明史料,在自述中称:“我整个地做南明史料研究的工作,开始于一九三九年即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夏天的。这时候,蛰处在上海的活埋庵中。”(55)柳亚子:《还忆刦灰中的南明史料》,《文学创作》,1942年第3期,第44-49页。由于受到日军的威胁,柳亚子于1940年12月逃到香港,一年后又逃难桂林。来到西南地区,当年的南明故地,使他对南明史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一直将“南明”作为规范的学术术语,并继续从事南明史的写作,还把自己笔名取为“南史”。(56)郑逸梅:《世说人语》,北方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1943年5月27日,柳亚子在桂林致信沈雁冰,声明“弟决计暂不来渝……现拟在此搞南明史”。(57)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第278页。他与桂林名士朱荫龙共同起草了一份《〈南明史〉编纂意见书》,并附有《南明史》拟目。(58)柳亚子、朱荫龙同拟:《〈南明史〉编纂意见书》(附《南明史》拟目),《大千》,1943年第1期,第38-40页。柳亚子坚持南明史史料搜集与撰述的信念,使他获得了“南明史泰斗”的称号。(59)柳亚子:《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柳亚子著,郭长海、金菊贞编:《柳亚子文集补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与柳亚子在研究南明史上同享盛名的朱希祖,在抗战时,也在南明史的研究上有强烈的责任感。作为历史学家,朱希祖的危机意识较常人要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欲纂述南明史乘”。当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聘请朱希祖为文史研究所主任时,他认为“两粤为南明诸王兴兵抗满之所,适于搜集实地资料”,于是赴任。经过南京时,“顺道访朱明旧院遗址,搜求明季史迹”。在广东讲学时,“辄与南中人士,访古问奇,所得南明史料,及两广方志尤富”。1937年抗战爆发后,朱希祖随中央大学迁往四川。朱希祖的学术面很广,但“于萧梁及明季历史,尤悉力赴之”,研究“南明史,则成《明季史籍题跋》六卷”。当时史料分散,结果“萧梁、南明二史,不及卒业”。(60)本段所引,皆参见罗香林:《朱希祖》,中华学术院编:《中国文化综合研究——近六十年来中国学人研究中国文化之贡献》,华冈出版部1971年版,第310-329页。朱希祖在抗战时写的南明史论著有《南明韩王本铉考》(未刊)、《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文史杂志》第二卷第七八期合刊)、《南明三朝史官及官修史籍考》(《清华周刊》第三十卷七期)、《广州征访南明史料记》(《中国学报》第一期)。上述朱希祖的原著,皆使用了“南明”和“南明史”的概念。他已把它们当作标准的学术术语。
抗战时,翦伯赞(1898—1968)介入南明史研究。从1940年起,他先后撰写和发表了《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等论文,(61)翦伯赞:《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第111-130页;翦伯赞:《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翦伯赞:《中国史论集》第二辑,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年版,第274-297页;翦伯赞:《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中苏文化杂志》,1941年第1期,第65-70页;翦伯赞:《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中华论坛》,1945年第10-11期,第38-50页。旗帜鲜明地将弘光、隆武和永历政权称为南明史上的政府。翦伯赞的南明史研究,主要针对国民党右派借南明史、明末农民战争史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行径而展开,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引起了巨大的争论,获得了左翼人士的支持,但其部分论文也被国民党政府所扣压,不予发表。(62)张传玺:《〈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发表记》,《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在朱希祖、柳亚子、翦伯赞等南明史专家叱咤风云之际,有一位默默耕耘但做出了实实在在成就的南明史家,他就是钱海岳。1937年抗战爆发后,钱海岳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随身携带的《南明史》书稿幸未丢失。在重庆,他任职于开国文献馆,继续修改其书稿。1944年,岁在甲申,距明崇祯甲申年(1644)相距三百年整,钱海岳终于完成了《南明史》初稿,“定为百卷”。(63)参见刘桂秋:《钱海岳简明年表初编》,《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10期。因为要继续修改和增补,书并未付梓,故他在社会上一直默默无闻。
与钱海岳写书未出不同,徐安之1938年在广州便出版了《南明诸王的复国运动》(二册),(64)徐安之:《南明诸王的复国运动》,广州时代动向社1938年版。在南明史研究中鞭先一着。此书的现实目的一目了然,就是针对日寇侵华所做的历史回击。这种撰著南明史的目的,在抗战时的中国颇为普遍。
抗战时南明史家形成的队伍,虽分散各地,但彼此之间有联系,并相互帮助,共同研治南明历史。1943年初,柳亚子曾托汪东(旭初)带信向朱希祖商讨南明史问题。朱希祖收到信后,打算闲暇时逐条答复。1月13日,朱希祖写了《答汪旭初代柳亚子问南明史事书》约三四千字以作回答。(65)曹辛华、钟振振主编:《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第6册《汪东年谱》,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页。南明史专家队伍虽然政治倾向各有所偏,柳亚子、翦伯赞倾向中国共产党,朱希祖、钱海岳倾向国民党,但在借南明史研究以表抗日不屈之决心上,立场基本一致。
战时,中国史学史专著开始用“南明”概念称述南明史书,对南明史学展开历史书写。
1940年魏应麒撰写的《中国史学史》和稍后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66)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并无“南明”的概念和南明史学的位置。1942年,萧一山在《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中开始用“南明”概念指称南明史,指出:“清初杨陆荣撰《三藩纪事本末》,述南明诸王事迹,颇简要,然比之计六奇之《明季南略》、温睿临之《南疆绎史》、吴伟业之《鹿樵野史》、徐鼒之《小腆纪年》、王夫之之《永历实录》、陈湖居士之《荆驼逸史》等书则详略有间。南明稗乘,繁夥不可胜纪,大概皆明末遗民藉以寄托其故国之思者,此亦文字之狱屡兴之一要因也。”(67)萧一山:《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国立东北大学《志林》,1942年第3期。后收入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518页。这是在史学史论文中,学者首次用“南明”概念来指称南明史并涵盖南明史学。

金毓黻还关注了近代以来学者对南明史书的撰写情况:“近人无锡孙静庵(其名待考)拟撰《续明书》一百二十五卷,惜未卒业。仪征刘师培、顺德邓实皆欲作《后明书》,亦皆未成,(自注云:邓实《南疆逸史叙》,余向有《后明史》之志,因循中辍,旧友中志余之志者,其因循多如余,按旧友殆指申叔也。)师培且请章太炎先生预为之序矣。最近则有海盐朱先生希祖,搜获南明野史,多为珍本,实突过傅以礼所见,间有未著录于《晚明史籍考》者,先生尝言欲撰《南明史》,因循未果。”(73)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160页。金毓黻提到的近代南明史家有孙静庵、刘师培、邓实和朱希祖。
继金毓黻之后,顾颉刚于1945年撰写了《当代中国史学》一书,除简要介绍了钱绮《南明书》并指出“‘南明’一词即为钱绮所首创”外,还说:“戴望对南明史亦曾用力,欲作《续明史》,惜仅成传数篇。”(74)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编《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第10页。顾颉刚特别对当代的南明史研究给予了关注,指出:“南明史的研究,由于民族主义思想的刺激。在清末时,对于史料的收集与研究,已经有人着手,刘师培及邓实皆欲作《后明书》而未成,师培书已由章炳麟预为之作序。最近则以朱希祖先生用力最深。朱氏藏南明珍秘史料极多,曾在《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二卷七期上发表其编纂《南明史》的计划,惜其书未成,仅有论文:《史籍五种跋文》(《燕京学报》第三期),《南明史籍跋文》(《图书月刊》二卷四期)。”(75)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下编《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第94页。顾颉刚与金毓黻二人都没有提到远离陪都的柳亚子和默默撰述的钱海岳,但毕竟都从史学史的高度对南明史学做出了难能可贵的总结。
史学史专著是对中国史学进行总结的学术专书。它们对“南明”“南明史”概念的应用和南明史学的书写,促进了这些概念规范化、权威化的过程,加速了“南明”史概念的传播。
六、抗战时“南明”语境的形成与概念的迅速传播
抗战爆发后,由于日强中弱的现实,以及大片北方领土沦于敌手的局面,“大西南”成为中国抗战的后方,一批批中国知识分子从沦陷区流落此地。他们从时空环境上,敏锐地感受到“南明”阽危和悲壮的氛围,觉察到南明抗清的局面将“历史再现”,于是清末革命党人借南明以抗清的意识随即复活,不同的只是将抗清转向抗日,借南明的不屈以表示抗日到底的决心。加上前述南明史专家柳亚子、朱希祖、翦伯赞等人的影响,社会上形成了鲜明的“南明”语境,人们普遍地用“南明”或“南明史”来给明末清初的福、唐、桂、鲁四王历史打上烙印。黄裳指出:“大后方文化界当时均卷入‘南明热’中矣。”(76)黄裳:《劫余古艳:来燕榭书跋手迹辑存》,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西南联大的教授吴晗声称自己到昆明“原是抱着搜辑南明史料的大计划去的”,十年来“先先后后买了百十种书,几百份碑帖”为研究南明史做准备。他还说当时“过路游客,在百忙中还上昆明和贵阳的图书馆作(南明史)研究”。(77)黄裳:《来燕榭少作五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2页。在此背景下,“南明”和“南明史”概念便在大后方风行起来。
以对南明史料搜集和史书撰写最执着的柳亚子为中心,出现了“南明”及“南明史”概念向外辐射的现象,不断向其周围的朋友、学人传播。
文学家阿英(钱杏邨,曾用笔名魏如晦)接受了老朋友柳亚子的“南明”史概念。柳亚子于1940年12月16日在给阿英的《海国英雄》(四幕历史剧)写的《叙》中,将阿英所创作的历史剧,直接冠以“南明史剧”:“如晦先生有创造南明史剧四部——《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悬岙神猿》的计划。而我平常好谈南明史实,便接连不断的通信起来。”又称在他自己撰写的《南明后妃宗藩志》即将脱稿的时候,阿英“已把他的南明史剧第二部《海国英雄》修改完成”。(78)柳亚子:《柳叙》,阿英:《阿英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此后,柳亚子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杂谈阿英先生的南明史剧》的文章,把阿英编写的历史剧称为“南明历史剧”。(79)柳亚子:《杂谈阿英先生的南明史剧》,《文学创作》,1942年第2期,第52-57页。阿英本来没有明确的“南明史”概念。他的《碧血花》又名《明末遗恨》,而非《南明遗恨》,(80)杨义主笔:《中国现代文学图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77页。但经过柳亚子不断地灌输“南明”概念,他也就接受了这一词汇。在1942年2月剧本《碧血花》出版时,阿英题赠于伶之诗即云:“十年生死不相违,探史南明费品题。忧国忧民频掬泪,‘璇宫’深处血花飞。”(81)上官缨:《上官缨书话》,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8页。
柳亚子“南明”史概念,还影响到著名文人郭沫若。1942年7月7日,郭沫若在他的《和亚子》一诗中咏曰:“欲读南明书已久,美人远在海之湄。薪樵岂有伤鳞意?大道如天未可衰。”后人在注释中说道:“南明书:指《南明史》。郭沫若在《柳亚子诗词选·序》中说:‘亚子先生……曾经有志于《南明史》的撰述。’”(82)王继权等编注:《郭沫若旧体诗词系年注释》上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0页。1942年7月18日,郭沫若在致柳亚子的信中称:“《南明史》深望早日杀青。著述如战机,似乎争取时间为要着。”(83)郭沫若:《郭沫若致柳亚子》,《戏剧春秋》,1942年第4期。转引自曾健戎、王大明编:《〈屈原〉研究》,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5年版,第225页。
柳亚子撰《南明史》一事,经过杂志社同仁的谈论,“南明史”概念被编辑们所接受。据题名为符号的人回忆:香港沦陷,柳亚子来到桂林,“我与陈(迩冬)在桂林编辑出版《大千》杂志,就商请柳亚子先生将他写的《南明史稿》交一部分给《大千》发表,柳慨然应允并很快赐了稿”。(84)符号:《柳亚子不识自己的字》,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第53辑《纪念武汉市文史研究馆建馆四十周年专辑》,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版,第51-52页。
柳亚子“南明”和“南明史”的概念,还影响到抗战时的中学教师。据时为桂林某中学教师的彭久回忆:“同事们互相勉励,为抗战而写文章。同事劝我取材于南明史。我说没有资料。又有人说,柳亚老研究南明史有名,正好也来桂林,快去向他请教并愿意立即陪我去。”于是,我们拜见了柳亚子,“向他请教南明福王时期陈子龙、夏元淳父子抗清的史实”。彭久第二次访问柳亚子,得知“亚老有十二本史剧的伟大计划。我们写了福王时期抗清的《江左少年》,《吴日生》,写了张煌言、张名振、郑成功抗清的《赵琼华》,写了桂王时期李定国抗清的《翠湖曲》。全凭亚老的《夏完淳传》、《吴日生传》和搜集到的几本小书。写作中有不明了的地方,就去请教亚老”。(85)彭久:《几时商略罄生平——回忆柳亚子先生》,《文教资料简报》,1985年第4期,第16-17页。在柳亚子的影响下,以彭久为中心的桂林中学的教师们,形成了研究南明史、编写南明史剧的风气。
受到柳亚子南明史概念影响的还有广东惠州人廖辅叔。廖辅叔(1907—2002)在“1943年,任柳亚子主持的‘南明史编撰委员会’秘书,参与撰稿”。当时“为生活所迫,以卖稿为生,还教授私人学生”。(86)何谦编:《幽兰——古琴家李仲唐口述实录》,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朱希祖与柳亚子有所不同,后者影响的是学术界,而前者的“南明”史概念还影响到了官方。朱希祖偏向国民政府的立场和优势,使他在抗战经费困难之际,向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史馆的议案,竟然获得通过。国史馆直属国民政府,负责编纂中华民国国史史料。然而,在一份“全宗号34”的《国史馆(1940—1949)》档案中,竟然藏有《南明史稿》。(87)施宣岑、赵铭忠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简明指南》,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65-66页。看来,朱希祖将南明史稿的修纂也纳入国史馆的工作任务中。
朱希祖倡导的“南明”史概念,也影响了他的儿子朱偰、女婿罗香林。1944年,朱希祖去世后,朱偰撰《先君逖先先生对于史学之贡献》一文以志纪念,文中广泛使用其父提倡的“南明”或“南明史”词汇。朱偰将其父的学术成就分为十二类:“史学原理、史实发现(文物史迹)、史籍考订、史籍辑佚、解决历史疑问、史事辩证、中国文学史、中国经济史、断代史(尤其是战国史、萧梁史、南明史)、目录学、氏族学、金石学。”(88)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4页。朱偰在介绍朱希祖“史籍考订”方面的成就时指出:“先君致力南明史料搜集,凡三十年,抄本秘笈,无不悉力致之……惜干戈扰攘,未能整理成书,然史籍之考订,已有发表者不少。其南明史籍题跋,约五十篇。”在“断代史研究”中,朱偰指出:“先君对于战国史、秦史、萧梁史、南明史,更有专门之研究。”(89)朱偰:《先君逖先先生对于史学之贡献》,《东方杂志》第40卷第16号,1944年。后收入徐建荣主编:《孤云汗漫——朱偰纪念文集》,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44-251页。子承父学,朱偰成为朱希祖“南明”史概念的重要传播者,并明确将“南明史”作为断代史。顾颉刚在朱希祖去世后,写挽诗道:“平生心事南明史,历劫终教志不灰。”(90)顾颉刚:《顾颉刚挽诗》,朱希祖:《朱希祖先生文集》(第六集),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总第4382页。顾颉刚接受了南明史为朱希祖终身事业的学界共识。罗香林在给岳父编好文集后,专门撰文介绍朱希祖的学术成就,文中大量使用了“南明”和“南明史”概念以作概括。
在知识分一批批退向西南地区、南明史专家对“南明”史概念推毂的背景下,“南明”认知几成共识。
黄裳面对知识界西迁,感时伤事,敏锐地体察到南明的“历史再现”,便“对南明史事给予了特别的关怀”。(91)黄裳:《劫余古艳:来燕榭书跋手迹辑存》,第58页。抗战时,江西人欧阳祖经“有一个学术研究的兴趣点是南明史。南明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年代。国难当头,天地玄黄,朝代更迭之时,往往是考验知识分子文人气节的时候。他研究的是南明史,实际上真正关注的是抗战。是一个学者在八年抗战中对国家前途的一些思考。南明史的研究,是与现实相响应的”。欧阳祖经关于南明史的著作,有《南明赣事系年录》和《王船山黄书注》等。(92)张国功:《温情与敬意——一个出版人的编余零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页。他也是一个将南明直接用在书名上的民国学者。“南明”史概念不仅在“大后方”西南地区流行,而且在其他地区也屡屡出现。1944年7月,湖南宁乡沦陷的消息传到陕北,谢觉哉写了《闻日寇窜宁乡》的《满江红》词,其中有句子曰:“中国若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杨度语),从明末直到而今,英雄几许!百万农军北伐时,十三雄镇南明史,岂是那十年奴化,能抑止?”(93)宁乡人民革命史编写组编写:《宁乡人民革命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157页。词中就使用了“南明史”的概念。南明史家柳亚子虽然逃离了上海,但“南明”史概念仍然在那里延续。1940年2月13日,潘景郑“自沪上青阁书肆”购得旧抄本《明季野乘》五种,随即写了题跋,称:“综此五种,皆志士眷怀故国而作,俱足补南明史事之遗。”同时,他打算“藏此以备他日南明史辑之需”。(94)潘景郑:《著砚楼书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9页。
南明史专家的努力,影响到官方对“南明”史的态度。抗战时,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时任该校教授的苏雪林,于1941年“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委托编写了历史传记集《南明英烈传》。这部集子歌颂了17世纪抗清复明的仁人志士。随后,她又以此为素材,写成南明历史小说集《蝉蜕集》,1945年由重庆的商务印书馆出版”。(95)方维保:《国家情怀:现代知识分子的成年镜像——论苏雪林的战时创作》,《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7页。“南明再现”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交织形成的焦虑,并非仅仅出自学术界,官方显然也有相同的感知。
抗战时,具有特殊含义的“南明史”在大学课堂上得以继续讲授。因日本入侵而西迁贵州的浙江大学就开设了南明史。1940年8月,夏定域应竺可桢之聘,赴遵义浙江大学文学院任教,“讲授《尚书学》、《南明史》、《清代学术概论》、《史部目录学》等课”。(96)夏家鼐:《夏定域与〈四库全书〉》,杭州市政协文史委编:《杭州文史丛编·文化艺术卷》,杭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浙江简志之二·浙江人物简志》下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1页。在浙江大学暂栖之地遵义开设南明史,其现实意义十分明显。而北平的燕京大学,在20世纪40年代似乎也开设了南明史的课程。据周汝昌回忆,当时燕京大学留学生林阿释(Arthur Link)和他的一位好友在校外一同租房居住,“其友名叫James Parsons,留学研究南明史”。(97)周汝昌:《外国朋友林阿释》,《师友襟期》,北京出版社2019年版,第395页。这位詹姆士·帕森以研究南明史为务,表明当时燕京大学开设了南明史的课程。无论是西南后方,还是北方沦陷区,讲授“南明史”实际上都表达了中国人抗战不屈的决心。
综上,抗战时,颇类南明以西南为根据地的时局,以及南明史家的推波助澜,对流落西南和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接受“南明”概念,普及南明历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七、抗战后政治环境的消失与“南明”史热的退潮
抗战后,借南明艰难处境以自警、南明不屈以抗争的政治环境突然消失,“南明”概念的使用和南明史的重视也随之降温。当然,“南明”及南明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可能全然消失,作为抗战时的记忆也无法抹去,仍然在民国末期流传和应用,但已明显处于退潮状态。
那批自清末即已立志修史的南明史家,其中朱希祖已经病逝,钱海岳依然没有发声,只有柳亚子仍在倡导南明史的编纂和研究。1945年11月9日,他致信新任上海通志馆馆长胡朴安,明确提出修南明史的愿望:“弟本拟恢复志馆,延揽人才,以修创南明史为副业。今志愿已虚,惟有请兄于志馆位置朱琴可、尹瘦石两兄,给以干薪,庶得借志馆之名,修明史之实,挹彼注此,同为文化前途而工作。”(98)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第327页。在这里,“南明史”已经成为柳亚子的事业,甚至想借上海通志馆来实现南明史的编纂计划。
对南明史颇为敏感的黄裳,战后回忆抗战时看过的南明剧目,仍然感叹不已。1947年,他在文章中回忆:“《桃花扇》究竟不失为一部成功的历史剧。现在虽然也有不少写南明史事的剧作,然而没有一部能超越它。”(99)黄裳:《秦淮拾梦》,江苏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42页。看来他已接受了柳亚子当年给明季剧目赋予“南明史剧”的概念。
黄裳对南明史的缅怀,又引起了明史专家吴晗的共鸣。1948年3月13日,吴晗在清华园给黄裳的书作序,称黄裳“特别对于南明史事关怀”,而吴晗自己原本也是“抱着搜辑南明史料”的目的前往南明旧都昆明的。(100)黄裳:《来燕榭少作五种》,第332页。同年,吴晗在给黄裳的《旧戏新谈》一书写序时,指出:“作者似乎对南明史事还在继续探寻。”(101)黄裳:《榆下怀人》,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107页。以上都以“南明”作为学术术语。
曾先后担任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国立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兼职贵州文献征辑馆的李独清,于1947年在编纂《贵州文献汇刊》时,将《香草园日记》选入,写了一篇《香草园日记序》。在这篇序中,李独清明确使用了“南明”史概念:“晚明杨文骢有《台荡日记》,《祁彪佳日记》多至十余卷,记崇祯、弘光两朝事甚详,治南明史者,视为瑰宝。”(102)李独清:《李独清文史论文选》,贵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86页。
光复后的台湾在大学课堂开设了南明史。台北市人杨云萍(本名友濂,1906—2000),曾留学日本,毕业后回到台湾。1945年,杨云萍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参议、台湾编译馆委员。1947年,他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明史、南明史、台湾史、历史哲学等课程。(103)周川:《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240页。在郑成功父子力撑到底的南明抗清基地台湾讲授南明史课程,一定是别有滋味。
抗战后的“南明”概念及其背后的南明史,显得云淡风轻,那往日的热闹,已随风而逝。对南明史研究繁盛状况的恢复和超越,还要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之后。
结 语
指代南明断代史的“南明”概念,在康熙年间陈鼎的《东林列传》中最先出现,但直到道咸间钱绮用作《南明书》的书名之前,都无人再用这一词汇。清廷统治的松动为钱绮应用“南明”概念作书名提供了契机,但同时代的人虽然叙述南明史事,却仍不敢提到“南明”一词。在东邻,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却对清朝排斥南明做出反弹,乾隆朝时黄景源率先以“南明”为书名,撰成《南明书》,同时代人成海应也作《〈南明书〉拟稿》,但前者不传,后者未成。至清末,中朝两国都兴起抗清运动,朝鲜人郑乔将其《南明史纲》寄赠当时已有借南明以反清之意的章太炎,增强了清末革命党人的“南明”意识和抗清斗志,使“南明”史概念得以传播开来。清朝灭亡后,民国肇建至抗战之前,虽然“南明”概念因政治禁忌消失而得以松绑,但也因为借以反清因素的消失而未受到特别重视。抗战爆发,促进了柳亚子、朱希祖、钱海岳等南明史家队伍的形成,引爆了他们对南明史研究和撰述的激情,中国史学史也展开了对南明史学的历史书写。由于大片北方领土沦于敌手,西南成为中国抗战的后方,一批批知识分子流落当地,敏感地觉察到南明抗清的局面将“历史再现”,加上南明史专家的推波助澜,全社会形成了浓厚的“南明”语境,普遍使用“南明”或“南明史”概念来谈古论今,使得这些概念盛行一时。抗战结束后,南明史的政治意义消失,“南明”史概念的应用和传播随之退潮。然而,“南明”概念和南明史学已成为不可磨灭的史学现象,不仅进入大学课堂代代相传,而且成为研究课题常研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