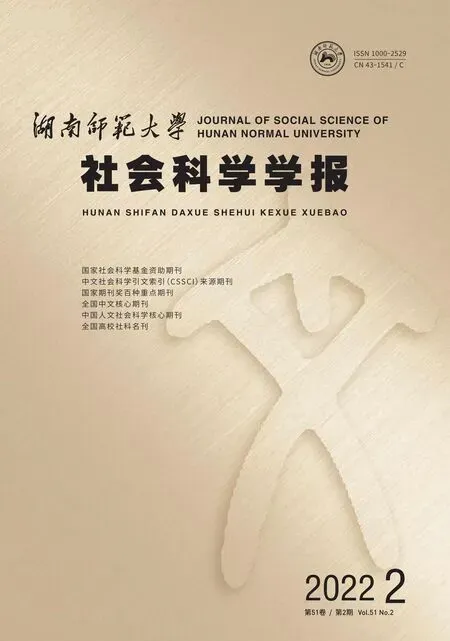清末民初国文教育与“龙学”发展新论
吴 海
随着对晚清民国学制改革研究的深入,学界渐渐知晓“中国文学”一科在成立之初的复杂情形①。遗憾的是,这场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国文教育观念对《文心雕龙》研究的推动作用,尚未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早在嘉道年间阮元与桐城派激辩文章正宗时,《文心雕龙》就因其独特的骈散属性成为两派论争的焦点;1904年学制改革时,张之洞殚精竭虑地弥合骈散、提倡宗经、重视文用,其主导的《奏定大学章程》中“中国文学研究法”与《文心雕龙》的高度暗合,或是“龙学”兴起最早的推手;在新式学校国文教育的顶层设计与具体实践中,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人申论不同的文学主张、提出不同的文学学科建设方向,《文心雕龙》是他们界定“文学”范畴时共奉的经典依据。可以说,“龙学”的演进贯穿了清末民初学制改革的始终,见证了国文教育由守成走向趋新的数次变革,这是“龙学”确立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历史环节。
一、国文教育改革中“龙学”的影响
作为清末民初龙学兴起的先声,清嘉道年间阮元、刘开等人围绕《文选》与《文心雕龙》展开了文笔之辨和骈散之争②。迄于清末,作为学制改革担当者之一的张之洞,其所面临的时局远比阮元时代要复杂得多。“国家”意识下,传统辞章学内部的派系亟须调和;西风东渐下,新式学堂“中学”与“西学”的平衡也要费一番思量。张之洞先后担任过四川、两广、湖北等地学政或督抚,又临危受命,制定全国性学制改革的纲领文件《奏定大学章程》,深度参与这一历史进程。种种迹象表明,张之洞主导的学制改革,确定文学教育规范,与随后《文心雕龙》研究的异彩纷呈,存在某种因果关联。
张之洞与《文心雕龙》的联系,最早可追溯到同治十三年(1874)其任四川学政时的《輶轩语》。其中 “古文、骈体文”一节有云:“试场策论用散文,今通谓之古文。对策间有用骈文者,但不常有,惟词馆应奉文字用之耳。然骈、散两体不能离析,今为并说之。”[1]较之阮元倡导骈体正宗,与古文派掀起文争,张之洞旗帜鲜明地主张“骈、散两体不能离析,今为并说之”,其不分骈散的态度尤为坚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桐城派刘开虽亦看重《文心雕龙》,然其《书〈文心雕龙〉后》评价韩愈与刘勰曰:“昌黎为汉以后散体之杰出,彦和为晋以下骈体之大宗,各树其长,各穷其力”[2],可见,刘开以韩愈为散体之宗,以刘勰为骈体之宗,并未将《文心雕龙》视作弥合骈散之工具。相比之下,张之洞《輶轩语》则强调 “梁刘勰《文心雕龙》,操觚家之圭槷也,必应讨究”[1],“操觚”出自陆机《文赋》“或操觚以率尔”,意为“写作”,“圭槷”则指测日影之圭表。这使得《文心雕龙》终于摆脱了各派文论配角、注脚的宿命,第一次被明确为所有文章家应共同遵守的规范,这应是龙学兴起的重要转折。
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进京奉旨参与《奏定大学章程》。据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所记:“今日之《奏定学校章程》,草创之者黄陂陈君毅,而南皮张尚书实成之”,“观此二科(笔者按:经学、文学)之章程内,详定教授之细目及其研究法,肫肫焉不惜数千言”[3],又据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记载,“经学各门,及各学堂之中国文学课程,则公手定者也”[4]“名曰章程,实公晚年学案也”[4],可见张之洞对《章程》制定起到了主导作用。就《奏定大学章程》与龙学的关系而论,其 “历代名家论文要言”的课程明确指出:“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5],这是官方学制重视《文心雕龙》最直接的证明。更重要的是,《奏定大学章程》中“中国文学研究法”与《文心雕龙》的高度契合,才是引燃此后《文心雕龙》研究的真正导火索。两者的近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注重文体分类、文体源流、专家文论
“研究法”延续《輶轩语》以来的辨体意识,《略解》第二十二、二十三条论辞赋、制举、公牍以及记行、记事等文体的古今异同,并强调“皆为文章家所需”;第八至十五条,主张应考察周秦至今的文体;第十五、十六条提倡注意骈散“古合今分之渐”,骈文“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第十九条凸显“骈散各体文之名义施用”。据统计,这篇不过千言的《略解》中,“文体”“各体文”等词出现了近二十次,可见其对“文体”概念的重视。同时,其第二十条“古今名家论文之异同”等,亦与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中“论文述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6]的写作主旨相吻合。通过强调“辨体”与“各体文”特征来化解骈散两派宗派之争,体现了张之洞深谋远虑之构想,也对日后“国文”教学与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注重五经与文学的关系
对于新式学堂 “中国文章”课程的重点是应“宗经”还是“重文”,张之洞与吴汝纶所代表的不同力量之间曾产生过分歧[7]。阮元的《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早早强调“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8]。不过,晚近桐城派在平衡经文时又有尊《古文辞类篹》过甚之嫌,如1898年吴汝纶在《答姚慕庭》中即认为:“后日西学盛行,六经不必尽读,此书决不能废。”[9]唯独张之洞对“中国文章”的定义,则特别强调文章与经史之关联,1902年其在回复张百熙的信件中明确指出:“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韩昌黎云‘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今日尤切。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1]《略解》于各朝代文体、骈散等文体之首,特列第五条“群经文体”,颇与刘勰《序志》“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6]之定位一脉相承。
(三)注重文章“体性”、 “文用”
《略解》第一、二、三条强调古文字、音韵、训诂的变迁,是为朴学之风的延续,也与《文心雕龙》中《练字》《声律》等篇契合;第四、二十七、二十八、三十四、三十九条强调文章与治化、世运升降之关系,其宗旨与《时序》相近;第五、三十五强调修辞立诚、有学无学对文章的影响,其说与《程器》《才略》相近。在文章风格方面,“研究法”第三十五条反对险怪、纤佻、虚诞、狂放、驳杂等妨害“世运人心”之作, 第三十六条反思六朝和南宋溺于好文之害,这亦与刘勰“折中观”遥相呼应。刘勰《程器篇》“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6]之说,成为新式学堂“中国文章”教育的最高理想,自是情理中事。
《奏定大学章程》尊崇《文心雕龙》的倾向,无疑对龙学的兴起有推波助澜之效。学界通常将1917年刘师培、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课程作为“龙学”确立的起点③,实际上,早在1904年《奏定大学堂章程》颁布之后,《文心雕龙》研究的集结号就已吹响: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专辟《刘勰〈文心雕龙〉创文之体》一章是在1904年;刘师培撰《文说》“篇章分析,隐法《雕龙》”是在1905年;章太炎旅日期间讲授《文心雕龙》是在1908年;李详补注的《文心雕龙》也是在1908年;而桐城派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发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龙》”,其前身《国文学》则可追溯至1909年。此外,还有1905年龙伯纯的《文字发凡》将《文心雕龙》引入修辞学,叶瀚的《文心雕龙私记》、林纾的《春觉斋论文》等专论不断涌现。这一时期涉及《文心雕龙》的研究较多,也不同于此前以校勘、评解为主的著述形式,而以教学讲义占据多数④。对于这一现象的归因,不能仅仅视作龙学兴起前的“自觉”,也不只是刘勰成书以来不断诠释、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有1904年晚清学制变革对《文心雕龙》研究的推动作用。
关于1904年晚清学制改革与“龙学”推进的因果关系,扬州学派的《文心雕龙》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佐证:刘师培将《文心雕龙》引入“文笔说”也始于此时。1905年,刘师培由沪避走台湾,又辗转逃匿至浙江嘉兴“平湖大侠”敖嘉熊家,协助处理温台处会馆事务[10],在此期间著述《文说》。《文说·序》云:“幽居多暇,撰《文说》一书,篇章分析,隐法《雕龙》。”[11]又曰:
昔《文赋》作于陆机,《诗品》始于锺嵘,论文之作,此其滥觞。彦和绍陆,始论文心;子由述韩,始言文气。后世以降,著述日繁,所论之旨,厥有二端:一曰文体,二曰文法。《雕龙》一书,溯各体之起源,明立言之有当。体各为篇,聚必以类,诚文学之津筏也。[11]
刘师培在《文说·序》中梳理了自陆机《文赋》以下的“论文之作”,尤推《文心雕龙》辨体、论文法之功,誉为“文学之津筏”。《文说》共《析字》《记事》《和声》《耀采》《宗骚》五篇,其中,《宗骚》以骚体“撷六艺之精英,括九流之奥旨,信夫骈体之先声,文章之极则矣”[11];《耀采》一篇则曰:“由古迄今,文不一体,然循名责实,则经史诸子,体与文殊,惟偶语韵词,体与文合”[11],均是延续扬州学派的文论主张。但我们更应重视两处新变:一是《记事》一篇[11],这篇颇受《文心雕龙·史传》与章学诚《古文十弊》影响的文论,显然已不同于阮元、阮福之竭力将“记事之属”驱出文囿;二是以《文心雕龙》“溯各体之起源,明立言之有当……诚文学之津筏”,这种“昭体”而“晓变”的意识,在阮氏“文笔说”那里是不曾有的⑤。
二、章太炎的文学观念、教育实践及其与“龙学”关系
在晚清民国学制改革如火如荼的同时,有关文学观的论争也是剑拔弩张。此前的研究很少关注文学观与文学教育实践的具体关联,但就民国学者的文学观而言,绝非水中月、镜中花,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章太炎的“广义文学观”、刘师培的“韵文学”主张以及黄侃等人推崇的 “情辞说”,都代表了此后文学学科建设的不同方向。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民国文坛出现的《文心雕龙》与不同文论经典的组合,支撑着不同的文学主张,呼应着不同的国文教育体系,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里先探讨章太炎的“广义文学观”与“龙学”及国文教育的关系。
章太炎“广义文学观”可看作是张之洞文学教育思想的延续。自1905年起,身为扬州学派殿军的刘师培将乡贤“文笔说”引入到现代“文学”内涵外延的讨论之中,阮氏“文笔说”所引申出的“情辞”“翰藻”迅速成为新旧学者确立“文学之界义”的争论热点。1906年,章太炎针锋相对,发表《论文学》的演讲,不遗余力地对“文笔说”进行批判[12]。若仅从文学观来看,章太炎提倡的“广义文学观”日后渐渐冷落,处于下风。章太炎弟子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叙》即云:“余今日之主张,已大不同。盖此编所讲,乃广义之文学;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13],此书印于民国九年(1920),可见十多年间“文学”观念的转变。
我们在追溯章太炎“广义之文学”之意义时,不可忽视其与清末“国文教育”实际形态的联系。在当时的学制改革中,作为“学科”概念的“文学”本身就存在广义狭义之分。1898年,梁启超依照“泰西日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类,参以中学”,草拟《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其中“文学”与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等并为“溥通学”分支[5]。梁启超的“溥通学”是集合了传统经史子集四部的概念,隶属其下的“文学”则约等于书院的词章学,是为狭义的文学概念。与此有所不同,1902年张百熙《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大学分科”虽然也“略仿日本例”:“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学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 其中“文学”一科又分为七: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5]。这里的“文学科”囊括经史诸子掌故等学科,是取“广义文学”范畴。前后两学制中“文学”界义之“小大之变”,不可不察。
在此基础上,我们重新回顾章太炎的文学观,可以窥见其与张之洞骈散结合论的渊源。《文学总略》云:“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今欲改文章为彣彰者,恶夫冲淡之辞,而好华叶之语,违书契记事之本矣”[14],章太炎强调文章乃“书契记事之本”,其论文之界域为:
鸿儒之文,有经传、解故、诸子,彼方目以上第,非若后人摈此于文学外,沾沾焉惟华辞之守。或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为文也。[14]
在此,“沾沾焉惟华辞之守”是指文选派,“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为文”则是桐城派,可见章太炎勾勒的“广义文学观”界域,远远超越了桐城、选学两派总和,与《奏定大学章程》“中国文学研究法”弥合骈散的指向一致。章太炎又强调“鸿儒之文,有经传、解故、诸子”,也是延续“研究法”规划的“宗经”“重视文用”的总体思路。
在文论经典体系的建构中,章太炎提出了《论衡》与《文心雕龙》的组合。对于阮元、阮福以《文选序》为经典依据,章太炎颇为不以为然,其说云:“《文选序》率尔之言,不为恒则”[14]“阮元之伦,不悟《文选》所序,随情涉笔,视为经常,而例复前后错迕。”[14]他提出文论经典“惟《论衡》所说略成条贯,《文心雕龙》张之,其容至博”[14],可见《论衡》与《文心雕龙》的组合,成为章太炎文论体系理论的支撑点。
章太炎为何要以《论衡》与《文心雕龙》相结合,强调奏记之文、经解之文与文学之文的关系呢?一是紧扣了当时张百熙、张之洞等人所规划的“文学科”的设想。张之洞《劝学篇·守约》所列“辞章学”,仅限于奏议、尺牍、记事,其《奏定大学章程》“中国文学研究法”则强调“宗经”“文用”,张之洞文教政策的这些层面,都为章太炎所传承;二也符合当时开展的文学教育实际。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回忆他的学堂汉文教育云:“汉文老师我在学堂里只有一个……说到教法自然别无什么新意,只是看史记古文,做史论,写笔记,都是容易对付的,虽然用的也无非是八股作法。辛丑十一月初四日课题是:‘问汉事大定,论功行赏,纪信追赠之典阙如,后儒谓汉真少恩,其说然欤?’”[15]这可见重视经史、重视公牍文书写作的文学教育模式,是当时新式学校普遍推行的范式。
三、刘师培的文学观念、教育实践及其与“龙学”承变
刘师培坚守传统辞章学的声律、辞藻内涵,尽管他在《文说》中一度转向“文笔并重”,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坚守“韵文学”,而他坚守韵文学的倾向早有端倪。早在1913年的《国学学校论文五则》⑥,刘师培即宣称“明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16],可见其重视骈文的原因,已由阮氏父子的骈散之争,提升到与“外域文学”相抗衡的意义。依此方向,刘师培对“韵文学”发展史有更系统的论述。其晚年所作《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一二课为先前旧作,然而,最后第五课《总论》部分,特立新篇“声律说之发明”“文笔之区别”,代表着其对“韵文学”中“文笔说”的最后申辩:
至文笔区别,盖汉、魏以来,均以有藻韵者为文,无藻韵者为笔。东晋以还,说乃稍别:据梁元《金楼子》,惟以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为文;据范晔《与甥侄书》及《文心雕龙》所引时论,则又有韵为文,无韵为笔。[17]
这段文字中,刘师培将历史上的“文笔说”分为三个阶段,汉魏是以“藻韵”来区分文笔,这样一来,《论衡》中经、史、子及朝廷文书中属于“精思著文结篇章”的部分,径可归为文。毕竟,那是汉代的标准,东晋开始则有《金楼子》的“吟咏风谣,流连哀思”和范晔《与甥侄书》及《文心雕龙》的有韵无韵两种标准。
刘师培选择的是延续范晔《与甥侄书》及《文心雕龙》的 “有韵为文”传统。他认为“至当时文格所以上变晋、宋而下启隋、唐者,厥有二因:一曰声律说之发明,二曰文笔之区别”[17]。在“声律说之发明”部分,刘师培“粗引史籍所言”,梳理出一套支撑“韵—文”的经典:《南史》中的《陆厥传》《周颙传》《沈约传》《庾肩吾传》、《宋书》中的《谢灵运传论》、陆厥《与沈约书》、沈约《答陆厥书》、《文心雕龙·声律篇》以及锤嵘《诗品》。由此,刘师培整理出音律与“四六之体”的发展脉络:
四六之体,粗备于范晔、谢庄,成于王融,谢朓,而王、谢亦复渐开律体。影响所及,迄于隋、唐,文则悉成四六,诗则别为近体,不可谓非声律论开其先也。又四六之体既成,则属对日工,篇幅益趋于恢广,此亦必然之理。[17]
可见,刘师培将阮元、阮福阐说的“情辞翰藻”重心转至“声律”,并初步构建了“骈文学谱系”,这也成为刘师培人生最后十余年孜孜以求的努力方向。
在讨论中国文学一科的成立时,我们常关注“文学史”的诞生与发展,而忽略了学科初创期蕴蓄的多种可能。章太炎与刘师培广义、狭义文学之争的实质,正是传统文学教育土壤里酝酿出的两种方向。我们不妨再看光绪二十七年(1901)刘坤一、张之洞所奏《育才兴学四事折》对“文科”教育循序渐进的规划:
童子八岁以上入蒙学,习识字,正语音,读蒙学歌诀诸书……十二岁以上入小学校,习普通学,兼习五经……十五岁以上入高等小学校,解经书较深之义理,学行文法,学为法论词章……设中学校,十八岁高等小学校毕业取为附生者……温习经史地理仍兼习策论词章,并习公牍书记文字……词章一门亦设教习,学生愿习与否,均听其便。[5]
这一规划强调经学、公牍书记文字之重要性,与章太炎“广义文学观”如出一辙,至于传统 “词章一门”,则“学生愿习与否,均听其便”,由此可看出辞章学的冷落。以此看来,刘师培1917年在北大继续提倡“韵文学”,纵使提升到与外域文学相抗衡的地位,骨子里坚持的反而是古代书院中最传统的“辞章学”。
刘师培尽管梳理出《金楼子》“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为文”的情文系统,但其本人似乎对“情辞韵藻”中的“情辞”不再重视,而寄意于对“韵藻”的阐释与创作,以与“外域文学竞长”。当然,《文选序》《金楼子》构建的主情论也未消退。清末李详补注的《文心雕龙》中的《总术篇》仍援引《金楼子》,称许阮氏父子“以情辞声韵附会彦和之说,不使人疑专指用韵之文而言,则于六朝文笔之分豁然矣”[6]。李详强调“文”不只在“用韵”,而有“情辞声韵”,这是对阮元、阮福早期“文笔说”主张的复述。
这里最微妙的区别还是在黄侃与章太炎、刘师培二师之间。黄侃似乎有重视“情文”的倾向,其重视情采,且尝试以《神思》来补充《金楼子》主情论,是其不同于先师之处。如《文心雕龙札记·神思篇》中,他对“神思”“文之思也,其神远矣”“神与物游”的解读,显然已越出对章太炎、刘师培论文的苑囿。又如《总术》对《金楼子》的按语:“文笔之别,以此条为最详明。其于声律以外,又增情采二者,合而定之,则曰有情采韵者为文,无情采韵者为笔”[18],均可见其对“情藻”的重视。黄侃《文选平点》中,《文选序》有其手批:“此序,选文宗旨、选文条例皆具。宜细审绎,毋轻发难端,《金楼子》论文之语,刘彦和《文心》一书,皆其翼卫也”[19]。据潘重规《黄季刚先生遗书影印记》记述,黄侃授潘重规《文选》已是民国十六年(1927)国立中央大学期间[20],此时黄侃重申《文选序》与《金楼子》, 可见,伴随着“纯文学”概念的兴起,“主情说”越发受到重视。
结语
通过梳理清末民初国文教育的演进,我们可以观察到其时文学教育的不同观念、不同侧重点与《文心雕龙》诠释的多义性。就文学教育的规范而论,通过比对先后为新式书院与新式学堂改革者的阮元、张之洞,发现正是他们对《文心雕龙》的一抑一扬,将《文心雕龙》带入到清末学制改革的激流,而主持学制改革的张之洞对《文心雕龙》文学思想的重视与提倡,为晚清民国文学教育树立了规范,是“龙学”兴起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从阮元“文笔说”对《文心雕龙》疏离的态度,到学制改革后刘师培“文笔说”中充分利用《文心雕龙》辨体思想的差异,为我们论证学制变革所确定的文学教育规范对晚清《文心雕龙》思想流布影响提供了佐证;就文学教育理念来说,探讨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人文学观与文学教育理念的关联,使我们看到文学学科发展的多样性,以及《文心雕龙》凝聚学者共识的重要性。
注释:
① “文学”一科在晚清民国的建立,陈平原、陈国球、栗永清、陆胤、陈广宏均有专著。对于“国文之教学”,程千帆曾于1942年发表《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弊》(《国文月刊》第十六期)一文,认为“研究之方法”与“教学之方法”并非一事。本文尝试从近代以来“国文教育”教学目的与方法之改变的角度,揭示《文心雕龙》与这场变革的关系。
② 周兴陆.章太炎讲解《文心雕龙》辨释[J].复旦学报,2003(6):122-127;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39。
③ 张少康认为,刘师培、黄侃先后在北京大学教授《文心雕龙》课程,促成了“龙学”的确立。张少康,等.文心雕龙研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35。
④ 李曰刚认为“民国鼎革以前,清代学士大夫多以读经之法读《文心》,大则不外校勘、评解二途,于彦和之文论思想甚少阐发……因此《札记》初出,即震惊文坛,从而令学术思想界对《文心雕龙》之实用价值,研究角度,均作革命性之调整”。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M].台北: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3: 2515。
⑤ 关于刘师培“文笔说”辨体意识的加强,更体现在1913年《文笔诗笔词笔考》与阮福《学海堂文笔策问》比对中。参见吴海.刘师培的碑传观与扬州学派[J].南京大学学报,2018(2):130-137;吕双伟.“骈四俪六”与元明清赋学批评的演变[J].云梦学刊,2019(3):90-97。
⑥ 《国学学校论文五则》与《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一课《概论》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