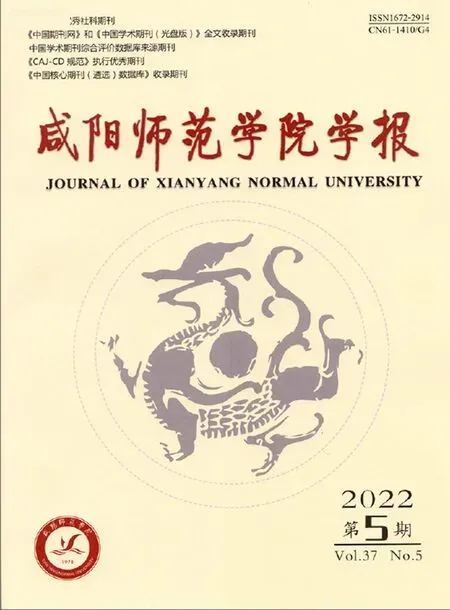尉缭书文字风格和内容体现出的时代特征
张 申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一部先秦著述能流传至今,必然是该书在历代的流传中被“当时”学者发现其内容有益,对解决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和矛盾有所帮助,才在确保该书传于后世的前提下稍稍扩大其影响和传播范围。且古之为书,一时有一时之文体,其内容所反映和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必有其时代特色。今本缭书首句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隋志》以后大多学者据此认为该书是尉缭及其弟子对这次“君臣问对”的整理,但《史记·秦始皇本纪》(以下简称《秦始皇本纪》)又有始皇任命大梁人尉缭为秦国尉的记载。国尉,秦官,若汉太尉之比,掌全国兵事,而《尉缭子》正是兵书;梁惠王即魏惠王,因其迁都大梁故又称梁惠王,《秦始皇本纪》中所载之国尉缭即由魏国大梁而来。这些不是巧合但又胜似巧合的问题,直接导致了缭书“年代之争”问题的激化。总之,不论尉缭是曾与梁惠王问对,还是向秦王政献策,他都有很大概率是魏人。问题的主要方面则是梁惠王与秦王政(十年)相差近90年,并且魏国和秦国的国情有很大差别。关于这一问题,前人已有所阐发,但笔者认为尚有研究之余地,或可从缭书文字内容的角度进行详细考察,找出有利于解决尉缭其人其书年代之争的证据。
一 从遣词用句看
(一)称谓方面
《公羊传》云:“《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1]113《战国策》中各篇有云楚者,亦有言荆者,古书单篇别行,因刘向汇而成书,以“避讳”例能知其中径言“楚”者成书当在始皇帝或庄襄王即位前;其云“荆”者成书则在始皇时。《张仪说秦王》云:“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2]95鲍彪注“荆”曰:楚也。始皇讳其父名,故称曰荆。知此书始皇时人作。”[2]96《尉缭子·天官》篇尉缭在问对时曾引“楚与齐战”的故事作为对“天官人事”的回答来证明天官、时日、阴阳等不如人事,“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以此推知《天官》篇非始皇时人作。始皇帝名政,一作正,名字之避讳有以“正”改“端”例。但缭书中“政”与“正”二字皆未避讳,如《原官》“审开塞,守一道,为政之要也”,《治本》“善政执其制,使民无私”,《兵教下》“宽其政,夷其业”;或如《兵令上》“善御敌者,正兵先合”,《制谈》“量吾境内之民,无伍莫能正矣”,《武议》“三军之众,有所奇正”。缭书不避始皇帝父子名讳,以此来看,今本当非《秦始皇本纪》中所载由大梁入秦之尉缭所撰。
除避讳的问题外,缭书中还有一些其他属于称谓范围内的记载,亦能从侧面体现其时代特点。第一,尉缭的重民思想向为古今学者所称道,今本缭书中共50 余处提到“民”字,30 余次提到“众”字,但无“黔首”之谓。“黔首”之名在战国前期即已产生,并得到广泛应用[3]。秦称民为“黔首”,始皇二十六年(前221)“更名民曰黔首”[4]239,是始皇帝所采取的一系列更定“名物制度”的措施之一,并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若缭书为“国尉缭”所撰,其书中所称当是“黔首”而非“民”。而且该书在秦地的流传中多少会沾染上秦国的文字风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缭书当非“国尉缭”所著。尉缭和孟轲是兵家和儒家两派重民思想的代表,《孟子》一书中提到“民”有180 余处,就全书的占比而言,尉缭和孟轲不相上下。从时代特征的角度而言,二书都是先秦杰出思想家对于当时诸国攻伐不休、人民流离无依现象的深刻反思,而孟子也曾与“好战”的梁惠王问对,“王好战,请以战喻”。同样,缭书开篇即言“梁惠王问”,亦曾言“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为非难也”。所以尉缭和孟子有相似的重民思想,其产生的土壤就是当时的“剧变”——即梁惠王时。需要注意的是,因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说流传甚广,故有学者以缭书中亦有此说为据,抨击尉缭乃是仿抄《孟子》而全无己见;也有学者以此为凭认为尉缭时代必晚于孟子,故认为缭书作者乃是国尉缭。此句出自缭书《战威》篇,与“天时地利”位于同一段的还有“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所谓上满下漏,患无所救”。又《荀子·王制》云:“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5]149有学者即据此以为缭书《战威》篇乃是抄自《荀子》,并言之凿凿认为缭书成书时代在荀子之后[6]。对于这类问题,其实古人已经给出答案,不必再过分纠结先秦两汉典籍的“互见”问题。《战国策·楚四》中《客说春申君》载:“孙子为书谢曰:‘疠人怜王,此不恭之语也’”。刘辰翁曰:“此韩非语,孙(卿)不当用”。补曰:“不知(韩)非正用孙(卿)语也。”[2]567第二,尉缭在问对时称惠王为“主”的次数有16 次之多。《战国策》注曰:“齐侯使高张唁公,称‘主君’。子家子曰:‘齐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称也’。《秦策》甘茂引乐羊曰‘主君之功’。《魏策》择言称‘主君之尊’云云,盖三晋以大夫为诸侯,故犹仍之。”[2]602田齐、三晋即立为侯之后取得了“君”的地位,但其臣仍习惯地称其为“主”,姚鼐说:“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事实上,“主”在春秋时不仅是“大夫称也”,更重要的是对卿、对中军将(帅)的称呼。其时,不但不能称君为主,称君为“主君”都不能被接受,都被认为是对君的侮辱[7]。秦自惠文王称王至始皇时已六世,《战国策·秦策》所载纵横游士与秦王问对时,皆称呼为“王”而不言“主”。战国时称国君为“主”大多发生在韩赵魏三国,而且多发生在战国前中期,这是由三晋历史传统所决定的。所以从称谓的角度来看,今本首句所言“梁惠王问尉缭子曰”是符合史实和战国时代特征的。
(二)用词方面
古人著书,尤其是先秦子书,在遣词用句等方面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即一时有一时之文体,一代有一代之通例。我们最为熟悉的兵家格言“十万之师,日费千金”,此说源自先秦兵书,“十万之师”是后世的说法,“日费千金”是汉代的用法。如《史记》“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4]2955;《汉书》亦云“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8]2801。而《孙子兵法》则云“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费日千金”[9]149;《尉缭子》云“十万之师出,费日千金”[10]。由《孙子》《尉缭子》二书皆言“费日千金”,可知其时代必相差不远。一些语句的运用有着严格的限定条件甚至是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以从先秦两汉典籍互见或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的角度,也可反推出缭书的成书时代。
战国纵横游说之士与君王问对时,为取信见任于时君,有一些惯用的陈述之法,如“臣闻”等,若涉及兵事时又常道“臣闻古之善用兵者”,如《国语·越语》载范蠡曰:“臣闻古之善用兵者……”韦注:“谓若黄帝、汤、武。”[11]302-303尉缭在与梁惠王问对时也常以“臣闻”来引出下文,《兵令下》又有“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的记载。缭书首句有“梁惠王问”,故或谓其为依托之伪书,或谓其必晚于梁惠王之世,此是不明古书著录之例也,黄丕烈《札记》云:“然此追称,群书多矣。《史记》无,然不必衍。”[2]1059
《史记·秦本纪》记载蜚廉、恶来是秦人祖先,但蜚廉、恶来父子俱为纣臣,“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4]174。战国时,纵横游说之士常以“武王伐纣”事作为劝谏或献策的说辞,缭书中也有两处相关记载,如《天官》“武王伐纣,背济水向山阪而陈,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商”和《武议》“武王伐纣,师渡盟津,右旄左钺,死士三百,战士三万。纣之陈亿万,飞廉、恶来,身先戟斧,陈开百里。武王不罢市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诛纣”。纣王在周以后绝大多数是以反面形象存在于世的,尉缭在书中的两处引用无疑也是将周武伐纣视为替天行道之举。但该书作者如果是“国尉缭”,作为仕秦的尉缭不仅不应当以周武伐纣作为佐证其理论正确性的依据,更不应该将蜚廉和恶来两位秦人的祖先作为反面的例证。
二 从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看
缭书的文字、内容和军事思想等,时刻体现着尉缭所处时代的特色,将其与先秦两汉典籍互见,亦可推知其年代。
班固云“兵家之策,惟在不战”[8]4359,“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师古曰:“已乱而后治之,战斗而后获胜,则不足贵。”[8]3812战国秦汉时人根据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是:杰出的兵家贵不战而不贵战。因为频繁的战争会不断消耗国力,长此以往就将国家陷入了危亡境地,“战胜而国危者,物不断也;功大而权轻者,地不入也”,“战胜则国宜安,而愈战则国危。功大权宜重,而愈求功则权轻”[2]201。尉缭将之深刻地总结为“战再胜,当一败”[10]。然而与“古之善用兵者”不同,战国时候所谓善用兵者,则终日交相攻伐,虽然能取得一时胜利并保全宗庙,但是有识之士却预见了这种情况并非长久之计,并指出这样对国家是无利的,“今世之所谓善用兵者,终战比胜,而守不可拔,天下称为善,一国得而保之,则非国之利也。臣闻战大胜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罢而城郭露。夫士死于外,民残于内,而城郭露于境,则非王之乐也”[2]133。对于什么样的战争才是应当被倡导的,苏秦向齐闵王道:“故明君之攻战也,甲兵不出于军而敌国胜”,此即尉缭所谓“国车不出于阃,组甲不出于橐,而威服天下矣”。很明显,尉缭的建议并没有被梁惠王采纳,梁惠王长期暴师于外,四处征战,虽然有一时之胜但难免衰亡,“虽战胜而国益弱,得地而国益贫”。巧合的是,苏秦在与齐闵王问对时所举的“终战比胜”的反例就是梁惠王。对于梁惠王没有采纳尉缭的建议而导致败亡的结果,直至明代尚有学者感叹,“令(梁)惠王能用之,宁第雄伯一时,尽洗三败之耻,必可包举六国,不为二世之亡,何至于踵韩赵而折入于秦”[12]。
这种“不暴甲而胜”的战争模式,被战国时人称为“战胜于朝廷”,如齐威王时邹忌讽齐王纳谏,由是齐国大治,“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2]97。尉缭子与此有着相似的论述,“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13]367如果实在不能“胜于朝廷”不得已而用兵,还希望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就必须做到两点:第一,“大国之计,莫如后起而重伐不义”[2]131。尉缭将之阐释为“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争私结怨,应不得已;怨结虽起,待之贵后。故争必当待之,息必当备之”[13]378。第二,要赏信罚必。“言赏则不使,言罚则不行,赏罚不行,故民不死也”[2]27,“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4]2289。尉缭同样认识到了赏罚对于士气鼓舞的重要性,故而其通卷都在论述赏罚之法,尉缭军事赏罚思想的主旨即是重赏重罚,所以招致了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其惨刻酷烈,秦国也因重赏重罚之耕战、首功军事思想为历代学者所批评。就赏罚而言,尉缭与战国时人的论述大体相同,如其总论“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与前之所言“兵胜于朝廷”的威制天下军事思想相呼应。其他如“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形乃明”[13]368、“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荣而显之”[13]374、“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13]384,这些都是具有“重赏重罚”的尉缭军事思想的具体体现。
缭书首篇《天官》载梁惠王向尉缭询问“黄帝刑德,可以(百战)百胜,有之乎”?首篇的问对将梁惠王的性格暴露得一览无遗。首先,梁惠王是一个过分迷信“天官时日阴阳向背”刑德之说的君王。梁惠王时魏国上下盛行“兵阴阳”思想,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晋楚鄢陵之战》记载“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后。王曰:……‘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14]169《战国策》亦载“臣战,载主契国以与王约,必无患矣”[2]50,“襄主错龟数策占兆,以视利害”[2]30。晋国军队一直有战前卜筮、祷誓的传统,魏氏久为卿并出任晋军将佐,至梁惠王时发展成“兵阴阳”思想也并不出人意表。其次,梁惠王不愿修“人事”,不愿任用贤臣,更不愿用心治理国家和军队,一心将取得胜利押宝在虚无的“百战百胜”的道术上。魏惠王太子申与其父一般无二,当时宋国人徐子可能就是摸透了梁惠王父子的心理故而以此向太子申进谏,“魏太子自将,过宋外黄。外黄徐子曰:‘臣有百战百胜之术,太子能听臣乎?’太子曰:‘愿闻之。’”注曰:“太子者,国本也。自将,必胜之易也或情之迫切。”[2]365由此可见,当时魏国上下弥漫着一股不修人事的风气。所以尉缭径直对梁惠王指出,“今世将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臣以为难”。尉缭认为,战胜的根本归根到底还在于修人事,“古之圣人,谨人事而已”。对于如何修、重人事,尉缭列举了几个关键:“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占筮而获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如果做到这几点就能不战而胜,“兵胜于朝廷”“使天下莫当其战矣”。尉缭此言,正是针对梁惠王时期魏国“重阴阳”“轻人事”所作的阐发。
孟子亦尝与齐宣王问对:“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15]154《礼记·曲礼下》:“大夫不名世臣、侄娣。”郑玄注:“世臣,父时老臣。”[16]37从一些记载来看,当时的君主喜任世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世臣视作国家维持长久的根本。战国时文武分职的情况并不像后世那样泾渭分明,世臣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等同于世将。梁惠王也大肆任用世臣世将,其任公叔痤为相为将即是其证。但是终战国之世,世将大多是以反面形象出现在史籍中的。尉缭也注意到了世将对国家的危害,指出“世将不知法者,专命而行,先击而勇,无不败者也”[13]403、“(世将)不能禁此四者,犹亡舟楫绝江河,不可得也”。战国时六国世臣世将基本掌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他们的另一个称谓是“封君”。六国封君较秦国封君有着更大的军政权力,如果将六国看作万乘之国,那么六国内的封君则是国中之国,即千乘、百乘。孟子和尉缭都注意到了这个危害国家“名实”的现实问题,孟子从政治的角度指出“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15]40;尉缭则从军事角度提出了“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13]384。
此外,缭书中的一些词语也明示着其献策的对象,如《踵军令》“凡称分塞者,四境之内,当兴军踵军既行,则四境之民无得行者”[13]405。魏为中央之国,其地四战,故曰四境。又《兵谈》云“兵之所及,羊肠亦胜……”[13]367,羊肠即赵国险塞名,在晋阳太原之西北,上党壶关有羊肠坂。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始置太原郡,治所在晋阳。所以如果缭书著者为国尉缭,则不当言“羊肠亦胜”。《兵令下》“诸去大军为前御之备者,边县列侯,相去三、五里”[13]414,秦新取地曰郡,非县。凡此种种,不再赘述。由今本文字内容来看,缭书著者不当是国尉缭。
三 与秦国国情殊异
缭书中有很多关于制度、名物和治民的思想,以致有学者以此来非议缭书,认为其或为《汉志》所载之杂家书,或认为今本二十四篇半是原兵家书半是原杂家书,至北宋元丰年间《武经七书》成书时杂糅而成。实际上,战国时期的许多兵家是集文武于一身的,既能行军打仗,又能定国安民,如吴起之为西河守;商鞅为秦左庶长总变法事,但在军事上与孙武、吴起等并称“孙吴商白”,称为名将;李牧号为名将亦总代、雁门之军政,“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4]2449。以此来判定缭书的成书年代,实不足据。
尉缭提出过很多治国牧民的对策。他首先注意到了当时“战国相攻”背景下“天下骚动”的情形,提出了以国富民治为基础的“威制天下”思想。如“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13]367、“耕有不终亩,织有日断机”[13]393,向梁惠王发出了“古治之行,今治之止”的警告,主张“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13]372、“万乘农战,千乘救守,百乘事养”[13]384。因为对于久历战争的万乘之国来说,“农战不外索权,救守不外索助,事养不外索资。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13]384。尉缭还注意到了“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绣饰,马牛之性食草饮水而给菽粟”[13]393这种使“天下靡费”的情况。对于魏国已经存在的较为严重的“今治之止”的问题,魏惠王依然为了一己私欲而沉醉于其“霸业”之中,“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斿(旗),从七星之旟”[2]442。结合史实来看,缭书中所描写的他献策国家“国罢民疲”与梁惠王时的魏国是高度吻合的,“南攻楚五年,蓄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罢弊。北与燕战,覆三军,获二将。而又以其余兵南面而举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犹取哉?且臣闻之,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弊”[2]1056。而这些情况是不会存在于秦王政时期的,因为至秦王政时行商君之法累已六世,对于已经行之百余年的国策,尉缭又有什么再向秦始皇献策的必要?而且在秦王政十年时天下大势已然是山东六国如秦“郡县之君”,“今秦出号令赏罚,不攻无功相事也”[2]97,尉缭所言,与秦王政时秦国的国情相去甚远。
缭书中也有很多尉缭以古圣王事例来劝谏梁惠王的记载,如“圣人所贵,人事而已”[13]376,“古之圣人,谨人事而已”[13]387以及周文王、周武王、太公望和齐桓公的故事。这种以古圣王故事来劝谏君王的事例多见于《战国策》,这也是当时六国纵横游士游说诸侯的常用手段。但对于秦国来说,至少在秦王政十年的时候是行不通的,因为秦国自孝公以来即认为儒生无益于国,秦昭王问荀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5]111-112秦昭王使子楚诵,子楚曰“少弃捐在外,尝无师傅所教学,不习于诵”,补曰:“《大事记》,不习于诵,此焚书之兆。”[2]280《淮南子·览冥训》:“弃捐五帝之恩刑,推厥三王之法籍”[17]66。《战国策·序》“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2]1196。所以从政治环境的角度来看,今本不当是国尉缭所著。
通过对今本缭书的梳理和考察发现,不仅尉缭献策国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与秦王政时期的秦国不符,其所献对策也在秦国行之既久。若将今本缭书视为一本兵书,如果著者是梁惠王时的尉缭,其军事思想无疑是具有先见性的,缭书也是极具价值的;如果著者为国尉缭,那么其军事思想的主体几乎都是拾前人牙慧,于当时的秦国几乎无益。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试作讨论。
一是兵法之教。缭书所载什伍之法、束伍之法、服章之法、符籍之法和金鼓铃旗之法等,统称“兵法之教”。其中如什伍之法等,实际上与商鞅变法是大体相同的,从现实角度而言没有再次献策的必要。而尉缭论述的其他如官号名物、服章、符籍和金鼓铃旗等法,不仅与其他史书记载的秦军军制迥异,而且也没有出土材料作为佐证。如符籍之法,“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书军令。伍符,军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汉军法曰吏卒斩首,以尺籍书下县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夺劳二岁。伍符亦什伍之符,要节度也。”[4]2759汉承秦制,以上记载不仅反映出战国以来秦汉已有了较为完备的符籍制度,而且与缭书的记载也有很大不同,可见秦王政并没有施行尉缭之策,这与《史记》所记载的任命尉缭为秦国尉的情况有很多不同。所谓兵法之教由来已久,《周礼》:“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阵,如战之阵。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士卒听声视旗,随而前却,故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春教振旅以蒐田,夏教茇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弥田,冬教大阅以狩田[18]51-52。先秦兵书战策多言出奇制胜,而鲜有论及金鼓铃旗者,而且越到战国后期越少。一是因为所论金鼓铃旗之法,对军事实践的要求较高,一般多是有实际统兵经验的大将方能为之。二是兵教之法多在战国以前,那时国人战时为兵解甲归田,需要时常对国人进行训练。而战国以来,募兵行之既久,士民素习战阵之法就没有四时讲武的必要了。此外,秦王政时久行商君之法,秦民连年征战必已素习兵法之教,如果秦兵无兵教也不可能累世战胜六国,苏秦谓秦惠王曰“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4]2242,换言之也可以理解为六国之兵教不如秦国。反观梁惠王时,虽然吴起离去后魏国还能获得一些胜利,但连魏相公叔痤都不得不承认是“吴起余教”的功劳,也可以理解为吴起之后就没有人能继续施行“兵教之法”了,“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拣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臣不能为也”[2]784,故尉缭针对当时魏国“不能为兵教”的情况献策于梁惠王,故缭书中有《兵教》二篇。
二是战争目的和方式的不同。梁惠王时期进行战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霸权,反而对于残灭其国、虏其民、得其地的欲望不甚迫切。因为此时去春秋不远,诸国的战争模式还没有从春秋时的争霸思想转变过来,“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2]266。秦王政十年时秦国进行的则是统一战争,目的是为了兼并六国、以一海内。缭书中的军事思想较为契合战国前期的战争模式。在当时以争霸为目的的指导下,提倡的是服人、安民、怀远和威制天下。对于战争,缭书总的指导方针是诛暴禁乱,“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13]383,这就要求发起战争必须要以正义为目的,“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13]383。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尉缭提出要“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在战争过程中要尽量减少对人民的影响,“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13]383,对于一些杀戮行为进行了抨击和否定,“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13]383。那么,到战国后期秦国进行统一战争时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秦国所进行的战争不仅没有安民,反而是攻战一地则驱逐其原住民,迁本国罪人实其地,如甘茂在宜阳之战后“反宜阳之民”。这是因为秦国对六国人民不信任,“秦不信敌国之民,故徙其国人使错居之”[2]860,在六国战争中却极少见到这种情况。秦国的驱逐政策直接加剧了流民现象的产生,“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鬼神狐祥无所食,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2]248。其次,秦国奉行的战争指导思想是大量杀伤六国的有生力量,据清人梁玉绳统计,可考的秦国杀伤数量在一百六十余万人左右[19]141-142,韩非言秦人“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20]5,张仪则称“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2]934。时人评价秦国“今秦者,虎狼之国也。注曰:秦欲吞灭诸侯,故谓虎狼国也。喻其贪残”[2]50-52。最后,秦国在战争过程中的贪残和战后驱逐平民的表现,归根到底是其“尚首功”的军事思想,是其在统一战争思想目的指导下的必然行为,“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虏”[2]333。所以秦国的这些表现和尉缭所提倡的军事思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这样一个仁义之人又怎么会去秦国给秦始皇献策攻伐六国呢?
三是赏罚之行与不行。在冷兵器时代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士气”对战争甚至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而提振“士气”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重赏,“明赏罚,使民有必战之心”。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奖励耕战,崇尚首功,设二十等爵以明赏罚,至秦昭王时已经“今秦出号令赏罚,不攻无功相事也”[2]95,即秦人有所不攻而无有敢攻秦者。反观尉缭献策国家所面临的情况则是赏罚不行、赏罚不中且士民不信,所以尉缭如商鞅一样提倡重赏与重罚,即“有功必赏,犯令必死”[13]413。一方面尉缭认为重赏是提振士气的最有效方法,“赏禄不厚则民不劝”[13]375,另一方面尉缭针对六国赏罚不公平的现象指出了要赏罚公平,这样才能有效提高将帅的威望,“刑赏不中则众不畏”[13]375,只有使士卒畏惧将帅才能“侮敌”。面对当时六国“千金不死,百金不刑”[13]389的弊政,尉缭甚至还提出了杀大赏小、刑上赏下的赏罚思想,“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故人主重将”[13]384。而以上这些弊政和尉缭提出的思想却是明显与秦国“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实际情况相反的,反而与魏国有功不赏、慢待功臣的惯例相吻合。
此外,或曰“兵家所言出奇制胜者多矣,言旗鼓步伐者少,然出奇制胜之法虚,旗鼓步伐之法实。虚者,聪明者自会;实者,非学不可。不教则不明,不练则不习。不明不习,卒乃予敌”[21]。自商鞅设计擒公子卬开始至始皇时“多与郭开金”,或予国尉缭“三十万金”行间于六国,秦国大部分时期所奉行的都不是“堂堂正正”的军事思想。但尉缭言兵均是“堂堂正正”,有别于以孙武子为代表的“兵权谋家”,故《四库提要》评价其“所言往往合于正”。而且缭书不仅记载了金皷铃旗之法,还记载了数处关于吴起在行伍时较为私密的事情,如“吴起与秦战,舍不平陇亩,朴樕盖之,以蔽霜露”“吴起与秦战,未合,一夫不胜其勇,前获双首而还。吴起立斩之。军吏谏曰:‘此材士也,不可斩。’起曰:‘材士则是也,非吾令也。’斩之”[13]388。以此来看,尉缭或是吴起后学,或是吴起为将时的亲密之人,因为只有相善的左右近人才能知晓吴起之为人以及这些不为诸子所载的“隐秘之事”。此外,韩非言“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披甲者少也”[20]59,而秦自孝公迄至始皇,几无兵家游说秦王成功者,也未见秦国有求兵书、盛行兵书的政治环境。所以从以上这些角度来看,今本著者也不当是国尉缭。
四结语
据上所述,基本可以梳理出尉缭书所体现的时代特征。从首篇首句来看,这是尉缭后人或其后学关于尉缭与梁惠王问对过程的整理,符合先秦古书成书的一般通例。尉缭在问对中所提到的当时国家存在的问题也与梁惠王时魏国的情况基本一致,尉缭在献策中期望施行的治国政策与治军法令,绝大部分是秦国自商鞅变法时就已经施行的,至秦始皇时已行之六世,献出一些秦国久行成法的兵法也没有什么价值,既不会被采纳,也不会像《史记》描述的那样受到礼遇。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尤其是流传至今的古代兵学名著,它所反映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都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张申《尉缭子作者及成书年代考》[22]从尉缭书中显示身份的语句、时代特点和反映的社会现实、战争规模、军令以及战争年表等方面对尉缭书的成书年代作了初步考察,认为今本缭书反映的主要是梁惠王时魏国的情况,故著者年世及成书时代可知。本文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更细致地从称谓等方面考证了书中问对双方也不应是尉缭与秦始皇。结合相关史实来看,与梁惠王问对的尉缭应该是在“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4]1847之时,但最终梁惠王并没有采纳尉缭的献策,以致明人黄献臣发出了“令惠王能用之,宁第雄伯一时,尽洗三败之耻,必可包举六国,不为二世之亡,何至踵韩赵而折入于秦”[12]的感叹。
——重读《孟子见梁惠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