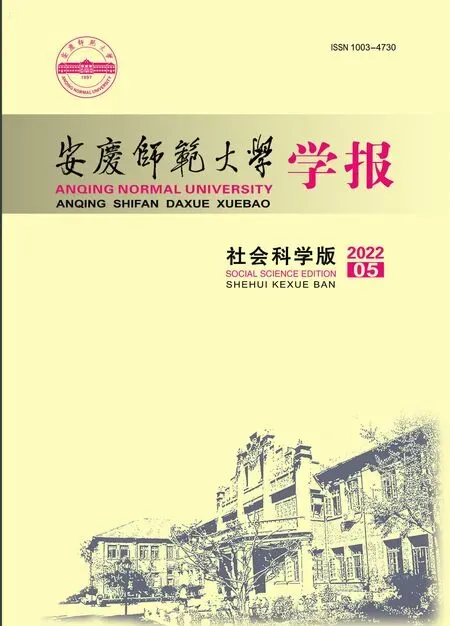《张恨水全集》补遗三题
高 强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1756)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作数量最为丰硕,与普通市民阶层联系最为紧密的作家,其人其作也构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 “传奇” 。1993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洋洋70卷的《张恨水全集》,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张恨水作品集。但因为张恨水的创作体裁不拘一格,创作年限跨度较大,且刊发其作品的报刊杂志种类繁多,种种原因导致尚有大量佚文佚作未被收录《张恨水全集》及其他各种张恨水作品资料书目。2014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张恨水研究专家谢家顺编著的《张恨水年谱》,披露了大量张恨水佚作,全面展示了张恨水的生平创作面貌,显现出巨大的学术价值。在此基础上,笔者近期新发现了张恨水的三则佚文,兹辑录于下并略作释读,供读者和学界同仁参阅。
一、《由天津到下关》:民国初期的交通乱象与社会感怀
1930年11月30日《大晶报》第2版和第3版刊有署名张恨水的文章《由天津到下关》,全文照录如下:
记者早日已闻津浦车拥挤不堪,因乘名义上之平浦通车,事实上之津浦通车,在平不能有把握,遂于十二日离平,当晚至津,以为必可谋得一睡铺票,因十三十四日,均有钢车南下,必可得其一也,而据各方报告,则三等无论矣,头等二等均须三数日前买票,记者大骇。以为如在津候三五天,资斧所耗且不计,而枯燥之旅馆生活,如何得度,即重赏旅馆茶房,令购一二等睡票,不得,则头等亦可,结果,居然得一票,而茶房则夸功之余,历述津浦每日寻常快车之拥挤,谓购票之时,售票处人挤如山,老弱不能向前者,则出一种费用始辗转得一票,得票之后,能否登车,又是一问题。因此项车,只头二等混合车一辆,余则为三等车或铁闷子车,以及敞车,七拼八凑勉成一列,车中满坑满谷,自无隙地。次至者,则扶老携幼,相率而登车棚之顶,寒风凛冽,车身摇荡,一切痛苦危险,均所不计。又次者,并车顶而不得登,则奔走呼号于站台之上,以俟明日车再来,栗不得退也。记者初犹疑其言近于虚构,至上车之时,据搬夫言,今早津浦常车,有二百人得票未得登车,其情形如何,不烦赘言矣。车中无可述者,惟有两事,给吾人以重大之印象。每站之前后,均有旧战壕遗迹,而站上则满贴欢迎 “巩固边防劳苦功高之张副司令” 之大字标语,张之巩固边防,直至现在,国人始认识之,而中俄战事,已成历史矣。由天津到浦口,车只误点两小时,在战后不能不认识为难得之事,而记者既至浦口,坦然加大衣于身,如释重负,不料事实有不然者,一步下车,只见人山人海,如潮涌而去,站台上则军警罗布,检查行李,于人浪沸腾中,则见检查者,摆荡于人腿下,记者自知不免,则执箱匙于手以听命令,直至最后一层,一武装革命同志见予西其服而革其履,且仅一小皮箱,则立予验讫执照一纸,乃随搬夫拥挤以登长江码头。七八年不见大江,旧地相逢本是一快,然而码头之上,则比站台之上,其拥挤更甚。一老妇携鸡笼二,提篮一,完全加于我肩,我又手一提篮而压搬夫之背,左右两方之人,紧如夹板透气不得,遥望登渡轮之栅门,则双扉紧闭,久之,门始开,又是一翻(一番)潮拥。记者被人抬上渡轮,亦不知如何已混入二等舱,舱中人立无隙地,搬夫索费声、茶房倒茶声,一切声音,振耳微响,候半小时,始开轮。既抵下关码头,又一搬夫,不问三七二十一,拿了我皮箱便跑,在人群中,杀出一条汗路,记者恐行李有失,当然紧紧跟随,幸而登岸,又为车夫搬夫所包围。然我由火车至下关码头,两重搬夫费,一重茶费,已费去七角,已不敢孟浪从事矣,候约五六分钟,人潮稍煞,始雇一搬夫,荷箱至一熟旅馆中小憩,主人本我同乡,而迎接者又至,心始大定,二小时后,乃乘一汽车,由中山大道,直驰入城。(十一月六日)
《大晶报》在发表张恨水的《由天津到下关》一文之前,编者特意添加了一则按语,谓: “这是新闻报快活林所载《啼笑因缘》小说的作者张恨水先生这次从北平到上海来的旅途笔记之一页,由此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战后的交通情形,特介绍于读者之前。” 由此可见,《由天津到下关》的确是张恨水的作品,并非他人冒名,也非其他不知名的同名张恨水之作。另外,编者在按语中向读者介绍说,张恨水的《由天津到下关》记录了 “战后的交通情形” ,所谓 “战后交通情形” 的详细面貌,则体现为一派乱象:从车票紧缺到车厢拥挤,从旅客吵闹混杂到搬夫争抢行李的场面,不一而足。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旅途书写的笔墨蔚为壮观,其中,出行艰难的感喟尤为常见,《由天津到下关》这篇张恨水行旅途中的实况笔记,较为清晰、形象地描绘了民国初期的交通乱象,为我们进一步理解现代文人的行旅书写,特别是为我们深入体会现代文人 “在路上” 的艰辛感受,提供了有益参照。
另外,在《由天津到下关》一文中,张恨水特别提及了两个让其印象深刻的事件。第一,车站前后随处可见旧战壕遗迹和 “巩固边防劳苦功高之张副司令” 的大字标语,这引发了张恨水的动情感触: “张之巩固边防,直至现在,国人始认识之,而中俄战事,已成历史矣” 。第二,张恨水抵达浦口车站时,有军警正在对旅客进行严格查验,但对方看见张恨水一身西服装扮后,即很快放行。后一件事无疑揭露了当时社会上看人下菜碟的媚俗风气,无需多言,而第一件事则返照出普通大众对中东路事件的观感。
所谓 “巩固边防劳苦功高之张副司令” 的大字标语,指的就是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中东路本是沙俄为侵略中国、控制远东而在中国东北境内修建的一条铁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沙皇被推翻,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发表宣言,声明废除沙俄同中国政府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放弃沙俄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的权益。1924年5 月31 日,中苏达成建交协议,签订了《中俄协定》等一系列协定,规定中东铁路的经营业务由中苏共管。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积极推行反共反苏的外交路线。1929 年7 月,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采取了武力收回中东铁路主权的行动,引发东北军与苏军之间的战争。结果东北军损失惨重,而日本关东军也借机生事,妄图从中渔利。12 月,东北当局与苏联方面停战议和,签订《伯力协定》,双方同意按照1924 年签署的中苏协定,恢复中苏合办中东铁路。
中东路事件爆发后的第三天,即7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党内就该事件发出《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接着又于7 月15 日发出《关于中东路事件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认为中东路事件是蒋介石和张学良 “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的共同行动” ,所谓收回中东路自管,旨在 “转移群众视线,使群众走上反苏的道路”[1]。因而中共中央提出了 “拥护社会主义苏联” “武装保护苏联” 的口号,要求满洲省委必须集中注意力对付这件事,并派刘少奇亲自去哈尔滨布置和指导关于中东路事件的群众性反抗示威,努力在政治上作加紧拥护社会主义苏联的宣传。目前历史学界的权威观点同样认为,中东路事件是国民政府为了达到其 “弃俄绝共” 叵测意图而有意挑起的争端,其结果则是自取其辱: “南京当局出于反苏的立场,在军事、外交都未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指使东北地方当局贸然采取挑衅行动,结果反授人以柄,进退维谷,徒招屈辱也在必然之中”[2]。共产党方面严厉批驳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东北军队与苏联作对是 “帝国主义” 行径,是出于维护无产阶级革命阵营的考虑,是阶级观念大于民族国家认同的体现;而现今的历史学界对中东路事件及国民政府语含贬斥,则是从后置的所谓正确立场出发做出的裁决。虽然民国时期的外交与内政 “实已打成一片,不可复分”[3],外交关系深刻影响着内政效果,如果敢于和外国人一战,很有可能收获内部民众的向心力,从而获得国内竞争的巨大象征资本,蒋介石便是从这个角度来为张学良的东北军人鼓劲。但政府层面的现实考量是一回事,落实到普通民众的实地感受则是另一回事。对于彼时彼地的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张学良敢于出头对抗强大的苏联军队,从对方手中夺回属于本国的铁路所有权,无疑是不畏强权、捍卫主权的英勇举动,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势下,尤其如此。所以,面对中东路事件,普通民众很少会考虑 “保卫苏联” 的阶级感召,也不会在意官方背后隐藏的提振声势、增加威望等现实目的,他们仅仅注目于国家主权的有无得失问题。张恨水于津浦路线上看到的 “巩固边防劳苦功高之张副司令” 等标语,以及他自己萌生的感怀,正是普通大众认识、看待中东路事件的形象说明,更是还原、逼近中东路事件这一历史现场的重要提示。另外,后来的左翼文学中,还出现过一些以中东路事件为创作题材的作品,相关作品文本内部或多或少都折射出了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相纠缠的情形[4],这便是张恨水赞许的 “巩固边防” 与共产党所宣传的 “保卫苏联” 之间矛盾的文学投影。
二、《九月忆上新河》:小品文作家张恨水与战时文人的浪漫怀想
1942 年10 月15 日出版的《今文月刊》创刊号刊有署名 “恨水” 的文章《九月忆上新河》,文章内容如下:
每到八九月之间,便让我很自然的会想到南京上新河。上新河在汉中门与水西门外,去城约十里。八一三后,南京日夜被轰炸,一家老小二十余口疏散不易,我就忽促的,把家送到上新河住了两个月。这两个月中,我生着恶性疟疾和骨节炎,在乡下住的日子较多。平生乡居日子不算少,而水村生活,这却是第一次。当时虽在极端紧张空气下让我感到这里很有趣。尤其是山居四年的今日,回忆当年,更是有趣。撮记所忆,也算是 “瞿塘峡口曲江头” ,令人一点秋兴吧?
出汉中门,有不整齐之马路一条,穿过稻田和菜圃。平常有极舒适而决对有座位之公共汽车,新街口汉中路开向这里,每半小时一次,车资是全程国币一角五分。便只这一点,已经令人有天上人间之感了。汽车停在街心的空场上,下车向江边走,立刻让人耳目一新。人家无论大小,照例是外面围着一匝竹篱,上面爬满了扁豆或牵牛花的藤叶。紫色的小蝴蝶,蓝色的小喇叭,间杂在绿叶丛中。篱笆里总有一半亩空地杂栽了不怎样高贵的花木。门外的路,在水塘或菜圃中间,三三两两的,分群拥着高大的垂柳,塘里的荷花,直伸到草岸边,红色的蜻蜓,在那里用尾巴打水。不但是看不出一点战气,而且没有一些城市的纷扰。我第一次来找避难所的时候,我立刻喊着满意了。
上新河的街有两条,去首都不远,自然是什么都有。还有个小码头叫江口,有小大轮开行巢县。江口上林立着茶酒馆和杂货店。我迁居在江滩,离江口只有一箭路。然而这一箭路的遥远,硬是两个世界,终日寂静无声。照例屋外是竹篱,竹篱外是一条青石板面的人行路,石板两面,长着尺来长的青草。左右隔壁,必相距五六丈路,才有邻居。但彼此联络不断,除了篱与篱相接之外,便是伸入云端的大柳树,枝条相连,犹如在空中横了一座翠峰。柳外面是江,然而不是波浪滚滚的大江。大江心里长了一片沙洲,长约十里,上面长满芦苇,把江分而为二,大的在洲外,小的在洲里。我们面对着是这条子江,其平如镜。每日除了那小轮经过之外,没有声息。
《红楼梦》写梦的手法也是变化莫测,不见雷同,有时象是描写一个真实的生活细节,结果却是写梦,若不细心去读,就很难理解;有时写梦通篇不用一个“梦”字,若不仔细看,不觉是写梦;多数则为直接点明,从正面展开梦境的描写,而其中有时又十分奇特,曲曲折折地写梦中梦,连环梦、梦中写梦、梦中又梦;有的前呼后应,使两梦内容互相印证……
我们第一个邻居是柳,第二个邻居是水。左边是公有的池塘,右边是邻家的池塘,后面是自己的菜园,菜园里也有一口塘。左面塘是西柳树所包围。右面塘是满塘荷叶。后面一口塘,却是绕着青芦。塘外总是竹篱,篱上爬着瓜豆藤蔓,隔了藤蔓,听到鹅鸭叫。有时两只鸭衔了一条小鱼,钻进篱眼,抢着打架。白的鹭鸶和黑的乌鸦,常常相对的站在柳梢上比着黑白。江滩上的地皮,是不如南京城内那样值钱,人家是充量的将篱笆圈着地面当院落。院落里栽遍了芭蕉,芙蓉,梧桐,鸡冠,玉簪,茉莉。便是院落里并不种花木,那门外浓厚的柳阴,罩着满地的青苔。开窗吹着任何一面来的水风,也清幽可人。
我们门外那条石板小路,顺了向下游走,不断的人家,都在高大垂柳下面临着那条子江。这里是江西新淦木商的殖民地,每幢屋子都修理得整齐疏旷。在河里有木筏铺排的浮岛,竹篱上也有牵牛花的绿藤,这是水村上异样的趣味。再向前走,由石板路爬上了长堤,到了临水人家的后面。这里更有趣了,堤外是一道小溪,里面长满了菱角蔓。人家的竹篱后门,和小的柳树丛,直伸到水里。有那采菱的小船,像一片大瓜皮,浮在菱角蔓上。船上没一人,却有打鱼的小翠鸟。堤里是围田,那杨柳成行的圈着平芜,画着绿的成圈。在柳林梢上露出一抹青山的淡影,在白云深处。
这里真沉寂极了,人家屋头上,伸出十余丈高的打竹绕梯楼,像一座小塔。呜呜的警报声来了,两个在塔上打绕子的工人,爱理不理爬下竹梯。子江边柳树阴下的打鱼人,两脚站在水草里,清理着他的渔网,偏头向天空看看。在江边上的人家,只有一件防空工作,赶快收拾了篱笆外竹竿上晒的几件衣服。但是这里人是镇静,不是麻木,你在这时由窗户里向外看看,三四个骑脚踏车的宪兵,一阵风似奔过了长户。柳树阴下,遍处是穿了灰色制服的壮丁、扶枪挺立着,飞机轧轧声,高射炮降落声,在紧急警报下发生了,水村里开始有了战争意味。我们扶老携幼,钻入平地挖[洞]上面堆土的南京式防空壕内。有几次敌机炸不远的广播电台,屋子都震动了。三十分钟后,警报拉了呜呜的解除长声。静止而死去的上新河,立刻有一声很自在的吆唤声, “卖老菱角” 。钻出防空洞,开了竹笆门外一看,一个江北妇人,头系蓝布,手挽竹篮,踏着深草中的石板路,转过了屋角。
就凭这一点,我永远忘不了上新河。
《今文月刊》于1942年10月创刊于重庆,颜悉达、汪应文、陈叔渠主编,王君一发行,发行所为文信书局。该刊封面印有 “杂文、散文、评论、新型综合刊物” 字样,可以看做该刊选登文章的标准与追求。对于该刊的刊名,该刊解释其既不是讨论今古文经之争,也不是唐宋八大家的风云月露之辞,而是反对古文的拘古泞古,因为该刊虽不反对述古,但认为古文形式固定、内容严肃、文章机械,因之以 “今文” 为刊名,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在文章的编辑方面,该刊采取兼收并蓄的方式,文言与今文皆可刊载,凡言之有据、读之有味的文章皆所欢迎。该刊所载文章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与专业性,同时不失趣味性,因此在创刊之后受到很大欢迎[5]。1936 年初,张恨水举家前往南京,次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大肆进攻华北,南京连遭轰炸。为躲避战火,张恨水便把全家迁到离城十里的南京西郊上新河居住,自己则每天下午步行到城内的《南京人报》报社办理事务,直到次日红日东升,方才下乡。张恨水在《今文月刊》发表的这篇《九月忆上新河》,追忆叙写的就是自己蛰居于南京上新河期间的见闻经历。
毫无疑问,《九月忆上新河》属于典型的小品文。作为一种特定的散文类型,小品文以短小灵活、简练隽永为特色,具有议论、抒情、叙事的多重功能,偏重于即兴抒写零碎的感想、片断的见闻和点滴的体会。明清时期,诸多文人雅士热衷于借助小品文来反映自己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趣尚,小品文进入了成熟期。现代时期,经由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探索,小品文再度兴盛。而张恨水这个主要被当作通俗小说大家的作者,其实同样在小品文领域,取得了耀目的成就。1946年5月23日,张恨水为其主编的北平《新民报》 “北海” 副刊撰写了一则征稿性质的文章,专门对小品文的内涵做了解释: “月半以来,投稿先生,大概也能分清眉目,只有散文一项,常常当作小品,投入本拦。同时也有些不爱文艺的读者,看了本版的小品,写信来质疑,认为‘这是无聊的文字’。我现在暂代小品画一界限,‘它是一种含有诗意的散文’。然而它不是诗,不是小说,也不是笔记,及一切杂文。小品就是小品,而且它决不无聊,它在轻言细语中,在低吟微笑中,有狂歌,有眼泪。不过你要大口吃江瑶柱,那我就没法子。爱吃口沉的人,你可以去吃咖哩鸡,可以去吃烤填鸭。小品它是清汤芦笋,至多是鸡丝拉皮拌黄瓜。也有人提议过,小品不必限于冲淡。这个我当然赞成。但那会更难作。因为雄浑一点,像议论文;浓厚一点,像小说;着实一点,又像笔记”[6]。以此观之,可以发现,《九月忆上新河》完全吻合张恨水称赏的那种以冲淡风格,在低吟微笑中,诉说往昔、描摹日常的小品文笔调。
《九月忆上新河》以抒情咏叹的舒缓笔调,追忆往昔,特别是对上新河周围的风光美景深表赞咏,显得最为悠然闲散、情趣盎然。与之不同,其余描写上新河往事的篇章,或多或少都流露出一定的苦闷、伤感心绪。事实上,当时张恨水一家迁往上新河后的生活,颇为艰难,尤其是张恨水往返城郊,常遭空袭,艰险异常: “南京城郊,根本没有什么防空的设备,随便在树荫下,田坎下把身子一藏,就算是躲了警报了。飞机扔下的炸弹,高射炮射上去的炮弹,昂起头来,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种震耳的交响曲,自然也就不怎么好听。但深入其境的,是无法计较危险的,因为天天的情形都是如此,除非不进城,要进城就无法逃避这种危险。炸弹扔过,警报解除了,立刻就得飞快的奔到报社。”[7]在这种紧张恐慌的情境下,张恨水很快病倒,甚至有性命之虞,乃弟张其范对当时的情形有过这样的记述: “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打进北京城半个月光景,二哥病故,丢下寡嫂幼侄,情景凄凉。我和惜秋(作者丈夫——引者注)拖着两家十口人,逃到南京。适逢大哥病在床上,他见嫂侄戴孝,揣测二哥已死,足足痛哭一个多小时。叫二嫂、侄儿到床边,深切安慰,并替他们筹划今后的生活出路。” 这时, “一家之中,集合到将近三十口人。不说生活负担,不是个病人所能忍受,而每当敌机来空袭的时候,共有十七八个孩子,这就让人感到彷徨无计。”[8]
迁居上新河期间,张恨水一家的日子过得其实非常艰难,这与《九月忆上新河》中透露出的那种安闲享受心境完全背离。可是1942 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当张恨水再度回首往昔时,却完全沉浸于对上新河安宁怡然岁月的描绘述说之中。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九月忆上新河》中的往昔岁月是张恨水在战争硝烟中,怀想出来的浪漫化形象,它 “是一种丧失和位移,是个人与自己的想象的浪漫纠葛”[9]。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简单判定张恨水笔端那个美妙的上新河是虚假无效的,只能说那是张恨水受战乱刺激而竭力捕捉并构设出来的特定上新河模样,经由这番浪漫化的回溯,作者得以从战争灾难中暂作逃遁,进而自我安抚。哪怕记忆中的上新河模样和上新河时光是脆弱的、粉饰的、想象的,但战时语境下作家文人的身份依靠就是由类似的微小记忆所顽强维系着。
三、《两句八股颂上海》:游戏笔墨与畏沪心结
1946年2月11日第4版《和平日报》刊载有署名 “恨水” 的文章《两句八股颂上海》,全文照录如下:
自太平洋战事发生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和上海报纸写文字。照着八股的规例说,这应该是个破题。写八股究不是无题诗,可以不要题目。凤子先生在上海见了面,没三句话,就和我要稿子,可又没出题目,让我写什么呢?答应了凤子先生,以人格担保,决对写一点奉上,只是找不着题目,难于交卷。一误就是两日。离沪之时,承梅子社长用汽车送我赴虹口再托朋友送上车,临别,再把人格担保一次,决对到京写稿。过了年,过了初一初二,还是没有题目。到了初二晚上,我想,别让我的人格发生摇动吧?立刻写。虽然有人约我上夫子庙听戏,也忍痛牺牲。然而,儒林外史曾用这两字挖苦过斗方名士之丑态的,又转上我的脑筋,题目在哪里?
好在我十岁的时候,还作过八股,在那极枯燥的文域里,用一种兜圈子手法作文的技巧,我还记得一点。传说有这么回事,有人把四书五经上的句子都当题目尝遍了。最后,老师把每章书文头上的那个圈儿,也出了个题。这位先生真有他的那一手,他作破题说:
“大圈在上,众人之言可知矣。”
这很好,冒得住下面任何一段书文。也有别一个说法,那破题了是:
“圣人未言已有象,故先之以赞美焉。”
这叫暗破,也好。不过破题以下是承题,至少得来三句,且须一转,一反问,就不曾听说有人作过圈圈那个承题的。在这里可以知道叫碰头好的文字,实在不容易动手,因为是太空洞了,换句话说,就是言之无物。这几年在重庆,很少给人捧场,所以文字胡说八道,总可以说得出。于今胜利了,见着人,尤其是对久别重逢的上海,应该来个好。不想我太没出息,在上海住了四五天,竟找不出一件叫好的题目。想来想去,只有拉出四书五经文字上那个圈圈儿的破题,来作一个譬喻,倒可以象征我这点敬意。
有人说,你能不能用这个圈圈,给上海作个破题呢?我说,若是不严格的指上海,岂止破题,承题也行,献丑了。
“在此圈中,生活始有所限焉。夫两仪未分之前,一元犹混之俟,故不知所谓点线面体也。乃画之以三百六十度之一圆形,则圈里之为圈里,槛外人得不瞠目相对也哉?(作八股用新名词,当然是笑话。好在这是打油诗之类,内行人原谅了罢)”
之所以断定《两句八股颂上海》属于张恨水佚文,乃基于这样三个原因:第一, “恨水” 是张恨水最为常用的笔名。第二,《两句八股颂上海》提到该文是由凤子约稿所作,而凤子曾为抗战时期的重庆《新民报》担任副刊主编,张恨水则与张友鸾、张慧剑、赵超构一道并称为重庆《新民报》 “四大台柱” ,当时张恨水与凤子即交往甚密。其后,张恨水对影视戏剧投入了较多关注,作为著名戏剧演员的凤子与张恨水的关系日渐紧密。抗日战争结束后,《扫荡报》易名为《和平日报》,《和平日报》上海版社长兼总主笔万牧子聘请凤子、程仲文、谢东平、冒舒湮等为主笔,凤子还兼编《和平日报》的 “海天” 副刊,这时凤子出面向熟识的张恨水约稿自然水到渠成了。第三,1945 年12 月初,张恨水告别重庆,1946年元旦张恨水抵达南京,农历新年年底张恨水在上海短暂停留后,旋即又赶赴北平主持《新民报》[10],张恨水这段经历,恰好契合了《两句八股颂上海》中的时间线索。
《两句八股颂上海》从自己被编者约稿,然后一再延期交稿说起,最终受八股文文体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的固定格式的启发,模仿给四书五经等古书上圈点作破题的方式,为上海写了两句赞语。显然,张恨水此文的写作带有鲜明的游戏笔墨色彩,这也导致了《两句八股颂上海》这篇文章的价值意义较为逊色。不过,《两句八股颂上海》虽然是一篇游戏笔墨式的小文,无关痛痒,但从作者自白的,在重庆期间发表过许多 “捧场” 的言论,如今胜利重回上海后,反而 “找不出一件叫好的题目” ;到将上海形容为一个大 “圈” ,而以瞠目相对的 “槛外人” 自况。凡此种种,均流露出张恨水对上海的畏惧感受。由此一来,这篇名为 “颂上海” 的文章,实质上表达的却是 “畏上海” 的主题。高产且极受市民读者欢迎的张恨水,是商业出版的宠儿,他也从中获利不浅,并且张恨水本人也参与多家报纸副刊的编辑工作,也就是说张恨水自己便积极投身于文化商业浪潮中。按理说,与商业出版紧密绾合的张恨水应该对上海这座商业化的现代都市怀有好感,可事实不然,面对上海,张恨水非但未显亲近,反而表现出如 “槛外人” 一般与上海格格不入的疏远感。类似的 “畏沪” 情形,在现代文人身上及其作品内部都十分常见,现代文学史上除却新感觉派等少数作家之外,很少有人不曾对上海这座商业化的城市表达微词甚至深表不满。某种意义上,畏沪感已然构成了现代文人和现代文学的普遍现象。正是在这一点上,《两句八股颂上海》这篇似乎可有可无的文章沟通了文学史层面的某种集体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