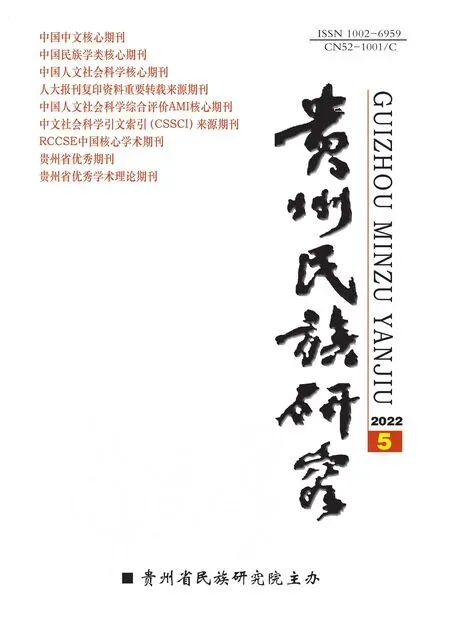吐鲁番涉医文书所见晋唐时期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认同研究
李艺宏 王兴伊
(1.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民族研究院,四川·成都 610041;2. 四川旅游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 610100;3. 上海中医药大学 科技人文研究院,上海 201203)
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中原文化随着西汉对西域的经营进入西域地区,“在思想观念形态上,吐鲁番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汉文化可以追溯到高昌郡时期”[1]。唐代的西州有中央政权主导下体系“完善的官学教育”[2]以及“佛教寺院为主的私学教育”[3],但都以儒家《五经》为主要教材,儒学在高昌深入人心,“成为每个人安身立命的价值准则”[4]。晋唐时期的儒家思想深入吐鲁番地区人民生活的各方面,“孝观念在佛教、道教中有结合被唐西州的胡人所接受”[5],还成为“西州下层女性的社会道德衡量标准”[6],“《孝经》被奉为陪葬品”[7]。
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众多族群在这里交会,中医药共同为这里各族人民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也成为其预防、治疗、诊断的选择,更是“带有价值观和好恶倾向的选择”[8],在吐鲁番长期多民族历史长河中,这样的医药文化亦是多族群的文化共享。“墓葬文化可体现文化特征及其文化认同”[9],因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是晋唐时期吐鲁番文化的重要历史记忆,也是晋唐时期多族群在这里共享的医药文化。文本以吐鲁番涉医文书为中心,分析晋唐时期吐鲁番涉医文书中儒家思想并揭示文化认同。吐鲁番涉医文书展现古代边疆地区人民对中原儒家文化的认同,是中国多元文化的例证,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经各族人民自主、自觉交往的具体叙事和生动表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着积极作用。
一、吐鲁番历史与出土文献
(一) 吐鲁番的历史沿革与民族构成
吐鲁番在传世文献中因地缘、文化等因素有多种名称。 《史记·大宛列传》 《汉书·西域传》称为“姑师”。“姑师”在被汉朝征服后余部改称“车师”,今吐鲁番一带。 《后汉书·西域传》 称“车师”,车师分前部、后部,因此在《汉书》中有“车师前后王”。由于两汉对西域的经营,屯兵屯田、置戍己校尉,后取名为“高昌壁”,高昌逐渐发展,魏晋时期初具城市规模。此后,吐鲁番地区经历了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西州回鹘王国……今天的吐鲁番。高昌郡时期(327-460):东晋咸和二年(327),前凉张骏置高昌郡,随后历经前秦、后凉、西凉、北凉。高昌国时期(460-640):北凉承平十八年(460),太守阚伯周在柔然的支持下,自称高昌王,灭北凉建高昌国,其后张氏、马氏、麹氏四姓相继称王。唐西州时期(640—840):贞观十四年(640) —九世纪中叶,唐军数万兵临高昌城下,高昌王麹智率臣民归顺唐王朝,唐置西州。
高昌的原始民族为姑师人,两汉期间,汉与匈奴长期争夺吐鲁番,车师人部分死于战争,大部分受战乱影响迁徙别处或融入其他民族,原土著车师人部分与汉人逐渐融合。从西汉在西域屯兵屯田开始,大量汉人进入吐鲁番地区,提高了盆地生产力水平和灌溉能力。到唐西州时期,吐鲁番地区迎来汉人的第四次大移民[10],形成了“儒学为正统的文化氛围,移民也居他乡却少有异乡感”[11]。
(二) 晋唐时期吐鲁番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新疆地区沙漠很多、高山横亘,只能沿天山南侧或是昆仑山北侧西行,因此西域段最先为南、北两道。《史记·大宛列传》载“初,贰师起敦煌西,以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北道”。《后汉书·西域传》指出了高昌乃西域之门户,更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两汉丝绸之路从兰州以西随乌鞘岭,过河西走廊,经武威、张掖、酒泉、安西、敦煌,到达新疆。“在新疆罗布卓尔分两道:北道沿天山南坡西行,经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在西翻越葱岭到苏联境内;南道沿昆仑山北坡西行,经若羌、且末、于田、和田,跨葱岭到达阿富汗、印度等”[12]。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西域段又发生重大变化,在中断干道的开辟上取得新进展,“《汉书》中的新道到北魏时成为官道”[13],中西交通变为三道,《魏书·西域传》载丝绸之路由两道变为四道。丝绸之路从两汉时期的两道增为三道,而“北魏时的四道实际上是由玉门至车师一途”[14],也就是三国时期的北新道。
隋朝时期,中西交通为北、中、南三条道,“新道”从敦煌玉门关西北出发,过横坑,沿库鲁克塔格,进入大海沙,至柳中,到高昌。《隋书·裴矩传》称伊吾、高昌、鄯善为“西域之门户”,可见吐鲁番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
丝绸之路的路线,除正史中提到的“南道”“北道”“中道”外,在西域地区纵横展布,吐鲁番从两汉时期就是中段北道的起点,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新道”的起点,丝绸之路由“南道”向“北道”转移。还有“以吐鲁番为中心四面散射的交通路径”[15]。围绕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集散地——吐鲁番,有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线,东西方商品和往来人员聚集于此,把当时的欧亚文化中心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物质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
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然气候和重要的交通位置,随着丝绸之路开辟和中西交往频繁,吐鲁番逐渐成为丝绸之路中段的贸易重镇和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更是西出西域中段的门户,促进了吐鲁番地区人口增多、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成为当时中西方交往的商贸重要节点,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镇。
(三) 吐鲁番出土文献
地处亚欧大陆腹地的吐鲁番地区高温少雨、气候干燥,地理环境特殊,使得写本文献能埋葬在地下而千年不腐。新疆地处四大文明的交汇处,是“一带一路”经济文化交流的核心区域,吐鲁番是丝绸之路的重镇,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中原医药在这里播散,可以反映其产生、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深层医学沉淀。“出土文书反映丝路实态和文化传播”[16],反映出吐鲁番地区人民对中医药文化的接受和运用。吐鲁番涉医文书是吐鲁番文化的历史记忆,这种形式“以专门用于书写文字的材质上的书面文献,其功能是跨越时空传递储存信息”[17],可以让我们了解晋唐时期儒家思想对当地人民在面对生命、疾病、健康时的影响。
(四) 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与历史
吐鲁番文书不仅“具有地域性的意义, 更因为它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而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与接受的通性”[18],可以为医药文化的传播及吐鲁番地区对中原汉文化的吸收提供史料,也为儒家思想在吐鲁番的流传提供历史例证。吐鲁番文献来自“佛寺洞窟、古城遗址、古墓葬等,墓葬出土文献或有宗教意义,或为墓主遗愿,或填棺以防出殡、埋葬时尸体移动等等”[19],是墓主或是使用者的医药文化倾向和文化认同例证。“中医出土文献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20],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是吐鲁番人民历史上医药选择的见证,是吐鲁番人民医药文化认同的见证。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是吐鲁番人民医药文化的历史记忆,边疆地区人民对文化的认同表达,被埋到地下逾千年后呈现在我们面前。
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所见儒家思想
吐鲁番不仅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种宗教在这里传播、共生,儒学、道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文化都在此驻足,为此地文化多样性带来了新鲜的活力,而且也以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中原医药的文化背景根植于中原儒道思想中,“儒家学说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21],其产生和发展都有深深的儒家思想烙印,因此对吐鲁番涉医文书背后的儒家思想进行分析。对中医药的使用是吐鲁番人民面对疾病时对中原医药的认可和自然的选择,更体现了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而这些认同就体现在吐鲁番涉医文书中。西域地区人们崇尚儒家文化,医学思想和理论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的“三行”“四德”“六行、六礼”“五亲、九族”成为吐鲁番人与人之间社会准则和价值判断。
(一) 儒家社会道德准则
高昌国时期,中原儒家经典在吐鲁番流行,儒家文化就已被吐鲁番地区人民所接受。成书于西汉时期的《急就篇》,又称《急就章》内容涉及姓名、身体、病患、衣物、器具、宅舍、仕宦、牲畜、百兽等,堪称当时生活的“微型百科”,虽然《急就篇》是西汉时期的蒙学课本,但书中“有62个人体生理部位器官、41种病名、36种药名,以及灸、刺、用药三种治疗方法”[22]。高昌时期的《急就章》 残卷 有:60TAM337:11、Ch 407V(T Ⅱ2024)、2004TBM203[23]以及MS 3562、MS 3723、MS 3939、MS 10452、MS 10541、MS 10568。MS 3562+MS 10541缀合,根据《急就篇》 内容补充为:“捲捥节爪拇指手,胂腴胸胁喉咽”[24],正是生理部位器官的残卷。
在墓葬砖志中亦有表现其墓主人或是家人的信仰和文化倾向。《高昌延和三年(公元604年)墓》:“故田曹司马,鞏孝感,禀资温雅……可谓雍穆九族,攸邦之轨则者”[25],主人名为“巩孝感”带有浓厚的儒家“孝道”思想,墓表中“九族”,亦是儒家家族文化的代表。《高昌延和七年(公元608年) 张叔庆妻子麴太明墓表》“故张叔庆妻麴氏女太明,稟性贞洁,体行纯笃,四德内融,休称外著。用能绢,皆九族,雍穆五亲,幼仕舅姑,有敬顺之名”[25],中亦有儒家文化“四德”“五亲”“九族”的表达。《高昌延寿九年(公元632年) 张伯玉·墓表》“春秋七十有三,於延壽九年五月甲寅朔,二日乙卯,致使六親哀[哉],九族悲酸。”[25]可以窥探在高昌国时期,儒家文化就渗透到了吐鲁番地区。
唐西州时期,儒家文化更深入吐鲁番人们的生活。《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8年) 张子庆萋墓表》“夫人四德内明,荣顺尅著。幼事舅姑,有敬顺之名,雍穆五亲,有休誉之称”[25];《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 刘住隆妻王延台墓志》“惟夫人讳延壸,志性忠贞,慈深素质。家风远振,五德备躬。不期积无盐,乃忽染患。医药方疗,其疾不廖”[25];《唐龙朔二年(公元662年) 张君夫人毛姿台墓志》“乡闰叹其和柔,鄰里仰其贞顺。祖为参军,孝悌为心依仁作志。……四德不日而成,六礼淡时而备”[25];《唐麟德元年(公元664 年) 张氏妻麴姜墓表》“……等彼珠蓬,节义贞鹿……,故得三仪。外振六行之美,方兴四德内容……”[25];《唐麟德二年(公元665年) 张君妻麴胜墓志》“即兰州广武府折衡麴仲第二……三行夙著,四德早闻”[25];《唐前封二年(公元667年) 范永隆夫人贾阿女墓志》“妇功四德,一行不亏”[25];《唐仪凤年间(公元676-678年) 后富君夫人张氏墓志》中“妇德允备,母仪□就”[25];《武周圣历三年(公元700年) 张智积妻麴慈音墓志》中“四德园备,令淑有闻”[25];《唐开元三年(公元715年) 张公夫人麴娘墓志铭》 “四德孤影於千龄,六行独高于万祀既尽美矣,而有终焉。方期千月,异登五福无爽”[25]。这些墓志中都有对女性“三仪”“四德”“五德”“六行(六礼)”等儒家思想的弘扬,也侧面反映出儒家忠贞、孝道、温和等理念在吐鲁番地区的扎根和发展。
(二) 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
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儒家仁爱思想渗透到了医学中,医术就成为了一种仁心仁术”[26],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医者对待病人更加友善和关爱。Дx.18165V“智信五常法,即现也,神农、皇[黄]帝种种医论,因此流行至今未绝,时林五浊后”[27],其中的“智信五常法”即是儒家思想中“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与中医医学相结合对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且文中“神农、皇[黄]帝’都是先秦时期中原的两大医学流派”[21],反映了吐鲁番人在面对疾病时,对古代中原名医良药的急切需求,是对中原医药疗效的认可及中原医药文化的认同。“用医学知识保障人的生命和健康,解除患者痛苦的医学人道主义思想正是建立在儒家生命神圣论基础之上”[28],“儒家仁学重视人的生命,从孝道出发重视保持身体的健康平安”[29],这些儒家人道主义精神在吐鲁番医药文书中被充分表达。MS 1074《解毒药方》残件“怜爱所语人,人皆信受”[30]不仅是对医者给病人看病的态度做了要求,更是在医学伦理上的要求。
汉语医药文献是吐鲁番医药文书中的重头,其中儒学中医理论也相应地在吐鲁番文献中有大量表达,如天人合一、阴阳五行、药物的君臣佐使等。《素问·宝命全形论》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体的健康应该顺应四时的变化。ДХ.02683《針灸甲乙經》:
是以春夏歸陽爲生,歸秋冬爲死;反之,歸。秋冬爲生,是以氣少多逆煩皆爲厥,有餘者厥。一上不下,寒厥到脒。□者秋冬死,老者秋冬生。氣上不下,頭痛顛疾,求陽不得,求之陰矣。冬三月之病,=(病) 合於陽者,至春正月,脉有死徵,皆歸出表。冬二月病,在理已。葉皆煞春,陰陽皆絕,期在孟春。=(春) 三月之病,陽病曰煞。病,至陰不過十日,陰陽交,期在濂[31]
四季变化对疾病的变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因而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应顺应四季的变化。73TAM509: 8/6《唐书牍稿》,这是一篇唐朝涉医书信,其中提到了天气变化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
秋末漸冷,惟所履清勝。前者使到,承違和。後信還,已抽減……緣患腰,迥轉不得,見每熨後日可減,即去,請無責及[32]
前者述由于天气变化导致身体不适,后者言患腰疾不能回转,经每熨治后缓解,可知唐代普通百姓在生活中面对天气变化所带来的腰疾时候知道如何自己救治及减轻病痛,也反映了当时人们遵循四时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及时调整身体的健康状况,更是对儒家思想影响下医药文化的认同。因此,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吐鲁番医学亦有其儒学的色彩,吐鲁番地区的人们也吸收中原文化,并自觉将其作为自身文化而运用和传承。
(三) 儒家文化的“孝”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吐鲁番地区儒家经典《孝经》 被奉为陪葬品之一。《高昌建昌四年(公元558年) 张孝章随葬衣物疏》中有72TAM 169“孝经一卷”,同墓葬中出土了古写本《孝经》残卷;《高昌延昌三十七年(公元597 年) 张毅随葬衣物疏》73TAM517∶24“孝经一卷”;《高昌重光元年(公元620年) 缺名随葬衣物疏》72TAM205∶2“孝经一卷”;高昌重光二年 (公 元621 年) 张 头 子 随 葬 衣 物 疏》73TAM116∶19“孝经一弓[卷]”[33]。不仅吐鲁番地区活着的人把儒家孝道作为宗法社会的衡量标准之一,还在死后随葬《孝经》带到地下世界。
1. 儒家“侍疾”行为
父母生病时,儿女要“侍疾”,这是儒家孝文化的一种体现,在吐鲁番文书中也得以体现。64ATM29∶44《唐咸亨三年新妇为阿公录在生功德疏》载:
阿兄在安西日已烧香发心,请佛生禅师读。一千遍金刚般若经起□□□□□彼□□□日设斋供养,并诵杂经六□□□忏悔。复于安西悲田寺佛堂南壁□□□众人出八十足帛练,画笙全、主丝等菩萨变一捕(铺),又发心为阿公修造,愿知。复至二月七日,更请十个尼僧□□□出罪[34]。
这份功德疏记载了儿子在父亲患病时为父亲烧香诵经、绘佛像,以祈求父亲早日康复的行为。子女为患病的父母乞求减轻病痛、早日康复是儒家孝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残卷中通过做功德、乞求父亲早日康复,是儒家孝道思想在佛教活动中的体现,受儒释双重文化影响。这也是唐西州人民“孝道思想”对佛教疾病观行为影响的体现。
如果父母生病不能在身边“侍疾”,就写信问候,并寄钱买药。64TAM5《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三》反映了身处异地的儿子对母亲疾病的关心:
平安以不?语□□□好努女力女看侍阿郎阿婆□□□□时道阿婆口气差未差□□□□在,次张住海 将藤麻四两□□□时检校取,若后有使人来□□□报来,并更有须提药□□□□麦绍贞将信金钱二文银□□□问语阿兄[35]
从文中可知,在母亲身体不适时,李贺子不能在母亲身边亲自侍奉,寄给母亲“金钱二文银”以供母亲买药所用。MS 7310《贤愚经第一》“不惜身命。以能身肉。济救父母危险之命”[36],文中子女不惜以“身肉”求父母健康,这与“佛教传入中国而成的愚孝‘割股疗亲’儒学思想”[21],有相似之处。
2. 儒家“守孝”
儒家宗法社会体系下,父母去世一般官吏遭丧都要回家守孝。唐西州父母亡逝,卫士可以请假服丧,体现儒家“以孝治国”的思想在唐西州的运用。宁乐28(5) +21(2),《唐开元二年闰二月蒲昌县牒为卫士范君住母亡准式丧服事》:
蒲昌縣 衛士范君住母楊——蒲昌府:得上件人辭,称母今月五日身 壯勘,責得里正趙君傲、保人劉叡 者范君住母亡。勘責不虚,别牒府季終舉申者。此已牒鄉訖,牒至准式開元二年閏闰二月[37]
宁乐18(2) +14(2) +7(3),《唐元二年三月一日蒲昌县牒为卫士麹义逷母郭氏身亡准式丧服事》:
遣訖,今更□□□符牒,知和均既替姜德臨川城防禦,牒城並牒和均知。玉示二日 郭年肆拾伍——人辭,稱母今月二十五日身亡,请處分者。准麹義逷母郭氏身亡,勘責府同,牒上州户曹 式者。此已各牒下訖。牒至准狀,故牒。開元二年三月一日佐史张義三月三日録事麹相受司馬闕檢案。玉示三日[37]
在吐鲁番文书中有父母去世,学生为了不中断学业,找人替自己去上学。66TAM44:114的《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 西州高昌县史□备牒为隆达等遭丧以替人入学事》,并且本件文书还盖有“高昌县之印”四方:
關替人孟須……通等牒□件隆逹等遭[丧]訴解見 学者……等問並情願入学不虚收領故牒 贞觀甘二年六月廿三日□俻牒 尉衞贇[35]
遭丧一般指双亲之丧,儒家守孝思想也影响着唐西州的学生,尽孝学生可以申请找人替其入学,且还盖有官家印章,可见这类事情已有明确条款,应不是个案,是唐西州时期的普遍情况。
3. 替生病的父亲服兵役
古有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替父从军的故事,在唐西州时期就有父亲年老带病,儿子代行兵役的孝举。72TAM225:22(a) 《武周久视二年(701年) 沙州敦煌县悬泉乡上柱国康万善牒属以男代赴役事》:
牒萬善今簡充馬軍,擬迎送使。萬善焉先帶患,瘦弱不勝驅使,又復秊[年]老,今有男虑琮,少秊壯仕,又便弓馬,望將替。處今隨牒過,請裁。謹牒。久視二秊二[月][日]懸泉鄉上柱國康萬善牒 付 司[34]
可见唐西州时期的儒家孝道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父母亡逝请假服丧政府可以出具证明,而父亲年老体弱、身体多病,儿子也可以替父从军,免除父亲的兵役。
对于高昌国时期的文献考察,“高昌国并非化外的异域,而是华夏之邦的重要组成部分”[35],对涉医文书的考察,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医药文化仍以中原儒家文化为主,这是吐鲁番人民对自身儒家文化身份和地位的自觉和把握。
三、晋唐时期在吐鲁番地区中医药文献中的儒家思想认同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成的重要作用
(一) 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人民主动接受汉文化
中华文化在新疆的传播历史悠远,“古代中国深深植根于文化生活各个层面的儒家天命观、天人合一、及老庄的虚无观,被广大群众作为生活的纲常理论”[38],被吸收到吐鲁番医药文化中。“文化认同反映了生存斗争的紧迫感和永恒性”[39],吐鲁番医药正是吐鲁番人民对生存斗争的紧迫和对生命永恒的尊重而自愿选择,这正好与“儒家的以人为本、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的人本思想”[40]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文化认同就是“各民族之间的彼此认同,各民族之间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彼此认同,才能构筑起中华文化共同体”[41],而这种“共同体以古老的事实而存在”[42],以出土文书所反映出来——就是晋唐时期吐鲁番人民在接受主动向中原文化靠近的过程中表现出来。
晋唐时期,以吐鲁番为代表的西域地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多元一体格局的典型地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地区,是“联系多民族的一条政治、经济纽带,促进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祖国的统一”[43],各民族医药文化在此地交流融会,增强了对中原中医文化、中原汉文化的认同感,对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积极作用。“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存在的意义和来源,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和联系的纽带”[39],历史上吐鲁番地区人民对中医药文化和中原汉文化的认同,是吐鲁番地区人民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文化基石。 《名堂经》 《针灸甲乙经》 《本草经集注》《张文仲疗风方》 《刘涓子鬼遗方》 《治赤穀方》《西州续命汤》 《伤寒杂病论·小青龙汤》 《伤寒杂病论·蛇床子散》[44]等中原医学经典、针灸、方药在吐鲁番地区传播,是吐鲁番人民对中原医药文化认同的最好例证。习近平主席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历史上各民族间交融交流,“中华文化沉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45],而我们的悠久灿烂文化正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涉医文书就是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人民在生活中不断实践和交流的文化宝藏,也是边疆地区人民在历史上主动认识、接受、认同中华文化的重要例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历史文化基础。
(二) 晋唐时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医药文化在吐鲁番地区传播所起的文化认同作用
纵观吐鲁番地区的医药文化,从高昌国时期就受到儒家医药文化的影响,在高昌时期,其民众的医疗健康都打上了深深的中原儒家医药文化烙印,更是高昌人民对中原文化的主动接受和认可,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在文化和思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文化具有真正生命力的基础是保持先进性和强大的文化力量”[46],晋唐时期中原文化处于世界先进文化的顶端,其开放包容的民族、文化、宗教政策,使吐鲁番地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有坚实的文化基础保障。虽然医学理论多元,但多源于晋唐医药理论,有一部分还保留了唐代医书的原貌,这对古代医药典籍的保护和医药文化的传承有重要价值。吐鲁番出土《张文仲疗风方》在中原传世文献中不复存在,却得以在吐鲁番地区出土。外来医药理论通过以吐鲁番为代表的西域地区传入中原,充实了中医药理论,拓展了中医药文化视野,也为唐以后中原医药的发展奠定了多彩的基础。这是中医药能够经久不衰、能经受住历史发展的考验而传承下来的原因之一,并继续对人类的健康做贡献,提供了历史上中医生存发展的例证。“历史记忆是人们通过文本、图像等媒介获得和保存的关于历史事件的记忆,传统文化是民族历史记忆、民族精神的载体”[47],吐鲁番涉医文书是中国传统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人民对中原儒家文化认同的历史记忆形式得到充分体现。
(三) 外来文化和医药理论丰富了吐鲁番医药,对中医药的发展和传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性
从吐鲁番文书中可见古印度医学的传入拓宽了中医的理论和诊疗技术,佛教、波斯教等外来文化的传入点缀了中医药文化的多样性,中医药对外来医药的包容、吸收并转化,为中医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吐鲁番为代表的“边郡地区医疗水平和医事状况,因其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域外医学影响,医疗状况有可能较高”[48]。“汉打通西域的门户,大力传播中原文化,同时允许多种文化在西域同时并存”[49],外来医药随之而来,为医药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如《张仲景五脏论》中吸收了部分古印度医学理论,而本草类著作《新修本草》 《海药本草》等都有大量外来药物。“印度传统医学文书《鲍威尔写本》 《毗卢本集》《医理精华》 《八支心要方本集》 等印度医学典籍,于阗文《耆婆书》 《医理精华》,龟兹文、梵文双语《百医方》,犍陀罗语医学文书“达子香叶散”,叙利亚语《用雪松油治疗脱发症药方》,还有粟特语、回鹘语等医学残件”[44]在吐鲁番地传播,为吐鲁番的医学注入新鲜血液,也显示其医学文化的多元性。晋唐时期吐鲁番医药文书受儒道释、景教、摩尼教、祆教等宗教文化影响,吐鲁番医药文书中相互吸收、取长补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吐鲁番医学文书。宗教本来就是观念,也是文化的代表,吐鲁番这种包容的宗教文化,为一带一路提供了一种交流模式,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四、结语
吐鲁番涉医文书是吐鲁番医药文化的载体,是晋唐时期吐鲁番历史记忆的载体,是吐鲁番人民文化认同的载体,是我国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处四大文明的交会之处和特殊的气候条件,千年前的文献得以展现在今人的面前。吐鲁番医药文献不仅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巨大影响,还接受了周边民族和文化的精髓,并转化吸收、成为己用,因此吐鲁番涉医文书中的杂糅化是多文化交流、多民族融合共生的生动例子。晋唐时期吐鲁番医药是以中医药为主、吸收外来医药,并有其地方特色的多元一体形式。吐鲁番涉医文书是连接文化交流、交融的纽带,而吐鲁番地区是民族融合和交往的棋盘。吐鲁番多民族、多文化通过医药这一具体的媒介,展现了文化共生、多民族共存、开放包容的场景。从晋唐以来,中医药就在丝绸之路上起着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也是丝路沿线人民健康的福祉,中医药文化智慧在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中还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古人的智慧,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