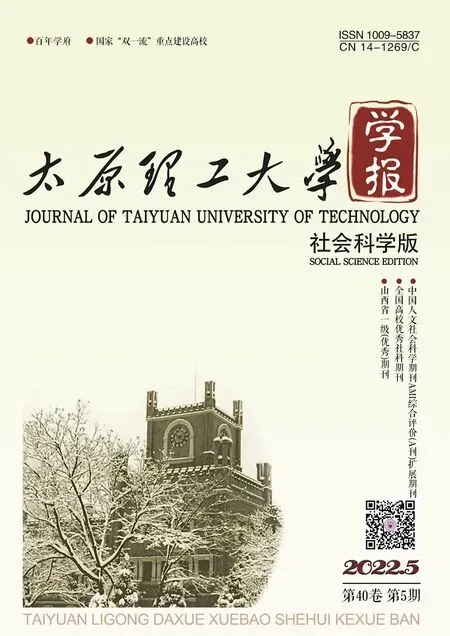汉初伦理化自然观的逻辑进程
路高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上海 201602)
汉初作为子学与经学的转折点,使人对自然万物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子学兴盛的战国时期,是“理性觉醒”和“思维伸展发达”的时代[1]8-9。此时,天的神圣性和伦理性不断地被剥离,而自然性和规律性则不断地被突显。荀子更是提出了“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2]375,把是非成败的原因归本于人之所为而非天之所预。对此,叶适给出了“人之所自为而天无预”的评价,批评荀子背离了“尧舜传之至于周”的“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的传统[3]650。而实际上,荀子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代表着战国中后期诸子自然观的主要趋向。
然而,到了汉初,天的神圣性和伦理性却又不断地被强化,以至于发展出了“天人相通”“天人相与”“天人一也”的伦理转向。对于这种现象,有学者认为是源于贾谊对“德”的形而上学的提升,使儒家伦理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4],但其忽视了贾谊的“德”是因为道家的“道”和“气”才获得了形而上的意义;也有学者注意到《淮南子》在“援儒入道”后,强调人的主体自觉意识,突出了天人之间的伦理关系[5],但其没有看到这是《淮南子》在“物类相动”的认识基础上,通过“天人相通”的伦理证明而实现的;也有学者主张董仲舒“天人相与”的伦理观是基于对历史与政治认知的主观性阐释物,而不是对自然万物的客观性说明[6],其忽视了董仲舒与贾谊、《淮南子》的思想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以下所论将结合这些问题,尝试对汉初自然观的伦理转向进行综合分析,希冀从中能够获得有益的启示。
一、“道德施物”的气物生成论
西汉建立之初,统治阶层不重儒术而持黄老道家“无为而治”之策。黄老思想注重从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中察知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反对人的恣意妄为,承扬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促进了汉初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贾谊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儒道,提出了以儒家理想为旨趣的“道德施物”的气物生成论。
(一)道为无形之气
道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核心范畴,由道家所首倡,可被理解为宇宙的实体、万物的本原或普遍的规律[7]1。贾谊继承和发展了道家的道论,提出了“道者无形,平和而神”和“道德之神专而为一气”的观点[8]325-326。其中,“道者无形,平和而神”是说道没有任何形体,而且平淡和顺、微明不彰、变化莫测,也可以将其理解为“道的本质因为虚所以没有形体,不偏不倚容和万物而神秘莫测”[9]267,或者是“道本身没有形体,但是却宁静而高深莫测”[10]262。在贾谊的思想中,“平和而神”的无形之道居于万物本原的地位,与老子的主张基本相同。但不同的是,贾谊在“有”的意义上,又将道理解为无形之气。
最早对道进行“有”的质料性阐释的是《管子》。《管子》提出以气解道的“精气”说:“抟气如神,万物备存……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11]493贾谊受此影响,进一步发展了“精气”说,并将其运用到对儒家思想的诠释中。他认为:“道德施物,精微而为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为目,目成也形乃从。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气,莫精于目。”[8]325其意在言明,“道德施物”是先从精微的眼睛开始,然后才有其他部分的产生,而这些都是“因之在气”的。据此,有学者指出:“‘道者无形’,既看不见,又摸不着,但却不是空无一物的‘无’,它就是‘气’”[12]。所以,在贾谊的思想中,道就是无形之气,而这样的道,其运作的第一步是“冰而为德”。
(二)道冰而为德
“道冰而为德”中的“冰”为动词,指凝结,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德由道凝结而成。由此推断,道不仅具有本原的意义,还具有质料性。同时,道又是无形之气。所以,“道冰而为德”也可以理解为“气冰而为德”。
气在未凝结之前,无形无象,不容易被人察觉,在德的状态下则开始有可见之形。贾谊曰:“德者,离无而之有。故润而腒然浊而始形矣。”[8]326可以说,德是道的具现。而这个过程就是气的“浊而胶相连”,进一步说就是气由清明无形的状态,凝结为混浊相稠连的形态。然而,这里涉及气如何凝结的动力问题。对此,贾谊并没有清楚说明,而是进一步提出了性的概念:“浊而胶相连,在物之中,为物莫生,气皆集焉,故谓之性”[8]326。显然,贾谊是把气凝结的原因归为性,但这不是说性具有独立性,因为性仍然是德的属性,而德又是由气而来的,所以性不可能具有独立性。那么,据此可以推断,贾谊的气是自为的,也可以说是自然的。如此的话,道作为本原,不仅是质料的,还是自为的,这一点在“道冰而为德”的“六理”中得到了具体展现。
(三)德有六理
贾谊认为“德有六理”:“道、德、性、神、明、命。”[8]324其中不仅有德本身,还包括道,而加之道为无形之气,德又为道的凝结,那么也就意味着无论是无形的气,还是产生德的“浊而胶相连”的气,都是德的属性。同时,德的其他属性,也是气的具现。
贾谊用玉的特性来解释德的属性。他说:“寫德体六理,尽见于玉也,各有状,是故以玉效德之六理。泽者,鉴也,谓之道;腒如窃膏谓之德;湛而润厚而胶谓之性;康若泺流谓之神;光辉谓之明;礐乎坚哉谓之命。”[8]324这里用玉像镜子一样的光泽来比拟道,取自于镜子能映照万物,并将万物的形状完整反映出来。在贾谊看来,这是因为镜子映照万物的特征与“道”的空灵通达相通,而玉的温厚如脂膏的凝结则符合“道冰而为德”的意旨。同时,“道冰而为德”的过程,又是气的“浊而胶相连”,相似于玉的“湛而润而胶”的特性,所以用它来比拟德的性。另外,这一过程又是道自发演变的过程。道自然而化,如同玉像音乐一般静谧的流动性,可以称为神。而从“神气在内则无光而有知,明则有辉于外矣”[8]326的表述可知,明是神在外的显现,所以用玉显现的光泽来比喻明。关于命,则取自于玉坚固的形体,这是玉受“道德”之命而“非以嗜欲取舍然”[8]326而成的。
总的来看,所谓“六理”就是事物具有的六种特性,它们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内在于德本身。同时,“六理”还包括道和德,这就意味着事物所有的特性都是来自一元的道。而道即是气,所以“六理”也就是气的六种属性。在贾谊看来,气正是依靠“六理”而生成了万物。
(四)六理为生者法
贾谊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六理”,德才能够生出“阴阳、天地、人与万物”,并称之为“生者法”[8]325。这也就是说,万物由德而生,又效法于德,而德又来自于道,道又是无形之气,所以无论是万物自身,还是它们效法的“六理”,又都源于气。这就完全排除了在此岸世界有一个彼岸世界的可能性,也就取消了人格神在人间的地位。而气不仅是万物的质料,还是催生万物的动力。
气的流动变化不仅产生了世间万物,还赋予了万物秩序。“六理”作为万物秩序的具体表达,内在于事物之中,又被称为“内度”“六法”“六术”“六行”。贾谊说:“是以阴阳、天地、人尽以六理为内度,内度成业,故谓之六法。六法藏内,变流而外遂,外遂六术,故谓之六行。”[8]316所以,“六理”是世间一切事物规律的总代称,其中也包括人事之理。
贾谊将人事之理归为六种,即“六行”:仁、义、礼、智、信、乐。他说:“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行和则乐与,乐与则六,此之谓六行。”[8]316很显然,仁、义、礼、智、信为儒家的“五常”,但贾谊为迎合“六理”之数,又增加了乐。接下来,贾谊又提出了人之德的“六美”,以对应于“六理”。
贾谊认为德有“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8]325而“六美”与“六理”不仅体现于万事万物之中,还展现于儒家的“六经”之中。贾谊说:“《书》者,此之著者也;《诗》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纪者也;《礼》者,此之体者也;《乐》者,此之乐者也。”[8]325从中可以看出,贾谊的“六理”表面上是万物产生的依据和效法的对象,但最终却是在说明儒家“六经”存在的价值。这种表达方式反映了在汉初黄老道家之学盛行的背景下,儒家为获得话语权而吸收道家思想的事实。而贾谊的这种做法,一方面为儒家经典与伦理道德观念提供了形而上的合理性依据,另一方面则奠定了汉初自然观走向伦理化的基础。
二、“物类相动”的天人相通论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名义上是淮南王刘安所作,但一般被看作是集众人之力而成的著作。尽管如此,但因其各篇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而且基本上围绕着一个中心,也被看作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完整之作”[13]。同时,《淮南子》又因集多人之力而成,使其具有了融合众家的特点,所以有时也被归于“杂家”。然而,《淮南子》虽然兼综诸家学说,但却是以道为本,所以也常被归入“道家”。而无论将《淮南子》视为杂家还是道家,都不能否认它在自然观方面与先秦道家的密切关系。《淮南子》一方面继承了先秦道家视道为万物本原的认识,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物类相动”的天人相通论。
(一)道生气
《淮南子》认为道生万物,这在《原道训》《俶真训》《时则训》《精神训》等篇中都有体现。其中,《原道训》:“道者,一立而万物生”[14]36。但在具体的生成关系上,《淮南子》认为先是道生气,而后气生万物。《淮南子》之所以这样理解,与其对宇宙初始状态的认识有关。
《淮南子》从时、空两个方面来认识宇宙:“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14]435然而,宇宙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宇宙由道所生,然后再从中生出气,正如《天文训》所言:“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14]94。其中,前一句话描述了天地万物产生之前的原初形态,称为“太昭”,也是道开始的地方,又称为“虚廓”。而“‘虚廓’,也是空虚、无形之意,‘道’开始形成于此”[15]141,然后才有了宇和宙。《淮南子》认为宇和宙是统一的存在,将它们并列使用。
宇宙的产生,就代表了“有”的出现。对于这个过程,《俶真训》引用了《庄子》的一段话:“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16]85。而《淮南子》认为:“所谓有始者,繁愤未发,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堮,无无蠕蠕,将欲生兴而未成物类。”[14]52这就将“有始者”理解为事物没有形成以前的、积聚未发而含苞欲放的状态,描绘的是道由空虚、无形的虚廓演变为混沌未分的宇宙的情形。宇宙混沌的进一步分化,就是气的产生。
(二)气生万物
气从时空统一的宇宙出发,不断运动变化产生出天地万物。其中,首先产生天地、四时,然后是万物。《天文训》:“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14]94-95这是说,气生万物遵循一定的规律,而非杂乱无章。气有清浊之分,其清者上升为天,而浊者下降成地;清气聚合容易,而浊气凝结困难,因此先有天而后有地;清气之精者称为阳,而浊气之精者称为阴,二者和合,形成四时;四时之气继续相交变化,最后产生万物。
继四时之后产生的是日月和星辰。《淮南子》:“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者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14]95这里已经涉及五行中的火气和土气,说明《淮南子》对于万物生成的理解已经受到了五行学说的影响。由阴阳到四时,由四时到五行,再由五行到万物的自然演化理论,是先秦时期各家学说交互融合的结果,对汉初自然观有重要影响。《淮南子》认为“火气之精者”和“水气之精者”分别产生日、月,而多余的气则形成星辰,这是说天上的清气。对于地上的浊气,《淮南子》认为是“水潦尘埃”生长出地上的万物。而对于人,《淮南子》则认为是由“精气”所生,如:“烦气为虫,精气为人”[14]263。这里的“烦气”就是浊气,“精气”就是清气。如此一来,地上的人与物就被区别了开来。生存于地上的人与物虽然都是在四时之后而生,但人秉受的却是“精气”,这就赋予了人沟通天地的特殊能力。
(三)道物一体
在气产生之后,道并没有止步,而是伴随气的运动变化,促成万物的产生。《天文训》描述气的产生时说:“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而之所以说道在气产生之后又促成了万物的生成,关键在于“始”字。“始”即开始、出发的意思。“道始于虚廓”,就是道从“虚廓”出发。“虚廓”只是对道原初形态的一种表述,而在此之后的宇宙、气、天地、四时、日月、星辰、人、物等,只不过是道的一步步展开。
《淮南子》用“始”来表述道的案例还有:“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4]134这里引用了《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7]174的话语来论述,但显然进行了改进,将“道生一”阐释为道“始于一”。“生”和“始”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对于道的意义却影响重大。“生”赋予道的是本原意义,而“始”则给以道启动的含义。如此一来,《淮南子》所讲的道就不仅仅具有宇宙万物本原的意义,还具有了宇宙万物产生的动力,伴随宇宙万物演化的始终。而《缪称训》:“道者,物之所导也。”[14]383这就排除了在人与万物之外有一个至上的人格神存在的可能性。
在《淮南子》描绘的世界图景中,世间的一切都由道而来,与道同在,或者说天地万物都是道自身形态的演化。荀子曰:“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2]497而道就如“有化而无别”的“实”,物就如“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的“化”,所以说道物一体。
(四)物类相动
道与万物一体的关系,为《淮南子》“物类相动”的主张提供了理论基石。《淮南子》:“火上荨,水下流,故鸟飞而高,鱼动而下,物类相动,本标相应,故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14]97可以说,世间的一切,无论是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还是天与人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类似的观念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但往往只是基于经验的观察而鲜见理论的论证。而《淮南子》则基于道物一体的认知,对物类相动的理念进行系统说明。
在先秦文献中,有很多关于“物类相动”的记录,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18]28;“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湿。夫类之相从也,如此之著也”[2]607。这两句话都是在观察自然现象的基础上形成的“物类相动”的规律性认知,而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突出圣人的地位和作用,而后者则强调规律的客观性。《淮南子》则以道至天地万物的生成演化为基础,将“物类相动”的观念合理地纳入其思想体系中。
天地万物都以气为质料,那么气所具有的属性也就内含它们自身之中,所以“物类相动”的媒介也必然是气。对此,《淮南子》说:“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介鳞者,蛰伏之类也,故属于阴。日者,阳之主也,是故春夏则群兽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阴之宗也,是以月虚而鱼脑减,月死而蠃蛖膲”[14]96-97。这些所举例子中的阴、阳,就是事物所秉赋的气的基本属性,而正是因为它们,物与物之间才能发生相动的现象。另外,《淮南子》提出“物类相动”的观点,不只是为了说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在为天人之间的关系建构形而上的基础,进一步阐明“天之与人有以相通”[14]808的具有伦理化倾向的自然观。
(五)天人相通
中国古代思想家相信,人与天地万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先秦时期,“在儒家有孔孟天道与人道合一、荀子的天人之分”,“在道家则表现为自然天道观念下的以人合天”[19]。《淮南子》中的“天人相通”论,主要继承了先秦道家以人合天的思想传统。
《淮南子》认为人秉受阴阳之气,顺应四时而生,在本质上与天并没有区别,正如前文“清阳者薄靡而为天”而“精气为人”,说明天与人在构成质料上具有共通性。《淮南子》认为天和人在形态结构上也是相通的,如:“孔窃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14]150-151。这表明,“《淮南子》认为天与人不仅同原,而且同构”,“两者之间结构非常相似,可以说人体是一个缩小了的宇宙,宇宙则是一个放大了的人体”[20]。这样一来,“天人相通”就有了充分合理性。
《淮南子》“天人相通”的论点,最终目的是要落实在人事上,强调人应该因顺自然规律行事,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如:“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落,国乃有恐”[14]193-194。因为在古人看来,天地万物既展现给人们某种规律性,又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往往希望从有规律的自然现象中为人的行为寻找到规范性依据。而“天人相通”的伦理化自然观,正是这种思想发展出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
三、“天人同类”的天人交感论
董仲舒是汉初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与主持撰写《淮南子》的刘安处于同一时代。据史书记载推测,董仲舒和刘安很可能出生在同一年,但是董仲舒离世的时间要比刘安晚十八年。二人的思想应该有着共同的时代印记,也可能产生过相互影响。以自然观为例,《淮南子》不仅以道为万物的本原,而且认为道与万物一体,并在此基础上为“物类相动”进行了合理性阐释,提出了“天人相通”的观点。而董仲舒在此基础上从儒家思想出发,综合诸家思想,进一步推进了《淮南子》“天人相通”论。
(一)天为万物之祖
董仲舒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不天生。”[21]410但是,根据董仲舒“一元者,大始也”[21]67和“元者为万物之本”[21]69的论述来看,元也应该是万物的本原[22]15。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存在两个本原呢?
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元确实有开始、发端的意思,这是因为董仲舒以治《春秋公羊传》闻名,而《春秋公羊传》开篇即见:“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18]4765。此处的元很明显是指时间性的开始和发端。对此,周桂钿先生将董仲舒的宇宙本原论归于“元一元论”:“董仲舒用之作为宇宙本原的‘元’就是开始的意思,它只是纯粹时间的概念,不包含任何物质性的内容,似乎也不包含人的意识,只是纯粹的概念”[23]36。然而,只有时间性而既没有物质性,又没有意识性的元是如何生成万物呢?毫无疑问,在逻辑上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考虑,如果把元理解为时间性的开始,那么在“一元者,大始也”和“元者为万物之本”中元所指的就不是本原,而“元者”才是。而“元者”又是什么呢?董仲舒说:“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21]69这句话至少提供了两条信息:第一,将人与万物区别开来,认为万物与人有不同的本原;第二,认为“人之元”是在“天地之前”的“天元”。根据董仲舒的理解,“天元”仍然是天。
董仲舒说“天有十端”:“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21]217这表明,“天地之前”的“天元”还是天。天就是董仲舒所讲的“元者”。按照董仲舒的意思,先有天,然后有天、地、阴、阳、五行和人。后者构成了天的十端,然后产生了世间万物。而董仲舒又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21]168这就将人抬高到与天地并列的地位。那么,人在天的十端中,地位是高于阴阳、五行的。但是,无论如何,天才是“万物之祖”。
(二)天人同类
《春秋繁露》中,董仲舒认为“人副天数”[21]354。其中,副指符合,数指数目或规律。“人副天数”的意思是指人身符合天的结构数量,或者说人身的变化规律符合天的变化规律。董仲舒天人同类的认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人的出生来看,人合于天数“十”而生。董仲舒认为:“阳气以正月始出于地,生育长养于上,至其功必成也,而积十月;人亦十月而生,合于天数也。是故天道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于天道也。”[21]324第二,从人的形体来看,“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21]318。董仲舒说:“求天数之微,莫若于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节,三四十二,十二节相持而形体立矣;天有四时,每一时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岁数终矣”[21]218;“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21]356-357。 第三,从人的德行来看,人的仁爱、好恶、喜怒哀乐等皆因天而成。董仲舒说:“仁之美者在于天”,而“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21]329;“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21]318。
由以上三方面可知,人的身体不仅因“天数”而成,而且人的道德情感也来源于天。对于前者,应该是当时思想家对于天人关系的一种普遍认识,因为在上一部分讨论《淮南子》“天人相通”论时,已经涉及人与天在形体结构方面的相副问题;而后者将人的道德行为和情感意志(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也归本于天,则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发展。而这种方式是通过赋予天更多的人性来突出“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21]466的地位。这种致思方式并不是董仲舒的发明,而是儒家思想在汉初各派思想交互融合过程中的一种自然演化。早在贾谊那里,就已经试图将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仁、义、礼、智、信等纳入到宇宙万物的演化体系中。董仲舒所做的只是继续推进这种理路,通过人格化的天,完成“天人同类”的证明。
(三)同类相动
对于万物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在《淮南子》中有“物类相动”,在《春秋繁露》中则有“同类相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明确提出:“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21]358单从字面来看,“物类相动”和“同类相动”只有一字之差,很容易将二者等同起来。但是,我们如果将它们放置在各自所在的思想体系中作比较,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着很大区别,这主要是董仲舒对“同类相同”“在天的地方,追求实证的意义”[24]229。
《淮南子》认为产生宇宙万物的气有清浊或阴阳之分,导致宇宙万物在属性方面有异有同,进而又造成它们在类别上的差异。类别相同的事物,因为具有共同性质的气而发生相动的现象,这为“天人相通”提供了合理性的基础。但需要注意的是:《淮南子》主要沿袭了道家的主张,强调人对于天道规律的因循;董仲舒承扬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理念,所追求的是如何在汉初道家学说盛行的情况下弘扬儒家思想。董仲舒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主张,把当时流行的天人观念引入到他的思想体系中,通过将天人格化而实现人与天的互通。这种做法,一方面为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提供了宇宙论的证明,另一方面也为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寻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由“物类相动”而发展来的“同类相动”。
董仲舒说的“同类相动”,主要是天与人的“同类相动”。因为在他的思维中,人的存在不仅先于万物,而且还配合天地化育万物,或者说人与天地共同成就了万物。而人之所以有这样的作用,关键在于人相副于天。这样一来,“同类相动”在天那里就获得了实证意义。但董仲舒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又通过“以类相推”的办法,建立起天与人之间更紧密的关系。
(四)天人相与
在董仲舒看来,人作为天的十端之一,就仿佛是以天为模型刻画出来的,无论是在胎儿时期的孕育,还是外在的形体结构,又或是内在的德性,皆相副于天,这就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地位抬高至与天地并列的层次。《淮南子》虽然也讲人在某些地方与天相仿,但它所强调的是人要因循天道规律。而董仲舒通过天人同类及“同类相动”的推论,突出的是交互性的“天人相与”。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了董仲舒与汉武帝的三次对话,被称为《天人三策》。董仲舒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25]2498此处说明,董仲舒是以“天人相与”的观念来理解《春秋》记载的历史事件,并得到了“甚可畏”的信息。结合他在《春秋繁露》中的论述,主要指人与天之间存在的感应关系。首先,当人君失道、政治败坏的时候,天就会降下灾异进行谴告;人君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补救,那么天就会惩罚他;人君如果受到了惩罚而仍然不知悔改,那么天就会更改天命而重新授予有德之人,如:“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21]259。其次,当人君施政有德而国家兴盛时,天就会降下祥瑞以示赞誉,如:“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21]101。再次,当有新的人君将要取代原有的失德之君时,天就会降下符应现象,如董仲舒援引《尚书》的话:“周将兴之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21]361。
以上董仲舒通过真实的或虚构的自然现象来与人事相链接的做法,就是所谓的“天人相与”,有时也被称为“天人感应”。本文选用“天人相与”的说法,意在突出天与人的相互作用。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天不仅可以作用于人,人也可以反作用于天,二者是一个相互交感的循环系统。
综上所述,汉初自然观从“道德施物”的气物生成论开始,经过“物类相动”的天人相通论的发展,实现了“天人同类”的天人交感互通的伦理转向。在这个进程中,贾谊把儒家的“六经”与“六美”归根于由“道”而生的“德”之“六理”,为汉初自然观的伦理化演进确立了基本方向。《淮南子》不仅以“道”为万物的本源,而且主张“道物一体”,并通过“物类相动”的证明,形成了具有伦理化倾向的“天人相通”的自然观。董仲舒则综合了贾谊和《淮南子》的致思路径,将儒家的核心范畴和人的道德情感归本于“天”,并通过“天人同类”的证明,在“同类相动”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人相与”的伦理化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是汉初思想家在先秦诸子已经祛魅的天人关系认识基础上,通过不断向天地万物注入儒家伦理道德元素而结出的果实。这种发展不仅提升了儒学的形而上学水平,而且为儒家宇宙论的形成和发展夯实了基础。放在秦汉之际的历史背景下来看,汉初自然观的伦理化演进,整合了儒家的“伦理秩序”和道家的“宇宙秩序”,为法家推动建立的大一统“政治秩序”提供了稳固的合理性依据,也为秦汉以降“儒表法里,以道为根”的基本文化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