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服饰研究再检索
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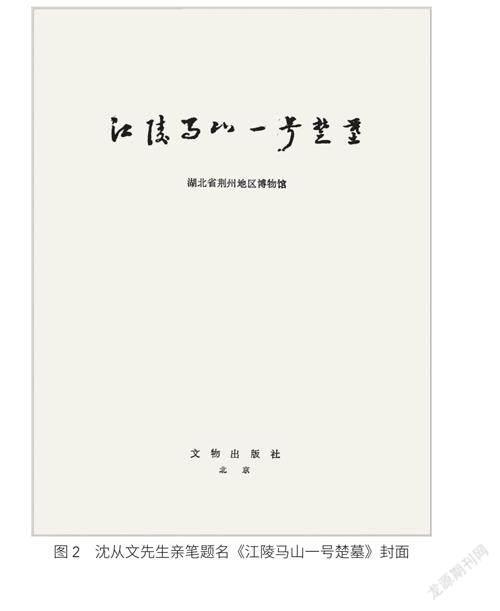
关键词:沈从文 服饰研究 诞辰120周年
2022年是沈从文先生诞辰120周年。站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回望沈从文先生的服饰研究之路,既是致敬沈从文先生,也是借此机会回顾和反思古代服饰研究的学科方法。
一、沈从文服饰研究之肇始
沈从文先生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2022年不仅是沈从文先生诞辰12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110周年。73年前(1949),沈从文先生就是从这里(当时称为“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起步,从文学创作转向古代文物研究,完成了他从作家到学者的转型。在北京历史博物馆的30年间,沈先生过手约几十万件文物,通过长年为文物编目、抄写陈列卡片、自愿为群众讲解等琐碎工作建立起了对文物的理性认识,尤其是对服装织绣藏品的科学认识。1953年,沈从文先生接连发表了关于织金锦的两篇论文,这是他最早开始的古代织绣方面的研究1。1956年,沈从文受邀到故宫织绣研究组兼任业务指导,在整理大量织绣藏品的同时开始对刺绣、染织、纹饰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认识,陆续出版了《中国刺绣》(1956)和《中国丝绸图案》(1957)两本专著,并发表了《谈染缬――蓝底白印花布的历史发展》(1958)、《丝绸中大团花的历史发展及应用》(1959)、《介绍几片清代花锦》(1959)、《蜀中锦》(1959)、《花边》(1960)、《谈广绣》(1962)、《谈挑花》(1969)等多篇代表文章。1963年,受周恩来总理嘱托,沈从文先生正式启动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撰写工作2。在历史博物馆期间,先生还曾多次帮助馆里收购服装织绣藏品,馆藏的大部分织绣藏品都是经由他手得以入库收藏(图1)。
在纺织服饰研究领域之外,沈从文先生对陶瓷、玉器、漆器、铜镜、扇子、杂项、图案纹饰、工艺美术等多个文物研究领域也有着深入研究,正如他写给时任馆长杨振亚的信中曾提到的:
我放弃一切个人生活得失上的打算,能用个不折不扣的“普通一兵”的工作态度在午门楼上作了十年说明员,就是为了这个面对全国,而对世界的唯一历史博物馆在发展中的需要……现在粗粗作大略估计,除服装外,绸缎史是拿下来了,我过手十多万绸缎;家具发展史拿下来了;漆工艺发展史拿下来了;前期山水画史拿下来了,唐以前部分,日本人作过,我们新材料比他们十倍多;陶瓷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也过手了近十万件,重点注意在可否供生产;扇子和灯的应用史拿下来了,也都可即刻转到生产上;金石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拿下来了;乐舞杂伎演出的发展资料拿下来了。
可以说,历史博物馆琳琅满目的古代文物为沈从文先生开启了一扇大门,沈先生在这里得以系统地接触文物、整理文物、研究文物;这里也成为沈从文先生毕生事业的分水岭,真正成就了他作为“文物大家”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奠基者”的历史地位。
二、沈从文服饰研究的三个特点
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大型学术专著,数次再版,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研究开辟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这部书既不同于清代的传统考据学研究,也不同于西来的近代考古学研究,而是立足于出土文物资料,广泛联系文献记载、民族学材料,甚至一些常识性的知识进行论证的文物研究方法,具有科学性与灵活性。概而言之,沈从文先生的服饰研究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经世致用式的研究
对沈先生文学作品稍有关注的读者会发现,在沈先生早期的文学创作中,文笔间时常会流露出一种自由舒畅的气息,这正是他所强调的文学的独立性,尤其是五四时期提倡的文学独立。
但是在转入文物研究后,沈从文先生却特别强调研究成果对社会的回馈和它的社会价值。他在很多场合和文章中都曾表达过这种思想,比如在1954年4月的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沈先生的发言主题就是《关于文物“古为今用”问题》,他在发言中提出了五点建议,并提到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就是“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使万千种古物能‘古为今用,新的历史科学研究,在文物和文献相互结合认识基础上,得到迅速推进”。4又如,在谈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物的问题时,他还写到:
人民是一切文化的创造者,这个偉大正确的提示,将由新的劳动文化史或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全面的证实。过去许多文物研究中的空白点,都可望在不久将来,得到适当解决,且可望由专门知识成为一般常识。特别是丝织物的研究,新材料不断出土,而材料整理出来后,不仅给我们研究工作以极大便利,还可望作到“一切研究为了丰富新的生产内容”,明白什么是优秀传统,宜于有所借鉴,达到“古为今用”目的,三千年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巧思,产生的数以万计的组织健康配色华美的丝绸图案,对于新的生产,必然还将作出一定的贡献5。(《关于长沙西汉墓出土丝织物的问题》)
可以看到沈先生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古为今用”这四个字,这种思想恰恰体现出他的服饰研究的经世致用的特点。
(二)全面通透式的研究
这种特点在沈从文先生的纺织服饰研究方面体现得尤其突出。沈先生对纺织服饰的关注不是从进入博物馆以后才开始的,他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就接触到了大量的西南少数民族织绣艺术品。到了1953年沈先生最先关注到了织金锦问题,这是沈先生研究物质文化史最早发表的论文,后来他又陆续关注到了纹饰、刺绣、染缬、图案、服装等纺织服饰的方方面面。此外,沈先生不仅关注这些纺织品的艺术特点,还关注它们的技术特点,这些都是纺织服饰研究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强调全面的广角镜头式的研究方法。
自沈先生开始至今,五六十年的纺织服饰研究基本上还是沿着沈先生开创的研究路径在进行,所以说沈先生的文物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奠基性质,提出的很多观点和假设在后来都得到了实物印证。所谓的通透也不单是指他在纺织服饰研究领域取得的很多认识的通透,而是对整个文物研究,包括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的全盘创新、全面通透。
(三)触类旁通式的研究
所谓“触类旁通”,其实就是广泛联系。我们研究的文物,看似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质地、不同的技术,但是归根究底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沈从文先生深知这个道理,因此他特别强调这些文物之间的联系,强调做研究的“凡事不孤立的原则”。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研究这些文物,就不能忽视这种联系。沈先生认为:
文物的产生、存在,不是一种孤立事物,实与其他地区东西有密切联系,而且还“上有所承,下有所启”,属于整个劳动文化史的一部分。
他还曾提到:
因为凡事不孤立存在,必有其相互联系处,同一时期工艺图案经常相互转用,而又各受原材料和制作条件制约,形象大同而小异,是十分明显的。凡事既有联系而又在不断发展中,兼受材料和技术限制,加上个时代爱好影响,进展必然就难一致。但总的趋势还是有线索可寻。我们试采用这个唯物辩证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服装和丝织物花纹技术的进展,取得的一些常识,作出的判断,经过近廿年数以百万计的新出土文物,作比较全面的分析,已证明方法是可取的,结论是十分有益的。不仅可以由古可以证今,也可望由今会古。由此取得的前展,是多方面的。6
具体到实际研究中,这种原则更是比比皆是,比如他在谈商代纹饰时,就广泛联系了当时铜器的连续规矩纹,“或和同时存在的锦纹相通”,“如据殷周器物不断发现附着丝绸残迹分析,则这个时期不仅已经能织出十分精美的平纹或方格纹薄质丝绸,且有可能已有原始彩织锦类产生。如联系‘凡事不孤立的原则,试就商前期方鼎平面反映的连续矩纹看来,或和同时存在锦纹即相通,因为同式连续矩纹,在近半世纪出土的商代白石刻人形衣着上,即明确出现于腰袖间”。
又如,沈先生在谈到平金绣技术问题时,他认为此技术产生的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的三四世纪。因为战国时候已经出现了错金银技术,既然这个技术可以用在铜器上,人们当时也有这个审美,那完全也有可能用在织物中8。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这充分体现出胡适先生曾提出的治学思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反映出沈先生一以贯之的创新精神。
在论证方法上,沈先生也特别强调“触类旁通”的原则。比如关于印染中的“弹墨”问题,他就综合运用藏族材料、故宫残存织物、还有诸如《红楼梦》这样的文学作品中对宝玉裤子的描写等所有可能用到的材料,都充分反映出这种研究思路9。
三、沈从文服饰研究的基本材料
沈先生的服饰研究之所以开辟了一条新路,这个“新”首先体现在材料上,这个材料就是考古学材料,而且尤其注意新材料和图像材料,实现文图互证。
沈先生特别关注考古材料,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刚发掘不久,沈先生就很快写成了《长沙西汉墓出土漆器和丝绸衣物》的小文,第二年又修改完成了《关于长沙西汉墓出土丝织物问题》。可以看出,沈先生非常关注最新发现成果并且善于从中发现新问题。他还曾亲自为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的发掘报告题写书名(图2)。10值得提及的是,当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相抵牾时,沈先生又不尽信文献,比如关于周代组配问题,他认为《三礼图》中的古玉佩琚、瑀、珩、璜、冲牙的排列方式,只见于战国汉墓,西周是否确有其制值得商榷11。60年后的今天,晋侯墓地等西周墓葬出土的大量组佩的缀合方式也的確证实了沈从文先生的曾经的质疑。
此外,沈先生对考古发现的图像资料尤其重视,坚持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也是考古学始终秉持的原则,比如对于汉代的冠制,文献记载很多,但沈从文先生根据大量出土图像所反映的冠的形象,推断“我们除了东汉梁冠和漆纱笼冠、平巾帻知识比较具体,文图可以互证,此外就还难言”。12关于“文图互证”,沈先生在写给时任馆长杨振亚的信时就很明确的提到了这一点,他总结自己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是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互证的一种综合研究:
这个说明,近于一种探索性工作,是为原计划编十册资料而提出,约有六千不同图象而着手的,是拟用图象为主,结合文献互证,来进行综合分析,因此涉及相关一系列问题。
还需要注意的是,沈从文先生虽然相信考古材料,但从不盲从考古材料,而是十分重视对材料的筛选和鉴别。“在谈到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木俑头上的柱形冠子,虽和文献记载中的獬豸冠或鹬冠有相通处,但侍从和伎乐俑一例戴上,就难得其解。14”这句话对我们现在的古代服饰研究尤其具有借鉴意义,现在很多研究都大量运用了考古资料,但不得不说很多还不科学,主观臆断太多。比如最常见的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墓主身穿的多层服饰实物,当初沈先生曾明确指出这些是赐衣殉葬的“襚衣”或“褮衣”“明衣”15,而现在的很多研究者将它直接作为汉代常服的一个实例,包括剪裁、尺寸方式都直接拿来作为参照进行复原,这种直接的“拿来主义”实不可取。
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蓬勃展开的考古工作以及诸多考古大发现,为古代服饰研究提供了诸多重要资料,沈先生也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奠基者。21世纪的今天,尤其是近十年来,考古学又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重要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比如近年来发掘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等,都发现了大量珍贵的服饰考古资料。如何利用好、阐释好这些资料将是对古代服饰研究者提出的新挑战。
四、沈从文服饰研究的学术价值
沈从文先生是古代服饰研究领域的开山式人物,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服饰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之所以这样评价,是因为这部大书从研究视角到研究方法,再到研究材料,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研究范式。《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的179条研究条目为以后40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罗列出了一个基本纲目,从研究什么到怎么研究,都为我们做出了精彩的解答。我们缅怀沈从文先生,就是要把先生提出来的这些问题继续不断深入下去,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领域探索更多新路。正如大家熟知的对沈先生的这句评价:“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16,赤子之心是一个真学者的基本素养,不朽的作品必定有纯粹的人格作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