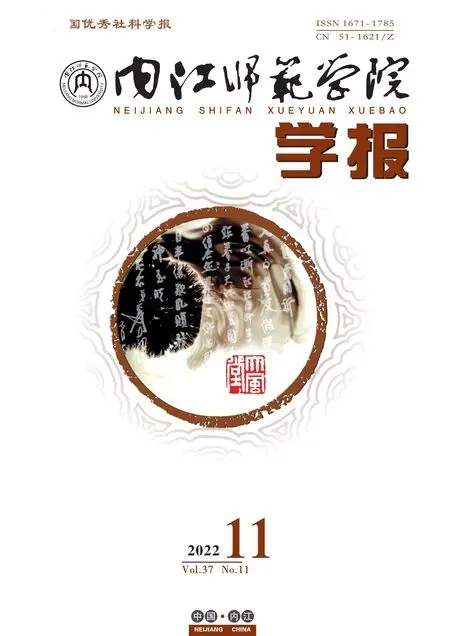宋代书家对俗书的认识
杨 世 铁
(内江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四川 内江 641100)
俗是一个美学范畴,作为造型艺术的书法有俗和不俗之分。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是唐人张怀瓘。他说:“故与众同者俗物,与众异者奇材,书亦如是。”[1]232张怀瓘借物来喻指书法。他认为,物有俗、奇之分。俗物就是“与众同者”,俗书就是没有特点、没有个性,与他人同的书法。
唐代是书法法度形成的时期,也是审美标准确立的时期。人们重视法度,以合法度为最高追求。在这种背景下,张怀瓘的俗书观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到了宋代,书法艺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由之前的重法度开始转向重个性(尚意)。人们开始一方面重视法度,另一方面又厌倦法度。他们学书不满足于学前人和像前人,而是注重表现自我。在此审美取向当中,他们审人察己,论书常常不离一个“俗”字。例如,“世多称李建中、宋宣献,此二人书,仆所不晓。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2]2188“在元和间,(释文楚)所书《千文》,落笔轻清,无一点俗气,飘飘若飞云之映素月,一见使人泠然有物外之兴,岂其书足以洗人之心如是耶?”[3]813-305“前人作字焕然可观者,以师古而无俗韵,其不学臆断,悉扫去之。”[4]812-431“或云欲其萧散,则自不尘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风。”[5]813-556“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6]813-65“永叔虽不学书,其笔迹爽爽,超拔流俗。”①[1]350
宋代书家眼中的“俗书”或者书之俗,不管是“俗气”“俗韵”“俗品”,还是“尘俗”“流俗”,无一不是直指书法之弊。细考之,此弊又各有不同,远非张怀瓘说的“与众同者”。
本文试对宋人书论中的俗书问题做一番探讨,弄清宋代书家判断书俗的标准,这不仅对于了解宋人的书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今天的书法实践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不合法度为俗
书法之法度形成于唐代,自此之后,人们学书就有了依傍。学唐人是最低标准,稍高的是学晋宋②。学唐学晋都被认为是合乎法度,如果只学时人,就认为是不讲法度,如米芾评价宋初书界的风气时说:
本朝……至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学其书,肥褊朴拙,是时不胜录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趣时贵书矣。宋宣献公绶作参政,倾朝学之,号曰“朝体”。……及蔡襄贵,士庶又皆学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学其体。自此古法不讲。[7]
他认为,无论是学李宗谔、学宋绶,还是后来学蔡襄、学王安石,都是追逐时人,因为不学晋唐,所以“自此古法不讲”。古法,在宋代书家看来,就是书法的法度。尤其是晋人书,不仅有法而且有韵,代表了书法的最高水平。而时人的字,看起来虽然也很美,则属于没有法度的字。
从明代开始,很多人认为唐人尚法、宋人尚意。言外之意,宋代书家书不重法度。其实不然。宋人尚意是在重法基础上的尚意。只有合乎法度才是学书正途,如果不合法度,就是俗。如对张旭的草书,米芾说:“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8]米芾认为,张旭的草书“不入晋人格”,变乱了古法,骂他是“俗子”。这样的评价自唐以来少有。人们谈到张旭,多是肯定。如《宣和书谱》说:“(张旭)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后之论书,凡欧虞褚薛,皆有异论,至旭,无所短者。”[3]813-297大意是说,张旭的字“无一点画不该规矩”,即所有的点画都符合规矩。对于其他书家常有褒贬,而对于张旭,人们“无所短者”,即普遍说好。书法史上对张旭的评价,说他的书俗或不俗,依据的标准都是合不合古法(该不该规矩),认为他的字合古法的就说他的字好,认为不合古法的,就说他的字俗。使用同一标准,大家得出的结论不同,这是眼光问题。历史上很多书家都会面临不同的看待,米芾也不例外。他晚年的字也有好与不好两种评价。认为米芾字好的人说,他年轻时“集古字”(意即取各家之长),到老来脱尽古人痕迹,终于形成自己的特色;认为他的字不好的人就说,他“不知所出”,即看不出学谁,意思是米芾不讲古法。
学书除了守规矩以外,还要遵循科学的程序。先学楷,后学行草,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合理的程序,如果不遵循这个程序,也会书俗。《思陵翰墨志》云:“士于书法必先学正书者,以八法皆备,不相附丽。……若楷法既到,则肆笔行草间,自然于二法臻极,焕乎妙体,了无缺轶。反是,则流于尘俗,不入识者指目矣。”[4]812-430
这个说法很好理解,不止笔法,严格的程序也属于学书的规矩,破坏了科学的程序当然是不守规矩。宋代书家的这一认识启示我们,学书当打好基础,绕开过程直求结果,或许能得一时之名,但终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字会越写越俗。
二、学不到位为俗
如上所述,学古人是学书正途。如果该学的没学到,即使外表极像,这样的字也被宋人视为俗。姜夔论大字用笔时云:“然柳氏大字偏傍,清劲可喜,更为奇妙。近世亦有仿效之者,则俗浊不足观。”[5]813-557
柳公权大字很美,后人向他学习(仿效之),本应得美,却“俗浊不足观”,这个“俗浊”就是学柳而没学到家的意思。
学书有不同的阶段,初期一定要学得像,后期要从像中跳出来,追求神似。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一直停留在第一个阶段,甚至有人以第一个阶段的标准去批评进入第二个阶段的人,这就更加荒唐。对这个问题,认识最深的是董其昌。他论王著、赵孟頫等借《阁帖》来学晋唐人时说:“书家好观《阁帖》,此正是病,盖王著辈绝不识晋、唐人笔意,专得其形,故多正局。字须奇宕潇洒,时出新致,以奇为正,不主故常,此赵吴兴所未尝梦见者,惟米痴能会其趣耳。”[9]867-422他认为,书学晋唐没有错,但不能通过《阁帖》来学。如果仅仅得其形似(专得其形),就是没有学到家(不识晋、唐人笔意),所以学书不能只求形模相似,而应“奇宕潇洒,时出新致”,“不主故常”。赵孟頫不明白这一点,不免有“奴书”“俗书”之诮。
米芾也有这样的认识。他说:“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见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钟法;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6]813-63米芾认为,晋人书有“八面”。唐代智永,虽也有八面,但已经少了钟法③。到了丁道护、欧阳询、虞世南时,连“八面”都没有了。再到后来,柳公权向欧阳询学习都“不及远甚”。他这段话的意思,后人学书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到了柳公权就成了“丑怪恶札之祖”,他的字自然也就成了俗书④。
总之,学书要学古人,学古人叫得法。只得法还不行,还得多下功夫,要学到位,否则一知半解,悟不到、猜不透,仅得皮毛,就容易书俗。
三、师法不高为俗
学书一定要眼界高,取法乎上方可,以丑为美或以俗为美,即使笔成冢、墨成海、纸成山,也难有大成就。宋人眼中的俗,有不少就是取法对象档次不高造成的,如章子厚论李建中书云:“李建中学书宗王,法亦非不精熟,然其俗气特甚,盖其初出于学张从申而已。”[10]宋初的李建中书名很盛,但在章惇看来,他后来虽然学王羲之,笔法也很精熟,因为是从张从申入门的,故“俗气特甚”。
黄庭坚是宋四大家之一,也有取法对象不佳这个问题。他多次谈到自己的草书俗问题:“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11]67“钱穆父、苏子瞻皆病予草书多俗笔,盖予少时学周膳部书,初不自寤。以故久不作草。”[11]48黄庭坚的草书俗是由钱勰和苏轼发现的:“元祐初,山谷与东坡、钱穆父同游京师宝梵寺。饭罢,山谷作草书数纸,东坡甚称赏之。穆父从旁观曰:‘鲁直之字近于俗。’”[12]后来他自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后,一直很苦闷,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很长时间内不肯为人作草:“数年来犹觉湔祓尘埃气未尽,故不欲为人书。”(《跋与徐德修草书后》)[11]48“余往在江南,绝不为人作草。”(《书自作草后》)[13]纵使他人百般乞求,也不大愿意为书:“德修持此纸来乞书,又为予作墨汁,予以烛下眼痛,未能下笔。”[11]48他不想写的原因,是怕别人说俗。后来偶有妙笔,一想到钱穆父的话,仍不免心中惴惴:“老来渐懒慢,无复此事(笔者按,指作草书)。人或以旧时意来乞作草,语之以今已不成书,辄不听信,则为画满纸。虽不复入俗,亦不成书。使钱公见之,亦不知所以名之矣。”[11]48真可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至于苏轼“病予草书多俗笔”,苏轼的原话是怎么说的,我们没有找到相关材料,从黄庭坚《跋自草与刘邦直》来看,苏轼确是说过这样的话,所以黄庭坚一作草书便令他想起苏东坡来:“建中靖国元年十月,沙市舟中,晚日入窗,松花泛研,爱此金屑铣泽,因为邦直作草,颇觉去古人不远,然念东坡先生下世,故今老仆作此无顾忌语。”[14]
黄庭坚分析,自己的草书俗是因为学了周越。周越是宋初名家,他在宋代影响很大,是很多人争相学习的榜样,《宣和书谱》评价他“落笔刚劲足法度,字字不妄作”[3]813-308,这当是公正客观的评价,不过,《宣和书谱》又说:“(周越)倘灭俗气,当为第一流矣”[3]813-308,又说他的字俗。别管周越的字俗不俗,格调不高是肯定的,黄庭坚正因为学习了他,所以自己的草书才“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⑤。
四、中规中矩为俗
米芾晚年在自评其书时说:“吾书无王右军一点俗气。”[9]867-425这句话表达了米芾对自己书法的自信,意思是自己的字不俗。说自己的书不俗为什么把王羲之拉扯进来?这句话很值得玩味。细思之,这句话其实暗含着王羲之的字俗的意思。
这样说恐怕很多人都不同意,因为王羲之是书法大家。他的书法开一代风气,为历代学书人所尊崇,也是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峰。不止普通人十分推崇王羲之,就是米芾也爱之有加。有一次,“芾在真州,尝谒蔡攸于舟中。攸出右军《王略帖》示之,元章惊叹,求以他画易之,攸有难色,元章曰:‘若不见从,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据船舷欲堕。攸遂与之。”[15]5-6看到朋友手里有王羲之的《王略帖》,为了得到它,竟不顾颜面以投河觅死相逼。如果王羲之的字不好,米芾恐怕不会如此。在米芾论书的文字中,也常常流露出他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拜。他曾评王羲之《相温破羌帖》,说:“右笔法入神奇绝,帖与王仲修学士家《稚恭帖》同是神物。”[16]《相温帖》和《稚恭帖》都不是王羲之名作,书学史上也很少为人们提及,但米芾仍然视之为神物,由此可见王羲之书法在米芾心目中的地位。
既然王羲之的字很好,自己又那么喜欢,为什么还要说“无王右军一点俗气”呢?这跟米芾的个性有关,也跟米芾到评价标准有关。
米芾是一个不喜欢被限制,追求个性释放的人,他论书作文都不满足于中规中矩,如他作论书语云:“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或遣辞求工,去法逾远,无益学者。故吾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辞。”[6]813-63一开始就明确地表明自己要异于前人的态度,从他所做的书论来看,也确实迥乎前人,没有“溢辞”。在运笔的方法上,他创造性地使用“刷书”,也有自己鲜明的特征:
米芾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6]813-65
从技法上看,“刷”就是用侧笔横扫,目的是取势。米芾晚年作书,恣意纵横,无所避忌。他曾放言:“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17]这种作书的态度正适合用刷的方式表现。正因为米芾生性放荡不羁,他才厌倦中规中矩、一笔一画地书写。等到他晚年形成自己的书风以后,他才敢说出右军书俗的意见。
米芾这里说的书俗与一般人的理解不尽相同,平时人们所说的书俗是个极含贬义的词,而米芾这里所说的俗是指稳妥、中规中矩。他认为,书法如果写得中规中矩,就会稳妥有余,放逸不足,这种情况就是俗气。
无独有偶,与米芾此意见相同的还有黄庭坚。他在《题杨凝式书》中说:“俗书喜作《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却到乌丝阑。”[11]第一句“俗书喜作《兰亭》面”是说俗书都喜欢写成《兰亭序》的样子。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理解:写成《兰亭序》面貌的都是俗书。这个意思很好理解,因为大家都规规矩矩地学《兰亭》,用《兰亭》笔法书写,最终导致千人一面,完全没有了个人的特点。所以,下文他接着说,一旦俗气养成,要想做到平常书写,也毫无办法。而洛阳的杨凝式不讲究规矩,率意而为,一出手便达到了《兰亭序》的水平。米、黄所说的这种俗气,不只王羲之有,只要大家都学某一家,形成固定的、僵死的模式,都会变成俗书。要破这种俗,须在守规矩的基础上敢于突破规矩。
米芾年轻时“规模古帖”(照古帖细致描摹之意,即中规中矩书写之意),“刻画太甚”,所以字俗,后来“以势为主”,“脱尽本家笔”,故能“沉着痛快,直夺晋人之神”。这个过程就是学右军无右军的过程,因为他摆脱了晋人的规矩,所以他的字才“无王右军一点俗气”。宋高宗也说:“前人作字焕然可观者,以其师古而无俗韵。”[4]812-431
“师古”就是向古人学习,有师法,重规矩,“无俗韵”,是指不死学,能变通,知道扬长避短,不中规中矩。能做到“师古而无俗韵”的书当然是“焕然可观者”,这是学书的最高境界。今人陈永正先生说,“拘法的俗书,比起无法的俗书更俗,更不可医。”[18]
五、胸次不高为俗
一般人学书只重技法,认为只要掌握了技法,书就算学成功了,所以学习书法的过程就是练习技法的过程。宋代书家更注重技法之外的胸次,如《宣和书谱》评李磎时说:“大抵饱学宗儒,下笔处无一点俗气,而暗合书法,兹胸次使之然也。至如世之学者,其字非不尽工,而气韵病俗者,政坐胸次之罪,非乏规矩耳。”[3]106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是饱学宗儒不着力技法,其书都“暗合书法”,因而“无一点俗气”;二是当世学书者,字虽“尽工”(合乎法度)却“气韵病俗”。这是两种情况,且一正一反,都是因“胸次”造成的。《宣和书谱》特别重视书者的胸次问题,多次谈到这个问题:“(罗)隐虽不以书显名,作行书尤有唐人典刑,观其《罗城记稿》诸帖,略无季世衰弱之习,盖自胸中所养,不为世俗浅陋所移尔。”[3]255“大抵唐人作字无有不工者,如居易以文章名世,至于字画,不失书家法度,作行书,妙处与时名流相后先,盖胸中渊著流出笔下,便过人数等。”[3]227胸次高低影响到书之雅俗,而解决胸次不够的方法是多读书,使胸中有数万卷书在,如前文论周越字“病韵”,就是因为他胸中无书。再如,“故善论书者,以谓胸中有万卷书,下笔自无俗气,约其得之。”[3]375
读书是字外功夫,它对书法的作用比起技法来更为重要。尤其是当书写水平达到一定层次之后,对学问胸次的要求就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决定其书俗不俗的,就不再是技法问题了,而是胸次的高低了。关于胸次和技法的关系,《宣和书谱》云:
有字性不可以无学,有字学者复不可以无性,故其为言曰:“习而无性者,其失也俗;性而无习者,其失也狂。”盖以谓有规矩绳墨者其习也,至于超诣绝尘处,则非性不可。[3]116
它称技法的训练为“习”,称字外功夫为“(字)性”。它认为,光练习技法而不去读书(习而无性者),“其失也俗”;光读书不练习技法(性而无习者),“其失也狂”。它还指出,要想获得技法(规矩绳墨者),通过训练(“习”)就行,而要想做到脱俗(超诣绝尘),就非通过读书不可(非性不可)。这个意思,姜夔和黄庭坚也说过:“然而襟韵不高,记忆虽多,莫湔尘俗;若使风神萧散,下笔便当过人。”[5]813-557“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11]47“记忆虽多”指心中只记着前人的笔法,“笔墨不减元常、逸少”,是指技法接近钟繇、王羲之,而“襟韵不高”,“灵府无程”都是胸次不高的意思。
苏轼的字,宋时曾有较大的争议,有人认为他的字缺少规矩,没有来历,不美,黄庭坚则认为这正是他的长处。黄云:
东坡书,随大小真行皆有妩媚可喜处,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11]46
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今世号能书者数家,虽规摹古人自有长处,至于天然自工,笔圆而韵胜,所谓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与也。[11]43
黄庭坚认为,苏轼的字“妩媚可喜”“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完全是因为“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通俗地说,就是苏轼作为学者,他的胸次比一般人高的缘故。
六、带有时病为俗
《宣和书谱》卷十九评周越说:“说者以谓怀素作字正合(周)越之俭劣,若方古人,固为得笔,傥灭俗气,当为第一流矣。”[3]449周越跟古人相比虽然得笔,只是因为沾染时习,未灭俗气,所以还不是第一流。书之时病,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又不一样。学书之人最容易追逐时尚,沾染时气,这样的字韵格不高,宋人则视之为俗。姜夔说:“大抵下笔之际,……专务遒劲,则俗病不除。”[5]813-555
此“专务遒劲”也是时病。在清代碑学兴起之前,笔法普遍偏软,这是学帖的必然结果,宋时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欲以“遒劲”纠正之,因而形成“务遒劲”的时病。
唐代也有时病。“至于字法之坏,则实由亚栖,而(李)霄远亦亚栖之流。宜其专务纵逸,如风如云,任其所之,略无滞留——此俗子之所深喜,而未免夫知书者之所病也。”[3]407
“专务纵逸,如风如云,任其所之,略无滞留”就是唐代的时病。这种时病是“俗子之所深喜”者,它跟宋代“专务遒劲”的时病有相似之处。“唐官告在世为褚、陆、徐峤之体,殊有不俗者。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6]813-63这也是说唐代的时病:唐明皇喜肥,于是徐浩、诸经生也开始写肥字,追逐这种时尚的结果就是使书变俗。为时病所染这种俗,说到底是学书者个人的风格为时代书风所掩,因为缺少了书家个人的特点,所以变得很俗⑥。
七、缺乏个性为俗
唐人重规矩,到宋代开始重个性。个性是艺术的生命。缺乏个性的字,千人一面,虽然取法很高,也会沦为大众化一般化的字。因而,对于死学前人而不知变通的字,宋人一概视之为俗。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俗一般来讲不是大病,只能算是缺陷。对于这种俗,宋人多不是从批评角度来说的,而是从其不同于一般的赞赏的角度来说的,如《宣和书谱》评潘佑的行书诗帖,说它“笔迹奕奕,超拔流俗,殆有东晋之遗风焉。”[3]256“超拔流俗”,就是超出一般的人。流俗,就是大众化,就是一般化。朱长文《续书断》评价王安石的字,谓“介甫相国笔老不俗”,此不俗,也是说他的字不一般。
对于这个意义上的“俗”,宋代书家在表达个人见解时,多采用含蓄的方式,使用“不俗”或者“超拔流俗”“绝俗”等说法。“(苏轼)后又于李玮都尉家见谢尚、王衍等数人书,超然绝俗,考其印记,王涯家本。”[2]2172
这些评价都是说时人书作的可取之处,由此而透露出宋代书家对书法艺术的追求,即讲究作品的非同一般,有个性。
书法作为艺术,最惧平庸,缺乏了个性就是平庸,这样的作品宋人称之为“俗”,因此可见宋代书家对于书法艺术的追求是不遗余力的。
八、结语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俗是宋代书家对不好的或有缺陷的或平庸的书法作品的统称。宋人于书俗最忌恨,认为俗一旦染成,就很难根除。黄庭坚云:“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书缯卷后》)[11]米芾也多次谈到他人的书俗问题,对自己的书俗也深以为恨,直到晚年,他才自觉摆脱了书俗。《海岳志林》记一事,表达了他在感到自己的书脱俗之后的欣喜之情:
徽宗命元章书《周官》篇于御屏。书毕,掷笔于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徽宗潜立于屏风后,闻之,不觉步出,纵观欣赏。[12]1
写到得意处,忘了自己身在皇宫,忘了身后还有皇帝在,把笔一扔,“大言不惭”: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这时躲在屏风后偷观米芾作书的宋徽宗也忘了自己的万人至尊的身份,不觉凑过来欣赏。由此可见,宋人做梦恐怕都想脱俗。
脱俗,是宋代书家对书法的理想,朱长文认为不俗是书法能品的共性:“离俗不谬,可谓之能。”(《续书断》“品书论”)[1]320当然,高于能品的妙品和神品,仅仅做到了离俗还不行,还得满足其他条件才行。
注释:
① 据《历代书法论文选》编者说明,《续书断》选自《墨池编》九、十两卷,然而四库全书本《墨池编》只有六卷,不审何据。
② 古时人们学书多从唐人入手,似乎对魏晋重视不够。其实不然。魏晋人的书帖多藏于秘府,民间很少见到,即使兰亭有定武刻本,也有怀仁用王羲之的字所集的圣教序,一般人仍然难以看到。见不到魏晋人书,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唐人书作为学习范本。
③ 指钟繇笔法。至于钟法是什么,米芾没说。
④ 以上对柳公权的评价是米芾的说法,我们只是转述,并不表示我们同意他的说法。米芾评前人书常有变化,如同是柳公权的字,他还说过:“柳公权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海岳志林》“评书”)一会儿骂它“丑怪恶札之祖”,一会儿又说它“无一点尘俗”,看似矛盾,其实很正常,尤其对于米芾这种性情多变的人来说,全在情理之中。因为人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件作品的评价不同,是艺术欣赏很正常的事。
⑤ 周越的书俗是后来才发现的,早期人们只看到了他的可取处,所以才有很多人学他。
⑥ “俗”的语文义之一就是大众的、普通的。这个意义上的俗没有贬义,但对于书法艺术来讲,大众化、没有个性则属于比较严重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