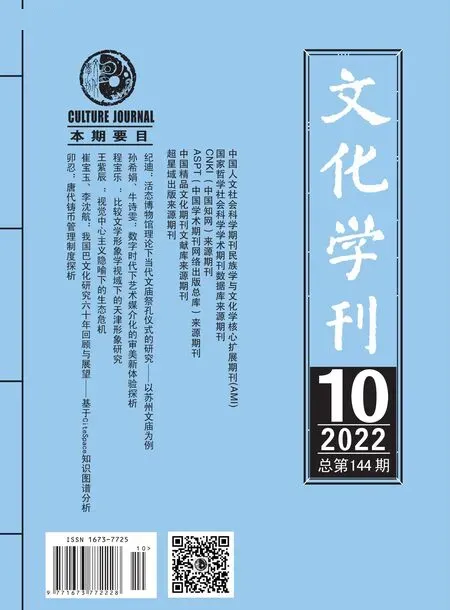聂鲁达爱情诗歌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
邢鸿儒
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 1904—1973)是智利著名民族诗人、外交家,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国际诗坛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1)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for a poetry that with the action of an elemental force brings alive a continent's destiny and dreams.”,被誉为当代拉美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1923年,不满二十岁的聂鲁达创作并出版了第一部爱情诗集《黄昏》(Crepusculario),1924年聂鲁达发表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Veintepoemasdeamoryunacancióndesesperada)。随后,他创作了《大地上的居所》(Residenciaenlatierra)、《漫歌》(Cantogeneral)、《船长的诗》(LosversosdelCapitán)、《黑岛纪事》(MemorialdeIslaNegra)等为他赢得国际声誉的诗集。这些作品之间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正如聂鲁达研究集大成者智利学者埃尔南·洛约拉(Hernán Loyola)所指出的,它们构成了“一部人类意识演进的历史”,[1]一部个人追求迈向完整人性的成长史。
一、聂鲁达诗歌在中国的译介
20世纪50年代至六十60年代上半期,国内外国文学译介由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扩展到更广阔的亚非拉国家,为了加强与非西方国家间的文化联系,巩固反殖民主义阵营,全国掀起了对亚非拉美国家文学作品的译介热潮。聂鲁达的政治诗歌在这一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1951年聂鲁达来访我国时,国内就出版了《聂鲁达诗文集》。[2]由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破裂,此后中国亦与国际上的亲苏派断绝了往来,因此,便停止了译入亲苏派拉美作家的作品,聂鲁达的作品也在其中之列。改革开放后,国内对聂鲁达作品的译介开始回温,并且越来越多的爱情诗歌开始进入中国读者的视线,其中影响较深较广的作品为《诗歌总集》(1984)、《聂鲁达诗选》(1985)、《聂鲁达爱情诗选》(1992)、《我曾历尽沧桑:聂鲁达回忆录》(1992)、《漫歌》(1995)、《聂鲁达诗精选集》(1998)、《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2003)、《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2004)、《聂鲁达(世界文学大师纪念文库)》(2008)等。这一时期译介的作品虽然有少量政治诗歌和散文,但主要是以爱情诗为主。不过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选译的爱情诗摈弃了被认为“不健康”的涉及性爱的诗篇,可以说聂鲁达爱情诗歌的全貌直至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逐渐完整呈现。[3]比如,聂鲁达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这本爱情诗集直至2003年才由李宗荣从英译本翻译成中文以飨中国读者。2004年,值聂鲁达百年诞辰之际,智利文化部创立了“伊比利亚美洲诗歌奖”;同年,我国西班牙语学界为纪念聂鲁达而推出了《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著名翻译家、西班牙语学者北京大学赵振江和滕威在书中第一次从西班牙语原文全译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以及其他部分诗集作品,如《漫歌》,尽力呈现聂鲁达的完整面貌。
综观聂鲁达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聂鲁达的形象经历了从“战士”(革命诗人)到爱情诗人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在介绍《聂鲁达文集》时说“包括在这个集子里的虽不是作者的全部作品,但可以说是他全部作品中的精华部分……他首先是一个优秀的战士,然后才是一个优秀的诗人。”[4]在这一时期,聂鲁达以革命诗人的形象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新时期翻译政治指向的消隐,同样为聂鲁达赢得世界赞誉的爱情诗开始被译入我国。20世纪80年代时,聂鲁达诗歌的译介还是政治抒情诗与爱情诗并重,到了20世纪90年代,其爱情诗则几乎完全取代了政治诗歌。至此,聂鲁达在中国的形象完成了从革命诗人向爱情诗人的转变。
二、聂鲁达爱情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虽然最早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聂鲁达诗歌是他的政治抒情诗,但事实上聂鲁达首先是一位爱情诗人。1924年,年轻的聂鲁达凭借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登上了智利诗坛。随后,在拉丁美洲这本诗集被誉为新浪漫主义爱情诗的杰出典范,并为他带来了国际认可。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5]自2003年译介入中国以来受到了大量中国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喜爱,成为了聂鲁达在中国最负盛名的爱情诗集。但诗集中的女性形象并未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在国外学界,这本诗集中的女性形象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便引起了诗歌研究及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性别研究学界的关注。赞成传记式解读的评论家们根据聂鲁达自己的一些评论,认为诗集的灵感来源于聂鲁达真实生活中的两位缪斯:阿尔贝蒂娜·罗萨·阿索卡尔(Albertina Rosa Azócar)和特雷莎·巴斯克斯·莱昂(Teresa Vásquez León)。然而这一判断并不准确,因为聂鲁达自己曾承认:“不是一个,是很多个”,并且狡黠地称她们为Marisol和Marisombra。Marisol是西班牙语中非常常见的女人名,但Marisombra一词在西班牙语中并不存在。聂鲁达机智地用与Mari-sol这一名字中sol(太阳)相对的反义词sombra(阴影)作为另外的“她们”的名字(Mari-sombra)。诗集中聂鲁达对爱人的各种不同甚至自相矛盾的描述从侧面佐证了缪斯的多元性:既有她“皮肤黝黑,动作敏捷”“欢快的身体”“炯炯有神的眼睛”和“嘴角带着水的微笑”的描述;也有关于她“白色的山丘”“白色的大腿”,目光中“有时会有惊怖的海岸出现”等的描述;有时她是像世界一样奉献自己的女性(诗1),有时她是沉默的女孩儿,在黄昏时分离开(诗10)。这类矛盾的女性属性的描述表明,这部作品是围绕着聂鲁达在青春期爱上的几个女人展开的:“一个”皮肤黝黑,“另一个”皮肤白皙。古斯塔沃·加西亚(Gustavo García)进一步指出,《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的文本是以青春期的姿态,构建了一个女性原型:“未知的女性”。[6]
正是因为青春期时的聂鲁达对女性的不了解和困惑,才有诗集中女性形象模糊和不确定的表达及描述。这一女性形象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是通过将女性身体进行变形和文本式拆解来呈现的:将女性的身体等同于自然界的元素,女性亦被简化为其身体的具体部位并通过抽象的意象来暗指。通过这一简化主义逻辑,诗人建构了一个看似有血有肉的抒情对象来唤醒情欲。尽管关于她的描述极尽语言美感,但她却沦为了服务男性欲望的次要角色。
女人的身体,白色的山丘,白色的大腿,
你像一个世界,俯顺地躺着。
……
皮肤的身体,苔藓的身体,渴望与丰厚乳汁的身体。
喔,胸部的高脚杯!喔,失神的双眼!
喔,耻骨般的玫瑰!喔,你的声音,缓慢而哀伤!
我的女人的身体,我将执迷于你的优雅。
开篇第一首诗《女人的身体》,年轻的聂鲁达用最直白的语言描写女人:“身体”即“肉体”,“肉体”又进一步被拆解为“大腿”“胸”“耻骨”;诗人用了大量的比喻建立起女性“身体”与大自然、大地的联系,凸显了诗人对女人与大自然在本体论上的认同:“我粗犷的农夫的肉身掘入你,并制造出从地底深处跃出的孩子”。对诗人来说她即是身体,是被“肢解”的身体部位:大腿、胸、眼睛、耻骨,同样她也是大地、大山、大自然。对女性身体的变形和拆解手法贯串了整本诗集,聂鲁达把她和自己最深爱和最感亲切的大自然密切勾连,诗中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建构于她与大自然的对等性。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如同一切大自然元素般“可触摸的”(女性)存在/身体,且不仅她的整个身体而是她的各身体部位都近似自然界中的元素。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从人类变形为自然元素的过程,这一过程恰恰与《创世纪》(《圣经》)中尘埃通过文字的力量变形为男性身体的过程相反:女性的身体被文字转化为“白色的山丘”“苔藓的身体”。不仅如此,聂鲁达从列举女性身体整体开始,逐步将其拆解为“部分”:皮肤、大腿、乳房、眼睛、耻骨等。变形和碎片化是年轻的聂鲁达尝试通过男性诗意欲望语言重现其爱人的策略,也是这部诗集最大的语言特色。
三、聂鲁达爱情诗《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在中国的传播
革命和爱情是贯串聂鲁达诗歌创作生涯的两大主题。在20世纪享誉国际的外国诗人之中,聂鲁达可以说是最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的。因为自他的政治抒情诗在20世纪50年代译入中国后,即在中国读者中广为流传且产生了较大影响。随之在改革开放之后,他的爱情诗开始在中国读者中流传,尤其当《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被译介,更是被广大年轻读者津津乐道。“从未有人用如此精彩的语言处理过爱情、激情和女性的性魅力”,[7]《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作为聂鲁达的成名作且至今仍然是国际畅销诗集之一,其文学艺术价值不言而喻。但是,诗集在我国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中传播时,诗集中女性形象的建构策略及其语言特色不乏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的方面。
在语言学领域,学者们越来越开始关注和探讨语言在性别身份的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在后现代语境下,语言不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主动地建构现实。话语,包括本文所探讨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中的欲望话语,在当今社会性别身份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推进,传统社会话语中广受诟病的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现象开始逐渐消失,但一些根深蒂固的性别主义意识形态及性别刻板印象仍然以不易察觉的形式出现在话语中,生产和再生产着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如前文所述,对女性身体的变形和碎片化是年轻的聂鲁达尝试重现爱人的语言策略。当诗集进入中国读者视线且为广大读者所喜爱时,诗集中的这一语言策略便进入了中国语境且开始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中国女性身份的建构与再建构。国外学界许多学者都曾指出,诗中的她只是诗人作为男性站在性别等级制度顶端的男性欲望投射:她并非一个“人”,只是一面工具性的“镜子”,用来折射男性诗人对爱情的欲望、困惑、和沮丧,[8]正如诗集开篇第一首诗《女人的身体》。诗集另一首最广为流传的诗篇《我喜欢你是寂静的》: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
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
好像你的双眼已经飞离去,如同一个吻,封缄了你的嘴。
如同所有的事物充满了我的灵魂,
你从所有的事物中浮现,充满了我的灵魂。
你像我的灵魂,一只梦的蝴蝶。你如同忧郁这个词。
……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
遥远而且哀伤,仿佛你已经死了。
诗中的她,除了紧闭的嘴,还像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像诗人的灵魂和忧郁这个词。诗中的女性只不过是“类似”“像”某种东西,仍然没有超越非人格化话语,而这一非人格化则建构了积极的男性诗人——被动的女性爱人(“物”)的二元对立式性别结构。
对女性及其身体的碎片化、客体化及工具化话语在《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里是显而易见的,话语中所隐含的性别主义意识形态属于社会认知的层面,是不易察觉并且被自然化的社会观念。[9]虽然,我们不能因为聂鲁达的话语中隐含了性别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认定他有性别歧视的意图,但我们需要警惕,这样的话语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在性别身份的社会建构过程中,其隐含的性别主义意识形态将在中国话语及文化语境中生产和再生产不平等的性别关系。
四、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聂鲁达的诗歌经历了从政治诗歌到爱情诗歌的译介转变,聂鲁达本人的形象也从革命诗人转化为爱情诗人。《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作为聂鲁达最负盛名且最广为流传的诗歌作品集,其艺术造诣不言而喻。但诗集中大量使用的将女性身体碎片化、客体化及工具化的男性欲望话语及阐发技巧值得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虽然笔者认为,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学者和性别研究学者因这本诗集中的男性欲望话语把聂鲁达定性为厌女诗人的结论有失偏颇,但我们仍需要警惕诗集中所隐含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将潜移默化地参与中国语境下性别身份和性别文化建构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