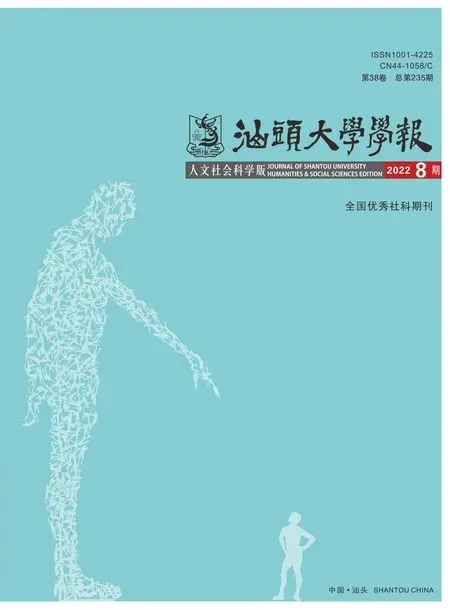自由、恶与存在
——论海德格尔的谢林阐释
赵 瑜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德国古典哲学是海德格尔一生致思的重要思想来源,而他对谢林哲学的评价尤其之高:谢林关于自由的论著是“德意志哲学乃至西方哲学最深刻的著作之一”①M.Heidegger,Schelling:Vom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1809)[M].GA Band 42,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88;中译本参见: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M].王丁、李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以下简称《谢林书》)本文所用海德格尔《谢林书》文本都使用了王丁、李阳的中文译文,部分译文有改动。参见:M.Heidegger,GA 42,S.7.;海德格尔,《谢林书》,第8 页。本文所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文本都使用了陈嘉映、王庆节教授的中文译文,并标注相应的德文版单行本页码,部分译文有改动。。在《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 und die damit zusammenhängenden Gegenstände)②以下简称《自由论文》。本文所用谢林《自由论文》文本都使用了先刚教授的中文译文,部分译文有改动。文中其他谢林著作也都使用了先刚老师译文,部分译文有改动。一书中,谢林通过重新阐释自由概念,寻找到了一种“恶的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s Bösen)③实际上在谈道恶的问题的时候,谢林并未使用“恶的形而上学”这一术语,而是在说恶的可能性与恶的现实性。笔者使用“恶的形而上学”这一术语,意在强调通过对“恶”这一概念的阐述,谢林把一种不同于存在者的“‘非存在者’,亦即存在本身纳入了视野”。对恶与体系关系的理解参见:王丁,“恶的形而上学——论海德格尔的谢林阐释”[J]《.伦理学术》,2018 年,02 期005 卷,第209-223 页。[1],从而实现了重新为存在奠基的内在目标。而这一内在目标与海德格尔所说的“重提存在问题”[1]SuZ2不谋而合,甚至可以说,海德格尔在谢林哲学中所看到的“本质性之物”(Wesentliches)正是谢林哲学中表现出来的对存在问题的再次追问和重新审思。
表面上来看,谢林在《自由论文》中所处理的是“体系”“自由”和“恶”三大概念之间层层递进的关系:如果体系能够兼容自由的话,那么需要纠正以往对自由概念误解,将自由看成是一种向善和从恶的能力;如果自由是一种善恶之间的能力,那么恶本身必然具有形而上学的地位。进一步说,恶本身并非一种否定性的存在,相反,恶是一种肯定性的力量。人自身内部具有两个本原——在向内收缩的私己意志(Eigenwille)和向外扩张的普遍意志(Universalwille)——在两者的斗争之中,普遍意志将私己意志统摄在自身之下,使得作为个体的人得以固定下来,并提升至上帝和爱。恶代表的则是私己意志提升并控制了普遍意志。换言之,只有通过恶,作为个体的人之自由才能得到完整的说明。因此,表面上谢林是在处理道德哲学的问题,但实际上对自由和恶的探讨已经深入到存在问题本身。
海德格尔总是批评其他哲学家“遗忘了存在”,而他的哲学要做的便是去重新追问存在的意义。但对谢林的评价不同,他认为谢林哲学始终在为同样的东西重新奠基。[2]GA4210这样一个同样的、本质性的东西便是存在问题。对海德格尔来说,重要的不是存在者,也不是空洞的存在概念,而是要去追问存在自身是如何得到理解、存在者如何在活动中展开了它的存在。而对谢林来说,个别存在者本身就是生成的,探索存在就是探索存在的历史,就是探索存在是如何从过去一步步发展、演化到当下并获得了自身全部规定性的。从这一角度来说,谢林的确是在思想上与海德格尔最为契合的哲学家,因此海德格尔才会认为谢林“相较于黑格尔,在哲学上敢于更为深远地前行”[3]62。
本文的核心论题便是展示谢林对恶的形而上学的阐述中展现出来的对存在问题的探索,并揭示谢林和海德格尔面对存在问题时立场的相似和最终路径的不同。在第一部分,笔者将从谢林的《自由论文》出发,展示谢林对自由、恶等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通过对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论述,谢林说明了恶或者一种根据意志(私己意志)对存在的推动作用。在第二和第三部分①第二、三部分的思考受益于吴增定教授在2022 年4 月10 日所作的讲座“根据、非根据与建基——论海德格尔对谢林《自由论文》的解读”,在此表示感谢。,笔者将揭示海德格尔与谢林的相似之处。一方面,笔者进一步阐释在谢林哲学中存在是如何“生成”的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被海德格尔认为是谢林哲学看到了“本质性之物”的表现。另一方面,笔者将以“非根据”这一概念为核心,指出谢林哲学在开端处的双重面向,并揭示后期海德格尔是如何通过这一概念完成了自身哲学的“去主体化倾向”的。在最后一部分,笔者将揭示海德格尔和谢林对个体的有限性问题看法的不同之处。对谢林来说,瞬间即是永恒,每一个瞬间中都能窥见永恒,有限个体始终是在与无限的张力中确定自身的位置;而对海德格尔来说,永恒即是瞬间,对永恒或完满时间的理解需要某个瞬间的领悟,换言之,无限性的落实依赖的是某种偶然的契机。而正是这微小的差异,反映了两者哲学旨趣在本质上的分歧。
一、谢林:人的自由与恶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展示谢林对自由和恶问题的思考。真正的自由要求一种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必然的恶,而恶的问题最终指向存在的问题——恶是在存在之中两个本原关系的一种“颠倒”。实际上,为恶在存在论意义上的辩护是在为一种在整体中的个别事物之自我规定的可能性的辩护,是在为一种可以容纳偶然性的体系而辩护。
谢林首先指出,真正的自由必然是和一种科学世界观整体相联系的[4]SWVII338,也即是说,真正的自由概念要在“体系”(System)中得到说明。体系不仅仅意味着一个整体,而且是一个内部各环节之间彼此协调、有着明确秩序和框架的整体;并且在这一整体中,每个个体都应获得自身独立的存在。而以往的哲学体系恰恰是无法接纳真正的“自由”概念的:无论是以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将自由看成是对必然性的认识的近代哲学,还是以康德为代表的将自由看作一种“自身规定”(Selbstbestimmung)的德国唯心论传统。按照粗浅的斯宾诺莎主义②谢林指出,实际上泛神论并没有否定一种形式上自由的可能性。但是,谢林仍然指责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观点是“死气沉沉的”,因为就连上帝拥有的自由都是不能去选择不存在的自由。因此上帝是“缺乏潜能的,并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虚弱无力的存在者,因为它在自身内根本不具有权力去成为另一种存在”。参见:F.W.J.Schelling,SW X[M].35.;谢林,《近代哲学史》[M].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41 页。的观点,个体是神的样态,个体的自由必然完全臣服于神的全能,因此自由仅仅意味着对必然性的认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鲜活的自由。如果如康德所说,自由即自律①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康德将自由的意志与自律的原则结合起来,指出自由是意志独立于感性世界的外在因素而根据理性的普遍法则起作用的能力。参见:Kant,GMS,AA 04:446-447,Gesammelte Schriften,Berlin:die Königlich-Preu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00ff.[2],是感性能力对道德律令或理性的服从的话,那么最终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体自由的。而在谢林看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要能够容许个体中有反叛整体的可能性:“个别器官仍然具有一种独特的生命,甚至具有一种自由,而这显然是通过它能够生病而得到证明的。”[4]SWVII346疾病意味着个体有不服从整体的和谐运作之可能性,而真正的自由概念必须容纳这样一种反叛系统的可能性。正如谢林批评斯宾诺莎的上帝是一个“虚弱无力的存在者”,是一个不具有真正意义上自由的上帝,自由概念必须在最极限的意义上容纳一种非存在的可能性。正如谢林在《斯图加特私人讲授录》(Stuttgarter Privatvorlesungen)中所说的那样:“因此上帝作为绝对存在者也是绝对自由的东西,而人作为一种从‘非存在’那里提升上来的存在者,也通过他的本质的双重关联而获得了一种完全独特的自由。”[5]SWVII457因此,谢林对自由做了如下定义:
那个实在的、活生生(lebendig)的自由概念却是说:自由是一种向善和从恶的能力(Vermögen)。[4]SWVII352
然而,如果自由是一种在善恶之间的能力,那么意味着恶作为独立的本原必须要被纳入原初的体系之中,甚至是纳入“神”的概念之中。也就是说,恶既不是从属于善的派生物,亦不是和善完全对立且毫无关联的存在。一方面,前者实际上是斯宾诺莎的观点——当斯宾诺莎认为一切样态都是来自于完美的上帝的时候,恶本身就不具备和善同等的地位,而是相对意义上的一种“缺乏”(Mangel)。这种“缺乏”不是对善完全的否定,而是只能在否定的意义上被思考,但其本质上依然是善。由此,在善恶之间的自由也就仅仅意味着在完满的善和不够完满的善之间的自由,而这依然不能回答不够完满的善的能力到底从何而来的问题。另一方面,第二种主张恶与善完全没有关联的“二元论”则意味着“理性的自身撕裂和绝望”[4]SWVII354;因为理性本身追求的是统一性,是能够在一个体系中实现概念之间的和谐运作。因此,谢林的体系必须要将恶作为具备独立地位的本原纳入自身之内,并且在这一体系之中,恶必然具备着肯定性的、建构体系的能力。海德格尔将这样一个任务称之为“恶的形而上学”。
谢林将这一任务具体规定为阐明恶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问题,可能性的问题又进一步首先被解释为“两个本原的可拆分性”[4]SWVII364。谢林提出了著名的“实存者”和“根据”的区分:“我们这个时代的自然哲学首先在科学里区分了两种本质,一种是‘实存者’,另一种‘是实存的单纯根据’。”[4]SWVII358从存在本身又是“原初意志”(Urwille)的角度来说,“实存者”和“根据”又分别可以被称为“普遍意志”和“私己意志”②谢林在不同的文本中会选择不同的术语。因为1809 年到1827 年被统称为谢林的“世界时代时期”,所以本部分在处理在不同的文本(《自由论文》《斯图加特手稿(1810)》《世界时代》原稿I)中的概念的时候默认可以将这些术语作以如下的对等方式来理解:“实存者”=“存在者”(das was Ist)=“本质”(Wesen)=“普遍意志”(Universalwille)=“理智”(Verstand)=“无所欲求的意志”(der Wille,der nichts will)=“爱”(Liebe)=“扩张的意志”=“光”(Licht)=“纯净性”(Lautheit);“根据”=“存在本身”(das Seyn selbst)=“私己意志”(Eigenwille)=“存在的意志”(Wille zur Existenz)=“收缩的意志”=“黑暗”(Dunkel)。根据行文的需要,笔者也将部分地对这些概念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对于存在物而言,存在物之实存的“根据”并非存在物本身,而是存在物内部的“自然界”,是一个虽然与存在物不可分割,但毕竟与存在物有所不同的本质[4]SWVII358。
第一个方面的本原是这样一个东西,事物通过它而与上帝分离,或者说事物通过它而存在于单纯的根据里。[……]就这个本原来自于根据并且是黑暗的而言,它是受造物的私己意志,而就这个意志尚未与光(理智的本原)形成完满的统一体(尚未把握光)而言,它是单纯的渴求(Sucht)或欲望,以及一个盲目(blind)的意志。[4]SWVII362-363
也就是说,只有依靠光,黑暗的私己意志才能被提升至完满的统一体,才有了真正的存在。而光就是被另外一个被称为“实存者”或“普遍意志”的本原:
理智作为普遍意志与受造物的私己意志相对立,它利用后者,将其作为单纯的工具而统摄在自身之下。但是,通过全部力量的持续转化和分离,原初黑暗那个最内在、最深处的点最终在一个本质那里完全升华为光,尽管就这个本质是个别东西而言,它的意志同样是一个局部意志(Partikularwille),但自在地看来,或者说就这个一直是所有别的局部意志的核心而言,它和原初意志或理智又是合为一体的,以至于二者如今成为一个联合的整体。[4]SWVII363
普遍意志来自于上帝,是人身上的光明本原。这样一种意志自身是完满的,不追求任何事物,因此是“无所欲求的意志”(der Wille,der nichts will);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自身拥有全部力量,因此又是“一切东西”。黑暗的私己意志则是欲求着某种东西的意志,它还没有达到自我意识,但是却已经是“一种‘沉浸于自身’的状态,一种‘寻找自身’和‘发现自身’的活动”[6]WAI30,因此可以将其称之为“存在的意志”(Wille zur Existenz)。
通过光明本原的提升,作为黑暗本原的私己意志不是消失了,而是在存在的统一体之中被转化为光;同时,私己意志仍然保留在根据里,甚至是作为给光明本原“提供支撑点、根据和基地的东西”[5]SWVII439。普遍意志是扩张性的,没有私己意志,普遍意志就无法持存下去。因为“单纯的爱(普遍意志)本身不可能存在,不可能持存,也就是说,正因为她在本性上是扩张的、无限可分享的,所以,如果她没有包含着一个收缩性原初力量,就会变得四分五裂”[6]WAI30。
在《世界时代》(Die Weltalter)原稿I 中,谢林将两者的关系表述得更加清楚和明确:
在存在里面,收缩的远处力量是一个封闭的力量,而肯定的原初力量则是一个被封闭的力量,也正是在这里,纯净性的本质采纳了最初的一些被动属性。这里产生出了一个已经变得温和的“光明本质”(Lichtwesen),它不同于纯净性最初的那道不可逼视的光芒,因为那道光芒在这里已经由于相反的本原而得到柔化。[6]WAI57
也就是说,普遍意志本身是耀眼的不可被直视的光,但这种光是不可持续的,无法在自身内建立起稳固的结构。私己意志作为一种收缩性的力量,想要将普遍意志落实、固定下来。于是,扩张性的普遍意志与收缩性的私己意志之间的对抗表现为存在内部一种疯狂的内在冲突。一方面这种冲突表现了原初存在的无秩序状态,但另外一方面也展现了原始生命的涌动。通过两种本原之间的交互作用,光芒驱除了黑暗,同时也柔化了自身,变成了一道“温和的”光明本质。由此,存在作为统一体被固定下来,在当下结束了原初存在的混乱状态,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结构。
回到恶的可能性问题上,在谢林看来,恶并非一种缺乏或者对善的否定,而是一种“私己意志的提升”[4]SWVII365,是立足于“本原关系的一种积极的颠倒或反转”[4]SWVII366,它“导致了针对全部存在的最猛烈的战争,甚至企图颠覆创世的根据”[5]SWVII468。具体来说,当爱的精神掌控着私己意志的时候,本原关系就会处于一种神性状态和秩序之中。而一旦私己意志被提升,反过来控制了爱的精神,那么就会重新回到一种混乱的无秩序状态之中。这也正是恶的产生:“一个单纯的局部意志占据统治地位,它再也不能像原初意志那样,把各种力量统摄在自身之下,使其联合起来,因此它必定会努力从那些纷乱交错的力量里,从一大堆欲望和肉欲里,塑造或拼凑出一个私己的、孤零零的生命。”[4]SWVII366因此,恶在形而上学上具有自身独立的地位,是建立在本原关系的颠倒之上,是一种私己意志的胜利。
恶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现实的(必然的)。谢林从“创世”(Schöpfung)的层面来说明恶之必然性。在人这种有限物之中,存在着来自于上帝的爱的意志;但同时,人自身又带有要将一切东西个别化的私己意志。在创世之初,人的存在就表现为这种爱的意志和私己意志的斗争和循环往复。人们诞生于作为核心的爱的意志,而爱的意志“作为一切意志的最纯净的本质,是一团吞噬任何特殊意志的火焰”[4]SWVII381;如果人想要在这团火焰中存活下去,就要消除掉全部的私己意志,从而和火焰融为一体。然而,私己意志的本性要求的便是要保留自身的特殊性,推动着人“企图离开核心,来到边缘,以便在那里让他的自主性得到片刻喘息”[4]SWVII381。因此,恶是一种普遍必然的东西。
总之,在谢林那里,恶的问题最终被追溯到存在自身双重结构的运动问题。人的内部具有两种本原力量,由此“人里面有最深的深渊和最高的天空,或者说,有两个核心”[4]SWVII363。而恶的可能性就是建立在这种本原关系的颠倒之上,恶的现实性则源于创世之初对人这种有限者的存在规定。谢林将自由等同于存在,那么恶在自由中的作用正如一种反体系的因素在体系中的作用,一种向内收缩的力量在原初存在之中的作用。而恶的关键就在于反体系的因素破坏了体系自身的和谐状态。在下一部分,笔者将进一步揭示,由恶的问题所开启的存在的生成运动在谢林哲学中的核心地位,这也正是海德格尔如此看重谢林哲学的原因。
二、作为“本质性之物”的“生成”
在本部分,笔者将展示谢林和海德格尔思考存在问题的一致之处——存在不是一个静止的现成存在者,而是要在根据与实存者的交互活动中生成的。并且,对生成活动的论述展现了谢林和海德格尔在面对个体之有限性问题上表现出的惊人的一致——有限个体存在之中已然包含无限。
在上一部分笔者已经将谢林那里存在的生成运动展示为一种私己意志和爱的意志之间的纠缠和交互运动。私己意志作为一种分离的意志,使得我们首先觉察到自身,进而与自身分离,与自身相对立,从而才开启了一系列的存在活动。《斯图加特私人讲授录》中,谢林引用了歌德的话,用以说明收缩性本原即私己意志是一切实在性的开端:“谁若想做大事,必须凝神定气,限制之中方显大师。”[5]SWVII429而爱的意志则是一种建立关联的意志,“它把两个本来可以独自存在,然而并未独立存在,而且离开对方就不能存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4]SWVII408。因此,原初存在在自身内就包含了两个方向相反的运动,并在这种运动和斗争中展开了自身的存在。
因此,对谢林而言,所有的存在都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Werden),即从原初的状态一步步成长、发展(Entwicklung)①“发展”(Entwicklung)这样一个词从词源学来说是由“ent-”(去除)和“wickeln”(动词,卷起来)两部分构成,因此,发展本身就有将卷起来的东西展开的含义。在谢林哲学中,“发展”与“外化”(Auerung)、“启示”(Offenbarung)、“演化”(Evolution)、“潜能阶次化”(Potenzierung)等概念都是同义的,都是指存在一步步地成长、生成过程。起来的。“我们内部有两个本原,一个是无意识的、黑暗的,另一个是有意识的。我们的自身塑造过程(Prosess der Selbstbildung)都包含那样一个过程,即把我们内部的无意识的现成已有的东西提升到意识,把我们内部天生黑暗的东西提升到光明,简言之,达到一种清晰性。”[5]SWVII433并且“真正说来,整个生命仅仅是一个不断提升(erheben)的意识生成过程”[5]SWVII433。换言之,当存在被谈论的时候,不仅那个当下存在的具体样态,还有存在自身在过去的每一阶次的样态都应当得到呈现,存在要展示自身是如何通过一步步的发展历程成长为“如其所是”的存在物的。
海德格尔对谢林这一思想极为赞赏,由此他认为谢林“本源地瞥见存在之本质”——“事物诚然存在(sind),但其存在(Seyn)之本质在于,展示绝对者在其中确立和展现自身的每一阶次(Stufe)和样态。存在不会消失在一种被叫作生成的外在流散上,相反,生成被理解为存在的一种样态。”[2]GA42214在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中,海德格尔就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此在的存在亦不是现成在手的,“生存问题总是只有通过生存活动本身才能弄清楚”[1]SuZ12。存在本身不是静态的现成存在者,所谓“存在的遗忘”都是不能认识到存在与存在者在存在论上的区别。而谢林的存在之生成的观点则恰恰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将存在等同于实存的做法,将存在区分为实存者和根据,并认为存在本身意味着一种实存者和根据的生成运动。
在《谢林书》中,海德格尔将恶的问题进一步归纳为:恶的可能性问题指向的是“永恒精神的绝对同一性的生成运动性”,而恶的现实性问题指向的则是“个别者之生成的问题”[2]GA42228-229,即“个体化原则”(principium indiciduationis)问题。正如前文所述,前者意味着存在在两种本原之间、在相互对立和斗争中展开了自身。而后者,“个体化原则”则指向了作为有限者的个体之生成问题。①关于谢林哲学中的个体性问题的具体阐述,参见巴黎索邦大学哲学系加朗希姆-科维雅克(Galland Szymkowiak)研究员的相关论述:M,Galland-Szymkowiak,“The Problem of Individua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Schelling,from the Identity Philosophy to the Ages of the World(1801-1811)”[J].In: Schelling-Studien.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zu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Verlag Karl Alber,2016:3-19.
谢林通过创世之初的“决断”(Entscheidung)来说明人这样一种个体存在的运动是如何开启的:
人在原初的创世中是一个未决断的本质——(在神话里,这个本质可以描述为此生之前的一个无辜状态和起初的极乐状态)——;唯有人能够自己做出决断。这个决断不可能出现在时间里;它位于全部时间之外。[4]SWVII385在谢林的哲学中,时间不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线性循环结构。确切来说,过去指的是“前世的时间”(vorweltliche Zeit),是原初本质从远古的黑暗世界演进的历史;而所谓的“现在”,是通过与过去的分离(Scheidung)②“决断”(Entscheidung)一词中的词根“分离”(Scheidung)已经暗示了两者的亲缘关系。产生的,但每一个当下都是以过去作为根基,每一个当下中都已经包含了全部的时间。“‘过去’不仅仅是‘现在’的先验根据。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使得现在存在,并将过去与现在区分开。”[7]人做出决断之时,永恒的时间才得以开启。因此,不是人在时间序列中做出了在善恶之间的决断,而是通过决断,人成了永恒的开端。“人在这里是怎么行动的,他自永恒以来在创世的开端就已经是怎么行动的。”[4]SWVII387也就是说,通过决断,人结束了自身内部的混乱状态,重新建立了私己意志和爱的意志之间的和谐关系;私己意志并未被克服和消灭,它伴随着人诞生,并作为黑暗的本原始终留在有限者的过去之中。
但对于人这种个体存在者而言,伴随着恶而诞生正是人之存在的命运,只有从黑暗中诞生并将自身重新提升至光明,生命才能坦然接受自身的命运并在上帝的爱中完全实现自身。也就是说,存在的运动一方面指向绝对者自身的生成运动,另一方面则指向了有限者的“决断”。但是,有限者的决断并不是一种“自在存在”,而是始终受着整体之必然性的引导和约束的“自为存在”③“自在存在”指的是有限者在一种无所关联的状态下的存在,而“自为存在”则强调只有在一种关联活动中才能讨论有限者的存在。。“个别行为都是来自于自由存在者的内在必然性,随之本身是伴随着必然性而被实施的。”[4]384换言之,个体存在的有限性不是对无限性的否定和对立,而是无限性在生成和转化过程中将自身固定在有限性之上,从而使得每一种有限个体的存在都能在自身之中看到神之无限性的光芒。个体之中已然包含永恒,正如先刚教授在《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代序)》所引用的谢林原话,“精神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在有限中呈现出无限”[8]6。
对于海德格尔,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关联更是通过一种生存论的表述被确立下来。在《存在与时间》中,此在的存在建构向来已经是“在世界之中存在”[1]SuZ53,没有世界作为“物”涌上前来的场域,此在的生存活动亦无从谈起。此在作为一种有限之物,在源始的意义上就是与无限的世界一起作为“双重本原”关联着的。此在本身的“操心”和“操劳”都凸显了它的有限性——此在向来已经被抛给了世界。但同时,此在又不仅仅是一种有限性的个体,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此在向来是生活在世界整体中的,始终要与它的“同代人”共同接受时代的命运,这构成了此在完整的本真的时间性存在。[1]SuZ384-387在《谢林书》的结尾,海德格尔写道:“立身于这一姿态中的人能作为一种历史性的人和一种命运照面,自己把这一命运接纳下来,并超越自己来承担这一命运。”[2]GA42281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此在在自身的命运中窥见了存在的命运并决心将其接纳下来,这使得此在拥有了突破自身有限性、在自身之中寻找无限的可能。
在这一部分中,笔者简要展示了谢林对存在的生成运动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在前期海德格尔哲学中与此在的生存论思想异曲同工,而对于后期海德格尔来说,也能为他克服“主体性视角”的努力提供帮助。在下一部分,笔者将进一步以“非根据”为核心,揭示谢林哲学中的存在的生成运动在开端处的双重面向,并指出这一双重面向与30 年代海德格尔的“转向”——克服前期“主体性视角”——的契合之处。
三、非根据(Ungrund)与存在之“自行回隐”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揭示谢林“非根据”概念的双重性质:非根据本身没有根据,因此在一切事物之先;但是同时,非根据又要为其他事物提供根据,因此它的存在是一种建基(Gründung)性的存在。通过对“非根据”这一概念的阐述,海德格尔表达了一种对《存在与时间》中基础存在论的反思,揭示了一种存在自行回隐的可能性。
谢林将那个在全部根据和实存者之先的东西称为“原初根据”(Urgrund)或者是“非根据”(Ungrund)。非根据本身不是根据和实存者的同一性,毋宁说,它是两者还未区分开之前的状态,是一种“绝对无差别”(Indifferenz)。甚至可以说,非根据本身是为根据和实存而奠基的:“无论是根据的本质,还是实存者的本质,都只能是那个先行于全部根据的东西,亦即绝对意义上的存在者,‘非根据’。”[4]SWVII408但同时,“非根据”(Ungrund)一词中的前缀“非”(un-)就有着否定的含义。那么,非根据自身是对“根据”的一种否定和反对,它自身是没有根据的。也就是说,“非根据”是一个绝对的在先的东西,它本身不能被任何其他事物奠基,因此自身是没有根据的;但同时,它又可以为其他存在给出奠基。因此,“这一无法被奠基的开端活动同时拥有‘离基深渊’(Ab-grund)与奠基/给出根据(Gründung)的双重作用”[9]①值得一提的是,雷思温老师在论文中也揭示谢林哲学对“非根据”的论述中所包含的危险——存在的一种堕入深渊的可能性。谢林所寻找的存在的开端是一个完全不经由任何中介、自己直接开启的绝对的在先者,而这样一种开端“结果使得世界和万物不但无法先行被理性以及超感性世界的形而上学概念所中介和规定,更是暴露了其无根据的、直接的原初偶然性”。舒尔茨(Walter Schulz)在给《自由论文》写的导论中也指出了谢林哲学中的非理性因素——谢林哲学提供了“一种哲学的草稿,这种哲学为后观念论和现代中作为反抗理性的力量的意志的规定做好了准备。”参见:Schulz,W.:,,Freiheit und Geschichte in Schellings Philosophie[J].In: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 und die damit zusammenhängenden Gegenstände,Stuttgart:Kohlhamme,1975:14.。
根据张柯教授的研究,海德格尔早在1927/28年的讨论课中就已经很重视谢林对根据和实存的划分,以及“非根据”这一概念。正如张珂教授在文中指出的那样,根据问题在海德格尔那里变成了存在问题:“根据的根据性运作即‘存在之自行置送’,而且‘根据之不性’(即Ungrund 或Abgrund之意谓)乃是‘存在之不性’亦即‘存在之自行回隐’。”[10]实际上,“非根据”与海德格尔在30 年代的思想转向是非常契合的。中期海德格尔放弃了从此在出发解释存在问题的路径,他的谢林阐释正是这样一种“去主体化”视角的展现。[11]在这种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自由论文》原本可以给出“哲学的第二个开端”[2]42198,并在另一处指出:“另一种开端的哲学首先是作为存在之真理的瞬间-场所(Augenblick-Stätte)的‘离基-深渊’的建基(Gründung des Ab-grundes)。”[12]GA94282
海德格尔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批评了《存在与时间》中的做法——要“提防自己把事物的现成存在或上手存在弄成对存在进行规定的第一和唯一尺度”[2]GA42198。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基础存在论中,海德格尔从此在这样一种向来已经对存在有所领悟的存在者出发追问存在的意义。然而,这里已经暗含着一种解释学的循环了:此在必须已经存在,才能对存在有所领悟。“照这么说,人必须首先抵达了敞开之处(Offenheit),抵达了存在之‘此’(Da),从而他自身在所有其他存在者之中在此-存在(da-zu-sein)。”[13]319换言之,此在的存在,或者说人作为此在本身依然是有前提的、需要被追问的。这一前提,即人如何抵达此在,在谢林那里便表述为作为根据之本质的“非根据”问题[13]319。海德格尔在《论根据的本质》(Vom Wesen des Grundes)的注释中强调了根据问题与存在问题的关联——“建基的必要性在何处?在‘离-基’(Ab-)与‘无-基’(Un-grund)之中。它们在何处?在‘此-在’(Da-sein)中。”②笔者为了凸显出“Abgrund”与“Ungrund”在词源上的一致性,在这句话中将“Ungrund”没有译为“无根据”而是译成了“无基”。[14]GA9127这里的“此-在”已经不再是《存在与时间》中的对生存有所领悟的存在者了,而是意味着一种离基和无基,在这种离基和无基之中人作为存在者才首次抵达了它的“存在之此”。换言之,《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的生存论”依然是从此在出发追问存在的意义,而在《谢林书》中,海德格尔已经认识到,人作为存在者并非“向来已经在此在之中了(作为理解着存在的本质);而是人从‘深夜’中首次被‘提升至此在’”[14]GA9321。
而人被提升至此在的关键,就在于一种“决断”(Ent-Scheidung)。对谢林来说是如此,对海德格尔亦是如此。谢林用创世之初的决断来比喻这种从非存在走向存在的过程。并且对谢林来说,从“非根据”走向根据是必然的。正如在上一节笔者指出的那样,这种决断与其说是人的选择,不如说是人这种存在者内部双重本原斗争的必然结果,是私己意志发现自身的必然结果。只有私己意志发现了自身,并试图建立起和自身的关联,才会使得爱的意志找到反抗者,从而借助这一反抗者实现自身,由此永恒时间得以开启。[4]SWVII375-376而海德格尔将创世之时受造者的存在揭示为一种“本质筹划”(Wesensentwurf),即“把某物内在的能在(Seinkönnen)在其必然性中置于其面前(vor-stellen)”[2]GA42234。也就是说,在创世之时,人作为此在抵达了它的“此”。海德格尔同样将创世的瞬间理解为时间之轮的开启:“当时间性真正本现时,即在曾是和未来在当下中囊括在一起的那一瞬间中,当人类完满的本质作为他如此这般的本质让他猛然醒悟时,人才会经验到,他必定总已是这个他所是的人了,并且作为这个已经自己决定了要去成为这个人的人而是。”[2]GA42268这里所说的“创世”更多的意义上指的是人重新思索自身和存在的关联,是人作为此在的“绽出”(Ekstase)。海德格尔不再从此在这类特殊的存在者出发追问存在的意义,而是认识到是存在为人开辟出了一个特殊的“寓所”,人只有重新思索本质问题时才能进入这一寓所。海德格尔和谢林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对作为自由或者存在的本原之诠释,只能基于本原的‘自身实行’,而这需要一种‘泰然任之’和‘绽出’的姿态转变。”[11]
因此,“人如何走向它的此在”这样一个问题可以被置换为“人走向的是何种意义上的‘在之此’”?“为了抵达此-在的敞开状态,不仅是神,而且人也要不间断地像一个轮子那样回-返(zurück-kehren)至他自身的能在的离基中,并且在那里与一种选择会面。”[13]324也就是说,“离基”对海德格尔来说,是此在还未将自身的存在固定下来之前的状态,是仍然保持着可能性至最大极限的状态,甚至是一种可以走向非存在之“深渊”的可能性。《存在与时间》中将此在生存的可能性理解为本真和非本真的选择,而在《自由论文》的启发下,海德格尔更进一步地意识到,离基之处是此在完全倾覆自身存在之可能性的“深渊”:
人类并不是某种现成的观察对象,不是我们事后再将每天寻常琐碎的感觉披在上面的东西,相反,人类是在深入存在的诸种深渊与高处的洞察中,在朝向神性的骇人之处、朝向一切受造者的生命之畏、朝向一切受造的创造活动的忧郁、朝向恶之恶性及爱之意志的洞察中被经验到的。[2]GA42284
也就是说,人所抵达的是这样一种此-在,在那里,存在既有可能敞开,亦有可能会自行封锁。而这正是后期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转向中的最为标志性的思想。对海德格尔来说,存在是一种馈赠,但同时,存在的命运也必然经历漫长的“存在之遗忘”。与其说海德格尔批评传统形而上学中对存在的遗忘,不如说他将“存在的遗忘”本身看成了存在自身被给予的命运,这一命运也被称为存在之“自行回隐”[15]。
在这一部分,笔者进一步指出了一种由“非根据”奠定的“非存在”在谢林和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对谢林来说,在实存者与根据之先的是能够同时“离基”和“建基”的“非根据”;对海德格尔来说,存在的自行敞开和自行回隐都是存在必然之命运。在下一部分,笔者将揭示两种看似相似的哲学在根本上的差异所在。
四、永恒与瞬间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从有限和无限的关系角度,指明海德格尔和谢林哲学的终极差异——谢林试图维护理性体系,个体只是永恒命运中的一个环节;而海德格尔则认为瞬间即尺度,在一种“绽出”之中,存在领会了自身之天命。
总的来说,尽管谢林论证了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自由论文》中,他还是在尽力否认一种恶的现实性,尝试回到一种上帝之神圣中。“当恶回归非存在或潜能状态,它就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成为基础、从属者,而这个东西本身已经不再与上帝的神圣性和爱相矛盾。”[4]SWVII405也就是说,在最终的意义上,爱才是最高者,它先行于一切实存者和根据。因此,对谢林而言,“恶”依然是某种需要被克服的东西。尽管恶本身具备着肯定的、建构体系的能力,但是它也仅仅是存在的某个环节,最终还是要回到上帝之爱中去。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说,“谢林的晚期哲学被认为是退回到了基督教的形而上学中。最终理性被提升,朝向恶的自由再次被颠倒为朝向善的自由”[13]21。更进一步来说,“恶”和“根据”都是不可真正被认识和把握的,它们代表的是去追溯存在的时候发觉到的自然界在存在之中存留下来的一些“黑暗的残余物”,仅仅从某段特定的过程来看它们才是存在着的。而经过生命的自我提升和塑造,“根据”也会被提升至更高的层次,从而回归到一种更高的统一性之中。
针对谢林哲学中“恶”与“根据”最终是要被克服的这一思想,海德格尔认为:“根据、实存及两者的一体性,三者的可统一性不仅越来越低,而且彼此间甚至被如此之远地驱散开,以至于谢林又落回到了西方思想已经变得僵死的传统中,没有创造性地转化它。”[2]GA42279也就是说,在海德格尔看来,谢林依然预设了一种终将被克服的“恶”,而不是将“恶”真正地接纳到存在自身的命运之中,将存在看成自身的自行敞开。这种做法和以往“遗忘了存在”的形而上学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换言之,谢林依然是一种“主体性视角”出发,或者说是从一种“神”的视角出发,追求的是一种神性秩序的整体。①关于谢林的《自由论文》是否还属于德国唯心论传统,至今依然还有争议。但笔者认为,无论是《自由论文》,还是谢林更晚期的一些作品,固然有超越了德国唯心论的部分,甚至有一些神秘化的倾向。但总体来说(尤其是与海德格尔的对比中),谢林仍然是在追求一种整体性秩序的。因此,《自由论文》当然还是应当被视作在唯心论传统中的讨论。参见:H.Schwaetzer,Schellings Freiheitsschrift und Baaders Beiträge zur dynamischen Philosophie [J].In:Mystik und Idealismus:Eine Lichtung des deutschen Waldes.Leiden: Brill,2020:416.因此,谢林哲学那里人的有限性不是海德格尔意义上个体的有限性,谢林不能认识到——“一切存在的本质都是有限性,并且唯有有限的实存者才拥有特权和痛苦,来存在于如其所是的存在中并把真实之物经验为存在者。”[2]GA42280
正如德国学者舒尔茨所说,“海德格尔的意图不是超人类的-无限的东西(das Übermenschlich-Unendliche)。海德格尔想要的是彻底的有限化(die radikale Verendlichung)”[16]36。只有一种追求“彻底有限化”的哲学才会认为瞬间就是“永恒性的本质”[2]GA42197,并且“唯有这些瞬间才是人类之本质规定的可能尺度”[2]GA42269。换言之,永恒即瞬间,海德格尔所追求的不是在全部的历史长河之中把握存在的整体性,而是在某一瞬间命运之轮的偶然开启之中,个体得以把握全部存在的命运。这正是其哲学与“虚无主义”无法完全撇清关系的原因之所在——世界作为整体本身建立在一种彻底的偶然性之上。
而对于谢林来说,瞬间即永恒,重要的不是存在在哪一个瞬间得以“走出自身”和“走向自身”,而是所有存在的活动都是在一种永恒的时间体系中展开的。所有当下、个体性都是整体性中的一环,而永恒赋予了瞬间以意义——每一事物之中都包含了一个永恒开端,透过每一瞬间,存在都能窥见自身之中的神性。
结论
在本文中,笔者从谢林在《自由论文》中对恶与自由的阐释出发,展示了谢林存在问题的思索——存在始终保持为双重本原之间斗争和统一的展开进程。在第二部分,笔者进一步阐释了谢林哲学中存在的本质就在于它的生成和发展历程这一核心观点,具体来说,谢林在根据和实存者的区分中将存在看成是生成的。由此,海德格尔认为谢林“克服了存在的遗忘”。在第三部分,笔者以“非根据”这一概念为核心,展示了谢林哲学中存在的生成运动在开端处的双重面向,并指出后期海德格尔通过这一概念完成了自身哲学的“去主体化倾向”,将存在的自行敞开和自行回隐都看作是存在的命运。在最后一部分,笔者揭示了海德格尔和谢林两者在哲学旨趣上的不同:谢林追求的是瞬间之中的永恒,有限个体始终是在与无限的张力中确定自身的位置;海德格尔追求的则是永恒中的瞬间,或者说是一种彻底的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