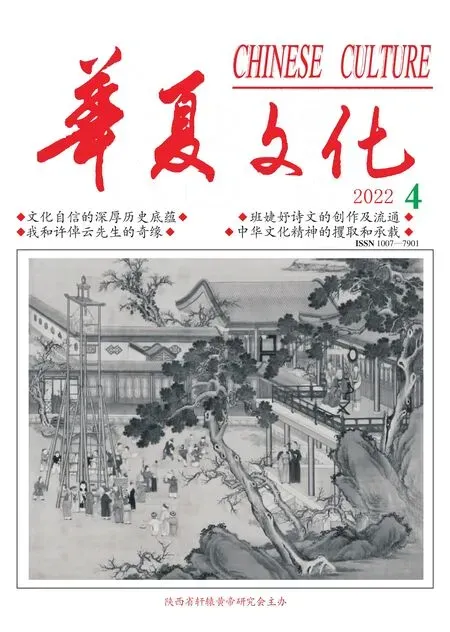班婕妤诗文的创作及流通
□刘 明
班婕妤能够引起文学史的关注,大概首先是《汉书·外戚传》载有她所创作的《自悼赋》(题名据《艺文类聚》),辞赋是汉代文学创作的主流,遂凭借该赋而获得第一篇女性创作的“宫怨赋”的美誉。班婕妤也成为中国女性文学史书写的“关键性”角色,或被奉为“圣人”,如称:“汉代女文学家被捧为圣人者有二人,一是班婕妤,一是班昭。”(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诗文创作如《怨歌行》或被认为是五言诗发展史上一篇承上启下的作品,《报诸侄书》被视为古代女性所写的第一篇文学批评专论,习惯将李清照《词论》称为女性创作的第一篇文学批评专文,作品集则被称为“妇人专集之最古者”(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绪言》),班婕妤收获了女性文学史的诸多“第一”。美国汉学家康达维也撰有《班倢伃诗和赋的考辨》予以专门讨论。兹重读相关史料,就班婕妤诗文创作的细节,特别是作品在中古时期的流通问题略作管窥。
推原西汉时期班婕妤“在场”的文学场景,首先依据的是班固《外戚传》和《叙传》对班婕妤事迹的集中记载,这是第一手的文学史料。班婕妤是班固的祖姑,班固纂修《外戚传》之班婕妤传不同于对其他后妃的处理方式,就是写录她笔下的一篇赋作,不惟借此标举品行修养,特别是文学创作方面的才华,亦可直接证实作品的真实性。班婕妤恐不止创作过《自悼赋》,班固亦想必经见了她创作的绝大多数作品,但又唯独该赋被选录在史传里,耐人寻味。除史传外,还有一条隐藏的线索表明班婕妤曾得到著名辞赋家扬雄的关注。《甘泉赋》里的“屏玉女而却宓妃”,按照《汉书·扬雄传》的解释是“微戒齐肃之事”,实际上说的就是许皇后和班婕妤失宠于成帝的事迹。扬雄与班家有通好之谊,《叙传》称“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印证扬雄与班家有着密切的交往。故扬雄不仅知悉班婕妤的宫内生活,而且也极有可能影响着她的文学创作,班婕妤的《报诸侄书》可视为例证。该文提出“推诚写实”的文学主张,批评“类多华辞”的创作倾向,怀疑就是扬雄反思赋作讽谏功能,进而批评赋作“丽以淫”影响下的结果。
班婕妤约略卒在哀帝、平帝间,或将她的生卒年系在元帝初元元年(前48)至平帝元始二年(2),如翟里斯的《中国文学史》,卒年又或系在哀帝元寿元年(前2),哀帝建平元年(前6),但都没有切实的依据。《外戚传》仅言:“至成帝崩,倢伃充奉园陵,薨,因葬园中”,并未明言逝在何时,不过康达维据此条材料也持卒在约公元前6年的意见(参见《班倢伃诗和赋的考辨》,下同)。实际上自班婕妤冷遇后宫,班家的政治待遇亦受到影响。《汉书·叙传》有“班氏不显莽朝,亦不罹咎”的记载,即便班婕妤在王莽新朝尚在世,恐亦处于冷清凄凉的境地,她的文学作品也很难引起时人的注意。班婕妤的作品仍有一定的保存方式,或宫内的文书档案,或班家有作品的写录本,诚如康达维所云:“班固可能是从家藏本中获得班倢伃的作品,而非宫廷的藏书。”进而东汉以降,班婕妤真正进入了被阅读和理解的视域,开始了她的文学史之旅。肇其始者,当然是班固笔下的史传,但史笔的字里行间又透露出有所拘忌的倾向。比如未题班婕妤的名字,这一点还不及她的侍女尚且题“李平”,而且有关她生平轮廓的记述也很简略,似乎有意在隐藏。出现此种情形的原因,应该充分考虑班家的外戚身份,而班固在《外戚传赞》里对外戚群体进行了一番总结,云:“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该评价当然也适用于班婕妤及班家外戚群体。《叙传》即提到班婕妤三兄班穉本受罪罚,因成帝母后的“后宫贤家,我所哀也”而获免,但也是“上书陈恩谢罪,愿归相印,入补延陵园郞”,长兄班伯也“称笃”且惶恐,显示都因班婕妤的受冷遇而政治地位受到了影响。根据谷永《黑龙见东莱对》所云:“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顷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藏,女宠至极,不可上矣。”班家曾经因班婕妤的后妃身份而显赫一时的。综合这些材料,似乎推测班婕妤尚不属于“保位全家”之列,故“不显莽朝”,这都使得班固笔下的班婕妤书写必然带有隐晦的倾向。这种情形,无疑“限制”了班固对班婕妤的史笔着墨,毕竟这关乎着家族的政治声望。有着出众才华而不止创作过《自悼赋》一篇作品的班婕妤,只可惜都因这种“限制”而难知其详,也间接地造成了后人对班婕妤其他传世作品的疑不能定。
康达维评价《自悼赋》的创作,“带有一种近乎自传性质的个人色彩”。结合外戚的视角,设身处地地推想班婕创作此赋时的心境,她除了被冷遇和排挤的悲伤,应该还会想到家族的荣誉问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班婕妤是了然于心的,所以维护家族的声望也是她写作《自悼赋》的一层动机。故赋作一开篇就写道“承祖考之遗德兮”,目的是强调家族的德望,也有借此微讽赵飞燕姊妹出身低贱、德不配位的用意。还写道“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离以自思”,则又在强调无时无刻不在反思遵循家教、妇道之严。还写道她“陈女图以镜监兮,顾女史而问诗”,表面上来看是在传达个人的道德要求和文化修养,实际上是写她自幼就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并不是像康达维所称的“班婕妤的教育情况了解非常有限”。这一切都意在表明,她虽然处于失宠冷落的境地,但家族的德誉并不会因此而有所贬损。当然,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班固选录此赋入传也不乏有为其祖姑班婕妤辩护、为家族辩护的用意。赋中写道“中庭萋兮绿草生”,印证写作的时空是春意盎然的宫内,春本来是希望的象征,她却“历年岁而悼惧兮,闵蕃华之不滋。痛阳禄与柘馆兮,仍襁褓而离灾”,确实写出了痛彻心扉的悲伤,甚至说是一种绝望,而发出“惟人生兮一世,忽一过兮若浮”的慨叹,及“勉虞精兮极乐,与福禄兮无期”的自我宽慰。这是在维护家族动机之外最具感情色彩的个人书写,与家族的道德训诫与文化修养书写融为一体,读来真切地体会到一位女性在家族荣耀身份的掩盖下面对世俗命运的无奈。
班固之妹班昭续修《汉书》,还同样作为班婕妤的侄孙辈,至少能够阅读到家藏本形态的班婕妤创作。不过,从班昭现存的作品(依据严可均《全后汉文》所辑)还看不出有班婕妤影响的痕迹,倒是创作的《女诫》依稀有她的影子,如写道:“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们,取耻宗族……间作《女诫》七章。”这与班婕妤《自悼赋》所写的“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离以自思。陈女图以镜监兮,顾女史而问《诗》……虽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自”,都强调女子要遵守礼仪,遵从女德,从中窥探到一以贯之的班氏家风。
班昭还极有可能在史传之外又进一步促成了班婕妤的固定化传播,依据是《列女传》,因为班婕妤即收在该书的“续传”里。《隋志》著录有《列女传》十五卷,小注称“刘向撰,曹大家注”,曹大家即班昭,她曾以注释的方式对《列女传》进行过文献加工。但《列女传》存在成书上复杂的文献问题,按照四库馆臣的意见,“其书屡经传写,至宋代已非复古本”(《四库全书总目》)。疑问之一就是班婕妤进入《列女传》是否出自班昭之手,可以肯定不是刘向的安排。北宋曾巩序录称:“曹大家所注,离其七篇为十四,与颂义凡十五篇,而益以陈婴母及东汉以来凡十六事,非向本书然也。”(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意思是班婕妤进入《列女传》,是班昭处理的结果,从班昭与班婕妤之间的亲缘关系也很容易理解,但遭到四库馆臣“其说无证,特以意为之”的批评。《崇文总目》也称:“陈婴母等十六传为后人所附”,同样不认为是班昭。兹以《四部丛刊》影印本(据自长沙叶德辉观古堂藏明刊有图本)《列女传》为据,班婕妤被收在卷八(属于“续传”),无四言性质的颂,有小传。小传的文本构成包括三部分,生平事迹、赋作(即《自悼赋》)和“君子谓”的评论,没有出现“班昭”或“曹大家”的字眼。生平事迹基本檃栝《汉书·外戚传》,但也存在着差异。例如开篇写道:“班婕妤者,左曹越骑班况之女,汉孝成皇帝之婕妤也。”玩其辞气,似非汉时人(比如班昭)的手笔,因为不会出现“汉孝成皇帝”的称谓,当然也有可能是经过后世改写的结果。另外小传称班婕妤“贤才通辨”,又称她读《诗经》等篇“必三复之”。此八字,不见于《外戚传》,是小传作者所“添加”。不清楚这么讲的依据,不过似乎表明小传作者对班婕妤有一定的熟悉度,但也很难据此就认为出自班昭之手。又照例写录载自《外戚传》的《自悼赋》全篇,没有提及其他的作品。最后的“君子谓”所云,最有价值的是对班婕妤赋作的评价,“及其作赋,哀而不伤,归命不怨”,但也只是就赋作思想内容的评价,缺乏对艺术旨趣的概括。
附带说一下《列女传》所载的班婕妤小传,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了彩漆屏风画,有班婕妤辞辇主题的画像。画像的右侧是榜题“汉成帝班倢伃”,左侧则是小传,同样是袭自《外戚传》,但与《四部丛刊》本却有文字上的差异,如开篇写道“班倢伃者,班彪姑也”,印证班婕妤生平事迹的文辞书写并不固定。
总体来讲,不管班昭是否是班婕妤进入《列女传》的选入者,毫无疑问的是,这都使得班婕妤借助《列女传》得到了稳固的传播,也获得了持续被阅读和理解的影响力,也间接地保证了班婕妤一直处在文学史的关注视野内。因为《列女传》是宣扬女性道德操守的典籍,也具有一定的政治讽谕性,所以是贵族阶层很看重的一部书,它具有一定的阅读力是毋庸置疑的。如曹植有一篇《班婕妤赞》(题名据宋本《曹子建文集》、《初学记》),赞辞云:“有德有言,寔惟班婕。”据他的《画赞序》云:“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淫夫妬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该篇当即《画赞》里的一篇,且从“淫夫妬妇”“令妃顺后”的用语,推断曹植所观班婕妤之画应是《列女传》里的班婕妤画像。又按《隋志》著录曹植《列女传颂》一卷,现存曹植作品还有《母仪颂》歌颂汤妃,《明贤颂》歌颂周宣王的姜后,都是见于《列女传》的人物,可以判断这些作品被收录在《列女传颂》里。《列女传颂》已经亡佚,仅有上述残篇被收在宋人重编的集子里,既然是一卷的体量,当不止限于这两篇,是否又作过“班婕妤颂”不得而知。不过根据曹植阅读过《列女传》的事实,他创作的《班婕妤赞》是依据了《列女传》里的班婕妤画像,应该是成立的。若果真如此,那么班婕妤选入《列女传》最迟是在曹魏时期。包括班婕妤在内新选入的人物,也都会按照《列女传》的固有体例而配上绘图。据《汉志》著录的刘向所序六十七篇,小注称“《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知刘向所编的《列女传》是配图的。
西晋的左芬也作有《班婕妤赞》(题名据《艺文类聚》),云:“恂恂班女,恭让谦虚。辞辇进贤,辩祝理诬。形图丹青,名侔樊虞。”“形图丹青”指的是将班婕妤绘成可供观瞻的画像,可能是画在屏风上的,也可能是《列女传》里的画像。据左芬之兄左思的《悼离赠妹诗》云:“何以为赠,勉以列图。何以为诫,申以诗书”,可以断定左芬笔下的班婕妤,同样来自《列女传》。左思也将其妹之才比况班婕妤,“穆穆令妹,有德有言。才丽汉班,明朗楚樊”(《悼离赠妹诗》)。傅玄也创作了《班婕妤画赞》(题名据《艺文类聚》),是《古今画赞》里的一篇,写道:“斌斌婕妤,履正修文。进辞同辇,以礼匡君。纳侍显德,谠对解纷。退身避害,志邈浮云。”依据的应该也是《列女传》里的班婕妤画像。综观曹植、左芬、左思及傅玄有关班婕妤的书写,主要就其品德着笔,几乎没有对她的文学创作有所评论。即便是所谓的“才丽汉班”“履正修文”,也应主要是针对《列女传》里的《自悼赋》而言。这几个例子,再加上《隋志》著录的除班昭注的《列女传》,还有赵母注本《列女传》七卷,除曹植《列女传颂》还有缪袭的《列女传赞》,主要是证实了班婕妤的传播,特别是那篇《自悼赋》,除凭借了《汉书》外,就是《列女传》载体的力度,而且都印证着作品的真实性。
除了史传和《列女传》,班婕妤的作品也可以通过集子的方式进行流通。女性的作品被编为集子最早的材料,是《后汉书·列女·班昭传》云:“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班昭逝后,由其儿媳妇丁氏将其生平作品汇为一编,即编了班昭集。班婕妤的作品,班家是否也会给她编为集子不得而知,魏晋时期应该已经出现班婕妤的作品集编本。班婕妤集最早见于《隋志》著录,题“汉成帝班婕妤集”一卷,小注还称“梁有班昭集三卷”。梁代出现了十余种妇人别集(据《隋志》著录),印证了班婕妤集最迟编在此时,至唐初尚有传本。班婕妤集既然编为一卷本的体量,显然集子里不会只有一篇《自悼赋》,而是还有其他的作品。另外,《太平御览》引《妇人集》还载录了班婕妤的《报诸侄书》,说明总集也是班婕妤作品流通的一种方式。南朝流通的“妇人集”有多种,如《隋志》小注称梁有殷淳撰《妇人集》三十卷,《梁书·徐勉传》也称他编有《妇人集》十卷行于世。此类“妇人集”的编撰,不排除抄撮当时流传的妇人别集,所载的《报诸侄书》当即抄自班婕妤集。班婕妤集及作为总集的《妇人集》,是观察其作品得以被阅读和流通的另一个重要视角。
魏晋时期除曹植等通过《列女传》阅读班婕妤外,西晋的陆机也创作了一首《班婕妤》诗,被收在《陆士衡文集》(依据清影宋抄本)《乐府十首》里,题“倢伃怨”。《倢伃怨》是一首乐府诗,辞云:“婕妤去辞宠,淹留终不见。寄情在玉阶,托意惟团扇。春苔暗阶除,秋草芜高殿。黄昏履綦絶,愁来空雨面。”《乐府诗集》也收有此诗,注云:“一曰《婕妤怨》……《乐府解题》曰: 《婕妤怨》者,为汉成帝班婕妤作也。婕妤徐令彪之姑,况之女,美而能文。初为帝所宠爱,后幸赵飞燕,姊弟冠于后宫。婕妤自知见薄,乃退居东宫,作赋及《纨扇诗》以自伤悼,后人伤之而为《婕妤怨》也。”据《乐府解题》,班婕妤在《自悼赋》之外还创作了《纨扇诗》,一般认为就是收在《文选》里的《怨歌行》。陆机仿《自悼赋》、《纨扇诗》之意而创作了《婕妤怨》,表明陆机至少读到了班婕妤的这两篇作品,阅读的载体应该就是班婕妤集。细读陆机此诗,能够印证班婕妤作有《纨扇诗》的证据仅“托意惟团扇”一句,而其他的诗意都来自《自悼赋》。如“婕妤去辞宠,淹留终不见”对应赋里的“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扃”,“寄情在玉阶”“春苔暗阶除”对应“华殿尘兮玉阶苔”,“秋草芜高殿”对应“中庭萋兮绿草生”,“黄昏履綦絶,愁来空雨面”对应“思君兮履綦”“双涕兮横流”。《纨扇诗》即《怨歌行》是否为班婕妤所作存在争议,不过陆机笔下的“团扇”意象确实不见于《自悼赋》,意味着班婕妤确实有一首包含“团扇”意象的作品。《乐府解题》认为是《纨扇诗》,陆机阅读《纨扇诗》及该诗的真实性也没有证据可以否定。
南朝人也依据当时流传的班婕妤集,进行评论和选诗。如钟嵘《诗品序》云:“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在五言诗的发展链条上,给予班婕妤很高的评价,并把她列入上品,云:“其源出于李陵。‘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钟嵘笔下的“团扇”短章,指的就是《纨扇诗》,且评价该诗“怨深”,与《列女传》评价《自悼赋》的“哀而不伤,归命不怨”不同。即在同一位班婕妤的笔下,出现了怨与不怨两种类型的创作。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就对班婕妤是否创作了五言诗提出了疑问,称:“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实际又是另外的情形,即这首“来历不清”的《纨扇诗》,除钟嵘外,《文选》和《玉台新咏》也笃定它的著作权是班婕妤,印证了他们选此诗依据的班婕妤集(或其他诗文总集)就是题班婕妤作,这在南朝应该是“普遍”的共识,故萧统等深信不疑,不作辩解。《文选》题“怨歌行”,载于卷二十七,李善注引《歌录》云:“《怨歌行》,古辞,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拟之。”《歌录》也将其视为班婕妤所作。《玉台新咏》载该诗题“怨诗”,有小序云:“昔汉成帝班婕妤失宠,供养于长信宫,乃作赋自伤,并为《怨诗》一首。”屈守元认为该小序抄自班婕妤集(参见《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即徐陵选此诗依据的是别集,这是相当精彩的意见。此段小序也评价说班婕妤“自伤”,虽然称“怨诗”,但伤而不怨,与《列女传》对《自悼赋》的评价相同。
总体而言,前人对《怨歌行》是否为班婕妤的作品有疑问,但却不能证实这种疑问。进入今人的文学史,仍然无法回避《怨歌行》的真伪性问题,如文学史家称:“《文选》又把乐府古辞的《怨歌行》题为班婕妤作,也有问题”(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修订本)。逯钦立的观点是认为“此诗盖魏代伶人所作”(参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康达维对于《怨歌行》是否出自班婕妤的辨析,带有西方汉学家的视角和眼光,认为:“《怨歌行》应是东汉时期的作品。不论诗作的风格,抑或‘弃妇’的主题,皆与一般公认为是东汉时期作品的佚名古诗和乐府诗相吻合”,“《怨歌行》很有可能与古诗和乐府诗的佚名诗出自同一文学传统。或许这首诗起初是一首有关‘弃妇’的民歌,后来,可能在魏晋时期,这首诗被附会于班婕妤的故事,以致《怨歌行》被认为出自班倢伃之笔。”也有肯定该诗出自班婕妤之手的意见,如萧涤非称:“余则深信不疑:第一,以时代论,有产生此种作品之可能。第二,文如其人。‘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不管六朝,无论魏晋,总之非班姬不能道。第三,按曹植《班婕妤赞》‘有德有言,实为班婕’,傅玄《班婕妤画赞》亦云‘斌斌婕妤,履正修文’。至陆机《婕妤怨》‘寄情在玉阶,托意惟团扇’,则明指此诗矣。”(参见《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又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称:“(《怨歌行》)是乐府歌辞,属楚调曲。成帝时乐府非常兴盛,班婕妤又是一位才女,她仿照乐府民歌的风格写出这首诗,是合情合理的。有人疑此诗为伪托,并没有可靠证据。”莫衷一是,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兹略陈己见如下。
从西汉五言体乐府歌辞的创作历程来看,班婕妤是能够创作出《怨歌行》这样水准而且整齐的五言诗的。同载于《外戚传》的有两首乐府体歌辞,一是《戚夫人歌》,辞云:“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另一首是《李延年歌》,辞云:“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两首诗的主体都是五言,只是尚未达致整体的五言化,至成帝时的班婕妤是能够完成整体五言化的“使命”的,标志就是《怨歌行》的创作。再者,《怨歌行》里的一些细节与《自悼赋》形成互文,如“新裂齐纨素”里的“纨素”,《自悼赋》有“纷綷縩兮纨素声”的书写。何谓“纨素”?一种说法泛指丝织品,一种说法指冬服(《汉书》颜师古注引李斐之语)。班婕妤笔下的“纨素”应该解为冬服,《自悼赋》创作在初春时节,乍暖还寒,故尚不及脱去冬服。在《怨歌行》里,以冬服裁做合欢扇,在孤独冷寂的冬日借以烘托昔日得君主恩宠的回忆。“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合欢扇的出现时间是考订此诗作年的实物依据,至迟在东汉后期出土的汉画像石里已经出现团扇的图案(徐州睢宁九女墩汉墓所出),故此诗创作在汉代应是没有疑问的。扇子的意象不见于《自悼赋》,但“明月”却有书写,即“蒙圣皇之渥惠兮,当日月之盛明”,“明月”实际上都是君主的象征。“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写的是受恩宠的情境,与《自悼赋》里的“奉隆宠于增成”“既过幸于非位”表达之意相同。“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对应赋中“历年岁而悼惧兮,闵蕃华之不滋”之意。“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表达的也是赋中“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扃”“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之意。综上两者之间的互文性,也可以印证《怨歌行》出自班婕妤之手是站得住脚的。在没有坚实的证据能够否定的前提下,将《怨歌行》的著作权系在班婕妤的名下,不失是一种严谨而求实的态度。
传世还有一篇《捣素赋》,载于《艺文类聚》,但有删节,《古文苑》所载者是全篇。康达维根据《古文苑》一书的疑伪性,认为该篇作品出自班婕妤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古人也有质疑,如唐代李善云:“然疑此赋非婕妤之文,行来已久,故兼引之。”(《文选·雪赋》注)清人孙志祖也称:“此赋六朝拟作无疑,然亦是徐、庾之极笔。”(《文选理学权舆补》)对于《捣素赋》的来源,在《艺文类聚》编纂成书的唐初时期,班婕妤的别集以及《妇人集》尚有流传,欧阳询也能看到这些作品集。因此,《艺文类聚》所录的《捣素赋》完全有可能就是来自班婕妤的别集或《妇人集》,印证作品产生时间的下限是南朝。该赋存在与《自悼赋》互文性的细节,如均以“明月”比况君主,“望明月而抚心,对秋风而掩镜”,《自悼赋》的书写是“蒙圣皇之渥惠兮,当日月之盛明”。此赋最值得注意的艺术特征有两处,一是对捣素声音的描摹,写道:“梧因虚而调远,柱由贞而响沉。散繁轻而浮捷,节疏亮而清深……或旅环而纾郁,或相参而不杂。或将往而中还,或已离而复合……任落手之参差,从风飚之远近。或连跃而更投,或暂舒而长卷。”将本来难以书写的声音之状,通过一系列形容词与动词的使用,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出来。一是对心理的描摹,写道:“阅绞练之初成,择玄黄之妙匹。准华裁于昔时,疑形异于今日。”从捣好的素练里选择最精美的布匹,还是按照昔日的尺寸去剪裁,但突然又想到相别已久,可能剪裁已经不再合身。又写道:“书既封而重题,笥已缄而更结。”那种期待所寄之物能够顺利送达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前人可能觉得此类精雕细琢而又婉转含蓄的文辞不可能产生在西汉时期,而应该是南朝齐梁时期的文风。根据王褒创作的《洞箫赋》对声音惟妙惟肖的描写,司马相如《长门赋》对宫怨心理的形象刻画,以及班婕妤《自悼赋》中“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这样细致的心理描写来看,班婕妤还是能够创作出《捣素赋》的。缺乏确凿的证据,同样不能将它视为一篇伪作,当然也不能排除它与《怨歌行》都在不同程度上经过了后人的润色和修饰,但班婕妤的“原创”性著作权是不宜轻易被否定的。
《捣素赋》、《怨歌行》与《自悼赋》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自足的书写世界,班婕妤曾受的宠遇,遭变故后的忧伤、悲戚和自我宽慰,都被淋漓尽致地传达了出来,它们必然是班婕妤笔下且收在集子里的作品。缺失了任何之一要素,都有损于班婕妤文学形象的建构及其影响力的传播,古人虽有疑但也不会“糊涂”到就着伪作来谈论她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