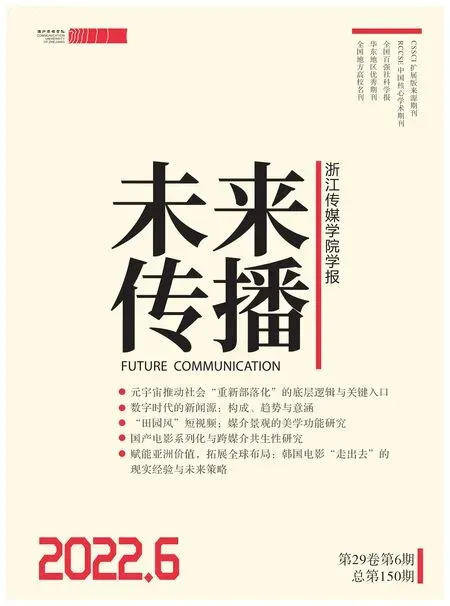理解泛媒介:基于三个层度媒介观的比较研究
要欣委,李明伟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广东深圳518000)
一、引 言
在学术研究中有一个现象:每个研究领域中最为关键的学术概念既是这个领域研究的生发点,同时又是最具争议的焦点。以文化研究来说,雷蒙·威廉斯曾指出:“英文里有两三个比较复杂的词,culture就是其中的一个。”[1]据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统计,仅1871年至1951年短短80年的时间,关于“文化”就有164种不同的界定。在传播学研究中,“媒介”无疑也是这样一个重要却又含混的概念。据威廉斯考证,medium 源自拉丁文 medium——意指中间。从16世纪末起,这个词在英文中被广泛使用。最迟从17 世纪初起,这个词具有“中介机构”或“中间物”的意涵。19世纪中叶,media这个复数名词开始被使用。之后随着传播通信的日益重要,media被广泛使用。与此同时,一些相关词汇随之出现:mass media(大众媒体)、media people(媒体人)、media agencies(媒体机构)、media studies(媒体研究)。[1](345-346)
通过对媒介概念的溯源,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媒介”是被当作方位词使用的,意指中间。而后开始有了名词的词性,并有了较为宽泛的所指。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传播手段的变革以及大众传媒的勃兴,媒介一词所指涉的范围开始专门化、窄化,越来越多地指代传递信息与维系社会联系的工具。media与communication一词的联系愈发紧密,“communications常用来指涉(这些)媒介”[1](119)。媒介与传播产生了一定的相互对应的关系,逐步被简化为信息传播的工具。由此我们也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什么之后提到媒介,它被更多地界定为传播之技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传播学学科开始成建制地发展,传播学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相继崛起。两种研究范式在媒介是否中立这一问题上针锋相对,但在对媒介是什么的认识上却是较为一致的:他们认为媒介即大众传播工具。媒介所指的窄化在学术研究层面得到了确认。
1964年,《理解媒介》一书出版并很快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该书的作者麦克卢汉关注很多此前并不被认为是媒介的事物,如轮子、武器、住宅、货币,他高举的泛媒介论大旗开始在传播学领域猎猎作响。麦克卢汉并不是最早对媒介持宽泛理解的学者,但毋庸讳言,他是最早将泛媒介思想体系化和发扬光大的人。循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将泛媒介作为另一条理解媒介的思路。2020年,彼得斯的《奇云:媒介即存有》一书译入中国,在学界引起轰动。在媒介观的“泛”上,他比麦克卢汉走得更远。他的媒介概念无所不包,有海洋、火、天空、陆地、坟墓甚至地球等。如此宽泛的媒介理解将泛媒介观推向了高潮,也为新时代认识媒介提供了新的思路。[2]今天,当我们更加自觉追求传播学的理论化和学科身份的时候,“媒介”作为传播学的基础与核心概念究竟该如何理解,就成了一个必须正视和严肃讨论的前提性问题。在学术研究中,起点往往决定终点,对媒介概念范围的划定这一基本立足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随之而来的分析路径。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依据媒介范畴的大小划分了三个层度的媒介观,在此基础上试图探究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各个层度媒介观大致的边界为何?其二,不同层度媒介观背后的生成逻辑是怎样的?其三,应当如何认识传播学研究中媒介范畴泛化的趋势?
二、不断延展的媒介:三个层度媒介观的对比
(一)媒介即大众传播工具
根据罗杰斯的说法,传播学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欧洲。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对传播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真正使传播学成建制发展的人是威尔伯·施拉姆。正如罗杰斯高度评价的那样:“施拉姆是传播学的奠基人,没有他对这个领域的贡献,就不会有传播学这样一个领域了。”[3]在《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一书中,施拉姆认为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勒温是传播学的先驱:“他们在一个被称为‘传播研究’的学术领域存在之前,进入进而创造了这个领域。”[4]但施拉姆的这种说法有其主观色彩和个人偏好,他关于传播奠基人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定量研究”[5]。与其说这四个人的研究确定了传播学研究领域,不如说他们的研究形成了一种统一的传播学研究范式:经验主义范式。
经验主义研究中的媒介范畴很小,被默认为传递信息的工具和渠道。施拉姆曾对媒介的概念做过以下说明:“媒介的概念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大众传播媒介出现之前就有了传媒。无疑,在大众媒介出现之前,传播信息的手段都应该纳入传媒的范畴。”[6]在施拉姆看来,媒介是指传播过程中一切发送、运输、传递、接收的介质和工具。在具体研究中,经验学派所指的媒介范围就变得更小了,更多的是指大众传播媒介。拉斯韦尔就曾将传播的结构划分为五个部分:谁(who)、说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拉斯韦尔将针对“通过什么渠道”进行的研究称为媒介研究,当提到媒介是什么时,拉斯韦尔将其界定为“广播、报纸、电影等传播渠道”[7]。
批判学派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进入兴盛期。在批判学派那里,媒介被视为信息传输和政治与商业意识形态的工具,它们既非中立,也无自主,而是受到政治、经济力量深入而强大的宰制与操纵。“对于批判学者来说,关键的问题是谁拥有和控制大众媒介。”[3](124)媒介仍被狭义地等同为大众传播媒介。如本雅明主要关注电影等媒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关注广播系统、报刊专栏以及后来被他们称为文化工业的电影和电视肥皂剧。霍尔等人的文化研究聚焦点也是大众传播媒介,他们认为大众传媒催生了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总的来说,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对媒介范围的认知有一定的共识,媒介即大众传播工具。
(二)媒介是人的延伸物
在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眼中,媒介是局限于当代的,而非历史的;是站在信息与内容立场的,而非其他的。媒介本身是不需要被理解的,它近在眼前,就是传播的工具。真正振臂疾呼要理解媒介的人,是麦克卢汉。施拉姆即使言辞透着傲慢勉强但也不得不承认:“在传播研究的发展史上,他(麦克卢汉)起过重要的作用。即使从肤浅的层次看,‘媒介’一词的走红,麦克卢汉也功莫大焉。”[6](126)麦克卢汉正是抓住了媒介本身这个立足点,与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
麦克卢汉的这一研究路径深受伊尼斯的影响,后者将媒介当作权力组织和社会的轴心来探索人类历史演化背后的机制。在1951年致伊尼斯的信中,麦克卢汉就表达了对这种研究取向的赞同与兴趣:“技术形式本身必然是有效的,形式本身的效力远远超过它提供的功能。沿着这样的研究路径,有可能组织起一个学派。”[8]与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相比,伊尼斯并不只着眼于大众传媒,他将视野放在了滚滚的历史长河中。在他那里,石头、莎草纸、泥版、诗歌、戏剧等都是媒介。更有甚者,他将货币、金字塔、高楼等也都视为媒介。(1)伊尼斯的媒介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以库利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继承。与芝加哥学派一样,伊尼斯的媒介观虽泛但未成体系,且伊尼斯的媒介也更多地关注“能附着信息(意义)的物质”,也未对“泛”的合理性相加论述。在这些方面,麦克卢汉比他们走得更远。这样宽泛的媒介观在麦克卢汉那里得到了发扬。
伊尼斯更多的是从纵向的历史维度在延展传播学研究中的媒介概念,麦克卢汉则从横向“类”的维度来拓宽媒介的范畴。如果说麦克卢汉是激进的革命者,媒介就是他手里抓着的“枪杆子”。正是对媒介本身的关注,使得媒介概念在他这里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如《理解媒介》一书的副标题“论人的延伸”所揭示的那样,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物。根据这一观点,麦克卢汉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泛媒介”体系。不同的媒介是人个别身体器官的延伸,如“箭是手和臂的延伸,来复枪是眼睛和牙齿的延伸。城市和海船是我们大家肌肤城堡的延伸,正如衣服是我们个人肌肤的延伸一样”[9]。麦克卢汉总结道:“我所谓的媒介是广义的媒介,包括任何使人体和感官延伸的技术。从衣服到电脑。”[9](319)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技术并不只停留在“实体物”的层面,还包括人的思想、制度等“抽象物”。1979年,在一场以《人与媒介》为主题的讲演中,麦克卢汉如是说:“人的一切人工制品,包括语言、法律、思想、假设、工具、衣服、电脑等,都是人体的延伸。”[10]总结至此,麦克卢汉泛媒介观的边界大致就比较清晰了——包括实体物与抽象物在内的人的一切延伸物。如此宽泛的媒介理解几乎涵盖了一切的人造物,有形的和无形的。麦克卢汉的泛媒介观打破了两种桎梏:一是媒介只包含信息传播技术的观点,将其他技术也纳入了媒介体系;二是媒介必然是有形物体的观点,将思想等无形物体也纳入其中。
(三)媒介是“自然”与“人工”的结合
麦克卢汉之后,各种媒介理论涌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法国媒介学家德布雷的媒介学研究和近年来发轫于北欧的媒介化研究。和麦克卢汉一样,这些研究都秉持着泛媒介观,但各有侧重偏向。德布雷的媒介学研究强调历史范畴文化的传承与延续。他所指的媒介是在特定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象征传递和流通手段的集合,包含自然语言、身体器官、符号的物质载体、技术手段、组织机构等。[11]以夏瓦、库尔德利为代表的媒介化研究侧重将媒介视为制度性的建构社会的一种力量。库尔德利曾对媒介做出以下定义:“我所谓的媒介包括一切制度化的、用于传播符号内容的结构、格式、形式和界面,这样的界定比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的意义宽泛得多。”[12]如果粗线条地划分,媒介学和媒介化研究中的媒介范畴与麦克卢汉的媒介范畴大致都可划归为一个层度:即比大众传播媒介宽泛很多,但并未超出人造物的范围。
彼得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在分析媒介时将其视为“自然”和“人工”的结合。[13]这里的“人工”与麦克卢汉“人的延伸物”的范围大致相当,既包含各种有形的人造物,也包含数学、性、白日梦等无形的“物”。不仅如此,彼得斯将“自然物”也纳入媒介的范畴。在此之前,“自然”常常站在媒介(技术)的对立面,是被技术改造的对象。在原始社会,人没有像猛兽一样的尖牙利爪和惊人速度,只能依靠媒介(技术)延伸强化自己的力量来应对残酷的自然环境。此后,人凭借技术变革对自然进行改造,这些改造对自然体系的改变极为巨大,以至于人类现在不得不将某些地域隔离出来将其称为自然。[13](1)在麦克卢汉那里,“自然”与“媒介”界限分明,自然环境和技术环境是彼此独立的两个系统。“技术铺就的环境会把地球包裹起来,电力信息环境会取代‘自然’的老环境,占据优先地位。”[8](365)技术环境的蔓延随之引发的就是自然环境的消退。
麦克卢汉认为每一种媒介都构成一种环境,故而有媒介即环境的说法。彼得斯在很大程度上接着麦克卢汉在讲:“我们以前说‘媒介即环境’,但是现在反着说也是对的:环境即媒介。”[13](3)“环境即媒介”中的环境既包含技术环境,也包含自然环境,媒介是“自然”和“人工”的统合。彼得斯呼吁我们在思考媒介时不应将“自然”排除在外,“应当将媒介看作一种友好的环境,它能为各种生命形式提供栖居之地”[13](3)。站在这样的视角,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彼得斯的媒介概念为何无所不包了。他采取了一种综合立场,将被麦克卢汉排除在外的“自然”也纳入了媒介的范畴,这无疑又进一步极大地拓宽了媒介概念的边界。
三、三个层度媒介观的生成逻辑
(一)内容第一: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研究中“边缘”的媒介
在经验学派之前,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已经觉察到媒介的重要作用,围绕传播和媒介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普遍对媒介持有一种比较宽泛的理解,如帕克就将媒介定义为“任何可能征服空间和时间的成就,包括面部表情、态度和手势、语调、文字、印刷、铁路、电报、电话等”[14]。由此可见,帕克并不单纯地从信息传递的角度去思考媒介,他将征服空间的手段如各种交通工具也视为媒介,这样的观点与伊尼斯的基本一致。那么,为什么到了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那里,媒介被窄化为了大众传播工具?这首先要从传播学的主流学派经验学派的哲学基础说起。经验学派的方法论源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哲学,“实证主义信念认为,科学的方法能运用于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以便帮助解决社会问题”[3](134)。因而经验学派自诞生之初就有浓重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倾向。当时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发展迅猛,报纸、收音机等媒介进入千家万户。而当大众传媒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遇时,经验学派成了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被时势造就的“英雄”。
政府极其重视大众媒介的宣传、说服力量,这与经验学派的实用主义一拍即合。经验学派致力于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充分实现军事、经济、政治功能,关注媒介内容、传播效果、民意测验。媒介对于经验学派来说只是信息流通的渠道,当他们看媒介时,看到的其实是媒介的内容。施拉姆就曾对传播研究应当关注媒介本身还是媒介内容有过论述,并借此批驳麦克卢汉:“虽然他(麦克卢汉)强调媒介本身的作用值得赞扬,但研究发现,和媒介传播效果的变异相比,信息传播作用的变异要大得多。”[6](130)大众传媒的强大效果蒙蔽了研究者的双眼,传播学汲汲于效力政府和商业机构,醉心于研究如何通过特定的内容来获得心仪的效果,对媒介的丰富意涵完全无视、无言、无感。
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针锋相对,但他们与经验主义范式的根本分歧点并不在于关注媒介内容还是关注媒介本身。他们认为经验主义的研究是一种在类似培养皿的真空环境中进行的研究,对研究的顶层设计不加考察。媒介固然是一种工具,但绝非是价值中立的工具,而是被权力和资本操控的工具。霍尔尖锐地指出:“经验主义范式的研究是一种‘内容分析’花园里的天真无邪。我们现在分析信息,不是通过明显的‘信息’,而是要分析它的意识形态结构。”[15]由此可见,批判学派视野中的媒介不过只是附着于权力的工具,是相对边缘的,它们很重要但却无力自主,因而是一个了无意义的被动角色。各种意识形态权力对媒介的操控才是研究应该火力全开解蔽祛魅的标靶。
(二)外化与延伸:麦克卢汉以人为原点的媒介本体论
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都把媒介当作一种无意义因而不值得研究的工具性存在。只不过在经验学派那里,媒介是一种中立的信息传播渠道。在批判学派那里,媒介是受意识形态控制的传播工具。媒介本身并非他们研究的重点。在经验学派那里,媒介仅仅是在5W的模型框架中占据一隅,甚至在关注受众和传播效果的研究传统中,媒介是被透明化的,没有存在的必要。[16]麦克卢汉独辟蹊径,强调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信息,传播研究应当关注媒介本身。他化用诗人艾略特的比喻来凸显媒介形式的重要性:“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盗贼用它来涣散看门狗的注意。”[8](207)如此一来,媒介就由之前绝对的边缘走向了中心。麦克卢汉将媒介提升到了本体地位,真正意义上的媒介研究逐渐成形。
与对媒介本身的关注相伴随的是对媒介范畴的拓展。麦克卢汉在思考媒介时摆脱了将其与信息相联系的定势思维,而把媒介视为人与社会演化的动力枢纽。在思考媒介是什么时,麦克卢汉是以人为视角的,他认为一切的媒介都是人自身的外化与延伸。“这样的观点基于技术与‘生物人’内在关系无比坚定的立场,强调‘生物人’和技术的本质关联性:所有的技术都是将‘无意识的原型形式’推向人的意识、社会意识的。”[17]人是一切媒介的原型,是一定意义上的元媒介(meta-media)。如果将麦克卢汉的媒介范畴看作一个圆的话,人就是这个圆的圆心。“凭借这种人与媒介的关联性,麦克卢汉让人以具身关系卷入了媒介的历史”[18],也让媒介以一种无比重要的形式卷入了人类的发展历史。
在思考媒介有何影响时,麦克卢汉站在了媒介的视角,将“媒介本身”作为影响人与社会的动力之源。媒介是人的延伸,“每一种媒介都有偏向,都创造一种环境”[8](360),媒介环境悄无声息地对人产生影响。与此同时,“每一种媒介因为各不相同的物理特性、内容表现与传播特征,而突出不同类型的感官,形成不同特征的文化类型和社会结构”[19]。作为人的延伸物的媒介反过来又影响人和社会结构。正是认识到媒介拥有如此强大的自主力量,麦克卢汉将媒介提升到了本体位置。这样的认识论赋予了媒介无限的活力与可能性,媒介的外延无限扩大。但“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认识又强调人是一切媒介的原点与原型,从而给了媒介范畴一定的限定。以人为原点的媒介本体论正是麦克卢汉泛媒介观内在的生成逻辑。
(三)媒介即存有:彼得斯基于媒介自身逻辑的媒介本体论
在《奇云》一书开头,彼得斯就对麦克卢汉深切致意,对麦克卢汉建基于媒介本体地位的泛媒介观表示赞同,并明确表明自己的媒介研究深为麦克卢汉的精神所鼓舞,受到他的引领。[13](18)除了麦克卢汉以外,彼得斯的媒介思想深受海德格尔和基特勒的影响。在这些学者的基础上,彼得斯试图建构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媒介观。这种媒介观强调一种“深层的生态意识”,以丰富而复杂的方式谈论自然。这样的视角是对由来已久的“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是万事万物的尺度”等观点的批驳,将人置于与其他生命平等的位置。彼得斯认为媒介研究不应害怕偏离以人为中心的视角,“而应当努力承担本体论中的基本角色。媒介并非世界,但我们只有通过媒介才能进入这个世界”[20]。彼得斯将媒介视为各种生命形式与世界发生联系、存有于世的“中间之物”。
与麦克卢汉将人视为媒介的基础和前提不同,彼得斯彻底站在了媒介的立场。将媒介视为一种基础,它是人存在的条件,是人不可或缺的某种帮助。麦克卢汉尽管也无比强调媒介本身,但他在认识媒介为何时,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视角。而彼得斯则将人推出了理解媒介的中心,他认为媒介是一个意义自在体。媒介有其自身的逻辑,不因人而存在,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建基于这种认识的媒介本体论比麦克卢汉的更为彻底,“人”不再是理解媒介的制约因素。这也就决定了他的媒介范畴比麦克卢汉更泛:“媒介是自然元素和人工创造的共同体现。”[13](4)
建立在这样一个整体层度的媒介观,为我们认识媒介和重估媒介的价值提供了机会。彼得斯有意颠覆将媒介视为表达人类意图的载体,他认为媒介非表意,媒介即存有,它为使用者创造生存条件。“如此一来,媒介的概念就从‘讯息’层面拓展到‘栖居’层面。”[13](17)从这样的视角再去看人、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便会一目了然。“人是浮游于多舟之上的生物,技术对人有不可或缺的中心地位。”[13](58)船作为技术物是人在海上的依凭,它使得人涉足大海成为可能,人借助自己的造物知晓和征服自然。也正是由于船的揭示,大海的媒介性开始显现。海是人与船关系背后更为基础的存在,它使得人和船得以浮,得以行动,得以存有于世间。自然是媒介(技术)实践的基础,是媒介(技术)之下更为深层的媒介。如此看来,人—技术—自然是一种共在的关联。当媒介具有“自然”与“人工”的统合视角时,媒介对于人来说建构起了整个世界。人的存有不可能脱离媒介,而媒介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这个物种终会沉没,而自然将继续存在,为新的生命存有提供可能。[13](418)在彼得斯眼中,媒介决定人甚至高于人,他将媒介的价值提高到了一个更为显著的位置。
四、泛媒介观与传播学的理论化发展
(一)媒介所指的泛化与媒介地位的提升
前论表明,传播学研究的路径取向和范式转型与媒介的认知研究逻辑有莫大的关系。如施拉姆所定义的那样:“媒介是插入传播过程的中介,是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6](134-135)依这样的认识逻辑,信息与媒介的关系很分明:信息是匣中宝珠,媒介只是盛放它的木盒;不围绕信息去认识媒介,势必是一种买椟还珠、本末倒置的媒介观。后来,这就成了主流传播学研究的支配性共识。
麦克卢汉摒弃了以信息为中心的媒介观,将媒介置于本体位置,大大提升了媒介的地位。在他那里,泛媒介的观念得到了发扬,一切人的延伸物、一切的技术都是媒介。麦克卢汉的媒介观仍是一种“效果观”。不过不同于经验学派关注媒介内容引发的短期的、直接的效果,麦克卢汉关注的是媒介自身作为社会变革的动因在长时间、大范围内所能引发的更为深远的效果。从当时来看,这样的创见为传播学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鲜活的动力。以致有学者评价:“迄今为止,传播学历史上思想贡献最大的是麦克卢汉。他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用一种怪异的声音梦呓般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惊人之论,让传播学为之一新。”[19](132)但麦克卢汉及整个媒介环境学派更偏重于媒介环境的深远历史意义和社会影响的效果研究,对媒介本身尽管有卓尔不群的俯察深思,但理论的生长性尚显不足。其次,以人为中心思考媒介在当时来看砸碎了“信息中心论”的枷锁,但现在看来反倒为更有新意地思考媒介设限。麦克卢汉之后,媒介的想象力陷入了瓶颈。
彼得斯适时出现,试图以媒介为眼来审视人类的整个生存境况。他满怀生态意识,尝试着将“生命的存有”推入理解媒介的中心。将媒介理解为各种生命形式创造生存的条件,而人类不过是万千生命中的一员,“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1]。无疑,彼得斯把媒介理解为一种可供性、一种可能。这是一种“关系”的入射角,媒介是生命与世界发生联系、存有于世的中间之物。从这个维度讲,媒介即生命,“是一种基础设施和生命形态,是我们行动和存有的栖居之地和凭借之地。媒介具有了生态的、伦理的和存有层面的意义”[22]。由此,媒介自然不是“人的延伸物”这一范畴所能涵盖的,必须加入“自然”的维度。从彼得斯的角度去看媒介,它的作用就远比“效果观”更基础、更深层、更重要。彼得斯真正立足于媒介自身的内在力量,将媒介作为一种思维、规律和视角,并把媒介的地位抬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媒介即大众传播工具,到媒介是人的延伸物,再到媒介是“自然”与“人工”的结合,媒介的所指不断扩大。其背后是视角转换的所得,即从以信息为中心思考媒介,到以人为中心思考媒介,再到以生命存有为中心思考媒介。不同的视角将媒介放在了不同的高度,从最早的信息第一,媒介处于边缘、从属地位,到麦克卢汉以人为中心的媒介本体论,再到彼得斯基于媒介自身逻辑的媒介本体论。媒介范畴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是媒介地位不断被抬高的过程。这一方面是因为媒介已经全方位地渗入人类的生产生活,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无所不在又兀然而立,让我们无从摆脱、无法忽视。另一方面也是来自于传播学科反思解蔽、正本立身的理论突破——泛媒介论正是这种理论突破的主力前锋。
(二)日渐生发:“泛媒介观”之于传播学研究
彼得斯曾指出,传播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有其固有的内在矛盾:“这是一个宣称拥抱所有生活中基础事物的领域,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十分狭隘,充满断裂并不断边缘化。”[20]偏安于以信息为中心的研究,把传播学带入了实用型研究的羊肠小道。将媒介视为完全受意识形态操控的组织,也限制了传播学的想象力。总而言之,将媒介的意涵窄化为大众传播媒介无疑是一种“技术短视”,这样的研究既无法“瞻前”也难以“顾后”,同时更无力放眼“四周”,这就湮灭了传播学研究开拓思路的很多可能。
从伊尼斯、麦克卢汉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转向媒介本身。正如黄旦所言:“应将媒介确定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入射角,这不仅仅是为了纠正传播研究重内容、重效果而忽视媒介的偏向,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从媒介入手最能抓住传播学研究的根本,显示其独有的光彩。”[23]何为传播学研究的根本及其独有的光彩?其实,传播学自诞生之日起,像是其他学科旁生的枝蔓,没有自己的理论根基,无法抓住“土壤”汲取养分。而寻找传播学研究的根本其实就是寻找一颗种子,它有生发的力量,能形成传播学学科理论基础和内在的知识体系。
“媒介”是实现这一目标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媒介为入射角,能更好地窥探“人”。如福柯所言:“人是这样一个生物,即他从他所完全属于的并且他的整个存在被据以贯穿的生命内部构成了他赖以生活的种种表象……”[24]这句话读来晦涩,但含义却十分清晰:人的存在十分复杂,他存有于世间就必须与诸多其他要素相互纠缠,这些是他们生存的背景。基于这样的复杂性,不同的学科都以独特的视角探寻人何以为人的种种可能,而媒介应当是传播学追问这一问题非常合适的视角。麦克卢汉对此的回答是:我们塑造了工具(媒介),此后工具(媒介)又塑造了我们。[9](17)彼得斯则认为技术固然对人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但也不应忽视其背后的自然因素。他主张采取一种统合视角,从更为基础、深层的角度认识媒介,进而更好地锚定人的生存状态。泛媒介观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沿着这条路径,或许能实现彼得斯对传播学研究的美好畅想:通过宽泛的媒介理解,必将“扩大媒介研究领域,拓宽研究的跨学科视野。研究者将不再强调人文与科学领域间的边界,并采用任何有益的形式探寻知识,传播研究应当成为人类思想跨学科重组的先驱”。[20]
近些年国内已有一些以媒介为视角而展开的别样研究。黄旦一反传统报刊史研究的媒介工具立场,力主以媒介为切入点,以媒介实践为叙述进路,开拓了报刊(媒介)史研究的新范式。新报刊史关注媒介的自主性作用以及在此作用下人类的社会实践,其视野中的媒介是历史的,包含不同时期不同类型。[25]这种研究主张在学界获得广泛响应,有学者将表达异见的奏折视为媒介,认为这一特殊的政治媒介作为节点建构起了一个贯通的民间传播网络,该媒介所形塑的政治事件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管窥媒介中的帝国政治文明的窗口。[26]有学者关注旗帜、警示灯、钟楼、电话等火警媒介相遇所形成的动态、开放、并置,但不均质的媒介矩阵对于救火行动这一社会实践的影响。在主导媒介的变更中,救火从城市大众的公共体验,逐步变成了救火机构自身的专业事务。[27]亦有学者将轮船视为地区、国家信息转递之媒介与信息融通、贸易往来之基础设施,它与报纸一起使得“海上网络”成为可能。[28]在中国数千年未曾断绝的文明历程中,还有浩如繁星的媒介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彼得斯热情洋溢地将中国称为“媒介王国”,历法、钟、香、墙垣、灌溉水利控制、防火手段、天宫图等媒介,都是人之存有和文明存续重要的中间之物,都值得我们潜心研究。[13](1-2)
重思媒介不仅为“回眸过去”的研究展开画卷,也为我们审视当下、展望未来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孙玮通过对传播内涵及意义的梳理,对何以能将城市视为媒介做出深度阐释。[29]胡翼青亦认为城市是真实与想象地理的彼此叠加,将城市视为一种“容器型”媒介,可以拓宽对“城市”和“传播”两个维度的理解,进而成为城市传播研究的第三种范式。[30]在媒介已经遍在如自然的当下,宽泛的媒介视角能更好地解释现代人的媒介化生存状态。以上管窥,“重思媒介”已经成为传播学研究重要的生发力量。
(三) 反思与讨论
泛媒介论不认为一切都是媒介。它只是突破了传统的媒介认知,但并没有把媒介泛化为世间所有。至少,泛媒介论所谓的媒介不包含媒介传播的内容,他们也不会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爱恨情仇是媒介。那种“一切都是媒介无异于取消媒介,进而取消媒介学”[31]的批评,是篡改了靶子以便轻而易举来驳倒。而且,一切都是媒介无异于取消媒介,单就形式逻辑而言也不成立。唯物主义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物质的,这就取消物质了吗?
当然,泛媒介论只是认识媒介的一种层度,它照亮的是传播的宏观的社会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传播学哲学化的可选路径。工具论层度的媒介认识,放大了特定传播内容及其可测量的传播效果,有利于社会为达成某种目的而进行行为干预。泛媒介论在更开放的视野中审视媒介,但并不把媒介视为整齐划一的铁板一块。他们更关注媒介环境的总体结构以及位居其中的主导媒介。例如彼得斯在诸多媒介中更为关注基础设施型媒介,他认为这类媒介高度系统化,能跨越时空将人与组织相联系,对人类的存有而言具有更为基础和显著的地位。再者,泛媒介观凸显了媒介在人类历史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但这不等于否认社会历史演化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泛媒介论不是单一、线性、机械的媒介决定论。
媒介为何?这近乎是传播学研究当中的“元问”和“天问”。不同视角与层度的认知,导向了旨趣各异的研究路径和范式。泛媒介论为传播学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开阔的研究视野和理论生长的空间,是传播学理论化最可进取的方向,国内传播学界于此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也许更重要的是,泛媒介论大有可能是传播学解决身份危机的突破口,传播学假此有望自立于社会科学的丛林,但这必得仰赖在这一道路上孜孜不辍的理论突破和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