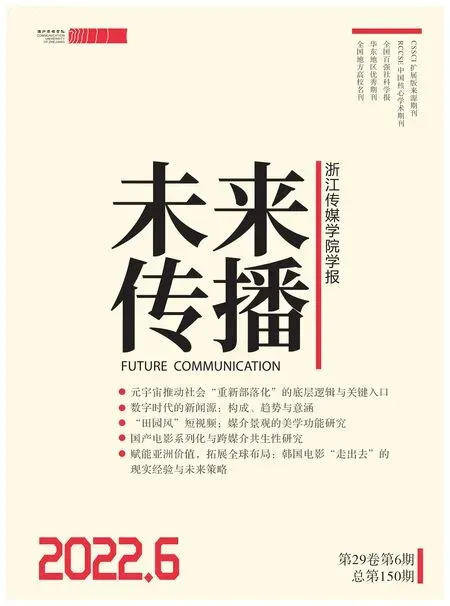“精英”与“反精英”:翁贝托·埃科作品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李 娟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2016年2月19日,翁贝托·埃科(1)意大利总理伦齐(Matteo Renzi)悼念其“作为欧洲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将深刻认知历史的智慧与推测未来的强大能力完美结合”,纽约时报以“最畅销的学者,驾驭两个世界”为题,追溯了埃科穿梭于小说创作与学术研究的一生。逝世的消息自意大利传至世界各地,引起广泛关注。与埃科有着数次交集的中国媒体界推出众多报道,从各个角度纪念与评述这位以广博著称的当代学术界巨擘(2)如凤凰网纪念专题“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澎湃新闻评论“埃科去世:后现代主义跟着它最后一位旗帜性人物,走到了终结”,东方早报评论“意大利作家埃科:人是在智慧的垃圾中成长”等。,之后再度推出埃科逝世一周年纪念专题(3)界面文化“我们为什么在乎这位意大利知识分子”, 澎湃新闻“埃科去世一周年,他的最后一本小说‘最接近我们’”。。在出版界,埃科的去世进一步激发了其中文译作的结集推出与主题阅读活动的开展(4)仅统计自埃科去世后至2020年7月的四年间,上海译文出版社新出或再版埃科作品15种。,相关书评、报道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中散见不绝,体现了埃科在中文出版界和阅读界广泛的接受度。
在汉语学界,自1981年王祖望先生的译文“符号学的起源与发展”(5)T.谢拜奥克:“符号学的起源与发展”,载《国外社会科学》,王祖望译,1981(5):61-65。对埃科作了首次介绍以来,埃科研究持续至今将近40年,成果丰硕,涵盖其小说作品、文学思想、诠释批评和符号学理论。然而,从出版译介与传播接受的角度来开展的埃科研究则极为鲜见(6)仅有张媛的硕士论文《翁贝托·埃科的叙事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北京外国语大学,2018),该文以比较文学研究视角切入,以埃科的叙事作品为研究对象,对其在中国的译介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其在中国学界的接受作出分析。。本文从跨文化阐释的视角出发,从传播接受的角度,拓宽中国学界的埃科研究,探讨中国当代的知识界和媒体界如何在自身的知识视野和文化土壤中理解与传播埃科的作品,并与之形成跨文化互动。
一、视角的提出:传播与阐释
在当前的学科范式下,作家作品大多仍囿于文学研究的范围,对于埃科这样的当代学院派精英作家尤为如此。然而,文学作品从写作、出版,最后抵达阅读环节,这一系列过程中涉及的经济考量、文化观念与媒体运作等社会化关系同样重要。对文学传播的场域、语境和文化符号系统的强调,为埃科作品在中国的跨文化旅行提供了另一种阐释的面向,其基础是基于中国文化土壤的阐释与传播。研究该题的最终指向是理解由媒体界、出版界、学术界和读者共构的阅读行为,呈现了当代中国怎样的精神气质与文化习惯。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翻译作品的跨文化特质更集中提出了阐释与传播的问题。翻译使作品在异质文化中产生持续的生命,翻译本身就是扩展至文化层面的跨文化阐释。作为起点的译介出版,其选择机制不仅关乎作品的文学价值,还与读者的选择、市场的流通和本国的智识氛围有关。译本的选择自一开始往往伴随着各方考量,译本的传播也并非单向的压倒性接受,而是在地话语与源地话语之间的双向选择,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阐释体系。这个交叉、共享的地带,正是文学研究可以进一步发问的所在。因而,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对文学阐释研究可以形成有益的扩充。系统地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第一人、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曾指出:“文化隐藏的现象远远超过其揭示的现象。奇怪的是,它隐藏的东西对文化的参与者最为有效。真正的难题不是理解外域文化,而是理解自己的文化。研究异域文化所能得到的不过是象征性的理解,研究的终极目的是更好地了解自己文化系统的运行机制。”[1]
这提示我们去关注文化与传播的同构关系,它表现为广泛的文化价值、传统和表征系统对传播运作及其意义建构过程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跨文化的语境关联中,还包括文化生产与传播内容的形式要素、观念和文化根源。在对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思想的创造性发挥中,美国文化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把传播看作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其典型的情形是:对从人类学角度看传播的人来说,传播是仪式和神话,对那些从文学批评和历史角度涉及传播的人来说,传播就是艺术和文学”[2]。
当代阅读研究也在传统文学批评的视野之外,探讨在社会场域和文学场域里,出版方、大众传媒、学术共同体与“普通读者”等不同话语方的介入与互动,共同构成了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图景。其中,阅读史领域的两位学者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与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研究对于文学研究多有借鉴价值。在他们看来,费夫贺(Lucien Febvre)与马尔坦 (Henri-Jean Martin)等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虽多有建树,但对技术层面和物质层面的计量分析并不足以完成对阅读的解释。“谁在读”“为什么读”和“如何读”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作为阐释者的读者身份仍然模糊。
在夏蒂埃看来,需要追问的是“当一位读者面对一个文本时,他如何构造其中的含义,他如何把该文本变为自己的东西”。这是由于“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一位读者总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这一共同体与他分享着与书写文化有关的同样的基本关系”[3]。受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启发,欧洲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提出了书籍的“交流循环”(communication circuit)模式,作者、读者与出版者在该模式中建立互动关系,借此检查文本在社会中扮演角色的手段。在其意趣盎然的《屠猫记》中,达恩顿试图运用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方法来探讨“心灵史”,关注阅读不仅在于研究人们读什么,还包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情感”。[4]不难看出,读者反应批评和接受理论对于阅读史研究的影响,读者逐渐被视作历史的或社会的建构,这促使学者转向阅读的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也为文学的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面向和社会学维度。对此,达恩顿指出:“文学理论包裹在一大堆令人看了眼晕的名词里,但是把它们作为整体来纵观,我们会找到一些文学批评家和图书史家共同关心的问题。”[5]
在跨文化传播视角和当代阅读研究的跨学科视野中,本文从传播与接受两个维度,展开对埃科作品的研究,涉及:(1)媒介中的埃科,包括埃科作品在国内的译介出版,大众媒体对其人其作的报道及形象建构;(2)阅读中的埃科,分别从学院派研究与“普通读者”的理解两方面展开。这些内容并非彼此独立存在,而是相互渗透和影响,是置身于中国当代文化思想土壤中对异质文化的跨文化阐发与吸纳。本文试图解决在当代中国的接受视野和阅读期待中,埃科的哪些思想是重要的,以及在中国的知识界催生或强化了哪些气质与内容的问题。这既在文学阐释的理论视域中,亦在跨文化的对视交流里,让我们有机会瞥见当代知识界的心灵和心态的一隅。
二、媒介中的埃科:形象塑造与价值实现
在汉语出版界(此处仅限于中国大陆),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打造“翁贝托·埃科作品系列”之前,已断断续续有若干埃科的作品出版。最早的可溯至重庆出版社的《玫瑰之名》(1987),该版本为多人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埃科的《符号学理论》,该两种书目前除了图书馆有收录外,图书市场已难觅其踪影。其后,作家出版社推出埃科的三部小说,分别为《玫瑰的名字》(2001)、《昨日之岛》(2001)、《傅科摆》(2003),采用的皆为台湾地区译本,是国内早期埃科迷较多接触到的版本。新星出版社译介了埃科早期的先锋派理论作品《开放的作品》(2005)与随笔集《误读》(2006)、《带着鲑鱼去旅行》(2009)(7)其中《带着鲑鱼去旅行》另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两种版本。,在虚构小说之外,进一步呈现了埃科作品的多重面向。需要注意的是,此三种作品皆为三辉图书公司策划出版,该公司长期致力于人文社科类精品小众图书的引进出版,尤为关注欧美思想界具有重大影响力但在国内鲜为知晓的当代知识分子,包括翁贝托·埃科、尼尔·波兹曼、安·兰德、托尼·朱特、马克·里拉、普利莫·莱维等重要作者,埃科是其较早策划出版的作者,可见中国的出版者对埃科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位。
三联书店聚焦于埃科的小说批评和诠释领域,推出《悠游小说林》(2005)和《诠释与过度诠释》(2005)两种,该段时期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有《符号学与语言哲学》(2006),为国内读者了解埃科的符号学思想提供了关键作品。此外,中央编译出版社则关注了埃科的美学史著作《美的历史》(2007)、《丑的历史》(2010)。至此,包括其他零星的译介作品,埃科的写作在国内图书出版界已得到较为完整的呈现,涵盖小说、先锋派理论、符号学、诠释学和公共随笔创作等主要门类。
自2007年开始,上海译文出版社开始系统性地译介埃科的作品,结合埃科访华与媒体热点,有意识地将其打造为出版社的重要品牌。在笔者对该社“埃科作品系列”责任编辑的访谈中,对方提到译文社从2004年开始策划埃科作品。其考量在于,在国际上埃科既是符号学、哲学专业领域的重量级学者,又是受到大众欢迎的小说家、评论家,是欧洲家喻户晓的公共知识分子,享有极高声誉,但在国内只有零散的作品出版,且采用的是台湾地区自英文转译的版本。全方面的作者定位是译文社在策划选题初期就力求做到的,其第一份文案里对埃科的描述就是“文艺复兴人”“半神式的人物”。因其身份多样,创作类型多样,而且每个类型都达到相当的高度,自一开始,译文社便已有在小说之外,出版埃科的随笔、文论、美学、符号学专著的思路。(8)本论文中涉及上海译文出版社“埃科作品系列”的出版策划和销售等相关材料,均来自笔者对该系列编辑的访谈。两位被访人较为低调,不希望在此透露身份信息,特此说明。
译文社出版埃科的第一部作品并非最负盛名的《玫瑰的名字》,而是《波多里诺》(2007)。这一方面由于《波多里诺》在当时是埃科的最新小说,策划方认为其从内容的可读性、新鲜感来说是不错的首发选择。另一方面,恰逢埃科有访华行程,出版社邀请他来上海做了新书首发活动,其时在主流媒体的书讯报道、专题,书评人的评论以及读者讨论会等方面发力推介,取得良好的效果。埃科的作品并非易读品,但依旧取得不俗的销售业绩,在装帧上亦有平装、精装、纪念版等多种形式,成为译文社持续维护的品牌。以《玫瑰的名字》为例,该作品在中国大陆共有三种版本,译文社版自2010年初版以来,一直持续加印,至2020年共有十几个印次,过十万册。(9)该系列编辑认为,《玫瑰的名字》之所以销售最佳,一方面在于其书名能够给人想象空间,另一方面则是有同名改编电影加持。
媒体对埃科及其作品的报道一方面呼应了出版社的策划定位,另一方面也从大众文化传播的视角建构着埃科的精英知识分子形象。从报道的数量与质量来看,中国的媒体界有两次埃科热潮:第一次是2007年埃科访华,应译文社之邀在上海做新书首发活动;第二次则是2016年埃科去世,澎湃新闻、《东方早报》《经济观察报》等众多重量级媒体刊文纪念,其中纪念文章《安伯托·艾柯:悠闲的愤怒和批评的姿势》(《经济观察报》,2016年2月20日)的阅读量达到13.2万。而界面新闻在埃科逝世一周年后继续推出专题文章,《我们为什么在乎这位意大利知识分子?》和《“行走的图书馆已闭馆”,来读下他的最后作品〈试刊号〉》两篇文章的阅读量分别达到17.3万和14.5万。对于一位并非通俗易懂的学院派作家而言,媒体对埃科的关注是引人瞩目的。
媒体对埃科的报道视角有较强的连续性和整体感,其主题可概括为“精英与顽童”。媒体对埃科的精英形象塑造首先是通过其博学来强调的,这一点主要体现为其涉猎领域的广泛与小说作品中海量的知识,尤其是为中国读者所不了解的欧洲中世纪。“埃科是罕见通才,可以在不同文化领域间自如跳跃。他博览群书且记忆力超群,私人藏书达5万册之多”[6],“集小说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评论家、符号学家等多种身份而享有‘多面大师’美誉”[7],“最后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作家”[8],“他理应被归类为本世纪早已式微的知识贵族中的一员:一个只有在类似18世纪的时代,从斯宾诺莎、笛卡尔和康德之类的博雅之士身上才得窥其丰采的人物”[9],“在学科与学科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学院与社会之间游刃有余地纵横穿梭”[10]。这与出版社自策划之始对埃科作为“文艺复兴人”的定位保持了共构性,也可看出在埃科作品以及埃科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图景中,出版方与大众媒体协同创造了媒介场域。
对埃科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强调是其精英形象绘制的另一个层面。无论是三辉图书公司着重于埃科系列作品中的公共写作,还是其后上海译文出版社进一步译介出版其随笔集《树敌》(2016)、《康德与鸭嘴兽》(2019),媒体界都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重要特质。“在他的观念里,一位终其一生都在重复海德格尔理论的哲学教授并不能算是一名知识分子,因为批判性创造,即批判我们现今所做之事或创造出更好的做事方法,是智力功能的唯一标志”[9]。这种对知识分子关注现实境况、发挥批判能力的素质的强调,亦体现在媒体对其小说作品的解读中。
更让媒体感兴趣的是埃科的“顽童”气质,这提供了一种对“精英”的抵消,暗示了大众传媒的合理身份。界面新闻在引述埃科回答《卫报》采访时谈及“我不是原教旨主义者,非要说荷马和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之间毫无区别,但是米老鼠和日本俳句可以具有同样的意义”,指出其“能够在高端文化和通俗文化两个看似互不兼容的领域自如施展才华,显然令埃科获得比同辈更加丰富的生存经验”[9]。这一方面与埃科本人的媒体从业经历有关,另一方面源于埃科长年涉足媒体专栏写作,对大众传媒多有研究,其《开放的作品》(1962)、《启示录派与综合派》(1964)、《詹姆斯·邦德——故事的结合方法》(1965)等论著或论文写作,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现代主义经典与007系列故事放在同等位置上阐述,显示了一种后现代学术对界限与框架的消解。
埃科小说作品的后现代气质,介于通俗性与高级性之间的游离感,亦为媒体提供了充分的阐释空间。无论是早期的《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昨日之岛》,还是后期的《波多里诺》,都有着充分的通俗元素:修道院谋杀案、圣堂武士与暗杀、海难幸存、十字军东征传奇故事等。故事主题对唯一真理的消解及一以贯之的怀疑主义气质被媒体视作为对传统精英立场的质疑。我们看到,从出版社到媒体,关于埃科的形象叙事形成一个稳定的链条:精英与反精英。前者提供了媒介生产的价值,后者以反对的形式为这一形象本身构筑了张力,从而体现了大众传媒需要的“冲突性”。这种形象塑造与价值实现一起,构成了埃科及其作品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场域,该场域内的话语交流还有待另一个重要的角色来共同完成——读者。
三、阅读中的埃科:学院派的阐释与“普通读者”的理解
我们已经看到,阅读接受的维度在文学研究以及书籍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而对埃科的理解与阐释在当代中国的阅读界则呈现为两端:学院派与普通读者群。这两个群体有一定的交叉性,比如,在专业研究期刊上发文的学者也可能会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在传统媒体或网络上撰写相对轻松的评论(10)这里最为突出的是复旦大学的马凌教授,她是国内学界较早关注埃科的学者之一,同时又以malingcat的ID在豆瓣网和媒体上发表数篇有关埃科作品的书评和纪念文字。;同时,学者与普通读者亦会相互引征观点(埃科去世后,各家媒体的纪念专栏都不同程度地采访或邀请学者撰文)。但从各自对埃科作品的切入点来说,学院派的阐释与普通读者的理解仍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与各自所属的媒介场域的性质有关。
在学术界,早在 20世纪80年代,国内已经出现了涉及埃科的小说作品的评论,主要以介绍为主(11)弋边:《世界文坛动态》(《译林》,1984(2)),该文章介绍了《玫魂之名》在美国受到欢迎的情形和小说的故事情节;王斑的《高雅的传奇故事》,(《外国文学》,1986(6)),第一次详细介绍了埃科《玫魂之名》的故事内容;另外钱钟书在其《管锥编增订之二》中两次提到《玫魂之名》。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论者比较具体地分析埃科的小说作品及电影改编(12)李显杰:《因果式线性结构模式:〈玫瑰的名字〉解读》(《电影艺术》,1997(3)),从故事情节、叙事结构、镜头运用等角度对电影《玫魂之名》进行分析,探讨其因果式线性结构模式;袁洪庚:《影射与戏拟:〈玫瑰之名〉中的互为文本性研究》(《外国文学评论》,1997(4)),介绍了当代侦探小说向玄学侦探小说演进的趋势。。进入21世纪,随着埃科小说在汉语学界的译介增多,相关研究也逐渐展开。由于埃科本人在小说诠释批评理论中多有建树,对其小说创作的研究或只是单一的作品解读,更多则结合其诠释学、符号学理论加以比照。如前文提及的马凌,较早地从这两种角度探讨了埃科的小说,其《玫瑰就是玫瑰》(《读书》,2003(2))对《玫魂之名》题目的来源及其内涵做出了分析,《诠释、过度诠释与逻各斯——略论〈玫瑰之名〉的深层主题》(《外国文学评论》,2003(1))则结合埃科的诠释学思想,指出《玫魂之名》是作者借以表现自己诠释学理论的文学载体。
研究埃科小说作品的论文体量庞大,此处特别指出孙慧与李静两位学者,二人的研究皆由博士论文发展为专著,呈现了一定的体系。孙慧的《艾柯文艺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从专题入手,对埃科文艺思想的组织结构、符号学理论、阐释学理论、文学思想及小说创作诸方面作系统微观分析,同时把微观分析的结论置放于宏观社会历史全景中去考证,力图多元化多维度检视其文艺思想。李静从符号学角度解读埃科小说作品,其专著《符号的世界》(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填补了国内该研究角度的空白。
埃科的诠释学理论是中国学界关注的重点,其中于晓峰的著作《诠释的张力》(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是该领域研究的扛鼎之作。该书按照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的发展轨迹和逻辑体系,集中关注并深入分析了埃科诠释理论体系及其在社会文化领域的运用和实践,以埃科的文本诠释理论研究为主题,重点分析埃科的主要学术著作而逐步归纳其诠释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并考察了在其他领域的运用,将埃科的诠释理论推向全面和综合,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此外,朱桃香结合埃科的符号学理论,探讨其读者理论和叙事观,《翁伯托·艾柯读者理论的符号学解读》(《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指出对读者作用的思考和讨论贯穿在埃科的理论专著、散论和小说中,把作者、文本和读者纳入符号学框架之下,演绎其文本符号三角,把读者的解读看作动态的过程,来体现文学的交际特征。《试论艾柯的百科全书叙事观演进》(《学术研究》,2017(5))在迷宫文学谱系中考查了埃科的百科全书叙事观演进,揭示其从20世纪50年代到万维网时代的叙事思想发展轨迹。
在中国学界对埃科的诠释理论的理解与回应中,需要特别引起注意是张江、李遇春、陈定家等学者围绕“强制阐释”的概念所著的系列研讨论文。(13)包括:张江的《关于“强制阐释”的概念解说——致朱立元、王宁、周宪先生》(《文艺研究》,2015(1)),李遇春的《如何“强制”,怎样“阐释”?——重建我们时代的批评伦理》(《文艺争鸣》,2015(2)),陈定家的《文本意图与阐释限度——兼论“强制阐释”的文化症候和逻辑缺失》(《文艺争鸣》,2015(3)),刘剑、赵勇的《强制阐释论与西方文论话语——与“强制阐释”相关的三组概念辨析》(《文艺争鸣》,2015(10))等。以之为契机,2015年7月24日至26日,由《文艺争鸣》杂志社主办的“反思与重构:‘强制阐释论’理论研讨会”在长春召开,来自学界的30余位学者展开讨论。其后,张江的《开放与封闭——阐释的边界讨论之一》(《文艺争鸣》,2017(1))以及对话文章《文本的角色——关于强制阐释的对话》(《文艺研究》,2017(6)),宋伟的《艾柯反对艾柯:阐释的悖论与辩证的阐释》(《文艺争鸣》,2017(11))对“强制阐释”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讨论和阐释。此一系列研讨与写作是中国学者在中西方的阐释学传统下,在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的背景下,以埃科的诠释学理论为源点,展开的理论对话与本土建设。(14)参见《“反思与重构:‘强制阐释论’理论研讨会”综述》,《文艺争鸣》,2015(08)。
学院派对埃科的阅读与接受始终严格限制在学术圈的话语场域中,兴趣集中于埃科小说作品的主题意象、艺术技巧和诠释学理论,以及埃科诸多学术涉猎之间的思想呼应。学者们或以“理解埃科”为要旨,在埃科本人的学术体系、西方诠释学理论以及后现代小说范畴内从各个维度分析埃科,或从中国的阐释学语境出发,探讨其诠释学思想在本土的意义和接受限度,体现了鲜明的对话意识,亦为典型的学术共同体内的话语生产与建构。相对而言,中国学界对埃科的符号学理论、美学思想、大众文化研究等方面缺乏兴趣,尤其缺乏对埃科作为人文学者的整体诗学维度的把握,在借鉴运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上也比较匮乏,因而在整体的研究视野上存在一定缺失。
观察“普通读者”群体对埃科的接受状况,豆瓣网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平台。这一方面是由于埃科的阅读门槛本就比较高(15)上海译文出版社“埃科作品系列”的责任编辑在回答笔者的访谈时认为,埃科的小说作品是面向大众读者,虽然里面可能有历史学、符号学方面的知识,但是抛开这些,读者依然可以享受跌宕起伏、悬念丛生的阅读乐趣;随笔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很有幽默感,也是面向大众读者,不过有些内容从思辨的深度来看,偏向对政治、经济、社会更多关注、更多思考的读者;文论更针对从事写作、从事文艺的读者,或做这方面研究的读者;符号学专著针对的则是符号学专业、语言哲学专业的读者。,另一方面是由于豆瓣网是当前网络平台中具有文艺气质和接受水准的读者群体的主要汇聚地,埃科作品的爱好者在该平台成立了“Umberto Eco小组”(由malingcat创建,小组讨论条目达到13页次),以埃科作品为主题的“豆列”中最为集中且更新及时的包括“我收集的Eco”(更新至2020年6月28日),与“Umberto Eco作品大陆版”(更新至2020年7月9日)。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两条“豆列”的制作者皆为专业的图书编辑,亦为埃科作品的深度爱好者,可见在埃科作品的传播链条中,出版社、责任编辑、非直接相关编辑、学者与普通读者群体在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和学术刊物等媒介平台上,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化的传播图景。
尽管通过豆瓣显示的评价人数不能精确地跟踪到埃科读者的阅读情况,但比较不同作品的标记数量后,我们发现,它与出版社给出的销售状况是吻合的。考虑到存在不同版次,我们采用以各版次中的单次最高评价数和最高评分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埃科的作品中按类别(小说、随笔、美学、文论)区分最受读者欢迎的分别为:小说《玫瑰的名字》、随笔集《带着鲑鱼去旅行》、美学作品《丑的历史》、小说理论《悠游小说林》(见表1)。

表1 埃科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的相关豆瓣数据收集(截至2022年4月15日)
除了对《玫瑰的名字》的共同关注外,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显示了与学术圈中的埃科研究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较少关注埃科的诠释学和符号学理论,更多关注其轻松搞怪的随笔创作以及对正统美学史的消解写作,而《悠游小说林》原本就是埃科的诺顿讲座的合集,既针对学者和学生,也为大多数小说爱好者而发。网络媒介中的写作与学术写作的体例、语言和风格原本就有较大差异,所以比较二者的美学特质并不能看出埃科的不同读者群之间的接受差异,但主题式观察在此有一定的价值。也就是说,学者与普通读者各自从埃科的作品中发掘什么主题,以之作为自己的阅读价值,而这又体现了怎样不同的期待视野。
以《玫瑰的名字》的豆瓣评论为例(此次略去了马凌的几篇书评,因其主要延续了学术写作的风格),读者主要以享受推理乐趣为要旨(如“论玫瑰之不可读”),或是对其中涉及的教派感兴趣(“你被那些教派搞晕了么?”),或是抱怨晦涩难懂(以短评为主)。而在作品集的编辑看来,此书之所以声名远播,除了小说本身的诡谲魅力之外,还在于有同名电影的问世及电影明星肖恩·康纳利(Thomas Sean Connery)的加盟。《带着鲑鱼去旅行》则以其戏仿的轻松风格受到读者喜爱,我们从评论标题如“刻薄是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老顽童翁贝托·艾柯”“褒贬的完美智商指南”“坏笑”等可见一斑。《丑的历史》则颠覆了读者对美学的惯常印象,有“震撼”效果。
这形成了一个同构性的传播与接受空间:埃科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阅读,经由出版社的选题导向,到大众媒介的形象塑造,学术圈的专业阐释以及普通读者的理解,“精英”与“反精英”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这既体现了埃科本人的复杂性,也显示了跨文化接受中,中国本土的智识氛围对于埃科的思想谱系中特定内容的选择性偏好。这提示我们,对埃科作品的接受传播研究,可以从达恩顿指出的“心态”的角度,为我们理解中国当代知识界提供一个有趣的视点。
四、阐释埃科:“高素质畅销书”
从广义上来说,文学研究是一种关于人及其所置身的世界的阐释学,而文学作品的阅读接受更集中体现了阐释学特质,传播维度的加入则在经典的文学阐释学之外为我们拓宽了来自社会以及圈层互动的视野。我们可以将埃科本人的创作和对跨越学院与大众之间沟壑的努力视为其文本传播链条的发端,进而在中国的跨文化旅行中经由出版方对其作品价值、商业属性的综合考量及译介的行为发生,结合大众媒介的报道与形象塑造,最终抵达两种场域的读者群体(有部分交叉),完成了阅读接受。同时,阅读消费的最终实现反作用于出版方,促使其根据销量情况实行加印,出精装版和周年纪念版等出版行为。这是一个动态的群体互动传播的过程,充满了可阐释的空间。
这种阐释首先要与埃科的作品文本所具有的特质有关。埃科本人曾提出“高素质畅销书”的概念用来形容后现代学院派小说,它区别于通俗畅销书,亦和现代主义以来小说远离普通读者的特质有所不同。埃科认为:“(高素质畅销书)包括提供虽然运用博学的影射以及高级艺术风格手法却仍然能够吸引广大群众的故事;换句话说(在最成功的情况下),即是利用非传统的方式混合两种不同构成成分。它吸引了所谓‘畅销书特质’的理论家想要对此提出解释但又倍觉困惑,因为这种作品教人读来津津有味,即便它包含了一些艺术价值,而且牵涉到昔日一度是高级文学专属的特权。”[11]“高素质畅销书”的出现,与接受群体的需要有关,创作者不能低估“通俗”读者群体持续扩大的事实,他们已经厌倦“容易”,而且读来立刻就能获得慰藉满足的文本。另外,往常被认为是“外行”的读者,其实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吸收了当代文学的诸多技巧。以至于当他们面对“高素质畅销书”时,反而不会像某些社会学家那样不知所措。
可以说,“高素质”和“畅销”这两个关键词可以用来形容埃科一生写作的最重要的特点。埃科对综合性的追求,始终贯穿在他对经典价值的维护与对大众文化的民主态度中,正如其去世时《纽约时报》以“最畅销的学者,驾驭两个世界”为题追溯了埃科穿梭于小说创作与学术研究的一生。[12]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釆访时,埃科将自己定位成“一个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大学里教书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在报刊开设专栏议论时事的公共知识分子。
对于知识分子的身份,埃科的态度比较暧昧。一方面,他认为知识分子与普通公民无异,“媒体总是对知识分子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认为知识分子对很多事情是无能为力的,好像这座房子着火了,你手头有一本诗集,但是这个诗集对你来说根本没有用”[13]。 对于自己的公共行为,埃科也否定其知识分子的色彩,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公民的职责。另一方面,在消弭了传统知识分子学的“精神导向”色彩以后,埃科强调了专家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在与米兰教区荣休总主教卡洛·玛利亚·马蒂尼(Carlo Maria Martini)枢机关于当今文化中信徒与非信徒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讨论时,马蒂尼曾担心两人的措辞会引起读者提出“晦涩”的指责,埃科回答道:“是否有人觉得我们过于艰涩并不重要,那些觉得艰涩的人无疑已被大众传播媒体调教成习惯使用简易的词语思考。让那些读者学习深刻的思考吧!因为不论是奥秘本身还是证据,均非显而易见。”[14]
埃科虽取消了知识分子精神的超越性维度,但保留了知识专家的身份,这种精英与反精英间的张力贯穿于埃科的理论写作与小说创作中,在其作品的传播与接受中被各方选择性吸取。同时,对“畅销”的追求也体现了埃科对文本接受方的思虑与尊重,但该种考量并未走向极端。埃科试图达成一种知识圈层的自洽,其内部的话语生产和结构享有自治权,从“模范作者”到“模范读者”形成阐释学循环链条。这种自洽还在于对自身限度的明确意识,即便涉足公共世界,也多以反讽的形式,批判的同时,实行对知识分子批判能力本身的消解。这种知识分子的骄傲与审慎并存的心态在当代中国的知识界(广义的)颇受赞许。无论是专家型知识分子,抑或为个人喜好而阅读的普通读者,还是从事作品译介工作并追求书籍商品价值的出版方,围绕埃科作品的精神特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交流生态,同时在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了对埃科的阐释与形象塑造。这一形象既是埃科本人的,亦与当代中国本土的文化心态相关,是一场丰富多义的跨文化之旅。
围绕埃科,一种同构性的特质呈现在文本作品、媒介的形象建构和双重话语体系的阐释中,共同落实着“精英”与“反精英”互动交融的智性气质。作为“标准作者”的“埃科”对其读者存在着开放式的召唤关系:一方面,“高素质”是对埃科的作品创作风格的把握,体现在多学科领域的交叉:艰深的符号学理论建构,百科全书式小说风格的建立。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出版方、媒体不遗余力地强调其“博学”“文艺复兴式”知识巨人的特色,而学界对埃科展开的研究,同样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解释色彩,与埃科本人的学术风格相贴合。另一方面,埃科并不强调“精英”与“大众”的分野,相反,他以其长期坚持的大众媒体专栏写作,表达了知识分子走出学院象牙塔的理念。他关注公共话题,警惕现代知识分子“无所不知”的精英倾向,拒绝本质主义判断,主张宽容多元,且在随笔写作中发展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轻松、戏谑的文风。
这种具有较高智识门槛,同时又保持了开放性的宽容立场,被出版界和阅读圈捕捉到。作为学院派人物的埃科,也因此获得了中国当代知识界的回应。这里尤其以复旦大学的学者马凌为代表,作为学术圈和媒体双栖的作者,她是最早关注埃科作品的评论者之一,其写作的系列文章既是对埃科作品的学术阐释,亦是当代知识界接受埃科的维度之体现。现列如下:

表2 (下文相关引用均出自本表格中的网址,不再另行标注)
在《玫瑰就是玫瑰》一文中,马凌指出:“埃科既富于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又兼有后现代顽童式的洒脱,在学者和作家双重身份间的自由切换,使他的高深符号学理论沾染上世俗的活泼,也使他的通俗文学作品保有知识分子的睿智,是难得的一位征服了欧美两大陆、跨越了雅俗两界河的人物。”《玫瑰的名字》在读者中引起的轰动体现了埃科“精英”与“反精英”气质的双重融合,而这与埃科本人对“诠释与过度诠释”以及作品开放性的思考是高度契合的。“既不僭用科学之名,也要避开游戏的陷阱”(《解构神秘:〈傅科摆〉的主题》),马凌的解读道出了中国当代知识界在思想领域的审慎和节制倾向,表现为对宏大叙事的警惕、对历史语境的观照及对个体命运的关怀。
在大众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中国的专家知识分子开始更多地将学术旨趣投向象牙塔之外,“普通读者”亦能获取曾经只有在学院之内才能享有的专业智识训练,“精英”与“反精英”之间的界限日益消弭,这样的知识与教育氛围为当代知识界阅读与接受埃科的作品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也与埃科创作的旨趣相投合。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作者、出版方、市场和读者群体的交流互动,共同建构了围绕埃科作品所生产的传播图景,不仅为我们理解埃科本人的创作,更为我们解读跨文化视野下来自中国语境的阅读接受行为提供了丰富的文学传播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