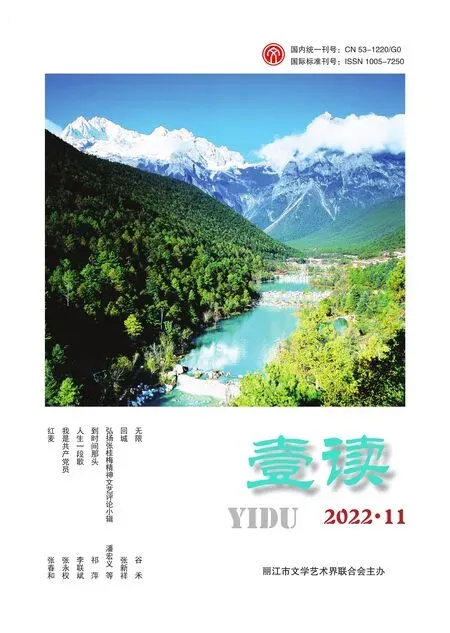无限(之一)
◆谷禾
《无限集》多为残片,如同一个人时常中断的纷乱思维,它重于记录、见证、个人思考和冥想,除个人日常生活和阅读的随记,形式上借鉴了集章,随笔、时文篡改、拼贴、微小说等文体。《无限集》是无序而杂乱的,但在我心中,这种无序和杂乱才更接近“诗”的原生态……
无限(00)
人类在遥远的星空图像中发现了无数古老的矮星系,这些暗红光芒的矮星系大多和宇宙的年龄相当,其中心都存在着一个年龄远超星系年龄、质量巨大的超级黑洞。也就是说,这些超级黑洞出现的时间要比宇宙更早。罗杰·彭罗斯把这一现象称为“上一个宇宙留下的黑洞残余”。基于此,他提出了“宇宙循环”理论,认为现宇宙是从前宇宙诞生出来的——前宇宙持续膨胀,所有物质被黑洞吞噬转化为能量体,宇宙最终回归小得不能再小的混沌状态。而在黑洞尽头存在着另一个相对应的强引力源——白洞——它是宇宙中的喷射源,不吸收外部区域的任何物质和辐射,而只负责发射,它发射的物质来源于黑洞与白洞相撞后形成的连接——虫洞。前宇宙物质在黑洞的奇点处被完全瓦解为基本粒子,通过这个虫洞传送到白洞并且发射出去(宇宙大爆发),诞生出现宇宙。人类身处的宇宙就处于这样的循环中——黑洞吞噬物质转化为能量体,宇宙所有的物质消耗殆尽后,大多数黑洞逐渐蒸发消亡,少数大质量黑洞瓦解为基本粒子,穿过虫洞进入白洞,爆发,成为现宇宙诞生时最早的星系核心。现宇宙诞生后,不断加速膨胀,物质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最终变成一片虚无的黑暗,被黑洞吸纳,穿过虫洞进入白洞后再次爆发,新的宇宙又诞生……如此循环往复。宇宙空间不断扩张,新星系也不断诞生出来。似乎有某种神秘因素影响着星系形成,这就又诞生了著名的暗物质理论——暗物质不仅促进了星系形成,可能也是引起宇宙大爆发的主因。人类所知的宇宙并无确证就是全部宇宙,也不能确定最古老的星系到底在哪里。宇宙中一定存在许多未被人类发现和认识的古老天体,它们身上可能保留着前宇宙的更多信息。“宇宙循环”理论给人类带来了类似神话的宇宙认知,虽然还未得到证实。如同黑洞被提出来时也没人相信、白洞和虫洞至今仍是幻想和猜测一样。也有人认为宇宙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星辰万物的布局与人类大脑的神经节点高度吻合——这就是说,造物主创造宇宙,又依照宇宙创造了人类大脑这个小宇宙,大小宇宙在不同轨道上生死轮回。造物在上,以宇宙的轮回作为尺度,人类和一只蚂蚁一粒尘埃毫无二致。没有时间,不存在空间,更遑论艺术和诗歌,只有运动才是无止尽。(注:所引资料源于知乎网)
无限(01)
光影变幻。铺展、聚散、游荡的浮云,
从高处绘出虎背的斑纹,那刻上我们
脸颊和身体的,也落向远山近水——
所有屋顶和坟墓一起从大地上消失了影子。
无限(02)
为了看到阳光,我们来到世上。
为了成为阳光,我们活在世上。①
我冻得直哆嗦——我想缄口不言
但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②
那一代人的梦,被侮辱
在泥沼里,在星期一的阳光下③马路边叫卖大白菜的中年妇女,她粗糙的手忙不停,她菜青色的脸迎着太阳。
注:①引子巴尔蒙特(俄);②引自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俄):③引自华莱士·史蒂文斯(美)
无限(03)
你见过星光照着青草吗?
它照见了青草上的大河,
它还照见风弯折的形状。
我在青草上睡去,星光
从天上,照见我怀抱的
凄凉梦想,还照见了我
锈蚀的脸,落叶的心。那么
遥远的,从仰望中落下
漫漫尘埃,一点点把我埋葬。
无限(04)
每年此日,须放下自己,须净手
须洗心,听不同的《安魂曲》
——莫扎特,勃拉姆斯,弗雷,威尔第
听《大弥撒》:巴赫,布鲁克纳,贝多芬
死亡一直堆积在那儿,骨头的反光
愈来愈明亮的末日审判,而散尽的
弹片和硝烟,把他们年轻的脸
嵌入淤泥和石头,留下我们苟且地活着
只此日,脱下躯壳,还原为人。
无限(05)
阅读的困顿,来自于纷乱的心境
蒙尘的书架上,更多书卷被黑暗淤积
一种责任和重负——你所期许与在做的
恍如一辆旧马车的南辕与北辙
有生之年,我们终将碎成更多粉末
时间的雨夹雪里,留下一地虚空
下一步,我们去哪里栖身?所有书卷
再无人造访,那些白纸黑字魂归何处?
我们回来,栖身一盏台灯下,也将生出
晚年心境,写下更多源于自我的灾异。
无限(06)
诗栖居于灵魂幽暗之地。它起自悲伤
而终于欢愉。舞蹈最初的灵感
源自水边的垂柳。
死,是生的无人地带,也是死者“凉爽的夏夜”。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更多的花
被自己的香气埋葬。
无限(07)
一只笼子在寻找自己的鸟①。
它(黑马)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②。
我们据此仿写道:“一颗头颅在地狱里寻找
砍下它的那柄斧头。”但是,除了目标的
单一性和多重性,两相比较,亦有云泥之别。
注:①引自弗朗茨·卡夫卡(奥);②引自约瑟夫·布罗茨基。
无限(08)
海明威写下“那只豹子不属于这里,但它还是来了,没人知道它来这里干什么”的最后一个字时,肯定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大洋彼岸逃出生天的这第三只豹子。人类动用搜救队、无人机、红外热相仪、最新北斗定位系统,历四十多个昼夜搜寻仍不见它的踪迹,肯定有无数人像我一样止不住好奇地一遍遍扪心自问:豹子究竟去了哪里,又是什么让它和已被捕回动物园的两个同伴做出了出逃的决定?直到我来写下这段不分行的文字,仍然没有关于它的任何确切消息传来。而在数千里之外的云南高原更多的人正在加入进来,试图阻挡十五只一路向北的亚洲象进入城市。海明威继续写道:“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被马塞人称为‘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在小说的结尾,海明威的主人公死在了乘着飞机向乞力马扎罗山顶飞去的梦境里,就像他把枪管插进口中并扣动扳机粉碎自己以及那只豹子风干在经年积雪的乞力马扎罗山顶一样……谁来告诉我:时至今日仍不见踪迹的第三只豹子是否因为再也无法忍受囚困的孤独和孤傲才结伴逃出动物园并从此消失在了所有群山和森林里?这些不同年代的豹子将在另一时空里相遇——那里高耸的乞力马扎罗山的每一块石头和积雪,都曾有过豹子的前世。
无限(09)
星期一早晨,他亲吻了
妻子,最后一次抱了女儿,
小心关上门,乘公共汽车
前往里特尼大街上
那座阴沉的灰色建筑——
他很守时(赴死亦如此)
他望着窗外的涅瓦河,流水
比圣彼得堡所有人都更长久。
他向卫兵报出名字——卫兵
没有从名册上找到他。“你来
干什么?要见谁?”“审讯员
扎克列夫斯基。”他答道。
“你可以回家了,”卫兵没有
抬头,“扎克列夫斯基今天不来,
没有人接待你。”——他不知道,
他的审讯员被审讯了,他的
逮捕者已被逮捕。从这一天起,
每个夜晚,他都穿戴整齐,
站在电梯口,等待着下一个
可能随时冲出的逮捕者——
他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
这个城市的其他人也在这么做。
每天晚上,他都例行其事:
清空肠胃,亲吻睡着的女儿,
亲吻醒着的妻子,从她手中
接过小小的行李箱,从容地
关门,仿佛去上夜班一样。
他站在电梯口,在漫长的等待中
消耗着内心的恐惧,并由此
获得安慰,以及十字架的赦免。
“……我们可以从这里进入他的
音乐。”他依然忍耐着,而我们
在他的音乐中,渐渐老去①。
注:①所引资料源于《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和《时间的噪音》(朱利安·巴恩斯)
无限(10)
那从月亮射来的光束并非源自月亮本身。几亿年以来,我们身处的地球、太阳系和更广大的银河系,一直在某个巨大的宇宙管道内做环形运动,并随同这个管道的低音和高音起伏着在宇宙中漂移。但这么巨大的管道也不过是宇宙的一根毛细血管,犹如你居住的城市里一根最普通的地下输水管道之于地球。无数星系诞生于此管道内,也将终老于此管道内,永远不能挣脱(也许它们压根儿没想过挣脱),这是星系的宿命。宇宙之大之繁复非人类(人不过是一粒粒星系尘埃)想象力所能及,恰如二维时空之外存在着三维和多维时空,不同时空交织在一起,我们看到的所有事物都无一例外的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造就了人类的“爱”,并由此奠定了人类作为万物灵长的地位。
无限(11)
2021年10月28日,扎克伯格宣布Facebook(脸书)将改名为Meta——该词源于近年来日益流行的“元宇宙”(Metaverse)概念。“元宇宙”空间维度虚拟而时间维度真实,其中既有现实世界的数字化复制物,也有虚拟世界的创造物,它是一个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又高度独立,真正囊括了虚拟网络、硬件终端、现实用户的,永续的虚拟现实系统,一个超级的虚拟共和国,扎克伯格们就是这个共和国的统治集团。阿德里安娜·拉弗朗斯对此有着更清醒(哗众取宠?)的认识,他指出,Facebook与其说是个社交平台,不如说是一个“国家”。人类进入“元宇宙”时代后,物理意义上的疆域和土地不再重要,Facebook尝试发行自己的虚拟货币,建立类似立法机关的所属机构,数十亿用户以“公民”的形象生活于其中,并对彼此的聚合有着明确想象,这样的Mate完全符合人类对“国家”的定义,而且过去一段时间,它通过疑似影响选举以及“封杀”特朗普等行为,已经展现了自己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政治兼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国家不是由边界定义的,而是由想象力定义的。所有国家都是“虚构”的,因为它的公民“永远不会认识其大多数同胞,以及见到和听说过他们,但在每个人的脑海中,都想象着他们共融的形象。这样来看,Mate虽然没有军队等专政机器,但它有源源的垄断财富(利润),活在其中的成瘾性用户(公民),不断扩张的虚拟边界(用户数量),只要它愿意,就可以各种理由“封杀”其用户(公民),强制用户对不同虚拟时空“多选一”,通过收购、拒绝互通等方式寻求并维持其一家独大和愈加强大,它掌握用户(公民)的所有大数据,并利用其对用户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它数字化的“绞杀”不带任何感情。我想到了房间里的大象,无数被“社死”的同类以及《变形记》里那只叫格利高尔的甲虫……这是我所读到的最可怕的未来之诗。(注释:所引资料来自《大西洋月刊》)
无限(12)
蟋蟀的叫声,再次把你带回
灰色童年。在无数个清晨,露水
的河流浸漫镰刀,光芒沿刃口滑过
扎紧的草捆把你的瘦弱肩膀越压越低
日落之后,暮色沿一片瓦楞漫开
你独自坐旷野上,被黑暗包围
等待浩瀚星空升上头顶,蟋蟀们
并无停顿下来的意思,叫声
更加恣肆——沿着叫声走去
你将抵达一片陌生的墓地。
仿佛神秘的引诱者,蟋蟀密集的
叫声分明来自坟墓深处,你想
找到那秘密通道时,大野突然静下来,
而后是长久的寂静。你从记忆中
抬起头来,去看那来路和去路
它已消失无踪,唯一城灯火
交织着光芒,更多蟋蟀的叫声,
从灯火深处隐隐传来。
无限(13)
我注视过一滴水在树枝上滑动
那么透明,却滞重,颤抖着
不掉落下来,溅起咚的一声脆响——
哦,这是林中,不是雨后街头
树枝湿漉漉的,闪着光泽
所有叶子扼紧呼吸,等着风起
我注视着一滴水,在树枝上滑动
它不掉落下来,溅起咚的脆响
无限(14)
从那道窄门里出来的人一律跛着脚,肩膀和脑袋一齐向着左边无限倾斜下去。围观者先是十分好奇,继而纷纷效仿,这种姿势后来成了这个城市所有人下意识的行为范式和白色衬衫的蓝色条纹。
无限(15)
人类和蜘蛛各自结了一张网,蜘蛛仅用于捕食和睡觉,人类则陷入其中不能自拔,生于网而终于网,生命由此被消耗,其中一部分人类异化成了一种叫“网虫”的新物种。
无限(16)
高速列车以350公里/小时的速度
穿过邻省和初冬,沿着铁轨疾行
不停下喝口水,也不加快了速度
除了呼啸的噪音涡旋,车体的安静
显而易见,更安静的车厢里的旅客
或昏昏欲睡,或沉于网事的元宇宙
他们不会想到,一个新冠感染密接者
已悄然上车。在被要求强制停车之前
列车和平时没什么两样,暮光照亮
车身和车窗,全部旅客明澈而安详。
无限(17)
“我站得那么静,头上的天空,
和水桶里的天空一样静。”多少年
过去了,我从远方回来,发如雪,
不再离去,听见自己平和的心跳,
倒映在水桶里,没有激起一丝波浪。
现在,我活成了一棵野树,生出根须
枝条,大地也褪去了鲜亮颜色,
犹如一幅潦草的黑白木刻画作
有风吹来,我头顶的叶子簌簌飘落,
黑夜如期而至,白昼慢慢收拢
也没有更多星子点亮夜空,从遥远
地平线尽头,群山汹涌,燃烧的落霞
借助一只倦鸟,送来灰烬的冰凉。
无限(18)
思想者坐在午后的街心公园,光影
落上他的铸铁之躯,还有斑驳的
锈迹、埃尘、鸟粪,但只要坐那儿,
他就不停止思想。他低首,眉头紧锁,
以手托腮,始终如一。他在想什么呢?
一个思想者,即使从地狱之门,漂泊
来到破旧街心公园,即使他是一个赝品,
也不改思想的形象——他到底在想
什么呢?而时辰已经来临,从远方
驶来的轰隆隆的铲车,越来越近了。
无限(19)
明万历皇帝朱由校荒于朝政,而专心木工手艺,他复制了“世界之窗”式的乾清宫,复原了诸葛孔明的木牛流马,发明了最早的折叠床(待考证),设计并现场督造了新皇极殿、中极殿和建极殿。他用一生的时间制作一只木鸟——木鸟长约五尺,展开翅膀约六尺,用金丝楠木磨刻的眼球有幻视功能,能看到过去和未来(这是他没有发现的)。木鸟在宫廷里低空飞行,所有的大臣和宦官、嫔妃、宫女莫不叹为观止,盛赞皇上是天纵之才。不单如此,每天早晚,从木鸟的嘴巴里还会清晣地响起“吾皇万岁万万岁”的男声,木鸟点头给他请安。万历皇帝沉醉其中,龙颜欢喜。他一生痴迷用榫子反对钉子,终于有一天,他把朝中政事托付给大宦官魏忠贤和弟弟朱由检,自己骑着这只木鸟飞走了。
无限(20)
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孛儿只斤·妥懽帖木耳也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木匠,他设计建造的龙舟长120尺,高20尺,上有帘棚、穿廊、暖阁、楼阁、殿宇等,需要24名水手同时操作才能行进。龙舟行进时,龙的脑袋、眼睛、嘴巴、爪、尾一起转动,仿佛真龙出世,活灵活现。孛儿只斤·妥懽帖木耳设计制作的“宫漏”是一个以水为动力的木质报时装置,高7尺,柜顶有3座微型宫殿,柜子里有3个小人儿,一个是拿着报时筹码的玉女,两边是拿着金槌和金钟的侍卫,每到整点时辰,拿着金槌的小人儿会自动敲响金钟,分毫不差。宫漏两侧有6个小飞人,随着钟声起舞,片刻后又退回原处。他被后世称为“鲁班天子”。孛儿只斤·妥懽帖木耳爱好淫乐,迷恋房中术,每夜与数女交合。他登基后,河南邓州暴雨三月不绝,黄州蝗虫肆虐,黄河决堤,一溃千里,饿殍遍野,乱民潮涌。孛儿只斤·妥懽帖木耳还是一个通灵的巫师,能从天象变化中算出人事变迁,据说在大将军察罕帖木耳战死前,他就推算出大都东南战场将失去一员大将,果然应验。令人遗憾的是,史书中并无他对蒙古朝廷和自己命运的预言,以及对300年后将有另一位比肩自己的“鲁班天子”横空出世的推算。也许,帝王的这种传承只有更神秘的造物才能知悉并一直掌控着。
无限(21)
在傻瓜的尽头,有一盏灯
一直照亮着
你们聪明人统治的这个世界
无限(22)
被纸枷锁住手脚的人,是否犯了
朝廷重罪,又或者,他们心中戴着
另一具乌沉沉的铁枷?千山万水荒芜
不见拘押的解差,他们一步一步
朝前走,铁枷锁心,就肉身扛着落日。
有多少回,我抬头望去,在所有
道路尽头,纸枷锁紧了他们的手脚
山川负雪蒙尘,亦如戴罪之身。
无限(23)
我并非厌倦了这满目疮痍的大好
河山——我所有的厌倦均源于热爱。
这大好河山亦如是。它一忽儿
把我当还家游子,一忽儿把我当月光的叛徒
无限(24)
在浓雾中,只有高楼
映出模糊的影子
原野不复为原野,隐现的城市
更像一座人间地狱。
巨鲸歌唱而我们继续工作
穿过地底,去另一个
陌生地方,作为孤单的生命个体
接受黑夜的再教育。
无限(25)
在自闭症患者的认知里,有病的是所有人唯独不是自己。他所有的快乐都建立在与外在世界隔离之后,他可能是人类中最杰出的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手工匠人、文学家、神学家、音乐家。在常人眼中,他们无一例都是病人或疯子。我亲爱的出生就身患自闭症的少年,竟然说得出我生活的城市所有地铁线路的站名和顺序。另一个中年流浪汉,每天午后准时去一个废弃的工地,用铁铲向地球深处挖掘,他的身后已堆起越来越高的石块和泥土。他告诉我,每天那个时辰,他总听到金子的敲门声从他挖掘的地底传来。他很快就会找到它们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或者后天,他要做的就是不停地挖掘。从他眼里射出的光,我在众人睡去后的月亮上也看到过。也许在月亮的背后隐藏着一条抵达他们幽闭内心的秘密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