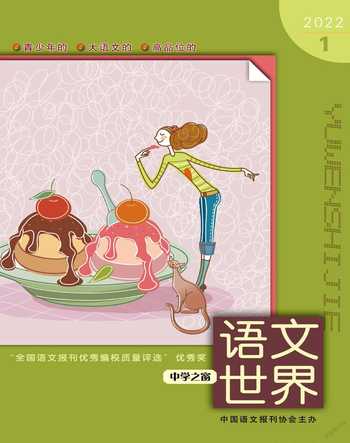刘亮程谈枕边书
宋庄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您的枕边书会经常变化吗?
刘亮程:年少时喜欢读字,枕边常放《新华字典》,繁体简体字一起读。后来读过一阵《汉语大辞典》。再后来,觉得《辞源》有意思,每个词都有出处,有源头,那是词的老家。一个词从源头出发,在语言文字里走几千年,有的把原意走丢。更多的词把自己走丢。写作者需要知道一个词的原意,用它时,用的是今意,但心中有原意。我写作用词量极少,不轻易用词,尤其不用成语,也拒绝新词。自己拿字结词造句。我写文章用字量也极少。没浪费过汉字。
很多书是躺着读完的,养成了躺读习惯。年輕时总有闲事缠身,得空才读书,读书成了休息,有个地方躺着读书,就是享受了。抱着书睡着,做的梦都不一样。
躺下读书时,脑子放在枕头上,感觉是不同的。
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读的枕边书的感受?
刘亮程:前些年写《捎话》,床头书桌上都是关于西域宗教历史的书,那架势像要写一部扎实的历史小说。其实不然。历史有其碰不得的地方,也搬不动。但那些书摞在枕边,会形成时间和年代氛围,会把历史的痛时时传递出来。到最后,你的文字不觉间穿越了历史。
前一阵读《江格尔》史诗,也是随手翻看,读到好玩处,便放手不读了。史诗有天真的好玩。但读多了也单调,尤其口传史诗,没有经过文学再造,格式千篇一律,思维模式也雷同,但仍可读。有笨拙的天真。这一阵看土尔扈特东归的故事,有小说、历史资料、专题论文等,又像要写一部历史小说了。其实呢,写的时候才会知道在写啥、写成啥。
您读过最有意思的书是哪一本?
刘亮程:记忆最深的还是早年阅读的几本书,一直留着。那是我上初中时读的书,因为在偏僻乡村,除了课本再没书可读,但我却有了几本书,它们是《唐诗三百首》《楚辞集注》《人间词话》《汉语大词典》等,都读旧了,现在还留着,封面的样子都能想起来。
我小时候家里有几本繁体竖排线装本的中医书,是先父1960年从甘肃酒泉金塔逃荒到新疆时带来的,我还有印象。先父是旧式中国文人,吹拉弹唱,号脉开方,样样会。后来我收藏了许多本中医书,都是线装本繁体字的,里面有大量对症下药的老方子,有时翻一翻。也曾想过在这方面下点功夫,日后自己或他人病了,开方子抓药。
那时候我们村里还有几本内地逃荒来的人带来的古典小说,繁体字,我读到过一两本,都破得没头没尾。其中有一本,早没有了书名,只剩下书瓤子,我反复读了多遍,里面主人公的旅行奇遇让我萌生了写童话故事的冲动。多少年后我才知道,那本书是《镜花缘》。
我后父是个农民,他不识字,但会说书。说《杨家将》《薛仁贵征西》《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说的都是片段,不完整。因为他听来的就是东一段西一段的。他说过的书后来我大多没再去读,总觉得自己知道那些书了,所以不必再读。唯独《三国演义》看过,但跟我后父讲的大不一样。我小时候听后父说的是一个“乱如麻”的甚至错的“三国”,但真的比我读的“三国”有意思。而且,有些章回,我现在还能按我后父的版本讲给别人。
哪些书对您的思维影响最深?
刘亮程:对我写作思维影响最大的,可能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学物理课学的,当时老师告诉我们没有绝对的大和小,大人相对于孩子来说是高大的,但相对于一棵参天大树,却是矮小的。这个极其简单的大与小的相对关系,直接打开了一个乡村少年的思维,并影响了多年以后我对自己文学世界的构筑。《一个人的村庄》便是一个人的相对论。那个小小村庄和村里的卑小事物,都找到了自己的相对位置,大小、尊卑、长短、远近,以及死生梦醒、来去轮回等,都被妥当地安置在一个村庄世界里。
后来我补课读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却没有读进去。他对一个作家的启发,仅那点大与小的相对关系,已经足够了。剩下的是用来启发影响整个人类的。在他构建的那个宇宙时空世界的对面,是文学所创造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也已经存在几千年了,作家是给这个世界干活的。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刘亮程:大概四五年前,我落户到菜籽沟村生活的第三年,又重读了一遍《老子》,是坐在书院一条小水渠旁的大杨树下,花一个上午读完的。年轻时候读过,一知半解。年过半百,竟读出了《老子》的好,也觉得读懂了。
《庄子》也是反复读过的书,年轻时就没读完,后来尝试去读完,仍然只读几个章节,便放下了。多少年来,多少章节可能被反复读过,也有一些章节或许从没有翻到。偶尔还会看,随手翻到一页,看完一小节,就有阅读的满足感,真的不需要读完。
再就是自己的书,《一个人的村庄》出版二十多年,换过四五个出版社,每次再版,都要重读一遍,其实也没什么要修改,只是不放心电子版书稿,在文档里放了几年,那些字和句子会不会乱走动。
自己的书,隔几年重读一遍有好处,有些文字睡着了,你一读,它醒来了。
(选摘自《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9月2日)
- 语文世界(初中版)的其它文章
- 一盏灯
- 作文与细节
- 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 刘亮程:一个人的自言自语
- 春天的步调
- 那一星游走于乡野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