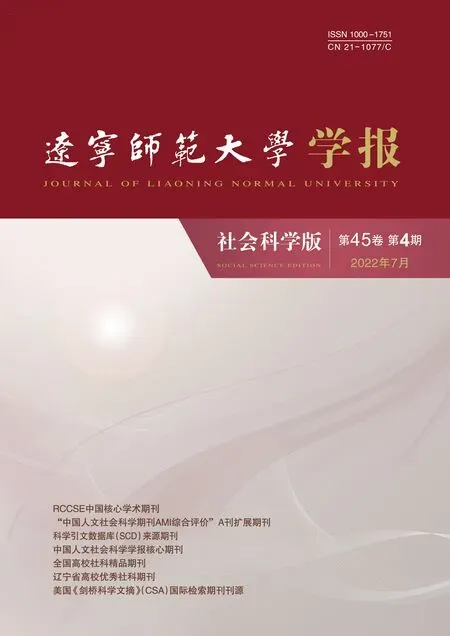孤独经验与社会想象——陈染小说《与往事干杯》的主题意义论析
印芷仪, 林春美
(博特拉大学 外文系,马来西亚 雪兰莪州 47300)
何为孤独?孤独是一种个人主观上与他人或者社会产生的疏离感,是“主体与对象相疏离所导致的一种刻骨铭心的精神空落感”[1],是个人将自我生存空间与外界隔绝的一种状态。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孤独又常常是个人主动的“封闭”选择。本文讲的“孤独经验”主要相关于个体不断与社会相疏离的态度和行为。“社会想象”是指个体在社会实践中主观构想的社会存在方式。“社会想象”并非写实记录,它的重点在于突出作家在文字中“建构”社会的方式。
《与往事干杯》是陈染创作于1991年的中篇小说名篇,填补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以女性性别为主体书写的结构性空白。以往学界多以私小说及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研究,本文则旨在从“孤独经验”和“社会想象”两方面讨论其文本的深层意涵。在《与往事干杯》中,个体的“孤独经验”表现在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遭受的情感创伤,以及女性身体和身份的多重困境中。“社会想象”则主要体现在主人公在经历“心灵磨难”后对待世界的态度,以及以女性视角体验社会的方式。
一、孤独起源:尼姑庵往事
陈染在小说中以自白的口吻,向闺蜜乔琳讲述了曾经历过的一系列往事。主人公“我”——肖濛,是一个瘦弱、愁思充满胸腔的青春期女孩。肖濛的家庭成分不好,父亲情绪暴躁,母亲则长期隐忍。作家将幼年的肖濛放置在城南胡同里,这样的住处设定似乎与其胡同情结有关。因为陈染此前曾专门撰写了与胡同有关的散文——《反“胡同情结”》,她自道:“对北京小胡同的感觉主要来源于母亲,……我曾随母亲在北京城南的一条曲曲弯弯胡同尽头的一所尼姑庵遗址居住了四年半。”[2]97正是受这段经历影响,陈染让小说中离婚后的母亲和肖濛住在一个破败颓废,有着“绿色天空”的尼姑庵里。从城南胡同搬到尼姑庵,对母亲来说仿佛是从“牢笼”挣脱出来,她对肖濛说:“这回妈妈要让你过好日子了。”[3]91
然而,尼姑庵对肖濛来说却是孤独的牢笼。十七岁的肖濛正处在青春期,本就敏感的她在遭遇青春期发育、家庭变故和升学压力后,更是战战兢兢地活着。在同学对她说“肖濛,你爸爸给你送生活费来了,在班主任老师那。是不是你爸妈分家了?真可怜”[3]92时,她脆弱的心灵再次受到重击,放学后路过陶然公园的湖,忍不住想跳下去。虽自杀未遂,但苦闷仍像黑云般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然而偏偏祸不单行,肖濛的母亲因遇到初恋“混血外交官”而对她疏于陪伴。由此肖濛每天回到尼姑庵看到的都是“绿色的天”。此处“绿色的天”是肖濛成长过程中灵魂孤独的象征,这种孤独直到男邻居的闯入才变为“湛蓝的苍宇”[3]95。
男邻居医生和肖濛均因无人陪伴而日日聚在一起吃晚饭,渐渐熟悉后,在一个闷热的夏夜,男医生与肖濛进行了不彻底的“性游戏”。虽然陈染在此处没有对人物心理进行过多刻画,但从对话中足以看出两人内心之复杂。这个男人极尽克制,不愿意真的伤害肖濛,对她是发自内心的保护和关爱,但另一方面却又真的想占有她。肖濛心里清楚,这个男人比她年长近20岁,足以做她的父亲,她虽觉得不该与这个男人“游戏”,却在心理上对其产生了深深的依赖。高考结束的晚上,男邻居成了肖濛的“处女地的耕作人”。这个男人的臂弯是肖濛在尼姑庵全部的、也是最后的安全感。也因此尼姑庵成了肖濛心灵寄托的永恒之地。即使后来母亲一次次被落实政策搬到更好的住处,肖濛也不再见到“湛蓝的苍宇”。男邻居是肖濛摆脱灵魂孤独的一剂良药,搬离尼姑庵意味着良药不再,自然也不会再有“湛蓝的苍宇”。
学界对于此处的分析多流于“恋父”的层面,然而本文无意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讨论肖濛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恋父”,因为过于执着恋父情结的分析会遮蔽作者真实的女性表达。戴锦华也曾说:“使用精神分析的‘套路’无疑可以使分析者获得完整的对陈染叙事的叙事,同时可以陶醉于弗洛伊德的无往不利;但在必然的削足适履,会损失一个文化个案的丰富性的同时,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再经典不过的男性的、关于男性的话语,必然使陈染的‘父亲场景’隐含的(此后愈加清晰而强烈)的复杂的女性表述继续成为盲点。”[4]
与其说肖濛对男邻居是“恋父”的,不如说男邻居与肖濛是保护与被保护、引导与被引导的关系。身为女性,肖濛的身体被男邻居渴望、凝视,男邻居一方面想保护她,一方面想占有她。肖濛则企图用身体的奉献来换取温暖,但“肉体的满足与灵魂的饥渴或者灵魂的满足与肉体的饥渴总是相伴而生”[3]75,身体的被渴望和被凝视恰恰是她孤独的来源。肖濛的第一次不彻底的性行为在男邻居的引导下发生,她像“小狗贪婪地渴望主人挠痒那样”[3]108渴望与这个男人亲密,这种引导与被引导的行为是肖濛作为未成年不断渴望爱的表现。与此同时,肖濛主动疏远男邻居,以及后来反过来主动要求男邻居成为“处女地的耕作人”意味着肖濛在成长阶段对爱的逃离以及对秩序角色的游离和对固有秩序的反思。引导和保护的角色为父亲一样的男性,他们更多的是心理意义和“功能性”人物——“他们隐形出席在女性的深层意识里”[5]。
五年后,肖濛与老巴相爱。透过肖濛的回忆,我们看到老巴是和男医生连在一起的:有老巴的身影,就会出现尼姑庵里男人的背影,恰巧老巴又是男邻居的儿子。陈染通过设置如此的戏剧情节,将尼姑庵作为全部孤独的起点和终点,也就是原点。尼姑庵包含着肖濛的所有记忆和秘密,是她寻找依靠和自我挣扎的汇合点。换言之,尼姑庵是肖濛青春期孤独的集合点,也是日后在生活中反复出现,难以抹去的背影。孤独意味着个体与世界的割裂和孤立状态,由尼姑庵作为背景出现的肖濛的身体和情感挣扎带给肖濛的是灵魂的永恒孤独。个体面对的情感冲突只是文本的表层含义,文本深层则试图唤醒读者对女性身份和灵魂等多重孤独的深切认同。
二、“故乡”:孤独的反复叙述
《与往事干杯》着重刻画了母女关系。母亲对女儿有着不可回避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女儿面对现实的态度和方法。对于肖濛来说,她对母亲既有无与伦比的深刻眷恋,也有女人间的性别审视。在父母分居后,肖濛将强烈的不安和亲密感全部投注于母亲,“我睡在母亲的怀抱里,像睡在天堂一样安全而美好”[3]84。她凝视母亲,从母亲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又在自己身上看到母亲的影子,主体与暗影杂糅在一起,融为一体。肖濛“像一个陌生的旁观者一样审视着这个女人……我曾伏在她的怀里,那里只是妈妈,而不是女人”[3]111。肖濛凝视母亲,在母亲的轮廓里看到自己,她看到的母亲是她想象中的有着无尽爱意的“理想母亲”[6],是理想女人的化身,是主人公孤独情绪的情感寄托。
母亲和混血外交官的恋情使得肖濛感到失去了情感的寄托,所以便逐渐从情感层面产生了对母亲的疏离。肖濛就是在这种对母亲既渴望又逃离的复杂情感中度过了少女时期。直到遇到老巴,肖濛才将对理想女人的幻想转移到自身。
老巴与肖濛交谈时一直在说“故乡”这个词,老巴用嘴探索肖濛身体时,停留在肖濛胸前,他眼含热泪地说:“那一双乳房,只有那一双乳房,才是他日思夜想、魂牵梦萦的‘故乡’,他的归宿”[3]131。此时老巴的孤独外化出来。肖濛对老巴是充满怜爱的,和他亲密时只想“满足他”,愿意为他奉献一切。此时的肖濛自己便成了理想女人。肖濛是老巴心灵的安放地,是老巴的“故乡”。肖濛决定回国后,老巴彻底失去了“故乡”,失去了来自肖濛的心灵支撑。老巴与肖濛的爱情悲剧与其说是客观现实的捉弄,不如说是主人公孤独情绪的极端外化。
随后,理想女人的形象进一步反复出现,这便是小说中肖濛对乔琳的情感投射。“我坚信自己不是个同性恋者,但我也坚信我对于她的信赖和需要不比对以往任何一个情人的肤浅多少。”[3]75“在这个使人们的心灵孤独无助的世界上,在这个表面亲爱、繁闹、热情而内心深处却永远无所依傍的人群里……乔琳需要我正像我需要她一样深刻。”[3]76肖濛在对男性和家庭失望的背景下,求而不得只能逃跑,逃到只有女性的纯粹同性世界里,以此来获得对孤独的慰藉。乔琳是肖濛内心渴望“另一个精神的家园”[3]76的化身,也是肖濛孤独灵魂的“故乡”,她们之间的同性联系更多的是灵魂与生命的相互关照。这即为西方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姐妹情谊”(sisterhood),即通过女性之间饱含欣赏的眼光来展现女性的魅力。此时对女性的欣赏不同于男性对女性充满欲望的窥视,是纯粹的美的欣赏,是心灵的契合。陈染将肖濛对异性的失望转化为对女性的欣赏,对同性的欣赏也是对自己性别的欣赏,即是最自我的欣赏。换言之,这种欣赏也是对肖濛自身身体和内心世界的孤独守护。
小说中理想女人的不断流转,使小说空间成为不稳定的存在,像流水一样延伸出更大的自由性,进而实现了对孤独经验的书写。美国女性主义者芭芭拉·琼森(Barbara Johnson)认为“女性的个人经验不只被排斥于知识范畴之外,还有任何属于个人范畴的都在加上一个‘女性’的编码后而被贬低……个人或至少是个人立场是一种播散权威及分解错误的父权制意义的普遍方法”[7]。借助芭芭拉的观点,我们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陈染通过反复叙述肖濛的个人孤独,颠覆了现实中男性预设的女性固化形象。
重复叙述孤独是陈染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孤独”不仅是文本人物的生存状态,也是陈染自身的生活写照。她在一次访谈中曾说:“我十八岁时,父母离婚……我以三分之差没有考上大学,和母亲借住在一个废弃的寺庙里,一住就是四年半。当时我没觉得多么不好,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对于一个正在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少女来说,是件很残酷的事。”[8]特殊的成长经历,使得陈染在生活中时刻带有孤独感,因此作家与主人公的孤独是互为阐释的关系。
不仅如此,陈染笔下的孤独已经不只是一种叙述方式,更是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哲学追问。孤独也不仅属于女性,它存在于每个个体中间。在《与往事干杯》中,孤独首先是一种生存状态,一种可以覆盖一切的生存困境。文本中出现的各个人物,无论是母亲、肖濛、男邻居还是老巴,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孤独特征和孤独体验。他们的孤独源自个体生命遭受的来自现实生存世界的压迫,并且他们因为孤独产生生存恐慌,只有在一个适合“孤独”产生的环境才得以“活下去”。“尼姑庵”的设定便是孤独得以衍生的庇护所,即使尼姑庵天空的颜色从绿色变为蓝色,尼姑庵带来的压迫感也始终存在。此外,孤独是一种对待外在世界的态度。文本中的人物一方面惧怕孤独,一方面却又在享受孤独。肖濛最后的选择是沉迷在回忆和幻想里,这种孤独的设定是在不断重复孤独并在内化孤独后所产生的独特人生境界,因为主人公选择了远离和无视这个世界。陈染充分挖掘了个体的孤独,并将孤独不断重复、深化为独特的孤独经验。作家将孤独经验与个人生存境遇紧密结合,从而使得人物在经历孤独创伤后,能从自身的孤独经验中获得继续生存的勇气。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孤独经验是一束可以照亮个体生存道路的亮光。
三、出路:社会想象
陈染对孤独经验的书写,展现了其自身想象社会的方式,并指出了个体走出生存困境的道路与方向,这也是《与往事干杯》的最有价值之处。
后现代主义认为文学创作不应该设置各类体裁界限,从而使作者、读者和批评家实现对文本最大限度地解读和解构。正是受此影响,中国文坛20世纪80年代末也兴起了“无体裁写作”的创作实验。《与往事干杯》便是这类写作实验的著名文本之一,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体裁风格。如陈染在文本中有这样的叙述:
男人 男人 男人 男人
男人 男人 男人
男人 男人
男人
女人
女人 女人
女人 女人 女人
女人 女人 女人 女人[3]96-97
乍看这是陈染在文本中进行的语言游戏,实际上这种“语言游戏”展现的是她从女性性别视角发出的对“人与人的关系是什么”的追问。男人或是女人都可以视为一个个孤单的个体,主人公们体验到的孤独,是人们在生存中无法回避的各种情绪的体验。即使男性和女性有着不可避免的性别“对立”,但在陈染看来,每个生命的个体都是孤独的。“男人男人男人男人 女人女人女人女人”的表述意味着即使有数量众多的同性别个体,个体之间也无法做到互相理解和心灵相通。从此处看来,陈染的写作实验使文本包孕了她对个体孤独生存的感动和敬意。
那么,陈染体裁变异的写作目的何在呢?她试图实现个体的精神救赎。肖濛伴随着两位男性的出现而成长。肖濛在与男医生的“性游戏”中扮演的是意识的主动者与行动的被动者;她在与老巴的“性游戏”中则是行动的诱导者与意识的被动者。看似肖濛一直都是支配者,但实际上这两个角色的层面并不相同。通过让肖濛成为“性”的意识主动者和行动诱导者,在同一人身上体现出不同角色的互换,体现了陈染对传统性规范的新思考。“传统的性规范和性角色定位,体现着……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9]而在陈染笔下,这种支配关系在男女共同分享快感的基础上被消解了,伸向了更有深度的层面——是一种在无法摆脱既有秩序后重新建构自我的方式。陈染真正想表达的是,在一个孤独又隔绝的世界上,应该更加珍惜个人(无论男女)的情谊而不要在乎文明的约束。然而,每个个体都无法与自身的性别、民族、阶层等具体身份“划清界限”,因此对个体的观照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空洞的形象,因此陈染在文本中大胆描写性爱场面,实质是展现了主人公在精神层面的自我救赎过程。
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不仅取决于自身已有的未定性,也取决于读者解码过程的具体化。除了作者的写作风格,读者对作品的鉴赏和解读的主体意识也是体裁变异的制约因素之一。读者能够对体裁变异产生影响是因为“读者参与了作品价值的创造和文体模式的建构”[10],因此读者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参与力量,作品的潜在价值和意义需要通过读者的接受反馈和无限补充才能得以实现。
陈染书写了一个个体边缘化和孤独失语的社会境遇。肖濛找寻自我及女性性意识的孤独经验构成了文本的中心,其寻找自我的心路历程和对社会的想象,是伴随着其精神层面的自我救赎来实现的。换言之,主人公的自我救赎,其根本目的在于引导读者坦然接受对既有社会话语的反思,是陈染站在女性视角想象社会的一种独特方式。
肖濛最后回到“自己的房间”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失去了爱人、亲情,被社会遗弃,等等。肖濛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女性,对外在的宽裕社会生活有很大的依赖性,但她的内心有所坚守,不愿在繁荣的社会中迷失自我。她内心忧郁,有着多愁善感和冷僻孤傲,她渴望过上精神富足的生活,因此与俗世闹得不可开交。她对外界社会有着近乎本能的对立,她更希望通过逃离来实现在精神世界的解脱。从中国到澳洲,肖濛一直在努力适应,她希望逃离“恶劣”的社会环境,但最后只能头破血流的回来。“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奔波和追寻之后,我已身心疲惫……我几乎整日整日地仰卧在沙发里,房间里暖暖的,我的身体全部伸展在温情的阳光中。”[3]74文本时常出现房间、窗帘、镜子等空间意象,实则暗指陈染塑造的与世隔绝的孤独感,也可以看出《与往事干杯》的个人叙事有着特定的空间。陈染在特定空间叙事的目的在于突出个体的孤独感以及与社会关系的紧张感,表现作者对待和想象社会的态度和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因为社会的诡谲变幻,曾以“大一统式”叙事的史诗文本成了“过去式”,肯定“想象”的符号特征也由此凸显出来。文本中出现了“尼克松访华”等历史印记,这些印记是陈染记忆碎片的虚浮背景。借此,陈染为书写社会注入了诸多“琐碎”感受,这是其搭建的用以想象社会的心灵脚手架。
长久以来中国人对身体的表述都是充满想象的。福柯认为:“性的话语从未脱离过权力的运作,它们并非站在了权力的对立面,相反,他们是在权力的话语之中建构起自身的。”[11]陈染在小说中肆意展现女性身体,通过描写女性身体和性爱体验来疏离男权话语的束缚,寄托了作家“崇高的理想性”[6]。解放身体同时也意味着是人性的解放,陈染在文本中所描绘的女性的身体和原欲的觉醒,象征着女性在男权社会话语体系中的解放。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肖濛两次的性爱经历:与男医生在一起时,肖濛一反传统女性顺从的角色占据主动;与老巴在一起时她则充满母性想要满足老巴的一切。实际上这种主动和满足的行为体现了女性在性行为中的绝对支配——性行为的进行与否或者如何进行,都由女性掌控,从而展现了女性独特的自我意义。陈染在作品中表现出对传统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反思,在凝视女性身体时构想了一个不再受到“父权”话语规训的文学图景。然而陈染在文本中又不只是观照女性,而是构想了一个个体自我更新的文学图景。
陈染在讲故事时说这是一个“死于华年”的真实故事。“死于华年”意指在一片繁荣的大环境中的个体死亡。20世纪90年代中外交流日益加深,社会氛围也较为开放,多元化的文化格局由此出现。陈染将创作视野投向对个人生活的叙述,因为“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12]。除此之外,此时的个人书写也带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特别性质:“一种创伤性的记忆,一种对于公共生活的不由自主的回避”[13]。
在文本中作家展现了她眼中一个崭新的、包容自由的文学景象。然而作家却又同时着力使主人公从自己的房间里隔着窗户眺望世界,由此便表达了女性在开放的大环境中依然会经历众多的纠结和矛盾。哲学思辨在《与往事干杯》中随处可见。肖濛在老巴去世后深陷在回忆中,这种回忆本身就是一种思辨。她在不断反省自己,最终得到了救赎与成长。在文本中,肖濛对待社会的方式总是一种复杂又无以言说的状态,她体验到的社会实际是她内化并加以想象的社会。在繁华的社会环境中,女性不断品尝孤独、享受孤独,以此来追求精神的解脱。个体“向内看”,将自身不断封闭,是个体在社会的繁荣中自我保存的行为,也是以女性视角进行社会想象的独特方式。
任何从个体角度来想象社会的写作方式,必然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这样才可以使文本能够进入社会的文化秩序。正如贺桂梅所说:“作家如果想在个体生存表现上再深入一步,必须放弃纯个人的情绪化厌倦或抒情态度,较冷静具体地进入个体实存的现实关系的考察中”[14]。陈染在《与往事干杯》中力图回归个体生存暧昧、含混和难以界定的本源状态,但同时她也通过个人叙事做了“回归”社会的努力。“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15]陈染在一次访谈中提及自己是如何走出精神的困境时说:“写作是我自我表达、自我平衡的一种方式,通过它为自己寻找一种精神的出路。”[16]当然,陈染在文本最后也不忘给其他生命个体指出摆脱困境的出路:“天黑了,夜深了,黎明了。明天,哦明天,仍然有一堆算不上失望的失望在等待着我。我笑了。这就对了,世界因此而正常,因此而继续。”[3]160这个出路饱含悲剧意味,有着悲天悯人的无奈和放弃。但正如前文所言,放弃本身也是一种意义,个体更应该关注的是自身精神的解脱。
张爱玲曾说:“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17]陈染或许就是在感到“惘惘的威胁”中进行创作的,她对个体生命的体会和感悟有着女性独有的细腻和智慧。总之,《与往事干杯》为个体生存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是借女性之笔发出的柔声细语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