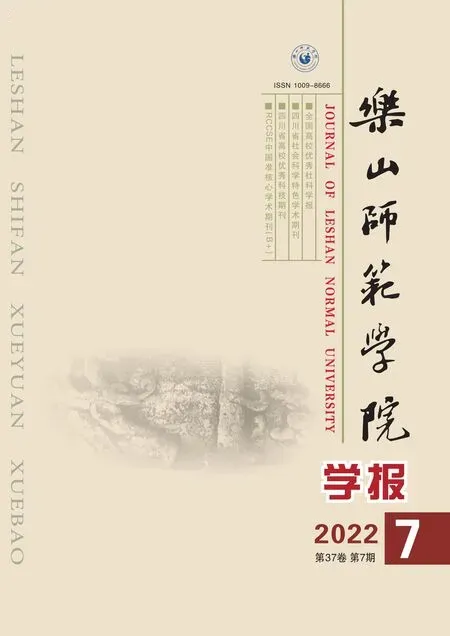以禅论书:苏轼书论中的禅宗文化精神
翟晓楠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四川 眉山 620010)
苏轼生活的北宋中叶,正是禅门宗风在士大夫群体风靡之时。士大夫往往精通内典,热衷禅悦。苏轼受到禅宗影响深刻已成学界共识,其诗文与禅宗的关联几近打通。相较之下,苏轼书论与禅宗影响研究却显得冷清,仅有的零星论文尚未道尽其妙。以禅宗理念观照苏轼书论具有多重意义:一是能够更加细致入微地认识苏轼书论思想的产生过程。二是透过苏轼书论独特的禅宗语言修辞,直抵其文学思维内核。作为才华横溢的诗人,苏轼叙述书法见解与创作实践的文字并非生硬干瘪教条式的经验与规律,而是诗歌和序跋。诗歌自不必说,苏轼的书论序跋也往往带有诗歌的修辞。黄庭坚评苏轼的书法:“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矣,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1]672于苏轼书论而言,此言也极度适用。三是从书法一门窥探苏轼知识、气度、性格的宽广博大,发现苏轼文化人格的形成轨迹。
一、书味禅悦:从书法艺术到宗教解脱
儒家文艺观念笼罩艺坛的时代,书法的社会价值常常被归之于“载道”,书法于个人而言的意义是完善自身道德。“兴至德之和睦,宏大伦之玄清”(赵壹《非草书》)[2]3,“沉密神彩,如对至尊”(蔡邕《笔论》)[2]6就是个中典型,类似言论枚不胜举。与之孪生的理念是评价书法美丑的标准是书法家人品。艺术理论发展至今,艺术创造与伦理道德早就被划分得泾渭分明,彼此不再干扰。那么,苏轼认为书法的意义又是什么?
苏轼《与参寥子》:“老师年纪不小,尚留情句画间为儿女戏事耶?然此回示诗,超然真游戏三昧也。”[3]6722好友参寥子(道潜)是和尚,年纪不小,还沉迷于诗文字画这类不属佛门弟子应习的正务,苏轼反而赞赏道潜赠诗体现了“游戏三昧”。何谓游戏三昧?六祖惠能《坛经·顿渐品》:“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4]358游戏是自在无碍之意,三昧是正定之意,合起来就是自在无碍而心中不失正定,也即超脱自在、无拘无束的境界,也是修禅者的终极目的。禅宗的修行与解脱方式非常多样且日常,苏轼将文学书法创作都视为解脱的途径就源于此。苏轼的新见,不仅完全背离了根深蒂固的儒家修身载道论,也为书法赋予了更广阔的价值。
苏轼《六观堂老人草书》:“物生有象象乃滋,梦幻无根成斯须。方其梦时了非无,泡、影一失俯仰殊。清露未晞电已徂,此灭灭尽乃真吾。云如死灰实不枯,逢场作戏三昧俱。化身为医忘其躯,草书非学聊自娱。”[5]3749整首诗强调草书的精神愉悦性和对抗生命空幻与虚无的悲剧感。
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曾说:“艺术和宗教乃是人们避开环境,从而获得快感的两条道路。艺术和宗教之间有着一种联盟关系,它们是达到相似的精神状态的两种手段。”[6]50这与苏轼以书法追求个人解脱、缓解现实不安、获得心理平静的观念如出一辙。
陈岩肖《庚溪诗话》:“东坡谪居齐安时,以文笔游戏三昧。”[7]173(句读应为“东坡谪居齐安,时以文笔游戏三昧”,作者注。)苏轼贬谪黄州,书法艺术就成了他对抗现实苦难、超越世俗纷扰、获得自由无碍的一种方式。苏轼的追随者僧人惠洪也是如此理解这位偶像,他说:“东坡居士,游戏翰墨,作大佛事,如春形容藻饰万物”[8]2986。
尽管苏轼认为写字是解脱方式,但也有前提条件。如《答孔周翰求书与诗》:“吟诗写字有底忙,未脱多生宿尘垢。”[5]1613如果吟诗写字变成了忙碌的事情,那么就没有脱离佛教所说的轮回之苦,要永远被烦恼折磨,无法解脱,所以日常书法创作应该保持随意轻松的状态,才能真正助人解脱。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曾有专门章节论及宋代诗学与游戏三昧,其书言:“问题的关键是在对于艺术活动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如果是执着的、认真的、殚精竭虑的苦学,苦练,苦吟,那么艺术就成为人生的束缚、负担;如果是随意的、戏谑的、轻松自如的闲吟,漫兴,戏作,那么艺术就具有缓和紧张、消弭分裂的作用,从而在心理学的意义上与宗教解脱相通。”[9]137
除了书法创作本身,苏轼论书文字常常戏谑诙谐,也是游戏三昧的体现。比如《题李十八净因杂书》:“刘十五论李十八草书,谓之鹦哥娇。意谓鹦鹉能言,不过数句,大率杂以鸟语。十八其后稍进,以书问仆,‘近日比旧如何’?仆答云:‘可作秦吉了也’。然仆此书自有‘公在乾侯’之态也。子瞻书。”[3]7811
李十八是李常,刘十五是刘攽,皆是苏轼至交好友。刘攽评价李常书法似鹦鹉学舌,虽然部分像人言,有可观处,但大部分停留在鹦鹉鸟语阶段,不可观处尚有很多。后来,李常书法进步,苏轼评价他的书法像秦吉了,秦吉了特点是更像人言,以之比喻李常书法,乃是赞其书法进益。秦吉了这个比喻,既上承刘攽建立的语境,又产生出其意料的幽默效果,体现苏轼善于戏谑的性格。
尾句苏轼认为自己当下所书颇有“公在乾侯”①之态,“公在乾侯”是谜题,谜底是《左传》“公在乾侯”句之前的“鹆”,苏轼调侃自己的书法作品像李常一样是学人语的鸟而已,尚有不足。尽管“打诨出场”常被视做宋代诗学的命题,但此文也颇有打诨出场的味道,更是苏轼游戏笔法的证据。换言之,这又何尝不体现了禅宗“绕路说禅”?
禅宗讲究语言“遮诠”,圭峰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遮诠表诠异者”言:“遮谓遣其所非,表谓显其所是。又遮者拣却所余,表者直示当体。”[4]406也就是不直接论述佛理,而是从反面作否定回答回应佛法问题。类似还有曹洞宗的 “不犯正位”,以及云门宗的“云门三句”等,都大量使用隐语,乃至于洞山良价《五位王子颂》全文使用隐语说明佛性。禅宗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把隐语发挥到了极致,以至司马光强烈谴责“今之言禅者,好为隐语以相迷,大言以相胜,使学者怅怅然益入于迷妄”[10]92。
禅宗僧人惠洪曾说:“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荆公、东坡、山谷三老知之。”[11]255苏轼以《左传》设置隐语(谜语),但《左传》仅仅提示了谜底的方向,并不交代本意,谜底与谜面距离极远,其勾连过程曲折离奇,含蓄隐晦,着实需要费一番思索猜量,不过明晓之后又不得不惊叹苏轼的巧思妙想。此文仅是一篇普通题记,苏轼都力求为之赋予更多的诗学和禅学意义,既可知苏轼文学功底,也可知禅宗思维方式对其影响之深。
二、以禅悟书:悟禅之道亦悟书之道
书法作为抽象的艺术门类,创作者要掌握创作技巧,领悟艺术精神并非易事。学习书法的方式也是书论家们的经典话题。回顾书法史,似乎每个成功的书家都留下了勤学苦练的逸闻趣事,“墨池”“退笔”之类故事几乎是他们传记的必备章节。
毋庸赘言,勤学苦练固然是取得艺术成就的必由之路,但是书法艺术抽象玄妙、难以言说的规律也并非练习就能获取,苏轼对这一点就有清醒的认识。《次韵子由论书》:“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5]426不善书法显然是苏轼的自谦之词,其后苏轼说对书法的规律认识深刻却是真实的,认识的途径是“通其意”,如果做到了通其意,就可以不用学了,也就是学有所成了。《跋君谟飞白》又道:“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世之书篆不兼隶,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谟真、行、草、隶,无不如意,其遗力余意,变为飞白,可爱而不可学,非通其意,能如是乎。”[3]7808苏轼认为蔡君谟真、行、草、隶皆成就不凡的关键也在于通其意,即通晓书法艺术规律。蔡君谟偶转飞白书,也能立刻融会贯通。此处,苏轼又强调了“不可学”,不可学指的是蔡君谟飞白书体。飞白书体笔画之间夹杂着丝丝点点的白痕,给人以灵动飘扬,不可捉摸之感,这源于书写中用笔力度、速度之巧妙变换,灵活运用枯笔,其规律更难以掌握。
苏轼与蔡君谟通其意的诀窍都不在于学。如果不是学,那该是什么?这不禁让人想起禅宗常说的“悟”,禅宗认为悟是获得禅宗最高精神的不二法门,而非“渐修”,刻意苦学。通其意不是书体外在点画末节,而是对前人各种书体特征、书法艺术气韵等抽象精神深入理解,与禅宗的悟完全相合。苏轼与黄庭坚讨论草书学习之法,也曾说 “学即不是”[3]7851,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唐人书法尚法度规矩,学是获取法度规矩最重要的途径。不过,据苏颂《题送■光序》记载,唐代跟随陆希声学习书法的僧人■光就曾说:“书法犹释氏心印,发于心源,成于了悟。”[12]757由此,唐人已经说明悟对于书法的重要性,但是这一理论在尚法度的唐代湮没无闻,甚至还要依靠宋人偶然记录保留下来。苏轼对于悟书法则有更加深入的论述。
余闻此经虽不离言语文字,而欲以文字见、欲以言语求则不可得。篆画之工,盖亦无施于此,况所谓跋尾者乎?然人之欲荐其亲,必归于佛,而作佛事,当各以其所能。虽画地聚沙,莫不具足,而况篆字之工若此者耶?独恐观者以字法之工,便作胜解。故书其末,普告观者,莫作是念。(《跋李康年篆心经后》)[3]7839
此跋写在朋友为亲人祈福抄录的《心经》之后,苏轼论述字之工与不工,就自然而然以禅宗观念说理。苏轼先阐明《心经》依赖文字而存,但如果仅仅关注文字语言本身,那么就无所获得。同理,篆书工拙与否也不能从篆书笔画来看。
为了深入论证这一理念,苏轼引了佛经典故。一是《法华经·方便品》:“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13]8二是《景德传灯录》卷十一:“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云:‘赤土画簸箕’。”[14]757“如何是和尚家风”是禅宗追问佛法第一义的常见句子,答者就回应以童子聚沙为佛塔近乎游戏之法也是成佛之途。李康年抄录《心经》的目的是追思亲人,只要达到这一目的,哪怕像童子聚沙为佛塔游戏一般不计形式之工拙也是值得赞许的。由此可知,苏轼评价书法工拙的标准是作品是否实现表情达意的目的。
论述过程中,苏轼一转再转,除了讨论书法之工拙,还论证了自己创作跋文也不当以文字见之。此方式极似华严事理圆融的表现手法,因为“事理之障,障他不得”,所以短短百余字的跋文中多个维度的事情竟然都被他说通了。也正如《石门文字禅》所说:“东坡盖五祖戒禅师之后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而成文。盖非语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从般若中来,其何以臻此?”[8]4033
虽然,苏轼在此文中无意讨论李康年善篆书的原因,却在为李康年写的《小篆般若心经赞》补充了答案。
草隶用世今千载,少而习之手所安。如舌於言无拣择,终日应对无所问。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墙壁。纵复学之能粗通,操笔欲下仰寻索。譬如鹦鹉学人语,所习则能否则默。心存形声与点画,何暇复求字外意?世人初不离世间,而欲学出世间法。举足动念皆尘垢,而以俄顷作禅律。禅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处安得禅。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间无篆亦无隶。心忘其手手忘笔,笔自落纸非我使。正使怱怱不少暇,倏忽千百初无难。稽首《般若多心经》,请观何处非般若。[3]2406
苏轼再次使用鹦鹉学舌典故,此举并非偶然,而是颇用了一番心思。鹦鹉学舌出自禅宗六祖慧能三传弟子大珠慧海的经典语录,“如鹦鹉只学人言,不得人意。经传佛意,不得佛意,而但诵,是学语人,所以不许”[14]2267,本意是探讨经教(文字)与佛理之间的关系。苏轼借之比喻书写篆字的困境,分析其原因是“心存形声与点画”,即沉溺于外在有形的点画与有限的语言,其情形就像举手投足都是烦恼而不得解脱然后作禅定、戒律以求超脱,但是一旦停止,一旦不作,就重新陷入困境。解决困境的方法只有“出世间法”,也就是佛教达到超脱生死境界之法,也是修习目的所在,喻指点画、形声之外的语言与书法抽象的艺术规律。
怎么才能获得出世间法,获得点画之外、形声之外的艺术规律呢?苏轼认为李康年知道方法,他的方法是“心忘其手手忘笔,笔自落纸非我使”,末尾 “稽首《般若多心经》,请观何处非般若”,苏轼再次提示李康年的答案也见于《心经》,《心经》有“心无挂碍”之语,也就是说李康年做到心无挂碍,摆脱了有形点画束缚,最终参悟到书法艺术的规律。
古人常有偶见某物而顿悟书理之事,苏轼《书张少公判状》:“雷太简乃云闻江声而笔法进,文与可亦言见蛇斗而草书长,此殆谬矣。”[3]7796尽管苏轼指出二人之说颇为荒谬,也并未全然否定顿悟书法的方法。
苏轼《书张长史书法》:“世人见古有桃花悟道者,争颂桃花,便将桃花作饭吃。吃此饭五十年,转没交涉。正如张长史见担夫与公主争路,而得草书之法。欲学长史书,日就担夫求之,岂可得哉?”[3]7872开篇就用了经典的禅宗故事:“福州灵云志勤禅师,本州长溪人也。初在沩山,因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来寻剑客,几逢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到如今更不疑。’祐师览偈,诘其所悟,与之符契。”[14]745志勤禅师开悟的禅机是桃花,比喻张旭开悟草书的禅机是担夫争路,志勤禅师领悟到了禅宗第一义,桃花不过是指示禅理的工具(第二义),也正如张旭领悟到了草书的规律,担夫争路仅是指示草书之法的工具。执迷不悟的人重复志勤禅师,称颂桃花,还把桃花当作饭吃了五十年,这正是堕入了第二义的迷障。愚痴之人执著去看担夫争路,永远也无法像张旭那样开悟草书的真谛。苏轼作此篇的目的也是告诫学书者要破除学习书法外在指示的迷障,其教育方式正是根植于禅宗“言语道断,心思路绝”以及“见性成佛、直指人心”的理论。
禅宗作为佛教一个派别,其典型特征是叛逆,叛逆传统经教文字与坐禅方式,冲破佛教经典文字对思维的限制,更加注重参禅者自身的觉悟心性,如二祖慧可认为:“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14]150,自身就具备佛性,心性与佛性并无差别,只需要观照自身,哪里需要向外寻找?
苏轼熟悉禅宗思维与表达方式,说出“我书意造本无法[5]481就自然而然了,“无法”于禅宗而言正是破除对佛教经典文字的执著,于苏轼而言,就是对前代书法,尤其是唐代过分强调法度的叛逆,“造意”则是自我具备佛性,只须向内寻找,彰显自我书法个性。
苏轼对书法“出新意”非常看重,除了自己创作是“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3]7814,而且是否出新意也是其评价书法的重要标准。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说“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5]738,盛赞颜真卿书法出新意与变法度。不仅如此,苏轼《跋叶致远所藏永禅师千文》评价以先祖王羲之书法为圭臬,被人认为“甚有家风”的智永书法作品,言“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刑,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3]7789,哪怕法皆是王氏旧法,苏轼也认为其中难以捉摸的“意”已经突破了王氏规矩。
三、以书悟禅:点画亦是禅机
苏轼认为禅宗顿悟方式与获得书法艺术规律有相通之处。更进一步,苏轼指出书法字画也是顿悟的禅机。
怀楚比丘,示我若逵所书二经。经为几品,品为几偈,偈为几句,句为几字,字为几画,其数无量。而此字画,平等若一,无有高下,轻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画之中,已现二相,而况多画!如海上沙,是谁磋磨,自然匀平,无有粗细。如空中雨,是谁挥洒,自然萧散,无有疏密。咨尔楚、逵,若能一念,了是法门,於刹那顷,转八十藏,无有忘失,一句一偈。东坡居士,说是法已,复还其经。元祐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若逵所书经后》)[3]7895
这篇题写在若逵和尚书抄写经书后的跋文非一般跋文语言自由、字数随意,反而句法排列森严,除去篇初与篇尾交代缘由的文字字数不等外,其他字数都规整严谨,一句四字。观其内容,几类禅师说法文字。究其文体,当属一篇偈文。
偈本来是印度佛教经典中的诗歌文体,是佛经中赞颂词。佛经汉译之后,虽然模仿中国诗歌四、五、六、七言诗歌形式,却依然受到佛经原文限制,变成一种既非诗又非文的不易归属的文体。唐宋两代,诗歌艺术空前发展,偈的诗学特质不断提升,宋代文人与僧人就创作了不少诗偈。
苏轼这篇偈文呈现出早期偈文押韵不甚严密的风格。不过,部分句子末尾如“一”“细”“密”“偈”的韵脚相隔虽远,也相对一致,不知是否是苏轼有意安排?“海上沙”“空中雨”两句对仗明显,比喻用得极妙,“经为几品,品为几偈,偈为几句,句为几字,字为几画”数句也极富韵律感。诗人苏轼似乎不能容忍质木无文的偈文,创作颇有匠心独运之处。苏轼使用这种不同一般跋文的形式,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本文交际对象为僧人,用此形式投其所好,僧人读之容易且熟悉;其二,本文书写在佛经文字之后,与前文佛经内容有所照应。
僧人抄写佛经示崇佛之意,循例应用正书。苏轼并没有言明若逵使用何种书体,“平等若一,无有高下、轻重、大小”之语,或是一语双关,一关若逵正书字体工整,一关佛教平等无差别境界。为什么能够达到平等境界,因为“忘我”,即佛教之“无我”。南宋楼钥记载苏轼文中所谓“二经”,一是《无量寿经》,一是《妙法莲华经》。《无量寿经》就曾论述“无我”,“於其国土,所有万物,无我所心,无染著心,去来进止,情无所系”[15]273,即对一切境界不思量,无所分别,不执著。接下来,苏轼又以海上沙粗细均匀、空中雨无疏密之分来表现无差别的状态。最后,又希望二人能够在“一念”“刹那”之间,了悟到“平等”与“忘我”法门,顿悟成佛,表述几近说法末尾僧众菩萨觉悟证果的套语。苏轼仿佛一位高僧,借若逵所写的两篇经文文字,宣示佛法大意。
禅宗开悟形式不拘一格,万事万物皆可做悟道禅机,苏轼以若逵书法说法,在禅宗史上也独树一帜,而且他巧妙地把书法之道与佛禅之道结合起来,这既体现书法创作的心理机制与禅宗开悟机制相通之处,也是苏轼书法与禅法修养深厚的体现。
四、以禅评书:禅语阐释书家书风
苏轼极其擅长说理,说理则需要大量论据。因他熟读禅宗文献,所以评论书法常取材其中,往往能把常人难言的书理玄妙之处道尽,也极大丰富了书论的文化资源。
与书法教育范式类似的是,苏轼阐释王安石书法也用了禅宗话语。《跋王荆公书》:“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3]7799苏轼说王安石获得了“无法之法”也是禅宗典故。五代宋初,释延寿作《宗镜录》卷十五:“无法之法,是名真法。”[4]498唐代陆元浩《仙居洞永安禅院记》:“由是多子塔前,迦叶授无法之法。震涅国内,达摩传非心之心。”[16]9100所谓无法之法就是佛祖拈花、迦叶微笑顿悟的情形,也就是说王安石获得的是不能通过语言文字描绘的书法之道。更进一步,苏轼认为王安石书法不可学,学了反而掉入无法获其精神的困境。苏轼从佛教典籍借来形容王安石书法的“无法之法”,后来发展成了评价书法的固定语汇,如元代书论家郑杓《衍极》所说“太白书得无法之法”[2]458,说李白的书法也得到了无法之法。
苏轼《跋鲁直为王晋卿小书尔雅》言:“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3]7852传统书论认为书法家性情与书风必然呈现字如其人的高度统一。不过,苏轼认为黄庭坚书风与人生态度却呈现了严重对立与矛盾,也就是山谷字不似其为人。
苏轼所说的“平等观”即无差别之意,“欹侧”即歪斜,就是说黄庭坚书法具有字画夸张、结构奇险、字体倾斜的特点,如此矛盾的原因或许就在于“以真实相出游戏法”。黄庭坚精研禅理,还被列入黄龙法嗣,佛教真如本体、唯一真实的宗教意识已经深刻影响其生命价值,然而真实相并不能通过拘谨认真的态度领悟,只能通过戏谑自由的方式获得,表现在书法字体上就是带有游戏意味的欹侧字。黄庭坚指称晦堂祖心“脱略窠臼,游戏三昧”[1]851,用之形容其书法风格也甚是恰切。苏轼在传统文化资源与书论语境中,似乎不太能够找到合理解释黄庭坚矛盾性的论据,禅宗话语则提供了有效阐释,且符合黄氏一贯的思想旨趣。
五、结语
苏轼是一位书法大家,且对书论颇有贡献,但其书论文字并非专著或者论文,而以诗歌、序跋为主。宋人诗歌交际性是宋代文学研究的经典命题,序跋仅从文体而言,就天然带着交际应酬的功能,更兼序跋在宋代成为风尚,创作成果蔚为大观。苏轼本人也是序跋爱好者,书论序跋多达一百余篇。因此,研究苏轼书论不能回避文体、交际等个性特征。关注这些因素,才能回应苏轼书论矛盾之处。以是否学前代法度问题为例,据前文所举,似乎可以得出苏轼主张不学、不可学,学即不是,实则并非全然如此。润州柳氏二位外甥柳闳、柳辟求取苏轼书法,苏轼答之以《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其一:“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5]1087其二:“一纸行书两绝诗,遂良须鬓已成丝。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5]1088第一首首联以智勇、怀素二位书家退笔成冢,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勉励后辈学习书法应当用功苦练,后两句又以柳家同姓柳宗元的典故告诫二人多向他们擅长书法的父亲柳瑾学习。第二首以唐代褚遂良“须鬓尽白”练习书法艰辛刻苦以及柳公权劝谏穆宗皇帝习书心意应纯正不偏的道德原则谆谆善诱。《题二王书》说“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3]7765,也强调努力练习对书家的重要意义。为何有此矛盾?柳家后辈以请教姿态向书名文名俱显的苏轼提问,就要求苏轼必须回归长辈身份,以正统道德原则作答。如果苏轼答之以“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对于还在学书阶段的晚辈就毫无意义,于苏轼而言,又不合身份。
苏轼一生经历复杂,交往对象来自社会各个阶层。苏轼书论大都是针对具体对象写的既契合其身份,又符合其学识的交际文字。如:前文提到写给僧人了性的《六观堂老人草书》,以《金刚经》梦幻泡影论述创作草书的必要性和书法的精神愉悦内涵;《书若逵所书经后》用偈文形式,又以佛理赞书写者书法作品佳妙之处,明显受到了交往对象与跋文对应正文内容限制。又如:同是佛家“平等观”,苏轼既拿来赞誉若逵字画若一,又用来称赏黄庭坚的欹侧字。
要之,调和苏轼矛盾言论,抑或寻章摘句建构苏轼书论体系并非易事,或许细读苏轼每一篇书论,更有助于认识一个真实的苏轼,了解苏轼书论的思想文化本源及其真正价值。
注释:
①《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引《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与《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两段文献不切文意,当引《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鹆跦跦,公在乾侯”。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学语”条下“鹆”注引《幽明录》:“荆州有参军,五月五日剪鹆舌教学人语,无所不名。参军弹琵琶,鹆每听移时。”因此,鹆与苏轼文中“鹦鹉”“秦吉了”一致,皆为擅学人语的鸟类。南宋杨简《慈湖诗传》注《召南•鹊巢》引楼钥语“鸤鸠之为鹆甚明,浙人呼为八哥儿,川人呼为阿八。”明代戴冠《濯缨亭笔记》:“鸟之能言者多称哥,如鹦鹉曰鹦哥,秦吉了曰了哥,鹆曰八哥。”由此,“鹆”或俗称八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