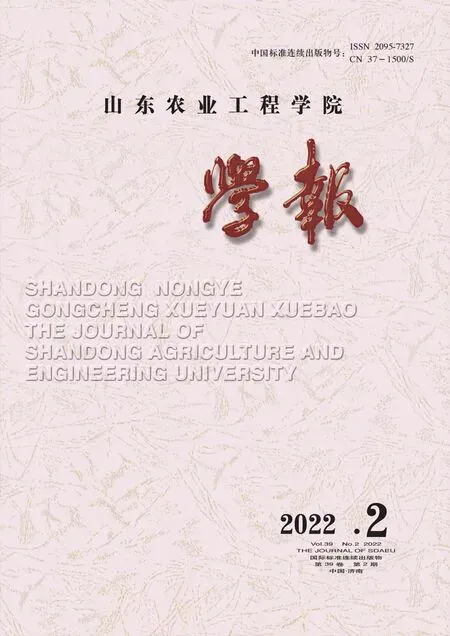安徽大别山片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模式创新
余茂辉,潘致霖
(1.皖西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2.武汉轻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23)
安徽大别山片区总面积约2.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380万人,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的农村贫困人口308万人,贫困发生率为22%,高出全国10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7.5%[1]。因其自然和历史的因素而具有独特的贫困特征,生态条件、扶贫减贫措施与其他地区存在差异,传统大水漫灌式的扶贫模式在该区域效果不佳,对于彻底解决片区根深蒂固的贫困现象收效甚微。2013年以来,针对区域贫困的特点,片区各县因地制宜的探索创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模式,其模式的创新为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1 安徽大别山片区总体贫困特征
大别山片区山地主要部分海拔1500米左右。片区地理位置差、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区域性贫困具有连片和顽固的特征。对该区域的贫困具体特征特点的研究是区域精准脱贫 “对症下药”模式创新的基础。
1.1 连片特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大别山安徽片区的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受制于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其工业发展制衡因素较多,农业则以山地为依托,有中药材等特色农业及其初级加工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精准扶贫元年(2013年),片区总人口1443.23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298.46万人,当地人均生产总值为12075.75元,地方财政收入只有79.19亿元,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523.74元,均低于省内平均水平,且总体经济发展状况低于同期全国平均值[2]。连片特困区集老、少、穷等特点,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片区整体市场投资过冷,地区税收绩效不高,政府和市场的双轮驱动作用动力不足。片区基础设施不足,教育、医疗水平低,人民生活水平难以得以较大的提升,从而导致了较严重的劳动力外流,进一步导致了片区贫困的恶性循环,陷入“贫困陷阱”。
1.2 连片特困区贫困覆盖面广、程度深
大别山区域内部贫困具有覆盖面广、程度深的特征[3]。在安徽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包括大别山区和皖北西部、涵盖了四个市、15个县(区)的地区,有12个县属于国家级连片特困县,扶贫对象基数大,其产业结构和增收渠道较为单一,农业结构调整制约因素多,农户经营性收入增长难度大,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外出务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积累少、负债多,产业形态特征不完备,县内主导产业类型中主要依赖自然资源、人文资源进行初级产品的加工。同时片区内诸生产要素中介市场不健全,自身发展能力严重不足。贫困的深度和广度在片区内导致了严重的人地矛盾和人与自然的矛盾,对山地无规划的的垦荒行为使得片区内脆弱的生态环境极易受到破坏,环境恶化导致的农业减产又进一步加剧了垦荒行为。由于当地经济状况落后,农村电力设备陈旧落后,城乡电网覆盖不全面导致片区内能源供应能力不足,保障基础用电尚且存在难度,工业的发展更是困难重重。虽片区内存在一定的矿产资源,如金矿、铁矿、铅锌矿等,但片区内羸弱的道路交通系统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不足以支持此类产业的发展。在这种种条件制约之下,2012年,片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的农村贫困人口300万人,贫困发生率超过20%,远高出全国12%的水平[4]。
1.3 连片特困区自然灾害频繁,返贫现象突出
大别山地形起伏大,自西向东夹于桐柏山和霍山(即皖山)和张八岭之间,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天然隔断。在区域内所有38个县市中,地形呈现出破碎化即山地、丘陵面积超过总面积50%的县有33个,比例高达86.8%。而作为深度贫困地区,大别山安徽片区内水利建设等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水利工程建设十分不完善,水资源利用和开发保护构架并不合理;同时由于片区地处于全国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同经济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区内受暴雨洪涝等自然灾害影响更大[5]。随着扶贫开发的深入,多个地区出现返贫现象,农民生活水平难以得以实质性提升。一些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的农户产生对政府扶贫工作的依赖心理,而这种心理使他们止步不前,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参与度不高,不愿发展自身能力,很容易扶贫结束即返贫。
1.4 连片特困区基础建设水平较低
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因其山区、丘陵低洼的恶劣地势导致区域内道路状况处于较低发展水平,道路质量低下。统计显示,片区内县域间有高速公路联通的占全部行政县的60.5%,有铁路联通的仅占52.6%;而全联通比例更低,分别为为39.5%、21.1%[6]。由于基础交通建设水平较低,农田和水利设施存在着较大的建设难度,可用土地资源的短缺严重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由于当地电力和通信设施落后,普遍存在农村电网改造不彻底、供电质量差等现象,基层信息化服务水平较低,对群众日常的生产生活都有着较大的影响;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当地配套设施建设欠缺,地方财政压力较大致使教育、医疗、住房三大民生投入不足,城镇化进程滞后,基层卫生医疗本领弱,妇幼保健程度较低。较低的基础建设水平导致片区内对外通道不通畅,区内路线网络不完善,河流水运发展严重滞后,农村、城乡客运水平低,安全应急保障不足。由于专项资金的匮乏,交通建设资金缺口大,片区内道路普遍存在着重建轻养现象,从而导致片区内交通不便,且与外界联系不紧密,加剧了片区贫困的“边缘锁定”效应。
2 大别山片区区域贫困形成机理解析
2.1 边缘锁定效应
安徽省大别山贫困地区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交界处的边缘,是区域经济的分水岭,区域行政区划远离省级行政经济中心。由于缺乏利益整合与协调,资源及产业缺乏有效的分工,导致关系重叠、区域重合、重复建设、产业雷同等问题。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上都存在着分化的特征。在行政指导下,根据省产业链布局完整、邻县产业同构、产业因素竞争等因素,将产业选择和产业链布局定位为三个产业发展方向,导致产业资源的浪费,加剧了地方资源稀缺的问题。相对丰富的资源禀赋受到交通条件和位置边缘化的限制,形成了富饶型贫困与结构性贫困的相互存在[7]。这是因为大别山地区在经济、文化、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都很落后。区域行政区发展程度相似,差异较小。周边边缘、地理位置、经济活动分散点和城市分布决定了该区域的内生发展模式,难以融入区域产业链的分工,难以接受有限的城市中心辐射效应。此外,在城市群虹吸效应的影响下,大别山地区的资源通过行政渠道、产业渠道、公共服务渠道和资源渠道流向三省的省会城市。这种工业和公共服务布局导致贫困县资源通过工业渠道外流,交通条件差进一步加速了人力资源外流,边缘贫困难以打破。
2.2 贫困陷阱效应
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有3位经济学家揭示了“贫困陷阱”的产生根源,他们分别是:美籍爱沙尼亚经济学家纳克斯于1953年提出的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于1956年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于1957年提出“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8]。这些理论认为,制度因素、人力资本、社会经济分层、社区效应和代际传播加强了区域贫困的聚集,陷于了一个难以被内生发展力量突破的“贫困陷阱”,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以致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只有当收入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时,他们才能突破贫困陷阱。
大别山位于省际边缘区,行政地理和物理地理的重叠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区域发展趋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作为一个综合性领域,虽然自然文化资源丰富,但基础产业密集,同时都很落后,公共服务共享能力不足,形成了整体贫困集聚的发展模式。由于安徽省大别山地区外边缘的多个中心以及资源竞争和收入扩散的市场地位,在市场竞争中,该地区本身并没有形成一个分化的市场,市场的多个中心难以扩大。从多个细分市场来看,已成为市场真空区,导致安徽省大别山在竞争中的薄弱地位。在市场互动中,它并没有得到自己的增长空间,而是成为了一个发展真空。“真空区”并不意味着该地区没有发展力量,而是发展潜力隐藏,难以实现。同时,由于大别山片区是国家连片贫困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属于深度贫困、发展滞后地区,在综合因素的影响下,贫困的自我加强机制和负反馈效应导致了片区整体经济情况长期处于低水平恶性循环陷阱中,形成恶性的路径依赖[9]。
2.3 PPE怪圈
Grant J P.(1994)提出了“PPE 怪圈”,即人口(Population)增长、贫困(Poverty)和环境(Envi-ronment)退化之间的恶性循环怪圈[10]。在安徽大别山区域,由于贫困导致片区内对人力资源的依赖强于其他地区,而人口数量的过度增长又会导致对当地资源的过度开发;资源的过度开发,又带来了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贫困人口由于生活需要及自身较低教育水平所致的淡薄的生态观念,使其不曾考虑环境破坏之恶果。而环境恶化又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致使生存条件更加恶劣,人们更加贫困。贫困又加剧了这种循环,使得陷入其中的人们无以解脱。贫困、人口与当地脆弱的环境互为因果关系,贫困、人口、环境形成互为因果关系,贫困导致人口增长和环境脆弱,而人口增长又加剧贫困和环境恶化,环境的脆弱进一步加深贫困,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的生计模式难以短期彻底改变。
3 大别山片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模式创新
脱贫攻坚战的核心是贫困户增收问题,更好地帮助贫困地区人们增收需要精准有效的扶贫模式作为指导。以往的实践经验证明,“一刀切”的扶贫模式在解决贫困问题上效用不甚明显,甚至会挫伤贫困户的脱贫积极性。基于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差异,在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的精准扶贫精神指导下,片区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深度探究当地贫困形成机理,在此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帮扶工作,创新性地探索出一系列成熟的精准扶贫与脱贫模式,以突破贫困的边缘锁定与路径依赖[11]。
3.1 科技精准扶贫模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临泉县、太湖县、金寨县和利辛县为代表的安徽大别山连片特困区“边缘县”,以产业发展为核心,通过精准赋能扶贫产业、精准选派科技人才、精准统筹科技资源这“三个精准”为导向,以“挂包帮”、示范基地带动、技术培训推进、合作社科技扶贫等方式参与定点帮扶,提升贫困户科学种养水平[12],从根本上扭转贫困地区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提升了地区资源开发水平和劳动生产率。
由于边缘锁定效应影响,临泉等安徽大别山连片特困区“边缘四县”存在着借外力扶贫易导致集体返贫的现象,而在科技精准扶贫模式的助力下,边缘县区可以突破交通和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的制约,获取及时有效的市场信息,合理规区域内的产业布局,打破其原有的经济内源性发展格局,充分利用先进的生产方式和高新技术,加快现有资源深度开发和有效利用,学习技术、依靠人才,从智力支持助力产业发展、抓典型树标杆、推进科普培育乡村未来等多方入手,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科技精准扶贫模式,走出了一条科技精准扶贫的新路。安庆市太湖县所采用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科技精准扶贫模式构建起“村有当家产业、户有致富门路、人有一技之长”的“三有”型稳定脱贫新模式带动贫困户稳定增收,是边缘四县中科技精准扶贫的典型[13]。在科技扶贫模式的指导下,四县在提高贫困地区人口总体素质的基础上,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发展目标,采取合理的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法,实现人才、资金、信息、技术、教育培训的整合,改善了生活环境,完成了依靠科学技术从简单扶贫向发展扶贫的转型,提升了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
3.2 金融精准扶贫模式
金融投入打破了固有的贫困、人口、环境的恶性循环“怪圈”,在大别山区的扶贫攻坚战中,金融扶贫是打好解决连片特困地区根深蒂固贫困现象组合拳秉要执本的重要措施,阜南县、霍邱县、寿县、岳西县、望江县采取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精准“滴灌”金融活水浇开致富花,开启了脱贫致富的“金钥匙”,成为皖西五县金融精准扶贫的典型代表。制约皖西五县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金短缺,而不健全的资金使用机制使得当地贫困现象雪上加霜。在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的指导下,皖西五县利用市场化手段,通过采用小额信贷、“政银保联合”分散风险、“征信+信贷”等方式发挥资金杠杆效应[14],提高扶贫资金的 “精准度”,把那些误配和错配的扶贫资金投向诸如经济发展以及促进人力资本和生活水平提升等项目上,健全地区金融机制,同时投入大量的专项扶贫资金,主要用于提高贫困地区的“自我造血功能”,并构建了金融扶贫长效工作机制,消灭了贫困赖以生存的土壤。同时,安徽省农业银行紧紧把握历史使命,积极推进关于涉农、扶贫金融服务信贷业务尽职免责制度有效落实,也为奋战在脱贫攻坚前线的工作人员免去了后顾之忧[15]。农村信用社等农村合作性金融机构有效提升了扶贫瞄准度,引导扶贫资金流向贫困人口,调动了贫困户的积极性,使扶贫绩效得到有效提升。由于金融业务和金融政策的双重作用消减了地区贫困怪圈恶性循环的影响,2019年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为20616.20元,较2013年增长1.77倍,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扶贫脱贫思想指导下金融扶贫模式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优势。
3.3 特色产业精准扶贫模式
特色产业扶贫模式是在市场规律的指导下,依靠当地资源的特点,在特定的乡镇、村等居民区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同时,依靠当地龙头企业培育区域经济的内生发展力量,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结合当地实际和贫困户意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解决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产业扶贫项目同质化问题;提供技术培训、信息共享和渠道建设支持,促进特色产业发展,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突破区域贫困积累,帮助贫困家庭摆脱贫困。
在特色产业扶贫模式的指导下,片区内的颍上县和宿松县根据市场需求和自然禀赋,大力发展稻虾养殖、油茶种植等特色产业和芦笋套种羊肚菌、大球盖菇、姬松茸等珍稀产品,支持和引导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充分发挥龙头企业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统筹区域产业规划,形成了布局合理、功能相对完善、优质高效的商业体系,不仅保证了贫困家庭的就业,提高了人均收入,而且提高了企业效率,提高了企业实力。以宿松县为例,该县北为山区,南邻长江,处于山地与河流过渡区。在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因户制宜的特色产业扶贫模式指引下,立足于本地资源禀赋,以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为代表的新农人领奏“致富曲”,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16],找到了绿水青山的“变金术”,发展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遏制了贫困导致的环境退化,做到了在保护自然的同时脱贫致富;而颍上县通过坚持扶贫开发与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保障性“输血”与持续性“造血”相结合,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产业项目开展扶贫。由于两县基础条件较好,同时在合适的政策支持下,颍上县和宿松县成为安徽省大别山片区内脱贫效果最好的区域。据统计,2016年至2019年,颍上县实施特色种养业扶贫到户项目29.6万个,享受到户项目贫困户达14.67万户;全县脱贫42849户108702人,78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贫困发生率降至0.26%[17]。
3.4 旅游精准扶贫模式
旅游产业具有从上游到下游一整条极长的产业链,一旦发展起来便可牵一发而动全身,带动整个地区共同发展,进而做到盘活当地经济、助力农民增收。传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一般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别山区由于森林海拔差异大,植被变化明显,高度从400多米至1700多米不等,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森林景观[18],拥有实施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得天独厚的基础。
旅游扶贫模式虽被广泛应用,但由于连片特困区因种种自身原因,如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经济发展模式落后等,很难整合自身资源充分发挥旅游扶贫模式的扶贫成效。但安徽省六安市却在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的指导下打破了这一“魔咒”,做到了“精准发力”,成为该模式下的典型代表。六安依山襟淮,承东接西,区位优越,境内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众多,旅游资源丰富。在引入旅游精准扶贫模式之前,当地贫困户增收渠道单一,除种植和劳务外再无其他收入,贫困陷阱效应突出;由于二三产业孱弱,当地消化大宗农业和旅游资源能力较差,同时当地薄弱的基础设施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快速流通。而六安市实施旅游扶贫最大的特点是做到了“精准扶贫”,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激发出贫困户想要脱贫致富的动力与潜能,把政府、景区、企业、协会、贫困户多方力量有机结合起来,在对区域内优势资源进行精准分析的基础上,全力发展“绿色(森林)、蓝色(水库)、古色、红色(红色旧址)”旅游,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4种旅游精准扶贫的模式:以金寨八湾村乡村旅游集聚区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以金寨县农村小院品牌联盟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以金寨县城郊的小南京生态农庄为代表的“邻里互助型”和以万佛湖景区为代表的“景区帮扶型”旅游精准扶贫模式[19],并与农业、林业、文化等相关产业和行业融合发展,形成了一整条旅游服务产业链,打破了贫困的自我加强机制和负反馈效应,使具体的扶贫措施得以定向精准辐射贫困地区。2019年六安市人均生产总值为2013年同期数值的1.53倍,六安的旅游精准扶贫模式为其他贫困地区发展旅游摆脱贫困提供了新参考。
3.5 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模式
参与式整村扶贫模式突出以人为本、以村为单位,准确定位到贫困户,其特点是由贫困户全程参与项目的选择、实施、管理和监督。在政府扶贫基金的指导下,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解决最突出的问题,重点开展综合项目,帮助贫困村改善经济、文化和社会,增加扶贫发展的综合收入,有效地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达到”集小钱办大事“的目的,最大限度地确保了贫困人口得到帮扶,使得贫困工作的精准度得到了较大的提高[20]。
潜山县具有安徽大别山片区内的独特情况,该县依托天柱山品牌优势,以整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将精准扶贫与乡村旅游相融合,以走出一条旅游引领的扶贫新路为指导。但由于该县资本运作水平相对较低,特色产业发展不足,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支撑和就业前的教育培训,导致该扶贫道路越走越窄。该扶贫模式实施后,潜山县针对贫困户发展产业主观意愿弱、生产方式粗放单一、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务工的情况,通过推动土地流转增值农户土地收益;同时通过制订发展种养殖业奖补政策,鼓励支持种植大户流转农户土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实现了劳动力就地转移,使贫困户通过地租和务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以跳出贫困陷阱;在此基础上引导技术传授,提升劳动力素质,增强创业致富本领,并积极搭建就业平台,解决务工就业难题,最后支持兴办实业,积极融入区域产业链分工。在政府引导、群众参与、科技投入、项目配套、逐步推进这一揽子计划的实施下,潜山县找到了正确的脱贫道路。2013-2019数据显示,该县人均生产总值增幅为1.72倍,其中2013-2017五年的年人均生产总值增幅为1.32倍,而2018-2019年人均生产总值增幅更是为1.23倍,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为1.60倍[21],表明该县扶贫开发绩效已开始进入逐年上升的正向循环,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模式的实施给该县域带来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新思路。
4 结语
2019年末,安徽大别山片区贫困发生率由2013年的9.1%降至0.16%,2020年4月,安徽大别山片区的金寨、临泉、阜南、霍邱等6个贫困县脱贫摘帽,标志着大别山片区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基本解决,成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精准扶贫是解决集中和连续贫困地区整体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安徽省大别山片区各贫困县根据自身特点和贫困状况,匹配科技、金融、特色产业、旅游业、参与式整村推进的模式扶贫,提高了连片特困地区农户的 “自我造血功能”,使生产经营模式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增强了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能力,并唤醒了贫困家庭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意识,是对传统扶贫模式创新,也为乡村振兴战略治理机制形成、治理成效获取、治理经验积攒打下了稳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