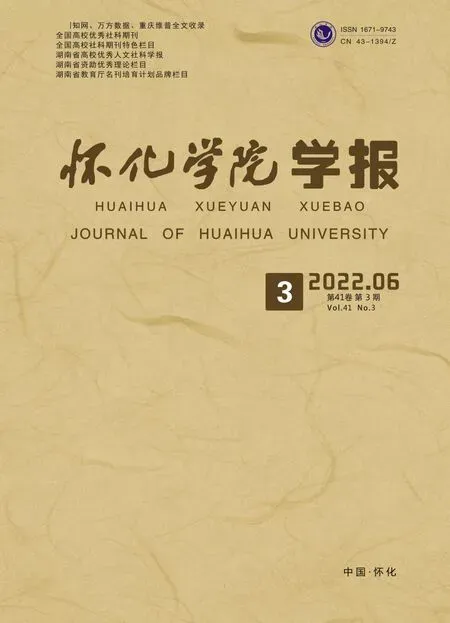李端棻近代教育事业轨迹探析
李心雨, 马国君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引言
李端棻(1833—1907) 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创者之一。近年来,学界对李端棻的研究有上升之势,并取得了重要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系统整理李端棻从入仕到回乡后的近代教育事业轨迹,可将其教育事业经历划分为初始阶段、转变阶段和成熟阶段。考察李端棻教育轨迹的阶段性特点,对全面认识李端棻与中国近代教育关系的问题具有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二、李端棻近代教育事业的开端
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运动被平息,中国与英法诸国并无大战,洋务运动正在进行,清廷似有稍稍恢复之迹象。久居京师、久浸儒学的李端棻难免沉浸在对清廷兴旺的期盼之中。他如普通读书人一般参加科考,可见其对参与清廷当时的政治建构很有兴趣。
同治二年(1863),李端棻考中进士,而后“选庶吉士,授编修,为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敦衍①所器”[1]12739。同治六年(1867),倭仁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与曾国藩、李棠阶等人讲求宋儒之学,反对聘请西人教习入同文馆教授天文算学,“谓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1]11737;而罗惇衍信奉宋明理学,对程朱学派尤为推崇[2]。可见,新手官员李端棻颇受倭、罗二人赏识。种种迹象之下,也可推测李端棻不仅在儒学上造诣颇深,也定是未在明面上涉猎和沾染西学。否则,在帝王都“敬惮”的顶头上司倭仁手下还不知进退,就未必能有顺利的仕途了。
在这种环境之下,李端棻很快就被培养成了一名按照传统模式工作的合格官员。在翰林院期间,李端棻曾典山西、顺天乡试[3],逐渐开始接触教育工作、积累教育经验。同治十一年(1872) 五月[4]117,在翰林院学习许久的李端棻终于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教育经历之一——出任云南学政。学政一职是清廷在各省安排的管理一省教育工作的文教职位,其本职工作即主持院试、岁考、科考、优贡试、拔贡试等考试;核查生员的道德品行;考核府州县学校的教职,会同督抚确定黜陟;搜罗刊刻书籍,或者检禁书籍;弘扬儒教,所以关系一省的士习文风[5]。李端棻到达云南后,也恰恰是按照这样的传统文教模式进行教育工作的。总体而言,李端棻此时的教育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家大势、教育经历、教育制度和官场环境的影响,但是却也与当时西南地区的军政形势相关:
其一,咸同年间继承了明清两朝经略西南的手段,即“以政治军事为干预先导,以经济商业为渗透手段,以文教融合为辅助策略”[6],力求教化不识中原文明、不听中原号令的西南土著的边疆治理模式。同治一朝试图将这种模式继续运用下去,幸运的是也得到了一定的治理成果——西南地区军事平乱状况形势大好,文教治边阶段也即将提上日程。具体来说,李端棻出任云南学政后,恰逢清廷平定云南少数民族起义出现转机——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大理克复。大理是云南少数民族起义军领袖杜文秀的盘踞之地,在未能攻克大理之前,清廷从未间断派遣学政前往云南任职,但几任学政均因克复地区并不理想而未能做出立足全省的文教政绩;自大理被攻克以后,云南全省肃清在即,从中央到西南地方都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云南全省的战后恢复工作上,文教更是重点恢复对象。因此,李端棻出任云南学政的意义也就隐含了抚绥地方、医治战争创伤、协助恢复西南社会秩序的职能,学政工作本身已经成了边疆治理的一环。值得注意的是,云南少数民族起义历时十八年之久,英、法在此期间均试图向云南进行渗透,马嘉理事件即典例。清廷一旦丧失对云南的控制权,中国的西南大门很可能洞开,外来势力的渗透则会愈加深重,甚至威胁到中国南方各省的整体安全。因此,在使用军事手段平息整个云南省的叛乱之后,除了必要的经济扶持手段,必然要用儒学的教化力量再次将各民族凝聚在一起,延续儒学精神文化纽带作用,避免国外意识形态的过度渗透。国内外情势如此复杂,政治能力尚不老练的李端棻自然要按照上位者的规划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工作。
其二,李端棻任云南学政期间,与岑毓英、刘岳昭等有政绩的云南官员多有交集,深受影响。换言之,云南官员的治理思路是经过群体考量的,相关治理方案始终处于清廷划定的范围之内,这直接影响到了李端棻的学政工作。同治十一年十二月,清军“克复大理府城,首逆伏诛,群酋尽灭,全郡肃清”,同治十二年 (1873) 五月云南省一律肃清[7]104,112。可见,同治十一年末至十二年五月已为战争扫尾阶段;李端棻、岑毓英及一批官员及时将精力放在文教工作上。同治十二年(1873) 三月初三,李端棻、岑毓英等共同上奏《军务肃清举行文闱乡试摺》[8]329:
臣等伏查滇省自军兴以来停科年久,上届举行庚午正科,带补两科,如额取中,边隅僻壤复睹盛世文明。现在全省军务将竣,士子志切观光,所有本年癸酉科文闱乡试,自应依限于八月内举行,并照部议带补辛酉一科暨将上年钦奉恩诏加额数名一并取中,仰恳天恩。
此折表明云南省本年八月乡试可正常进行,并且官员们申请扩大录取名额,足见战事已去。同时,教育机构亦开始恢复,以大理府为例:同治十二年(1873),巡抚岑毓英、西道陈席珍、总兵杨玉科于大理府太和县县学旧址之上新建敷文书院,云南县知县黄金衔于云南县设立宾兴馆等;同治十三年(1874),大理府西道陈席珍设立道义学,云南知县黄金衔于云南县改建五云书院[9]19-27。教育机构的恢复、科举考试的正常进行,均昭示着社会秩序的正常化。可以说,李端棻的学政工作是按照云南官员共同期待的轨迹进行的,其教育思想和行为完全属于守旧姿态。他按照传统的学政路径“在其位,谋其政”,在云南任上4年有余[5],政绩斐然,得到广泛认同,也无外乎宣统元年云南京朝官请求为其复官[1]12740。
从入仕到出任云南学政是李端棻的近代教育事业的开端,是他所积累的一笔宝贵的教育经验。无论是对地区的战略性把握、对中国社会基层教育的考察,还是对儒学治心功效的把握,抑或是对为官之道的体会,李端棻都有了全新的感悟。此时的李端棻虽然仍将自己的教育工作置于旧式教育模式之下,但是这是基于对情势的分析而得出的最优解,可以真正使得教育为意识形态服务,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助力。传统教育模式虽然已经显示出种种弊端,却为李端棻深入中国教育管理的深层区域打开了缺口。如果没有见习传统教育模式的经历,李端棻未必能够充分了解中国教育现状的优势与劣势,也就未必能够打造较为合理的教育改革蓝图。可以说,李端棻教育思想的发展源于他在传统教育模式的实践中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性认知,以及逐渐开始形成独到的政治见解。也正因如此,李端棻才能够在今后教育制度不得不改变的时候敢于迈出教育改革的步伐。
三、李端棻教育思想的转变
19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产业链进一步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飞速,列强对殖民地的压迫愈来愈强烈,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威胁更甚。19世纪70年代,日本侵入台湾;19世纪80年代,中国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在这种前途未卜的局势之下,李端棻会不会担忧其曾经在西南地区的治理成果化为泡影?清政府在外无强敌武力干涉的情况下尚能依靠云贵大员作战平乱从而控制西南局面、延续传统治理模式。然而,在国外势力不断渗入的情况下,相对平稳的局势就难以维持了。此时,外国势力的威胁已成为影响西南地区安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清廷对西南边疆安全问题的考量已着重聚集在觊觎中国西南地区的外国势力上。这种来自西方的冲击和威胁,正如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 所上 《筹议海防折》[10]159中所写:
今则东南海疆万馀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精准地概括了中国民族所面临的严峻危机——近代中国国力衰微,经济结构落后,文化教育僵化,国防科技力量薄弱,在国际上毫无地位,毫无话语权。不得不说,这种情势对李端棻的刺激非常大,如何利用教育链条输送新式人才,如何打通仕途与新学之间的通道成为他的政治考量。这标志着李端棻开始形成人才兴国的治国理念。这种想法的产生与李端棻多次担任乡试主考官,曾主管一省文教不无关系。于李端棻而言,从剖析教育和科举考试入手是最为便捷和容易的方式。
中国古代教育过度注重儒学的思想控制力和政治控制力,从而导致人才培养出现以下特点:一方面,儒学人才相对充裕,专科之才却凤毛麟角;另一方面,普通儒学人才基数相对较大,但是思维灵活的高级儒学人才却相对短缺。当外来冲击到来的时候,不懂世界规则的儒生们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了解西方,往往错失先机。李端棻把这种根源归结于传统教育过于封闭,因而也就必须为中国的核心政治区域注入新鲜的血液,必须为教育变革积蓄人才力量。也许,在李端棻看来,提拔带有传统气息和新学色彩的青年、培养能够将中西方文化学成并融汇于一身的新型儒生就是扭转中国教育发展方向的第一步。“喜奖拔士类”[1]12739的李端棻开始利用科举制度选拔可造之优士,以期造就新一代儒学精英——他对梁启超的发掘便是代表性的例子。
光绪十五年(1889),李端棻典广东乡试,提拔梁启超为第八名[11]。李端棻作为一名负责乡试的清廷官员,他为清廷选拔人才的标准也必是符合传统科举考试制度的要求的。那么梁启超为何能让李端棻另眼相看呢?从其乡试答卷中可以找到一些依据。当时的试文题目源于《论语·述而》,试文原文如下[12]: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不语怪力乱神。
梁启超的答卷,则以“圣人揭经学之要,所以存经也。盖诗书礼学,经之本也”论述“子语与子不语”的原因以及展开对“神异不经之说”的批判[12]。
吾子之教也,盖其慎也……故论好学以治经为本,而亦非默守一编也……殚其力以与道相求,好古发于至情,而真积既深,不主良知之说,斯芟夷危言,考证古恉(旨),庶可守先待后,为斯文独严吾圉之防,故曰所以学经也。
梁启超的试文内容虽不涉时政,只谈论经义,但其展现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学识积累却是毋庸置疑的。诗文中“好学非默守一编,竭力求圣人之道”,颇有携圣人之道与时俱进的意味。可见,梁启超对儒学精神的领悟程度是有高度的、灵活的,他对传统儒学经义的理解亦有独到之处。李端棻在向张之洞推荐梁启超的信中写道[3]:
弟爱其妙龄好学,会试后,以先叔京兆公所遗幼女结婚,近益研中外之故,所造愈深。彼乡荐时,以乡居鄙远,未及晋谒,而执事已移武昌。近始远来,补修弟子之职,望赐见之。
由此观之,李端棻十分欣赏梁启超,爱其资质,爱其好学;他亦观察到梁启超确实能够“精研中外,所造欲深”,这仿佛是对他挑选人才方式的一种肯定的验证和回应。他积极为梁启超的仕途铺路,帮助他融入官僚队伍,将自己入仕多年的经验,毫无保留地用在对梁启超的培养之上。若是没有李端棻的悉心教导和斡旋,梁启超未必能厚积薄发。从梁启超所撰《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中“饮食教诲于公者且十年”[13]2等语中,也可感受到二人之间的深厚情谊。
李端棻与梁启超相识后近十年的时间里,列强愈加猖獗,亡国之危的味道也愈见浓烈,西方的文化思想和政治理念也成了诸多有识之士重点研究的对象。李端棻在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的转变,一方面是受到当时所见所闻的刺激,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梁启超等人的影响。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廷的统治危机加剧,这对中国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刺激几乎是达到了顶点。梁启超作为李端棻政治构架中的肱骨,不仅继承了李端棻发展新式教育的政治抱负,也在推行新的教育制度的力度和热情上远远超过了李端棻。李端棻亦是在这种感染下首次获得了提携新式人才的成就感以及推崇新学的信心,他的思想变化开始更多地体现在了他的行为上。
戊戌变法前夕,光绪皇帝准开经济特科,以此为变法遴选人才,李端棻荐举唐才常、熊希龄等共16 人[14]。他引领了一大批具有维新思维的儒学精英走向晚清政治舞台。在举荐人才的同时,李端棻的教育改革理念也开始公之于众。他分析了洋务运动所办学堂的种种不足之处,提出自己对中国教育改革的见解。光绪二十二年(1896) 五月初二日,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指出当时的教育不涉“治国之道、富强之源”以及多处学堂“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等弊病,得出“此诸馆所以设立二十余年,而国家不一收奇才异能之用者,惟此之故”[15]593的结论。梁启超在同年所撰《学校总论》发出“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之问,得出“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15]598的结论。1898年,梁启超在其所撰的《戊戌政变记》中评价洋务运动写道:“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则与不改革何以异乎?”[15]604李端棻与梁启超对旧式教育制度的批驳跃然纸上,二人的认知方式和认知深度也随着国家情势的变化而提升,且处于一种日渐开阔的趋势。
在近代中国饱受屈辱的残忍事实下,无论是传统儒学教育的启蒙还是古代传统教育框架的限制都已经难以成为禁锢李端棻推行新式教育事业的枷锁了。在梁启超出现之前,李端棻的心中就已经埋下了教育改革的种子;在梁启超出现之后,这颗种子已然成树。如果以梁启超的出现作为一个分界点,在此之前,李端棻的新式教育思想处于一种含蓄的状态;在结识梁启超之后,李端棻的教育主张和教育行为开始蓬勃而出并达到高潮,其政治生涯也在此时达到顶点。在李端棻教育思想的转型阶段,他极度希望通过原有的人才选拔模式向官僚队伍输送新式儒学人才从而影响晚清的政治格局。这也就促使李端棻与维新派并行,使得其教育改革的政治色彩愈发浓厚。然而,在晚清政治斗争中,转型文人的政治力量不足以支撑李端棻的政治抱负和教育理念。再加上刺激到了传统掌控者们的敏感神经,由此,维新儒学精英们几乎都遭到了清算,李端棻本人也被清除出权力中心,发配边疆。
四、李端棻教育思想的成熟
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端棻受恩赐返回故里。此后,其近代教育思想开始臻于成熟。他从实践历练中体悟到不同于理想状态的现实差距,教育思想愈发容纳骨感的现实。也正是在贵州之时,李端棻终于开始体悟到近代儒生与儒学、新学二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引导近代儒生转型的曲折性。
此时段,清廷开始实行新政,而后公布了新学制,这也就意味着李端棻苦求多年的教育改革事业终于有了合法依据。在家乡的李端棻虽无官身,但仍以士绅的身份参与到贵州的教育改革事业之中。李端棻《应经世学堂聘》[16]7一诗如下:
帖括词章误此生,敢膺重币领群英。时贤心折谈何易,山长头衔恐是名。糟粕陈编奚补救,萌芽新政要推行。暮年乍拥皋比位,起点如何定课程。
“敢膺重币领群英”,李端棻依旧注重培养新一代儒学精英并积极承担起为贵州培养人才的重担。他在经世学堂讲学的目标依旧在于“启迪民智、宣传近代教育”。在此阶段,李端棻的讲学内容转变非常大,“定期召集诸生讲演,阐发民权自由真理,月课以培根、卢梭诸学说命题”[16]7。诸如“剖析帖括词章”“制定新课程”这样的事,对于李端棻这样的旧式儒士、官员来讲是难能可贵的。究其原因,可分析如下:
其一,李端棻经历生死之后不再是官员,回乡后其身份桎梏也消失了,政治斗争压力变小。他完成了自己从“官员”到“士绅”的身份认同,心理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对教育改革仍矢志不移,甚至愈发坚定。在李端棻《和文信国乩诗》[16]3中有云:“多情亦有王炎午,强拟予为信国文”,诗后作注为“先生在戍所,京中讹言有密为赐帛,门人某某等设位遥祭,为文以哭之”,可见当时情势之严峻凶险。李端棻可谓是命悬一线,能够活下来,自是更加珍惜个人价值的再创造。回乡之后的李端棻,没有官员身份的束缚及戴罪之身的限制,他的顾虑变少,社会关系简单了许多,也就可以大刀阔斧地践行教育改革了。
其二,李端棻回乡后,恰逢清末新政教育改革实施,这无疑是一次机会。李端棻在其诗歌之中明确表示支持新政,而且新政教育改革也恰恰与他的教育理念相符合,他自然要抓住机会一展抱负。同时,他的内心对这次新政抱有很大的希望。清廷的变革力度加大,甚至要超越戊戌变法,这无疑是在弥补维新变法失败的遗憾。
其三,李端棻的个人阅历丰富且颇有影响力。李端棻曾在云南任学政,曾任乡试主考官,又曾官至礼部尚书,他本人又对教育改革有高深的见解,可谓德高望重。1902年,贵州巡抚邓华熙邀请李端棻主讲经世学堂;同年,李端棻和于德楷、乐嘉藻等人在贵阳创办了贵州第一所公立中学堂——贵阳府中学堂;1906年,巡抚林绍年批准李端棻、任可澄等人的呈请,把贵阳府中学堂迁址,改名为贵阳中学堂,后又更名为通省公立中学堂,即后来的贵阳一中的前身[17]。可见,李端棻能够汇集一批士绅共谋贵州教育改革,也能得到贵州巡抚邓华熙、林绍年的信任。
其四,李端棻对贵州教育比较落后的局面感到忧心。李端棻在光绪二十九年所作《普通学说》(即经世学堂的上课讲稿) 中提到在中国教育改革的三个阶段中,贵州整个省的参与度是不强的;而且贵州与东南诸省相比,地处偏僻,接触西学的程度较弱,近代教育发展水平不高[18]。国家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李端棻期望贵州学子积极向学,也期望能为家乡培育大批人才。
然而,李端棻在贵州经世学堂这样的高等学府讲学期间,其宣扬民主、民权等内容的课程受到了守旧儒生的反对。后人在李端棻《闻谤自责》后作注:
先生主讲经世学堂……一般学生哗为以怪,即黔中名士,其后且在京师拥讲席谈革命如某某等者,当日亦著竹枝词以讥之。其时民智寒陋,可见一斑。未及期年,先生亦解馆[16]7。
李端棻开始明白,教育改革最艰巨、最根本的障碍不在于清廷,而在于清廷继承且操纵下的古代教育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普通守旧儒生见识有限,他们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背离了儒学精神的精髓,自然也就不会反省。事实上,不是儒学遏制了古代王朝的发展脚步,而是古代王朝为了维护统治而扼住了儒学的咽喉,利用儒学的正统性作为自己的挡箭牌罢了。当古代王朝被迫打开禁锢思想的闸门时,早已习惯了旧式教育模式的诸多儒生大多画地为牢了,更何况普通民众。李端棻曾是阅历丰富的中央大员,他见识广博,思维开阔,其爱国之忧、家国格局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绝不是普通儒生一时一刻所能理解的。
当然,李端棻是不反对儒学的。他只是反对专钻帖括、不研格致、不重政治的学习方式和教育方式,这一点在其《请推广学校折》中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维新派在新式学堂的课程安排中,也并未将儒学课程剔除出去。这无疑是要培养具备儒学精神以及西学学习能力的儒学人才。需要清楚的一点是,传承儒学并不是支持“腐儒”,对儒学的理性认识是体现在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考以及对儒学精神的真正体悟中的。李端棻在《赠何季纲表弟》[16]19中写道:
霸主事功惟足食,圣门货殖亦称贤。治生岂曰非儒者,择术何妨法计然。欲救国贫先自救,萌芽商学要精研。
在李端棻的认知里,精研商学是自救治国之道,亦是通向儒家圣门的正途。深思其背后深意,莫不是在表达儒家思想文化精髓即是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在当时的国情之下,对于“术”的理解要求更高,尤其体现在对西方技术、政治等多个方面的接纳性的提升上。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所积淀的优势也是不可被抛弃的。中国古代文人志士在儒学教育的影响下历来注重“修身”。有才无德、不修己身,就算掌握高明的“术”,也注定无法被赋予“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中国古代教育要求受教育者才德兼备、养吾浩然之气,而儒学教育恰恰是承载文育与德育的二元载体,是本我至圣的重要媒介。儒学的传授形式固然重要,但其所蕴含的君子品质是更值得汲取的营养。
李端棻回乡之后,他对于社会基层教育感知愈加深厚,对社会问题与教育问题的理解更加透彻。如果说,为官之时,他奏请建立京师大学堂、上呈《请推广学校折》是以高层的身份从大方向上进行教育改革引导。那么,他回乡之后,为经世学堂设立课程、撰写《普通学说》、牵头建立中学等,则是将改革的方法细化,结合家乡教育形势进行具体化的实践。可见,李端棻在教育心理、教育思想和教育行动上真正开始臻于成熟。这也证明,李端棻对近代中国西南地区教育水平的认知更加细致,其教育视野再一次被扩宽,开始思考儒学、新学与儒生之间的现实关系以及儒生的转型问题等。
五、结语
通过考察李端棻的教育事业轨迹及其教育思想的转变与成熟,可以见证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发展历程的曲折性。李端棻作为旧式官员、儒士,从接受传统教育的培养并遵循传统教育模式工作,转变到发掘可锻造的传统儒学精英、剖析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尝试教育改革,再到大力传播新学、制定具体培养方案、培养具备新式思维的新儒学人才,最终完成了其教育思想的转变与成熟。李端棻把握时局,将教育事业与国家命运相联系,将教育理念付诸教育实践,将对传统教育的理性分析注入新的教育模式,是推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先行者。值得注意的是,李端棻向教育改革前沿迈进之际,仍然兼顾对儒学的思考、诠释与继承,这对于我们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与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好的启示。如今,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变化对教育实力的要求更高,深入分析李端棻的教育事业轨迹、认知中国近代教育的变化特点,不仅对于发掘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古今智慧、增强文化自信有助力,也对我们继续提升教育特色、提高教育质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