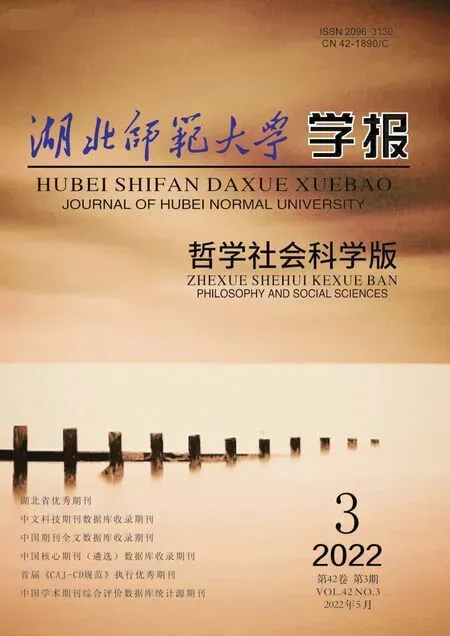温情的赞歌
——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民间情结
谢 倩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 人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1)
在汪曾祺初入文坛的20世纪40年代,正好赶上了抗日战争,当时的文学界倡导文艺要服务于抗战、服务于工农兵,汪曾祺这个时期的作品主要是收录在《邂逅集》里的8篇小说,都是根据自身情感意识创作的,讲述的都是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和民间风俗人情,与当时的战争主题毫无关联,可以说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与当时的文学思潮格格不入。
新中国建立初期至70年代,在举国上下倡导写英雄、唱英雄的社会主义文学盛行之时,汪曾祺留下了3篇小说《羊舍一夕》《看水》和《王全》,其中前两篇是写几个农村孩子在“文革”背景下纯洁、真诚、朴实的成长叙事。作品中既没写时代标语口号,也没歌颂英雄,更没写“文革”的苦难经历和对社会的控诉,而是以一种田园牧歌的调子,随意轻松的心态,关注身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是与汪曾祺坚持民间写作,不追随主流的写作立场是分不开的。
80年代汪曾祺复出后创作的小说,没有迎合当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表达时代的主流文学,一转笔锋回到40年前民间日常生活的凡人琐事,醉心于家乡高邮地区普通百姓的柴米油盐、风俗人情以及悲欢离合的平民生活。他始终用温情的目光去注视笔下的各色各样小人物,并善于将其美化,发掘他们身上的美和诗意,很少臧否美丑善恶,而是将感情倾注在朴素平淡的字里行间,表达作者对乡土生活、家乡小人物以及地方风俗的关心,体现出作者独特的民间审美追求。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汪曾祺的写作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跨时代的作家。从40年代走上文坛初露头角,80年代自成一家,汪曾祺的小说创作道路不受任何时代主体和文学思潮的影响,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进行创作,叙述着家乡高邮熟悉的风俗民情。民间成为汪曾祺寄托心灵和追求自由精神最好的港湾,纯朴而美好,亲近而致远,蕴含着作者内心深沉的情感,并以文学独有的眼光从民间生活中发现美、欣赏美、弘扬美,有着鲜明的情感价值取向,这可能源于作者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时代政治环境等多种因素。
汪曾祺1920年出生在江南水乡高邮的一个是士大夫家庭,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后因废除科举制度而没有继续考取功名,而是继承了家里的药店,成为一名乐善好施的眼医。祖母是名门之后,掌管家里的柴米油盐,对饮食起居非常讲究,深受祖母的影响汪曾祺后来写过很多关于美食的小说。父亲是一位精通音乐、绘画、书法的大才子,并且性格非常温和,是一位生活很有情调善于发现美、创造美的人。家境殷实,家庭和睦,乖巧可爱,备受长辈的喜爱的汪曾祺,从小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加上影响一生的四位女性祖母、母亲、继母、伯母都是温柔善良知书达理之人,汪曾祺就在这样温馨幸福的家庭中无忧无虑地成长的,让他感受到生活是美好的。也正是这样自由自在、轻松愉悦的童年生活促成了汪曾祺成年后总是以善意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他的文字也是乐观的、积极向上的。这一切为他成年后以一种独特的眼光去发现生活美的重要原因。汪曾祺小时候受家庭环境的影响,饱读经史子集,所以孟子性本善观念和庄子哲学中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精神对汪曾祺的思想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儒家思想中人道主义精神对汪曾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为他一生创作民间意识、民间情怀的小说提供了思想基础。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开设的习作课,要求学生“贴近生活写”对汪曾祺一生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这为他积累了文学创作的技巧和写作的叙事方式。尤其是沈从文笔下唯美的湘西淳朴民风民俗,深深地触动汪曾祺从小生活的市民社会的风土人情,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各行各业的普通老百姓的茶余饭后和生存技能。儿时的汪曾祺生活在江南水乡的高邮县,那里青山绿水,风景如画,民风淳朴,这样的生活环境和质朴的乡民为他后期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天然的素材和背景。
了解汪曾祺生平的人都有着同样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动力支撑着他这位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大少爷”成年后经历大学被迫中断学业、毕业后的失业、“文革”时增补为右派、被迫创作样板戏等等磨难都没有把他击垮,仍诗意地面对生活并发出“生活是很好玩的”高歌。汪曾祺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1]这与汪曾祺坚强乐观的面对生活,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好,并一直保持乐观旷达的心态是分不开的。也许正是因为他经历了无数的风雨才造就了他的豁达开朗,保持着积极的心态对待生活和写作,特别是80年复出后用作品给人们传递生活是美好的,给苦难寂寞中的人以抚慰和鼓励。
一、平淡的民间叙事
汪曾祺一生的小说创作,独特的艺术个性,在中国当代文坛无疑是独树一帜的,他主动把自己的创作从纷繁复杂的时代主题和文学思潮中抽离出来,转向民间大地上的风俗民情,写儿时的回忆,以《大淖记事》《受戒》为代表的细腻真实、诗意栖息的民间生活,与他本人诗意化的人生追求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人们还在为蹲牛棚、写检查的痛苦挣扎时,他却能随遇而安地寻找生活的新乐子;当人们在痛定思痛控诉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时,他却以诗情画意的温馨书写人情美、人性美的赞歌。苦闷的时代,坎坷的经历,艰辛的生活,汪曾祺仍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品尝美食,书写人间的真善美,赞美这民间的一草一木,一人一技,他曾不止一次说过“我是一个乐观的人”,即使逆境也能感受生活的快乐和诗意。加上他写小说不迎合时代主体、政治导向、不谋求什么功利,表现明显的文学自主意识,1949年出版的《邂逅集》基本上无人问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解放前我很少想到读者。一篇小说发表了,得到二三师友的称赞,即为已足。”
汪曾祺小说在叙述上特别倾情于对民间的精心描写。他的小说基本上没有一开始就交代故事发生的起因,总是不惜笔墨地对一个地方的自然环境、盛产物品、风俗民情、职业技艺、历史典故等描写。如《异秉》中的那些生意场上各种门道的叙述;《职业》中各种行业吆喝叫卖声的描写;《戴车匠》中小店的位置及周围街坊邻居的描写;《大淖记事》的开篇便是对大淖的历史考证和大淖沿岸春夏秋冬景物的描写,接着介绍从淖里坐船开始介绍炕坊、浆坊、鲜货行、轮船公司、再到沿途的居所住所的瓦屋,接着引出了人物及风俗人情,如那里的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挣钱,那里的女人野的不行的,媳妇都是跑来的,姑娘可自己找人、生私孩子,媳妇可以在外面“靠”一个。作者通过民间这种风土人情以及人物的生存方式塑造人物,多方面表现人物的性格,这也构成了汪曾祺小说独特的叙事方式,所以读他的小说总给人一种欣赏风俗画的感觉,人物总是融汇在风俗画中展现出来,都洋溢着浓郁的风俗气息。
二、诗意的民间语言
“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1]这与汪曾祺一直致力于民间的创作风格是一致的。语言的内涵凸显出作家的审美和文化积淀,“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是汪曾祺以一贯之的写作思想。坚持立足于民间的汪曾祺,从小积淀民间语言的素材,如《八千岁》中描述八千岁相骡子相马有一绝时一系列动作的描写“敲敲”“捏捏”富有节奏的叠音词和一“走”、一“拽”的动作快慢鲜明的对比,宋侉子游刃有余的相牲口的技巧,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读汪曾祺的小说无不为他那独具韵味的语言震惊,一部分得力于他巧妙的语言形式,一部分得力于他民间语言的叙事方式。其小说语言多使用短句叙事,极其简洁,甚至只能用交待概括了,很少有渲染、夸张、虚构、反语等复杂的表现手法,甚至连比喻都没有,读他的小说就好像听一位慈祥的老者用平和的语言在给你讲述他经历的过往,一会交待一下这个事,一会又插入那个事,一会又把张三的事单独交待一下,交代完了,小说也就结束了,这种交待使小说具有了独特的线条感,汪曾祺小说的民间风土人情基本是这种线条勾勒出来的,没有任何的色彩渲染和故事虚构。
比如《受戒》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十三岁来的。这地方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作者就用这种线条这勾勒一下,那勾勒一下,就把庵赵庄勾勒成一幅风俗画。汪曾祺这种简单诗意、独具魅力的语言,加上自幼迷恋于家乡的风俗人情和倾心于民间诗意化的生存环境,可见汪曾祺对民间语言的炉火纯青的程度是情理之中的事。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纯朴自然,细细品味起来却余音绕梁。尤其是语言上的短句子的使用和民间语言真实性,使小说充满了诗情画意。《故乡人·打鱼的》中描写夫妻二人结网、赶鱼、打鱼的场景以及夫妻二人简短朴素的对话,看似平淡的如一日三餐,读起来让我们感受到他们诗意的生活,也大概就是汪曾祺语言的魅力吧。
《七里茶坊》高个儿与掌柜之间的对话: “不吃莜面! 一天吃莜面。你给俺们到老乡家换几个粑粑头吃。 多时不吃粑粑头,想吃个粑粑头。”这种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的民间话语,使小说读来更加有味儿了,这也是汪曾祺深入民间仔细体验生活的真实再现。 在《寂寞和温暖》中有这样一段叙述:“稻子收割了,羊羔子抓了秋膘了,葡萄下了窖了……”在这段生动有趣的文字中,将各种口语化的意象以“了”字为结尾串联起来,给我们呈现一幅生机盎然的景象以及欢悦明快的生活场景,同时也宣泄着主人公的喜悦心情,简直绝了,看似作者随意的书写,其实是他扎实的民间语言功底的再现。
汪曾祺不止一次在他的文论里提到民间语言在其创作中的重要性,这与他编过几年的《民间文学》是分不开的,他曾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提到不读民歌,是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的。在 《小说笔谈·语言》中谈到:“在西单听见交通安全宣传车播出:‘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在校尉营一派出所外宣传夏令卫生的墙报上看到一句话:‘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再吃’,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语言。这样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 不能增减一字。”[2]
三、温情的民间关怀
汪曾祺之所以不追随文学主流,而刻意选择旁逸斜出,另辟创作主题,除了努力写回忆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间送小温”的民间关怀情结。汪曾祺出生于士大夫家庭,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深,长大后具有传统士大夫的风范,一直秉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和服务社会的宗旨,既有超然世外的豁达乐观,又饱尝悲悯天下的情怀。他在小说中始终以一个隐居者的身份关注民间生活,百态人生,表达着对他们的深切关怀和对小人物的美化和同情,谱写着人性的赞歌。
这也使他执意远离政治舞台,摆脱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努力将个人生活、平民琐事与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区别开来,他的小说很少有政治相关人物,即使有作品内容需要牵涉到的生产队长、保安队长、一些小单位的书记、主任,他在描述中基本上聊聊几句一笔带过,尽量淡化他们的权力与影响。尤其是当时在被时代和政治造成巨大的伤痛后,大部分人选择控诉、揭露社会的“暗角”来宣泄时,而汪曾祺选择的却是回顾儿时的记忆,用美好的事务来抚慰人的心灵。在《受戒》中描写的角色都生活在与现实遥远的民间世界里,几乎就是一个现实版的“世外桃源”,与其说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自我保护,倒不如说是先生的民间情怀,这也体现出他对民间生活饱含的浓厚的人情味。其实他也创作了一些反映社会阴暗的、龌龊一面的作品,但我们读起来几乎感觉不到负面影响,仍然给我们传达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这也是他专注于民间人物的塑造,接受、欣赏民间世界的和谐感很独特的一面。他曾经指出:“我有一个很朴素、古典的说法,就是写一个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3]《受戒》里寺庙中和尚也可以有七情六欲,吃肉、打牌、娶媳妇, 他们也可以毫无戒律地保持着生活的自然与纯真,在作者的眼里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这也体现出作者对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出家的和尚们的同情之心。在《一辈古人》中作者对拉皮条的薛大娘没有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待,而是投注更多的宽容和理解。小说《珠子灯》中写的孙小姐自从丈夫去世后她心里的那盏灯就灭了,整天平平淡淡地躺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她死去。平淡朴实的文字使我们读起来似乎未感受到孙小姐的痛苦,但是文字的背后掩藏着无限的悲凉、无奈与绝望。汪曾祺以男性的身份控诉封建礼法对那个时代对女性的伤害,这正是汪曾祺对生命给予的关怀和尊重,这也正是他人道主义的精神的体现。《大淖记事》中里温柔善良的巧云忍辱将受伤十一子带回家照顾,乡亲们自发杀鸡凑钱帮助为爱抗争的一对年轻人,他们俩的爱情不受世俗和现实的阻扰,让我们为之赞叹。对于人世间的是是非非,作者更多的使用温情的态度,怜悯的目光寻找民间的美好存在,并将道德与人性做了完美的统一,善意与温存成为他文中潜隐的仁者之心。很多人都喜欢将汪曾祺和老师沈从文相比,翠翠无期的等待与巧云“甜蜜”的爱情结局相比,汪曾祺更多的是仁爱、和谐,正如他多次提到的“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4]他在作品中将美好的东西展示给读者,滋润人们的心灵,增强人们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体现出他对民间眷恋的真情流露,所以他称自己为“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
四、独特的民间审美
汪曾祺为人冲淡平和、含蓄内敛,他不是写大人物、大思潮的“大作家”,而是醉心于柴米油盐、茶余饭后的“小作家”。他的小说都是写平民生活的日常,基本不写惊天动地的时代大题材,专攻方言口语、风土人情,地方风俗,民间小人物并将其美化,回避丑恶,不置臧否。如《安乐居》中养猫遛鸟,喝酒聊天的酒客们。《受戒》中明海出家的原因、过程,小英子一家的幸福生活以及和尚们做法事、杀猪、打牌、算账。《异秉》中王二“熏烧”摊子发家的过程,保全堂的规矩和晚间闲坐趣谈等等。汪曾祺曾说他“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5]所以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尽管生活在底层,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悲哀与无奈,以朴素与温和的态度去面对,并满足乐观。他们乐天知命与坚忍不拔的人生态度正是汪曾祺所坚持的民间审美取向。
现实中的高邮人民真的生活在世外桃源般的诗情画意中吗?真的如汪曾祺笔下所描写的那样和谐美好吗?其实不然,社会矛盾也存在,悲剧也时常发生,只是这些矛盾和悲剧经过作者艺术的处理,他把苦难淡化,冲突和缓,甚至深深隐藏,尤其是平明百姓韧性乐观的生存意志和乐天安命的生活态度遮掩了人世间的不如意。《寂寞和温暖》中奢酒如命、心狠手辣、独断专行的胡支书整天无所事事,人们恨之入骨。当阮沈沅提意见却被他打成右派,受尽了人间的侮辱和折磨,这是一个典型的滥用职权的故事。《大淖记事》中强势的刘号长强奸了巧云, 打伤了小锡匠,在我们读者看来,这本是强权欺压、棒打鸳鸯的社会悲剧,但在作者的叙述中只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锡匠们开了会向县政府递了呈子,没有答复,游行三天,又“顶香请愿”三天,才争取了大茶馆会谈,刘号长画押具结,调离此地,这些细节的叙述没有任何表达作者主观情感的字句,也没有世人的诅咒和不满,就是简单的叙事,像平静的水面上的细微波浪一样自在自然,汪曾祺对民间生活这种率性自然的思想发自内心接受,同时也表现了老百姓大度的生存意志和生存智慧,把苦难超越了,呈现给我们一种世俗人生的诗意境界,这也正是汪曾祺所追求的民间审美价值所在。
汪曾祺因追求诗化、和谐、平淡自由为人称道,有一种来自民间的自然、古朴、天真的意趣和发自内心地去接受民间生活的点滴,尤其是他坚持和弘扬民间的天真、善良和诗意,描绘了一幅幅丰富而可亲可爱可感的民间人物的人物群像,为我们呈现出原始生命本真,打通了现实与审美之间的桥梁。用欣赏与眷恋的眼光,注视着民间大地上淳朴乡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散发光明的美好人性,他也力图用一颗怜悯之心描摹理想的人类生存图景,让我们从中找到心灵慰藉,探寻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