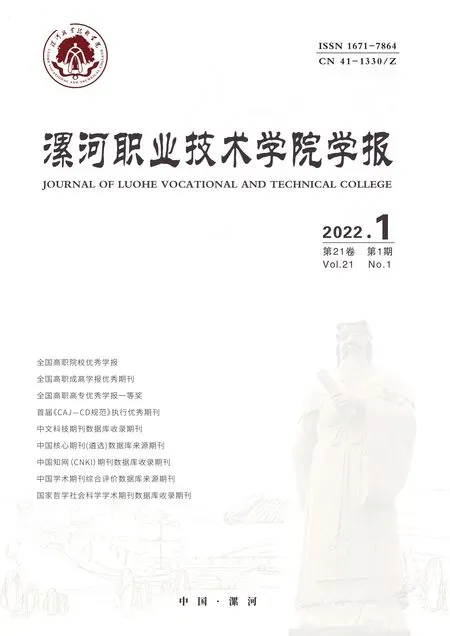外交术语的产生与文体特征
郭耀军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外国语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术语是通过固定的文字来表达某个领域特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1]。术语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用以表达一个固定概念,往往准确、简明、严谨、用法固定且语义单一。外交领域也有大量专业术语,如“新型大国关系”“sharp power(锐实力)”等。学界长期以来将以上词汇作为外交新词研究其翻译问题[2],或者将之置于政治术语的概念之下,作为政治术语的一个特殊类别[3],也有许多外交话语的研究提到了外交术语,但都没有将这种外交领域的特有词汇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独立出来,并对其进行深刻的考查[4,5]。王晓莉和胡开宝研究了“新型大国关系”英译在英美的传播与接受,点出了“新型大国关系”是外交术语,但其研究的重点是外交术语个案的传播效果[6]。现在有必要正式提出外交术语这个概念,和法律术语、医学术语等并列,这样有助于研究其内在特征,并可为其翻译奠定理论基础,为新的外交术语拟定提供理据支撑。外交术语(diplomatic terms)为国家在外事活动中用来传达外交理念和外交立场的专门用语。每个外交术语都有严格意义的界定,是国家外交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外交政策的集中体现。
一、外交术语的生成机制
外交语言是民族共同语在外交领域使用中产生的一种语言变体。外交术语和民族共同语词汇相比存在着差异,从现有外交术语中归纳的生成机制如下。
(一)借用
民族共同语中的一些词汇,外交领域用语也会借用。这种来自“借用”的词汇,在民族共同语中表达多个义项,而在外交语境中,只能采用特有的语义。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德国演讲时提出“中国智慧”,“中国智慧”可以指中国人的智慧或者带有“儒”“道”思想的思维方式,在外交话语体系下,它专指为各种世界难题所提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案”。“stake-holder(利益攸关方)”是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于2005年9月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演讲中提出的,后来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广泛使用[7]。“stakeholder”本指“股票持有人”,被外交领域“借用”,指具有牵涉到利益的国家或者地区,美国是一个经济强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治的走向,外交领域借用了不少经济领域的词汇。
(二)新造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不断变化,各个国家间关系的变革,国际关系的调整,造就了新的外交思想和政策,原有词汇不能准确传达应有含义,新的外交术语也就应运而生了,使外交语言更加准确和严谨。当然,一般不存在纯生造(coinage),因为除了需要充分的造词理据之外,还要为大众所认可和理解。通过对民族大众语言的改造和加工,使其集合成一个新的意义体,从而获得鲜明的外交语体特征,这也是外交术语产生的最通常路径。其中使用最多的是通过修饰和被修饰关系把词素(词汇)与词素(词汇)结合起来,构成外延较小的术语。这种在外交领域存在,不同于其他用语的专门词汇或者词组,只在外交语境中使用,意义明确,具有特定的内涵。例如,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美时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8]。这是中国在当前时期重要的外交构想,“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一个新生术语,即是在“大国关系”前加上“新型”来限定,表达“不同于以往大国对抗的大型国家之间的关系”[9]。英语中,常常在一个词根上增加前缀或者后缀的方式形成一个新词。比如,unilateralism(单边主义),是在lateral(边的)词根上加上前缀uni-表“单一”,加上后缀-ism表“主义”。“Chimerica”(中美国)由“China”和“America”组合而成,用以表达“中美共治”的思想[2]。
(三)外来词
现代语言都不可避免地使用外来词语,词语是概念的外壳。本民族语言中没有找到其他语言使用的术语表达,或者受到强势外部话语的影响,而采用了直译或者音译的方式,这便是外来词。本质上说,这也是一种借用,只是借用了其他语言的概念,而非本民族共同语。毛泽东多次使用“纸老虎”来指称国际反华势力,之后英语中便用直译的方式产生了“papertiger”这一术语。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规范英译为“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一带一路”作为简称,要译为“the Belt and Road”或者“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the land and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概念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一些西方报纸索性采用音译的方式,翻译为“yidaiyilu”,逐渐为西方社会所接受。
二、外交术语的类型
对词语分类的方法有很多,比如稳定性、内部结构、概念范畴等。根据词类进行划分,外交术语指称对象常为具体概念,因而仅涵盖名词和动词两大类,其他词类不涉及。这里的所谓词性是一个泛概念,包括词和短语。
(一)名词性
外交中需要指称外交构想、意图或者理论,这些都离不开对名词及名词词组的使用。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10]明确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构想。“三个世界”对应了明确的国家主体,属于名词类。“两个中间地带”“一条线”“一大片”等都属于这种。美国在独立战争前后用“isolationism(孤立主义)”这一术语来表达不和其他国家结盟,以便少受其他国家干扰,维护自身利益的政策主张。还有“dollar diplomacy(金元外交)”“big stick policy(大棒政策)”等名词在外交术语中使用率最高,据粗略统计占到了70%以上。
(二)动词性
外交构想需要在具体的行动中逐步实现,外交术语中的动词或者动词词组常用来指称这些行动路线或者政策途径。比如中国的“不折腾”“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美国的“Return to Normal(回归常态)”“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美国再强大)”等。
还有一些术语,表达了一个事件,比如“弯弓不发,后发制人”“America First(美国优先)”,但其本质仍为一个动词词组。“弯弓不发,后发制人”表面意义为“弯弓不首先发射,后发制人”,除了整体借用民族传统语句的因素外,“弯弓”的使用隐喻了“强大的国家”,暗指中国,道明了“后发制人”的行为主体。术语的主体强调“后发制人”,有时候在使用时仅用“后发制人”,而省略“弯弓不发”。“America First”中“America”指明了行动的主体,避免歧义,组词的主体为“First”,“First”属于形容词,隐含了“goes first”的含义,可以归于动词类。
三、外交术语的文体特征
在考察了大量中英文外交术语的基础上,总结外交术语的文体特征,既有术语的共性,也有外交术语的特性。
(一)政治敏锐性
外交话语具有极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极强的政治性。外交直接涉及国家利益,中国一直强调“外交无小事”,后被各级涉外部门奉为准则。恰当的外交术语能传达正确的国家价值观念,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11]。反之,则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014年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新闻发布会上严厉斥责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藏独”分子达赖喇嘛,宣称“中方多次就达赖赴美窜访(the Dalai Lama's visit to the US)问题向美方表示严重关切。”“窜访”被外事译员译成中性词visit,未能有效传递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的感情色彩和政治立场,导致一些西方媒体纷纷套用visit的表达[12]。
(二)表达简洁性
术语的产生将原有思维包装为一个整体,在使用中就不必将原有内容全部说出来,这避免了思维的繁重,也使表达简化[13]。外交术语来自外交话语,是外交话语的集中体现,是话语的术语化,往往短小精悍,高度浓缩,一个词语传达了丰富的内涵。相较于其他表达,术语更注重经济性,甚至注重音韵的美感。
“一带一路”,并没有指出哪个带哪个路,但其内涵很明确,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4]。仅用四字表达了16个字需要传达的概念,暗含了中国的发展与周边国家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要从海上和陆上同沿线国家发展经济合作,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一带一路”四个字,可以说语言凝练到极致。
(三)结构稳定性
外交术语是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是语素的凝固,表达一个特定的内涵。它结构稳定,构造成分不能随意拓展或者减少,也不能随意替换。比如,不能说“中国特点的大国外交”,只能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为一个凝固的整体,表达特定的外交含义。2013年习近平在莫斯科演讲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命运共同体”不能表述为“命运共同圈”“命运统一体”。
(四)内涵规定性
每个术语必须含义清晰而明确,不能含混不清导致歧义产生,这也是一切科学术语突出的特点,单一而固定。外交术语的产生过程往往首先被某个人所使用,后来逐步被认可而广泛使用,一旦固化下来,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时都必须对其有同样的解释。比如,2013年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与中国周边外交要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亲、诚、惠、容”这个术语自此就固化下来,是中国新一届领导层结合历史与现实,对中国与周边关系的一次重新定位,把中国与周边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到情感高度。
(五)民族特色性
语言是人民大众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和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价值观念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个国家的外交术语也往往带有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外交也一定千差万别,具备自身的特点[15]。中国拥有数千年传统文化,语言中存在大量充满智慧的表达。我国领导人在外交中经常使用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话语。“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在外交中多次使用,用来表达国与国之间应摒弃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平等交流、相互协作和共同发展。
“韬光养晦”出自《旧唐书·宣宗记》,原指“收敛锋芒,隐藏自己的声名和才华,养精蓄锐,等待时机”[16],在20世纪80年代末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则被邓小平同志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传达了中国想保持低调,一心一意谋求自身发展,不想和任何一个国家对抗和竞争的外交战略[17]。
(六)跨文化交际性
跨文化交际性是外交的特性所决定的。外交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将自己的理念传播出去,国家特有的传统文化在话语权力强大的时候,往往难于传播。要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就需要外交术语从世界文化中吸收营养,才易于被不同文化所接受,这就是术语必须具备的跨文化交际的特质。中国外交话语讲究排比、对仗、比喻、押韵,注重语言的美感,但往往使外语受众不能理解其深刻内涵,没有起到良好的传播效果[18]。
国际社会经常把“韬光养晦”解读为负面含义,把它翻译成hide one's s capability and bide one's time(隐藏实力,以待时机)、hide one's capability and pretend to be weak(隐藏实力,假装微弱)、hide one's ambitions and disguise its claws(隐藏野心,收起爪子)以及conceal one's true intention(掩盖真实意图)[19]。国际社会对“韬光养晦”概念的负面解读,是因为“韬光养晦”文化背景深厚,难以被西方世界理解。当“韬光养晦”被当作中国的外交战略、方针和指导思想时,这种负面解读使中国无法把“永不当头、不搞对抗、低调发展”战略目标清晰地传达出去,反而给“中国威胁论”增加了又一可靠例证,所以应该注意外交术语的跨文化交际性。
(七)隐喻性
隐喻是语言中的普遍现象,可以说任何领域的沟通和交流都是基于隐喻思维和隐喻语言之上的[20]。这一点在外交术语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外交话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概念隐喻,外交术语离不开隐喻的使用,隐喻的使用使外交话语更加委婉或者易于理解,外事交往中,为了避免刺激他国,并塑造本国良好的外部形象,更应该注意语言的攻击性。
隐喻可以分为“新奇隐喻”和“常规隐喻”。“韬光养晦”是新奇隐喻,由“隐藏宝剑的光芒”的“源域”映射到“低调发展”的“靶域”。美国将伊朗、朝鲜等国家定义为“the axis of evil(邪恶轴心)”,“轴心”本指二战时期德意日等国家组成的轴心国,现在将伊朗等国家类比二战时期的德意日,激起伊朗等国家的强烈反对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的隐喻不一而足,如“纸老虎”“零和博弈”“软实力”“另起炉灶”“一边倒”“稳住阵脚”“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邪恶轴心”等,“常规隐喻”比比皆是,比如“新型大国关系”即属于这一类,该隐喻基于国际关系中最常见的“根隐喻”,即国家是人,因为国家是个抽象的东西,理解为“人”之后才会有各种“关系”如伙伴、敌人等,还有“关系”概念本身也是抽象的,没有物理意义上的新旧之分[21]。
总体来说,外交术语的研究成果的数量和外交的重要性极不相称。外交术语是外交语言的精华、核心,是外交概念的重要载体,是外交话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际话语权的表现。因此,如果没有对外交术语全面深入的认识和把握,外交话语体系的构建只能是空中楼阁。
本文从多学科的视角,从界定、产生、类型、文体特征几个方面对外交术语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希望能为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贡献才智。
(衷心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杨明星教授对本文框架给予的精心指导和无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