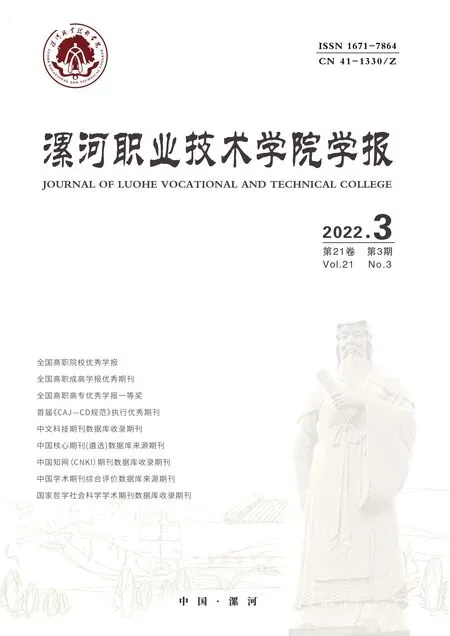《毛猿》中的阶级、工作与身体
刘彦博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1450)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在谈论什么是阶级时,不无困惑地说:“class很明显是个很难解的词,不仅是在其词义的层面上,而且是在其描述社会分工这个特殊意涵的复杂层面上。”[1]阶级主要被理解为经济集团,虽然确定某一阶级相关的经济因素可能会有争议。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阶级主要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来确定,而且还要考虑生产过程中的人们地位作用以及分配方式。阶级分化会导致社会分层与权力与文化差异,从而导致身体的差异,《毛猿》中人物的阶级划分主要包括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三类。工人阶级主要代表包括罗伯特·斯密斯(绰号扬克)、派迪和勒昂等,资产阶级主要代表包括米尔德里德·道格拉斯小姐和她的姑妈,而中产阶级的代表主要包括轮机师二副、警卫、一个团体的秘书等。阶级、劳动对身体体格、衣着进行着型塑以及规训,而身体为了自身的维持也有一套身体功夫来适应工作。
传统上要研究人的发展及其受压迫的状况,就要考察人们在工作场所因为工作的内容而结成的社会关系,要讨论社会的具身性和组织机制,工作场所与工作的内容仍然是至为关键的因素。雇佣劳动中的正式活动、社会环境背景已经成为众多的社会学和历史研究的课题。每一代人都要面对这些预先确立的社会关系、技术力量和行为规范,这些结构的效应对他们的身体有不可避免的影响。身体是不同阶级的工作的定位场所,也是工作的源泉,阶级、劳动与身体之间的复杂互动为我们提供众多引人深思的信息。
一、前期工业社会的工作与身体
克里斯·希林认为“在前工业社会,工作场所往往和家在一起,使生产性工作和再生产型功夫融合在一起。”[2]在《毛猿》这一剧作中,前期工业社会与深度工业社会的劳动有不同的效应。在扬克没有阶级意识之前,他认为自己比资产阶级更像人样,认为“他们不过是臭皮囊。开动这条大船的是谁、难道不是我们吗?”[3]面对扬克的狂妄与无知,爱尔兰老水手派迪则回忆起了自己年轻时代:“噢,真想回到青年时代的那些美妙的日子去啊!噢,那时候有许多桅杆高耸入云的快船——船上都是好样的、健壮的人——那些人都是海的儿子,就好像海是他们的亲娘。噢,他们的皮肤干净,眼睛明朗,还有笔直的背和丰满的胸膛!他们都是勇敢的人,是大胆的人。”[3]416-417
首先从派迪对生产工具的描述上看,他年轻时使用的生产工具是“快船”。快船又叫快速帆船,是19世纪中期一种尖船头的海船,船桅高,流线型,为高速行驶而建造。种种迹象表明,派迪回忆的是前期工业时代。工业社会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的一种社会认知范式,工业社会是指在一个社会,技术的使用足以驱动规模生产,支持高度分工为基础的庞大的人口。这种结构在西方发达的工业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取代了前现代的农业社会。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瓦特改良的蒸汽机被认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但是在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的许多成果还未被应用于工业,“快船”就是一种未装配蒸汽动力的帆船。
在前期工业社会里,工作还带有前工业社会的特点,工作场所往往和家、家乡这些概念相联系。派迪把大海比作水手的母亲,可以看出,身体与工作环境的关系是极其亲密的。
环境对身体的型塑,作者从派迪的眼睛、背部和胸膛这三部分来进行展现。“眼睛是最了不起的身体器官,尺寸大不过乒乓,却能够同时处理一百五十万条讯息。我们收到的外部世界信息有百分之八十是来自眼睛,比其他感官提供的信息加在一起还多三倍。”[4]因此,派迪说自己年轻时眼睛明亮,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它不仅可以表明年轻时代工作环境的友好性,同时还可以表明自己比扬克的视野更为开阔,可以清楚地看清事物的本质。与此形成对照,工业时代工人的眼睛是“愤恨的小眼睛”,“愤恨的小眼睛”除了直指体型的丑陋,同时也暗喻着在现代社会工人无法对社会、工作及自身有清晰的认知。
就部位而言,背部位于人体躯干的后部,在脖子和骨盆之间。自从人类开始直立行走,背部的肌肉需要加班加点的工作,才能为我们全新的直立姿势提供支撑。在英语文化中提到背部,通常强调它的脆弱性,例如有“watch one’s back(当心)”“with one’s back up against the wall(碰壁)”“stab one in the back(背后捅刀子)”。在前期工业社会里,水手派迪笔直的背部则是力量和勤奋的象征,并没有受到工作的重压。
胸部位于颈部和腹部之间,它包括心脏、肺、胸腺、肌肉以及其他各种内部结构。在前期工业社会里,水手派迪的胸膛是丰满的。丰满的胸膛并不是说胸膛是宽大的,原文中丰满的胸膛用的是“full chest”[5],指的是呼吸的状态顺畅。自从人类直立行走、追逐猎物,男性就必须改进自己的呼吸状况。派迪的年轻时代并没烟尘污染,反观当下:“烟囱里喷出的黑烟污染了海,污染了甲板——该死的机器打呀、跳动呀、摇晃呀——道阳光也看不见,呼吸不到一口新鲜空气——我们的肺被煤灰塞满——在这个地狱一般的炉膛口里,断了我们的脊梁,碎了我们的心——这个该死的炉子——我们的性命随着煤一道也送进去了。”[3]417-418
在生产性的工作过程中,前期工业社会的场所、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工作节奏对身体进行了定位,身体成为工作效应的定位场所。不仅如此,此时在派迪看来身体功夫和工作也能融洽、融合。身体功夫是以人类再生产的视角,考察人类以其身体为对象和目的,对其身体自身所做的劳动,以便维持自身的生存,充分发挥身体的功能效用。在派迪的描述中,生产型工作与再生产型功夫是统一的。
再生产型功夫与生殖劳动工作通常指的是家庭内部的身体工作与角色,包括了清洁、做饭、照顾孩子等。这个词是在女权主义身体话语中出现的,关注的是女性如何被限定在家庭劳动领域劳动而不能自救。其实,不只是女性,任何人只要试图维持身体最低限度的功能运作,都可以被视为身体功夫中的再生产型功夫。
在派迪口中的再生产型身体功夫包括唱歌、睡眠、晒太阳和抽烟斗等。任何社会的再生产都不可能离开这些维持基本身体功能,但是,派迪的唱歌、睡眠和工作却是同一的。唱歌、睡眠的同时船却在连天带夜的穿梭,船后是闪着火光的浪花;晒太阳也是如此的惬意,太阳甚至能温暖他的血,结束一天的工作后,还可以悠闲地抽烟斗,欣赏落日、云彩。在他的描述里,快船是真正的船,船上的水手是船上的一部分。大海则如同母亲,把作为生产工具的轮船与身体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因此,派迪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充满了宗教的热忱,他甚至把自己的船叫作“荷兰飞人号”。“荷兰飞人号”神话是起源于17世纪航海民间传说中的幽灵船,据说这艘船永远不能驶抵港口,注定要永远航行海洋。“荷兰飞人号”的比喻也强烈地表明了工业社会前期生产工具和身体的同一性。
二、高度工业社会的工作与身体
人类进化导致出现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在灵长类动物的演化历史上——猿人、直立人、智人、现代人相继出现是一个正向进化的过程。在《毛猿》中,却出现了众多的“毛猿”“野兽”“尼安德特人”的意象来指代工人,工人阶级的身体出现了逆向进化的种种表现。
剧作的第一场,场景设置在烧火工人的前舱,他们住的是上下三层的一排排窄窄的铁架子床。屋里挤满了工人,他们喊叫、咒骂、大笑、欢唱,这些共同行为构成了水手们的集体欢腾,这种欢腾的语言让人震惊。
在剧本的开头:
Gif me trink dere,you!
‘Ave a wet!
Salute!
Gesundheit!
Skoal!
在剧本上也把这种“语言”称为“七嘴八舌的声音”,如剧本的第一句话是“Gif me trink dere,you!”(喂!给我喝一口!)与规范英语拼写相差万里,只是下层阶级语音的记录;接下来的几句竟然来自几种不同的语言,Gesundheit是德语,意为“祝您健康”;Skoal来自挪威语[5]11。语言上语源的不同固然可以表现美国文化的混杂性,同时更重要的是它的诗学效果——现代工人彼此之间好像是语言不通的“毛猿”。
作者在第一场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工人和旧石器时代的尼安德特人的模样相类似,所有的人胸脯上都是毛茸茸的,长长的双臂,凶恶的小眼睛显露凶光,额头低低的向后削,看上去力大无穷。扬克作为他们的代表,比其余的人更健壮、凶猛、好斗、有力、自信。他们因为畏惧扬克强壮的身体,不得不表示某种尊重,工人群体内部好像也是遵循动物相处之道的法则。而这群人,特别是扬克“毛猿”身份,最终被资产阶级小姐米尔德里德·道格拉斯的一句“这个肮脏的畜生”再次确认。
在奥尼尔看来,工人阶级身体的返祖现象无疑是悲惨的,因为它代表的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造就了人类生活的新荒原。这些肉体彼此之间咄咄逼人,却没有思维能力,对资本主义构不成威胁,那么这些驯顺的肉体是怎样产生的呢?很显然在这部戏剧中,对工人身体的规训并不是来自公开的身体胁迫,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重组的空间。法国社会学家福柯曾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分析了学校、医院、工厂等场所如何对身体进行封闭、分割和分等[6]。福柯的分析,对我们理解《毛猿》中工作对工人的身体定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就空间而言,轮船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它游离于大陆之外,对身体本身就是一种限定。另外,轮船的各部位有着强烈的等级性,对人起着分割及阶级定位的作用。例如,在司炉工的前舱,隐私是不存在的,上下三层的铁架子床摆满了整个空间,而船上的轮机师、二副等,他们的房间却有私密性。司炉工住在逼仄的空间,在污染的甲板上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而在头等舱所处的上层甲板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上层甲板是资产阶级的休憩处,风光明丽,新鲜的海风吹拂。在工人工作的炉膛口,环境昏暗、煤灰四溢,当打开炉膛口的时候,亮光刺眼、火焰升腾、声音震耳欲聋,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图景。在基于空间分配的生产过程中,身体只能朝某一专门的方向发展,最终确定了身体的属性。就此时期的“身体功夫”而言,也与前期工业社会有明显差异。身体功夫与工作失去了同一性,扬克脸上洗不掉的煤灰成了意蕴丰富的隐喻[7]。
综上所述,身体虽然是私人化的,但又是沉重的,肉身经常带有宏观结构——特别是阶级结构打下的烙印。在剧本中,工人的语言、着装甚至长相无一不体现出阶级的分化。另外,奥尼尔除了深刻认识到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所导致的身体差异,还清晰地指出生产性工作历时性变化导致的身体改变:健康的身体到动物性身体的蜕化。空间、时间、制度都是身体的规训性力量,身体功夫的调适功能由于压迫的加深趋于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