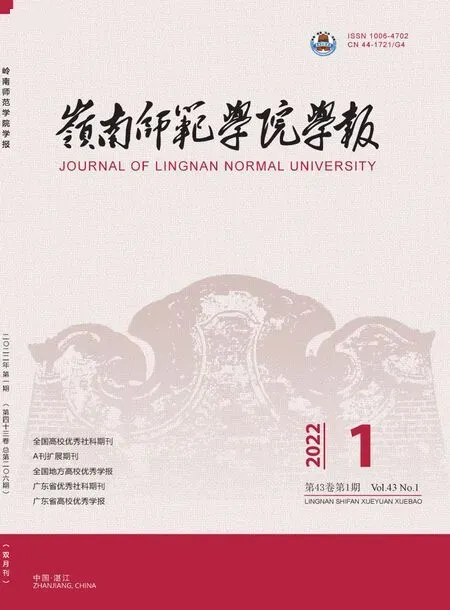主体的“自救”:论福柯对马可·奥勒留的挪用
金 露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福柯作为法国当代十分激进、富有反叛性的思想家,青年时期就对传统的理性思维方式持有怀疑,认为它“无法让人们真正认识‘自我’”[1]4,因而要学会非常规的思考方式。从他晚期的著作及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内容来看,福柯在经历“五月风暴”等诸多社会运动后,研究范围在时空上逐渐转向此前不愿谈论的古希腊-罗马。就晚期的“古典转向”而言,福柯在《主体解释学》(HermeneuticsoftheSubject)中屡屡提到一位古罗马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并多次引述其《沉思录》(Meditations)中的文本。福柯认为,“在马可·奥勒留那里,亦是如此,他多次提出这个命令:不要关心其他事,最好是关心自己吧。因此,在Ⅱ-8中,有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决不会倒霉的,因为我们不关心别人心里在想什么。在Ⅲ-4中:‘不要用人生的一部分去想象别人的所作所为。’……因此,不要盯着别人的事,只对自己感兴趣”[2]259。
马可·奥勒留是斯多葛学派晚期主要的代表人物,于公元161年继位为古罗马的第十二位皇帝。《沉思录》是他写给自己的书,在十二卷的篇幅中他与自己展开对话,内容涉及个人的行为准则、如何追求个人幸福、如何成为有德之士等。据学者刘北成指出,福柯“在写作《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andPunishment)时还嘲笑海德格尔以及德里达把柏拉图说成堕落从而美化早期古希腊文化的观点,表示自己不想谈论古希腊,‘不愿陷入希腊文化复古主义’”[3]269。加之他早期著作《古典时代疯狂史》(l'histoiredelafolieal'ageclassique)对疯癫史仅追溯到中世纪;《词与物》(OrderofThings)中,福柯认为思想与文化第一个间断性的认识从17世纪中叶开始;《规训与惩罚》以18世纪达米安行刑一事,引出刑罚与权力问题;书写《性史》(SexualHistory),福柯最开始的打算只是从16世纪的性史研究开始,可知他早期对古希腊-罗马文化主要持不屑态度,也不愿花费精力对其进行研究。而马可·奥勒留,这位处在柏拉图思想与基督教光环之下,略显黯淡的古罗马哲学家缘何会引起晚年福柯的注意?福柯挪用马可·奥勒留文本的用意何在?考察此类问题是理解福柯前后期思想的内在连续性、晚期伦理思想及当代权力与主体问题的关键。
一、福柯缘何挪用马可·奥勒留
古希腊-罗马人很早就将目光投向主体。以马可·奥勒留为代表的斯多葛学派,关注内容之一即是德行与主体生存的关系。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卷六中写,“只有一件事有很高的价值:就是真诚和正直地度过你的一生,甚至对说谎者和不公正的人也持有一种仁爱的态度”[4]90。卷十一中:“没有什么比那种豺狼似的友谊(虚伪的友谊)更可耻的了。要尽最大努力避免它。善良、朴实和仁慈都明确无误地在眼睛里展示”[4]185。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将对内在品质提出的要求,作为主体生存与处世的基本原则。此种对主体及内在精神活动的关注,为晚年福柯提供了新的思考。20世纪60、70年代,福柯频繁卷入到社会活动中,频发的政治运动使他逐渐意识到“知识问题不能脱离权力问题,知识或话语不仅受制于内部规则,而且更取决于各种力量的斗争”[3]167。根据德勒兹对福柯的解读,将可视性与陈述结合在一起的正是权力,而权力的本质是一种力量关系,不平衡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塑造主体。当福柯探究是何种力量塑造主体时,发现对犯罪、医学、精神病学追溯至近现代并未解决问题,“今天的历史,今天的主体经验,或许并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的产物”[5]10。要探索主体在历史初期如何被塑造,需转向“将力量连系到自我”的古希腊-罗马。转向马可·奥勒留等更为久远的古典思想,福柯要走向的是谱系学(genealogy)结合考古学(archaeology)本身提供的道路,即对主体展开“如何形成”的历史性、回溯式追问,探究其构成问题,抵达权力的本质,为近现代处于权力之网中的个体寻求希望。
其次,福柯在《主体解释学》中选择引述的是拥有特殊身份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这一“在罗马世界的政治领域里是唯一必须全身心地关心其他人的人”[2]236。对于一个以关心他人为职责的人,支配技术和自我技术的矛盾在其身上尤显突出,福柯所关心的,正是马可·奥勒留如何处理关心自己与关心他人的关系。通过考察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我技术,福柯要在外界现实的抗争途径之外,向内寻求一种新路径,以解决个体自由与权力规训的矛盾。他“曾经解释这种转向和以前关注的知识-权力理论的关系:‘如果想分析西方社会的主体系谱学,那就不仅必须考虑支配技术,而且必须考虑自我技术。可以说,必须考虑这两种技术的互动关系,因为人支配人的技术需要借助于个人对自己采取行动的方式’”[1]269。将对古希腊-罗马时期自我技术的讨论,作为支配技术的补充,分析主体的谱系,使福柯能从个体内在出发,考察身处权力网络中的个人,如何取得相对独立的位置、通过自我技术寻求主体自由。《沉思录》卷七中:“在任何工作都能按照符合于神和人的理性做出的地方,也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们害怕,因为我们能够通过按我们的结构成功并继续进行的活动而使自己得益,而在这种地方,无疑不会有任何伤害”[4]90。福柯注意到,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谈到帝王权力的地方很少,仅仅陈述行为的一般法则,即不把君权、帝权当作特权,只作为一份须审慎完成的工作或使命。马可·奥勒留“时时提醒自己做诚实的人,注意人性的要求。道德真诚对于皇帝来说不是由他的特殊任务或特权所界定的,而是由人性来定的——这种人性是他与其他人共享的”[2]239。他将君权当作一份从人性出发需做到真诚的职业,不是为了更好地监督帝国。首先是为自己担忧,“使自己得益”,并“在自身对自身的关系中找到了实施其君权的法律和原则”[2]243。因此,回访马可·奥勒留的文本,为福柯提供了如何处理好自我与他人普遍关系的启示,即善于运用自我技术,在权力关系中发挥主体的意志作用。
福柯曾在《主体解释学》课程最后,指出该年度的授课目标:“不必为认识自己搞出一部连续的历史,让它或明或暗地以一种普遍的主体理论为前提,但是,我认为必须从分析各种反思方式开始,因为它们是如此塑造主体的反思方式……以便可以赋予‘认识你自己’(knowing yourself)这一旧的传统原则它的意义(可变意义、历史意义、绝非普遍的意义)”[2]540。德尔斐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使“关心自己”的原则在其光芒下变得晦暗不明。一方面,福柯所做的是为“关心自己”寻找恰当的位置。他认为,在苏格拉底-柏拉图时期以后,也就是公元1-2世纪的斯多葛主义与马可·奥勒留的哲学中,“关心自己”有其重要位置。在《沉思录》卷六中,马可·奥勒留提示:“返观自身,不要让任何特殊性质及其价值从你逃脱”[4]74。卷七中:“关照内心。善的源泉是在内心,如果你挖掘,它将汩汩地涌出”[4]111。另一方面,福柯在《主体解释学》中对古代的各个修养史阶段进行关照,以《阿尔西比亚德篇》为导言,随后转向希腊化和罗马时代。他在1984年5月29日接受的访谈中提到,回归古希腊时代是为了“使欧洲思想在作为已有的经验的希腊思想的基础上,能够完全自由地重新启动起来”[6]521。福柯认为,使欧洲思想不能“完全自由地重新启动起来”,是因为基督教的影响。因此福柯回归至基督教以前的古希腊-罗马时期,试图摆脱的便是此种被基督教文化约束的状况。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自我解释学,不是否弃自身,也不是柏拉图式的将关心自己和关心他人进行必要的联系。反之,自我和他人的关系在罗马化时期被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此时不再是柏拉图时期的以关心他人和城邦为终极目的,而是将关心自我目的化。以马可·奥勒留的主张为例,《沉思录》卷四中,“那在我们心中的支配部分,当它合乎本性时是如此对待那发生的事情——使自己总是易于适应那已经存在的和呈现于它的东西。因为它不要求任何确定的手段,而是在无论什么条件下都趋向于自己的目标;它甚至从与它对立的东西中为自己获得手段,就像火抓住落进火焰中的东西一样”[4]90。主体的行为跟随它的理性,使自我达到合乎本性的目的,即使在对立的事物中,也是为了自己。福柯在“围绕着自我解释学在古代的缓慢成型重新组织整个研究”[7]109的同时,选择居于其间(苏格拉底-柏拉图与基督教时期之间)的斯多葛学派与马可·奥勒留的文本作为对照引述,试图重新找回一种自由形式的思想。挪用马可·奥勒留,是在看似连续的“认识你自己”的柏拉图传统和基督教文化的巨大影响下,重新探寻某种断裂,以此突破对主体的既定认识,亦是福柯对自身非常规思考方式的延续。
二、福柯对马可·奥勒留文本的挪用
“挪用”(misappropriation)是新历史主义的主导符码之一,有引用、参考、注释、套用、反讽等几种常见形式,包含对话语、文体、内容、题材的“挪用”等诸种表现形式。在此,福柯以引用加评论的方式,对马可·奥勒留的文本进行了内容上的“挪用”,有时也“从被引用的文本和话语中抽离出来并再次进行表述”[8]27。“新历史主义的‘挪用’既不是对对象的重复被动的‘复制’‘粘贴’和抄袭,也不是完全扭曲颠覆的臆断和消解,是一种互动互渗的积极的重读、重写和建构”[8]33-34。它基于原文本,将原文本作为出发点,同时是主体“积极的自我塑造和获取个性的手段”[8]35。福柯对马可·奥勒留等古典资源的挪用,是要为他此前研究的主体陷于权力关系中的悲观哲学,寻找某种更为积极的出路,以扼制或抵抗生存无希望的境况。除此,《主体解释学》中,显而易见的是福柯并非只对马可·奥勒留作单独引述,而是将其置于整个古代文化中来看——从柏拉图到基督教时期。因此在具体探究福柯对马可·奥勒留文本“积极的重读”时,必定要注意它与不同时期文本的对照,以及对照下显出的独特性为福柯提供的启示。
把自己塑造为主体,需要他者(1)福柯本人未对“他者”问题作过专门论述,但他关注的主体是被权力/话语/知识塑造的处于社会边缘的主体,事实上是另一种他者。福柯看到现代性进程中,理性对于作为他者的各类非理性进行的控制,因此他挪用马可·奥勒留以提醒主体关心自己,也就是关心受制于理性及其产物、被过分他者化的主体自身。此处的“他者”仅相对于“主体”而言。的介入,这是西方世界修身(2)福柯的“修身”与儒家的“修身”概念,两者均为一种自我实践,内涵上存在较大差异。对福柯而言,“修身”是他的研究方向转向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以后,关注自我的美学实践,包含“自我治理”“自我技艺”“生存美学”等,是把人生变成一件艺术作品的生存范式;而汉语中,出自《礼记·大学》“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中的“修身”概念,是儒家试图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达“明明德”的目的,即达到对天道真理的追求,改掉不良习性,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实践和主体性历史中的重要论题。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对话中,他者在修身实践中不可或缺,阿尔西比亚德经哲学家引导开始关心自己,为了将来能更好地治理城邦。到罗马帝国初期,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同样重要,但他者参与的方式截然不同。福柯从塞涅卡的书信中看出,此时他者“向个人援之以手,让他走出他所处的生活状态、地位和方式。这是一种对主体自身生活方式的影响,不只是传授知识,从而取代无知状态”[2]160。罗马时期的他者,不再以传统意义上的言语教育或传授理论知识的方式介入,而直接向主体伸以援手。福柯还从希腊化-罗马时期斯多葛学派的文本中发现,此前,“有关修身实践的大部分文本都是一边倒的:即来自导师、提出建议的人一边……这些劝告完全是徒劳的、空洞的,实际上并不处于人们的行为和经验之中,这是一个没有内容、没有实际用处的规定”[2]187,斯多葛学派的文本表明了某人(被指导者)对自己体验的反思。在塞涅卡《论灵魂的安宁》开头,塞里努斯用自白的方式向塞涅卡询问意见;在弗隆顿和马可·奥勒留的通信中,马可·奥勒留书信第六卷中致弗隆顿的第六封信记录,“这封信最大的特点是涉及在被指导者看来良心指导可能意味着什么”[2]188,我们看到“这封信不是以有关良心指导的专业的和技术的关系为中心的,实际上,它的支点是友情、感情和柔情”[2]189。马可·奥勒留通常要对白天所做的事进行回忆和反省,此后写信给弗隆顿。弗隆顿是马可·奥勒留的修辞学老师而非哲学老师,对方的哲学素养高低不再是良心指导的关键。福柯从塞涅卡和马可·奥勒留的文本中,发现了不同于柏拉图时代的思想指导方式。首先,不再以知识和理论,而是以直接提供帮助的方式介入。《沉思录》卷五中,指导具体到起床这一微小的事件中,“早晨当你不情愿地起床时,让这一思想出现——我正起来去做一个人的工作”[4]56。其次,劝告不再是空洞、没有内容的。“不是有关泛泛的语言或者话语”[2]195,而是由被指导者主动提出的、关于生活的具体反思,《沉思录》就以马可·奥勒留对自己进行指导的方式完成。卷十中,他写,“一从睡眠中苏醒就问自己,如果另一个人做了正义和恰当的事,对你是否将有什么不同”[4]165。最后,这种行为突破了传统教育的范围,从与哲学家两个人之间的事,逐渐发展为与其他人的社会关系。福柯引述斯多葛学派和马可·奥勒留的文本,对古代修身历史上,需要他者介入的修身实践作了补充,从唯哲学家提供理论指导,寻找到另一种以被指导者为中心的、更为开放且具体的修身技术。此时的自我,在福柯看来,从与他者严格的指导关系中被释放,使主体而非他者的重要性凸显,给予了前者更大的自由和自主空间。
在此基础上,福柯在希腊化-罗马文本中发现“自救”这一概念。基督教式的拯救总需要一个他者,而自救“是与诸如死亡、不朽或彼岸世界这类东西无关的。人不是与一个戏剧性事件或另一个肇事者有关而自救的。自救是用一生来完成的活动,其唯一的肇事者就是主体本人”[2]218。“自救”以人终生的修身功夫为拯救途径达到自身,充分发挥主体的意志,不受制于他者,如《沉思录》卷九中写:“让你在来自外部原因的事物的打扰中保持自由吧。”[4]151如果说马可·奥勒留的主体意志仍是限定在本性与自然法则的范畴内,那么福柯的挪用则试图使主体在自救层面达到最大程度的自主。
其次,不受制于他者,并不意味着脱离外界。斯多葛学派与马可·奥勒留认为人是世界中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世界而存在。当自我向外界敞开时,要面对如何处理认识世界与把握自我的关系。福柯在与其他古代哲学思想的对比中发现,马可·奥勒留有其独特的将认识世界作为途径、以把握自我的方式。伊壁鸠鲁认为认识物理的必要性是为了摆脱与生俱来的恐惧、担忧和神话,而斯多葛学派的认识自然,在伊壁鸠鲁提出的这一基本向度之上,还指“把握我们的现状,也即把我们重新纳入一个完全理性和令人放心的世界中”[2]236。换言之,斯多葛学派更关心的是个体能够通过认识自然,把握自己身处的理性世界。在斯多葛学派内部,福柯将塞涅卡与马可·奥勒留把握世界的方式作了细致区分。塞涅卡在《自然问题》中有对天地、星辰、江河等关于世界宏大的研究,对于为何撰写此类看似离“自我”很远的论题,“塞涅卡在《自然问题》第三部分的序言结尾处这样说:‘我们要通过观察、审视事物的本性来获得这种解放’”[2]320。亦或,“只有把世界探索个遍,才能达到自身”[2]311-312。塞涅卡从上帝俯视世界的地方观看此岸,看到与神性有共同结构的理性自身。马可·奥勒留审视世界的方式与塞涅卡不同,前者通过观察世界万物的结构和细节,见其肌理、骨骼,从而认识到人的理性和神的理性之间的共同本性和功能,福柯将此称为与塞涅卡“对称的反面”。马可·奥勒留认为,此种认识方式离不开沉思的训练和对事物独特性要素的观察。具体而言,“第一,在时间中分解对象的训练;第二,把对象分解为各构成要素的训练”[2]351。《沉思录》中:“如果你把一支乐曲分割成一个个的声音,然后对每一个声音自问,你是否被它征服,那样你将对悦人的歌曲、舞蹈和拳击比赛评价颇低”[4]179。若将歌曲、舞蹈、拳击比赛分解开,成为一个个音符、动作时,对人的情感冲击自然会减弱。“通过这种训练,我们不仅可以认识到对象是由什么构成的,而且知道它的未来会怎样,它会分解为什么,以及它在何时、怎样、在什么条件下会解体。因此,人们通过这种训练会理解对象的复杂实在和它在时间中的脆弱存在”[2]345。福柯的挪用弱化了马可·奥勒留文本中强调的,不会被分解的唯有永恒的德行,而是将他认识世界的独特视角——分解对象提出。主体以不从此岸与现实世界抽离的方式,达到把握世界的核心、认识对象的目的。个体在其中不被外界引发的恐惧或激情支配,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在世界中确立自身。
最后,文德尔班曾在《古代哲学史》中谈及斯多葛思想的特点之一:“‘哲人’让自己的意志符合自然的普遍法则,并且顺从于这种法则,那么他的行动就是自然的和理性的。在这种顺从中,他只是按照人之理性的要求来行动。斯多亚学派的伦理原则是顺从世界的法则,以此方式它具有某种宗教色彩”[9]290-291。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第六卷中同样表明了此种态度:“无论什么事情发生于每一个人,这是为了宇宙的利益的:这可能就足够了”[4]89。“如果神灵对于我,对于必须发生于我的事情,都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么他们的决定便是恰当的,因为即便想象一个没有远见的神斗士都是不容易的”[4]88。这是马可·奥勒留顺从世界的法则:人的意志要听从宇宙、自然和神。福柯如此激进而富有反抗性的思想家,在挪用斯多葛学派与马可·奥勒留时,自然不会完全接受此类“顺从”。他在《主体解释学》中,提到古希腊悲剧中人与神或命运的抗争议题,“它是有关诸神的嫉妒和人的暴行之间碰撞、较量和互动的论题。换言之,当诸神与人发生冲突时,考验就出现了,诸神给人带来了许多不幸,想知道人是否能够抵抗,又是怎样抵抗的,看看最后是人还是诸神取胜”[2]518。在福柯看来,对斯多葛学派而言,人和神的关系不再是希腊悲剧中的较量,“恰恰相反,正是诸神通过家长式的恨铁不成钢方式强加给人类一系列考验、不幸”[2]519,神为了考验、训练人,才使他们遭受各种不幸,以便他们身体强壮、英勇无畏。福柯对命运的“顺从”无疑是积极的,恶人不配遭受神降临的考验,因为“人生作为考验,这是善人专有的”[2]513。“变好是在所引起的痛苦中完成的,因为这种痛苦是一种考验,它被主体作为考验来感同身受。对于古典斯多葛派,我们可以说这是有关取消个人痛苦体验的思想”[2]517。接受神赐的痛苦是为了“变好”,而非消极意义上的接受命运的不幸、放弃抗争。因此,福柯对斯多葛学派顺从世界法则的挪用,采用了个体如何在世界中接受考验、获得成长的视角,全然不同希腊式的命运悲剧。
三、作为“自救”的自身伦理学
自笛卡尔以来的17世纪哲学,“认识自己”的理性法则取代了“关心自己”的修身训练[2]7,人们力图摆脱在哲学内部进行精神性的思考,认为主体本身通过推理分析就能达到真理。在此期间,由于对主体内部思考的欠缺,“虚无主义开始盛行。到了当代,道德既不以宗教为根基,又不需法律干涉,这样,道德危机发生了”[2]7。为克服道德虚无主义,19世纪哲学再次含蓄地提出了精神性问题,重新转向对内部及自我的关注。这种哲学也是对古代的主体从自我出发去寻求真理的方式的回归。此时福柯返归的马可·奥勒留的哲学及修身训练,是他作为个体,在17世纪以来的道德虚无感下寻求的自救之路,也是被歌德的浮士德所哀婉的“精神性知识”。福柯在《主体解释学》中分别考察了公元1-2世纪的犬儒主义者、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学派,以重新找回能改变主体生存方式的精神性知识:一种“对主体本身下功夫的真理”[2]227,而非纯粹认知范围内的真理。主体要改变自身,不是如塞涅卡选择向下统览世界,就是如马可·奥勒留通过分解的思维直达事物的核心,“记住对所有事物都使自己注意它们一个个的部分……也把这一规则应用于你整个的生活”[4]179。总之,不能通过维持现状来认识自己。这类似于被福柯引述的犬儒主义者德梅特利乌斯的观点,认为知识可以分为两种,有关外在世界的无用知识和与人的生存直接相关的有用知识,后者能使人战胜恐惧、蔑视痛苦,使灵魂达到德行的高度;或伊壁鸠鲁派的观点,认为“自然研究赋予了个人大胆、勇气和顽强,让他不仅可以面对人们想强加给他的许多信仰,而且还可以正视人生中的危险和想给他们制定法律的人的权威。毫不畏惧、大胆、倔强和矫健”[2]283。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提供的对认识世界方式的指导,与德梅特利乌斯的“有用知识”、伊壁鸠鲁派的“自然研究”同质。他认为我们的义务是要“观察和实践一切事情,同时完善你应对环境的力量,训练思考能力,不炫耀但也不隐藏地保有一种来自对每一个别事物的知识的确信”[4]163,目的都在于令真理作用于主体、改造主体,使二者接连,而非在虚无中屈从法律、知识或道德。
于福柯个人而言,他在质疑一切理性与既有规范的同时,又不相信任何乌托邦理想,即早期极力批判现代知识与制度等对人的规训,拒绝任何“理想的社会模式”。要如何在不是作用于此、就是作用于彼的权力关系中,寻找一个自洽的答案或希望?为此,他将伦理学、自我意志等现代观念引入马可·奥勒留的文本,并弱化斯多葛哲学中“将自我的意识看作自然的一部分、看作普遍理性的一个片断的倾向”[1]502,试图转向内部精神去寻找新的道路。斯多葛学派认为:“当一个人的神圣的部分能够有德地体现意志时,这种意志就是神的自由意志的一部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意志也就是自由的”[10]338。《沉思录》中,人的意志与神的关系同样如此,“讲到身外的神(或者说宙斯)把自身的一部分分给了人的理性灵魂(即身内的神),人凭内心的神,或者说凭自己支配的部分,就能认识身外的神,就能领悟神意”[4]3。福柯虽也关注到个人意志问题,但在引述马可·奥勒留时,不再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中,理性部分是神的意志的一部分,而将其独立出来。德勒兹将此种人的自由意志从外界脱离或分化,理解为“自我关系取得了独立性,这就如域外关系的褶皱与弯曲是为了作出一片衬里使自我关系得以出现”[11]104,只有使自我关系成为与政治、法则、道德等权力关系独立的“内在调节法则”,主体才能治理自己,而后治理他人。换言之,“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必须夹带与自我的关系;在权力强制性的规则中,必须夹带施行权力的自由人随意规则……这就是希腊人所做的:他们褶皱力量,却不致使力量不成为力量”[11]105。权力的规训与他人关系在此并未消除,但其中已夹带主体的自由意志——不再如马可·奥勒留所说的,从属于神。故而,福柯挪用马可·奥勒留的文本,通过对自身与他人治理方式的考察,在古代关于自我的修身关系中,找到了某种形式的出路与自救方式,如福柯言,“如果真的只有在修身关系中才有抵制政治权力的首要的和终极的支点,那么建立一种自身伦理学也许是一种紧迫的、根本的和在政治上不可或缺的任务”[2]259。
四、结 语
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课程伊始说:“我使自己有点像一头跃出水面的抹香鲸,留下一串稍纵即逝的泡沫,让人相信,使人相信,人们也愿意相信,也可能人们自己实际上相信,在水面下,有一条人们不再看得到的抹香鲸,它不再受任何人觉察和监视,在那里,这条抹香鲸走着一条深深的、前后一致和深思熟虑的道路”[12]6-7。福柯一生都在为质疑与突破权力范域而努力,致力于打破知识-权力对个体的禁锢。通过对马可·奥勒留文本及其他古典时期文化的思考与挪用,福柯延续了对权力的思考和自我的关心,在通向主体的自由之路上持续前行,这种复归,“与其说是回返,毋宁说是救援”[1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