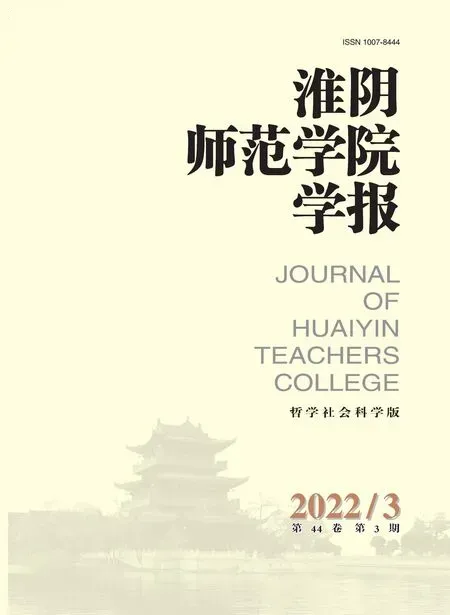明清盐商与淮安运河古镇河下的盛衰
杨满仁
(淮阴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3)
明清时期,因为盐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盐政与河工、漕运一样,被视为事关国计民生的要政之一。“煮海之利,两淮为最”,两淮盐业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据考证,“淮盐占到明代盐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在明代财赋中占有更大的份额”[1]。如此,便同时产生了数量众多的经营食盐的巨商大贾。盐务的兴盛带动了城市的繁荣,明清时期苏北淮、扬等地集聚形成了以盐业为主、依托城市、服务城市的城郊型繁华市镇,河下即为其中著名市镇之一。到清代中后期,河下古镇走向衰落。梳理河下古镇盛衰之间的社会历史面貌和文化发展情状,探讨盛衰背后的经济政治原因,无疑对当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淮盐产销与淮安河下的兴盛
河下位于今淮安市淮安区老城西北三里之外的古运河畔,其西、南阻里运河,北侧为古淮河山阳湾。据清末民初人王靓宸《淮安河下志》卷一《疆域》记载:“河下镇为山阳辖境,淮郡城外第一大聚落也。郡有城三:南曰旧城,北曰联城,又北曰新城。[新城]之西、联城西北,闾阎栉比,商旅辐辏者,河下也。”又载:“自明改运道,径指城西,贾舶连樯,云集湖嘴,繁滋景象,俶落权舆。继以鹾商纷然投足,而后人文蔚起,甲第相望。志乘标扬冠冕,阖邑称鼎盛者,垂三百年。”[2]21可见河下因盐业而兴,藉河运之便,成为淮安城外盐商云集、人文鼎盛的第一大市镇,繁盛长达300年。
淮安河下之所以成为盐商麇集之地,是与当时政府的盐政密切相关的。明弘治(1488—1505)年间,户部尚书山阳(今淮安)人叶淇奏改开中之法,实施纳银中盐的运司纳银制度,为河下的繁荣带来了重大机遇。所谓开中法,是明初实行的贩盐专利制度,“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3]。也就是政府为了充实边境军粮储备,而令商人输运粮食到边塞,粮食入仓后换取盐引(贩盐凭证),再到各转运使司指定的盐场支盐并运到指定地点销售。而所谓运司纳银制度就是召商开中引盐,纳银运司,类解户部太仓以备应用。此制度实施以后,盐商只需在运司所在的地方纳银就可中盐,因此,不但两淮赴边屯垦的商人全部撤业退归南方,而且在全国最重要的西北垦区的土著商人也迁至两淮。
明代两淮盐运使司驻扬州,下辖通州、泰州、淮安三分司,有学者考证,淮安分司亭灶、卤池的发展幅度要比泰州、通州二分司大得多,且淮安分司淮北五盐场采用晒盐法,比淮南煎盐法的生产效率高得多[4]69-70。淮安分司署本驻涟水,而淮北批验所本在涟水城南淮河岸边的支家河口。明中叶以后,由于黄河夺淮入海,批验所旧基在淮河南岸,当河流之冲,弘治、正德年间曾多次圮毁,后虽移至淮河北岸,但洪水困扰始终没有减轻。在此情况下,淮安盐运分司改驻淮安河下,而淮北批验盐引所改驻河下大绳巷,淮北巡检也移驻乌沙河。据《淮安河下志》卷二《公署》记载:“淮北批验所在大绳巷,本为程振扬旧宅,因案籍没,房屋入官,商人以资赎回,留为公用。嗣因旧批验所塌卸,遂以此为之。湖运向章,盐由场过老坝、三坝,至河北堆积包垣,届时出运,过掣署过秤,名曰‘批验’,方许上船,由乌沙河过堤,上运河大船。”[2]58随着淮安分司暨监掣等鹾务机构并驻河下,此后淮安西北关厢之地便成为淮北盐斤必经之地,大批富商大贾卜居于此,及至康熙三十年(1681)前后,侨寓河下的徽商西贾和其他贸易人户,总数可能多达数万。[5]6甚至有盐商从扬州迁居河下,其中最著名的首推程量越一支。《淮安河下志》卷五《第宅·程莲渡先生宅》记载:“吾宗自岑山叔信公分支传自第九世,曰慎吾公,是为余六世祖,由歙迁家于扬,子五人,长上慎公,次蝶庵公,次青来公,次阿平公,次莲渡公。莲渡公即余五世祖也。莲渡公诸兄皆居扬,公一支来淮,为淮北商,居河下,其所居之宅曰‘五字店’,五字乃旗名也。”莲渡公即程量越,是淮南盐务总商程量入的弟弟,“生子九人,俱成立。孙、曾蕃衍,旧宅渐不能容,分居各处,亦尚有一两房仍居老宅”[2]137。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构乱,温、台诸郡妇女被俘过淮者甚众,量越出金赎千余人,各资给遣归”[2]375。能够出金赎回千余人,且资助被俘者回归,可见程家财力之雄厚。除程量越一支外,歙县程氏还有不少人迁居河下,清初在淮安业盐者有13家,皆极豪富,以至当时有“诸程争用盐策富”[2]381的说法。
盐业的兴盛还带动了金融、典当等行业的发展。嘉庆年间,河下钱铺有三四十家,大者三五万,本小者亦三五千不等。上自清江、板闸以及淮城并各乡镇,每日银价俱到河下定,行人鼎盛,甲于他处。加以河工、关务、漕务生意特殊,有利可图,因此十分繁荣。[6]
二、盐商与河下市镇文化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文化的繁荣,而以宗族为基础的盐商大量聚集又使河下文化具有明显的世俗人文性、包容性、伦理型等特征,主要表现在市镇生活的世俗化、人文学术的繁荣和以家族为单元的园林别业的蜂起。
(一)盐商与河下市镇生活
因盐商多为举族经营、代代相继,大量盐商聚集河下,遂使河下迅速繁荣。明人邱浚《过山阳诗》云:“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曾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西湖即淮安城西管家湖,河下居管家湖嘴,诗中西湖嘴即河下,将河下和扬州相提并论,虽未免有文学的夸张在里面,但还是能够从中见出河下的繁华。
由于河下是新兴的市镇,城市街道等公共设施和慈善公益场所不少皆由盐商筹资建设。如河下最繁华的西湖嘴大街,此处“自运河筑堤,聚处者众。后又为淮北监掣之所,南自运河口,北抵相家湾,万商之涧,尤为繁盛”。然而其地崎岖,不便往来。徽州盐商程氏“捐白金八百两,购石板铺砌。由是继成善举者,指不胜屈,郡城之外,悉成坦途”[2]62。又有盐商程钟,乾隆中于西门外运河岸上设普济堂,建广屋一所,具一切器用经费,计输银一万四千余两,救活流民贫病者数万计,乾隆皇帝御书“谊敦任恤”匾额,派侍郎沈德潜便道赐之,沈德潜还为其作《普济堂记》。此外,盐商们还资助修建庙宇、创办书院,多方面促进了河下市镇的繁荣与发展。[4]187-198
乾、嘉以后,各地来淮的商人们还纷纷建起了会馆,如新安会馆、福建会馆、润州会馆、浙绍会馆、定阳会馆、四明会馆、江宁会馆、江西会馆等。众多会馆成为流寓河下经商的外籍人士定期聚会的场所,“每当春日,聚饮于中,以联乡谊”。此外还有楚人在都天庙旁建立公所,亦为会馆之类。[2]491-492会馆是由商业性人口流动而促成的社会组织,一旦建立并稳定之后,它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商业家族构成了纵横两个方向的人口聚集结构,从而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迁移与汇聚。有学者认为:“城市社会的演变主要体现在人口结构上。工商业人口的比重增加、市民阶层出现、社会组织中的业缘关系逐步取代血缘、地缘关系,社会流动增加和社会价值观念转变等,而会馆、公所的产生顺应了明清时期城市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满足了人口聚合所提出的要求。因此,区域市镇化的发展与移民经济和会馆、公所有着紧密联系。”[7]美国汉学家施坚雅提出:“人口密集本身就是一种与先进技术有关的生产潜力。”[8]会馆的大量出现既是河下市镇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也是其迅速繁荣并成为运河沿岸经济文化重镇的重要原因。
明中期以后,江南等富裕地区奢靡之风盛行,河下作为盐商聚集地,也出现了比较普遍的奢侈现象。关于河下盐商的豪奢,《淮安河下志》有云:“方盐策盛时,诸商声华煊赫,几如金张崇恺,下至舆台厮养,莫不壁衣锦绮,食厌珍错;阛阓之间,肩摩毂击,袂帷汗雨,园亭花石之胜,斗巧炫奇,比于洛下。每当元旦、元夕、社节、花朝、端午、中元、中秋、蜡腊,街衢巷陌之间,以及东湖之滨,锦绣幕天,笙歌聒耳,游赏几无虚日。而其间风雅之士,倡文社,执牛耳,招集四方知名之士,联吟谈艺,坛坫之盛,甲于大江南北。好行其德者,又复振贫济弱,日以任恤赒济为怀。远近之挟寸长,求嘘植,及茕独之夫,望风而趋,若龙鱼之走大壑。迹其繁富,不啻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之所叙述,猗欤盛哉!”[2]23盐商的衣食住行,莫不奢靡无端。尤其在美食方面,淮安本就是鱼米之乡,水产甚丰,又是南来北往商人汇聚之地,这些盐商和河、漕、盐、关的官吏们一起,成为创造淮扬菜的主体。茶坡《鲈鱼歌》云:“淮阴近日鲈鱼美,不待秋风常出水。市南市北何处多?钓台西去枚生里。细鳞簇簇白如银,入馔充盘妙无比。”所写的正是淮安美食。
除了美食,盐业等商业的繁荣还促进了河下医业的发展,“他们小病大医,无病进补,服药唯恐不贵,故悬壶者环居其侧,以为生财之肥源。故河下素有丛医镇之称”[2]13。著名的山阳医派代表人物,著有中医四大经典之一《温病条辨》的吴鞠通就是河下人,据其《温病条辨自序》,他十九岁有感于父病弃举业而从医,七年后赴京城,检校《四库全书》,其学医的初始时期正是在河下度过。[9]
(二)盐商与河下人文学术
封建社会钻研经术、博取功名始终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志向,盐商业鹾致富,然大多仍始终不忘读书明经的正途,所以特重家族子弟的教育。且因其富有,多能延聘宿儒名士教授学业,子弟教育条件皆很优越。故明清时期河下人文蔚起,科名相望。据统计,明清两朝此地竟然出了56名进士,其中状元、榜眼、探花都有,可谓煊赫当时。此外还有举人、贡生百余人,武进士、武举十余人。[2]341-350更有多人在《明史》《清史稿》中有传,这在江南诸多名镇中也殊为罕见。
淮南程氏为寓居河下盐商之第一大姓,族中不乏饱学风流之士。如被袁枚称为程氏四诗人的程嗣立、程崟、程梦星、程晋芳,其中三人居于河下。程嗣立,人称“水南先生”,廪贡生,乾隆初,举鸿博,与兄垲并工文章,善书法,嗣立兼精绘事。兄弟就故家曲江楼,结诸名士为文社,金坛王汝骧评骘其文,极一时之选。[2]380有《水南遗集》传世。程崟,大盐商程维高第三子,进士,历官兵部郎中,有《二峰诗稿》《编年诗集》。程晋芳,“歙人,业鹾于淮。乾隆初,两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君独好儒术,磬其赀购书五万卷,穷日夜讨论之。天子南巡,君献赋行在,召试第一,赐举人,授中书。寻举进士,授吏部主事。《四库》馆开,以荐为纂修官。书成,擢编修”[2]388。程晋芳与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吴敬梓等人皆有交游,其本人也博综群籍,著作甚丰,所传有经学著作《周易知旨编》三十余卷、《尚书今文释义》四十卷、《尚书今文解略》六卷、《诗毛郑异同考》、《春秋左传翼疏》三十二卷、《礼记集释》、《诸经答问》十二卷,有目录学著作《群书题跋》六卷、《桂宦书目》,诗文作品《勉行斋文》十卷、《蕺园诗》三十卷。[2]443据《淮安河下志》所辑,程氏尚有程钟、程用昌、程志铎、程襄龙、程维高、程均、程垲、程銮、程秋水、程哲、程沆、程洵、程益、程锁、程得龄、程世椿、程擢等多人有集。与程氏交往颇密的河下吴氏也是当时的文化望族。盐商吴宁谔,为诸生,有名,曾与从兄吴宁谧共同参与当时曲江楼文学盛会,其子吴玉镕承世学,淹贯群书,见闻广阔,中乡试第二、会试第十三,有《稻孙楼诗》。吴宁谧子玉搢,号山夫,幼承家学,博通群籍,尤其精通金石考证之学,游京师之时,当时的大学者翁方纲等争着拿出所著之书相质;秦惠田所著《五礼通考》多出于玉搢手订。吴玉搢所著有《别雅》五卷、《金石存》十五卷、《说文引经考》二卷、《六书述部叙考》、《日知录评注》、《山阳志遗》四卷、《山阳耆旧诗》四卷、《四朝黄河图说》、《天玺神谶碑图说》一卷、《十忆诗》、《钝研斋文集》三十卷。
河下明清学者中最著名的当属清初考据学者、乾嘉学派杰出先驱阎若璩。阎若璩也出身于盐商之家,明正德初,其六世祖由山西太原迁至淮安经营盐业。阎若璩父亲阎修龄为淮上名士,望社创始人之一,母亲是明嘉靖己未科状元、清河丁士美的孙女。阎若璩长于考据,二十岁时,读《尚书》二十五篇,即疑其讹,自是沉潜三十余年,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至此大明。梁启超评价道:“自此以后,今文和古文的相对研究,六经和诸子的相对研究,乃至中国经典和外国经典相对研究,经典和‘野人之语’的相对研究,都一层一层的开拓出来了,所以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10]阎若璩的学术著作十分丰富,计有《四书释地》一卷、《释地续》一卷、《再续》二卷、《三续》二卷、《潜邱札记》六卷、《尚书古文疏证》、《毛朱诗说》、《续朱子古文疑》、《丧服翼注》、《孔庙从祀末议》、《孟子生卒年月考》、《校正困学纪闻》、《日知录补正》、《宋刘攽、李焘、马端临、王应麟四家逸事》、《阎氏碎金》、《博湖掌录》等,另有《眷西堂诗集》。
河下优越的经济环境催生了浓郁的人文氛围,明清数百年间人文荟萃,除了上文所列,还有明代文学家吴承恩,清道光帝师大学士汪廷珍,清代数学家骆腾凤,天文历算家汪椿、吴玉楫,画家黄粲、尚培英等。
(三)盐商与市镇园林文化
河下盐商大多为外籍寓居于此,业盐以获巨利,便纷纷修建园林别业,经二百余年的不断经营,淮安河下已是园林广布,“虽仅附郭一大聚落,而湖山之胜,播闻海内”[11]510。据清末人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考索,自明嘉靖间至清乾嘉时期,河下构筑园亭计六十五座,其中不少皆由盐商所购或修筑。其中著名者如依绿园、菰蒲曲和荻庄。
依绿园,清吏部考功司主事张新标、翰林院检讨张鸿烈父子的别业,在萧湖中,有曲江楼、云起阁诸胜。这里曾是清初淮安文学社团望社的主要活动地点。张新标曾大会海内名宿于此,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毛奇龄当时避难淮安,“预其胜,赋《明河篇》,一夕传抄殆编”。日后毛奇龄与张鸿烈同登康熙己未博学鸿儒,又都被敕参与纂修《明史》,诚为淮安文化史上的佳话。后此园相继为盐商程用昌、程眷谷所得,易名“柳衣园”,有曲江楼、云起阁、娱轩、水西亭、半亩方塘、万斛香诸胜,皆为李元庚所亲见。乾隆年间,盐商程垲、程嗣立“聚大江南北耆宿之士,会文其中”[11]531。以金坛王罕皆、耘渠两先生和长洲沈归愚(德潜)主坛席,河下周白民、程嗣立等称“曲江十子”共襄盛会。所著《曲江楼稿》风行海内。史载前后两次文学盛会,足可见当日河下之人文鼎盛。正如李元庚所感叹的那样:“时寰宇升平,人文蔚起,河下又当南北之冲,坛坫之英,风雅之彦,道出清淮,鲜不至柳衣园者。吁!一园而数易其主,而主是园者,皆通儒硕彦,递执骚坛牛耳,且百余年,何其盛与!”[11]531
程眷谷另有宅名可继轩,在梅家巷头,亦为当时名园。由此宅脱颖而出者有他的后人程垲、程嗣立、程捷、程擢等,均以文才显名。
菰蒲曲是程嗣立的别业,在伏龙洞。园中有来鹤轩、晚翠山房、林艿山馆、籍慎堂、稻香楼、二杞堂诸胜。据时人文集所记:进入此园,小桥绿柳,有山林气。坐其室,几案图书,无不入古。园中迤逦而北有楼,楼外树数株,中有银杏,高三丈,大可合抱。可见此园规模和园中景色之美。
另一著名园林当属程鉴的别业荻庄。程鉴,字我观,号镜斋,少孤贫,用盐策致富,成为淮北大商。富裕以后乐善好施,赈恤寒困。程氏荻庄甚为壮观,园在萧湖中,门在莲花街,有补烟亭、廓其有容之堂、平安馆舍、带湖草堂、绿云红雨山居、绘声阁、虚游、华溪渔隐、松下清斋、小山丛桂留人等众多景点,其楹、额皆为名家或地方官员所题。史载:“此园三面临水,芦荻萧萧,栖霞岭不为过也。”[11]544《淮安河下志》卷八引《潜天老人笔谈》云,乾隆四十九年春,皇帝南巡过淮安,诸盐商曾拟自伏龙洞至南门外起造十里园亭,以荻庄建行宫开御宴,后因时间仓促作罢。镜斋之子程沆致仕告归后,曾于此宴集南北名流,拈题刻烛,一时称盛。其中袁枚题云:“名花美女有来时,明月清风没逃处。”赵翼题云:“是村仍近郭,有水可无山。”足见当时宴游者对此处之喜爱。
三、纲盐改票与河下的衰落
河下兴既因盐,衰亦因盐。清代盐务全盛时期,两淮盐商多达百数十户至数百户。[5]8然而到嘉庆年间,淮北盐务即开始由盛转衰,这主要是由于不合理的“湖运旧章”所致。原来淮北盐斤在产地价格甚为低廉,但因场盐斤到各口岸,中间需经淮安西北掣验改捆,这虽给当地工人带来大量的谋生机会,但也给盐运增加了大量成本,以致官不敌私,私盐盛行。当时淮北大使林树保议改淮北运道,竟引发一场盐工骚乱,“倚盐为生者,麇集累数千人,各持香哄于署(淮北批验公署),遂毁。楠木厅火一昼夜,香澈四野。大吏为按诛首恶,林亦罢去。……未几,而纲盐废矣”[11]541。所谓“纲盐废”即道光中叶的纲盐改票。时两江总督陶澎有鉴于淮北盐务疲敝之极,上疏改行票盐:凡富民挟赀赴所司领票,不论何省之人,亦不限数之多寡,皆得由场灶计引授盐,仍按引地销行。(1)黄均宰《金壶浪墨》民国版。这一政策的施行将纲盐商世袭垄断的特权和暴利尽行剥夺,对河下盐商的打击是巨大的,自此群商大困,人口凋敝。史载:“三十年来,一切都成陈迹,富商巨室,均归销歇,甚者无立锥之地。游手骄民逃亡殆尽。与夫水亭花榭,皆废为瓦砾之场,惟有麦畦、菜圃、梳柳、苍葭点缀荒寒,俨同村落。即不事盐策,耕且读者,亦强半左支右绌,苟且图存,求如曩时繁富之万一,邈然不可复得。”[2]23清人黄钧宰《金壶浪墨》也有类似记载:“改票后不及十年,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12]李元庚的《山阳河下园亭记》中也多有反映,如前文所述的荻庄,“道光初,鹾务凋敝,南河袁司马埛,出五百金,意购为公宴之所,程族阻之,遂中止。旋成废圃矣”[11]545。为《山阳河下园亭记》作序的丁晏年少时曾游于荻庄、柳衣园,其序云:“道光甲申,纲盐改票,鹾商失业,售拆此园,刬为平地。此记所云高台曲池,沦为乌有,不啻雍门之涕矣。”[11]507可谓道尽了河下的盛衰兴废之叹。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3]河下因盐而盛,又因盐而衰,在其盛衰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生产方式的变化对运河沿岸市镇发展的巨大影响,以及经济因素对城市发展的支撑和解构。淮安河下的兴衰至少表明了两点:一是作为清中叶以后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淮安河下的由盛转衰充分说明导致社会变迁的是经济的、政治的和技术的、地理的因素与竞争、冲突及结构性张力等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经济因素,并不是通常人们所想象的因为有新的更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替代运河运输的结果,因为嘉庆、道光时期的中国还没有铁路。二是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繁荣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河下经济社会的兴盛催生了繁荣的人文学术、饮食、医学和市镇园林等文化,但随着经济的衰落,繁荣的文化也随之凋零。可以说,淮安河下古镇的盛衰史生动地反映了明清运河文化的发展史、明清盐商的社会生活史和盐政的变革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