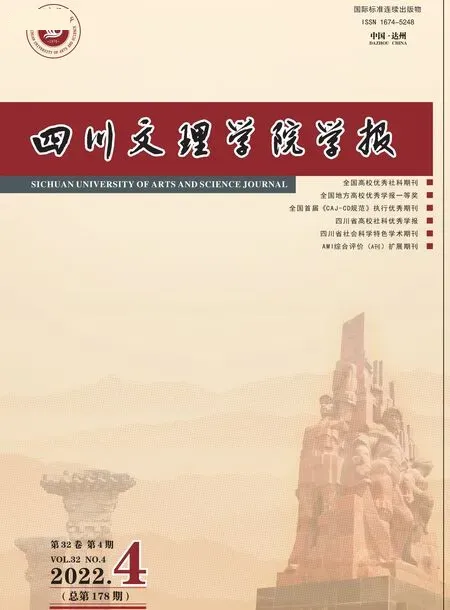再析朱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康德衡
(三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当今社会,谈到宋明理学颇有一些人会联想到戴东原的“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1]188“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1]275就会联想到新文化运动批判过的“吃人的礼教”。仁者爱人,儒家自古以仁爱自居,却为何在此事上如此没有人情味呢?理学又为何会在现代人心目中产生如此的阴影呢?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座高峰,一代大儒朱熹饱受近现代人诟病的一个地方是他认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提倡寡妇守节,以此作为儒学礼教杀人的证据之一。其实,“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并不是朱熹最早提出的,这句话实际上是程颐在特定环境下所说,朱子只是做了引用而已。
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2]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朱子提倡的道德标准是针对地位身份较高的士大夫阶层,而不是严苛地针对广大底层的老百姓。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论实质,探究其在历史上真实的状况,即这句话是否起到过“礼教杀人”的作用。唯有这样才能够正本清源,荡涤程朱理学这处不白之冤,使程朱理学焕发本自圣洁的光辉。
一、现实中的程朱对妇女再嫁持宽容态度
南宋时期,面对外敌入侵国家危难,朝廷上下投降派颇有势力,朱子重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具有警示作用。这条原则用于士大夫阶层,是完全正确的道德标准,倘若仅仅用在约束寡妇改嫁这种“小节”问题,则是舍本逐末之举。而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
最早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程朱等人,皆有亲友女子“夫死再嫁”的情形,不仅他们本人没有反对,在当时也不是什么“有伤风化”的事。
在这个问题上,程颐自己写的文章应比弟子后学整理的语录更能体现其本人的真实思想。程颐给父亲程珦写的传记《先公太中家传》的部分内容被朱子收录到了《近思录》卷六“家道”中,这段文字如下:
“先公太中讳珦,字伯温。前后五得任子,以均诸父子孙。嫁遣孤女,必尽其力。……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惧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归嫁之。”[3]651
程颐颇为郑重地记载了其父接回寡居的甥女,助其再嫁,作为其父乐于助人的例证之一加以赞许。朱子也特地从二程文集中选取这段内容,收录到《近思录》中。这其实已可说明程朱对于寡妇再嫁的问题,并非那样苛酷森严。
在《朱子语类》中,朱子师生间还有对这个事情的讨论:
问:“取甥女归嫁一段,与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
曰:“大纲恁地,但人亦有不能尽者。”[4]3250
朱子的意思大概是原则上说寡妇不应再嫁,但人情上讲也不能完全这么办。
在《朱文公文集》中,朱子则说得更明确:
“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4]3025
既然圣人不能禁,那常人自然更不必禁了。朱子甚至有更进一步的看法,不但丈夫死了,妻可再嫁;即便丈夫活着,如其不成器,妻子也可主动离弃。《朱子语类》里有这么一段讨论:
“建阳簿权县。有妇人,夫无以赡,父母欲取以归。事到官,簿断听离。致道深以为不然,谓夫妇之义,岂可以贫而相弃?官司又岂可遂从其请?”
曰:“这般事都就一边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无以自给,又奈何?这似不可拘以大义。只怕妻之欲离其夫,别有曲折,不可不根究。”[4]3469
这段话大意是:某地一妇人,因丈夫贫穷,父母打算让她回家,到了官府,判决允许其和丈夫离婚。朱子的学生不以为然,认为夫妇之义,怎能因为贫穷就抛弃对方呢?官府又怎么能批准其请求呢?
朱子的看法却开明得多,如果丈夫确实不才,不能养活其妻子,那又怎么办?这种情况就不能光用大义来苛责妻子了。当然,如果因其他原因要离婚,还是应该仔细探究一下。
其实程颐也有类似宽容的看法,丈夫要和妻子离婚,也不应过于张扬妻子过恶,而要让对方离婚后还能有再嫁的机会。
(程子)曰:“古之人绝交不出恶声,君子不忍以大恶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见其忠厚之至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浅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说话,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个含容意思。”
(有学生)问:“古语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绝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
(程子)答:“是也。”[3]243
冯梦龙的《喻世明言》第一卷,可谓程子师生这段对话的生动实践。《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是《喻世明言》开篇第一个故事:女主人公王三巧因丈夫蒋兴哥经商长期外出,耐不住寂寞有了外遇。事情败露后,蒋兴哥并没有对妻子苛责辱骂,仅仅是一纸休书,忍痛听任老婆改嫁。女方父母对女儿的行为也能理解,没有过于责怪,倒是安慰王三巧道:“恁般容貌,怕没人要你?少不得别选良姻,图个下半世受用。你且放心过日子去,休得愁闷。”[5]
蒋兴哥在王三巧改嫁之际,还念及旧情赠送了丰厚的陪嫁。这一善举为以后两人能够破镜重圆埋下了伏笔。从这个故事足见当时人们对于妇女出轨持相当宽容的态度,并无森严残酷的“吃人礼教”。
以上事实,并不是程朱二人的理论和实际严重脱离,而是他们对待妇女改嫁问题本来就是如此认为的。“听其言,观其行”唯有从行动中最能准确地判断人的思想实质。
程颐师生之间的这段对话,亦更加令人怀疑后人所编语录中程颐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真实性。历史上诸如“郢书燕说”“三豕过河”“三人成虎”“曾子杀人”之类的以讹传讹的现象并不鲜见,编纂程颐语录时此类错误也在所难免。这种解释具有更大的合理性与可能性。
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符合儒家道德原则
“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6]“儒者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7]“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8]“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9]
儒家是博学多识的一个学派,因而对待事物能够从客观实际出发给以实事求是的分别对待。儒家的道德要求,对于士大夫阶层是严要求,高标准;对于普通百姓则根据实际做了相应的调整,所以有了“礼不下庶人”的原则。繁琐严格的礼教对于为生存忙碌奔波的底层民众既没有必要,也很难执行。如此,寡妇改嫁只是“小节”,大丈夫“失节”是“大节”,是极为严重的问题。作为“小节”,在“对亡夫忠诚”和“生活压力”之间,是可以做“权变”的。
儒家高度重视气节和荣誉,坚信名誉是比生命更贵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一条基本的、普遍的道德律条,并不单纯针对妇女改嫁。婚嫁问题的适用仅仅是此原则的一个特例。假如程朱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一条严苛的道德原则强加于底层妇女身上,那么他们无异于违犯了儒家另一条重要的原则“礼不下庶人”。[10]而这是不可能出现在他们身上的极小概率事件。
作为一代大儒,朱子同样对于荣誉名节的养成高度重视,史载:
授以《孝经》,一阅,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11]
在读《孝经》的时候,朱熹感觉写得非常有道理,忍不住题了一句:“做不到这样,我就不是人。”
朱熹对于为政者的卑躬屈膝、毫无气节的做法更是嗤之以鼻。在《资治通鉴纲目》引范祖禹之论曰:
“自汉以女嫁匈奴,而後世习为故常,不以为耻而以为法。以为畏之邪?则是以天下之大而畏人,至于纳女,耻也!以为谋之邪?则是以女为间,而欲夺人之国,亦耻也!高祖不谋于众贤,而问诸亡国之臣,宜其不知耻也。夫匹士求偶,犹以其类。今乃以天子之女而弃之戎狄,变华为夷,岂不哀哉?然终唐之世,人君行之不以为难,其臣亦不以为非,由高祖启之也。”[4]2174
此段议论前部分重点在于批评统治者“和亲政策”有损国格,后部分其注重点亦在妇女本身之个体价值与尊严。所谓匹士求偶的原则,即布衣百姓为自己女儿寻求配偶,还要注重才貌品类气性之合拍,以此对照可见把天子之女弃之戎狄之可哀。
清代名儒汪绂说:“程子此章之言非过也,常理而已。孀妇怕寒饿死而失节,何异于臣怕战而降贼哉?”[12]汪绂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并非专指妇女再嫁。这也符合儒家一贯倡导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道义标准。清华大学国学院陈来院长指出:
“‘节’本来亦指气节、节义,即指道德操守,因而如果把节理解为道德、操守的意义,而不仅仅把节限定为贞节,则‘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正是孟子‘舍生取义’的另一种形式的说法。特殊地看,在贞节的意义下,程颐这句话是从儒家舍生取义的一般原理中引申出来的。”[13]
当代研究朱子理学的大家朱杰人教授也说:
再从儒学思想大系统来看, 孔子倡“杀身成 仁”“匹夫不可夺志”, 孟子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司马迁泰山鸿毛之说,可以说与程朱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一脉相承的,都是针对知经识理的君子提出来的道德规范。[14]7
针对那些紧紧盯住程朱理学这一“谬见”不放的当代学人,朱杰人又提出严肃的批评: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更主要的是针对知经识理之君提出的,是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失节”重于“饿死”,“气节”重于“生命”,这涉及到一个人的人生观、生死观的问题,这是对男人的更高层次的精神要求。程朱“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是特殊场合提出的,是针对士大夫而发的,乃举孤孀为例而勉励强调士大夫之守节持道。学者不于程朱贡献及其理论的现代价值等大处用力,而锱铢于特定场合所论妇女再嫁问题,实在是舍本逐末,非学术正途。[14]7
三、礼教杀人在宋明社会并非事实
在南宋时期,程朱理学尚未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甚至还一度受到朝廷的毁禁。那么,“礼教”在社会实践中的真实情况如何呢?宋代妇女的婚嫁并没有受到此条戒律的影响,一直到明代主流社会并不支持妇女守寡。
对于绝大多数的底层劳动妇女来说,如果丈夫死亡,那么势必是要再嫁的。两宋时期,大土地所有制的兴盛与发展,导致许多无地少地的底层人民失去生活依靠,随着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大多数劳动人民都从原本“一亩三分地”的主人转变成为地主“打工”的佃农。
在农耕文明时期,“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模式是常态,男子可以说是支撑家庭生计的主要劳动力。丈夫一旦去世,妇女就会失去依靠。除了极少数卓越女子可以依靠自己来维持生计、抚养孩子、伺候公婆,绝大多数守寡妇女为了生存,都会选择再嫁。
大家知道,宋朝是古代经济发展的巅峰时期。这时候商品经济发达,物质的丰富折射到思想上,就催生出了“重利轻义”。
这种思想反映到婚姻问题上,就是妇女对贞节观这个概念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不只是妇女本身,就连当时的许多官僚、诗人等,也多从现实出发,认为寡妇没有必要守寡。
比如宋朝《夷坚志补》卷十四中《解询娶妇》记载的:靖康建炎之际,解询和妻子走散了。后来解询在去做官的路上另娶了一位妻子,在重阳节掌灯的时候,解询思念起原来的妻子。他的新妻子知道后,为他准备出行的器具去寻找旧妻,并说:“我与俱行。倘君夫人固存,自当改嫁,而分囊聚之半;万一捐馆,当为偕老。”[15]608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新妻自己对改嫁这回事没有什么抵触,也不觉得再嫁就是不光彩的。
当时的社会价值观中,大家都没有将妇女的贞节看得很重,所以在当时人们的思想里,再嫁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无关贞节,也不会对名誉、地位等其他方面造成不好的影响。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明确规定:“不逞之民娶妻,给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16]对于普通平民已婚女子来说,如果因丧夫而守寡,妇女如果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生活,是允许直接改嫁的。
到了南宋时又进一步规定,如果丈夫外出三年不回家,也是可以再嫁的。其实纵观宋朝保护寡妇再嫁的政策诏令,可以看出是一步步放松条件限制,尽可能地保护寡妇的权益的。
明代朱子理学已经上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反对寡妇改嫁”是否就在民间盛行起来了呢?
著名的明代白话小说集《三言二拍》,反映了当时普通群众对妇女改嫁的看法。《况太守断死孩儿》是《警世通言》第35卷,故事梗概如下:明朝宣德年间,丘元吉与邵氏夫妻恩爱,后来元吉病死,妻子邵氏立誓为丈夫守节。双方亲属非但不支持邵氏守寡,反倒苦口婆心轮番劝阻,“父母家因其年少,去后日长,劝他改嫁。叔公丘大胜,也叫阿妈来委曲譬喻他几番。那邵氏心如铁石,全不转移。……众人见他主意坚执,谁敢再去强他。自古云:‘呷得三斗醋,做得孤孀妇。’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从长计较,倒不如明明改个丈夫,虽做不得上等之人,还不失为中等,不到得后来出丑。正是:做事必须踏实地,为人切莫务虚名!”[17]
从小说的记述看出,在明代社会,事实上亲属普遍不支持妇女守寡。从“替邵氏从长计较,到不如明明改个丈夫”一句,足可以看出作者也是明确反对孀妇守节的。
再比如《初刻拍案惊奇》的第6卷《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中说贾秀才得知老婆被歹人迷奸,并没有因此嫌弃她,反而加以安抚道:“不要短见,此非娘子自肯失身。这是所遭不幸,娘子立志自明。今若轻身一死,有许多不便。”[18]76如此,才有后来夫妻两人巧施妙计成功复仇。“那巫娘子见贾秀才干事决断,贾秀才见巫娘子立志坚贞,越相敬重”。[18]80
这个事例中,贾秀才作为一介儒生,并没有对意外失身的妻子心生厌恶,反倒是“越相敬重”。由此可以看出,儒学熏染并未令读书人心理扭曲。
还有,从明代小说《二刻拍案惊奇》关于“男女大欲,彼此一般”[19]一段议论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待“男女大欲”相当开通,绝不是今人所认为的那样冷酷苛刻。
综上,理学盛行的明代,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绝不可认为存在大量所谓的“礼教杀人”现象。
四、亟需适时纠正对先贤之误解
总的来看,对于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产生的异议,极有可能是后学门生在编纂程子语录时发生错误。程颐在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是在特定语境下且有特定含义的。二程的后学门人在做文字辑录时,也难免误解了老师的实际所指。当代人以偏概全,却自认为古人教条。如此竟然还获得了廉价的优越感,何其可悲可叹!
首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在程朱等理学家看来,是对正人君子的基本要求。此语应该是对气节高度重视的儒家的普遍道德原则,适用于男子的忠贞不渝,也适用于有身份的女人。比如,宋庆龄等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本来以“孙中山夫人”享誉,一旦改嫁带来的荣誉损失则无比严重。古人云“礼不下庶人”,拿这种严格繁琐的礼教约束普通百姓就有悖人伦了。诚如陈荣捷先生所言,朱子所说妇女不再嫁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已, 朱子所谓“大纲恁地,但人亦有不能尽者。”如此,并不能因为妇女改嫁问题上的具体是非,来否定儒家“重义轻利”基本原则的正确性。
再者,儒家在处理抽象的“道德伦理”和具体的“生活实践”上,是贯穿着一条“经权”理路的。“经”是基本原则,“权”是灵活变通,要综合运用。在寡妇改嫁问题上,对配偶忠诚不渝是“道德原则”是“经”,因生活压力而改嫁则是“生活实践”是“权”。
第三,道德是具有时代性的。我们不能拿今天的道德标准去对古人妄加评价。儒家的观念里,生生不息、繁衍后代乃人生的重大意义之一。寡妇改嫁则不利于养老抚幼,原有的家庭无以为继。儒家更多地是从这一社会功利加以考虑的。
但是,清代以来,处于部族统治的需要,对汉族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文化管制政策,一定程度导致知识分子阶层心理的扭曲,于是将压力转嫁给女子守节来实现心灵上的平衡,也不是不可能的。
上述可见,无论理论抑或实践,儒家之态度,还是有人情味的。有些地方比现代人遇见同类事情的处理手段更为宽容。至于到清朝治下,在礼教名目下弄出许多残酷凶虐之事,如清末民初尚有类似鲁迅笔下祥林嫂之类的悲惨事件,则此时之儒家早非真儒家矣。其深层原因或和元朝统治时期弄出一个宣扬郭巨埋儿之类恶行的“二十四孝”类似。
满清统治者大力宣扬忠义节烈等,也是为了便于统治,固化人们对身份的认知,造成君贤、臣忠、民孝、家安的太平景象。此时,除了对男子提出了更严格的忠君思想之外,对女子的忠孝贞洁观,也加以大肆鼓吹宣扬。
最后,我们引用朱杰人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以增加文章的亮色,算作狗尾续貂的反用吧。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一种崇高的品德与境界,是儒家思想中自强不息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绝精神与信念,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不同流合污的高尚气节,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丈夫的骨气。从这一角度来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对信仰的执着追求,是一种死守善道的精神,具有刚强坚毅的浩然正气,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唯守此大节,方可立于天地之间而不朽。[14]7
——以《程朱阙里志》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