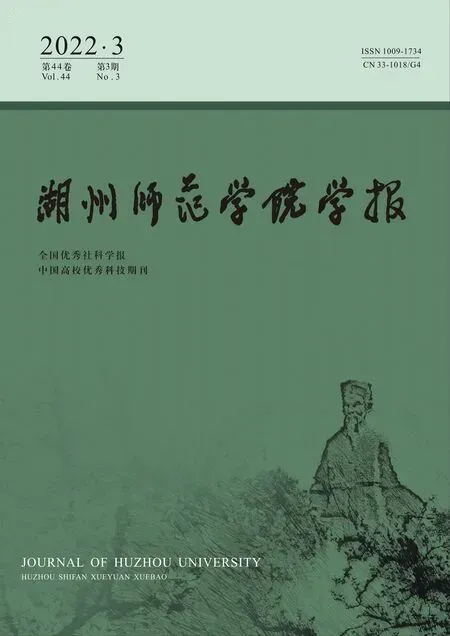“獭祭曾惊博奥殚”*
——清儒冯浩笺注李商隐诗特点发微
田 竞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冯浩,字养吾,号孟亭,嘉兴桐乡人。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卒于嘉庆六年(1801),得年八十三岁。乾隆十三年(1748)冯浩三十岁时,中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参与纂修《续文献通考》。其后,担任过两次乡试考官,两次会试考官,以及咸安宫学总裁,短暂地任过一年山东道监察御史[1]41。乾隆二十二年(1757)其母亡于京邸,他于第二年护送母亲灵柩返乡,因“心疾滋深,服阙后,庚辰北上赴补,中途而返,遂不复再出”[2]391。他仕途短暂仅为官八年,但颇为长寿。归家养病后,除先后入崇文、蕺山、鸳湖书院培养后学外,其毕生心力在于笺注李商隐诗文,所作《玉谿生诗集笺注》(以下简称为“冯注”)“是清代李商隐诗集最完备精审的笺注本,也是李商隐研究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3]142。王鸣盛曾在《李义山诗文笺注序》中盛赞冯注:“读之直恨先生不具千手眼,尽举天下书评阅之然后快也。”王鸣盛对冯注之欣赏,不仅停留于赞叹夸奖,还助其声势,回击时人质疑,认为“或谓著述家蹈空者固多,若注释则安能蹈空为?予谓不然。夫躁于求名而懒于考核,俗学之恒态也……若先生此编,则从实学中来,非袭取可得”。称他为 “真读书人之可贵也!”[4]818-819
不独当时人诟病冯注的穿凿附会,后代学者对其缺点也多有探讨。蒋凡先生在《玉谿生诗集笺注·前言》中曾评价道:
至于夸大牛李党争对李商隐的影响,把他的许多无题诗及其它篇什都附会为干求当时权相令狐绹之作,主观片面,连冯氏也不得不说:“穿凿之讥,吾所不辞耳。”这又是冯本的不足之处。[4]9
台湾学者颜昆阳则批评得更为严肃,他在《李商隐诗笺释方法论——中国古典诠释学例说》一书中写道:
冯浩对方法学虽无新的发明,然而却将这套方法(“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相结合)的功能发挥到几乎极限,同时也将它的弊病暴露无遗……并且在笺释作品时,更是大多使用逐句凿实的解法。其穿凿附会,非常的严重。李商隐诗的意义也几近僵死矣。[5]90
如果将冯浩的具体笺注文本对照义山的诗句,认为他过于穿凿附会的评价确实是中肯而正确的,但在这其中,难免对冯浩作注的用心有所误会。其实正如上文蒋凡先生所提到的,冯浩本人未尝没有意识到这个缺点,他曾在《僧院牡丹》诗后的注中写道:“不善悟者不可与言斯集。然廋辞隐语,非风雅正声,学者慎勿效仿之,后人必以此诮余穿凿入魔也。”[4]744这既是提醒后世之人不可盲目效仿李诗的迂曲用语,也是为自己所作的注解为何落入“穿凿”进行辩白。冯浩毕生致力于此注,后因病魔侵袭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仓促出书。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十一岁时,重校重版此书,而嘉庆元年(1796)再版此书,只是“以补充为主,力求详备”(1)蔡子葵:《冯浩〈玉谿生诗〉笺注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1期,第18页:“三版本比较结果:庚子本较癸未本无论诗歌系年、笺解、校注均有较大变化,嘉庆本较庚子本小有变化,以补充为主,力求详备。”。两次重校,为何冯氏始终未曾修订这些所谓的穿凿之处(2)(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蒋凡标点:《玉谿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24页,《重校发凡二条》:“初恐发病,急事开雕。既而检点谬误,渐次改修,积十五六年,多不可计。既欲重镌,通为校改,大半如出两手矣……今逐条讨核,不目审而心会者,弗以录也,学者庶可见信。”,笔者曾对此非常疑惑,但在细究冯注所引书目,并关照其生平、师承之后,对这个问题便有了自己的一点看法想要表达:冯注“穿凿附会”的问题固然是历代注家在注解如谜语一般的李诗时皆难以避免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冯浩受清代朴学思想的影响,以注诗来实践考据思想及方法的结果。冯浩先将李诗系年,再以史证诗与系年互为补充,是在集部注释中实践考据学求实的方法;冯注广征博引,所引书目极为广泛,李诗中所涉名物、事典、物典无一不考证详尽,正是将考据学求真的思想理念付诸实践。但由于李诗曲于用典的特点,冯浩以朴学考据的方法作注,那么穿凿附会则是这种实践性所难以避免的结果了。下文便主要从《玉谿生诗集笺注》的笺注特点入手,来详细说明此观点,有关生平和师承对此问题的影响,则另文论述。
一、以史证诗:细意钩核,发诗文之含蕴
顾炎武于《日知录》中总结宋明理学的经验教训:“昔之清谈老庄,今之清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肱股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周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3)(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自此开始,清代学术便走上了彻底否定明代空疏清谈之风的道路,发展至乾嘉两朝,朴学成为学术主流。作为清初“兴复古学的倡导者”,顾炎武又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4)(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的训诂方法,于是“康熙中叶以后的学术界,在为学方法上,逐渐向博稽经史一路走去,呈现出有别于宋明理学的朴实考经证史的历史特征”[6]69。在此背景下,主要生活年代在乾隆一朝的冯浩,所受朴学考据思想的影响很深,甚至于他修养立身的准绳,也是朴学思想的外化:其子冯省槐、冯集梧为其所作《行状》中证实了这一点,“(家父)生平不谈理学,而居家接物秉于至诚。尝言:‘人必真实无妄,可以不欺人,即所以不自欺。世之好为机警者,吾不能也’”[1]32。故而从朴学方法及思想笺注李诗的角度来研究冯注当是可行的。
冯注中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冯浩先为李商隐作年谱,然后将其诗文系年,再对李诗进行注释。清人钱陈群为其作《序》,其中就提到了“爰细意钩核,发诗文之含蕴,以详谱其行年。年谱定而诗之前后各得其所矣;诗得其所,文之前后亦莫不按部就班,而本传之同异自见,于是作者之心迹大彰灼于卷帙间”[4]817,就是对冯浩先为李商隐作年谱以钩核其诗文年代次序的做法表示赞同,并认为他的笺注更加接近义山诗的本意。冯浩在《玉谿生诗笺注发凡》中也曾表露过自己为什么采取先勾勒李商隐一生行迹,然后再以史证之的原因:
年谱乃笺释之根干,非是无可提絜也。义山官秩未高,事迹不著,史传岂能无讹舛哉?今据诗文证之时事,一生之历涉稍详,史笔之遗漏或补,读者宜细阅之。[4]820
冯氏认为作义山年谱是因为“义山官秩未高,事迹不著”,义山生平尚且不清,其诗篇经过八百多年的流传谬舛则更是不少,那么求之以史书来辨析前人注释的讹误便成为必要,因此可以说冯浩是自觉地运用朴学的考据方法来注释李诗。正因为此,冯注中所引最多的书目为正史类著作。通过对正史类著作的大量引用来探寻李诗背景,再以此为基础笺注李诗,成为冯注最显著的特点。
经过笔者粗略统计,冯注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是《旧唐书》253次,后依次为《汉书》250次、《史记》220次、《后汉书》205次、《新唐书》134次。所引正史类著作共18种,按照引用频率排列如下:《旧唐书》《汉书》《史记》《后汉书》《新唐书》《晋书》《陈书》《隋书》《南史》《北史》《南齐书》《北齐书》《三国志》《梁书》《宋书》《周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
实际上王鸣盛也注意到冯浩偏重新旧《唐书》来作注的特点:“注之者倘非贯穿新、旧《唐书》,博观唐、宋人纪载,参伍其党局之本末,反覆于当时将相大臣除拜之先后,节镇叛服不常之情形,年经月纬,了然于胸,则恶能得其要领哉?”[4]818《新唐书》与《旧唐书》相较,史料更加丰富,可是冯浩又明显更加倚重《旧唐书》,采缀尤多,冯注中并未道明缘由,但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比两书优劣,或许可从中得见冯浩取舍之缘由:
(《新唐书》)刘安世《元城语录》则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即其说而推之,史官记录,具载旧书,今必欲广所未备,势必蒐及小说,而至于猥杂。
(《旧唐书》)《本纪》惟书大事,简而有体;《列传》叙述详明,赡而不秽。颇能存班、范之旧法。(5)(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六,史部二,正史类二。
可见《旧唐书》虽较为粗糙,但更具有“史官记录”的真实性。或许这也是冯浩以朴学求真精神来笺注李诗所更为看重的。而他所引用的《旧唐书》史料,也主要集中在《本纪》与《列传》中。
在笺注《安平公诗》时,他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来辅证崔戎封号为“安平县公”,而在此诗系年依据及崔戎传记的采用中,皆依据《旧唐书·本纪》及《崔戎传》。冯浩依据诗中有“明年徒步弔京国”句系年至唐文宗太和九年,是年李商隐往来京师,他被华州刺史崔戎所赏识。原诗自注“故赠尚书讳氏”。《旧唐书·崔戎传》有“赠礼部尚书”,《旧唐书·本纪》中有崔戎调任兖海观察使,于是李商隐随同至兖州。而《旧唐书·崔戎传》中又有“高伯祖元暐,神龙初,有大功,封博陵郡王”,与首句“丈人博陵王名家”相合。自此断定此诗所作年份,破解后文诗意便依此事而定[4]30-31。而《新唐书·崔戎传》中仅记载了“崔戎,字可大,玄暐从孙也”,并未载其封号,后文虽录有崔戎深受百姓爱戴,免除杂税“姜芋钱”及“脱靴”之事[7]4962-4963,相较《旧唐书》史料搜集更为详尽,但未曾一字提及“博陵”,因此冯注不引《新唐书》,而以《旧唐书》之文笺注此诗。
冯注对新旧《唐书》的引用更偏重于《旧唐书》,而对于《新唐书》的引用,绝大多数以其《本纪》《传》与《旧唐书》相参照来耙梳史料,钩核史实。但冯氏对《新唐书》新增的《宰相世系表》颇为重视,并且多次引用。不仅在卷一、二的编年诗中如《赠宇文中丞》(6)(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蒋凡标点:《玉谿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9页。注为:“宇文鼎字周重,父邈,亦御史中丞。”《安平公诗》(7)(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蒋凡标点:《玉谿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0页。注为:“戎为博陵安平崔氏大房,封安平县公。”里与《新唐书》《旧唐书》《本纪》《传》互为参证,尤其在卷三无法编年的诗中,引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来考证史实的例子更多,其中尤以《送崔珏往西川》诗的笺注最能体现冯浩的考据手法。按照冯注一贯的注释风格“细意钩核,发诗文之含蕴”[4]817,此诗所提“崔珏”为何人,结合《李商隐年谱》方可断定此诗作于何时何地,真正的诗意是什么。冯注为:
《新唐书·艺文志》:《崔珏诗》一卷,字梦之,大中进士第。《宰相世系表》:崔氏清河小房珏。《北梦琐言》:珏尝寄家荆州。按:《崔八早梅有赠兼示》诗自注之崔落句,《唐音戊签》采入崔珏逸句,未知其更有别据否也?余检李频有《汉上逢同年崔八》诗,李为大中八年进士,其诗意谓己方作客,羡崔还家,与珏之寓荆州第进士颇相似。《李群玉集》在长沙裴幕时亦有崔八,约在会昌大中间,然皆不书其名也。检《新书表》所列珏与邠、鄯、郾、郸同房,而分支七八世。邠、鄯辈子孙极盛,子名皆从玉旁,而珏兄弟行绝少。若无他据,而仅以《义山集》注合之,则本集固分崔八、崔珏,似明是两人,何可妄合哉?俟再详考。[4]655-656
前文引用史书文集详考“崔珏”其人,发现常与“崔八”混淆,冯浩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发现崔氏谱系下此二人分而列之,当为不同的两人,据此订正前书所误。其笺注引书已如此详尽,但他始终对此诗持审慎态度,并不将此诗系年。此诗笺注之末,对于李诗诗意的揣摩,冯浩笺评为“随常情景,一无感触,当在义山未游巴蜀之前。但无可定编,聊列于此,与前题崔八相辨正焉”[4]657。冯浩注李诗态度之谨慎可见一斑,并非所谓刻意穿凿之辈,故而我们仅从方法学的角度来考虑冯注之穿凿是否损减李商隐诗意未免失却冯注本心,更应从冯注的笺注特点及朴学思想入手,来研究冯注的学术价值。
冯浩以史注诗特点的另一表现,则是对地方史志的重视。根据笔者统计,冯注共引用地方志类著作26种。其中载记类3种:《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越绝书》。地理类23种:《水经注》《三辅黄图》《长安志》《洛阳伽蓝记》《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齐乘》《河南通志》《荆楚岁时记》《雍录》《嵩山志》《吴地记》《岳阳风土记》《岭表录异》《明一统志》《南方草木状》《游城南记》《桂海虞衡志》《西事珥》《方舆胜览》《蜀中名胜记》《广西通志》《四川通志》。
以冯注对《华阳国志》的引用为例,因其“述巴中南中之风土;次列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之兴废,及晋太康之混一,以迄于特、雄、寿、势之僣窃;以西汉以来先后贤人,梁、益、宁三州士女总赞……”(8)(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六,史部二十二,载记类。对西南地区地理历史记载极为详尽,于是冯浩笺注涉及巴蜀地区的李诗时,常引此书作注。《华阳国志》在冯注中共引用10次,分别为:卷一《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中“遗音和蜀魄”句,《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中“锦里差隣接”“勿贪佳丽地”句,《病中早访招国李十将军遇挈家游曲江》中“犹放沱江过锦城”句,《咏史》中“力穷难拔蜀山蛇”句;卷二《巴江柳》中“移阴入绮窗”句,《井络》中“井络天彭一掌中”句,《迎寄韩鲁州瞻同年》中“寇盗缠三蜀”句,《张恶子庙》中诗题,《柳下暗记》中“无奈巴南柳”句(9)(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蒋凡标点:《玉谿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4页、76页、77页、89页、148页、356页、359页、443页、467页、500页。。这10处引用中8处为名物事典考证,有2处在考证地理及事典之后附有按语以辨明诗意。这2处有按语的为“锦里差隣接”及“力穷难拔蜀山蛇”句:冯浩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第一条注中认为“从翁”是与李商隐同居于玉阳山学道修仙之人,此诗是义山为送他赴杨嗣复东川节度使幕中而作[4]73。在笺注“锦里”句时,冯浩先依据《华阳国志》解释“锦里”得名缘由,但在按语里认为“此句不特地势,亦寓对居节制之意”[4]76,义山并不是为了强调地势差异,只是为了证明二人学道时住处相近。在“力穷难拔蜀山蛇”句中,冯浩先引《华阳国志》注解五丁拔蛇的典故,在按语中则有“去佞则如拔山”[4]148。
冯注对地方志充分利用,但又不尽信,地方志与正史相印证,又以地方志补充正史空白并纠正正史谬误,充分体现了朴学求实的方法。可以说冯浩就是一位考据学家,他用朴学的注释方法来笺注官迹不显、正史评价有失偏颇的李商隐的文学作品,在方法上是可靠可信的。因,此冯注除了考证详尽之外,其注解较之前人之注更加贴切。他以清儒求真审慎的态度详细考证多方引用来笺注李诗,敢于驳斥前人妄说,敢于提出自己对李诗句意的观点,体现了一位考据学家的自信和魄力,也是对朴学求实方法的进一步发扬。
二、旁征博引:诗有博通之趣
冯氏曾于《玉谿生诗笺注发凡》中写道:“夫文有一定之解,诗多博通之趣。兹编也,我自用我法耳。”[4]823冯浩所谓的“博通之趣”,可从其笺注中所引书目得知,于此可尽显冯氏学问淹博,考据严谨。“唐时崇尚道教,义山旧有‘学仙玉阳东’之事”[4]335,加之他刻意曲折诗意,因此诗中多用道教及佛教故事用语作典。冯浩作注时贴合李诗特点,为剖析李诗用典,对释老典籍也广为采擢,故而冯注中释家类与道家类引书数量相当可观。冯注中所引道家类典籍21种:《度人经》《庄子》《列子》《抱朴子内外篇》《文子》《华山志》《列仙传》《阴符经解》《真诰》《老子注》《黄庭经》《登真隐诀》《墉城集仙录》《神仙传》《道德指归论》《洞仙传》《集仙传》《道德经》《云笈七签》《枕中书》(10)冯注中称其为:“枕中记”。《神仙感遇传》。
冯注李诗征引道藏颇多:在笺注《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二十韵》第十一句“金铃摄群魔”中,冯浩注为“《真诰》:老君佩神虎之符,带流金之铃。又曰:仙道有流金之铃,以摄鬼神。《云笈七签》:九星之精化为五铃神符,威制极天之魔,召摄五方神灵”[4]336-337。虽然典故中语涉“金铃”的并不少,但冯浩在篇末诗笺中认为此诗应该为李商隐自叙学道身世之作,纠正了朱氏(朱鹤龄)以此诗为悼亡而作的说法(11)(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蒋凡标点:《玉谿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0页:“盖学仙时多与女冠相习,唐时风尚如此耳。或兼比己之婚于王氏,默叙行藏,则大可也。‘戊辰’必为纪年,必非悼亡后矣。”。因此在注释全诗时,多引道藏作解。冯浩将最后一句“胜景侍帝宸”引陶弘景所著《真诰》注为“桐柏真人领五岳司侍帝晨王子乔,青盖真人侍帝晨郭世干。又曰:侍帝晨,并如世之侍中”[4]340。对“侍帝晨”这一道家对侍奉天帝的仙官的称谓注引恰切精当,全篇注文至此条理清晰,逻辑顺畅,有力地驳斥了前人误以此诗为悼亡诗的说法。此当为解诗精妙之处。
冯氏对道藏的广泛引用,对道教名物细致笺释的同时也易造成对诗意注解的附会。在卷二《重过圣女祠》[4]369一诗中,认为此诗诗眼全在首联“白石岩扉碧藓滋,上清沦谪得归迟”中的“沦谪”二字之上,这种解法是正确的,体现了冯浩对李义山诗意的精确理解。但是在注解中,冯氏先后引《真诰》《墉城集仙录》《登真隐诀》等道藏书籍,解释诗中名物典故,但尾联“玉郎会此通仙籍”,冯氏从仙籍讲起,引入神仙世界的等级次序,最终以此将诗意定为以图“修好于令狐”,强将此诗附会于与令狐父子的恩怨之中,便又是因为过于依赖道藏文字典故的表意,而忽视了义山作诗的审美需求。义山自巴蜀而归,又记起当年经过此地,一来一往人事变迁而自己又遭贬外地,将自己孤独求索的境遇比之圣女求仙籍的波折,以女仙自况,是义山诗的常用手法。此诗注文博采广征甚为精彩,但笺释落脚于希图求得令狐的原谅,则未免穿凿。
除此之外,因义山诗中也多次引用佛教名物,冯浩为笺注李诗便先后引用释家类书籍18种来作注:《维摩经》《金刚般若经》《大般涅槃经》《楞伽经》《菩萨本起经》《起世经》《法念经》《妙法莲华经》《僧伽经》《因果经》《菩萨本径经》《佛藏经》《阿难问事经》《报恩经》《法华经》《佛说法海经》《法苑珠林》《释氏稽古略》。《题僧壁》一诗为冯注中引用佛经笺注李诗的一例典型。此诗语涉多个佛经典故,但冯浩并未曾引用和尚道源的注文,可能因为道源的注文“属于释事忘义,只究心于注出典,李商隐诸多隐晦作品的诗旨,道源是茫然不知的”[8]185。而冯浩对这首诗的笺释并不停留于注解佛经典故的阶段,以他对李诗的理解,此诗虽有佛教论理诗的显著特点,但更多的是义山“盖久不得志,因悟一切皆空矣”[4]503的遣怀之作。冯氏为了证明此观点,尤其以注解颔联所下功夫尤多,其将“大去便应欺粟颗”释为:
《维摩经》:若菩萨住是解脱者,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佛藏经》曰:四天下中普雨大石,皆如须弥,有人以手承接此石,无有遗落,如芥子者。按:句意类此,俟再考所本。或引一粒粟中藏世界……[4]504
即使是同一典故,《维摩经》以比喻诸相皆非真,巨细可相容;《佛藏经》则更注重彰显佛法广大。冯氏于此细微之处并不定夺,只将引书列出,后文按语以“或”开头,提出自己的理解。
将“小来兼可隐针锋”释为:
《维摩经》:举恒河沙无量世界,如持针锋举一枣叶而无所娆。《大般涅槃经》:诸佛其身姝大,所坐之处如一针锋,多众围绕,不相障碍。[4]504
《维摩经》偏向论说佛理,而《涅槃经》则强调菩萨住大涅槃的境界相。颔联两句同为辩论佛法须弥芥子之意,但引书不同,诗意也有差距。冯浩为保存李诗多义的审美特点,这两句诗都各引两部佛经保存了多重诗意。两部佛经经文差异如此细小,但冯浩引用颇为熟练,足见清儒冯浩的博学。其后颈联承接颔联须弥芥子之意,注“旧松”“新桂”“琥珀”,将诗意引入过去、未来、当今三世。结合前文可知诗意为李商隐感叹僧人世世舍身求佛法,但一切皆空。此诗冯浩将其系于义山赴东川幕中(12)(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蒋凡标点:《玉谿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03页:“义山好佛,在东川时于常平山慧义精舍经藏院剏石壁五间……”,诗人奔波一生潦倒一生,与僧人何其相似。有人或许认为这一类引文太过繁琐,但冯浩几校其稿不忍割舍,当是他所谓诗文笺注“博通之趣”的趣味所在了,这番趣味既保存了李诗丰富多义的语言特色,同时也突显了冯注的博通与精妙。
冯注的“博通之趣”还体现在他学识渊博,对医药学书籍掌握运用也很熟练。正如王鸣盛所言“真读书人”。冯注所引医家类书籍9种:《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本草纲目》《本草释名》《本草图经》《黄帝素问》《玉函方》《箧中方》《唐本草》。举两首诗为例。冯注为解《送阿龟归华》中末句“碧松根下茯苓多”,曾引《唐本草》作注(13)(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蒋凡标点:《玉谿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67页:“《唐本草》:茯苓第一出华山。”。冯浩一方面认为此诗“意境不似玉谿”,另一方面据《唐本草》认为茯苓产自华山,《万首唐人绝句》将此诗题作“华阳”,冯氏据此辨析此诗“为香山诗也”[4]767。前人虽对此诗“蓄疑者久矣”,但冯浩以《唐本草》作注,有理有据证实此诗“必白公送侄归家之作,乃《香山集》漏收,而反入斯集”[4]767。历代注李之作不少,如何能穿过如此之多的文献,探求李诗真意,这是冯注始终所追求的境界。于是冯注以考据之功,辨析前人谬误,便是其自觉追求博通的必然结果了。五律《访隐》一诗颈联有:“薤白罗朝馔,松黄暖夜杯。”“薤白”与“松黄”二物,冯氏引《本草图经》注为“薤似韭而叶阔,多白、无实,有赤、白二种,白者冷补”“松花上黄粉名松黄,山人及时拂取,作汤点之甚佳”[4]746。薤白或许常见,但将松树的花粉称作松黄并不为人所熟知,加之义山诗常常割裂原典词意,此类名物如不能明晰,容易对读者造成误解。因此,冯注的博通能够顺畅诗意,又能明晰义山之意。
至于后人诟病冯注烦琐累赘,这与“义山之诗,谲怪情深,隐晦感伤,其旨纡曲,其词诞漫,他深受道家思想之影响,……又在道观学仙,熟读《黄庭经》之类的道典,一定熟知道家的‘秘诀隐文’手法。因而,他笔下之形象,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给人一种扑朔迷离之感”[9]30。这样的特点密不可分。李诗的很多诗篇或受一时心绪的激荡,或为时事所作,但时事已邈远不可追寻,其诗旨则无法捉摸,只可做一些名物考证方面的笺注。但深受清代考据之学影响的冯浩在笺注时追求博而通的艺术特点,因此他对某些篇什的笺注便不自觉地拘泥于字词,尽管冯氏本意并不如此,但他为追寻李诗真意所作的考据功夫,呈现于卷面则有了烦琐的弊病。冯注卷二《木兰》一诗中,先后引《本草纲目》《本草图经》《本草释名》《群芳谱》《平泉山居草木记》《益部方物略记》六部书,《离骚》《子虚赋》《蜀都赋》,白居易《题令狐家木兰花》《木莲树图序》五篇诗文有关“木兰”此物的大量相关内容注解诗题,冯浩引《本草释名》解释此条注释为何如此烦琐的原因:“木兰、杜兰、林兰、木莲、黄心,其香如兰,其状如莲,其木心黄。是一物而异名也,似误混矣,故不惮详徵之。”[4]372近六百字的注文仅是为辨析“一物异名”的诗题“木兰”而作,又与后文笺评此诗为权相令狐而作并不相关。如此大费周章地解释“木兰”此物,这便又是冯注追求博通的弊端了。
冯浩为注解李诗,用尽毕生所学。其博通则不仅体现在注文引书涉猎广泛,更为重要的是他注文的精妙,对义山诗意的理解十分到位。在《初食笋呈座中》一诗系年中,先引《汉书》“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注第三句“皇都陆海应无数”中的“皇都陆海”[4]26指长安附近。故而在笺语中,冯氏引《竹谱》中对鲜美可食用的“筍”的记载,将此诗系于义山早年随崔戎赴兗海观察使任上:
戴凯之《竹谱》:“九河鲜育,五岭实繁”,九河在今德州平原之间。大约北地多不宜竹,时必有以筍为方物献者,故纪之。浩曰:《竹谱》云:般肠实中,为筍殊味。注曰:般肠竹生东郡缘海诸山中,有筍最美。正兖海地也。[4]26
长安地处北方,气候条件不适宜生长竹子,更难以将其作为食物。但在《竹谱》中,晋人戴凯之记载了一种与“笋”同音的“筍”,便为现在所称的莴苣。此物能够生长于北地,且以兖海地栽培最佳。因此,冯浩对此诗的系年应是正确的。
冯注虽为人诟病烦琐,但其中大多数的注文是简略得当的,对后世读者理解李诗诗意起到了重要作用。《桂林路中作》尾联“欲成西北望,又见鹧鸪飞”,李商隐有意以纡曲的言辞将律诗的对仗打破,但是又以暗含的典故,使得律诗风格依旧工整有序。冯浩引《禽经》一言道破其中奥妙:“子规啼必北向,鹧鸪飞必南翥。”[4]295西北望东南飞,貌似不工,却对仗整齐。这确实是朴学求真思想在集部注释中的体现。
三、朴学考据:琐屑情事,皆有所指
李商隐诗历来有“诗谜”之称,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写道:“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4]829王渔洋言道:“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10]119二者都提到笺注李诗之难。有清一代笺注李诗的注家多达数十家,其中朱鹤龄、姚培谦、屈复、程梦星、冯浩注本为全集笺本。诸家之中,以冯注本流传最广。但在“冯氏之后,很有趣的是,李商隐诗的笺释反而盛极而息,从乾隆末期到清末民初将近一百四十年之间,竟未再出现一个完整的笺本。究竟什么原因?很难说。有一种可能是冯氏的笺本,实在已经非常详尽,在方法学上如果没有什么新的突破,想超越冯笺,实非易事”[5]92。冯浩以年谱系诗,对诗意的精心揣摩,对诸多事典的层层剖析,总体上揭示了李诗的讽喻主旨,可以看到冯浩以朴学考据方法来笺注李诗,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他于《玉谿生诗集详注自序》中言其“夫笺注义山诗文者既有数家,皆积岁月以寻求,顾作者之用心,明者半,昧者犹半,岂诸家之力有所不逮欤?”[2]307历来注家“所不逮者”便是冯氏以为“自来注释家半明半昧,不得作者之意”[1]21。而他认为自己能够将李诗诗意格而通,无所迷混,并能得作者之意的原因,便是他引以为豪的考据之法(14)(清)冯浩:《清代诗文集汇编·孟亭居士文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5册,第307页下,《卷一·玉谿生诗详注自序》:“于是徵之文集,参之史书,不惮悉举而辨释之;诗集既定,文集迎刃以解,鲜格而不通者;迺次其生平,改订《年谱》,使一无所迷混,余心为之惬焉!”。而这同时也验证了清儒以考据之法来注释集部诗文是可行且颇有成就的。
冯氏笺评义山《海上》诗有言:“义山身世之感,多托仙情艳语出之。不悟此旨,不可读斯集也。”[4]27冯氏认为义山诗中“仙情艳语”之类的诗歌,是李商隐因陷于党争之中蹉跎岁月,一生窘迫难以明言,因此用意深婉,以情爱及修道之事来自伤身世。冯氏以“比兴”的观念来看待李诗,那么对其诗歌用典的考据则不遗余力,冯氏认为如此方能读解李诗,而这正是朴学思想的体现。如以《有感二首》(九服归元化)为例,历代注家皆以此为李商隐讽喻“甘露之变”之作(15)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年,第131-135页:“钱龙惿曰:‘甘露之变,从古未有之事也。’……义山诗云‘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极言训等之冤,未尝甚其罪也。”“何(何焯)曰:‘上篇深斥训、注,下篇则哀涯、餗、元舆等。’”“沈德潜曰:‘为甘露之变而作。’”“姚(姚培谦)曰:此为甘露之变鸣冤也。”,认为此诗是李商隐为时事所感,激愤而作。可是义山不敢明言,因此李诗曲于用典的特点恰好在此诗中可集中体现,但因为义山刻意曲折诗意,要想证明《有感二首》确为讽喻“甘露之变”的诗作并不容易。此诗冯浩以名物考证与史学考据相结合,可谓得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首先,在第一条注中,冯浩引用新《旧唐书》《新唐书》《李训》《郑注》等七百多字洋洋洒洒来记述这一事件,因此随后其对三十二句诗文的笺注皆围绕如何证明此诗为暗讽“甘露之变”而作这一主题。其次,冯浩秉持朴学考据的严谨精神,试图对诗句意象抽丝剥茧地层层解析,来捕捉李诗中用典之意,从而追寻《有感二首》的主旨。第二句“三灵叶睿图”朱(朱鹤龄)注将“三灵”解释为天、地、人三才,明显偏离“甘露之变”的主题,程(程梦星)注未能明确指示“三灵”具体之意,仅引用《隋书·音乐志》泛泛而谈“睿图作极”,而冯注则认为“三灵”指“日、月、星垂象之应也”,点明首联便暗指帝王大略。第五句“有甚当车泣”究竟是谁当车而泣,朱鹤龄引《三国志·魏志》注为嘉平六年,司马师废曹芳帝位的“高平陵事件”后,曹芳泣涕拜别郭太后之事,冯浩引《汉书·袁盎传》笺注为西汉袁盎劝谏汉文帝不宜与宦官赵谈同车出行,赵谈哭泣而下之事。虽然朱、冯二注皆语及宫廷之事,但冯注明显更加贴近李诗本意,司马师夺权废帝的政变相比于宦官家奴胁迫人君的“甘露之变”,其程度不同差异过大,不够贴合义山本意,而冯注则从首联的暗指君王,至第三联暗指宦官伴君,更符合律诗各联层层递进的意旨。第二首九、十句“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程注引《礼记》将“清君侧”释为“刑人不在君侧”,引《诗经·大雅·荡》“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虽然有助于读者理解诗意,但对于揭示李诗讽喻“甘露之变”的主题并无补益;冯注引《公羊传》将“清君侧”注释为春秋晋国大夫赵鞅反叛朝廷,以“清君侧”为名,驱逐宠臣荀寅、士吉射,将“乏老成”句释为李商隐暗讽朝中岂无社稷之臣,却偏偏重用志大才疏的李训从而导致甘露之败[11]121-130。故此冯浩笺评曰:“谋诛宦官,反被惨祸,诚堪怜愤;然文宗任用非人,亦不能辞其咎。义山措语皆有分寸。”[4]46
正是因为冯浩坚称义山诗的隐曲之处,皆可以在义山身世事迹中寻到答案,冯浩以注杜所需的“诗史”意识来注李,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因为杜甫诗歌的性质决定要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它”[12]20,因为二者作诗之法的不同,李诗曲于用典的特点,决定了其诗意往往掩盖在绮丽词句之下,令注者难以捉摸其诗意,冯浩所依凭的考据之法有时也难以捕捉纤微的诗意。因此考据之法用于义山抒发情感的作品则易陷入穿凿。在《射鱼曲》(16)(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蒋凡标点:《玉谿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83-384页。《射鱼曲》:“思牢弩箭磨青石,绣额蛮渠三虎力。寻潮背日伺泅鳞,贝阙夜移鲸失色。纤纤粉簳馨香饵,绿鸭回塘养龙水。含冰汉语远于天,何由回作金盘死?”中,冯氏耗费大量笔墨考据首句“思牢弩箭磨青石”中的“思牢”之意。中原物产及正史中未有“思牢”此物记载,冯氏将此字形训诂为“簩”。又据《南方草木状》及《岭表录异》中考证为一种皮薄质坚能够刺穿犀牛大象的竹子(17)(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蒋凡标点:《玉谿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84页。冯注第二条“集皆作‘思牢’,他书或作‘簩’。”第三条“嵇含《南方草木状》:簩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径不过二寸,皮粗涩,以镑犀象,利胜于铁,出大秦。按唐刘恂《岭表录异》亦本此语……”。以《太平寰宇记》中所载“贺州簩竹,有毒,人以为觚,刺虎,中之则死”,引《禹贡》《异物志》《郡国志》《后汉书·东夷传》,将“青石”考证为一种弓矢(18)(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蒋凡标点:《玉谿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84页。冯注第三条:“《异物志》夷州土无铜铁,磨砺青石,以作弓矢。此石弩楛矢之类……《禹贡》:荆州贡砮,砮石中矢镞。”,以此二物考证为基础,冯注认为整首诗的用典皆为南方之物,因此冯氏笺评为“盖李卫国贬崖州而作”[4]385,则明显是过于穿凿附会了。钱(谦益)注笺评《射鱼曲》为:“义山学杜者也,间用长吉体,作《射鱼》《海上》《燕台》《河阳》等诗,则不可解……疑是唐人习尚,故为隐语,当时之人,自能喻之,传之既久,遂莫晓所谓耳。”[4]385钱氏认为此诗隐语已不可解,仅将其看作义山学李长吉之诗,此诗钱谦益的笺评则更为中肯。
总之,之所以冯注时而陷入穿凿之感,是由于冯浩笺注李诗最根本的思想当为前文所提到的“年谱乃笺释之根干,非是无可提絜也”。他以勾勒李义山一生行迹交游为注诗依据,将李诗作为信史而考据验核,认为李诗“无非借艳情以寄慨”[4]822,这样的笺注思想是本于朴学考据精神,但却难以避免穿凿,有损于李诗形象性文学性的意义阐发,却有助于清儒笺注集部诗文的探索。冯注以史证诗、追求博通的笺注风格,对清代考据学在集部注解方法的探寻颇有裨益。集部著作中很多诗文是作者一时情绪的宣泄,或者因事而抒情写意,其写作的背景邈远不可追寻,为诗文作注的难度要比为经史作注更为困难,加之清代注经已盛极而衰,因此考据之学亟须开拓一片新的天地,集部注释便进入了清儒的视野之中,“注杜”“注李”成为一时风尚。但由于杜诗“诗史”的特性,因此笺注杜诗在方法学上对注释集部诗文的可借鉴意义并不甚大。李诗因为其“诗谜”的特性,加之李商隐作诗素有“獭祭鱼”之称(19)(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蒋凡标点:《玉谿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25页,《杨文公谈苑》:“义山为文,多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李诗之征事博奥,撷采妍华,恰是最能够实践考据学方法的实验场。笺注李诗对注释集部诗文探索意义更大。之前的注李著作虽多,但冯注本确实是其中最完备精审的一部。而冯浩在以史证诗的特点之外,广泛引用各类典籍,以更为开放宽宏的态度,将古今之书纳为己用,他所看重的是考据之法对中华典籍的归纳整理作用,而非困于考据、训诂(20)(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蒋凡标点:《玉谿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23页,《玉谿生诗笺注发凡十二条》:“集中双声叠韵属对精细,而押韵每宽……且所重不在韵,故略之。”之中。冯注采擢典籍,不局限于经史之内的注李成就推动了朴学考据之法的演进。
《文心雕龙》所谓“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13]212。李诗用意之曲折,大概为“言隐荣华”[13]215之类,因此冯氏认为 “盖义山不幸而生于党人倾轧、宦竖横行之日,且学优奥博,性爱风流,往往有正言之不可,而迷离烦乱、掩抑迂回,寄其恨而晦其迹者……”[4]822则不得不辨理明意,以正其诗意。冯浩强调 “诗有博通之趣”,因此其注并不局限于一定之解,而是将有关诗意的典故罗列出来,供后人采择,“虽作者意不及此,亦堪搜剔”(21)(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蒋凡标点:《玉谿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页,冯注《赠赵协律皙》第四句“更共刘卢族望通”,罗列《晋书》中所载刘琨、卢谌、温峤等姻亲关系,段末冯氏笺评有此语。,其目的正是为了避免穿凿,兼顾读解“诗谜”的阅读感受,如此方能保持李诗多义的审美体验。其穿凿之感,是以考据之法注“诗谜”般的李诗所难以避免的,仅以此来判断冯注的学术价值,则是对清儒以考据之法笺注集部诗文的探索和实践过度否定。如能究其用心,反观冯浩在注李时朴学实践精神的发扬,在研究中方能更好地吸收冯注的思想精髓。
——论《江格尔》重要问题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