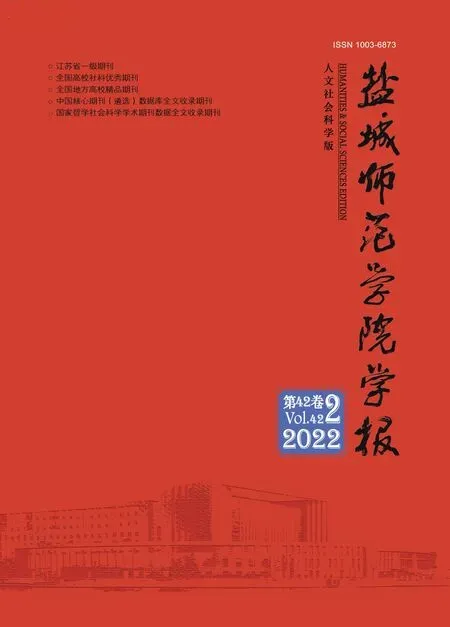词集重刊与词坛新貌
----论雍乾年间的“山中白云”风
黄浩然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明清之际,“世人言词,必称北宋”。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诸家,通过蒐集、整理、展示以姜夔、张炎为代表的南宋雅词,宣扬“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的词学主张,有力地扭转了当时的词坛风尚[1]发凡。通常而言,词人的创作一般经由选本和别集呈现,因此,浙派对词人词作的整理不仅体现在选本的编纂上,也体现在别集的修订上。这种努力在张炎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朱彝尊等人从各种渠道获得张炎《玉田词》的四种抄本,在《词综》初刻本中选录众多张词;其后又获得张炎词足本----《山中白云词》,不仅加以整理、刊刻,而且在《词综》补遗中予以增选。康熙五十六年(1717),《词洁》的编者先著在追述康熙初年的词风转变时就特别提及张词:“四十年前,海内以词名家者,指屈可数,其时皆取途北宋,以少游、美成为宗。迨山中白云词晚出人间,长短句为之一变,又皆扫除秾艳,问津姜、史。”[2]随着浙西一派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张炎在康熙词坛逐步获得前所未有的词史地位,清人的次韵之作也随之大量涌现。不过,这些词作的次韵对象基本集中在《词综》所收的张词,超出《词综》范围的张词则相对较少。出现这样的局面,与《词综》的选本性质有关。一方面,《词综》所收录的张炎词作虽然远不能与《玉田词》《山中白云词》相比,但这些词作经过朱彝尊等人的精挑细选,更能体现浙西一派的论词旨趣;另一方面,《词综》和《山中白云词》推出之时,北宋词风仍占据文坛主流,浙派之外的词人更易被《词综》中的张词吸引,尚无暇顾及其别集。不过,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张炎的词别集相对而言流传未广。康熙四十四年(1705),杜诏奉命分纂《御选历代词》,始得朱彝尊所寄《玉田词》抄本,“时亦未知有‘山中白云’名目也”。到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杜氏在奉命修纂《钦定词谱》时才因同馆楼俨之故得见《山中白云词》[3]171。而从康熙六十一年(1722)到乾隆元年(1736),《山中白云词》在十五年间重刊三次,其作为足本别集的优势才逐渐显现。
一、《山中白云词》的重刊
《词综》初刻本所据《玉田词》并不完备,朱彝尊颇以为遗憾:“顷吴门钱进士宫声相遇都亭,谓家有藏本,乃陶南村手书,多至三百阕,则予所见,犹未及半。漏万之讥,殆不免矣。”[1]发凡朱氏所见,乃是钱中谐所藏陶宗仪手书本。李符《龚刻山中白云词序》记载了整理过程:“越数年,复睹《山中白云》全卷,则吾乡朱检讨竹垞录钱编修庸亭所藏本也。累楮百翻,多至三百首,始识向购特半豹耳。参殷孝思璧全一语,更阅陆辅之《词旨》载乐笑翁警句奇对,无有出于是编之外者,知为完书无疑。竹垞厘卷为八,与诸同志辨正鱼鲁,缄寄白门,余复与龚主事蘅圃取他本较对,或字句互异,题目迥别,则增入两存之,锓枣以传,可称善本。继又从戴帅初、袁清容集内得赠序疏与诗,因附刻于后,而其生平约略可见。”[3]167尽管卷首殷重《玉田词题识》称是编“几经兵燹,犹自璧全”[3]166,但整理者还是根据陆行直的《词旨》做了必要的考辨。在“厘卷为八,与诸同志辨正鱼鲁”之后,朱彝尊将其“缄寄白门”,由李符、龚翔麟“取他本较对”。除校勘之外,李、龚二人还从戴表元、袁桷集中辑得《送张叔夏西游序》《送张玉田归杭疏》《赠张玉田》“附刻于后”,以资知人论世。康熙十八年(1679),《山中白云词》由龚翔麟附刻于《浙西六家词》之后。不过,这一词集在康熙早年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直至康熙六十一年,上海曹炳曾城书室才将其重新刊行。
曹炳曾的《山中白云词序》详述了重刊的缘起:“曩者余友简兮陆先生相契甚笃,朝夕过从,讨论古今乐府诗余,必推玉田张叔夏,一日出《山中白云词》见示,乃先生手录披阅者。曰:‘世无善本,何锓枣以传!’余曰:‘唯唯。’时犹习举子业,未尝专读古书,不知叔夏为何时人也。未几,先生与子源渟相继谢世,欲求所谓玉田词者,杳不可得。间尝披阅词选,得见数阕,觉慷慨洒落,于周待制、柳屯田诸名家外,别出蹊径,而律吕调谐,一一应声叶节。追忆简兮之语,为太息自悔者久之。去年秋,有客以残编数种求售,翻阅未竟,忽睹此卷,正畴昔先生所手编者,不禁狂喜,亟购得之,以付廉儿。于是复叹四十年间人之存亡,书之离合,莫不有数存乎其间。而《白云》一帙,若终有待于余也。会余刻《海叟诗集》,因将此编重加参订,附以《乐府指迷》、名贤诗序赠别之作,精书镂板,以酬宿诺。”[3]170“简兮陆先生”即陆敏时,“字子逊,尝读《诗》至《简兮》之什,见贤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有轻世肆志之心,心窃慕之,因自号为简兮”[4]。陆敏时与曹氏昆季过从甚密,陆氏过世之后,炳曾之弟煐曾作《沁园春·挽陆简兮》表达哀恸之情。陆敏时曾向曹炳曾推荐《山中白云词》,只不过曹氏当时“犹习举子业,未尝专读古书”,甚至不知张炎为何时人。后来,曹氏“披阅词选”时得见张炎词,认为其词“律吕调谐,一一应声叶节”,于柳永、周邦彦之外“别出蹊径”,此时“追忆简兮之语,为太息自悔者久之”,而“欲求所谓玉田词者,杳不可得”。康熙六十年(1721),在机缘巧合之下,曹炳曾重获陆敏时“所手编者”,重新参订并予以刊行。
对于曹炳曾所述,学界存在一些质疑。吴则虞先生在谈及陆简兮校本时指出:“此本与龚本相出入者仅数处,不过十数字耳。八卷之分,既出自朱氏,校订之役,实成于李符,又何以简兮自居其功耶?窃疑陆氏之书,实即龚本略加批校而已。巢南付刊时,恐未见龚本,故误为陆氏所编次。眉首行间,陆氏或有校语,惜未刊出。”[3]213-214对此,郑子运有着不同的看法:“陆简兮抄本并不是出自龚刻,因为李符序龚刻本云:‘继又从戴师初、袁清容集内得送赠序疏与诗,因附刻于后,而其生平约略可见。’陆抄若出自龚刻,陆氏又常在曹氏面前揄扬张炎词,曹氏不当‘不知叔夏何时人也’。陆抄本后来遗失,曹氏从书肆中所购为龚刻本,而曹氏误以为与陆抄本相同,吴则虞据此误以为陆氏剽窃了龚刻本的成果,遂使陆氏衔冤地下。曹刻的卷数分合、加注的异文,与龚刻完全相同,而且全载龚刻的序文,所以,曹刻出自龚刻。”[5]
探讨这一问题之前,要将龚本和曹本进行全面的比对。吴则虞在整理《山中白云词》时以龚刻为底本,参合了包括城书室本在内的诸多版本。在其校勘记中,龚本和曹本的异文如下:
(一)卷一《琐窗寒·旅窗孤寂,雨意垂垂,买舟西渡未能也,赋此为钱塘故人韩竹间问》“试香温”:曹刻本“香”“温”互倒,同《词综》及水竹居本。[3]16
(二)卷二《还京乐·送陈行之归吴》“醉吟处”:曹本“吟”作“游”,水竹居本、四印本作“胜游多处”,《词谱》亦作“胜游”。[3]34
(三)卷二《长亭怨·为任次山赋驯鹭》“朝回花径”:龚本作“花□”,曹本作“花径”,许本同,水竹居本作“花底”,四印本亦作“花底”,兹从许本。[3]39
(四)卷四《意难忘·中吴车氏号秀卿……》(别本)“明月又谁家”:曹本、宝书堂本、许本“明月”作“明日”。[3]73
(五)卷五《壶中天·月涌大江》“鸥犹栖草”:曹本、《历代诗余》“鸥”并作“沤”。[3]100
(六)卷六《满江红》(近日衰迟)“顿荒松菊”:“荒”,曹、许本注云:“一作就。”龚本无。[3]120
(七)卷七《水调歌头·寄王信父》“化机消息”:曹本“机”作“几”。[3]123
(八)卷八《思佳客·题周草窗〈武林旧事〉》“汉上重来不见花”:曹本“重”作“从”。[3]144
(九)卷八《渔歌子·十解》(其五)“更无人识老渔翁”:曹本“识”作“说”。[3]146
从这九条异文来看,两本之间的差别确实如吴则虞所言,“仅数处,不过十数字耳”。两本之间极高的相似程度表明,曹本或者曹本所据的底本源于龚本。由于曹炳曾称底本乃“畴昔先生所手编者”,且曹序并未言及龚本,因此可以说,曹氏所据的底本----陆敏时所“手录披阅者”----源于龚本。至于两者之间为数不多的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曹氏“重加参订”的成果,前六条当属此类。周中孚称曹氏“家多藏书”[6],这些与龚本的相异之处应该是参合了当时的相关文献,比如《词综》《历代诗余》等。另一类是传抄、刊刻过程中出现的异文,后三条当属此类。“机”与“几”、“重”与“从”、“识”与“说”,或形近、或音近,相对而言容易导致手录之误。
在厘清两者关系的基础上,我们重新来审视吴、郑之间的不同观点。吴则虞认为“陆氏之书,实即龚本略加批校而已”,“巢南付刊时,恐未见龚本”,都没有问题。不过,“误为陆氏所编次”之说恐怕难以成立。曹氏所谓“手编”,应当等同于上文的“手录披阅”,而非“编次”。换言之,曹氏应该并未认为陆敏时是《山中白云词》的分卷者和校订者。郑子运认为“陆简兮抄本并不是出自龚刻”,而“曹氏从书肆中所购为龚刻本”,都缺乏更有力的根据。曹氏自称当时“不知叔夏为何时人”,是因为“时犹习举子业,未尝专读古书”,对张炎不甚了解,不能将其作为“陆简兮抄本并不是出自龚刻”的理由。至于曹氏所购买到的“乃先生手录披阅者”,故而曹氏感叹“况我良友,手迹如新”。因此,所谓“曹氏从书肆中所购为龚刻本,而曹氏误以为与陆抄本相同”的观点也很难成立。
城书室本《山中白云词》刊行之后,曹炳曾将之赠予杜诏,杜“惊喜出望外”。雍正四年(1726),城书室本重刊之时,杜氏为之序,回顾自己与《山中白云词》的渊源,并阐述自己对张词的体认:“从此泝源北宋,研味乎淮海、清真,一归诸和雅。”[3]171由此可见,杜诏的思路与朱彝尊很不相同,他是经由张词溯源北宋、研味秦周,这在康熙词坛其实颇具代表性[7]。
乾隆元年,仁和赵昱宝书堂本《山中白云词》刊行。卷首厉鹗《山中白云词题辞》云:“元张炎叔夏《山中白云》八卷,吾乡龚侍御衡圃得钞本于秀水朱检讨竹垞,因镂版以传。侍御晚节家居食贫,物故后,琴书散落,是版几入庸贩手,吾友赵君谷林幸购得之。谷林好畜僻书,必留其真,力于校勘,复弗吝流布人间,可谓得所归矣。”[3]168龚翔麟晚年贫困,身后“琴书散落”,所刻《山中白云词》雕版辗转流传,后由赵昱购得。赵氏“好畜僻书”,“弗吝流布人间”,据之刷印以行,故赵本的行款与龚本一致。厉鹗对版本源流的介绍虽然无误,但也遮蔽了一些信息。他只提到“吾乡龚侍御衡圃得钞本于秀水朱检讨竹垞”,但并未言明朱彝尊本源自钱中谐藏本,其中或许有言外之意。根据厉鹗的叙述,《山中白云词》流传线路是:秀水朱彝尊→钱塘龚翔麟→仁和赵昱,如此一来,钱塘厉鹗所参与的这次重刊活动就具备了传承浙西词派统序的意味。
十五年间的三次刊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山中白云词》自刊本问世以来流传未广的局面,这也为张炎在雍乾词坛影响力的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撑。
二、张炎生平的深入研究
浙西词派的形成,以《词综》编纂为重要标志。《词综》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不再按类、调编次,而是按人编次。这一体例的确立,使得词人生平的考订成为编纂者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在别集整理的过程中,有关词人生平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只能通过概略的记载来了解张炎的生平。而在发现足本词别集之后,龚翔麟就在其《刻山中白云词序》中开展了相关考订工作[3]167-168。《山中白云词》卷八有《风入松·久别曾心传,近会于竹林清话,欢未足而离歌发,情如之何?因作此解。时至大庚戌七月也》,有《临江仙·甲寅秋寓吴,作墨水仙,为处梅、吟边清玩。时余年六十有七,看花雾中,不过戏纵笔墨,观者出门一笑可也》,“则此甲寅实元仁宗延祐元年也”,龚翔麟据此推算出“宋理宗淳祐戊申为玉田生始生之岁”。龚氏查阅《宋史》,知张俊有五子,然“玉田生出谁后”,尚无法考证。《山中白云词》卷一有《甘州·庚寅岁,沈尧道同余北归,各处杭越。踰岁,尧道来问寂寞,语笑数日,又复别去。赋此曲并寄赵学舟》和《疏影·余于庚寅岁北归,与西湖诸友夜酌,因有感于旧游,寄周草窗》,龚氏据以称张炎“至元庚寅始返江南”。《甘州》《疏影》两阕亦见于《百家词》本《玉田词》,不过其中的“庚寅”均作“辛卯”。龚翔麟整理《山中白云词》时虽然“取他本较对”,但他并未将上述异文校记,而是将张炎北归时间遽定为庚寅,有失审慎。而谢桃坊则根据《大观录》证明,“张炎于辛卯春尚在燕蓟”[8]。
那么,浙西诸家如何赋予祖籍陕西的张炎一个浙西的身份?通过考订,龚翔麟解决了这一问题:“其先虽出凤翔,然居临安久,故游天台、明州、山陆、平江、义兴诸地,皆称寓、称客,而于吾杭必言归,感叹故园荒芜之作,凡三四见,又安得谓之秦人乎?”朱彝尊《鱼计庄词序》有类似表述:“在昔鄱阳姜石帚、张东泽、弁阳周草窗、西秦张玉田,咸非浙产,然言浙词者必称焉。是则浙词之盛,亦由侨居者为之助。犹夫豫章诗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调焉尔矣。”[9]虽然龚翔麟对张炎生平的考订稍有不妥之处,但其在这方面的努力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可惜的是,曹炳曾在刊行城书室本时并未作进一步的探究,对张氏的介绍仅限于“张叔夏,名炎,号玉田生,又称乐笑翁,西秦人,或云临安人”[3]170。直至乾隆元年赵昱重新刷印龚本,有关张炎生平的研究才走向深入。
在龚翔麟《刻山中白云词序》的基础上,厉鹗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考订:
侍御序考叔夏生于宋理宗淳佑戊申,循王五子,叔夏未知出谁后。《宋史》不载,固无从考索。第袁伯长《送叔夏归杭疏》云:“古梅千槛,空怀玉照之风流。”玉照,张镃功甫堂名。功甫是循王诸孙,叔夏出功甫后无疑也。叔夏父名枢,字斗南,号寄闲,邓牧心《伯牙琴》中有《张寄闲词序》云:“子炎能世其学者是也。”功甫名偏旁从金,以五行相生之次推之,叔夏于功甫为三世,于循王为五世,与袁伯长赠诗注云“为循王五世孙”者相符矣。特功甫、斗南之父均未审耳。功甫生自朱门,儒雅好事,杨诚斋以“佳公子”“穷诗客”目之,有《玉照堂词》一卷,斗南所作六首,见弁阳翁《绝妙好词》,陆辅之《词旨》“属对”又载其“金谷移春,玉壶贮暖”,“拥石池台、约花兰槛”之句,今逸其全。叔夏声律之学,师承有自盖如此。邓牧心又云:“叔夏《春水》一词,绝唱今古,人号之曰张春水。”孔行素《至正真记》云:“钱唐张叔夏尝赋《孤雁词》,有‘写不成书,只记(按,当作“寄”)得、相思一点’,人皆称之曰张孤雁。”二词今俱见集中,亦唐人“刘夜坐”“郑鹧鸪”之比也。附识于首,俟后之读《山中白云》者考焉。[3]168-169
根据《山中白云词》中的词作和《宋史》的记载,龚翔麟推知“叔夏生于宋理宗淳佑戊申,循王五子,叔夏未知出谁后”。厉鹗认为“《宋史》不载,固无从考索”,故而他从精读已有文献入手。龚本《山中白云词》后附袁桷《送叔夏归杭疏》,其中有“古梅千槛,空怀玉照之风流”。玉照乃张镃功甫堂名,而“功甫是循王诸孙,叔夏出功甫后无疑也”。邓牧《山中白云词序》称“其父寄闲先生善词名世,君又得之家庭所传者”,但并未提及寄闲之名。厉鹗在邓氏《伯牙琴》中发现《张寄闲词序》,得知“叔夏父名枢,字斗南,号寄闲”(1)笔者所寓目《知不足斋本丛书》本《伯牙琴》有《张叔夏词集序》而无《张寄闲词序》,故厉鹗所见之版本当与此不同。。张镃之名从金,张枢之名从木,张炎之名从火,厉鹗其以五行相生为世次之名。厉鹗以为“功甫是循王诸孙”,故称“叔夏于功甫为三世,于循王为五世,与袁伯长赠诗注云‘为循王五世孙’者相符矣”,“特功甫、斗南之父均未审耳”。考证出张炎与张镃、张枢的关系之后,厉鹗又对镃、枢二人作了简介。镃“生自朱门,儒雅好事”,杨万里以“佳公子”“穷诗客”目之,有《玉照堂词》一卷,而枢“所作六首,见弁阳翁《绝妙好词》,陆辅之《词旨》‘属对’又载其‘金谷移春,玉壶贮暖’,‘拥石池台、约花兰槛’之句,今逸其全”。读《山中白云词》者可由此得之,张炎于声律之学师承有自。邓牧《山中白云词序》称“《春水》一词,绝唱千古,人以‘张春水’目之”,此事在当时已人所共知。而孔齐《至正真记》载“钱唐张叔夏尝赋《孤雁词》,有‘写不成书,只记得、相思一点’,人皆称之曰张孤雁”,并不为人熟知。这里的《至正真记》四卷,乃元孔齐著,杂论元代朝野琐事。此书流传不广,赵昱、赵信小山堂藏有抄本[10],厉鹗则善加利用。
赵昱《山中白云词题辞》[3]169对张炎也颇有考订。他认为“词源于诗,未有词工不能诗者”,张炎“词清空秀远,绝出宋季诸名家上,意其诗必有可观”,因此,赵氏的探究基本集中在张炎诗作上。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二张鹿徵条下云:“山居钞书颇多,著述甚富,予所见者,仅《玉光剑气集》《謏闻正续笔》数种而已。曩造其山居,见案头有手抄宋季张炎叔夏诗集一卷,今其遗书不可复问,诗亦流传者寡矣。”[11]自此之后,张炎诗或已失传。经赵昱搜寻,仅在袁桷所纂《(延祐)四明志》发现其《题腰带水》一绝,“语意佳绝,且有承平故家之感”,颇可与其词相互参详[3]169。
赵信的考订工作集中在有关张词的本事上,其《山中白云词题识》提及明汪砢玉的《珊瑚网》。是书卷三二名画题跋“陆行直碧梧苍石图”条云:“‘候虫凄断,人语西风岸。月落沙平流水漫,惊见芦花来雁。可怜瘦损兰成,多情只为卿。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此友人张叔夏赠余之作也,余不能记忆。于至治元年(1321)仲夏廿四日戏作《碧梧苍石》,与冶仙西窗夜坐,因语及此,转瞬二十一载。今卿卿、叔夏皆成故人,恍然如隔世事。遂书于卷首,以记一时之感慨云。季道陆行直题。”[12]赵信将这段记载视作张炎《清平乐》一词的本事,固无不可,但他似乎也忽视了其中的重要信息,即至治元年时张炎已下世。
从龚翔麟、厉鹗、赵昱到赵信,张炎生平研究日渐深入。其间,相关文献的搜集、研读起到了关键作用。借助邓牧《伯牙琴》,厉鹗根据五行相生之理推出张炎之世次;借助《(延祐)四明志》,赵昱辑得张炎佚诗一首;借助汪砢玉《珊瑚网》,后人获知张炎卒年之下限。当然,诸家考订也有不足之处,其后亦有学者予以辨证、补充。如江藩指出:“史浩《广寿慧云寺记》称镃为循王曾孙。石刻碑文后,有镃孙柽跋,盖以五行相生为世次之名者,始于功甫。……枢与柽名皆从木,是为弟兄行。木生火,故玉田生名炎也。以张氏世系计之,叔夏乃循王之六世孙。”[13]270总体而言,上述讨论基本奠定了张炎生平研究的大致格局,后来丁丙等人虽然也有所推进,但多为锦上添花。
三、雍乾词坛的“山中白云”风
尽管张炎的词坛地位在康熙年间已经确立,但《山中白云词》当时的影响力并不大。在《全清词·顺康卷》及其补编中明确提及“山中白云词”的只有两首,分别为邵瑸的《声声慢·题山中白云词》[14]9302和杜诏的《壶中天·再用前韵志别,并简缪虞皋》[14]11191。而随着《山中白云词》的多次重刊,“山中白云”在《全清词·雍乾卷》中出现频率明显提高。首先,雍乾词坛有不少题《山中白云词》之作,比如郑沄有《月下笛·玉田〈山中白云词〉题后》[15]5345,李澧有《芙蓉曲·题张玉田〈山中白云词〉卷》[15]6487。其次,词人在创作中主动提及己作与张词的渊源。朱彭有《曲游春·访陆氏皆山楼遗址》[15]1842,其小序云:“宋季澄江陆起潜与张玉田交好。玉田《山中白云词》有题起潜皆山楼四景,及重登皆山楼作,云:‘楼面惠山,而澄江之山,自北而东,自东而南,崒嵂清丽,应接不暇。西有大江,月白潮生,对之神爽。’余久客此,遍访土人,俱不知有斯楼之名,又何从觅其遗址耶?聊作此解,以贻后人。”朱词以“遥思排闼青来,伊人遥隔”为结,句下自注云:“‘看排闼青来,书床啸咏’,叔夏词中句。”(按,此句见于《山中白云词》卷六《摸鱼子·己酉重登陆起潜皆山楼正对惠山》,即朱氏所谓“重登皆山楼作”。)再次,品评时人之作常以“山中白云”为美学典范,比如金兆燕《醉太平·题李端舒词集》有“琅笺句新。瑶音字芬。知君词客前身。定山中白云”[15]990,李澧《洞仙歌·题王麟洲〈珠尘乐府〉》有“竹翁遗调在,琴趣茶烟,只许山中白云并”[15]6434。
“山中白云”在词作中的反复出现,表明《山中白云词》在雍乾词坛的流传程度远超康熙词坛,而这一点在词人的追和之作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
在《全清词·顺康卷》及其补编中,词人对张炎的追和基本集中在《词综》所收录的张词。超出的十余首可以分为两类:一部分词作的追和对象既见于《玉田词》又见于《山中白云词》,而康熙年间《玉田词》尚易觅得,其流传程度甚至超过《山中白云词》,因此这类作品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山中白云词》的刊行;另一部分词作的追和对象仅见于《山中白云词》,包括查慎行的《新雁过妆楼·赋菊,用玉田旧韵》[14]9119、邵瑸的《绿意·荷叶,用玉田韵》[14]9319、《渔歌子·用玉田韵》(十首)[14]9321、《木兰花慢·吴快亭书来,知其客登州,词以怀之,用玉田韵》[14]9335、吴贯勉的《台城路·登鸡鸣寺,用玉田游北山寺韵》[14]10035。其中,邵瑸追和的《绿意》在《词综》中归属无名氏,《山中白云词》卷六有《红情·〈疎影〉〈暗香〉,姜白石为梅着语。因易之曰“红情”“绿意”,以荷花荷叶咏之》,吴贯勉追和的《台城路》虽然并不只见于《山中白云词》,但是《玉田词》卷上作《台城路·雪窦寺访同翁日东岩》,而《山中白云词》卷二作《台城路·游北山寺》。到了雍乾时期,越来越多的词人开始追和《山中白云词》中的张词。这些追和之作中有两类现象值得注意。一方面,《山中白云词》超出《玉田词》的那一百四十三首词日益受到关注,比如王又曾有《台城路·舟中望惠山,用玉田韵》[15]679,方成培有《八声甘州·用玉田韵》[15]1726,陈朗有《柳梢青·咏雪,和〈山中白云词〉韵》[15]4353;另一方面,对《词综》与《山中白云词》的相异之处,词人开始倾向于后者,比如詹肇堂有《探芳信·春日过东城汪氏园林,追忆丁亥夏日,与沈椒园先生、卫卓少明府觞咏于此,今二十年矣。椒园先生已归道山,卓少明府尚官粤西,存殁聚散之感,黯然于怀。因歌此曲,即用张玉田西湖春感韵》[15]1937和《八声甘州·坠花堕絮,绝影东风,追念昔游,迥如天上。凄然身世之感,不独悔北辕南柁之劳劳也。用玉田生北游归别沈尧道韵》[15]1958,其追和的两首词在《词综》中分别作《探芳信·次周草窗韵》《甘州·饯沈秋江》,而在《山中白云词》中分别作《探芳信·西湖春感,寄草窗》《甘州·庚寅岁,沈尧道同余北归,各处杭越。逾岁,尧道来问寂寞,语笑数日,又复别去。赋此曲并寄赵学舟》。种种迹象或许可以表明,《山中白云词》在重刊之后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在《山中白云词》广为流传之后,一种与《山中白云词》紧密相连的现象应运而生,那就是集山中白云词。集句词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的王安石,谢章铤指出:“第考之《临川集》,荆公已启其端。咏梅《甘露歌》三首,草堂《菩萨蛮》一首,皆是集句。……蘅圃《题〈蕃锦集〉》云:‘是谁能纫百家衣,只许半山人说。’当是指此,非泛言诗中集句也。”[13]3467据学者初步统计,“宋词人有集句者即有王安石、苏轼、赵彦端、张孝祥、杨冠卿、辛弃疾等六七家之多”,不过,“宋人为集句词既乏规模,造诣也不高,尚处于形式上探索、价值上轻忽的拓荒阶段”[16]。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朱彝尊“集唐人诗句,自一字以至十余字,辏成小词”,“长短自合,宫商悉谐,似唐人有意为之,留以待锡鬯之驱使”,其《蕃锦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前贤[17]。到了乾隆年间,集句词又出现了新的变化,“通阕只集一人之句者”开始出现,其中“一人”就是张炎,而集句者以江昉为代表。
江昉,字旭东,号研农,又号橙里,安徽歙县人。寓居扬州,与厉鹗、王又曾等过从甚密,有《练溪渔唱》二卷、附《集山中白云词》一卷。金兆燕《集山中白云词序》云:“然挦扯诗句,不过五言七言;若排比词家,或易同音同调。未有抉百弓之畎浍,另起波澜;卸七宝之楼台,自为榱桷,如橙里词人之集玉田词句者也。”[18]相对而言,集词句成词的难度要比集诗句成词高一些,而“通阕只集一人之句”的难度也就更高。比如,其《摸鱼儿·月夜登金山》云:
舣孤篷、水平天远,古台半压琪树。石根清气千年润,禅外更无今古。浮净宇。对此境尘消,江影沉沉露。停杯问取。任一路白云,炯然冰洁,空翠洒衣屦。 凭阑久,说与霓裳莫舞。此时心事良苦。浦潮夜涌平沙白,落叶空江无数。还自语。听虚籁泠泠,无避秋声处。离情万绪。正独立苍茫,呜呜歌罢,小艇载诗去。[15]1627
从词调到词题再到词句,这首词与《山中白云词》卷八《摸鱼子·为卞南仲赋月溪》颇为相近。张词云:
溯空明、霁蟾飞下,湖湘难辨遥树。流来那得清如许,不与众流东注。浮净宇。任消息虚盈,壶内藏今古。停杯问取。甚玉笛移宫,银桥散影,依旧广寒府。 休凝伫。鼓枻渔歌在否。沧浪浑是烟雨。黄河路接银河路,炯炯近天尺五。还自语。奈一寸闲心,不是安愁处。凌风远举。趁冰玉光中,排云万里,秋艇载诗去。[3]138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除了“秋”与“小”的区别外,江词在相同位置沿用了张词中的“浮净宇”“停杯问取”“还自语”“秋艇载诗去”。另外,《山中白云词》卷六《摸鱼子·己酉重登陆起潜皆山楼,正对惠山》上片末句为“空翠洒衣屦”,江词也与之完全一致。诸多的相同之处反映了通阕只集一人之句的难点所在:即便《山中白云词》拥有二百九十六阕,但这对集句者而言恐怕并不算多,毕竟集句过程中要考虑到词调、词题、词韵等多方面的限制。因此,金兆燕称江氏《集山中白云词》是“牵橘柚槐榆而为兄弟,杂金银铅汞而配丁壬”。江氏本人创作态度严谨,“笔不苟下,稿辄数易,刿鉥肝肾,磨濯心志”[18]沈大成序,自然比观者更能体会其中的难度,但他集张氏一人之句达一卷之多,这也充分体现了其个人对张词心慕手追的程度。
从“山中白云”乏人提起到反复出现,从追和对象主要集中在《词综》到几乎遍布《山中白云词》,从朱彝尊“集唐人诗句”以为词到江昉集山中白云词,张炎在雍乾词坛的影响力较之顺康大大提高。
四、结语
随着《词综》《山中白云词》的相继刊行,在浙西词派大力推尊下,张炎的典范地位得以确立。不过,康熙词坛对张炎的关注,更多集中在《词综》所收录的张词上,其《山中白云词》流传未广,连杜诏在参与编纂《御选历代词》时都“未知有‘山中白云’名目”。从康熙六十一年到乾隆元年,曹炳曾、赵昱在十五年间三次重刊《山中白云词》,在重刊过程中,厉鹗、赵昱、赵信等人充分发掘历史文献,奠定了有关张炎生平研究的大致格局。自《山中白云词》多次重刊之后,学界对张炎的关注逐渐从《词综》转向《山中白云词》,雍乾词坛也呈现出新的变化:词人在创作中反复提及“山中白云”,追和对象几乎遍布《山中白云词》,集山中白云词的现象开始出现。因此可以说,《山中白云词》的重刊,无论是对张炎典范地位的提高,还是对雍乾词坛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美丽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