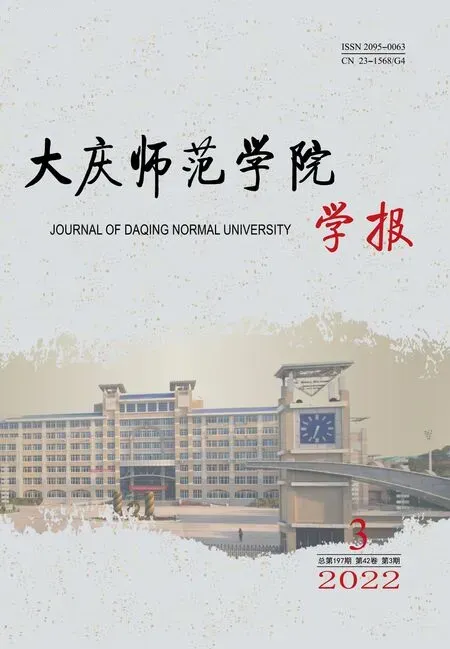《云中记》的思维方式和小说叙事特征探析
张大海
(大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是全国各民族文学创作丰富性的集合。虽然少数民族作家多以汉语发表文学作品,但他们各自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审美体验,仍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给读者带来新的阅读感受,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新的启发。这也是近年来,民族文学得到越来越多重视的原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藏族作家中先后产生了扎西达娃、阿来和次仁罗布等众多有研究价值的作家。不同于扎西达娃和次仁罗布等人的小说创作,阿来作品的构思多集中于民族文化和现代文明社会不断交融的时代背景。小说《云中记》,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在这种构思下的文学写作特征。尽管读者和评论界已经对这部小说的多元创作背景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解析,但因为这部小说文化价值的丰富性和阿来在创作时所秉持的多元文化思维,仍让《云中记》蕴含了更值得期待的审美阐释空间。本作的思路,首先要确定《云中记》的基本写作结构,让读者了解阿来是如何以藏族时空观、世界观和科学意识的行文方式来建构起小说的叙事策略;其次,还要将文学批评的视角还给阿来,让他以自己的世界观来解释小说中的情节和隐喻,而不是以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来解释小说。因为唯有如此,读者才能从更为直观的角度,理解阿来创作的意义。
一、多线索的篇章结构
对于读者来说,精研一部小说可以从一个大前提开始,再过渡到情节和人物分析,以及相应的语言文字研究,这样才会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网络。对于大前提的理解,通俗地说,就是要了解小说的基本结构,比如章节编排以及人物进退。对这些问题的梳理,会成为这部小说的支撑性知识。当这些支撑性知识确立后,再进行更为细致的文本阅读,对小说的理解才会变得相对容易些。《云中记》因为具有不同于其他地震文学的结构性特征,所以,对它的理解,也要先从小说的基本结构谈起。
按照阿来的设计,《云中记》共分为十二章。但从这些章节的内容结合度来看,它的整体结构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小说中的第一章到第五章,讲得是小说主人公阿巴回到云中村最初六天的生活;第二部分是小说中的第六章到第十一章,讲得是阿巴在云中村住下后的第一到第六个月;第三部分是小说的第十二章,也是整部小说的尾声,讲得是发生山体滑坡的“那一天”的故事。这样的时间安排是一种顺向的时间设计,它在小说的整体叙事层面上属于第一层,其总体指向符合科学时空观。在进一步的阅读中,读者会发现这部小说还具有第二层叙事结构,也就是阿来以科学时空观为叙事前提,再辅以情感叙事,重新创作出按照苯教时空观为叙事特征的新的小说结构。这种设计正是阿来的与众不同之处。
阿来的第二层叙事使小说形成类似电影拍摄效果的、以故事套故事的小说叙事结构,这是《云中记》有别于一般地震文学,并能深化小说情感的地方。以第一层的时间叙事来看,阿巴一个人上山的行为,从小说内容判断应该是2013年。这是小说的主要叙事时间线。除此外,其他的二级叙事时间线按照阿巴的思绪,以意识流的方式分别记录地震前后的生活:如2008年的地震后急救情况,2009年的移民村生活,少年阿巴的生活,阿巴昏睡的十年生活(约1976—1986年),更早的土司时代生活,新世纪的村镇旅游情况,以及神话时代的阿吾塔毗和矮脚人等叙事段落。在这些不同时代的故事中,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因为历史和情感的延续性,而积攒起联系到现在的文化记忆。由于每一个时间线都可以对应一个故事的起源,同时这些故事在情感的召唤下,又形成连续性的从神话到现实的历史关系。读者在阅读时,以不同叙事段落的视角分别进入,又以情感的总和形式走出,其整体的大叙事脉络就像藏族氆氇中以五彩线开始,以彩虹般织物结束的“织彩为文”的过程。如果要整合其中的关系,读者就要有既能理清每一条彩线上的小故事,又要有能将这些小故事集合成一个完整的大故事的技能。这是一种断续式的写作,又是一种多线索协同并进的创作方法。虽然在部分章节中,阿来有对同样场景进行重复描写的情况,但作为整体的观感,这种重复仍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文本解释。
二、民族特色的时空观
公元7世纪后,随着佛教传入西藏地区,藏民“普遍接受了佛教的灵魂不灭和六道轮回的思想”。(1)陈庆英:《论产生活佛转世的思想基础》,《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31页。这在藏族作家的时间观念中,往往就是因果叙事和多时空叙事的构思基础。比如9世纪的藏译本佛经《虎耳譬喻经》,其故事所遵循的循环时空观,就是:“基于线性时间观支配下的往世故事和现实故事之上的。”(2)周利群:《循环与线性交互的佛教时间观》,《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第130页。同样的情况,在《云中记》第二层叙事中出现的不同方向的时间叙事,也是在这种时空观支配下的结果。不过要说明一下的是,这里的时空观,其实也是生死观。而苯教生死观和藏传佛教生死观最大的不同,就是苯教没有轮回的观念,这也是阿来在《云中记》中,除科学时空观外的主要叙事逻辑。
(一)阿来:从田野到文学
阿来是一个既有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生活经历,又有成都的现代生活经验,还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作家。在他的思想中,基本体现了一个藏族作家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文化景观转变过程。
阿来自出生到成年,在阿坝州政府所在地马尔康县一共生活了36年。(3)参见阿来:《穿行于多样化的文化之间》,《中国民族》2001年第6期,第23—24页。马尔康县(2015年11月,马尔康撤县设市)曾是以藏民为主要世居人口的县,其中:“1950年藏族人口21140人,占总人口89.17%;回族人口600人,占总人口的2.53%;汉族人口1960人,占总人口8.27%。”(4)四川省马尔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马尔康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页。到了1956—1960年,马尔康县汉族人口一度占总人口的51.81%。(5)参见四川省马尔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马尔康县志》,第76页。阿来1959年出生,按照当时马尔康县的汉藏人口比例,阿来在心理上自然会成为汉藏文化的双向认同者。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汉语是统领着广大乡野的城镇的语言。藏语的乡野就汇聚在这些讲着官方语言的城镇的四周。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不同的心灵景观。”(6)吴怀尧:《阿来:文学即宗教》,《延安文学》2009年第3期,第104页。这里让阿来好奇的心灵景观,是藏语思维和汉语思维所建构的心理世界。1996年,阿来应聘到成都《科幻世界》期刊社工作,这让他有了更多观察汉语世界的机会,同时,也为他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心灵景观提供了有益的科学参考。
不同地区的汉藏人口比例对当地作家的文化影响有明显差异。比如,与阿来同年出生的作家扎西达娃,他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人。据1964年6月巴塘县人口普查结果,全县总人口中,“藏族23207人,汉族1511人,纳西族236人,回族5人,苗族1人”。(7)四川省巴塘县志编纂委员会:《巴塘县志》,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101页。藏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92.97%,汉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6.05%。成年后,扎西达娃又长期生活在藏族人口比例颇高的拉萨。以他开始文学创作的20世纪80年代为例,1982年,“拉萨市总人口313359人。其中,藏族268142人,占总人口的85.57%;汉族43411人,占总人口的13.85%”。(8)拉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拉萨市志》(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1247页。巴塘和拉萨,都是藏族人口比例偏高的地方,虽然扎西达娃接受过汉语教育,且能使用汉语写作,但从他生活环境的藏汉人口比例来看,他对藏语世界的了解要明显多于对汉语世界的了解。这种民族文化基础形成了他更接近藏族传统神话和民间传说的魔幻现实主义写作。
与扎西达娃的生活环境不同,因为阿来生活的地区有汉藏双向文化的民族基础,这导致他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祛魅现实主义的创作特征。他的写作要“书写这片蒙昧之地的艰难苏醒”,(9)阿来:《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阿来文学演讲录》,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年,第231页。他不会为满足人们对西藏神秘感的需求而创作,也不会为呼应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1900—1954)的“香格里拉”情结而创作。在阿来的笔下,最有价值的地方,莫过于他向读者展示了现实中的西藏生活。
(二)阿来的时空观
在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志怪小说中,如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使用的时间倒错叙事,(10)参见王慧:《〈聊斋志异〉叙事时间》,《蒲松龄研究》2004年第4期,第67—76页。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使用的轮回、因果叙事,都是在类似神学时空观影响下创作的作品。(11)参见常红星:《〈阅微草堂笔记〉佛教因果观探究》,《宗教研究》2016年第2期,第220—229页。在当代的汉族作家中,对时空的设置一般都相对客观化,即使有倒叙、插叙等内容,也不会明显地违反牛顿时空观。这在现代科学的表述上,就是基本遵循英国天体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1882—1944)在1927年提出的“时间之箭”的概念。依据此概念,时间不具有循环性,其单向度的线性特征否定了宗教轮回的可能性,它将宇宙万物的最终结局指向了不可逆转的万物消耗。(12)参见彼得·柯文尼、罗杰·海菲尔德:《时间之箭》,江涛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6页。卫藏地区的文艺作品,典型的如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在叙事上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意义上的“时间之箭”,就在于它可以通过叙事的分化,将人物、故事、情节等内容,按照不同的时间循环进行重新整合,以此形成不同叙事方向的故事。而“藏传佛教继承和发扬了印度佛教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学说”,(13)乔根锁、徐东明:《关于藏汉佛教因果报应论的比较研究》,《中国藏学》2011年第4期,第44页。这也决定了接受藏传佛教影响的卫藏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多维时空,建造隶属于“复线历史”(杜赞奇语)的文学史。
阿来的小说基本接受单向时空观,比如他的非虚构小说《瞻对》,以及他的成名作《尘埃落定》都是如此。与此同时,他也不排斥藏传佛教的多时空叙事特征,比如《尘埃落定》,虽然大部分叙事内容仍符合牛顿时空观,但在小说的结束部分,阿来以第三视角写“我的灵魂”对“我”的关照,就已经有了藏传佛教中轮回时空观的味道。如此看来,《云中记》中不断变动的时间叙事方法,以及突破现实之障的神性思维,其结果就是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在一个大趋势不变的时空前提下,在不同叙事单元中出现的、不同方向的分层叙事。在这种叙事模式下,梦境、神话、传说、史实,当然还有阿巴自己以及别人的回忆,都可以熔炼其中,形成针对大趋势文本的解释性叙事。除《云中记》外,阿来的小说《遥远的温泉》《格萨尔王》《瞻对》也有分层叙事的特征。如果将这种思维看作一种小说创作的方法,去比较阎连科的小说《受活》,读者就能明显地意识到这种时空交错的分层叙事方法,要较注解式的小说创作有更多的叙事主动性。而要掌握这种叙事的主动性,以《云中记》的经验来看,那就是还要在小说中建立起叙事的锚点。
(三)《云中记》的叙事锚点
《云中记》的故事线索来自2008年的5·12大地震,按照一般的叙事逻辑,这一事件当然应该成为重要的叙事起点。描写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的小说,比如晓洲的《震城》、歌兑的《坼裂》都是这样做的,但阿来作为汶川地震的亲历者,却没有这样做。他在地震后迟迟没有动笔的原因,是他意识到了文学区别于新闻的地方,不在于重复苦难的现场性,而在于“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14)阿来:《不止是苦难,还是生命的颂歌》,《长篇小说选刊》2019年第2期,第6页。他在小说中使用的祭师阿巴,出场时是以登山者的形象出现的,同时出现的还有跟随他登山的两匹马,因为牲口出汗,产生了阿巴“四年多时间没有闻到”的特殊气味,这成为小说的第一个叙事时间点。按照小说的叙事节奏,这一叙事点处于第一阶段6天叙事的起始位。相对标准时间,这种将马的气味间隔作为计时方法的“事物型时间”,大概略等于海德格尔以此刻的存在来证明意义的时间观。(15)参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欧东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03页。在《云中记》中,这种计时方法也为藏民采用。如小说中“祭山神的日子就定在了采摘樱桃之前。”(第一章)、“父亲是修机耕道时死的。”(第二章)、“云中村重新通电的那个夜晚,阿巴清醒过来了。”(第四章),这些并不精确但又有记忆特征的事物型时间是很多小说家在写作时经常运用的计时方法,它代表了事物的存在价值与记忆(历史)之间的关系,在使用习惯上也比较适合有前现代思维的普通藏民。对文学创作来说,这种事物型时间的意义,在于让某个事物或者某个景物成为小说套层结构的一部分,可以有效避免标准时间的非情感性特征,而有利于小说故事的连接。
在大故事中不断地套出小故事,是有利于小说展开叙事边界的,而为了稳定这种展开的叙事边界,阿来在《云中记》中设置了两个锚点,其一是阿巴的祭祀,其二是地震以及随后的山体滑坡。他让所有的套层叙事都围绕着这两个锚点展开,这保证了小说“收”的范围和按照“时间之箭”而来的整体叙事走向,避免了意识流式的无限创作。事实上,这两个锚点也是这部小说最基本的两个叙事原点。阿巴祭祀是主叙事,整部小说的大框架都围绕着他的祭祀过程展开,并随着他以身殉祭完成叙事的闭环。地震以及潜在的山体滑坡是次叙事,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积淀在小说的底层,地震和山体滑坡虽然没有成为主叙事,但它又是整部小说的逻辑起点和人物的最终归宿,对小说人物关系,包括各种小故事群的发生都起着间隔与引导的作用。
三、民族特色的世界观
1984年,王富仁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提到,鲁迅小说研究应该:“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首先理解并说明鲁迅和他自己的主导创作意图!”(16)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9页。现在研读阿来的小说《云中记》,其中的视点也应当是“回到阿来那里去,理解并说明阿来和他自己的主导创作意图”,应该将《云中记》放在它所在的文化体系中去理解,而非回到研究者自己的知识结构或阅读史中去理解。虽然在分析小说时,让研究者绝对地回避自己的知识结构并不现实,但作为一种可提醒的研读方向,研究者仍应意识到小说叙事中的“隐含作者”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并不是通过阅读小说发现自己,而应当是在小说作者的非隐喻性写作,或者相关的文化背景信息中找到作者自己的阐释文本。如果用通俗的、常识性语言来说,就是要用作者提供的各种信息来解读作品,而不是用研究者的文化范式来解读作品。这是两个方向的解读,当然也会是两个结果的解读。
(一)他者文化中的边缘认同
阿来是来自祖国边疆地区的作家,他在了解其他文化体系的作家时,也比较注意关注这些文化体系内相对边缘的作家。如使用意第绪语写作的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4—1991),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瑞森(Toni Morrison,1931—2019),(17)参见阿来:《看见》,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54页。还有生活在非洲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18)参见阿来:《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阿来文学演讲录》,第154—156页。这些文化资源加上阿来的文学意识,逐渐让他创作出一种既有藏族文化背景,又有现代生活故事,同时还打破了西方“东方主义”幻象的文章写作风格。(19)参见阿来:《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阿来文学演讲录》,第1—27页。
不同于其他作家对宗教的神秘化理解,阿来小说中的宗教元素只是一种带有民俗意味的文化符号。这点我们从他的《机村史诗》《蘑菇圈》《三只虫草》《河上柏影》等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中都能感受到。在《云中记》中,他也依然秉持了这一立场。阿来说:“我这种人生观是带宗教感的。”(20)易文翔、阿来:《写作:忠实于内心的表达》,《小说评论》2004年第5期,第19页。虽然阿巴在现实生活中是边缘人物,但阿来在这个人物的设置,乃至最终结局上并没有对他进行完全边缘化的处理。其实,就“阿巴”在藏语中的解释来说,就有两种意思,其一意为“作法”,是指在人去世后作法事的阴阳先生。(21)参见杨冬燕:《(白马)藏族信仰习俗现状调查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第71页。其二意为“神汉”,是指西藏的男性巫师,发音是近似“阿巴”的“拉巴”(lha-pa)。(22)参见孙林:《西藏中部农区民间宗教的信仰类型与祭祀仪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624页。可以说,通过“阿巴”这个名字的命名,阿来完成了对苯教的理性借鉴,而要解释阿巴为什么会随着滑坡体消失的原因,也应当从这里开始。
(二)《云中记》中的苯教思维
阿来在小说中一再强调阿巴是苯教的祭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尽管阿巴本人从来就没有说全过这个称号,但仍不妨碍阿来对他文化身份的持续性命名。因为在苯教的观念中,人死后的灵魂并不像藏传佛教那样遵循轮回转世的规则,而是要依附在某个寄魂物上,变成当地的保护神,这种宗教观念应该是阿巴与云中村共存亡的心理基础。而且在苯教丧葬仪轨中,用活人献祭和用马殉葬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马既可以成为死者死后的坐骑,又可以成为死者的替身,(23)参见霍巍:《从新出考古材料论西藏本教丧葬仪轨的源流》,《藏学学刊》2013年刊,第1—18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阿巴执意要仁钦给他准备两匹马,且毫不计较云丹报价的原因。可以说,在这部小说的开始,阿巴已经在内心深处决定了要以自己和两匹马为祭品,超度云中村的逝者。这是小说的伏笔,而唯有了解苯教思维的读者,才能将其阐释出来。小说中还有一些细节,比如多次暗示仁钦的妈妈寄魂于鸢尾花,其道理也如同阿来在《格萨尔王》中描写的众多寄魂在花朵上且不得超度的女子。(24)参见阿来:《格萨尔王》,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同样,阿巴之所以要抛撒风马、柏枝,也是相信这些物件对云中村众多逝者的价值。当然,如果就一种更加古老的祭祀习俗来说,阿巴最后随滑坡体而去的行为,可能也是一种以自己为祭品的“人祭”活动。这不仅是阿巴在为自己作祭祀,也是为整个云中村的逝者和生者作祭祀。其中的颟顸,自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三)人祭与阿巴的归宿
在历史上,人祭在藏族先民的祭祀活动中并不鲜见,且已得到考古证实。(25)参见霍巍:《西藏高原史前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第46—60页。在我国史书中,如《隋书·卷八十三》中提到的西域女国(即苏毗国)就有“岁初以人祭,或用猕猴”的记载。南京大学高国藩教授《黑城本〈大黑根本命咒〉与吐蕃人肉祭祀巫术》对唐代吐蕃人肉祭祀活动也有相当的考证。虽然后世少见藏民的人祭活动,但藏民杀牲祭赞的习俗在一部分地区仍持续到解放前。(26)参见恰白·次旦平措:《论藏族的焚香祭神习俗》,达瓦次仁译,《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第40—49页。这种带有巫术性的祭祀活动在苯教习俗中,就是一种“赎罪替身”,其方法是:“以人或动物为祭品,将某一个人乃至某一社群遭受的灾祸和邪气带走从而达到隔离‘污’与‘洁’的目的。”(27)郭净:《藏传佛教寺院羌姆与驱邪仪式》,《民族艺术研究》1994年第5期,第53页。知道了苯教中“赎罪替身”的道理,再来理解阿巴要执意随云中村滑坡体消失的想法,也就有了他的合理性。事实上,阿巴“以身殉职”的用意,也正在于他要以一己之力带走整个云中村的污秽与邪气,留给活着的云中村村民一个“洁净”的移民生活。这是阿巴作为祭司的最后献身,也是他要以鬼魂的形式继续守护逝者的使命。
当然,阿巴和阿来《天火》中的多吉之间最重要的差别,还在于小说人物的聚焦关系上。阿巴是《云中记》自始至终的焦点人物,他引领了小说中多个分化的叙事线索。而多吉只是《天火》中某一时期的人物,他去世后,小说的叙事结构并没有改变,灾难仍在继续,人们之间的龃龉也没有停止,在疗治灾难方面,多吉的死似乎没有任何意义。这在阿来的意识中,就是:“没有一个人或一种人,或一个家族,像长河小说中那样始终处于舞台的中心。”(28)阿来:《机村史诗2:天火》,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60页。而阿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作品的核心,而且无论是由幸存者组成的移民村,还是由遇难者组成的云中村,他都是众所周知的人物,是作为祭司引导神与大地关系的“媒介物”。因为这样的人物设定,整部小说的叙事过程只能由他推进、也只能由他完成。这就是我们在《云中记》和《天火》中看到的,以人为主的情感问题和以故事为主的历史问题的区别。显然,阿来更在意的是《云中记》中的情感问题,而这又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不忍碰触的伤痛记忆。
四、《云中记》的科学意识
《云中记》不同于一般地震文学灾难描写的地方,还在于它的科学意识。阿来的小说创作理念,从1990年代的历史传奇和民间故事,如《阿古顿巴》(1986)、《旧年的血迹》(1989)、《行刑人尔依》(1997)、《尘埃落定》(1998)、《月光下的银匠》(2001)等,经《格拉长大》(1995)、《空山》(2003—2008),逐步过渡到《山珍三部》(《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2016)的环保主题,推动他变化的潜意识,主要是由于阿来在《科幻世界》杂志社工作期间(1996—2006)所受到的科学思维影响。从阿来后来发表的作品看,这一时期也是他的创作蓄势期。待到阿来创作系列小说《机村史诗》(原名《空山》)时,他已经将带有现代文明特征的多种物件,比如收音机、电话、报纸、水电站等列为小说叙事的主题,尤其是水电站,以及伴随水电站而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地质勘探人员,一再地成为阿来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带有现代文明和科学素养的象征性人物。这种情况,在《云中记》中也概莫例外,比如小说中的余博士和地质学家。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传统藏族作家的笔下几乎不会出现这样的人物,这恰恰证明了现代文明对阿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阿来的科学意识在《云中记》中的例子还可以在第一章中找到,比如他写道:“3月,渠水奔向返青的冬小麦田。李花开着。桃花开着。前些年政府大力推广的叫作车厘子的外国樱桃繁密的白花也开着。//4月,那些花相继凋谢。//5月,李树、桃树、樱桃树上都结出小小的果子。小桃子毛茸茸的。青绿的李子和樱桃脆生生的。”(29)阿来:《云中记》,《十月》2019年第1期,第7页。这应该是借鉴了美国土地伦理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沙乡年鉴》的写作方法。类似的写作方法,阿来在《成都物候记》中也使用过。利奥波德对土地的理解,显然对阿来的创作产生了启发。(30)参见黄鹤,税雪,唐梦曦:《文学执信与生态保存——阿来访谈录(下)》,《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3期,第86—93页。
由《云中记》中的科学意识,还可以看到阿来在散文创作和小说写作之间的互文关系,也就是说在他写某部小说前,他的某篇散文中已经有了与这部小说相近的信息。读者在读他的散文时,是有可能预知到他可能的小说创作的。比如他的散文集《大地的阶梯》第六章《雪梨之乡读金川》的第三部分《雨夜读金川故事》,其对大小金川之战的资料引述就是对非虚构文学《瞻对》的预演。就某些带有启发性的线索来说,阿来发表在《作家》杂志上的散文《故乡春天记》,也可看作是《云中记》的提前预演。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虽然这是阿来2017年1月发表的散文,但据文中时间推测,这篇文章应该写作于2013年。一个证据是文中提到的“五年前的汶川地震”,另一个证据是文中提到的2013年的芦山地震(震级7.0级)。可以说,阿来在《云中记》中将叙事的时间点设置在2013年,绝非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至少对经历了汶川地震和芦山地震的阿来,他已经将地震设定为一种“事物型时间”的叙事起点,而云中村的滑坡之所以能够成立,也可以从2017年6月的新磨村滑坡(在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中得到回应。无疑,叠溪地震的历史,以及新磨村的悲剧强化了阿来在《故乡春天记》中的地震记忆,并推动了他以故乡阿坝州为旨归的情感积淀。《故乡春天记》中提到的“大雪山叫作阿吾塔毗,山的南边是我家乡马尔康县”,(31)阿来:《故乡春天记》,《作家》2017年第1期,第20页。已经预告了“云中村”的位置,按照《云中记》中给出的“岷江”和“阿吾塔毗”的提示,可知在阿来意向中的云中村,应该是一个在岷江上游且在马尔康或黑水县境内的或在它们附近的村落。岷江上游地区包括松潘、黑水、茂县、理县、汶川5个县级行政单位,这个区域有岷江断裂带、龙门断裂带等断裂系统,且早在2000年,就有地质学家认为这里将有可能发生7.0—7.5级地震。(32)参见周荣军、蒲晓虹、何玉林等:《四川岷江断裂带北段的新活动、岷山断块的隆起及其与地震活动的关系》,《地震地质》2000年第3期,第285—294页。由此可见阿来融科学于小说的写作功力,绝非新闻类、情感类的地震文学所能比。
五、结语
《云中记》有两个意义,其一是对当代小说创作方法的启发,其二是对边地民族心理的展示,且这两个意义之间互有关联。自1980年代以来,当代小说在众多作家的参与下,有过多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探索,产生了一批极有价值的成果。魔幻现实主义、新历史主义、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文学概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评判当代文学写作成绩的重要标识。阿来等少数民族作家通过“对传统汉语语法逻辑(文化逻辑、文化价值)的颠覆与超越,实现‘第二汉语’叙事理想。”(33)罗庆春、王菊:《“第二母语”的诗性创造——四川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语言艺术论》,《凉山文学》2014年第1期,第63页。这里的“第二汉语”,就是相对于内地作家的边地文学语言。实际上,正因为有了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创作,汉语才有了与民族文学协调前进的组合方式与表达空间,而少数民族的故事与生活,包括他们的心理和世界观,也才会以他们所理解的方式,自内而外地展示给读者。这对于马原、范稳等自外而内的观察者,当然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另一方面,对汉语的发展来说,其长期的历史趋势亦当如以英语为交流语言的跨文化背景创作,只有产生出更多文化背景的写作者,其意义才会如同顾颉刚的历史想象,让“外来者与边缘居民周期性地给予中华文化以活力”。(34)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在这一可能场景到来之前,就是以阿来为代表的边地文学写作实践,《云中记》的意义,也将会在这种写作实践中,呈现出它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