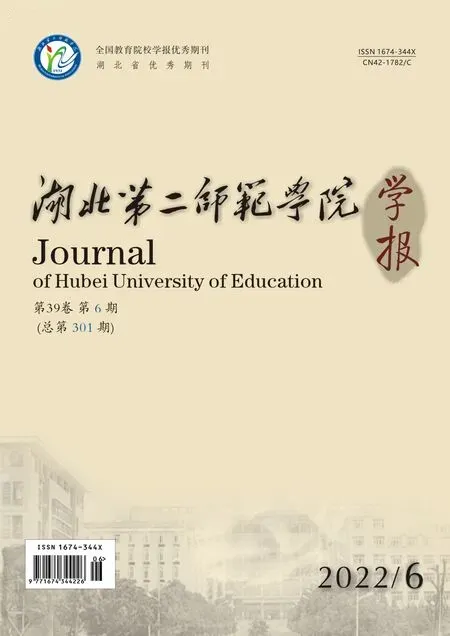《伊芙琳》的社会语境与历史隐喻分析
陈芷蔚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广州510006)
乔伊斯小说《伊芙琳》中的女主伊芙琳作为弱势、经济无法独立的女性角色,时常受到巨大的生活压力,由此产生了一种逃离意识,但最终选择了妥协,是一种丧失自我、言行失格的行为。在当时男权逼人的社会背景下,无疑注定了她的人生悲剧。乔伊斯意识流的写作手法直观上淡化了小说情节,将篇幅多用在自我意识活动变化中,全文中重要的一点即主人公伊芙琳的感情麻痹,体现在自身目标的缺失、优柔寡断、缺乏勇气和反抗意识上,其受到人物和环境等外部阻碍,逐渐形成一种感情麻木、失去自我的表现,丧失了对美好事物和未来的追求。
一、《伊芙琳》的语篇分析和性格逃离冲突
(一)《伊芙琳》语篇分析
文中多以“她”来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从而推动故事情节。在文中,主人公的压抑苦闷生活主要是通过麻木的精神来表现的。通过象征主义手法的应用,用“灰尘”“灰蒙”等环境词汇象征当时都柏林的社会精神瘫痪情况。文中起始就描述主人公独自坐在床边,思绪翻涌着选择是去是留。[1]她的头依靠在窗帘上,窗帘上的灰尘被嗅入到鼻孔中。通过暗喻的方式,将灰尘的含义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的物质上,同时暗示了一种沉闷压抑的环境,也突出了当时社会的沉沉死气,整个社会充斥着一股死板、丧失活力的气息,灰尘无法清理,也从侧面展示了主人公和都柏林社会人群的精神麻痹状态。文中从一开始描述了她站在拥挤的人群之中等待船只,不免引起读者思考和遐想。[2]“she answered”中,这句话主要通过主位和上一句述位的she链接,在文中的she对于he的提问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并冷漠处理。此时她的视线注视远方,内心世界处于两难抉择之中,脑海之间斗争与挣扎,在去和留之间来回挣扎,内心的不安和焦躁让主人公陷入一种极度痛苦的情绪中。“she felt her cheek pale and coid and out of a maze of dis-tress,sheprayed to God todirect her,to show her what wsa her duty。”她感觉到了自己的脸色苍白冰冷,在这种极度矛盾的去与留之间摇摆不定,让她陷入快要崩溃的边缘。她的心理矛盾,正处于无助彷徨的时候,她将希望寄托于上帝,希望上帝给予指明道路。[3]但实际上这种祈求毫无意义,最终的决定还需依靠自己。一旦依靠别人就会迷失自我,优柔寡断的性格也增添了主人公的悲剧色彩。但在急剧的混乱中她仍旧保持一丝理智,在面对情人为她做的一切时,她竟产生放弃后对不起情人的感情,在另一方面也考虑了她压抑的家庭,弟弟父亲都是沉重的负担。伊芙琳在去留上面对人生的两难,弗兰克突然闯入伊芙琳单调枯燥的生活,突破了死气沉沉的压抑感,和她讲述了遥远国度的冒险经历,给伊芙琳描述了全新的体验和世界,尽管相处感情模糊,但伊芙琳依旧产生了一种与情人私奔的心思。私奔的念头一旦产生,便表示需要抛弃原有的生活环境、原生家庭,开始新生。情人的果断和主人公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走和留的过程中,伊芙琳依旧会考虑如果离开真的会幸福吗?是遵守对妈妈许下支撑家庭的承诺、还是和弗兰克开创全新的生活?她是否真的已爱上他?多种考虑均体现出了伊芙琳对于未来的迷茫和对情人的不信任,缺乏坚定的信念。
(二)主人公的性格与逃离之间的冲突
从主人公的回忆中读者可以了解到伊芙琳的身世背景,母亲去世后她需要辛苦地赚钱养家,不仅需要照顾一家上下,还必须忍受残暴父亲的辱骂和刁难。直到弗兰克的出现,才逐渐让她产生一种逃离、反抗的意识。但是在逃离抉择上却选择了放弃,主要矛盾可以表现为几点:(1)家庭的负担和对于母亲的承诺。在母亲去世前主人公许下了尽力支撑这个家的承诺,这种诺言也随之成为了捆住伊芙琳的枷锁,将她束缚在沉重压抑的环境中。她的不反抗和善良性格让她成为了家庭的重要经济支柱,如果她选择离去,则代表伊芙琳违背了和母亲的约定。[4]作者对于伊芙琳的性格描述,让读者可以看到她极度缺乏自信和勇气,无法突破责任的枷锁,无法放弃家庭与父亲,再独立开创新的生活。(2)对于家庭的不舍。家作为伊芙琳成长生存的地方,无论多么的不堪不幸,都曾经伴随了主人公的童年,作为一个安身之地,虽然痛苦,但并未想过逃离,可以为她提供一种归属安全感。而情人所描绘的生活又新鲜充满吸引力,但突然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进入陌生的地方,让软弱的伊芙琳不由生起一种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惧感。[5]尽管在文中作者描述出的父母相处是一种暴力威胁和刻薄的过程,但在离别抉择的时候,伊芙琳依旧会浮现和父亲相处的画面,这也体现主人公对家的眷恋,对家人的不舍,对于这个从小到大的家庭产生了一种难以割舍的纽带。(3)父权的社会。在文中的男权社会背景下,伊芙琳作为女性角色,在致使她放弃私奔上也占据了重要的因素。母亲在托付遗言时并没有将重担交付给父亲或者家中其他男性,在后面也提及了弟弟在外奔波鲜少回家。可见在当时的爱尔兰社会,以男性作为主导地位,而女性仍需要依附于男性或者依照男性的规定来生存,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在这种观念里,女性逐渐成为一种没有思维的角色,在家庭中被迫成为温顺牺牲的角色,辛苦操劳。可悲的是,母亲还要将这种思想强加在伊芙琳身上,使其成为了男权牺牲品。所以伊芙琳作为女性角色被束缚在家,也是无法逃离原生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4)传统思维和依赖。从传统观念来讲,伊芙琳的悲剧可以延伸为当时爱尔兰社会的悲剧。在爱尔兰民族运动发展得轰轰烈烈时,其中夹杂了反抗和瘫痪、传统和现代色彩交织的思想,和原有的封建形态形成鲜明的对比。乔伊斯的父亲作为爱尔兰独立运动的领袖帕内尔的政工人员,最初的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在帕内尔亡故后家庭经济便每况愈下,而父亲又不干预家政,尽数交给母亲打理。[6]《伊芙琳》一文的创作背景下,乔伊斯正处于是否离开都柏林的抉择中。而小说里主人公的矛盾纠结思想也暗喻了作者自身的挣扎苦楚。不仅被传统的观念所束缚,同时也受到现代化变革的召唤。但小说主人公在面对瘫痪的环境下依旧未能逃出囚笼,担心一走了之后的议论,贪恋家庭的归属感,以及对于传统的固化思维和对未来的迷茫,均是造成伊芙琳逃离失败的因素。但乔伊斯则带上爱人远去,乔伊斯选取并接受了现代化召唤,毅然选择了走向现代文学,即为张扬人的个性化发展,构建出一种符合人性发展的道德观念。从依赖这一方面来讲,主人公在面临选择时,其独立人格比较薄弱,更依赖于他人,将自身的未来托付给他人意愿,在这种思维下,就算逃离成功,伊芙琳也无法获得新生。在逃离都柏林时,主人公陷入一种未知内心的状态,她的离开是建立在弗兰克的怂恿和父权家庭压迫下,她的逃离是作为一个爱人、妻子的身份逃离,在固有的思维下,她的逃离只是从一个原有的家庭中进入到另一个家庭充当妻子的角色进行奉献付出。逃离是依赖于另一个男人身上的逃离,以一种卑微姿态进入到新的家庭被剥夺,并非是一种救赎。在长期的原生态、专横压迫的环境下生长,主人公逐渐形成一种依赖性、麻痹自我意识的心态,所以一旦产生逃离的心态,必然会出现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也从侧面体现出了女主的无法独立、缺少思维能力的性格。所以真正的救赎,单靠依赖他人是无法成功的,唯有明确自己的人格、突破原有的精神控制枷锁、转变瘫痪的大脑,才会真正地逃脱成功。
二、《伊芙琳》的象征隐喻和社会语境
(一)《伊芙琳》的历史隐喻性
爱尔兰位处于欧陆边缘,它在12世纪被亨利二世关注后,就逐渐发展成了血腥的殖民统治。因为爱尔兰的社会背景和英国统治,让爱尔兰的社会环境处于一种扭曲的状态。这让20世纪的爱尔兰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在《都柏林人》的小说集中写出了第四个短篇小说《伊芙琳》。小说《伊芙琳》深刻表现出现代派意味,主要通过隐喻来体现,而隐喻的语言性又包括了重复、象征、意象等。文中讲述了伊芙琳在痛苦不堪的家庭负担下,与水手弗兰克约定共同离家出走,但最终在反复的纠结思考下放弃了逃离的故事。乔伊斯也曾表示,该篇文章是给予爱尔兰社会历史背景的隐喻创作。在历史的隐喻下,大英帝国的身影以一种广泛背景存在,在虚构的文中充斥了东方主义色彩。伊芙琳的痛苦悲剧和瘫痪消极色彩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当时爱尔兰人民的共同悲剧,对于乔伊斯而言,若国家失去了主权,缺少了民族精神,人民处于一种没有尊严的基础上生存,那势必会让民族处于一种麻木瘫痪的状态,而都柏林则是瘫痪的中心。《都柏林人》是作者的早期作品,为现实主义小说。《伊芙琳》不仅包括了现实主义色彩,也通过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深化了社会主题,在表现手法和协作技巧上进行创新,具有鲜明的现代派色彩。而现代主义文学可以较好地通过暗喻来表现本质,洛奇认为,现代主义小说的隐喻和转喻互相渗透,在保护转喻特征的同时,也在写作中加入了一些隐喻联想,具体表现为重复的使用一类语法、语言的词汇让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词汇相似性上。而这种语言在重复的潜意识里,把读者的注意力带入到转喻表层的象征。在《伊芙琳》中,将语言重复带有节奏表达出本身专喻式突出的效果,艺术性的展现出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与矛盾。小说中都柏林的社会瘫痪主要是通过伊芙琳的压抑沉重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来表现的,主人公的挣扎矛盾心理影射出都柏林人民当时身心麻痹,对于新生活迷茫畏惧的写照。通过环境来侧面烘托出人物的情绪,彰显出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着力于渲染出一种沉闷的黑暗,这种黑暗如一张看不见的网,无处不在的控制压抑住都柏林人民的一切。伊芙琳每天都要打扫一次卫生,可灰尘无处不在,象征着一种沉闷缺乏生机,也是都柏林人群在多年不变社会下的一种精神麻痹状态。一个人的心灵若是蒙上了灰尘,则会失去对于未来的憧憬和活力,一个社会若是笼罩上灰尘,便会停滞。当时的爱尔兰已经处于一种长期不变的瘫痪状态,这种状态用于对抗战争无疑是一种飞蛾扑火、薄弱的抗争,最终会以失败告终。而海洋、私奔等词汇均是对新生活、新思想的追求和探索,预示了新生的意义。到了故事的最后,作者描述了逃离的船只被波涛汹涌的海洋阻隔,这也暗示了在新生活的跨越上的一道阻碍。汹涌的海浪、栅栏均是困住伊芙琳去向新生的监狱,主人公最终无法摆脱瘫痪的旧环境,在命运的选择上徘徊,从瘫痪麻痹到觉悟,觉悟到抗争,但最终又以失败告终,象征人民抗争又回到原地,在抗争中的迷茫,也更深次地体现出了难以改变的社会境况。
(二)《伊芙琳》的社会语境
全文都是用第三人称来描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通过大量的心理描述、倒叙、环境描述和独白等给读者带来一个保守生活中痛苦挣扎的软弱女性形态。在殖民的统治下,在共和党人与民族主义者长期抗争的复杂环境下的乔伊斯,看出爱尔兰社会是一个有残暴的殖民文化和无法计量的差异伦理、文化等联合的整体。乔伊斯认为,如果仅仅借助传统来看待伦理和宗教文化等是无法找出问题所在的,女主人公的角色象征是他为了批判爱尔兰社会的卑劣、腐朽等行为而创作。他在这种社会背景滋养下,最多的主旨便是反映文化侵略。在19世纪末的传统社会,他突出了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大海不仅象征了跨越新生的阻隔,也象征了未来新生的洗礼。但是伊芙琳最终放弃了登船跨海,也是因为受到了长时间的精神压制,产生一种负罪感。海水不仅代表了希望和未来,同时也会伴随未知的风险,即是新生和死亡的分界线。面对这样一种灵魂的洗涤,只能通过摆脱现状来重新定位自我。但是主人公并没有将新生的路程当做未来的一环,因此在选择上犹豫不决。将反讽和批判表现在《伊芙琳》中,反映出了爱尔兰人民对自身的认知矛盾、恐惧和盲目、止步不前,暗示了作者反对把爱尔兰的民族英国化。将社会的现实通过伊芙琳的困境呈现给爱尔兰群众,让群众重视审视社会困境。通过女性的特殊角色在社会历史语境的格局,侧面揭示了英国对于爱尔兰殖民的霸权以及压迫。从日常的家庭矛盾和纠纷内涵了背后的宗教文化、政治、伦理经济等问题,表达出了作者对于殖民意识的强烈反抗和批判。
三、结语
综上所述,“瘫痪”一词贯彻了《伊芙琳》整个主旨,在文中它表现了主人公的行为以及感情上的麻痹。以伊芙琳作为基点,通过非人物目标、目标缺失、静态动词、环境成分等体现了伊芙琳犹豫矛盾、缺乏自我的性格,以伊芙琳的感觉和心理过程表达伊芙琳在窒息生活中缺少自我和精神瘫痪,惧怕未来的生活,作者从各个层面上展示主人公的被动软弱、麻痹无助,并将矛盾深化到整个爱尔兰社会,升华了瘫痪的主旨。主人公的逃离只是她在埋葬自我时的无力挣扎和呐喊,她的悲剧和生命归宿不仅仅是个人的状态,更是整个爱尔兰人民的命运,只有将这种状态真实深刻地进行批判,才能够唤醒整个爱尔兰人民的觉醒,从而使其勇于挣脱精神麻痹的囚笼,反抗压迫与剥削,进行自我的救赎。
——谈《都柏林人》子集《姐妹们》标题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