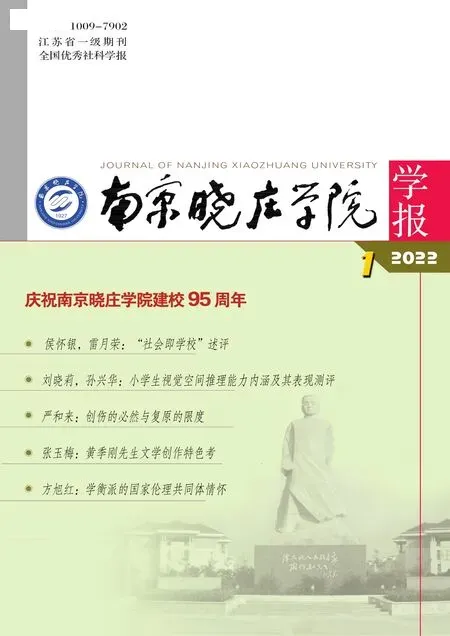学衡派的国家伦理共同体情怀
方旭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伦理道德是以共同体形式存在的人类独有的原则规范和精神价值,人类的共同体以及人类参与其中的共同体已经不是自然形式的共同体,而是经历了人类历史实践活动不断建构的具有伦理属性的共同体。没有共同体就没有人类的存在,没有伦理共同体就没有文明人类的存在。而伦理共同体的存在则以具有情感自觉和理性自觉之个体为基础,伦理道德就是个体与共同体及其公共本质的统一。共同体可以在伦理的层面分为不同的形态,黑格尔曾经将伦理实体(伦理共同体及其公共本质)分为家庭、社会、国家三个形态,并认为国家是最高的伦理共同体。但今天看来,特别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之后,黑格尔关于伦理共同体形态的思想需要拓展。但在国家还没有消亡的历史阶段,我们仍然需要维护国家伦理共同体,并以一个更加理想的国家共同体参与到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才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和现实需要的。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无论是从其现实形态还是从其文化精神来说,都出现了问题和危机,如何保证国家共同体的存续,如何建构国家共同体的认知,建构何种民族国家精神,是当时国家的迫切历史任务。包括学衡派在内的不同学派以不同的视角和方式追求着同一个核心目标,即国家的独立自主。学衡派作为当时提倡“中庸”式理性思想启蒙的思想流派,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民族精神谱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形成和维系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有非常重要历史作用,并将继续发挥深远影响。其国家伦理共同体情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阶段的今天则更显其理性价值,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
一、 历史文化认同:维系国家伦理共同体的历史情怀
民族国家既是历史的存在,也是现实的存在,是历史存在和现实存在的统一。民族国家是客观存在,也是文化存在,是客观存在与文化存在的统一。民族国家是包括所有国民个体的政治和伦理共同体,是个体和共同体的统一。国家的历史形态和现实的客观存在形式,是国家的外在主体,而历史文化和时代精神则是民族国家的精神主体。在近代遭受列强侵略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客观形态存在的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险,民族国家的传统精神在应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也显得过于僵化陈腐而无能为力。不但无能为力,反而是民族国家救亡图存历史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和精神枷锁。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而勇于探索的志士仁人一路披荆斩棘,流血牺牲,最终深入到了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关系的深层地带,探究国家出路。辛亥革命失败,帝制复辟,促使资产阶级为了救亡图存,不得不大力批判传统文化,乃至于出现了一些极端否定历史文化的思想和言论。部分新文化派学者极端批判传统文化,否定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自强独立之间的关系,乃至将二者对立起来。从动机上说,也是出于爱国,从客观效果上说,发挥了极大的开启民智,挽救国家危亡的历史作用。但从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长远发展来说,当时极端否定历史文化的现象,存在潜移默化地消解民族国家伦理共同体认同和延续的危险。学衡派当时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针锋相对地对新文化派极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割裂民族精神与国家复兴之间关系的观点进行了尖锐批判。
学衡派国家伦理共同体情怀首先体现在其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辩证认同上。这种认同体现的是一种对国家共同体文化深处的爱国主义伦理精神,强调历史文化是民族国家共同体不能分割的精神实体。学衡派始终都在强调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对国家伦理共同体的重要意义,认为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是公民对国家伦理共同体产生自豪感、责任感、使命感和归宿感的源泉,而自豪感、责任感、使命感、归宿感都体现了个体与国家共同体统一的伦理精神。这种理性认知基础上对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共同体之间辩证关系的强调是对新文化派思想启蒙的辩证,在当时以新文化运动为主导的先进留学生群体中,是非常难得的。吴宓认为,“文化为全国人民精神上之所结合”(1)吴宓:《我之人生观》,《学衡》1923年第16期。,这也可以理解为吴宓认为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可须臾离的精神实体,因此现实的国家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张其昀把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精神和国家存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清晰而深刻的阐述:“我国之所以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其道在中……历圣相传,无不兢兢焉以中道相戒勉。孔子集古代思想之大成,足为我民族意识之代表。……二千年来,孔子之教虽能未尽行于中国,而持中、调和、容让、平衡诸观念,固已莳其种于后代国民之心识中,积久而成为民族精神。我民族所以能继继绳绳,葆世滋大,与天长地久,赖由此也。源长难竭,根深则难朽,岂不信哉?”既指出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是具有典型人文主义特征的“中庸”之道,更明确肯定了“中庸”精神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之精神纽带作用,进而强调“中庸”之道是国家立足和发展的根基和源头。此文化之根必须要深植,此文化之源必须要远疏,国家之发展才能有根有源,既是文化根源,也就是须臾不可离的精神实体。诚然,学衡派也认为“吾国近世之腐败,中外有识之士所共见,诚不可不求其原因,而思所以改革之者。”(2)张其昀:《中国与中道》,《学衡》1925年第41期。然而,不可认为中国近世之落后全由传统文化负责,而不假区分地要彻底否定。特别是孔子思想之真精神,所谓“持中、调和、容让、平衡诸观念”,为滋养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从人类高度自觉和高度文明和谐的理想角度而言,自有其价值真理蕴含其中,也是合乎人文主义的典型代表,对此应该要有精深的研究和基本的自信。学衡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也深深地受到了白壁德的影响和鼓舞,白壁德的人文主义主张世界文化平等对话,互学互鉴,“白壁德先生立论,常从世界古今全体着眼,本不屑计一国一时之得失,然亦足以为吾国人指示途径。若更细究西史,则知吾国古圣贤所言国家盛衰之理,治乱得失之故,实已见之于西洋,得征而益信。”(3)吴宓译:《白壁德论欧亚两洲之文化》,《学衡》1925年第38期。白壁德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救亡图存关系的看法,更加坚定了学衡派对民族文化精华之于民族国家独立富强价值的自信。
学衡派对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情怀既表现为对历史文化的热爱,更表现为对传承和发展民族历史文化的神圣使命。新文化派主张要爱国救亡,就必须批判传统文化,只要能让中国强大起来,即使全盘西化也在所不惜。学衡派则认为,传统文化确实有阻碍民族国家进步的糟粕,国家的现代化当然需要批判传统,但传统文化的真精神需要继承和发展,而且这种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使命感是爱国救亡不或缺的,是民族精神人格和国家主体性确证不可或缺的。柳诒徵就指出:“吾国之人,苟不自勉于传播中国之文化,则彼我文化之交换,终不易相得益彰。吾闻美国某大学欲设中国学术之讲座,无所得师,不得已而请一日本人承其乏。呜呼,是实吾民之大耻,抑亦吾国学者之大耻也。”(4)柳诒徵:《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学衡》1924年第27期。在学衡派看来,国家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不可不体现于文化的层面,因此在民族国家间的文化交往中,要有基本的文化平等和自信,文化的交流要追求相得益彰的效果。因此,不能传承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被看作是国家和人民的耻辱,其中的爱国强国之情溢于言表。这种热爱自己国家历史文化所传递的国家伦理共同体情怀,在陈寅恪眼中的王国维身上近乎以一种文化宗教式的方式表达了出来。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自杀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爱和使命感,这种爱不是简单的兴趣或喜好,而是一种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恰恰是民族历史文化培养出来的,即“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种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自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5)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学衡》1928年第24期。“心安而义尽”把民族文化与个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一语道尽,民族文化建构的价值体系是其所教化之国民的精神性实体,是个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应该成为一个国家公民内心中的信仰,作为一种文化信仰,表达的是深层次的爱国情感,应该是对历史文化的认同、情感和实践意志的统一。出于历史文化,也出于情感和现实理性的考量,学衡派的爱国精神在文化发展的层面也总是坚守着中国自古相传的“中庸”之道。正如郑师渠评价的,学衡派“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在于人伦道德,尤其是理想人格,它是中国人民战胜外敌、复兴民族最重要的精神支柱的观点;强调吸取历史经验,一方面要积极输入外来文化,一方面要不忘本民族的地位,致力于建立民族的独立文化的观点……如此等等,均属创见,在今天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6)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学衡派坚持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追求文化平等,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7)《学衡》宗旨,《学衡》1922年第1期。的宗旨践行着自己对民族国家伦理共同体的义务和使命,既是他们对中国传统精神的传承和发展,也是我们今天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追求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
二、 政治伦理启蒙:维系国家伦理共同体的现实使命
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热爱不仅仅是对国家及其传统文化的历史情怀,更是对国家现实任务和使命的勇敢担当。经过近代以来的一次次救亡图存的尝试和失败,特别是民主共和革命失败后,学衡派和新文化派对于只有通过思想文化的启蒙才能实现国家救亡图存之目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各自的启蒙思想,无不体现着一个国家公民对自己国家共同体的伦理责任。无论是像新文化派那样恨铁不成钢的尖锐批判乃至否定式启蒙,还是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中庸”式启蒙,实际上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共同体的存在和延续而勇敢承担公民于国家共同体之伦理责任的体现。这一现实而又紧迫的伦理责任在当时聚焦于对国民进行政治伦理的启蒙上,成为学衡派和新文化派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陈独秀认为民主政治必须通过伦理觉悟才能实现,学衡派也认为伦理道德是民主政治的核心精神,他们在国家政体及其精神内涵方面的启蒙,是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特征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辩证表达。
学衡派主张国家共同体应该以民主的形式存在。他们赞同民主政治之启蒙,反对专制制度,强调“民治”思想觉悟的重要性。新文化派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人民不知道国家是属于自己的公产,君主不知道人民是主人而自己是公仆,不知国家为何物,何谈救亡图存。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的时候指出,中国的国民脑海里实在是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所以共和在中国连块招牌也挂不住,故而必须要进行政治伦理的启蒙(8)陈独秀:《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青年杂志》1916年1卷6号。。学衡派对此也是高度肯定的,刘伯明就指出:“吾国政治,自古以来,崇尚专制……生息于斯制之下者,乏直接参与政事之机会,即有此机会者,亦限于极少数之人。”(9)刘伯明:《共和国之精神》,《学衡》1922年第10期。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显然不能很好地解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本质,不能合理处理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因此,要想救亡图存,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统治者,都应该要进行民主思想的启蒙。在民族国家性质及其存在形式上的启蒙,学衡派与新文化派都主张国家伦理共同体的普遍性和公共本质应该平等属于每个公民个体,而这种普遍性和公共本质的合理表现形式就是民主政体。胡先骕就指出:“民治主义,国之正轨,而无治共产主义,尤为政治理想上之极则也。”(10)胡先骕:《论批评家之责任》,《学衡》1923年第3期。不但要追求民主政治,还肯定了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共同体最为理想的形式。因此,对当时的帝制复辟,学衡派同样坚决反对,并且和新文化派一样认为民主制度要想在中国确立,必须要使“民治”观念深入人心。胡先骕认为,“今日共和既立,复辟帝制,自非吾人所欲。因之吾人之责任,务必以全力,使民治主义遍布于一般无识之平民,使其‘意见和思想咸趋于该途’,则共和之基础方能稳固。”(11)胡先骕:《论批评家之责任》,《学衡》1923年第3期。这番论述跟陈独秀等关于民主政体与国民民主思想的观点如出一辙,并认为对国民进行民主思想的启蒙是学衡诸人的责任和使命,也是促进国家伦理共同体现代转型进而救亡图存的政治和伦理责任。
学衡派的民主政治启蒙强调个人与国家伦理共同体统一的“中庸”本质。学衡派认为,民主既要体现国家赋予人民以权利,同时强调个人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义务,是权利义务的统一,民主制度应该体现这一“中庸”精神。专制时代没有做到二者的统一,现代社会如果过于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同样可能做不到二者的统一。所以,与新文化派侧重强调个人对国家的权利不同,学衡派则针对新文化派的主张强调个人对国家的义务,反对极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主张民主制度的真精神应该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刘伯明指出:“自由必与负责任和,而后有真正之民治。仅有自由,谓之放肆,任意任情而行,无中心以相维系,则分崩离析,而群体迸裂;仅负责任,而无自由,谓之屈服,此君国民之训练,非民治也。”(12)刘伯明:《共和国之精神》,《学衡》1922年第10期。过度强调公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有可能导致国家共同体的解体,但如果仅仅强调个人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责任和义务,则有可能导致屈服和专制,必须二者平衡才是真民主。吴宓发展了中国传统“忠恕”观念来强调民主权利和义务之间的统一关系,他指出:“吾国国民徒言权利,而不讲义务,故政局分崩,民生疾苦”,故要提倡“忠恕”之道,权利义务要辩证统一,“故忠恕之一端,既足察人品之高下,亦能定国家之祸福也。”(13)吴宓:《我之人生观》,《学衡》1923年第16期。而缪风林则从古希腊“中道”观念和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来阐释二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希腊人守中节,而近人趋多极端,如经济上资本劳动之争,美术上自然唯美主义之说,毫无中节遗义。……以言国与民,则有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国民遂不得谐和。”(14)缪凤林:《希腊之精神》,《学衡》1922年第8期。由此可见,学衡派试图在所有层面都追求中庸和谐,认为爱国之启蒙不仅仅是要让人民懂得自己在国家共同体中的政治主体性和伦理主体性,同时也要强调个人主体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之责任。这种统一就是刘伯明所说的共和精神,他认为:“盖共和之精神非他,即自动的对于政治及社会负责任之谓也。”(15)刘伯明:《共和国之精神》,《学衡》1922年第10期。这种自动的负责任就是个人主体性的体现,既是对自我权利的深刻自觉,更是公民对社会、国家之责任的高度自觉。所以,学衡派认为,民主作为现代性国家政体,深层次上体现的是个人与国家伦理共同体的统一,是理想的公民和理想的社会的统一。学衡派对国家民主制度的阐释,仍然以人文主义为目标,比如缪凤林指出:“《理想国》中谓‘吾人国中,应有一种智慧,不偏重一事情,而念念顾及国之全体,使人因是能维持国内之平安与国际之和平’,‘有此智慧者,惟治国之哲人’,‘国家苟有此智慧,则为文化国家。’其意审矣。”(16)缪凤林:《希腊之精神》,《学衡》1922年第8期。学衡派强调民主共和就是“中庸”精神在爱国层面的体现,最好的政治体制就是个人与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个人自由是国家共同体的责任,维护国家共同体的整体性和共同性,维护其他公民的自由也是个人的政治义务,更是伦理义务,国家共同体及其公共本质本身就是个人的家园和目的。
三、 人文主义精神:国家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体统一的道德理想
学衡派阐发其文化救国思想,特别强调人文主义的伦理精神在爱国层面的体现,在西方现代爱国精神的启发下,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家国天下的道德理想。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思想不局限于当时危急存亡之现实的应对,既有对民族国家历史的肯定和继承,又展望中华民族未来千年之和谐与昌盛。既要在无尽的历史长河中思考民族国家繁荣昌盛的根基,又不抱狭隘民族主义,在人类世界共同体中看待中国的存在与发展。无论是从纵向的历史长河中,还是在横向的人类世界共同体中,学衡派都认定爱国必须归宿人文主义,而对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特别是对民族精神的道德核心即仁爱理想追求,是爱国主义和天下主义的最高境界。在国家硬实力和文化自信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学衡派思想之人文精神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依然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学衡派肯定和继承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并认为爱国的最高表达就是“家国天下”的人文主义情怀。无论是爱国还是治国,核心都会落在伦理道德的普遍实现上,最终国家得治,天下太平和谐,便是道的实现。而儒家所讲的道,在白壁德和学衡派看来非常合乎他们所讲的人文主义,即“以理制欲”,“归本于中道”。治国的最理想方式是“为政以德”,强调德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高于功利和知识,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典型体现。而“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国家的治理方式必须践行大道,国家的治理目标必须是为了实现大道,即大道行于天下也必须通过国家伦理共同体的和谐有序才能得以实现,而爱国治国之大道最高之精神即为“中庸之道”。张其昀说:“我先民观察宇宙,积累经验,深觉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并且认为“中道”精神就是历史经验实证的人文主义,是做人之本,立国之基。“昔者子产铸刑书,孔子伤之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此虽孔子私言,实足以代表中国古代政治家之气概。古人所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也。呜呼,‘中庸之德也,其至矣乎’!我中国之民族精神,其在斯乎,其在斯乎!”(17)张其昀:《中国与中道》,《学衡》1925年第41期。张其昀认为中国传统,国家治理崇尚德,国与国之交往,不尚力而尚德,不在国与国之利益欲望,而在是否合乎人文的理性精神,德政仁政背后所体现的就是爱国爱民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虽经历史更迭而无所断绝和动摇,“君子依乎中庸而行,虽朝代屡更,而社会之潜势力,仍然固定而无可动摇。”(18)张其昀:《中国与中道》,《学衡》1925年第41期。这一点不仅仅在学衡派自己身上得到了验证,而且在学衡派批判的新文化派身上也是如此。学衡派认为,虽然新文化派尖锐乃至极端批判传统文化,但他们思想启蒙之目的和努力所展现的,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培植的深厚爱国主义精神。柳诒徵就明确指出:“某某者,反对孔子之教最坚最力者也,然其所持之爱国主义,曰勤、曰俭、曰廉、曰洁、曰诚、曰信,固无不出于孔子之教也。”(19)刘诣徵:《论中国近世之病源》,《学衡》1922年第3期。虽然在学衡派看来,新文化派是科学的人道主义和情感的人道主义的倡导者,但就其爱国精神方面的深层次特征而言,亦合乎传统之人文精神。学衡派和新文化实际上以不同的视角和方式传承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爱国主义精神。
学衡派认为爱国是公民对国家的伦理义务,是个体与共同体的统一、特殊和普遍的统一。国家作为共同体所具有的整体性、普遍性和实体性是人文之理的根源与本质所在,爱国主义精神归根结底是人对自己的伦理义务,是个人价值拓展和提升的必然内容,这也体现了人文精神的核心要求。在新文化派大力倡导公民之于国家的权利的政治伦理启蒙之际,学衡派则着力强调公民对国家伦理共同体的义务。这种义务要求就是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前面曾提到吴宓认为传统中国的国民只知道讲权利,而不知道讲义务,致使政局分崩,民生疾苦,裁兵理财,徒资虚说,教育实业也未收大效,而且江河日下。所以必须要强调公民对国家的义务,这种义务在传统帝国是忠,在现代社会就是爱国。传统的忠君爱国虽然有浓厚的专制色彩,但其与现代的爱国之间依然是相通的,深层次的精神结构是一致的,故“忠恕之一端,既足察人品之高下,亦能定国家之祸福”(20)吴宓:《我之人生观》,《学衡》1923年第16期。。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和精神提升逻辑,“立己”和“达人”在国家伦理共同体中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其核心的精神本身并不因为专制的内容而被完全淹没,恰恰和西方的民主之真精神有殊途同归之处。缪凤林认为:“希人之意,最善之个人,即属最良之公民,个人之目的与国家之目的同也。亚里士多德有言:‘国家者,相同之人求达其所能达之最善生活之结合也。’此语之意,不仅仅国家为个人之达其理想之工具,公共生活之自体既属理想。易言之,国家之自全,即个人之目的而已。个人欤?国家欤?一而二,二而一者也。”(21)缪凤林:《希腊之精神》,《学衡》1922年第8期。国家和个人是互为目的的,这本身就是以伦理共同体形态存在的人类必然会有的文化和精神特质,是个体与实体相统一现实要求。国家共同体既可以保护个人的生存和满足个人的需要,国家共同体中的公共生活及其价值原则,也是个人人生目的和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人价值自我拓展的必然环节。因此,爱国并不是对一个外在于自己的国家的外在义务,而是公民对自己身心家园的内在义务,是对道的义务,归根结底是人对自己生命价值的伦理义务。所以,梅光迪说:“以挽垂危之民族,以振已丧之民族精神,此乃神圣之职务,凡属含生之伦,皆当百死不辞者也”。(22)梅光迪:《近代大一统思想之演变》,载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9页。正因为学衡派认为爱国是神圣的职责,学衡诸人多有表达自己坚定的爱国之心。比如吾芳吉说:“中国若亡,吾断不肯远遁,必攘臂而起,赴边杀敌,以了此生。”(23)吴芳吉:《与吴雨僧》,《吴芳吉全集》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65页。吴芳吉还记录了吴宓类似的爱国誓言,表达彼此之间欣赏和互勉。学衡派默默从事的文化思想工作,本身就包含着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对国家伦理共同体的归依,也是对国家伦理共同体所蕴含的精神实体的皈依。
学衡派强调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统一,认为合理的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世界主义则是对人的理性价值和崇高情感的再拓展和再提升,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不符合人文主义的精神。梅光迪认为:“民族主义在适当的范围中,为现代国家独立自存之唯一条件,人人当爱惜珍宝之,发扬光大之”,但他批判极端浪漫主义主导的民族主义,国家层面的极端浪漫主义类似于个人层面的极端浪漫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只知道争自己的存在和利益,甚至国家层面的任情纵欲,是不合乎人文精神的,比如帝国主义。梅光迪认为,“帝国主义,即极端的民族主义,而法西斯主义,又为极端的帝国主义。”(24)梅光迪:《近代大一统思想之演变》,载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9页。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对殖民地的侵略和奴役,显然违背了人文主义“以理制欲”的核心精神,只有利益和欲望,没有公理存在。学衡派期待的是人文主义精神指引下平等的文化对话和交流融合,以期形成一种世界性的人文主义,用人文精神将世界联系成一个文明的、公理主导的共同体。白壁德非常期待东西方文化交流基础上的人文主义世界共同体,“十九世纪之大可悲者,即其未能造成一最完美之国际主义。科学固可谓为国际的,然误用于国势之扩张,近人道主义、博爱主义,亦终为梦幻。然则何苦告成一人文的,君子的国际主义乎!初不必假宗教之尊严,但求以中和礼让之道,联世界为一体。”(25)胡先骕译:《白壁德中西人文教育谈》,《学衡》1922年第3期。所以,白壁德人文主义的世界共同体仍然建立在其对近世人道主义的批判基础上,是一种道德理想。学衡派则很自然地将其与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庸”之道联系在一起,吴宓指出:“爱护先圣先贤所创立之精神教化,有与共生死之决心。如是则不惟保国,且可进而谋救世。”(26)吴宓译:《白壁德论欧亚两洲文化》,《学衡》1925年第38期。学衡派的世界主义情怀,大致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中国近代以来遭遇西方列强侵略之现实基础上对世界和平的渴望,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世界和平的世界性反思的一部分,而一战也是学衡派人文主义批判浪漫主义和科学主义时经常使用的典型反面实证依据;其次是中国传统“天下”观念的传承和发展,在近代以来国家出路的探索中,从太平天国运动,到康有为主张的君主立宪、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再到新文化派、学衡派,始终试图追求理想的“天下”秩序,背后的传统精神是不可忽视的;再者是白壁德世界人文主义情怀的融和发展,为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情怀提供了更宽阔的视角和理论基础。学衡派追求世界和谐的人文主义,可以说是对传统“天下”观念的发展,也可以看作是对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探索。
学衡派始终把国家当作是一个伦理的共同体,而非仅仅看作是一个政治的共同体。把国家看成是个人生命存在和生命意义无法分割的客观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的统一,并特别注重强调其精神共同体的终极重要性,这是学衡派相较于新文化派更深刻的地方,也是能对今天提重要供借鉴意义之所在。如果说新文化派强调个人独立、自由和权利的政治伦理启蒙是国家民主制度最基本的内涵,是彼时中国民主政治急需的时代精神,是国民走向独立和觉醒必备的素质要求,更符合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的历史大势和规律。那么,学衡派的国家伦理共同体情怀强调国家共同体的存在秩序和价值原则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实现,是个人生命和价值体验拓展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和形态,则既是在完善对民主的诠释,更是超越民主政治制度,在更普遍、更高的角度,在绝对目的层面进行的千年忧思,是对民主制度中的个人更高精神需要的关怀,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当下社会发展中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泛滥导致崇高价值的祛魅,共同体意识淡化,共同价值体验缺失,是人们常常出现孤独感和虚无感的深层次原因,也是分离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现实危险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现实的问题也正是学衡派当初对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忧虑之所在,其所追求的家国天下的人文情怀,也是我们今天在仍不断努力丰富和发展,以应对这些现实问题和困境的价值体系的核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