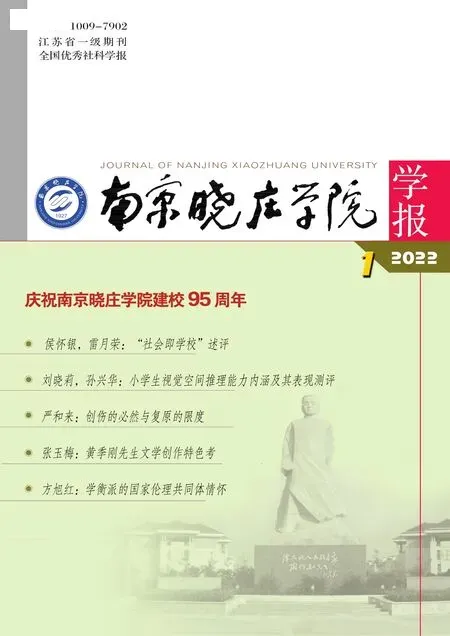世界:先验现象学、身体现象学到精神分析的理论进路
张 磊
(南京晓庄学院 幼儿师范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一、 引言
先验现象学是一门研究事物本质的哲学,然而先验现象学为了摆脱其隐含的观念论倾向,逐渐表现出一种通过身体现象学走向精神分析的理论可能性。现象学家胡塞尔“一直否定传统的知识再现论,即洛克的观念论,它根据一种内在的心灵再现或心外存在物的翻版来说明知识”(1)Moran, D:《现象学:一部历史的和批评的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他所创立的先验现象学主张悬搁一切预设的知识观念,并将一切意义都还原到主体性之内。这使胡塞尔在悬搁已有观念体系的同时,又将现象学变成了一种蕴含着自我与世界分离的研究“自我经验”的哲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胡塞尔的现象学仍然是笛卡尔发现我思之继续(2)Moran, D:《现象学:一部历史的和批评的导论》,第191页。,而其基于“自我经验”建立起来的先验自我也具有笛卡尔二元论中“我思”的观念特征。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是继胡塞尔之后的第二代现象学家,他为了克服先验现象学中的观念残留,强调“我思”中思的身体主体性,认为我所是的主体性与这个身体和世界不可分离(3)徐晟:《我思:主体及其处境——从笛卡尔到梅洛-庞蒂》,《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第131-137页。。为此,他以身体作为图式提出“沉默的我思”(tacit cogito),指出观念的背后应是具体的身体活动。然而,梅洛-庞蒂本人也意识到身体图式仍然具有观念的残余,终究没有逃过他所质疑的意识构建。不过,他以此为起点提出了更具本体论意义的肉身(the flesh)概念,并通过它将现象学的研究引入世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身体现象学。在肉身中,形与质、观念与身体不再是严格区分的两个部分,而是交织的不同侧面。可以发现,梅洛-庞蒂所说的肉身是个具有无限深度的概念,它是世界的交织,是朝向自然的一种可逆的、普遍的欲望。他希望凭借这种交织的欲望将肉身引向精神分析,并将精神分析上升为世界的精神分析,将其看作是世界的表达。在其后期著作中,梅洛-庞蒂一直尝试通过身体现象学的概念重新理解这种世界的精神分析。在他看来,作为心理动力的性欲与心理地形的意识、潜意识等概念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描绘世界并在与世界的交织中被自然所改造。因而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一书中,他甚至认为潜意识必须在肉身的基础上才能够被认识。
为了详细勾勒出先验现象学向精神分析的这种世界转向,本文将首先简述先验现象学的观念论缺陷,借此厘清作为身体现象学出现起点的“沉默的我思”;其次,阐述“沉默的我思”到肉身的转向,并通过肉身的可逆性与普遍性将身体现象学引入世界;最后,以身体现象学概念为基础,尝试继续梅洛-庞蒂的理论构想,重新理解古典精神分析中的核心概念。
二、 先验现象学:世界的入口
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一种先验现象学,它提倡悬搁一切已有的哲学与科学观念,通过对事物的直观把握发掘其本质。这是一种现象学还原,它有助于摆脱已有的观念束缚,但同时也隐含了观念构成的逻辑。因为胡塞尔所用的现象学还原直接通向先验的自我领域,它将一切意义置于先验的构成性自我之中,而这一过程正是笛卡尔发现“我思”之继续。因此,尽管先验现象学并未汲取笛卡尔思想中任何独断论的哲学内容(4)Moran, D:《现象学:一部历史的和批评的导论》,第159页。,但是胡塞尔的理论中仍然隐含着意识主体与世界的划分,存在着主体建构他人与世界的观念论倾向。
早期的梅洛-庞蒂在继承胡塞尔先验现象学思想的同时,也致力于消除其中的唯心主义倾向,却同样不慎落入了观念逻辑的陷阱之中。他强调自我与世界的不可分离性,认为世界只能被描述而不能被观念所构建。为此,他提出了“沉默的我思”以反对笛卡尔理论中“我思”的自明性所带有的观念逻辑。“沉默的我思”是一种先于任何哲学的、自身对于自身的呈现(5)徐晟:《我思:主体及其处境——从笛卡尔到梅洛-庞蒂》,第131-137页。。笛卡尔最早提出“我思故我在”,认为无可置疑的“我思”便是我存在的最好证明。梅洛-庞蒂并不同意这种主张,他认为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是一种“我思”的观念,而忽视了这种观念必须以“我思”的活动为基础。既然“我思”的基础是“我思”的活动,那么它一定是历史的、具体的,因为“我思活动并不是与事件和时间无关,确切地说,我思活动就是事件和历史的基本模式”(6)Merleau-Ponty, M.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Routledge. 2002, p.235.。因而,梅洛-庞蒂用寓于身体的“沉默的我思”来指代这种具体的“我思”的活动,认为它是“我思”背后“我思”活动的原始面貌。在他看来,“沉默的我思”就是以身体为载体,所有的意义都必须通过身体的感觉而获得,也就是说,意义在被领会之前已经作为活生生的前反思而存在(7)Watts, J. 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Unconscious.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in South Africa.2011,19(1), pp.24-45.。可惜的是,“沉默的我思”也必须在语言的历史中不断被把握,它最终成为了另一种基于身体的构成性意识。这样一来,梅洛-庞蒂在使用“沉默的我思”替代“我思”的同时,也沿用“自身意识的神话”,沿用了胡塞尔将观念作为前提的逻辑思维,故而也就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抛弃身心二元论,契合现象学的本质。
先验现象学是身体现象学的前导,是现象学走向世界的入口。虽然梅洛-庞蒂的“沉默的我思”也没有完全摆脱胡塞尔甚至笛卡尔的意识哲学的基本倾向(8)杨大春:《从身体现象学到泛身体哲学》,《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7期,第24-30页。,但他对身体的重视,对世界与个体的不可分性的强调,使其通过“沉默的我思”将“我思”变为身体之思,将身体与世界统一在同一场域之中,为身体现象学的出现以及现象学延伸入世界打开了一扇门。
三、 身体现象学:世界的延伸
为了彻底打破“自身意识的神话”,打破观念的基础性,梅洛-庞蒂提出了“肉身”的概念,并使先验现象学走入身体现象学。他所说的肉身无法在传统的哲学概念中找到,因为它“既不是精神,也不是实体,它是相当于水、火等的元素,但又不同于这些元素”(9)Merleau-Ponty, M.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8,p. 139.;它更多的是一种世界的存在原则,这种原则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开放的,并为所有可能性提供了开口。事实上,肉身正是通过这种开放性将身体纳入世界的维度,并获得本体论的意义。这样,主体与世界都从肉身中获得了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与世界、身体与世界都在肉身的背景之下相互开放、相互展开、相互交织,从而消除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成为了一种共同发展的存在。于是,寄于主体的“我思”不再作为世界的前提,而是世界存在本身,它成了贴合在存在之中的平行之物,并与身体分别成为肉身中相交织的不同维度;不再是主体对世界的意识把握,而是主体身体与世界的互动体验,是主体与世界的欲望交织;它在包含主体的世界的交织中不断生发与绽出。如此,世界通过感性的面貌牵引着个体,个体则通过欲望的体验朝向世界。这样的两种漩涡、两种本质,便在肉身之中同心汇聚。这一背景下的身体已经超越了纯粹物性的身体,成为一种现象的身体、一种世界的延伸。因而,有人将肉身描绘成是“历史和自然的联结”(10)Weiss, A. S. Merleau-Ponty’s Concept of the “Flesh” as Libido Theory. SubStance.1981,10(1),pp. 85-95.,也可以说,肉身是在世界中存在并不断超越世界。可以看到,梅洛-庞蒂所说的肉身成为了世界的本质,它是交织可逆的,也是普遍开放的。而肉身正是通过这种交织与普遍将事物的两面相贴合,将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身体与世界统合在了一起。
交织与可逆是肉身维度,是梅洛-庞蒂通过肉身消除主体与客体、个人与世界的二元之分,使世界得以在身体中凸现的关键因素。简而言之,可逆性是指当主体在感受世界的同时,世界也在以同样的方式感受着他。梅洛-庞蒂认为所有的思都来源于看或触,是肉身的交织,而这种交织是可逆的。故而,不论是笛卡尔所说的“我思”还是梅洛-庞蒂提出的“沉默的我思”都必须“……以某种方式看或感,因为我们所知的思想发生在肉身之中”(11)Merleau-Ponty, M.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8.。而肉身盘绕在自然之上,它恰恰是在世界的交织之中显现。正如两面相对的镜子,每一面镜子都需要在另一面中体现,没有哪一面可以单独囊括它们的意义,最真实的意义在两面镜子的相互贴合与反射之中产生。准确地讲,在这种分享世界肉身的可逆性中,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世界交织在一起(12)Wang, J. Waves of Being: Merleau-Ponty with Bion and Meltzer toward an Ontology of Music.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2015,43(2), pp.210-221.。这样,与世界相交织的身体甚至世界之物都不再具有主体性,它们成为肉身的维度之一,成为被肉身所缠绕的通道。
肉身的交织与可逆使肉身的普遍性成为必然,也是肉身抵达世界的最终一步。世界首先是一个整体,然后才被我们的感觉所把握(13)Marshall, G. J. A Guide to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2008.。而与世界相交织的身体便通过可逆性与整个世界相互侵越,使其得以在感受世界的同时也被世界所感知,获得“我们普遍的身体”(generality of our body)。事实上,肉身的普遍性并不直接来源于世界的交织,而是交织的缝隙。它并不作为被其消弭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体而存在,而是这种视与被视、触与被触之间的构造原则。正如梅洛-庞蒂所指出的那般:“最好还是用‘元素’这个旧术语来意指它(肉身),这是它被人们用来谈论水、空气、土和火时的意义,也就是说用它的普遍事物的意义,即它处于时空、个体和观念之中途,是一种具体化的原则,这种原则在有存在成分的所有地方给出存在的样式。”(14)Merleau-Ponty, M.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p.139.
因此可以说,正是肉身的可逆性与普遍性,将其与自然纳入了同一运动的两个方面(15)Barbaras, R.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Merleau-Ponty’s Concept of the Flesh. Jor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ction).2008,19(5), pp.20-26.,通过它,世界得以被统合进同一的元素与构造之中。
四、 精神分析:世界的表达
由上文可以看出,梅洛-庞蒂引入肉身的概念不仅取消了思的主体性,也取消了身体的主体性,他通过肉身的粘合将身体拉进世界,也使“我思”归入了世界的沉默中。不难发现,失去观念基础的身体现象学已经无法出声,它只能通过身体与世界的欲望、体验等来描述世界,而这正是精神分析所做的。正如梅洛-庞蒂所说“Do a psychoanalysis of Nature: it is the flesh, the mother”(16)Merleau-Ponty, M.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p.267.。在这里,梅洛-庞蒂并没有说现象学,而是用了精神分析。从这一点来看,身体现象学在借用精神分析来描述世界。但是,鉴于精神分析自身的二元论倾向以及弗洛伊德本人在其理论观点上经常出现的前后矛盾,梅洛-庞蒂认为需要通过肉身对精神分析进行校正,以一种非弗洛伊德的方式回到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纳入到世界的话语体系之中(17)Merleau-Ponty, M. Themes from the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J. O’NEILL, Trans.). Eva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如此,身体现象学便通过精神分析获得了对世界的表达能力,而精神分析也通过身体现象学进入世界,获得了新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精神分析获得世界表达的结合点便是肉身与性欲,以及由此产生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意识与潜意识。
(一) 肉身:性欲的交织
性欲是肉身中交织的维度,可以直达世界的深度。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性欲大部分情况都是指狭义的性器的性欲,它在不同的阶段出现于不同的身体部位并推动心理的发展。与此同时,弗洛伊德也提出了一种广义的性欲,即作为身体不同区域欲望汇聚的性欲(18)Freud, S.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1938,SE 23,pp. 141-209.,它是一种朝向他人粘合的欲望。因而梅洛-庞蒂认为,性欲是一种投射与吸附的关系(19)王亚娟:《梅洛-庞蒂自然研究中的身体之思》,《世界哲学》2012年第3期,第67-76页。。这样,投射主体的身体和其所欲求目标的客体之间不再是一种截然的断裂,而是性欲粘合下由自身抵达自身的同一个世界。在它们这种侵越与转化的相互性关系中,交织的性欲天然地获得了肉身的可逆性与普遍性,成为世界背景下交织的脉络,笼罩着个体与世界。
交织的性欲直达世界的深度。事实上,与柏拉图认为欲望指向缺乏的想法相同,弗洛伊德也主张性欲是对需要的满足。在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中,性欲中投射与吸附的身体是感性的身体,因为“每一种知觉都是世界的震动……它唤醒了世界中所有存在的回响”。因而可以说,感性的身体通过感知觉不仅直接触摸、拥抱世界,同时也进入了世界的不可见之中。在这种与自然的交合过程中,性欲不再是对个人身体需要的满足,而是感知觉变得更加充满的过程,也是一种朝向世界的溢出(20)Mazis, G. A. Merleau-Ponty and the Face of the World: Silence, Ethics, Imagination, and Poetic Ontolog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6.。这样的性欲,必定是在世界之中生发而成的,必定推动个体朝向世界。如此,以性欲为动力性基础的精神分析不再是个人的精神分析,而是“一种思想体系,它讲述的是成为我们自然的一个元素……”(21)Merleau-Ponty, M. Phenomen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Preface to Hesnard’s L’Oeuvre de Freud (A. L. Fisher, Trans.). In H. Keith (Ed.),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Reprinted). 1993.,而性欲就是推动这个过程发展的中介因素。因此也可以说,精神分析被肉身深化为研究世界之性欲的理论,最终成为了一种交织的存在论(22)宁晓萌:《弗洛伊德哲学与梅洛-庞蒂的“肉身”概念》,《世界哲学》2016年第1期,第80-86页。。从这个角度理解,作为精神分析根基的潜意识与意识系统也将在世界系统之下重新建构。
(二)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意识与潜意识
如果说精神分析中的性欲是世界的脉络,那潜意识与意识便是世界的根和叶。既然性欲联结着世界的深度与表层,那么作为被压抑的性欲经验的潜意识便是不可见的世界之深度(23)Merleau-Ponty, M. Child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The Sorbonne Lectures 1949—1952 (T. Welsh, Tran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0.。因而,构成个人心理地形结构的意识与潜意识便通过性欲进入世界,成为其表里与深度。事实上,Romanyshyn曾直接将意识与潜意识类比为世界之中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24)Romanyshyn, R. D. Phenomen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Contributions of Merleau-Ponty. Psychoanalytic Review.1977,64(2),p.211.。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是身体现象学中的概念,它们是一种共存与绽出的关系,它们是肉身的两面,且可见的来源于不可见的。可见的指可被感之物,它是带有质地的质、深度之表层、实在存在之上的切面、被存在之波带走的粒子和微粒(25)Merleau-Ponty, M.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p.136.;不可见的则是指无法通过感知而得的另一个维度,它是肉身的深度,是观念的来源。世界的肉身之中,可见的既不是不可见的表层机构,也不是作为不可见的对立的存在,正相反,可见的因不可见的而成为可能并像光束一样可见。因此,将意识与潜意识看作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实际上是为它们确立一种新的深度与绽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意识与潜意识不再是双层的结构(26)Moya, P., & Larrain, M. E. Sexuality and Meaning in Freud and Merleau-Pont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2016,97(3), pp.737-757.,而是世界的一体两面:潜意识使得意识得以被意识,意识是潜意识的绽出与显现。如此一来,建立在最直接、具体、有确定性的感觉基础之上的意识(27)Freud, S. The Ego and the Id.1923,SE 19, pp.3-66.,不再是主体的创造,而是肉身的一次显现、是世界中涌动着的潜意识在当下的一次表达。
意识是自然之光,它从潜意识中蹦出就像可见的从不可见中生发一样,这得益于身体与世界的协作。我们知道,潜意识像不可见的一样在世界中流动,它是肉身的深度,是“意识的潜在性”。这样的潜意识存在于世界之中、存在于感与被感、视与被视的间隙之中,因而我们可以通过身体的感觉像眼睛汇聚光线一样把握住它,使其显现成为黑暗之中射出的自然之光。此时,起源于感官的意识因为受制于身体的独特性,也在不同的主体中表现出差异性。可以说,当感知觉被“点燃”时,人的特殊性就变得明晰起来,它的火焰在身体消灭之前是不会灭失的(28)Wang, J. Waves of Being: Merleau-Ponty with Bion and Meltzer toward an Ontology of Music. pp. 210-221.。这里,身体成为意识生发的间隙,是世界潜意识在个人身体中呈现的通道,因而主体身体的不同也决定了其中所包含的流动的个人潜意识以及展现的意识的不同。同时,作为历史的肉身的综合与绽出的意识注定是片面的(29)Brooke, R. Merleau-Ponty’s Conception of the Unconsciou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1986,16(4), pp.126-130.。例如,在面对花时,我的身体感受到了与花的所有交织,这感觉中的一部分通过身体器官的汇聚而成为显现的感觉、成为构成意识的感觉。而与此同时,身体像这朵花一样,也具有外部可见的与内部不可见的部分。因而,身体在与外部交织的过程中,自身也处于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交织与协同之中,这种内与外,表层与里层便是肉身的深度。如果说我与花的交织能够涌现出潜意识的话,那具有深度的身体自身的交织与协同则放弃了一部分无法综合的潜意识知觉,而使被感官所把握的那一部分潜意识跃迁出来成为意识。身体是独特的,不同的身体具有不同的深度。因而,潜意识在这些不同身体中所放弃与跃迁的原始感觉也并不相同,并因此展现出迥异的意识。正如Christopher Macann所说,意识的每一次进步与发展都是以对存在本质的原始感觉的损失为代价的,而这种原始感觉的损失正是意识独特性的根源(30)Macann, C. Consciousness, Self-Consciousness and the Unconscious. Existential Analysi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Existential Analysis.2015,26(2), pp.328-339.。
五、 总结
理论的发展史就是不同思想的碰撞史。隐含的观念逻辑使得先验现象学走向了身体现象学,而欲望的交织可逆又让身体现象学得以通过对精神分析的重新理解并表达世界,胡塞尔、梅洛-庞蒂与弗洛伊德三位思想家就以这样一种方式发生了碰撞。首先,梅洛-庞蒂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出发,以“沉默的我思”使思从观念回归到身体,继而通过身体发现了作为世界深度的肉身。这一过程中,他彻底地摒弃了胡塞尔现象学中残留的观念逻辑,将现象学的研究方向更直接地指向情感、体验与欲望等精神分析的主题,使现象学远离了西方传统的观念论哲学(31)Keller, K. D. Phenomen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Psychosis. Existential Analysis.2008,19(1), pp.17-32.,并获得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其次,梅洛-庞蒂的肉身概念与弗洛伊德的性欲概念不仅扮演着联结的角色,也在推动精神分析向世界的转变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肉身成为了世界的深度,它的交错与交织使得世界得以显现。梅洛-庞蒂在借用精神分析中的性欲来描述这种交织过程的同时,也使得精神分析的立足点转向世界成了可能。这不仅为精神分析解决自身的二元论矛盾提供了新的借鉴,也为其从个人走向群体、从精神病研究走向普通心理学指出了一种新的可能。
可以看到,我们希望在精神分析与身体现象学交汇中,发掘一种本体论的精神分析或现象学的精神分析。正如文中所述,身体现象学需要通过欲望来表达,而精神分析恰恰提供了一种欲望的观点。因而,如何在经验中重新理解欲望,便是一种本体论的精神分析。在这样一种本体论的精神分析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从本体论角度思考如何用本质直观考察病症的诸多维度;心理的原初状态如何从世界中产生;以及如何在世界背景下重新组织这些经验与欲望。这样,不仅是精神分析,所有的心理学都可以借此回到对经验——不是纯粹的经验,而是杂多的、不断生成着的欲望的经验——的研究。
总而言之,梅洛-庞蒂在利用精神分析对情感、体验、关系等的重视及讨论化解身体之思的观念性的同时,也通过其肉身概念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精神分析的新角度。这使得现象学和精神分析在相互接触之中引导我们朝向一种从实质中脱离出来的哲学(32)Merleau-Ponty, M. Phenomen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Preface to Hesnard’s L’Oeuvre de Freud (A. L. Fisher, Trans.). In H. Keith (Ed.),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Reprinted). 1993.,而这种新的哲学需要我们继续探索与寻求。笔者认为,在对这种新的哲学的研究中,我们应当以身体现象学思想重新架构精神分析的理论体系,对精神分析做出宏观把握。与此同时,也需要在精神分析的具体实践中真正理解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并不断重新回顾身体现象学的鲜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