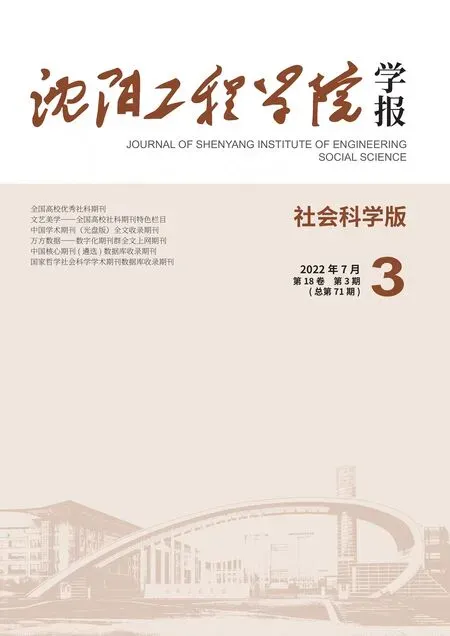班宇小说与“80 后”文学创作“去历史化”的背后
常佳玥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文学写作的历史性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它不仅是许多作家的创作追求,还是批评界的重要标准。洪子诚曾在他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一书中指出,盛行于五六十年代文学作品中的宏大叙事似乎成为了一个远去的文学现象,随之而来的是个人化叙事的兴起。基于这本书的成书年代,所讨论的还是70 后作家,他指出,很多批评家认为“‘70年代作家’是没有‘历史’,没有‘历史记忆’的一代,他们的作品只有‘现代时’,也自觉拒绝‘历史’。”[1]109随着时间的迁移,当“80 后”作家开始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时候,这种由批评界对70 后作家所作出的“历史匮乏”的评价也延续到了“80后”作家的文学创作上,甚至折射出更加激烈的批评势态。无疑,当“经典历史圣殿意识”式的批评标准与专注于生活的日常性、个人性书写的文学创作观念相遇时,总会碰撞出激烈的火花。于是,“80后”作家自然而然地被贴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他们缺乏与历史的有效互动,秉承一种“去历史化”的文学创作观,这成为“80 后”作家饱受质疑的原因之一,也造成了“80后”创作主体的历史焦虑。
一、“去历史化”的背后:“80 后”文学创作的新转向
“80 后”作家的孤独出场,以及在主流文坛所遭受的冷遇,使一些作家在近年来开始有意识地转变创作方向,内在化地接受来自主流批评界对经典历史的推崇,试图以此摆脱创作的焦虑。而在焦虑之外,更为迫切的是一种“再无可写”的危机,当耗尽了“青春写作”的经验,“80 后”作家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虚妄和同质化之中。转身投向历史,去寻求更为广泛的创作题材和更为深邃的精神资源似乎成为一种自我救赎的途径。“新世纪以来,一些作家开始从这种浅薄的表象化感性书写中脱离出来,有意识地抗拒割裂历史的创作态势,并试图接续文学传统强调的观照人与现实的精神价值。”[2]而在“80 后”作家中,张悦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她的长篇小说《茧》无疑是一部转向之作,不再耽搁于青春的幻想,而是直面祖辈、父辈的恩怨纠葛,展示几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她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表示“80 一代”早慧而晚熟,出发虽迟却总会抵达,从而显示了向历史靠拢的意识。然而,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对于“80 后”来讲,他们没有经历过前辈的历史风暴,对大历史也没有更多的体验,这种匮乏势必会给创作带来一定局限,也注定了他们不可能重复前辈们的文学经验。因此日常生活的表达和个人性的书写依旧是他们的主要创作方向。就像张悦然所说的那样“我会努力让自己小说的视野更宽阔,但我不会放弃个人化的表达。”[3]这种相似的观点在班宇那里则显得更为斩钉截铁:“历史可以被日常拿来被思考,却不能成为小说创作的容器,我只是在写人的故事。”[4]
因此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称“80 后”作家的创作为一种“去历史化”的表达,然而“去历史化”不等于抛弃历史,只不过他们不再重建五六十年代的宏大叙事,而是有意识地回避对重大事件的书写,并以碎片化的事件勾连起个体对历史的思考和参与。在“80 后”作家“去历史化”的背后实则是一种将历史推向幕后的选择。
近年来,由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位“80 后”沈阳籍作家所创作的一系列对东北创伤记忆和对边缘性人群进行重新挖掘的作品,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有评论者将其命名为“新东北作家群”“铁西三剑客”。他们的出场,已然创造了“80 后”文学创作的一种新转向,让日常生活与历史直接对话,以个人的身份和体验重塑历史的另一面。在他们笔下,历史既是隐喻又是记忆和经历。他们在解构历史的同时,也在建立一种与历史对话的新方式。
作为“铁西三剑客”成员之一的班宇,有着从小生活在沈阳市铁西区工人村的经历,这使他亲眼目睹了90 年代随着国企改制而带来的“下岗潮”对于普通工人家庭的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衰败与没落,以及由此带来的底层群众对生存困境的无奈与挣扎,深深扎根在他的记忆深处,并成为时时撞击他心灵的特殊经验。正因如此,他在城市书写中聚焦个体的生存状态,展现个体在一个时代落幕的冲击下,那种焦灼、困窘,无所依附,也就无从逃避的生存境遇。通过对一个个个体命运的塑造,勾连起父辈的失落与子辈的找寻,从而在日常生活的书写中完成了对东北上世纪90 年代那段特殊历史经验的回顾与确认。因此以历史作为日常生活思考的方式是班宇在小说的书写中始终秉持的创作观念,这可以看作是“80后”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转向。
二、对个体人物生存与命运悲剧的聚焦
“铁西三剑客”在人物的塑造上,倾向于两类群体形象:父一辈和子一代。通过两代人的代际关系来透视人的生存本真,展现底层群众在命运边缘的挣扎与呼号,从而描绘出一条完整的心灵轨迹。相比于双雪涛和郑执,班宇小说所呈现的悲剧美学更为引人深思。他的小说里几乎没有血淋淋的事实,也没有生离死别的场面,更没有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但他以悲剧为底色,以近乎黑色幽默的语言来塑造人物。在最为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在柴米油盐的琐碎片段里,充斥着的是人与虚无和荒谬那种无力又无奈的抗争,一种注定失败却又不断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徘徊的生存悖论。
1.父一辈的失落与挣扎
在班宇的小说中,父一辈是一个失落的群体,他们经历了90 年代的下岗潮,目睹了东北经济的衰微和转型。这种失落属于个体,但同时也象征着一个失落的共和国长子形象。他们在经历了惊心动魄、或早或晚的裁员过后,最终都无可避免地走向了他们共同的归宿。但也许下岗本身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下岗之后无以为系的生活现实。从体制内有着稳定、可观收入的产业工人到街头巷尾、风餐露宿的小摊小贩,从生活走向生存,这其中的失落与艰难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作家在这些失落的父辈身上却找寻到了一种无声的抗争和一种无言的力量。尽管结局确实是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并非是历史洪流中一无是处的失败者,因为他们曾在失落中苦苦挣扎,同时也不断地在绝望中寻找着希望。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在面临困境时,对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找寻要远远强于其他种需求。而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同样证明了,人在受到极端的制约与压抑的时候,往往会释放出不再受任何力量所约束的原始生命力,它以保护自我为本能,给人以压力。这两种理论都恰好确认了班宇小说中人物,尤其是父一辈在生存困境中苦苦挣扎的精神基础。《盘锦豹子》中的孙旭庭在经历了失去胳膊的严重事故之后,又面对妻子的出走、儿子的叛逆及父亲的死亡,这一系列的变故使向来隐忍坚强的他终于开始产生了转变,向厂领导争取销售岗位,换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包括后来离开工厂,自主创业。这是他在生存困境面前,有意识地摸索与抗争,让苦难破碎的生活回归正轨所做出的努力。然而,长期的压抑和痛苦并不会就此消失,终于在陌生人上门讨房时爆发出了巨大的反抗力量,“他趿拉着拖鞋,表情凶狠,裸着上身……孙旭东看见自己的父亲手拎着一把生锈的菜刀……从裂开的风里再次出世。”[5]43-44这种抗争出于自然本能,这一刻的爆发象征着人物身上原始生命力的回归,和对个体尊严的捍卫,实现了对命运虚无有力挑战,从而使孙旭庭成为了真正的“豹子”式英雄。
如果说《盘锦豹子》的结局是班宇对于他所认同的悲剧美学的有意识升华,那么《逍遥游》所呈现的则是虚无的扑面而来和无处遁逃。在《逍遥游》中,父亲许福明被塑造成一个“不靠谱”的人物,他婚姻内出轨,并与母亲离婚,平时靠拉脚为生,没有稳定收入,在女儿许玲玲的眼里,他是一个不要自尊、不顾体面、一事无成、一无所用而又荒唐可笑的男人。这是对传统父亲形象的颠覆,也是对父辈权威的解构,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不靠谱”的形象背后,则是作家真正想要呈现给我们的一个有关父亲的神话。因为就是这样的父亲,在得知女儿患病后毅然决然地卖掉了自己的谋生工具,而在前妻过世后,又重新回归了女儿的生活,用年迈的身体撑起了生活的重担和父亲的责任。许福明的回归,象征着人对无边空虚的主动拥入,明知无法战胜但也无所畏惧,选择主动承受空虚带来的无形痛苦本身就是一种勇气。倘若没有“出走—回归”这样一个模式的设置,那么许福明这个人物则仅仅是被动地承受生活的拷打,而有了这个模式,他则充满了耶稣为人类受死般的光辉,一个伟大的父亲形象、一个可敬的底层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逍遥游》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悲剧,正因为如此,才更加悲壮。它展现了失落的父一辈在命运边缘的苦苦挣扎,明知没有出路,却依然坚守,毫不退缩,是历史变革中的普通人在虚无浪潮中为反抗生存的无意义所做出的无声反抗。正如黄平所言,“班宇不是表现生活的悲剧性,而是将生活提升为悲剧。”[6]
2.子一代的找寻与苦闷
“铁西三剑客”的小说创作在某种程度上都展现了一种父子宿命轮回的生命体验。在班宇的作品里,父与子不仅仅是面临着严重的代际冲突和难以化解的隔膜与冷漠,还要面对命运悲剧重复上演的可能性,即父一辈的生存困境在子一代的身上得以延续,且这种生存困境在子一代那里往往也无法化解,他们继续着上一代的抗争实验,找寻着没有未来的未来,更平添了彷徨与苦闷。
子女对父母来讲,不仅是血缘和生命的延续,还意味命运的延宕和理想的寄托。在班宇的小说里总有这样的特定处境:“父一代遭遇下岗,在经济上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此同时,经济支撑却是子一代成长的必要条件。子一代的需求和父一代的匮乏彼此加剧、互相彰显,最终激化了两代人的危机时刻。”[7]这一点在《盘锦豹子》《肃杀》《逍遥游》《空中道路》中都有体现,其中又以《逍遥游》最为突出。
主人公许玲玲的形象被李陀称为“穷二代里的文青”,贫穷而又身患重病,接连经历失恋和丧母两个打击,身边除了一个“不靠谱”的父亲和两个自顾不暇的朋友之外,一无所有。疾病所带来的肉体上的折磨,窘迫的生活现实和与父亲之间的隔膜所造成的精神困境,使许玲玲无所遁逃,与父亲主动选择拥入虚空不同,许玲玲就生活在虚空中。但是她无时无刻不梦想着逃脱,哪怕只是获得暂时的喘息。秦皇岛之旅给予了她这样一个契机,使她暂时忘却了生存的困境,并获得了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可惜的是结局仍以失败告终,许玲玲的哭泣与害怕,也蕴藏着多种因素,就像李陀所说的:“班宇在这个情节里,……把一种难以分析、难以说明、十足暧昧的‘原生态’生活‘原封不动’地摆在了我们眼前。”[8]或许这个尴尬的结尾使沉溺在幻想中的许玲玲认清了现实,那便是于她来讲,幸福转瞬即逝而虚空永恒。
她一直渴望自己成为一只格陵兰睡鲨,获得自由长寿的生命,但是她又对睡鲨的孤独处境产生了深深的担忧,当曾经的同伴早已静静地沉入水底的时候,它还在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地活着,这不就是一场无止境的虚空吗?因此格陵兰睡鲨隐藏着许玲玲内心的欲望与恐惧。而路边那棵自燃的枯树,似乎预示了她的未来,那是生命力消亡的征兆。生命到最后无非是一堆灰烬。至此作者将许玲玲彻底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和无限的虚空中。结尾处,许玲玲就像小说开头一样静静地坐在了父亲常拉她看病的车里,允许了父亲同样短暂的温馨的存在,这或许是一种父女关系和解的暗示,但是有关他们的未来的出路依旧无从寻找,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这也许才是生活的原生态。
许玲玲的找寻以失败告终,她依然在虚空里等待着、挣扎着,而《冬泳》中的“我”则在命运的操纵之下彻底沉溺掉。在这篇小说里班宇运用了《俄狄浦斯王》式的悲剧范式,“巧合”“突转”与“发现”无处不在,逃避、寻找都无法逃脱宿命的安排。“我”对新生活的希望与侥幸起于隋菲却也终于隋菲,但是这种希望却是在对谎言和罪恶的遮蔽下进行的。因此当真相层层揭开的时候,“我”在坦白与隐瞒之间面临着两难的困境,无论哪一种都足以摧毁“我”往后的人生,于是“我”终于认识到被命运逼到了绝境,既然是如何也摆脱不了的绝境,就只能以自毁的惨烈方式完成对悲剧命运的逃避和罪孽的洗刷。
在班宇对子一代的书写中,他们并没有完成对父一辈生存困境的化解,这种父子宿命的轮回依旧在延续,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苛求作家用文学的方式为他笔下的人物虚构出一条出路,因为他写的本来就是找不到出路而又没有未来的群体。当然,班宇也没有完全绝对化处理这一主题,而是在《盘锦豹子》和《空中道路》等小说里留下了不多但依旧珍贵的希望。《盘锦豹子》中儿子孙旭东最终与父亲达成了和解,从一个顽劣叛逆的少年开始回归生活正轨,他的命运或许因此会得到改变,就像作者这样的子一代在父一辈失落的身影里确认了那段特殊的历史记忆,并开始了对东北想象的重构,这未免不是一种希望、一种出路。而最为可贵的是,当成年的子一代真正进入到生活中去的时候,扑面而来的重压和失败的实感,使他们终于理解了同为“失败者”的父一辈。
三、叙事技巧与艺术风格的个人化表达
“铁西三剑客”虽然也着力展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某段时期的工业发展状况,以及工业体制的变迁,但是他们与草明、艾芜等前辈对工业题材的处理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路径。在前者那里,“作家在塑造工业长子形象时,非常注重把他们放在思想斗争的考验中,以对比和反衬的手法,艺术熔铸他们身上的英雄品格。”[9]而到了后者这里,则不再进行宏大叙事的建构,而是探索出带有浓烈个人风格的艺术表达方式。
1.叙事的“后先锋性”
有学者认为,后先锋性是指“一方面,先锋文学回归到比较传统层面的讲故事和人物刻画,另一方面,它同时保留着自己的先锋基因、语言品格或工艺流程,于形式和结构以及所营造经验的‘当下性’层面保持着自己去革命化之后的经典品格。”[10]班宇小说的叙事就带有后先锋性。他专注于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生活日常性的挖掘,然而在创作手法上,现实主义却只是其中一种。通读他的小说就会发现,他的创作手法和叙事形式是多样的,他可以熟练地运用纯正的现实主义手法写出《逍遥游》《盘锦豹子》这样的作品,也可以借鉴古希腊悲剧理论中对情节的构造方式写出《冬泳》,还可以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写作《蚁人》,更可以对魔幻、超验、荒诞、陌生化的隐喻或梦境等现代主义叙事手法灵活运用。
首先,是在人物刻画上采用极简的白描式手法。他擅长使人物“素颜”出镜通过语言和细节描写透视人物,在生活的原生态中感知人物的性格特质及精神症候,少有心理描写和外貌描摹。其次,在叙事上常常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即某人在做某事,没有多余的铺垫,也很少环境的说明,且多以第一人称作为叙事视角,如《逍遥游》的开头直接就讲述了许福明带“我”看病的过程。然后在许福明与“我”的行动中,自然而然地带出了生活困窘的事实。再次,在叙事结构上,往往会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但结尾往往又采取戛然而止的处理方式。比如《肃杀》,虽然用大量的内容描写了“我”的家庭境遇和各种变故,但是其结构动力便是“寻找肖树斌”,最后肖树斌的出现便是小说的高潮所在,然而小说又在高潮处戛然而止,有关肖树斌为什么偷走父亲的摩托车,他经历了什么都只能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这种高潮即结局的设置在《逍遥游》《盘锦豹子》中也被呈现,在庸俗琐碎,似乎无意义却又不断消耗的日常生活秩序中,人物无法摆脱生存的困境,唯有在脱序的时刻,才会有诗意的彰显和平地一声惊雷的爆发,也因此虚构的意义油然而生。
2.地域化景观与口语化写作
谈论“铁西三剑客”就不能忽视东北特殊的地域文化,这不仅仅是因为地域环境赋予他们广阔的写作空间,还因为东北潜在的文化语境和特殊的审美方式时时刻刻浸染着作者的心灵与思维,从而逐渐形成一种无意识的创作心理。
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寒冷荒芜的生存环境,游牧民族果敢直爽的性格基因,以及东北人民边缘化的生存地位,都衍生出了一种粗糙、生猛的生活美学。“铁西三剑客”正是在这样一种地域文化基础上来展开自己的文学想象,实现有温度的文学书写。因此我们无法脱离东北、脱离沈阳去理解班宇,他的小说就是与这片土地自然、有机地交融着。
首先是取材,尽管班宇的小说不都是对下岗工人这一群体的讲述,但是也不能否认这一群体在作家的创作中带有优先性,这无疑是受到特殊的时代背景、地域历史,以及本人从小的生活经验的影响,班宇曾说过他对工人形象的理解出于他的父辈。而他对工厂也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因为作为曾经的重点工业区的铁西区,工厂林立,机器轰鸣不断,班宇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耳濡目染,对于工厂和机械他是再熟悉不过了。尽管工厂在他的作品里仅仅是作为一个背景而存在着。但是这并不妨碍着他对工厂这一城市景观的建构。此外还有许多,比如街旁的啤酒屋、大排档、卖凉皮麻辣烫的小摊、骑着倒骑驴走街串巷拉脚叫卖的,都构成了独特的城市景观被写入作品。这些景观所建构起来的东北形象是不同于小品艺术所带给人们的那种定型化想象,它更残酷却也更真实,它是东北生存境遇的另一面,却也是最普遍的文化真相。
其次是语言,“铁西三剑客”都有一种卓越的语言转化能力,即他们能够将东北方言的幽默作为解构生活的一种方式。李陀就大力赞赏过班宇自然流畅、不见斧凿的语言能力,即他能将口语与方言有效融入叙事和对话,造就充满东北风味和时代气息的语言风格。因此也有人称班宇的写作是方言化写作,但是他自己却并不认同,他曾说他有一种讲普通话的错觉,所以在作家自己的认知里,方言的代入并不是有意为之,他只不过是用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性语言来书写自己的文学世界。然而正是这种对文学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所采取的一种融合方式,使他的小说在雅俗之间释放魅力,同时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和个性。语言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作用尤为突出,通过人物之间大量的生活性对话描写,其精神症候跃然纸上。方言的幽默、戏谑和粗粝深化了班宇小说的悲剧意识,进而完成了对传统生活的解构。在班宇的小说里,生活不再庄严肃穆,也不再惊心动魄,而是充满了日常秩序之内的庸常和琐碎,当然也会有脱序时刻偶然的一场爆发和瞬间的一丝诗意,从而使生活走向高潮,只不过短暂的高潮之后,人最终还是要回归正常的生活秩序里,去重复司空见惯的平凡生活。
四、结语
无论是在文学观念,还是创作题材和叙事技巧上,班宇的小说都以突破宏大叙事的“日常生活性”表达,通过对工业体制衰败下个人生存境遇和命运悲剧的细致讲述,在记忆与真实之间还原了被大众娱乐文化歪曲了的东北城市图景和东北文化想象,夺回了被父辈丢失的历史阐释权。他们不仅用个人性书写回望了父辈失落的身影,也确认了一段逐渐远去的历史,并完成了对自身精神的探索。这种尝试显示了80 后作家走出青春文学自我体验的狭小空间后的一种新转向,也是青年写作的历史性的一种新可能,他们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前辈们所经历的历史风暴并不是唯一的,每一代人都有着自己对历史记忆的独特感知,就像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亦有大历史的沉重,他们或许没有能力,或许没有兴趣去重建前辈们的恢弘过往,但他们却也没有放弃以自己的方式去建构与历史对话的新可能,即使出发虽迟,但终究会抵达。也许现在反驳“80 后”是“没有历史记忆的一代”为时尚早,因为他们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成长。但对日常生活叙事的回归,对“去历史化”的文学表达并不代表着对历史的遗忘和抛弃,个人与历史永远呈现着复杂的交织状态,这一点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