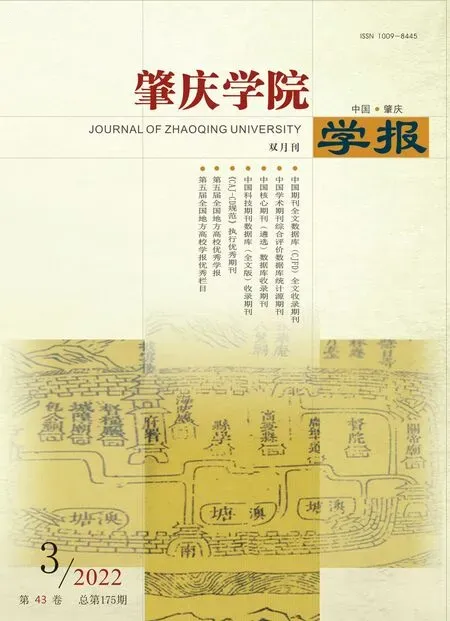规范论视阈下的回译研究
——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例
王 毅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
一、引言
《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完成的一部英文通讯报道文集,书中真实记录了他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集政治体裁的严肃性与纪实风格的活泼性为一体。斯诺在报道中保持着美国人特有的幽默感和新闻记者独有的敏锐性。一方面,他的文化身份使其成为一个疏离冷静的旁观者,另一方面,身为一个美国人,他对苏区红军的认知与描述会得到外界的格外关注。整部文集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描述了红色根据地大大小小的人物与事件,对于多位开国元勋的描写朴实而细腻,他们在苏区艰苦卓绝的岁月伴随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在斯诺笔下生动地浮现出来。该书于1937年由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发行,之后多次再版,时至今日,依然是西方读者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必读作品。
这部文集在国内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除了作品本身体现出的政治与思想价值外,董乐山先生的精彩译笔也是这部文集能够畅销不衰的重要原因。斯诺从一个“文化他者”的视角用英文描述了中国特定时期的历史与政治风貌,让世界了解了真实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汉译这部著作是一个“回译”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还原”的过程。本文旨在用翻译规范论的视角解析《红星照耀中国》这部回译作品在国内形成深远影响力的原因,并试图揭示在服务于目的语环境背景下,翻译规范与回译评价标准两者之间的诸多共同诉求。
二、回译与规范
以色列著名翻译理论家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是描述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致力于在社会秩序的背景下去考察翻译行为。图里认为翻译不仅是译者的个人行为,还会受到社会诸多层面的制约,在他构建的理论体系中,翻译是在一定社会秩序下逐渐凝结成的一种受制约的特殊社会行为。翻译规范作为一种行为准则,调节着两种语言和文化系统。他将翻译规范分为“起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起始规范”是指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具体说就是在翻译的充分性与可接受性之间作出选择;“预备规范”又分为“翻译政策”和“翻译的直接性”,前者指翻译背后的国家或是赞助人意志,后者指目的语文化对译作的容忍度;“操作规范”指译者在实际翻译行为中作出的各种决策,包括宏观层面的“母体规范”与微观层面的“文本—语言规范”,前者指翻译内容的安排与取舍,后者指对文本的细节化处理。“起始规范”在整体上控制着其他规范的运作,“操作规范”是对“起始规范”与“预备规范”的践行和集中体现,三种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译者的行为[1]。
“回译”指A国人用本国语言描述B国文化,之后又译成B国语言的过程。“回译”可分为“无本回译”和“有本回译”,前者指原文内容回到没有可兹参照的目的语上来,过程会伴随着文化回译;后者指在回译过程中有原本可追溯并可以复原[2]。《红星照耀中国》是埃德加·斯诺用英语创作的关于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著作,因此从整体看,其中文译本属于“无本回译”范畴,但鉴于原作的纪实性,从微观看,部分文本也具备“有本回译”的可能。
回译虽有别于传统的翻译行为,不过依然受社会秩序与准则的制约。翻译是目的语文化的事实,本土文化和话语机制是翻译行为得以发生的前提和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3]。传统意义的翻译是一种受本土文化局限的阐释,回译则不同,它是在本土文化推动下阐释,译者显然感受到了更多的自由,迎合母语读者审美观的欲望也愈加强烈,翻译的过程必然少了些羁绊与妥协,多了些助力与主动,所以规范下的回译会呈现出某些特有的样态。
三、回译中的初始规范及实现条件
“初始规范”是译者在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一种倾向性选择。如果译者服从于源语文化规范,那么他追求的是译文的充分性;如果译者向目的语文化规范靠拢,他便将可接受性放在了首位。换句话说,“起始规范”就是要在尊重作者和照应读者之间做出选择。就回译而言,充分性的诠释更多见于异化策略,通过直译和对异质感的保留实现对原作的尊重;可接受性则需借助归化策略,巧妙地使语言要素得以变形,利用对母语自然的驾驭能力实现文化互通。
受文化间信息转换通道的制约,充分性与可接受性往往难以调和。如果说在一般的翻译作品中充分性与可接受性由译者的主观选择而定,那么在回译这一客观背景下,两种倾向性可实现最大程度的共融。《红星照耀中国》讲述的是中国故事,目的是有效阐述并传播革命思想,所以从客观上就决定了实现可接受性的基本条件。同时,作为一部纪实通讯,书中涉及大量的人物、地点与事件,对于这些要素的还原属于回译中的“有本还原”,加之为了充分呈现作者对于中国革命的独到见解,这些都为实现充分性提供了可能。
如果说回译的性质为“初始规范”准备了客观条件,那么能否实现充分性与可接受性间的共融还要取决于译者这一主观因素。董乐山在翻译实践中一直追求译文的可读性和流畅感,这点在他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中体现得尤为充分。鉴于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他通过化名,充分利用“文化身份的隐身”,使《第三帝国的兴亡》读起来仿佛就是读中文写作一般,原文中的一些文化与语言的异质元素已经在他精妙的译笔下悄然褪去[4]。1950年董乐山进入新华社外文部工作,后转入翻译部任职,长期从事与新闻翻译相关的工作。工作的性质使董乐山一直把信息传递的严谨性与充分性放在首位。其实在1937年,在胡愈之的组织与带领下,《红星照耀中国》的汉译工作就已完成。1976年董乐山在原基础上又对与历史不符之处和误译做了大量重新考证与修正,译者的工作经历与职业态度都为译文充分性提供了保证。
四、预备规范对回译的导向性
“预备规范”包含翻译政策与翻译的直接性两方面。翻译政策指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或特定历史时期中影响文本选择的因素,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文本可以被引入到目的语文化中;翻译的直接性指目的语文化对翻译的容忍度,具体说就是何种语言风格是受鼓励的,哪些内容是被禁止的或是可以被包容的。翻译政策与翻译的直接性有着内在的联系,两者往往在文本的选材上共同施加影响。
《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发行当时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至今日这部著作依然能够保持着持久的思想活力与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幕后推动。其实这部书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精心的组织与安排下完成的,也可以说从一开始就为这部英文通讯文集的翻译设定文化背景,营造了接受条件。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胜利完成长征,但国民党却对外界封锁红军已经在陕北成功会师的消息,并利用手中的宣传机器歪曲事实,混淆视听。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迫切希望冲破舆论封锁,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存在,同时阐述自身思想,争取和团结抗日力量。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斯诺进入苏区采访的思想导向,也为日后对采访内容的回译创造了先决条件。
当时我党领导人开始从国籍、政治背景、思想倾向及报道风格等方面来选择合适的记者做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代言人。经过多方斟酌,后由宋庆龄举荐,最终选定埃德加·斯诺。斯诺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城的一个贫寒家庭,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于1928年来到上海,担任欧美几家报社驻远东特约记者与通讯员,他的报道一直秉承客观、公允的准则。在华期间他与中国多位著名进步人士保持联系,思想逐渐倾向于社会主义。斯诺的出身背景,报道风格以及后来的思想转变都决定了我党对他的报道内容会有着极强的接受度。
在斯诺到达延安后,周恩来专门为他制定了采访行程,并保证其充分的采访自由。为了使苏区的思想能够被精确完整的传递到外界,我党还为斯诺安排了多次与领导人面对面的采访。如在对毛泽东的采访中,为了确保内容的真实准确,由时任苏区宣传部副部长的吴亮平担任采访翻译,内容最终由毛泽东亲自校阅。
我党不仅对采访活动做了细致的安排,更是对后续的翻译和发行高度重视。鉴于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将《红星照耀中国》这样一部传递延安声音的书翻译、出版并发行是极其困难的。1937年,在以胡愈之为首的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与组织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多位成员开始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出版这部著作。这项工作也得到了斯诺本人的大力支持,他不但拿出了底稿,还无偿出让版权。受当时环境所迫,中译本被改名为《西行漫记》作为掩护。译本一经发行,便在海内外爱国华侨中引起轰动,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
1976年,中国新的风向虽在萌生,但出版界与翻译界的禁忌仍多。这段沉寂的历史得以重现要得益于时任新闻出版局局长陈翰伯的魄力与胆识。他委托三联书店的负责人找到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希望能够凭借其深厚的翻译素养忠实再现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凭借陈翰伯的高瞻远瞩,中国出版界逐渐走出了文革的阴霾,展现出了全新的气象[5]。由此可见1938年“复社版”《西行漫记》与1979年三联重译版《红星照耀中国》见证了我国不同时期翻译政策对文本选择的导向性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回译文本内容的选择也是愈加开放和包容。
五、回译评价标准与操作规范的统一
“操作规范”是实际翻译行为中采取的决策、方法与技巧,由“母体规范”和“文本—语言规范”组成。前者指对被选择文本中内容的取舍;后者是“操作规范”的核心,是指具体文字层面的运作。斯诺曾对原稿进行过三次修改,董乐山所选译的是1937年该书第一次出版的全文原稿,并对其未做任何改动,而且还补全了先前译本中删减的关于国际共产国际部分。从“母体规范”看,复原关于李德的部分是对当时党内路线斗争的真实再现,对于这部分历史资料的重现反映出新时代下我党求真开明的翻译政策。无本回译作为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除其基本评价标准应和一般翻译保持一致外,也有其特殊性,评价标准需借助操作规范实现。王宏印提出的无本回译评价标准对操作规范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语言标准
由于没有可参照文本,所以无本回译只能是尽可能地贴近目的语的表达习惯,也就是从语言结构与遣词方面符合中文的表达[6]。
《红星照耀中国》作为一部通讯报告文集,兼具了新闻与文学的双重特质。书中有大量精确的记述,同时也不乏文学性的描写与抒情。下面一段是对红军艰苦环境的描写:
原文1:For sheer dogged endurance,and ability to stand hardship without complaint,the Chinese peasants,who compose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Red Army,were unbeatable.This was shown by the Long March,in which the Reds took a terrible pummeling from all sides,slept in the open and lived on unhulled wheat for many days.[7]
译文1:中国农民占红军的大部分,他们坚韧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可能也有外国的军队能够吃得消这种同样的风吹雨打、食物粗粝、住所简陋、长期艰苦的生活,但我没有见过[8]。
这段译文的显著特点就是四字格的连续使用。“坚韧卓绝、任劳任怨”都是等值于原文的翻译,争议在于“风吹雨打”的使用。“pummeling”意为用拳头连续打击,并发出砰砰声,如果单凭这个概念义就引申其为“风吹雨打”未免有偏离原意和过度揣测之嫌,但结合后面对红军吃住的描述来看,这个四字格的使用就显得恰如其分了。汉语重主体意识,往往“以意役形”,形成有序的意念流,其中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四字格的使用。四字格是中华语言的瑰宝,在翻译操作中,尤其是在文学翻译中,使用精当可使译文熠熠生辉。许渊冲曾在“语言竞赛论”中指出,既然中西语言无法达到等值,而翻译过程又是文化间的统一或妥协,那么实现这一过程的唯一路径就是扬长避短,发挥译语优势。[9]四字格还有雅致、畅达的特性:
原文2:The streets were completely deserted and everything stood in crumbling ruins.[7]
译文2:街上阒无人迹,到处都是断垣残壁[8]。
原文3:He seemed a sort of hoary grandfather by contrast with others.Yet he was no specimen of decrepitude.He had an erect and vigorous step,bright and merry eyes.[7]
译文3:与别人相比,他(指徐特立,毛泽东的老师)似乎是个白发老翁。然而他并不是老朽昏聩的标本。他步履矫健,双目炯炯[8]。
以上两句中四字格和谐凝练,生动传神。值得注意的是译文3中连用四个四字格,在人物的刻画上极具表现力与画面感。
(二)文体标准
就无本回译的文体标准,王宏印提出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与原文体对应一致;另一个是根据受众面的需要改变文体类型,使其上升或下降。[6]通讯是运用记叙、议论、抒情等多种手法,生动、形象地反映事件或人物的一种报道形式。《红星照耀中国》虽然在整体上属于严肃文体,但在人物刻画上又不失活泼性。董乐山敏锐地捕捉到了通讯的新闻性与文学性,在翻译客观事件时多用直译,风格谨重,在涉及人物刻画与地域风貌的翻译时则放宽自由度,文字欣畅细腻。下面一例便是对文体对应很好的诠释:
原文4:A bright-eyed lad without a shadow of whisker on his face arose and declared:"I have only this to say.When the White Army comes to a village in Kansu,nobody helps it,nobody gives it any food,and nobody wants to join.……[7]
译文4:一个眼光明亮的少年,嘴上还没有长毛,他站起来宣布:“白军来,没有人帮助,没有人给他吃的,没有人参加。……”[8]
这是一位红军小战士的话语,外貌描述虽不是作者的着力点,但董乐山没有放过任何一丝对人物细节塑造的机会。“whisker on his face”直译为“脸上的胡子”,但董乐山却生动地译为“嘴上没有长毛”。两种翻译的概念义都是“未完全发育成熟的青年”,但背后的联想义与画面感却截然不同。“嘴上还没有长毛”出自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15回:“俗语说道,‘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多指“没有社会阅历与经验的年轻人”。可是阅历与经验往往伴随着沉稳和世故,而在这里译者恰恰是想借此烘托出小红军战士的率真与直言。革命需要的是像小战士这样的活力与激情,当时多位红军军长也不过二十多岁,如陈再道、寻淮洲。这一处的翻译操作所呈现出的不仅是人物生动的画面,更是红军在面临国家危局时刻所换发出的生机与希望。
在对这部通讯文集翻译的过程中,董乐山敏锐地发现了多处可资参考并可以复原的史料,通过对局部的“有本还原”可以使译文在最大程度上做到文体对应。
原文5:Replace all doors when you leave a house;
Return and roll up the straw matting on which you sleep;[7]
译文5:上门板;
捆铺草[8];
比较后不难看出,译文不但较原文简化许多,而且在
语义上也与原文相距甚远。如此改译并非是译者“自作主张”,而是在具体操作规范中的“有本回译”。1928年初,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遂川县后随即驻扎下来,并要求战士们生活中要自律,尤其夜晚要露天宿营,不要打扰当地百姓。由于当地气候潮湿,一些士兵就借了百姓们的稻草和门板当做床以隔湿。但不少士兵用后没有及时归还,百姓意见很大,毛泽东知道后就提出了“还稻草、还门板”的纪律,官兵们都能够严格遵守。可过了几天,又有农民抱怨道:“借去和还回来的不是一块,我家的门板是斗榫的,对不上号,找起来很是费劲。”还有农民说,战士们把借去睡觉的稻草弄得遍地都是,却不收拾。了解到群众的意见后,毛泽东就将“还稻草、还门板”改为“上门板、捆稻草”。两字之差,不仅解决了问题,还进一步加强了军民之间的关系和融合。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部队宣布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也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身[10]。这里的“有本回译”体现出了文体标准中的文献性和文化还原性。
(三)文化标准
因为语言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性,所以语言层面的回译也伴随着文化回译。随着翻译中语言形式的变化,译文一定是向着目的语文化方向靠拢,并尽可能摒除源语国家或他国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干扰[6]。在具体的操作规范中,回译中的文化复原还体现着译者的文化价值观。
原文6:For a decade this distant country had been run like a medieval sultanate by Ma family.[7]
译文6:这个边远之地就由马家像一个中世纪的苏丹国一样统治着[8]。
这句话的背景是指当时的西北三省几乎由姓马的回族将领世家来封疆制之。如果忠实于原文,“distant country”应翻译为“边远的国家”,但青海和甘肃北部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怎能称之为“国家”。在一些西方记者眼中,中国西北地区有着独有的民族性,加之当地民众的突厥血统,就把该地区自下定义为中国以外的“国度”。这种按照宗教、语言和血统划分国家的方式源于对历史缺乏了解,同时也是意识形态所致。马家和马氏兄弟在这一地区存在的历史可追溯到北洋军阀时期。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奉旨护卫慈禧太后西狩,后封提督,在辛亥革命中通电拥护孙中山,后受蒋介石委派管理该地区。其实在民国期间,很多地区是国民政府管辖力所不及之处,只得委派当地军阀代为管制。但这一地区是中国之领土是毫无争议的。斯诺虽对中国怀有特殊感情,理解并支持中国革命,但毕竟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是有限的。“country”这个词的使用或许是他无意为之,但董乐山保持了回译中的话语权,这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更是文化标准的体现。
原文7:Still,they easily had the cleanest habits of any soldiers I had seen in China,and carefully refrained fromthe national gesture of spitting on the floor.[7]
译文7:他们(回族士兵)仍是我在中国看到的习惯最清洁的士兵,没有随地吐痰的恶习[8]。
译者在翻译中回避了“national gesture”,随地吐痰是部分中国人的恶习,但还不致上升至举国如此的层面。译者在这里做了巧妙的文化过滤,既突出了回族士兵的清洁生活习惯,又不致让原文本中无形的对比使国家形象受损。
文化标准在回译操作规范中的体现其实是一个文化身份选择的问题,一旦文化身份确定,接下来便是在尽可能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实施一定程度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干预。但这种干预不是对目的语国家和文化的刻意美化,而是基于历史和文化客观事实的一种话语权的体现。对干预度的把握既体现这国家的翻译政策又彰显着译者的文化观和翻译素养。纵观《红星照耀中国》,译者本人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一个“他者”的文化视角,对书中所涉及人物的描述,无论在生活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是完整呈现。这些都彰显出国家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与译者求真务实的文化精神。
六、结语
《红星照耀中国》是西方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第一部采访记录。埃德加·斯诺以他热情和生动的笔触记录了日渐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点点滴滴,大到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小到士兵与百姓的言语神情,是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从宏观看属于“无本回译”,但其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又使其可以做到局部的“有本还原”。这部通讯纪实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充分体现出回译这一特殊翻译行为所要遵循的社会规范,翻译规范对回译既有推动与导向作用,又在操作层面制约着译者的行为。在文化回译的背景下,译者不但要将读者的阅读体验放在首位,还需在翻译时还原文体风格并使其符合目的语国家的文化标准。董乐山凭借其深厚的文字底蕴,杰出的翻译能力使无本回译的评价标准与翻译操作规范得以有机融合,成就了中国翻译史上的一次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