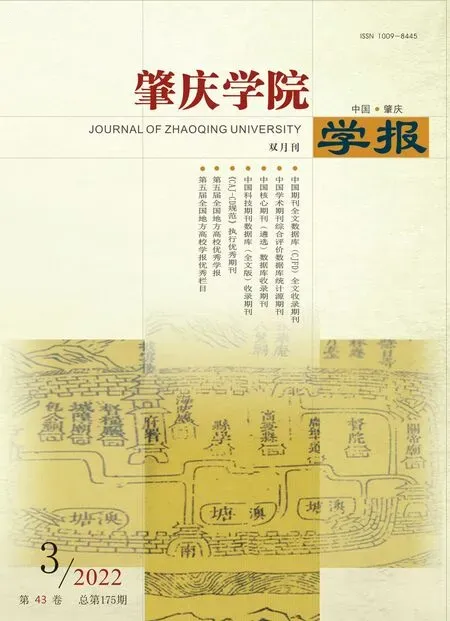晚清广州行商与九善堂活动考述
黄 怡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关于广州善会、善堂的研究,目前学界成果比较丰硕。夫马进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考察了中国善会善堂诞生的历史背景、清政府的慈善救济活动、善会善堂组织与中国近代地方自治的关系[1]。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试图透过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历史,看社会经济改变与价值观改变的关系[2]。邱捷的《清末广州的“七十二行”》论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州行会的联合团体“七十二行”在地方政治、经济生活中产生的影响[3]。熊燕的《九善堂与清末民初广州社会》认为善堂具有“护商”性质,善堂的组建者——七十二行商人亦官亦商,同时具有政治性和社会性[4]。衷海燕与梁灏的《近代广州的慈善组织与地方社会——以崇正善堂为例》对崇正善堂的救济思想、筹建过程、组织架构、经费收支、慈善活动等方面展开论述[5]。关于广州九善堂的研究,学术空白已有所填补。但现有学术成果很少将广州十三行与九善堂联系起来,少有学者关注到十三行后人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发展去向。本文试图以晚清广州九善堂的活动为主线,初步探析“后十三行时代”行商在广州进行的慈善活动。
一、鸦片战争前广州慈善行业发展概况
若要论述广州地区慈善事业的发展,则十分有必要将清朝建立以来广州的慈善事业发展历程作一简单梳理。广州慈善组织的建立起步较晚,前期发展缓慢,清晚期之后才逐渐发力。总体来看,雍正时期建立的慈善组织较多,乾隆、嘉庆年间有所下降,同治至光绪年间才恢复到雍正时期的发展势头[2]332-399。在整个清朝统治时期,官办慈善机构的数量始终都占较大比例,根据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一书统计,1646年至1911年间,广东地区的育婴堂共55所,其中官办31所,民办19所,创办人身份不明14所[2]332-399。而后期民间慈善机构的增多离不开广州行商在经济上的支援。
广州地方官府从事的慈善事业包括创办育婴堂、恤嫠局、敦仁馆、普济堂、漏泽园以及各类综合性善堂等活动。广州最早的官办慈善机构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所设立的育婴堂。“粤东育婴堂之设肇于康熙三十六年,总督石琳、巡盐御史沈恺曾率同商人云志高购买西门外第十甫钟氏废园起建堂屋,石琳自为记”[6]974。后来在官府的号召下,广州豪商富贾曾积极参与到该育婴堂的重建活动中。“埠商沈宏甫等四人共捐银一千两于大东门外子来里价买民地,另建新堂计房屋三百余间”[6]974,这也是广州商人参与慈善救济活动的最早记录。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发布新的法令,“京师广宁门外,向有普济堂,凡老疾无依之人,每栖息于此。司其事者,乐善不倦,殊为可嘉。圣祖仁皇帝曾赐额立碑,以旌好义。尔等均有地方之责,宜时加奖励,以鼓舞之。”[7]433广东各地官府为响应朝廷的号召,开始积极倡导建立类似普济堂这类的民办慈善机构。而地方官府的政绩也逐渐和慈善机构创办的多少挂钩,因此自雍正二年(1724)上谕发布后,全国民办慈善组织官僚色彩日渐浓厚。乾隆以后,全国慈善机构的创办渐成体系,分为官督民办、官办、民办三种类型。民办者一般由社会筹措,官办者则由政府出资,官督商办者则是民间捐助与政府自助相辅相成。康熙五十九年(1720),广州最早成立的民办慈善机构——敦仁馆正式建立。“敦仁馆在五仙门外马头,康熙五十九年绅士邓可韬等捐建”[6]975。在敦仁馆建立之前,广州各类慈善组织都是由官方创办、管理。
育婴堂、普济院、漏泽园等都是功能较为单一的慈善组织,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鸦片战争之后的广州出现了综合性慈善机构——善堂、善会,这种机构通常涉及到慈善义举的许多方面,包括从事施药、施棺、义冢、育婴、恤嫠和救生等多方面的活动。就各地创办善堂、善会来说,唯广东善堂林立、甲于他省。同治十年(1871),广东地方绅商在广州城西十八甫创办了爱育善堂。“爱育堂在城外十八甫,同治十年为官绅商民捐建,为开设义学、施药、施棺、捡拾胔骼、栖养废疾诸善事公所”[6]975。爱育善堂的建立正是广州综合性慈善机构兴办的开始。“粤之有善堂,此为嚆矢。自是而后,城乡各善堂接踵而至”[8]173。自此之后,广州官府依然参与管理这些善堂,但不占据主导地位,而是交由民间人士管理、控制,具有官督民办的性质。由于官府放开对民间慈善事业的限制,此类综合性慈善组织逐渐在广州大量出现。
二、“后十三行时代”九善堂开展的慈善活动
清末民初,在广州省城内外,善堂或善堂性质的慈善机构有数十所之多,“九大善堂”只是其中最活跃的一部分。九善堂是广州各大善堂的统称,作为广州慈善事业发展的里程碑,它的建立推动着广州社会的发展。本文所论述的“九善堂”依据现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大源村大源北路林安物流园北门左侧设立于1920年的九善堂碑,此碑明确指出九大善堂包括:述善堂、爱育善堂、广济医院、广仁善堂(两粤广仁善堂)、崇正善堂(崇本善堂)、惠行医院、明善堂、润身善社、方便医院[9]1163。但也有学者认为九善堂只是固定称呼,并非具体指代九个善堂。如著名的慈善史学者梁其姿教授认为,“九大善堂”不一定指代固定的九个机构[10]221。除了上文所提及的爱育善堂,另外八个善堂在广州都有具体的地理位置。据方志记载,“两粤广仁善堂在新城靖海门外吉昌街”,“广济医院在新城油栏门外迎祥街东”,“惠行善院在新域晏公街”,“崇本善堂在十一甫光”,“述(善)善堂在黄沙”,“明(善)善堂在城西第七甫”,“方便医院在城北高冈”[8]174,“润身善社在大东门外线香街”[11]161。
明清之际,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发达的对外贸易,广州商业繁荣、商人云集,至晚清时,在广州西关、新城一带,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商人团体——广州七十二行。广州七十二行(西共堂)作为广州商人的联合体,管理并控制着九善堂。清末,广州的商人团体经常以行会的名义参与到慈善事业中,七十二行是他们的联合机构,并通过九善堂这一机构活跃于社会活动中。
关于“广州七十二行”,有两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广州七十二行只是广州商业、手工业、工业等行业的统称,并非指具体的数目,原因在于不同的史料中所记载的“七十二行”的数量、名称都大有不同。第二种含义是“广州七十二行”有具体数目。本文中所指“广州七十二行”,引自《宣统番禺县续志》所记载,“广州商业以七十二行著称,七十二行者土丝行、洋庄丝行、花纱行、土布行、南海布行、纱绸行、上海绸布帮行、疋头行、绒线行、绸绫绣巾行、顔料行、故衣行、顾绣班靴行、靴鞋行、牛皮行、洋杂货行、金行、玉器行、玉石行、南番押行、下则押行、米埠行、酒米行、糠米行、澄面行、鲜鱼行、屠牛行、西猪栏行、菜栏行、油竹豆行、白糖行、酱料行、花生芝麻行、鲜果行、海味行、茶叶行、酒行、烟叶行、烟丝行、酒楼茶室行、生药行、熟药行、参茸行、丸散行、薄荷如意油行、磁器行、潮碗行、洋煤行、红砖瓦行、青砖窰行杉行、杂木行、铜铁行、青竹行、电器行、客栈行、燕梳行、轮渡行、书籍行、香粉行、银业行、银业公会、矿商公会、报税行、北江转运行、北江栈行、南北行、天津公帮行、上海帮行、四川帮行、金山庄行是也”[11]240。《民国番禺县续志》中又有一话,“谨案七十二行之名系因光绪间大学士刚毅来粤筹饷,责令粤商各行担任台炮经费,时商会尚未成立,由总商岑敬舆将经费分令七十二行檐负,故名称相沿至今,实则当时已不止此数,其无力者未有列入也”[11]240。另又有1907年创办的《七十二行商报》发刊词称:“吾粤商团之组织起自何时乎□则我七十二行为之滥觞也”;“溯七十二行之名目,始成于科场之供应,继彰于商包厘金,至此次粤汉铁路事担任收股,而社会上之信仰愈益隆重”[3]82。《宣统番禺县续志》与《七十二行商报》发刊词所记载皆是同一件事,即将1899年大学士刚毅南下广东筹饷,并命令总商岑敬舆组织各行商人召开会议以筹集款项一事,作为广州商人视“广州七十二行”为统一联合体的标志。
尽管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权被取消,但作为广州商人群体联合的象征,广州七十二行实际上延续了十三行的部分功能,它仍然能够利用广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开展对外贸易,每年大量的中外交易依旧在广州进行。商业的持续繁荣使得行商积累了大量财富,这又能够为广州慈善行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得益于发达的对外贸易,九善堂作为地方民办慈善机构,其运营经费一方面由广州七十二行商中的有力者资助。以爱育善堂为例,行商在其创办之初就多有出资。“是年三月,经始先试办于洋行公所,多方劝谕签捐者三萬两有奇,各行认捐者每年六千两有奇”[8]173。另一方面,各大善堂还通过租金收入、附商生息等方式凑集善款,此过程也多由部分行商操作。九善堂普遍采取董事负责制,这是一种绅董轮值的管理制度,管理者也由这些出资者担任,或由出资者的家族充任。具体方式是在资助者中推举数名为会首,由这几名会首轮流管理堂中事务。如《香港华字日报》一则告示,“每年由十大行推举值理,周而复始,现当瓜代之期,拟于初九日邀集各行商在堂筵□,公推戊戌年以檀香、土丝行为值理”[12]。又如“方便医院章程”就有所规定,“总理原举行头行公推办事之人,由其通行举殷实公正者当之”,“本院定章递年推举两行为协理。其倡建总理值事均为董事,所有院中钱银各事,各归当年总理专管,协理帮同兼顾,以佐其成。”[13]235再如爱育善堂章程,“本堂向由原日创办者及捐助年捐之银业行……米糠行等行头内,每年轮值两行为年值理,由各该行推举身家殷实,热心任事之商董数名代表……”[14]。在广州七十二行商有条不紊的运营下,九善堂很快发展壮大起来。
在广东省内,九善堂开展了颇多救济活动。
光绪七年(1881)清查坟山公所的经费,除了官方拨款外,“其余惠济义仓、爱育善堂等每年亦拨款补助。”[11]163光绪年间,曾有一官员名曰邬彬,因沙茭总局(贲南书院)经费支绌,特地筹设广益会,并出资在江鸥购买沙田以支持沙茭局办学,“复联络七乡同人建东山社为自治基础。省城爱育善堂、香港东华医院,皆踊跃输助,慷慨不吝,顺直赈捐,报效千金。”[11]354朝廷为鼓励商人们有更多的报效,“给予‘乐善好施’字样建坊”。
广仁善堂,“凡得银一万二千八百九十余两,乃与广州广仁善堂合资在番禺中山购置围田,由内地推公正绅商管理,递年租入,分给各堂施善法,至良惠,亦至普也”[15]139。
崇本善堂,“集资设立捕属册金局,利赖甚广,办理团练,里闾获安。二十八年停罢科举,以册金及公交车费拨充教忠学堂经费,复解囊助之”[11]266;“光绪戊戌年与广济医院、香港东华医院合办平粜”[13]241,等等。
方便医院,“与九大善堂办平粜总公所以济饥民”,“港澳有疫即由该院董事每日到轮船迎接病人”[13]235,等等。
在广东省外的慈善活动,九善堂亦参与其中。
广仁善堂就曾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广西灾情登报请求救济。“申报函:三月二日筹解头批赈米三十五万八千二百斤。三月二日被灾甚重,连接梧、柳、浔、桂、平、龙等纷纷告急谓草根食尽,鬻子过地,饿殍载道,目不忍睹,请即再筹接济……”[16]。
述善堂曾向广西捐建风雨亭,其记曰:“广西若盗乱既然三年,乃请于□□朝弥盗必先振荒使人不盗,乃请□□颁帑,乃盗贼旱溢,有振有邙……述善堂者,诸善堂之一,既□振若干石,又贷子农责成远付之,西怀远墟千里之间,四五里则为一亭……”[17]。
崇正善堂曾代他人向琼州灾情捐款。“琼州叠灾,所刊求唳告白,令人不忍卒读,而省中各善堂合力劝捐,闻初二日有一人乘坐肩舆至十一甫崇正善堂与绅董相见,某董议及琼郡灾延数月……其人闻而愀然,即在囊中取银数千元交堂中值理……”[18]。
再有川蜀之地洪水为灾、生灵涂炭,“爱育堂不忍坐视,于初一日将谕单所开川民苦况情形标贴门前,劝捐施赈,不设录簿,亦不沿门题。”[19]
当然,九善堂的救助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广州作为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在鸦片战争之后,大批洋商、传教士、外国学者来到这里,他们或是创办学校,或是兴建医院,或是创建教会慈善机构(如两广浸信会),带来了近代化的管理方式和创办经验。在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影响下,广州传统的慈善救济活动也发生了变化。除了原有的施粥施药、收养难民等活动之外,各善堂增加了培养人才的内容,开始注重“教养兼施”。如方便医院就曾设立了一所附属高级护士职业学校[20]263,爱育善堂创办义学,教其读书识字以便营生等[21]。
九善堂广行善事,美名遍及全广,时人不乏夸赞。如:“两粤广仁善堂广设讲堂启迪庸昧,诚足□怡目注善心悠扬”[22];“城西十九甫爱育善堂好行善举,施医、施药、施棺、课童各等事美不胜言”[23];“省城西十七甫爱育堂施药施赈,历久长新,另开设义学至今二十余载,人皆称羡不已”[24],等等。
作为广州七十二行商代表的九善堂,往往与广州商会共进退,以行商—善堂—商会三点一线构成的商人网络在清末民初的广州参与了大量的地方公事。双方相互配合,在举办地方公益、推进地方风俗变化等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绩。
三、广州十三行商后代参与九善堂活动
作为广州十三行覆灭后的延续,广州七十二行仍以广州下九甫的文澜书院为主要阵地,遇到紧急事务需要商讨时,本质上由商人自发组织而成的广州七十二行就会聚集到文澜书院。据史料记载,“文澜书院在太平门外下九甫绣衣坊,国朝嘉庆十六年西关绅士呈请创建,深四座,广三间,右为清濠公所,左有巷外,巷外为清濠公所公产。房屋平列八间深,各六座,前界绣衣坊,后界洪恩里,计得屋十二间,另有屋一间在徽州会馆界内,未经以囘,合计屋十三间,均为洋行商人捐送。”[25]250文澜书院兴建之初,伍怡和行、叶双观行、卢广利行、潘敬德堂四大行商都有所出资,并捐送了部分田产[26]4。鉴于一部分广州十三行商的后代仍参与组织广州七十二行,因此七十二行商以文澜书院作为商讨九善堂事务的重要场所,倒也算得上一脉相承。以文澜书院为中介场所,以九善堂为重要机构,鸦片战争后的广州七十二行商人重新建立起了联系。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十三行商开始走向分化。其一是留在广州的一部分行商或是仍从事着茶叶贸易而改称“茶行”,或是从事于丝绸、布匹、杂货等行业,并逐渐成为广州七十二行中的一员[11]332;其二是行商、买办远赴上海等新开埠的通商口岸,重新建立起与外商的商业联系[27]94。不管是留在广州或前往上海,昔日的广州商人们依然热衷于广州的慈善事业,并通过九善堂传递着爱心。
在广州十三行时代,行商们时常需要向官府“捐输”与“捐纳”。行商在凭借垄断对外贸易特权而获得巨大商业利润时,封建官府必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义务。鸦片战争前,十三行商对军需、河工、修路、赈灾、济贫、助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捐资,如道光元年(1821)伍怡和行与卢广利行合捐十万两将桑园围改筑石堤、兴建文澜书院等[6]574。因此,在广州十三行不复存在后,十三行商的一部分社会责任开始转由七十二行商来承担,九善堂恰是七十二行履行其社会义务的重要机构。
而广州十三行后代也能踏着祖先的足迹继续前进,其通过九善堂参与慈善活动的案例在史料中也可发现。如同文行的创始人潘振承的第五代传人——潘佩如,此人又名潘宝珩,是潘正炜四子的孙子,在清末曾候选知府花翎二品顶戴三品衔,查阅“倡建两粤广仁善堂总理芳名列”[13]231,潘宝珩一名赫然在列。再如天宝行梁经国之子梁纶枢,曾在官府中担任官职,后因赴省乡试皆不第,开始全力接手天宝行从事商业活动,在后来的史料中也可以找到他参与善事的记载,广州沙茭总局的创办他多有出力,“慈善义举,网不实力奉行,复兴邑绅梁纶枢、潘亮功等,筹设沙茭总局,排难解纷,弭患无形,乡人德之,年七十二卒。”[11]354查“倡建两粤广仁善堂总理芳名列”[13]231,“梁肇恺”一名位于其中,此人正是天宝行梁经国之孙、梁纶枢之次子。盖梁肇恺承袭其父之风范,热衷于慈善事业。潘佩如、梁纶枢等人都属于具有商人、官员两种身份的士绅阶层。一般来讲,绅士多是地方上有名望、有势力的地主或退休官僚。他们或通过捐纳功名而获得绅士身份(如伍崇曜),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或通过家世取得。地方绅士大多绅商兼具,既获得了封建社会的政治身份,又是大商人、大地主。由此可见,九善堂虽然以商人为主体,但个别善堂也有集绅、商于一身的民间人士参与。
五口通商后,大批广州昔日行商、买办纷纷奔赴上海等通商口岸寻求商机。上海在开埠后的第十年,外贸总量超过广州位居全国第一。大批广东商人、买办前往上海,是其获得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众多在上海的广东商人很快联合起来,并组建了同乡组织——广肇公所。“广肇公所,在二十五保三图公共租界海宁路。同治十一年,粤东广州、肇庆两府人公建。另设广肇义学,并设广肇医院、广肇痘科分医院。又,广肇山庄,初在新闸大王庙,后嗣迁闸北叉袋角广肇里”[27]140。
作为由广州、肇庆两地商人创办的同乡组织,广肇公所也曾对九善堂有过资助。《申报》中有几则新闻可证明在沪经商的广东商人曾捐助过九善堂。如1885年7月11日《代收粤赈助款交广肇公所转解数》:“德生义助来鹰洋十元……”[28]。再如1885年7月19日《上海广肇公所经解粤省爱育堂赈款开列》:“第一批五月二十五日汇寄二千两,第二批五月二十八日汇寄银二千两,第三批六月初四电汇港解西商捐英洋六千元,第四批六月初五汇寄银二千两,嗣后随手□解为报闻”[29]。爱育善堂也曾登报感谢在沪广肇公所商人的捐款,如1885年7月25日《上海文报赈寓抄登爱育堂复信》:“诸位大善长先生大人阁下五月二十六日奉到第一号赐函当经奉复,又于本月初二日接到五月二十三日来函,第二号来函并由宁波轮船载来白米□百五十四石……”[30]。又如1885年7月26日《广东爱育善堂绅董复上海施封翁书》:“敬复者昨奉赐函如亲大教并蒙尊处惠助赈济洋银四千元……,大善长大人闻望日隆德棋复大普济各省灾难,何止恤邻,广行无量……”[31]。
因此,在社会剧烈动荡、变革的时代,许多昔日行商后代仍参与广州七十二行创办的九善堂活动,作为清末民初广州慈善事业的重要载体,九善堂在省内外开展了多项慈善活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官方救济系统贫乏无力的状态,并在客观上促进了广州慈善事业的近代化。
四、余论
综上所述,作为广州十三行覆灭之后的又一商人群体,广州七十二行建立了九大善堂,十三行后代可通过其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开清末广州善堂民办化之风气;同时它又履行了社会义务,在社会局势动荡、民不聊生的情况下,缓解了广州地方官府的慈善救济压力,成为广州社会救济活动的有力补充。
1952年,方便医院由广州人民政府重新规划,扩大院址,改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1954年,惠行善院由广州市公益社团联合会接收、统一领导,后来改为广州市公益社团联合会第一诊所,继续为市民服务;1955年,润身善社由市公益社团联合会统一领导,停办医务,改为荣华街小学,后又并为中山三路小学荣华校区[32]。九善堂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他各善堂,或因经费不足停办,或改建成小学、市场,但不管如何,九善堂始终都是广州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