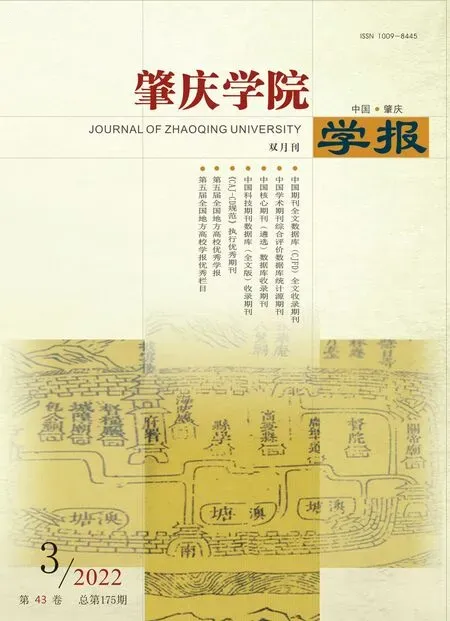释“言不必信”:传统儒学视野下的守信问题
王 格
(上海财经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433)
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生活共同诉求的一种基本美德,也是一个正常运作的社会所必须广泛采用和遵守的规则。在康德哲学中,不说谎是一条“可普遍化”的原则,所以是“定言令式”,即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人们都不应该说谎——康德以此排斥了任何哪怕迫不得已的假承诺。但是,这只是一种哲学抽象理论上的推演,在现实生活世界的考虑中,似乎多少有些不近人情。很明显,一旦落实到具体生活世界中,善意的谎言和不得已的假承诺随时都可能会以一种非常正面的情形出现,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大都会乐意去接受。
一、“信近于义”——儒学视野下的守信难题
儒学传统十分重视“信”,在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论语》一书中大量论及“信”,孔子甚至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政治上则是“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汉代大儒董仲舒将信与仁、义、礼、智一起列为“五常”(《贤良对策》),从此成为中国儒家道德文化的重要纲维。
在今天一般看来,守信就是讲信用,就是一诺千金。可是,先秦主要儒家学者却似乎并不这么看。在《论语》一书的记载中,孔子虽然多次强调“主忠信”,强调朋友有信,而且孔子反复强调的“慎于言”大概也包含着守信的层面,但是,孔子对一味守信似乎并不太赞赏,甚至有明显贬低的意味,这一点从“子贡问士”章可以看出: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胫胫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1]
在此,孔子把“言必信,行必果”这样一种在常人看来理应受到褒奖的人给予了比较低的品级,被看作“小人”,虽然不一定特别低,可能也还可以勉强算作“士”。《论语》中还有一处在解读上有些模糊可疑:尾生可能是一个忠实守信、一诺千金的典型人物,但孔子却对他评价不高。而在另一处,孔子的弟子有子明确地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言外之意是,如果“信”(承诺)背离了“义”,那么是不可以去兑现承诺的。孟子大概是有见于此,所以才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即“义”更为根本。荀子亦然,他指出,“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荀子·强国》),这是为政层面上的。总之,在有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学者看来,“义”跟“信”是有交叠的两件事情,有义而不信的,也有信而不义的,但二者取舍时我们应当选择义而不信。也就是说,“义”对“信”是有优先性的,要成为“信”的准则和依据所在;如果守信的行为将要违背义,就可以通过不守信以成全“义”。这是儒学对其守信的理论原则进行抽象论说的起点。
“义”也是儒家最核心的价值观念之一。早期的“义(義)”字可能与威仪有关,但周代以后,“义”便开始确立其道德哲学的独特意涵,并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为诸子百家争相论述的核心概念之一[2]。就儒家传统而言,《中庸》明确有所谓“义者,宜也”,宜是合宜,处理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亦即是应当如此的意思。“应当”和“不应当”构成了伦理学的基本判断,即所谓“应然”,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出现“不合宜”的“实然”状况相对。因此,我们今天经常使用的正义、道义、见义勇为、义不容辞、大义凛然等语词,所关涉的都是直接与“应当”相关的问题。在与情感相关时,有“仁义”;在与理智相关时,有“理义”;在与仪式、节目、制度等形式相关时,有“礼义”;等等。
可是,“义”虽然如其字源学涵义一样,表明是一种权威性的尺度,是对人们行为的绝对评判,但落实到日常经验中时,它却往往缺乏客观化的准绳。在康德哲学那里,行为的“可普遍化”构成了“义”之于“信”的尺度性作用,从而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客观化。而“义”在儒学中难以做到外在的客观化,特别是在孟子的“义内”说作为主流的儒学传统中,判准的主体内在性决定了实际运用上会有诸多的麻烦。这个难题大致上可以说是:“权”作为与“经”相对的一个大原则,一方面给予处世应事中随时而变的活动性,让人们在生活中不会因为哲学而走极端;另一方面,“权”与“经”之间的张力,特别是“权”的尺度问题却是在抽象论说中摆脱不了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困境,甚至留下重重“潜规则”生长的空隙。作为内在准绳的“义”,似乎无法成为一种可以外在言说的客观化尺度。如果更加形象地表述,一端类似于刻舟求剑,另一端类似于见风使舵,二者之间怎么把握,是儒家伦理处境中人们如何立身处世的难题。这一论说困境不断地困扰后代儒者,具体就“信”而言:如果守信这件事是可以权变的,那么作为其尺度“义”究竟如何约束这些可能出现的权变?
二、“谨之于始”——抽象的解决
在一次“策问”中,朱熹给学生出过这样一道考试题:
问:忠信所以进德,而夫子之所以教,与夫曾子所以省其身,亦无不曰忠信云者。而夫子又斥“言必信行必果”者为小人。孟子亦谓“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二端异焉。然则学者将何所蹈而可?将不必信且果者耶,则子路有欺天之失,微生有乞醯之讥。将必信且果耶,则硁硁之号,非所以饰其身也。二三子其扬榷之。[3]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展示,到底该不该守信,在《论语》《孟子》文本中似乎出现了一些前后矛盾之处,朱熹考问学生该如何理解。本节我们将考察朱熹本人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
朱熹对“信”的阐释集中在对《论语》“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一句的解释:
此言人之言行交际,皆当谨之于始而虑其所终,不然,则因仍苟且之间,将有不胜其自失之悔者矣。[4]73
“言必信”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杜绝虚假言语,另一方面是践行诺言。朱熹强调的是“谨之于始而虑其所终”,即从一开头的言语就要谨慎,他认为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最后不论是否去践行都不好。在《四书或问》中,朱熹有更直接的表述:
人之约信,固欲其言之必践也,然其始也,或不度其宜焉,则所言将不可践者矣。以为义有不可,而遂不践,则失其信;以为信之所在,而必践焉,则害于义,二者无一可也。[4]629
由此可见,朱熹坚持“信”本身的意义就是践行其言,并认为这种要求是无条件的;不管怎样,“失信”都是不好的。在朱熹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可不可以不守信”的问题,只是在于最初的言之不慎,避免“言之不慎”的方法是要“虑所终”。朱熹在与人论学的书信中指出: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未可便说言不必信,盖言欲其信,然须是近义然后言可复,而能全其信,此正言虑所终之意也。[5]
由以上可知,在这个问题的解答上,朱熹与康德的确有共通之处,强调守信具有绝对性,朱熹坚持“言而无信”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出现都是不可以的,或者至少是不好的。而朱熹所谓“虑所终”虽然不一定是康德所言的“普遍化”,但也有相通之处,朱熹的“虑所终”强调的是承诺之前必须考虑最终执行诺言时是否“合义”。因此,对于“信近于义”的“近”字,朱熹给出创造性诠释,认为说“近”就相当于说“合”:
问:“‘信近义,恭近礼’,何谓近?”曰:“近只是合,古人下字宽。今且就近上说,虽未尽合义,亦已近义了;虽未尽合礼,亦已近礼了。”[6]768
如果会出现不“合义”,一开始就不可给出任何承诺,这样才能避免“所终”可能会面临的“二者无一可也”的两难状态。可以看出,朱熹强调绝对的守信,而这一点先秦儒家学者们可能并不认同,除了上一节提到的孟、荀的论说,《左传》中还记载有一段叶公对胜的评论,其中将“信”作出了不同流俗的重新界定:
子西欲召之,叶公曰:“吾闻胜也诈而乱,无乃害乎?”子西曰:“吾闻胜也信而勇,不为不利,舍诸边竟,使卫藩焉。”叶公曰:“周仁之谓信,率义之谓勇。吾闻胜也好复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复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左传·哀公十六年》)[7]1947-1948
叶公认为,真正的“信”不是说出去的话就一定兑现,就像真正的勇敢不是以卵击石去送死。正如前文已经提到,“复言”不一定是信,因为根据孔门弟子有子的观点,只有“信近于义”的情况下,言才“可复”。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当时儒学已经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影响力,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叶公对作为德性范畴的“信”以及“勇”给出重新界定,也可能是展示了基于儒家守信观的一种哲学解答:将仁、义提到高一层次,对普通人所谓的信、勇进行约束,认为这样的“信”和“勇”才是真正的(即具有道德价值的)信和勇。可是,朱熹并不愿意重新界定,他对此作出如下的评论和解释:
或曰:然则叶公所云“复言非信”者,何耶?曰:此特为人之不顾义理、轻言而复者发,以开其自新之路耳。若信之名,则正以复其言而得之也。今不警其言不尽义之差于前,而责其必复其言之失于后,顾与信之所以得者而乱之,则亦矫枉过其直矣。诸家乃引之以释此句,以为信不近义,则言有不必复者,是乃使人不度于义而轻发其言,以开诞谩欺伪之习,其弊且将无所不至,非圣贤所以垂世立教之旨意也。[4]629
朱熹将叶公的论述看作是有针对性的策略性教诲,但这其实与《左传》原文的语境并不合。朱熹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警其言不尽义之差于前”,非常严厉地批评诸家由此而“以为信不近义,则言有不必复者”的解释开启了极大的弊端:欺伪。朱熹对《孟子》中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一段,则是紧紧抓住“大人”二字进行调和和圆场:
问:“‘大人言不必信’,又如何?”曰:“此大人之事。大人不拘小节,变通不拘。且如大人不是合下遍道,我言须是不信;只是到那个有不必信处,须著如此。学者只要合下信便近义,恭便近礼。”[6]775
众所周知,与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孟的讲法不同,理学家的思想是具有高度理论体系性的,他们所探讨的是可以作为行动准则的条理化的“理”。朱熹所采取的规则是,严格遵守“言必信”,但将“义”的作用提前,作为承诺与否的判准,而不是履行与否的判准——这当然与孔子所讲的“慎于言”是一致的。所以,按照这种标准,生活中是不能轻易给人很多承诺的。如果进一步严格推衍并且去执行,那么朱熹哲学将会与康德伦理学一样,极端的情况是成为一门高度形式主义的伦理学,不具有生活世界的高度实践性。当然,这只是朱熹守信论说的直接推演,而作为儒家的朱熹绝对不会真的这样,他会去避免极端情况。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朱熹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论说逻辑上自洽性的追求。
当然,并不是每一位理学家都会选择朱熹的解决方法,心学的思想家大概大多不会同意朱熹对“言必信”的遵守。比如,与朱熹截然不同,晚明王学的周汝登(1547—1629)在其《四书宗旨》中这样解释《孟子》这句话:
有意便是必,无必便是义,义亦强名,在亦无所,若有义有在,则非义之义矣,大人勿为。[8]
周汝登显然是将王学“四无”下的工夫论思想注入其中,以一种超越对待的论说,进行了另外一种创造性的哲学阐发,但那最终将可能取消世俗的道德价值。
三、“要盟不信”——具体的处境
据说在孔子身上发生的与守信相关的一个最著名的案例便是“蒲人要盟”事件,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
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9]
孔子在这里单方面毁约,不遵守已给出的承诺,给出的理由是“盟”的性质为“要盟”。所谓“要盟”,是指一方在另一方要挟之下强迫签订盟约,孔子以此为由对此采取不遵守的态度。北宋理学家二程兄弟对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所记载的“蒲人要盟”的这段历史曾表示过质疑:
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为,况圣人乎?果要之,止不之卫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将何辞以对?[10]16
但在另一处,二程却也正面提及了这件事:
盟可用也,要之则不可,故孔子与蒲人盟而适卫者,特行其本情耳。盖与之盟,与未尝盟同,故孔子适卫无疑。使要盟而可用,与卖国背君亦可要矣。[10]72
这段话是将“蒲人要盟”作为论述要盟不可用的依据,而末尾的“卖国背君”一语似乎透露出很可能有非常特定的话语背景,即大概会与当时北宋国家政治外交上的“要盟”有关。而这两处的截然不同评论,大概是缘于不同的话语场景,这其中正可透露给我们更可能的信息是:也许在二程看来,究竟选择守信与否,要看当时的具体场合进行忖度——大义凛然之下,可以要盟不用。
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对于“要盟”为什么可负,孔子给出的理由是“神不听”。在春秋时代的国际外交中,也有人认为这样的盟约是可以不具有约束效应的,比如《左传》记载:
楚子伐郑,子驷将及楚平。子孔、子蟜曰:“与大国盟,口血未干而背之,可乎?”子驷、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强是从。’今楚师至,晋不我救,则楚强矣。盟誓之言,岂敢背之?且要盟无质,神弗临也,所临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临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左传·襄公九年》)[7]1006
这里子驷、子展为“背盟”行为辩护的一大段说辞,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从盟约上去抠字眼来看,并没有真正的违约;其次才是“要盟可背”的问题。也就是说,“要盟不信”这一条原则也并不能构成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因为辩护者第一步的辩护是试图论证没有真正违背盟约内容,只有退一步的辩护理由才是“要盟不信”。与孔子的说法一样,这里“要盟不信”依据同样是“神弗临”,大概是因为古人“盟”的时候是对天神起誓的,违约会受到来自天神的惩罚。天神作为正义的象征成为了一个更高的约束力,允许了在听命于天神的情况下可以违背人间的盟约。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指出了“神临”与否的依据和理由“所临唯信”,并接着对“信”作出了一个道德价值判断上的界定——“言之瑞,善之主”,这当然反映出先秦儒学背景下,将作为原始信仰的人格神向作为“价值之源”的神的转换。“仁”和“义”作为价值居于神的地位,具有了神圣性和绝对性,因此才有了“义”之于“信”的优先性地位,这样的“信”(包括在某些情况下的“不信”)方才具有道德价值。易言之,儒学中“义”作为一种内在尺度,其根源是具有神性的。
有趣的是,北宋苏辙在《论刺客》一文中,认为《史记》对刺客曹沫事迹的记载可疑,他提出的理由有:(一)曹沫是“知义”之人,不该“要盟”;(二)如果真有其事,就应该是“要盟”,但《春秋》的记载为“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盟”的“要盟”性质,不符合《春秋》体例[11]。这当然是苏辙多少有点牵强的反驳,但从中可以看出的是,“要盟”的性质判别,以及对“要盟”的态度是很难一概而论的。可是,究竟何者为“要盟”?如果一切可被视为不平等的盟约都可以废除而不承担的话,那么“普遍化”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要盟”因此甚至可成为“背信弃义”的托辞。在唐代元稹《莺莺传》中,张生始乱而终弃,崔莺莺在给张生的信中就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12]当然,这只是崔氏的书信婉辞,抛开其他问题的争议,以“要盟”为由为不守信的行为辩护,这种用法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同时,我们马上可以联想到,如果反过来是张生给崔莺莺的信,“要盟”可能就成为一种被滥用的借口,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面对一个具体场景、具体事例的处理方式,作为个案会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如果将其抽象归纳成一条简单的“准则”而普遍推行,则可能会出问题,因为很多事件的具体情况会复杂得多,往往因时因地而变。
四、结语
在儒家视野下,“权”作为一种高度智慧,其依据是“义”,所谓“义不容辞”,发源则是“仁”。儒学中仁、义在一种很宽泛的意义上成为道德价值的根源,但它们本身并没有实质内容。在宋明理学的语境下,这种本源是“天理”,所谓“天理难容”。在这个意义上,理学家的仁学即理学。但是与此同时,儒家伦理要密切落实到日常生活中,这种落实表现在与“权”相关的问题并不作为抽象而被阐释和探讨,而是具体的场景具体地应对,天理、良心等因此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易言之,“权”是在天理(义)大背景下的随时权变。虽然今天的学者也可以在一种较弱的意义上通过类型学的方法从中归纳出若干“类型”[13],可是,“类型”的指导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具体的场景可以有千万种的不同。因此不难理解,在儒家论说中,“权”往往被看作是一种很高的智慧。孟子举了若干事例对“权”进行阐释,如“嫂溺援之以手”“紾兄之臂而夺食”“逾墙搂处子”等(参见《孟子·离娄上》《告子下》相关文段)。在每一件具体事例中,基于特定时空下的文化背景,大多数是比较容易选择的,但如果从中归纳出规则,却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前文已经提到,在儒家思想中,“义”是具有某种神性的道德约束力,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儒家传统的“义”失去了原有的超越性制约,而成为此岸的、现实的利益考量,“义利之辨”的基础变得十分岌岌可危。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守信的抽象论说很容易沦为一种游戏规则,而失去其原来的崇高道德价值。
另一方面,追求普遍化的哲学与我们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似乎始终处于一种“不离不杂”的关系中。比如,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说谎了,可能是出于善意的谎言,也可能是上文说到的“要盟不信”,但这种事件却并不会作为一种简单抽象的规则通过普遍化而产生恶果,相反,它们还会造成局部的美好和正义,这一种复杂的微妙,不能用简单的规则来概括,因为每一个具体的事例往往有其复杂的时空背景。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曾经这样说:“有一种神秘的感觉驱使哲学家从抽象思维转向直观,那就是厌烦,就是对内容的渴望。”[14]历史上儒家学者们的思考也总是在这抽象思维与内容直观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