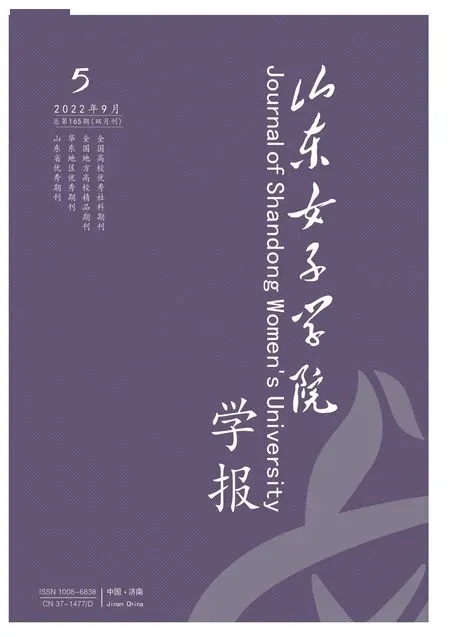在性别与阶级之间:论何殷震的妇女解放思想
章舜粤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09)
妇女解放问题是近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之一,妇女运动是近代中国诸多社会运动中的重要一环。一般认为,强调妇女解放与阶级斗争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特点。如有论者即指出:“十月革命后,随着他们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化,他们的妇女解放思想也随之变化、发展。他们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代替资产阶级人权平等学说作为分析中国妇女问题的理论武器,帮助中国的知识妇女认识到只有投身社会革命,和劳动妇女相结合,才会获得妇女运动的发展。”[1]67但事实上,将阶级斗争理论和妇女解放理论融合起来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者何殷震。她在强调妇女解放运动中的阶级斗争属性时又强调阶级斗争中的妇女身份,亦即同时由“性别中的阶级”和“阶级中的性别”出发,试图走出一条以阶级革命瓦解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女界革命之路,从而在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女权主义论述中显得独树一帜。近年来,她独特的理论贡献已逐渐为学界所重视(1)例如刘禾、瑞贝卡·卡尔、高彦颐等人指出,何殷震以“男女有别”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形态、私有制、雇佣劳动和改头换面的性别奴役”,对于当今跨国女权主义的理论建设工作具有方法论意义。宋少鹏指出,何殷震的理论具有无政府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双重特性,“使其‘女界革命’的思想具有了原创性,在晚清主流女权论述中独具一格”,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今天仍有理论价值。而刘人鹏认为,何殷震的思想与中国台湾20世纪90年代后性/别运动隐然有所呼应。见刘禾、瑞贝卡·卡尔、高彦颐:《一个现代思想的先声:论何殷震对跨国女权主义理论的贡献》,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5期;宋少鹏:《“西洋镜”里的中国与妇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刘人鹏:《〈天义〉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视野与何震的“女子解放”》,载《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2期。。本文拟梳理何殷震以阶级理论寻求瓦解资本主义父权制根基之路的思想,并予以相应之分析与评价。
一、将“男女革命”纳入阶级斗争理论的视野
何殷震,江苏仪征人,又称何震,因为反对“用父姓而遗母姓”的男女不平等传统,她同时采用父母姓氏,自称何殷震,在其主编刊物上往往以较小字号,并列何、殷二字[2]819。1907年2月13日,何殷震及其夫刘师培,听从马君武建议,应章太炎之邀请赴日本东京参加同盟会《民报》的工作。他们在日本与亚洲各国的革命者来往甚多,后深受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人影响,成为无政府主义者。1907年6月,何殷震组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6月10日,何殷震作为编辑兼发行人,开始出版《天义》作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后经无政府主义者张继介绍,刘师培、章太炎和幸德秋水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讲习所”,《天义》慢慢也变成了“社会主义讲习所”的刊物[3]81-82[4]。
男女之不平等,是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普遍认识到的社会现实,但如何解释男女不平等的起源、现状以及应采取怎样的破解之道,则各有看法。何殷震可能是最早将中国妇女解放纳入阶级斗争范畴之中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之一。1907年7月,她开宗明义地在《天义报启》中指出,从古至今的所有社会,均属不平等的阶级社会:“地球之上邦国环立,然自有人类以来,无一事合于真公。异族之欺陵,君民之悬隔,贫富之差殊,此咸事之属于不公者也。自民族主义明,然后受制于异族者,人人均以为辱;自民约之论昌,然后受制于暴君者,人人均引为耻;自社会主义明,然后受制于富民者,人人均以为羞。由是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遂为人民天赋之权。然环顾世界各邦,其实行种族革命者倚占多数,若政治一端,虽实行共和政治者,犹不能尽人而平等,经济一端更无论矣。试推其原因,则以世界固有之社会,均属于阶级制度,合无量不公不平之习惯相积而成,故无论其迁变之若何,均含有不平之性质。”[2]818换言之,她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造就的民族与国家不平等、封建制度造就的政治权利不平等、资本主义制度造就的经济不平等归因于“阶级制度”。尤须注意的是,何殷震虽然认可阶级理论对各类不平等现象的解释力,但仍毫不留情地批评这些“同道中人”缺乏性别视角,没有意识到男女不平等亦是一种不平等之“阶级制度”:“顾今之论者,所言之革命,仅以经济革命为止。不知世界固有之阶级,以男女阶级为严。无论东洋有尊男轻女之风也,即西洋各国号为男女平等者,然服官议政之权,均为女子所无,则是女子所有之权,并贱民而不若。更反观之于中国,则夫可多妻,妻不可多夫,男可再娶,女不可再嫁,服丧则一斩一期, 宾祭则此先彼后。即有号有均平者,既嫁之后,内夫家而外母家,所生子女,用父姓而遗母姓,又安得谓之公平乎?夫男女之间,其制度失平且若此,于此而欲破社会固有之阶级,不亦难乎!”[2]818-819
何殷震鲜明地将阶级视角引入性别问题之中,尽管她所批评的“今之论者,所言之革命,仅以经济革命为止”可能并不确切。事实上,梁启超早在1899年便曾在《论强权》中提到男子对妇人有“强权”,正类似资本家与劳动者的阶级关系:“今日资本家之对于劳力者,男子之对于妇人,其阶级尚未去,故资本家与男子之强权,视劳力者与妇人尚甚远焉。故他日尚必有不可避之二事,曰资生革命(日本所谓经济革命),曰女权革命。经此二革命,然后人人皆有强权,斯为强权发达之极,是之谓太平。”[5]354可见,近十年前,梁启超便曾以女权革命和经济革命作为未来平等世界的必经之道。但在梁启超看来,弥平资本家与劳动者之不平等的经济革命与弥平男女不平等的女权革命是并举的两种革命,二者之间没有密切关系。
何殷震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不仅提出“非破坏固有之社会,决不能扫除阶级,使之尽合于公”[2]819,而且更进一步将阶级斗争与妇女解放结合在一起,指出“故欲破社会固有之阶级,必自破男女阶级始”[2]819。因为男女阶级制度最为顽固、压迫最为深重,所以她主张由打破男女阶级入手,破坏阶级制度:“夫以男女阶级之严,行之数千载,今也一旦而破之,则凡破坏社会之方法,均可顺次而施行,天下岂有不破之阶级哉!”[2]819换言之,她将男女革命内嵌于整个社会大变革中,“把破‘男女阶级’视为开启一切革命的起点,贯穿诸革命过程,也是革命的终点”[6]153,指出“夫居今日之世界,非尽破固有之阶级,不得使之反于公;居今日之中国,非男女革命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亦不得合于真公”[2]819。因此,可以说何殷震虽不是中国最早用阶级话语解读性别问题者,但却可能是最早将男女革命纳入阶级斗争范畴,并将其置于全体人类的解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的思想家。
二、同时注重“性别中的阶级”和“阶级中的性别”
何殷震何以突破梁启超等人割裂地看待经济革命与女权革命的观点,而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这与她对妇女受压迫起源的认识密切相关。
何殷震指出妇女受压迫起源于阶级制度。她认为,原始社会实行原始共产主义,男女较为平等:“试观太古之初,人民于共产制度外,兼行共夫共妻之制,未尝以财产为私有,亦未尝以女子为私有也。”[7]197她将妇女之受压迫起源于财产私有制及由其衍生出的阶级压迫:“及人民欲望渐萌,欲去他人之财产为私有,并欲取他部妇女以为一己私有物……是女子私有制度之起源,与奴隶制度之起源,同一时代,均共产制度破坏之时代也。”[7]197-198何殷震特别强调婚姻关系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发生变更,“贫富之级既严,由是,男子由奴隶之制度进为农奴之制度,由农奴之制进为今日雇工之制;女子由掠夺结婚之制进为买卖婚姻之制,由买卖结婚之制进为今日一夫一妻之制”[7]197-198。这就把私有制的产生、生产关系的变更与“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联系起来[8]68。
何殷震指出,自资本主义工场生产以来,妇女在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产品无法与机器大生产相竞争,且不再占有生产资料,“生产机关遂为富民所独握,致贫女所劳之职业鲜克支持,不得不为富民司工作。”所以原有的家庭妇女不得不脱离家庭,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者:“为女子者,不得不仰资本家之鼻息,以投身工场,而昔日家庭之女王,遂为赁银制度所束缚,以为赁银劳动之人。”[7]112
此前的中国女权主义者主要从“性别”的角度着眼探讨男女不平等问题,往往强调妇女共同的“女子”身份,将妇女作为一个被压迫的整体,从而要求争得与男性一样平等的权利。而何殷震在指出作为性别的妇女在整体均是受压迫者的前提下,点出前人所忽视的“性别中的阶级”问题。
她指出,妇女中也有社会上层和下层的阶级分别,而女工等劳动妇女是妇女中受压迫最为深重的群体:“中人以上之家,女子舍育子、治家而外,鲜事工作。……惟中人以下之家,鲜克支持,为女子者多自食其力,或从事农作,或出为雇婢,其下者则为娼妓”[7]134,而卖身于“富民”的贫女,“所罹之苦,罄竹难书”“生杀之权”却全然操于同为妇女的“主妇”之手[7]111。即便在限于困厄的贫苦妇女中,也可分为四等,“最下者为娼妓,稍进则为妾御,又稍进则为婢仆(此指鬻身者言),进而愈上,则为雇婢及女工。”[7]115她指出,正如男界中分贫富阶级之外,“女界之中,以贫民占多数,或为工女,或为雇婢,其衣食亦仰给富民”[7]140。有的富豪之妻妾,置装、化妆的花费抵得上贫户数年之用,她们养名犬、乘豪车、饰艳服等等,“而制纱各厂之女工,则垢衣恶食,日受鞭挞”。何殷震问道,“则贫女之陷于此境,孰非尔等贵女所掠夺?”贫苦妇人没有饭吃,“各衙门、各公馆里面,做太太、做小姐的,何等阔气!”[7]168“孰非由于财产之不均乎?孰非由于资本家之罪乎?”[7]112
何殷震不仅重视“性别中的阶级”,同时也敏锐意识到“阶级中的性别”,指出女性无产者之痛苦,还受传统男女性别秩序之深刻影响。她哀叹:“今世界可悲、可惨之境,无过于劳动者,而劳动者中,舍少年劳动而外,即以女子劳动为最苦。”[7]290由于资本主义工场(工厂)所生产的物品并非民生日用所必须,导致民生日用品价格攀升,使男性工人的工资“不足以赡其身家”,为了维持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因此逼迫家庭妇女参与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来,“出而谋食,以供朝夕之需”[7]112。且赤贫之女既无可能占有机器等生产资料,“复无入学之资”,所以“女子失业者必日众”[7]115,从而使女子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处于弱势地位,成为廉价劳动力,以至于在全球范围内,女工的数目甚至接近男工的两倍[7]113。
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女工除了在工厂做工,“于家庭为妻、为母”,还要承担养育子女和家务劳动的重任,“彼之劳动,终夕不休”[7]113。更令何殷震愤怒的是,“资本家之于女工,妨其日力,害其健康,弭其幸福”“役他人之力,以生一己之财;既迫人于贫,又利用其贫以增一己之富”[7]119,不仅“以女子为生财之具”[7]113,更借此把女子当成“玩物”乃至“用物”“复以丑恶之行而败其节操”[7]119。正因为女工工资之低,于是往往“于工作之外,兼业卖淫,以补其不足”,或成为婢女、小妾,但还要因此承受污名[7]117-119。何殷震不由得感慨,“今日之制度,则劳力、辱身之苦,毕集于贫女之一身”[7]120。
总之,何殷震一方面强调“性别中的阶级”,即从阶级的观点看待性别问题,指出妇女受压迫的来源是私有制和阶级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深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且同为妇女亦有阶级之别。另一方面,也强调“阶级中的性别”,从性别的观点看阶级问题,指出在资本主义父权制下,妇女因性别弱势更受剥削,且还要受家庭、生育、婚姻制度的多重压迫。
三、以女界革命求得解放
明晰妇女受压迫的原因之后,自然要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近代中国早期女权主义论述从“文明论”出发,认为妇女作为“国民之母”和“文明之母”,对于现代国家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自晚清开始掀起了“倡女权”“兴女学”等一系列风潮,为构建民族国家而服务。继而又有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诉求,要求男女平等,提出妇女与男子既要同担责任,亦要共享权利,确立独立地位。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下,近代中国发起了妇女参政等一系列妇女运动[6]。而何殷震既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当下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自然对上述方案有所批判,认为这无法从根本上达到妇女解放的目的。
从性别的角度看,何殷震认为男子主张“兴女学”有为“一己之自利计耳”之嫌疑。她指出,有的男子要求妇女进女校以学习手工、烹饪等技术,以至于学习师范、医学、理科等,“盖欲使女子学成之后”,可以到社会上谋得职业,赚取钱财,“以纾一己之困耳”。又因为当时的女子教育,“首崇家政一门”,女子即便不到社会上工作,也是为家庭服务,而在男权社会中,“实则家为男子之家,治家即系为男子服劳”[7]137。而女校中的伦理一科,更是从道德层面对妇女进行规训,第一认同家庭伦理,第二推崇相夫教子,第三夹杂以军国主义,“以激发女子革命之心”,事实上是为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家庭、国家服务,“非迫女子为家庭奴隶,即迫女子为国家奴隶”[7]194。
从阶级的角度看,妇女进女校学习纺织、裁缝、烹饪、造花或医学等各专科学问、技术,除了替男子赚钱之外,更维系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何殷震指出,妇女表面上得到了“赁银”(即工资),获得了(经济)独立,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独立:“然倚赖男子为生活,与依赖资本家为生活,其陷于奴隶,正复相同”。故而学习了技术而参加劳动生产,从而获得表面上一定经济独立地位的妇女,实际上是沦为了无产阶级,“非独立也,乃依赖资本家为生活者也”。从这个角度而言,参与工厂劳动的妇女和进行家庭劳动的妇女一样,均为劳动妇女,只不过一个是“为夫服劳”,一个是“为资本阶级服劳”而已,并无本质不同[7]194-195。因此,何殷震虽然不否定妇女学习文化知识的意义,却在其维护固有阶级和剥削制度这一更深远的意义上,认为这无法达成妇女的真正解放。
针对妇女争夺选举权等参政运动,何殷震认为妇女解放的“根本之改革,不在争获选举权”[7]139。何殷震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认为那不过是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已,所以“此国会政策所由为万恶之原也”。即便是号称追求社会主义,搞议会斗争的西方社会党人,尽管有不少已经当选议员、参与政权,但劳动人民受阶级剥削、压迫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劳动之民,仍屈身于赁银制度,以作富民之奴隶,虐待之苦,与昔不殊”[7]140。她点明妇女参政运动在性别口号下被遮蔽了的阶级问题,指出无论是在限制财产的少数选举还是在普选的基础下,只要存在阶级差异,“则以贫富阶级不除,贫民衣食系与富民之手,不得不媚富民也”,所选出来的无非是上层阶级的妇女而已,“其议员亦仍属贵女”[7]140。因此,即便妇女争得普选权,其结果相比过去的妇女受压迫于政府和男子之外,无非是“另受制于上级之妇人”“别增一重之压抑也”[7]141。换言之,必须看到妇女群体这一性别同一性内部的阶级差异性,在阶级制度下所争得的男女平等参政权,“不独男女不平等,即女界之中亦生不平等之阶级”[7]142。
对于妇女解放问题,何殷震给出的根本解决途径在于进行“女界革命”,而所谓的“女界革命”事实上内嵌于政治、经济、社会革命之中。何殷震所创办的《天义》,其宗旨为“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7]580,而“欲实行种族、政治、经济、男女诸革命,均自破坏社会始”[7]45-46。破除私有制及其所带来的阶级制度,在其“女界革命”理论中具有核心地位。她认为,“欲实行女界革命,必自经济革命始”,而所谓的经济革命,“即颠覆财产私有制度,代以共产,而并废一切之钱币是也”[7]204。换言之,即废除私有制,“惟土地、财产均为公有,使男女无贫富之差,则男子不至饱暖而思淫,女子不至辱身而求食,此亦均平天下之道也”[7]50。在《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一文中,何殷震更直接呼吁“实行共产”。她引述蒲鲁东的话:“财产者,掠夺也”,以白话告诉妇女们“就是因为有钱的人,把财产掠夺了去,所以弄得多数的人,穷的没有饭吃”,因此必须实行“共产制度”,才能解决问题[7]168-169。何殷震甚至以极为激烈的语气,高呼“势必实行公产”“势必排斥富强学说,势必杀尽资本家”,以解决“财产分配不平均”,才能真正解放妇女,并且解放全人类[7]115,118。
总之,何殷震等人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妇女受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将“阶级中的性别”和“性别中的阶级”结合起来,以受压迫的妇女尤其是其中的劳动妇女为革命的主体,与政治、经济、社会革命同步推进,反对现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以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不平等而达到人类的真正平等、共同解放为革命目标。这一系列论述不得不说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相融合的先声。
四、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视域下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妇女解放思想之结合
何殷震的理论著述主要发表在《天义》,而它自1907年6月出版第一号起,至1908年3月共出版了十九期,文章二百余篇,仅存在了短短9个月的时间[7]5。大约十年之后,即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一些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剖析中国妇女问题。考察他们的观点,不难发现与何殷震的思想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陈独秀指出,“照现在的经济制度,妇人底地位,一面脱离了家庭的奴隶,一面便得去做定东家的奴隶”[9]47,这与何殷震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倚赖男子为生活,与依赖资本家为生活,其陷于奴隶,正复相同”之说,如出一辙[7]195。又如李大钊评论争取参政权的自由主义女权运动所追求的“都是与中产阶级的妇人最有直接紧要关系的问题,与那些靡有财产、没受教育的劳动阶级的妇人全不相干。那中产阶级的妇人们是想在绅士阀的社会内部有和男子同等的权力。”[10]414这一观点也与何殷震批判参政运动“亦不足以济多数之工女,不过使少数女子获参政之空名而已”[7]141相类似。何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与何殷震观点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其实,何殷震等无政府主义者正是有意识地将马克思主义文献传入中国的最早一批知识分子。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李大钊等人直接受过何殷震的影响,但或许可以说他们共同从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汲取了理论资源。
1908年3月,《天义》第十六至十九卷合刊(春季增刊)中发表的《女子问题研究:第一篇 因格尔斯学说》[7]497-499,实际上即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第二章里资产阶级婚姻家庭部分的摘译,这可能是中文世界里第一份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中文译文。此外,《天义》还于1907年12月30日刊登了《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一节;1908年1月15日刊登了《〈共产党宣言〉序言》;1908年3月刊登了《〈共产党宣言〉序》和《宣言》的第一章全文[7]204,264-270,419-430。尽管在1906年,中文世界中就有大段摘引《宣言》的文献,但如《天义》这样单独将《宣言》某一较为完整的部分提出来作为理论背景的介绍,是晚清所罕见的。
在这些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阶级理论和妇女解放理论是最核心的主题,这显然体现了摘编者的理论旨趣。1908年1月15日所登恩格斯的《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之后,附有一段编者按语,盛赞“《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7]2703月所刊登的《宣言》第一章全文之前,刘师培又作序介绍《宣言》的历史,指出其要旨为“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完全赞成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观点,但对于《宣言》中介绍的阶级斗争理论却十分赞赏,认为《宣言》“复以古今社会变更,皆有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7]421。并在最后解释“绅士阀”(bourgeoisie)和“绅士”(bourgeois)等阶级斗争理论所常使用的术语时,指出“绅士阀”即为“含有资本阶级、富豪阶级、上流及权力阶级诸意义。”又解释“绅士”“系指中级市民之进为资本家者言,与贵族不同,犹中国俗语所谓‘老爷’,不尽指官吏言也。”[7]431而全文刊登的《宣言》第一章,正是《宣言》里最为集中阐述阶级斗争理论的篇章之一。又如《天义》还曾翻译哈因秃曼(今译亨利·迈耶斯·海因德曼)的《社会主义经济论》,而译者指出“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认为自从有了阶级斗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才算有了根据[7]431。
如果说刘师培更重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则何殷震似乎对其妇女解放理论更感兴趣。1907年12月30日附在何殷震《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后的《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婚姻和家庭制度一节,正是为了佐证在财产私有制度下婚姻的实质为金钱关系这一观点。因此编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虽然与无政府共产主义不同,但对《宣言》中所指出的“以为资本私有制度消灭,则一切公娼、私娼之制自不复存;而此制之废,必俟经济革命以后”这一观点深表赞同,表示这直击问题本质,“可谓探源之论”[7]205。而1908年3月刊登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节选,编者再度重申婚姻关系背后的金钱关系,“实则均由经济之关系而生耳,无异雇主之于工人也”,因此要想破除这种金钱婚姻,争得妇女解放,“必自经济革命始,彰彰明矣”[7]491-495。何殷震的多篇文章显然受此影响极深,如她指出“处贫富不均之世,娼妓、妾御之制,绝无消灭之一日”[7]119,即表明娼妓制度与私有制的根本联系。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天义》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最早出现的文本被命名为《女子问题研究》,其主旨是关于家庭的起源和私有制的关系,亦即关于妇女解放的。因此,与其说何殷震是引介了阶级斗争理论而运用于妇女解放问题,不如说她是为了说明妇女解放问题,而引介了阶级斗争理论。换言之,至少在何殷震那里,妇女解放问题是第一位的,阶级斗争理论是第二位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为妇女解放服务的。这是她与刘师培等人的巨大不同。
总而言之,何殷震是一位杰出的早期中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其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诸多论述在当时相当独特。她对“性别中的阶级”和“阶级中的性别”的关注,对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女权主义论述都是一种超越,而与若干年后的马克思主义者遥相呼应。当然,她的理论还不够成熟,也不成系统,更没有太多的具体实施方案,但不可否认的是她对此作出的努力大大推进了中国妇女解放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尽管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后来人未必都了解她的理论贡献,但其理论尝试仍在其后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有所回响。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不少她所试图解决的问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从这个角度讲,何殷震的妇女解放思想不仅有其学术史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