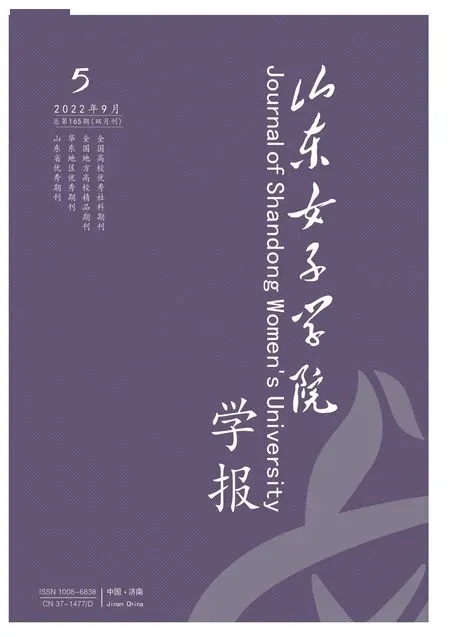路径与取向:情感史与中国古人情感
李志生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近代以来的史学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都如此。但历史的发展并非全然是理性思维的结果,情感在历史发展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有鉴于此,20世纪上半叶,年鉴学派的学者们就提议关注情感在历史上的作用。1985年,美国社会史家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与妻子凯萝·斯特恩斯(Carol Stearns)提出了“情感学”(emotionology)这一术语。其后,情感学研究蓬勃展开,并迅速成为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1)对此的讨论,参见[澳]查理斯·齐卡:《当代西方关于情感史的研究:概念与理论》,《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0期,第246~256页;王晴佳:《拓展历史学的新领域:情感史的兴盛及其三大特点》,《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87~95页。·妇女史研究·,以至在1995年,有人这样评价情感研究:“过去20年,情感研究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3;至2010年,更有人提出,当代史学已出现了“情感转向”(emotional turn)[2]237-265 [3]101。情感学研究者高调强调:“不但情感塑造了历史,而且情感本身也有历史。”[4]2
自19世纪始,西方人对中国人逐渐出现了一种刻板印象,那就是“缺少情感的中国人”(the emotion-less Chinese)[4]57;西方情感史家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没有一种把社会结构建立在情绪纽带之上的文化思想”“情感不被认为具有创造、保持、伤害或摧毁社会关系的能力”[5]185-186。的确,在古代两千年的时间里,对于情感,中国人遵从的是儒家“发乎情,止乎礼”[6]567的要求,相较于西方人,我们先人的情感表达更加含蓄,因此,从情感史的角度观察与探讨中国古人情感确实难度更大。但认为情感对中国社会并未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缺乏情感文化的看法,则是值得商榷的。通观历史我们看到,中国古人是富于情感的,只是因时间、场合、人群、性别、人生阶段、民族等的不同,他们的情感表达存在差异并更加婉转,一句话,中国古人的情感是完全能够构成历史的,他们的情感是对理性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
一、情感史的内容框架
1985年,在后现代主义浪潮推动下,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与妻子凯萝·斯特恩斯(Carol Stearns)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极具影响的《情感学:厘清情感史与情感术语》一文[7]813-836,提出了“情感学”这一历史研究的专门术语,并促成了情感史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他们指出的情感学研究内容也为后来的情感史发展奠定了内涵基础。
斯特恩斯夫妇指出,“情感学”(emotionology)一词是指情感表达的社会性,也即一个社会或一群人在某一时期情感表达比较一致和认可的方式。斯特恩斯夫妇强调,应严格区分“情感”和“情感学”这两个不同概念,“情感学”研究的是“社会或社会内部有关基本感情的标准以及人类对待社会行为规范的态度”[7]813。
情感史关注情感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比如对愤怒、妒嫉、爱情、恐惧等情绪与情感,不同社会、文化、时期都有不同规则(2)斯特恩斯夫妇就研究了美国的妒嫉史、恐惧史、羞耻史、欲望控制等情感史主题。,人们则在某一集体观念或社会通融原则下,学会与应对各种情感规则,所以,威廉·雷迪(William M.Reddy)说:“情感在很大程度上(但不是完全的)是习得的”[8]4。
芭芭拉·罗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是美国情感史研究的又一位重要学者。她反对宏大叙事,因此鉴于情感生活的复杂性,提出了著名的“情感团体”(emotional communities)理论。基于她的西方中世纪史研究,她提出关注人们在家庭、议会、行会、修道院等不同场所的不同情感表现,以及这些团体的情感准则、情感联系、情感评价和情感表达的不同,她认为,社会内部存在着许多情感行为可供人们选择[9][10]237-243。罗森宛恩的研究提示我们,社会差异下的情感取向与情感规则应得到特别关注。
总括如上理论并结合既往的研究,情感史考察的内容大致包括如下几方面:(1)某一社会、团体、人群、民族的基本情感规则,以及它产生、发展、维持、变化的时间、原因、方式;(2)某一社会、团体、人群、民族等集体应对情感规则的方式、内容与特点,以及这种应对所反映的群体生存状态;(3)个人应对情感规则的方式与结果,以及其背后的历史成因与特点,所反映的个人生存状况;(4)历史上的重要情感事件,以及它对当下社会及未来历史产生的影响。
历史上的情感多属私人事务,所以,情感心理或变化一般不会作为显性史实被记载下来,这样,欲研究情感史,就首先要面临处理史料的问题。最直接的、也是必然的第一步,就是做抉隐探微的史学考证,以从隐蔽的书写中爬梳出情感的记载。但情感史研究的史料处理绝不止于此,情感史学家的研究显示,“情感转向”与此前史学的“语言学转向”有密切关联[11],“因为如果要揭示情感表述的历史性,必须研究文本产生的语境和社会文化背景”[12]129-130。按照“语言学转向”的相关研究,语言是一种先于人的存在,它的意义不可能一目了然,所以,文本记述背后的意义、涵义与文本产生的语境,就都需要进行细致的文本探讨,以揭示出语言与文本演变背后的语境,这也是处理情感史研究史料的至重一环。
二、情感史下的中国古人情感
对于人的情感,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13]3080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七情”。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时,情的存在是一直得到承认的,即便是相对刻板的儒家经典也如此(3)对中国古代情感理论、情感史的梳理,参见李海燕:《心灵革命》第一章,修佳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5~61页;Norman Kutcher, The skein of Chinese emotions history, In Doing emotions history,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3年,第57~73页。。既然是一种社会存在,“情”也就需要有存在规则,如此,在中国古代的各个时期,对“情”就有了或礼或律的规范。比如,对于夫的纳妾,礼、律都要求妻“不妒”,也就是面对夫之纳妾或幸婢,妻不能产生妒忌之情或出现悍妒行为,否则就有可能面临被休——“七出”(4)“七出”也称“七去”,是男子休妻的七种方式,它最早出现在儒家著作《大戴礼记》中(见黄怀信主撰:《大戴礼记汇校集注》卷一三《本命》,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1388页),唐时被纳入法律,成为唐朝的法定离婚方式之一(见(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律》,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7~268页)。。而对于哀,古代赞赏失去父母时的激烈情感表达,所以在史书中,面对父母亡故的孝子、孝女,一定是“哀毁殆不胜丧”[14]1019[29]2565,4616“居丧毁瘠骨立”[15]1006[29]4910的;但对失去婚姻伴侣,则必须克制,即使夫妻感情至深也须如此,否则将不为社会所接受。像曹魏时的荀奉倩,就因丧妻悲伤过度而亡,他也因此受到了世人的嘲笑:“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热病,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16]489。以情感史的视角观察,中国古人对其所在时代的情感规则,是有着集体应对方式或个体通融态度的,这从荀奉倩的例子已可看到。下面再以几例个案进一步细致观察一下中国古人的情感及其身后的情感史历程。
第一例个案是项羽。作为一代骁雄,项羽叱咤秦末政坛,他“虐戾灭秦”,成为秦末汉初“号令三嬗”者之一[17]759。他在楚汉之争中,兵败乌江、垓下被围,最后他“上演”的霸王别姬,也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典故。关于霸王别姬,目前最早的记载是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17]333。
霸王的别骓、别姬,让我们看到了英雄末路的悲壮情景。东汉时班固撰《汉书》,他对霸王别姬的记载一如《史记》(5)见(汉)班固:《汉书》卷三一《项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17页。。对项王的泪别爱姬,汉代的司马迁和班固,都未以男儿有泪不轻弹、英雄志短、儿女情长来要求他,反而他们都视他为一位壮志未酬的英雄,一位侠骨柔情的男儿,所以,在他们的笔下,项羽是为左右所“仰视”的。
但对司马迁、班固的后人而言,项王的泪别虞姬、洒泪垓下,就只能用“俯视”的态度来表达了。五代时的吴越王钱镠,曾总结出了一句古人名言:“古人云:妻子如衣服,衣服破而更新;兄弟如手足,手足断而难续”[18]1417。在这样的情感观下,恋恋于男女情/夫妻情的男人,无疑是恋恋于温柔乡的没出息的小男人,他自当遭到鄙视。
钱镠所总结的儿女情长观在宋明时期依然延续。宋人刘叔友就曾对霸王别姬作过这样的评论:“项王有吞岳渎意气,咸阳三月火,骸骨乱如麻,哭声惨怛天日,而眉容不敛,是必铁作心肝者。然当垓下诀别之际,宝区血庙,了不经意,惟眷眷一妇人,悲歌怅饮,情不自禁。……乃知尤物移人,虽大智大勇不能免。”[19]229-230虽是“大智大勇”,但心心念念于妇人者,也会被误前程而成为反面教材。所以,在修撰目的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20]28的《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就索性将霸王别姬的桥段全部删除了。
《三国演义》的流传,更将钱镠之语、之意推向了山村鄙野、民夫村妇。在《三国演义》的第十五回,面对张飞“弄丢”了自己的两位夫人,刘备只是淡然地重复了钱镠的那句古语:“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21]127兄弟义浓,这在《三国演义》的明代作者眼中(6)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否为罗贯中,从1930年代就出现争议,但此书最迟出现于明中期则并无争议。对此的讨论,参见卫绍生:《〈三国演义〉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241~244页。是最值得称颂的英雄品质,而儿女情长、夫妻情蜜则是应被摒斥的狭隘之情。
世事变迁,社会的情感规则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明代特别是明末兴起的“情教”运动推动下,“有情”终变成了值得颂扬之情,对此,“情教”的提出者冯梦龙说:“自来忠孝节烈之事,从道理上做者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妇其最近者也,无情之夫,必不能为义夫;无情之妇,必不能为节妇”[22]36。冯梦龙提出“情教”的出发点虽是调和人之情与儒之理,但“情”的至重性与宗教般的意义还是被他彰示出来。
在“情教”思想的冲击下,清人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就对“儿女英雄”重新作了定义:
这“儿女英雄”四个字,如今世上人大半把他看成两种人,两桩事;误把些使气角力好勇斗狠的认作英雄,又把些调脂弄粉断袖余桃的认作儿女:所以一开口便道是某某英雄志短,儿女情长,某某儿女情薄,英雄气壮。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23]3。
以明清时期这样的“情教”思想衡量,霸王别姬的项羽自然是一位至情至性的英雄,这也正是这一时期项羽的悲剧英雄、悲情英雄角色确立的原因(7)对戏剧中项羽形象演变的分析,参见任荣:《项羽在戏曲中的形象演变》,《剧作家》2011年第2期,第94~100页。。
项羽的事例使我们看到,情感无疑具有生物与文化的双重属性,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英雄儿女情,就有被仰视作英雄至性的,也有被俯视为儿女情长的,男女情爱规则依时代变迁而发生着变化,不同时期的文化塑造了不同的儿女情,它也改变着对前代儿女情的认识,这就使儿女情这一情感具有了历史。
第二例个案是武则天。武则天革唐命、建大周,这也使她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8)武则天之前,曾有女子陈硕贞(“贞”或作“真”)率众在浙东起义并称帝,《旧唐书·高宗纪》记载:永徽四年(653),“睦州女子陈硕贞举兵反,自称文佳皇帝”(第72页)。陈硕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称帝的女子,但她的政治影响仅限于浙东地区。,而她的成功绝不能不提她与唐高宗的爱情。
武则天两度入宫,第一次是作为唐太宗的才人,“太宗闻武士彟女有才貌,召入宫,以为才人”[24]23。但在太宗时武则天并未发达,所以直至太宗去世她依然还是才人之封。按唐代制度,才人的职掌是“序燕寝,理丝枲,以献岁功焉”[25]250,处理皇帝的宴寝是才人的重要工作。太宗病重,太子李治入侍父皇,奉药递膳,长陪左右,这就与专掌皇帝食宿的武才人有了相见机会,且这种机会还不会太少。以事后的发展看,在太宗去世之前,武才人与未来的高宗皇帝应是日久生情,他们即便未种下爱情的种子,也起码有了两情相悦。
一旦父死子继、李治登位为皇帝后,心中萌动的情好就在遇到适当契机时迸发为了爱情风暴。关于武则天的再次入宫,史记:“太宗崩,(武则天)随嫔御之例出家,为尼感业寺。上因忌日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澘然”[24]23。此时恰值王皇后与萧淑妃争宠,借着王皇后欲扳倒萧淑妃的东风,高宗成功将武则天召入宫中,并授予她二品昭仪,这足足比先夫太宗给的五品才人高了三品。此后,政治手腕与能力俱佳的武则天,又一步一步挤掉了王皇后,并最终于永徽六年(655)荣登了皇后宝位。再之后,她参与朝政,被尊为“天后”,与高宗并称“二圣”。高宗驾崩,她再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把持朝政。至天授元年(690),她连垂帘都嫌弃了,索性废掉唐皇睿宗,改国号为周,自称皇帝。
这一切,都是历史的理性发展吗?当然不是。有学者就称,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是“爱情的感性胜过一切”[26]64。唐高宗与武则天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不但改写了男性政治史,更改写了女性历史,在武则天的带动下,唐前期不但出现了一波女性参政高潮(9)参见Jennifer W. Jay: Imagining Matriarchy: “Kingdoms of Women” in Tang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16, No.2, 1992,第220~229页。,更使当时的政治透出了诸多女性意识(10)参见陈弱水:《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族生活》卷下《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5~203页。。一句话,唐高宗与武则天的爱情大大改变了历史进程及其样貌。
武则天是高宗之父太宗的嫔御,所以,武则天与高宗的恋情实属不伦。但“唐源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27]3245,在唐前期的帝室中,不伦恋绝非仅此一例,高宗之父太宗、之孙玄宗也都有过不伦恋,但结果却不相同。
唐太宗的皇后是号称贤后的长孙氏,她卒于贞观十年(636)。其后,太宗甚宠一位杨妃,而这位杨妃原是太宗母弟、齐王元吉之妃,玄武门事变,元吉被杀、杨妃被没。太宗甚至一度欲立这位杨妃为后,对此,《新唐书》记:“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帝宠之,欲立为后”[28]3579。但太宗的这一想法被魏征所谏止。唐玄宗以子妇杨玉环为妃,其事人所共知;玄宗极宠杨贵妃,这也是世人皆晓。但即使面对“天生丽质难自弃”的爱妃,玄宗也只做到了“三千宠爱在一身”“从此君王不早朝”[29]238,“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30]2178,而绝未产生过立后之意。
太宗和玄宗在与爱妃的不伦关系中,也应都产生过爱情或深情,但即便如此,当他们面对舆论或世人时表现出的却是“理性抑或是缺乏勇气”[26]64;虽然他们与高宗所处的情感规则背景并无大变化,但他们应对规则的策略与结果却与高宗迥异,如此带来的政治结果也就有了巨大差别。
第三例、第四例的个案来自唐、明两朝的官宦士人家庭。个案三的男主人公是唐朝的李顼(11)对李顼妻妾关系的详细分析,参见陈弱水:《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族生活》卷下《唐代的一夫多妻合葬与夫妻关系——从景云二年〈杨府君夫人韦氏墓志铭〉谈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255页。。李顼(805—848),父李绛为宪宗朝(805—820)宰相,家出山东士族高门,可谓是世人羡慕的婚宦两全之人。李顼娶同出山东士族高门的卢氏为妻,依卢氏父卢商为她撰写的墓志,卢氏(814—832)少早成婚,婚时年仅十三。婚后两年,卢氏开始身体欠佳,之后又遭公爹遇害及婆母过世,身体状况更趋恶化。病中的卢夫人思念家人,李顼便将她送回娘家,以慰藉其心、将养其身。但大和六年(832),卢氏还是卒于其父的解县(今山西运城西南)官舍,后归葬舅姑墓侧(12)参见《唐李公夫人范阳卢氏墓志铭》,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11~912页。。单看李顼与卢氏的婚姻,履历、情感并无特殊之处,它是两姓高门的联姻,夫妻感情平平淡淡,从送病妻返回娘家看,丈夫也能关照到妻子的感受。但是,李顼有妾章四娘,而章四娘的墓志也留存下来,对照卢氏与章四娘的墓志,我们就会对三人的情感关系恍然大悟了。
不像卢氏的墓志由家父撰写,章四娘的墓志是夫婿李顼亲撰的。按照章四娘的墓志,她出身于南方会稽,“容止闲默,谦冲自率,礼法天传,女工神授,弦管草隶,辈流罕比”,在李顼的眼中,爱妾章四娘是才、德、美兼具,当然,李顼最初纳章为妾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她的音乐书法才慧。章四娘晚卢氏一年亡故(大和七年,833),在章四娘的墓志中,李顼毫不掩饰他对爱妾的感情:“顼主章氏十有二载,至于情义,两心莫辩。衔涕编录,万不纪一”[31]914-915。按学者的说法,这几句话“十足是恋人的口吻”[32]253。在章四娘墓志的“铭”中,李顼又写道:“京邑之北,古原寂寂,窆我令人,悲风淅淅”[31]915。这几句再次表明,“章氏是李顼情爱之所托”[32]253。
这样,在李顼、卢氏和章四娘的三角关系中,李顼与章四娘的夫妾情才是占据家庭情感主导位置的。章四娘成为李顼的妾妓,早于卢氏嫁为李顼妻五年,此时,李、章二人早已建立了极深的感情,卢氏的嫁入反倒像是第三者的闯入。最终,卢氏妻的力量不足以打破李章夫妾的亲密情感与关系,她在这一情感纠葛中最后身心俱疲,力瘁而卒。
李顼及其妻妾的情感关系,折射出了中国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婚姻模式下的夫妻、夫妾情感归属与真实景况,也展现了男性士人在应对夫妻妾情感时,是如何通融于情感规则与个体情感取向之间的。
第四例个案的主人公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才女王端淑,从情感史的角度看,王端淑的为夫纳妾、与夫的情感纠葛,都应还有待发之覆。王端淑(1621—1701),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父王思任为明礼部侍郎、晚明著名文学家,母姚氏善吟咏,夫丁圣肇为父好友丁乾学子、钱塘贡士。王端淑以才女之名著称于江南,其父甚以其为傲,故言:“身有八男,不及一女”[33]147。
王端淑长相美丽、聪明周全,同辈文人赞她“状貌颀皙,亭亭有玉树当风之致”“端淑生而容姿婉丽,性聪慧周”[34]卷首;她还多才多艺,专书画、擅诗文,目前有集《映然子吟红集》和所编闺秀集《名媛诗纬初编》传世。王端淑做事张扬,“每遇游玩,夫人则披纤罗之锦、雾縠之裳,羽翠葳蕤,明珠的皪,飘飘然若月殿中人也”[34]卷首;她“负才荦荦”[35]790,“立言”意识极强(13)古有“三不朽”之说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十三经注疏》,第4297页)。,其时的文坛领袖毛奇龄选编浙中闺秀诗集,未收入其作品,王端淑便寄诗毛奇龄:“王嫱非不无颜色,怎奈毛君笔下何”[36]16。依史文的记载,王昭君远嫁匈奴,是因未贿赂画师毛延寿,所以未能得到按图索骥的汉元帝的临幸。王端淑以王昭君自比,以毛延寿喻毛奇龄,“一藏其名,一切其姓”[37]52,用典极妙,所以一时盛赞如潮。
仗着自己的才貌,也自信于与夫婿的情感,王端淑便以“怯弱多病,不禁摧折”[34]卷首为由,自己出钱为丈夫纳了一房妾室陈素霞,对此,王端淑记云:“陈素霞,字轻烟,南京人,甲申春归夫子,予脱簪珥为聘”[34]卷一七。此事着实有些匪夷所思,首先,基于人性,王端淑为何要为自己的婚姻增加一个第三者?其次,从王端淑的生平看,她寿长八十余,即便此时不壮健,但也应不至于“怯弱多病,不禁摧折”。再次,丁家也无断后之虞,因为王端淑已育有一子。又次,王端淑并非是一位不妒的女子,我们看到,纳妾一事虽为王端淑肇端,但当其夫一旦疼爱起新妾来,王端淑的妒意与不满也就随之而来,她做诗并直名为《甲申春予脱簪珥为睿子纳姬昵甚与予反目》[38]98,此诗明在诉说为妻的凄怨,但更道明的是与丈夫反目的决绝与强势。所以,她为丈夫纳妾的目的,就不能依其所说,而应另当别论。
依高幽真为陈素霞所写的小传,陈素霞也是一位饱读诗书、多才多艺的才女,她“博览史籍,妙解声韵,兼擅诸技能,作黄庭小楷。其女红刺绣,无不精晓。时年十四,修美淡逸,咸目为苏蕙、左芬不之过也”[34]卷首。这段话使我们注意到,在称赞陈素霞妇才的同时,也赞扬了她的美——“修美淡逸”,但又将她比作了前辈才女苏蕙和左芬。苏蕙是前秦苻坚时期(357—385在位)的才女诗人,其夫窦滔任“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39]2523。虽极具才情,但苏蕙的婚姻坎坷、相貌不明,因之,在明清人的眼中,苏蕙就是一个“怨妇”才女形象(14)如叶绍袁《午梦堂集·序》就说:“苏蕙羽仙,终为怨妇”(第1页)。。而历史上的左芬,更是一位著名的“无色”才女,对此,《晋书》记:“芬少好学,善缀文,名亚于思,武帝闻而纳之。……后为贵嫔,姿陋无宠,以才德见礼”[39]957。所以,夫人沈宜修、三女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并为著名才女的明人叶绍袁说:“古来名媛,文君无德,左芬无色,荀奉倩妇无才。三者兼备,能无造物之忌乎?”[40]428苏蕙和左芬的典故,叶绍袁知晓,高幽真同样应该明了,所以在高幽真的眼中,陈素霞最突出的特质还应在才上,对其“色”“修美淡逸”的形容,恐怕也只是套话。这样,也就解释了王端淑并不惧陈素霞进入家门的原因。
王端淑或看重的就是陈素霞的才,从她乐于推助陈素霞进入才女之列就可看到,陈素霞的诗被王端淑收入了她所编的《名媛诗纬集》中。因着妻妾均具的才名,也缘于丈夫的“傲世不阿”,丁圣肇、王端淑、陈素霞夫妻妾“三人名遂噪越中”,以至“一日隽彦毕集,四方闻风艳慕、执贽来访者,牛酒具前,金帛拥后”[34]卷首。这不正是王端淑所追求的盛名、盛景吗?所以,王端淑打造的才女之妾的陪衬,也终是达到了她的所想所要。
但造化弄人,才名的追求可以通过外化手段巩固、放大,但夫妻情感却时时不为人所左右,这样,丁圣肇与陈素霞夫妾的情深意蜜,就导致了王端淑与丈夫的反目。反目归反目,强势的一方仍是王端淑,此时,她是家庭财富的主要贡献者,她的才华、地位与声望,都远超了她那位不成器的丈夫,所以,她虽心存怨望与情愁,但仍可大度地视庶出之子女为己出,也可一直与妾室共处,这样的结果就是她长寿而陈素霞早逝。
陈素霞嫁丁圣肇八年,育有一女一子,卒年二十八。按高幽真的说法,陈素霞的逝世是“因子息不禄,欷歔成疾”[34]卷首,但可以想见,在这样一个夫妻角色倒置的“彩凤和乌鸦”配中,陈素霞的存在会是怎样的尴尬、情感生活会是怎样的压抑:夫妾真情流露,便会有“大夫人”的幽怨见于家中或纸上;而自己的唯一依靠——丈夫,也压根靠不住,因为这位丈夫就是要仰人鼻息、靠“大夫人”来养家的;即便是爱妾去世,丈夫的悼亡诗也要由“大夫人”捉刀。王端淑代丁圣肇写的《悼姬》一诗,有句“寒色香飞堕,马嵬误玉环”[38]78,其意指贵妃无罪,是玄宗误了贵妃,恐怕这也是王端淑与丁圣肇的共同心声,情感之中甚或家中都不能做主的夫婿,哪有保护爱妾、追求夫妾真情的资本呢?
与李顼的夫妻妾三角情感关系相较,王端淑三人的感情世界多与之不同。因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缘于儒家性别观念的松动,像王端淑这样的才女在很大程度上反转了传统一夫一妻多妾世界中的情感关系,即便此时的王端淑们依然处在不平等的婚姻关系中——男多妻妾而女只能从一而终,但对婚姻中的夫妻妾情感,她们已多了主动、少了被动,明清才女文化的发展,才女于家内、地方社会地位的提升,都使夫妻情感的规范与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如上四个中国古代情感事例,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古人不但有“情”,而且其情还有历时与共时变化,因此,中国古人的情感发展、变化,也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其中的一个个鲜活、富于情感之人,并不止是这一历史中的数字与尘埃,他们的喜怒哀乐更是这部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国古代情感史的延展
芭芭拉·罗森宛恩在《为历史上的情感忧虑》一文的开篇写道:“作为一个学术分支,历史学最早研究政治的变迁。尽管社会史和文化史已开展有一代之久,但历史研究仍专注于硬邦邦的、理性的东西。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情感是无关重要甚至是格格不入的。”[9]821这是史家在梳理史学史或情感史出现原因时经常引用的一段话。情感史的出现,针对的是近代以来的理性史学,情感史学者希望通过对情感的考察,找回近代以来被摒弃的感性世界。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情感史又是一门交叉学科,对此,情感史学者普兰普尔指出:“情感史可以被其他学科所吸收,既可以为性别史、性史、身体史、环境史和空间史增加一个新的维度,也可以拓宽民族史、全球史、社会史甚至经济史的研究领域”[3]101。在此,笔者仅以日常生活史、性别史和差异视角,略谈一下中国古代情感史的延展。
情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日常生活史的出现,同样是西方现代史学对“社会科学化”的一种反省。科学的史学将人类历史看成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其特点是“见物不见人”,但“忽视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必然导致对历史规律认识的简单化”。而“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就有情感的存在,关注名人的情感会使我们看到历史理性之外的事物,会使我们领略感性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而大众情感同样是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日常生活史强调,研究“每个人、每个群体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人们公开或掩盖、实施或抑制其愿望的方式,最终说明社会压力与刺激怎样转化为人们的意图、需求、焦虑与渴望,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是怎样接受和利用外在世界的”[41]。大众的情感未必具有改变历史的力量,但探讨他们的情感世界无疑会使历史更加饱满与生动而不再硬邦邦。有基于此,作为日常生活的情感,除了名人外,大众情感也应成为中国古代情感史研究的一个重点。
人类社会由男女两性构成,进入阶级社会后,性别就成为了社会建构的重要内容,这也就是琼·斯科特提出的“社会性别”[42]151-175。就男女而言,人常说女人是感性的动物,这也透露出情感之于女性愈为重要,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就更如此。个中门道,其实早就被古人参透,东汉才女班昭在其著名女教著作《女诫》中,就曾引《女宪》之说:“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迄”[43]2790。这说的是夫妻情,妻能获夫欢心、抓住夫婿情感,一生就有了依靠,反之,则一世休矣。如此,夫妻情就不仅是中国古人生活的一项内容了,它更关乎亿万女性的生存及生活品质。
有性别之差的同时,还有其他差异,比如时代、人生阶段、社会阶层、地区、民族等等,而这些差异都会使古人情感呈现出不同样貌。就社会阶层而言,等级是中国古代立政与统治的基础,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就是其时社会秩序规则的基本内容。在这样的等级社会下,后妃的情感纠葛绝然不同于民妇,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再就人生阶段来说,夫妻情与母子情在中国古代更是两个不同范畴。另据罗森宛恩的提示,差异还包括不同场合、不同地点的人之情感表达差异。据此观察,中国古代的男女在不同场合,同样有着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比如,男性在公领域和私领域,其情感表达的开放度、持久度等都有差别;而女性在儒家体制内与佛教情境下的情感表达同样也有不同。所以,探讨中国古人情感史,就既要关注其历时性特点,也要探讨共时性的不同表征与成因。
最后,引用情感史学者王晴佳的一段话来说明情感史研究的意义:“情感史并不否定理性主义分析,而是想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在理性和感性的双重层面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深入的分析”[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