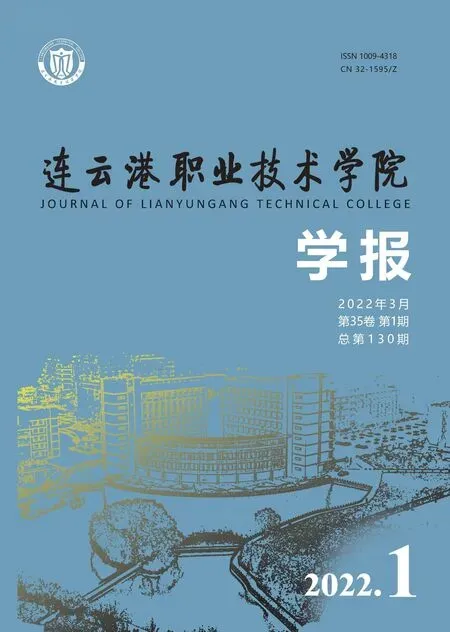诗歌的肉身
——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诗中的主体与世界
于锦江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诗歌文学总是期待一种理解,主题分析也好,形式分析也罢,文学批评的意义就是以某种方式让读者得以进入诗歌的内部,使其某种内在意蕴成为语言符号的可见之物。对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而言,这亦不例外,他对意象、动词、句法的独到使用构建了复杂而深邃的知觉世界;通过在词句中利用视觉、触觉等感官的作用,这一艺术世界中的主体与世界达成了一种彼此纠缠、联结的关系。面对深度的世界,诗人以包含知觉、心灵的身体之光将其语言带入一个可见的文学符号的领域。对特氏这样的诗者,正是借助法国学者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理论,得以窥见能与之相通的道路——诗的叙述主体与其包含的艺术世界何以构成自身又何以彼此打通?
一、知觉中的主体
在特朗斯特罗姆的诺贝尔奖授奖词里,其诗歌的“呼吸”与“运动”的特质被给予了极高的赞誉,正是通过对意涵复杂而丰富的意象的统合,在充满生命力的词语的运动中,特氏打开了别样的诗境。但,语言的运动,诗的呼吸,就之根本,其实已然给出了一个前提性的奠基者——一个具备知觉能力的主体的可能性。只有预先允诺这样的主体,如此这般地感知自身与世界,诗的运动才得以可能。那么,如何将意象的变换与集中透过知觉的能力予以展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中表现出来的感官能力绝不是一种机械化的纯粹感受,换言之,人的感官能力总是与一种情绪,与思维,与心灵之意识相联系。对于第一首《序曲》,很多评论家关注的是梦与醒之间交替的主题,但在这里不妨换一种视角,即这种“醒”的特征是如何被表现的,在第二段的开始,特氏写道:
“黎明时分,知觉把住世界/就像手抓起一块太阳热的石头”[1]27
迷离的梦境或是死亡的漩涡都需要一个能动的知觉主体。因为在诗中,生命在这里首先把握到的就是一种世界的热度,一种知觉的体验——触觉在这里是手握着石头而产生的硬度的感知,又是一种炽热的温度在其中交织。还不仅仅如此,太阳这一词汇从来不只是温度的表现,还是一种光晕,是刺眼的颜色的冲击。第二句就以此表现了三重感受的交织,此种“交织”仍然是意向性的,总是指向了一种生存状态,即“黎明时分”所暗示的能够知觉的“我”。于是,对于生命之为生的理解,从这一诗句中可以有一个极好的体现,知觉把握世界,不仅仅是我对世界有一种单纯的感知能力,更是在其背后生命之活力——一种穿越梦境与死亡的欲望,总是与这种知觉合为一体。
同样是1954年17首诗中的《风暴》亦是这般知觉的体现。诗的上段,写的是漫游者静态的视觉观察,如一副古老的油画,古老高大的橡树如同巨角驼鹿,矗立海边。下一段,情况改变了,“他在夜中醒着/听到橡树上的星宿/在它们的厩中跺脚(stamping in their stalls)。”[2]4从视觉到听觉,从静态到动态,转变的不仅仅是纯粹的感官与感官之间的切换,这中间浸透了生存的体验,似乎是风暴临近时瞬间顿悟的惊诧的情绪;照应上一句的代表生命成熟的时节,作为生存主体的人,不断自我生成的可能性就在每一次心脏的跳动之中——星宿,是否是命运之声响呢?于是,就在这回响之中,生存的主体亦是知觉的主体,是感受生命、万物的活生生的人,情绪与欲望,梦想与挣扎,包容在同一个身体中。
其次,上述这种知觉体验在某主体那里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作为知觉主体的人,并非幽灵,而是一个切实在世的具体的人,换言之,是一个拥有身体的知觉主体。特朗斯特罗姆是关注身体的诗人,在他关注主体的内在与生命活力之时,人之在世与具体身体的关系并不被他忽视。他清楚地知道,灵活地驱动人之身体的种种器官、肢体的感受力,将之入诗,正是他诗歌中生命力涌动的可能性之所在。于是,特氏的诗歌才区别于所谓观念哲学在纯粹意识领域的推演,其智性与哲思深藏在身体活动中,向着世界无限外化。
《内陆暴雨》描述了诗歌主人公在开车时遇见暴雨而产生的对情景的感受与内在思绪,这一过程不是分散或割裂的,而是来自同一个诗歌主体的整体知觉,即是以具体的身体为中介的统一的时间过程。第二段“曲蜷着,合上眼帘。/一个向内的运动,更好地感受生命。”[1]146自我的内省,向内部的思绪运动,绝非是单纯的形而上学,不是一个幽灵一样的“我思”,正是合上眼帘的这一动作,特氏将“我思”拉回了现实,点出了此乃具体的身体之中的一个运动的环节。眼与心,灵与肉,就统一在我们在世的这个身体之中:“一阵音色混杂的呜咽。/一个铁器时代嘶哑的小号。/或许来自他身体的深处。”[1]147
所以,这一身体/知觉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不是所谓主体/客体对象化的截然二分的关系。作为主体的人的知觉活动总是依凭身体而与世界之间开出一个场域。在此知觉场中,主体与世界敞开自身,彼此纠缠联结。《打开和关闭的空间》诗中开篇就写道:“用其工作(with his work),有如用其手套(as with a glove),有人这样感受世界(universe)……手套突然开始扩张、膨胀(growing,grow huge)/并从内部使得整个屋子黑暗。”[2]21特朗斯特罗姆上来就给了这一主体一个身体性的特征,有工作、戴手套都是面向现实实践活动的身体才能具备的能力,它们暗示了现实的身体可能会疲惫或产生状态的变化。一个疲惫、无力感知世界的主体,才是封闭的,才变成了“虚无”。他在写给好友罗伯特·布莱的信中也谈及,这一所谓的空间,既是物质实体性的中性空间,又因其完全是空白而具有虚无性(void)[3]58。随后,诗人似乎通过这种“无”暗示了这一疲惫的身体所产生的意识,一种朝向原初世界之内省的倾向,甚至成为一种威胁主体性的存在——“黑夜不是在我面前的一个客体,它包围我,它渗透我的所有感官……几乎抹去我的个人同一性。”[4]391然而,好在人之身体乃是空间的钥匙,它信赖着脚下坚实的大地;自然之象征的草、云与作为人类身体活动之象征的风筝,在虚无中拉动了隐线。主体与世界,总是在一个同在的空间场域中,即一个知觉场中。于是,主体向世界的敞开与外化,世界向主体的侵入与渗透,就是在通过身体展开的知觉场中共在而进行的;恰如梅洛-庞蒂关于足球运动的绝妙比喻,即知觉主体在世界之场域中,就如足球运动员在足球场,他们已然融入这一赛场,并无必要去精细地比对和丈量来确定自己与赛场的位置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何诗中那个飞奔的男孩是处在所谓的“打开的空间”,这里恰是一个知觉的场域,身体活动与世界自然,交织、缠绕,身体感受风之动,云之悠悠,亦是身体将自身投向世界。
其实,回顾上文对特氏诗歌的知觉主体本身的三点分析,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如果诗之生命力、诗之意象的聚集与置换总是与知觉主体相关,总是与知觉场中的“世界”关系相关,那么身体/世界的纠缠关系究竟是如何奠基的,其关系的性质何在?倘若要深入这些诗歌的肌质,进一步思考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意蕴,这些追问就必须予以回应。
二、主体与世界之肉
世界,就正如上文所述,在特氏的诗歌中,已不再是科学视角中的对象之物,而是时刻与“我”以视觉、听觉、触觉等知觉方式发生关系的总体,是总与知觉主体经由“肉”(chair/flesh)而缠绕不清的世界。什么是“肉”?这里使用“肉”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又何在呢?其实,在超越了早期现象学的庞蒂看来,肉,已经不再是纯粹精神的或物理性之物,而更类似古希腊思想中原始的元素。它既是为世界奠基的最终极、原始之物,也是“最一般之物”,是为事物赋予具体化的原则,赋予其意义的东西。[5]176这才使得上段末尾之处的发问有了第一个回答,主体与世界的关系这时有了一个背靠的基石——身体和世界拥有同样原始之核,这种同一的来源使得两者的交互生生不息地展开了。那这又如何在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中被体现,或者说,庞蒂的哲学如何具备介入诗之批评的可能。
第一,在特氏的诗歌中,主体之肉身与世界之肉彼此共在、纠缠这一思路亦是其创作的思想基底之一。《联系》这首诗就是一个典型:“看,这棵灰色的树。天空/通过它的纤维注入大地——/大地喝完后只留下/一堆干瘪的云。”[1]41开头一个“看”,向读者呈现出一个匿名的主体,一个视觉的观察者,他引导读者观察和审视诗歌随后的词句,从而给出具体的意象,聚合为诗歌的场景。无疑,无论是引导者还是被引导者,都同时被设想为知觉的主体,换言之,就是因为预设了读诗者,与叙述者同为能够领会这一“看”之内容的主体,“看”所包含的内容才成为意义的呈现。于是,天空与大地,与主体之间,正如题目所提示的那样,才是一种水乳交融的“联系”。“喝”这一动词的使用尤其值得关注,因为与其说是这一动词以拟人的修辞让大地成为人,不如说是特氏将一种“同一”的接触方式、知觉运动赋予万物。诗歌下文“被盗的宇宙”,就仿佛是大地狡黠的体现,而“短暂的自由”,却从我们体内喷出,世界与我们,恰如莫比乌斯带的内与外的交织。事物之于世界就其“只不过是可能的凝结之一而言,它被我们内在地恢复、被我们重构和亲历。”[4]451所以,世界与主体的关系就以诗境当中联系的整体展现出来,每一次交互,每一次渗透,成为整体当中运动的环节,这不正是彼此同在的肉身吗?如此,世界就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早已完成了的,而是在我们知觉的交织中正在生成。”[6]
当然,“肉”并不意味着世界与主体就是一物。之所以还有纠缠和敞开的运动,因为他们彼此之间仍然有所区分。主体的自我维系同样是与世界关系中重要的部分,主体知觉的生成使得主体从肉之裂隙中诞生、运动,成为自身。于是,自我“反思”(r’flexion),自我精神的内省,对“自我”的发现,在此之后才得以可能。特氏尤为关注的内在的我,不是笛卡尔的自我,而是在知觉中醒来为世界筹划的自我——“我醒成不可动摇的可能,它抱着我/穿越飘摇的世界”(《管风琴音乐会上的短暂休息》),所以“让世界抽象是一切做法都注定会失败”[1]242;因此,这般主体才被许诺了朝向世界整体,不断打开自身的力量,这一过程“从每个灵魂里生长”[1]243。
第二,主体之肉,绝非是某一个特殊的个体,正是因为“肉”之观念蕴含的原初的普遍性,“我”就不得不转向了“我们”。既然每一个个体,总是与这一“世界”共在,而彼此之间共同的具有打开自身的能力。那么,对于具体生存的每一个人来说,理解一个世界,就不仅仅是只“为我”而在的世界,这同样是一个有他人存在的世界,而且必须设想,我们共同面对同一的可感世界。当然,对于具体的在世生存的人,其现实生活要面对的,既有自然的世界,也有文化的世界,两者绝不能被割裂。
对作为诗人的特朗斯特罗姆而言,亦是这样。一方面,他与自然同在,同每一个人一样依附于这片生存于其上的大地。另一方面,世界的本质意义,真理的面容,总是在文化历史之中,在“我们”的共同体中——“没有一种不和历史和地理领域相关联的本质和观念。”[7]143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创作的中后期,特氏诗歌中关注现实的成分越来越多,因为若要去思考这一“我们”共在的生活处境何为,就不可能将他人置身事外而独处幽篁。诗人自身的思想倾向也在与他好友及译者罗伯特·布莱的通信中表现出来,在多篇信件中特氏十分关注国际政治的局势,对不义的战争、西方政客的行径亦多有愤慨之词。但特氏诗人的身份总是被外界误解,如诗人自己的抱怨,总有评论家指责他不够介入。这也许并不公允,因为特氏显然是以自己的方式在针砭现实,与此同时,他也试图在政治介入与诗歌表达之间留下余地。《论历史》一诗,看似是通过自然意象的隐喻,历史人物和地理坐标去沉思历史,但其矛头正是直指当下——“激进派与保守派像场悲惨的婚姻一起生活/互相削弱,又相互依靠。/但我们,他们的孩子,必须走自己的路。”[2]26在诗人眼里,过去的历史总是被陷于西方政客们因利益纠葛而导致的罪行中,民众总是作为其承担者,诗中第三节以“Dreyfus”提及的正是当年法国那位无辜受罪的犹太裔军官。如上文所引的诗句,诗人呼吁当代人打破历史的迷局,而他正用诗歌的力量为历史乃是“我们”而非“我”作出有力的辩护——“一张报纸已经躺了好几个月……就像古老的回忆慢慢变成了你(gradually changing into you)。”[2]26
综上所述,从原初之“肉”的观念出发,特氏诗歌中知觉主体同世界的关系性质由此得以阐明,从而可以进一步分析诗人在现实中以诗歌介入的深层缘由。诗歌的主题化,不是诗人偶然兴起,文本的完成与叙述主体对世界的把握,对自我、他者的认识息息相关。而“肉”的原始的性质也表明,越向世界、他者敞开,就不可能不面临广袤世界那可见的边缘,思之道路的晦暗之所,那沉默的“肉身”。作为敏感而智性的诗者,特氏的诗与庞蒂的思,竟殊途同归。下文笔者将说明,诗与哲学的道路何以在此触及可见与不可见的界限。
三、诗与可见者的边缘
诸多研究者都点出特氏诗歌中凸显神秘的一面,例如,翻译者李笠在他对《车站》的分析中,诗人诗中神秘的来自外部的不可知以及心灵感受的复杂,最终导向“一种宽慰或拯救的力量”[8]。其他研究者面对这一主题,也往往更关注这种神秘的外延,即其作为自然的或是文化、宗教的表象物。但笔者要面对的,是神秘本身的性质。世界的神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特朗斯特罗姆在诗歌中主题化的神秘是如何被构建的,或者说,既然神秘总是不可触及,诗者又如何将其从不可见中拉进语言的维度。
其一,特氏的诗歌总是有如此的前提:如此质的丰富的世界总是有作为人的感官/理性无法穿透的部分。上文的分析中已经提到,庞蒂同样认同这一点,世界本身,总有无法被知觉的眼睛所穿透的部分,那是在萨特的存在主义中被视为“荒谬”/“恶心”的自在存在;但在庞蒂这里,此乃世界自身之无限丰富的体现,是本源之“肉”中沉默的部分。这沉默的力量,无论对庞蒂还是对特朗斯特罗姆,都不会是如萨特所言的“恶心”之物而需要被弃置或超越,沉默而潜在的力量蕴含一种原始的整体与和谐的可能。《车站》正是蕴含这种隐喻,李笠对《车站》的分析出色阐释了自然意象的种种象征意义,可是他在试图去讨论那个使得全诗由静转动、从沉闷走向明丽之境的“抡锤的男人”时仍保留了对其身份不确定的态度。这个人物实际上并非就是不可分析的,因为此人同样是全诗整体的象征性内容的一部分,他指代的就是那个先于“我思”的“我能”的主体,是笔者开始就点出的特氏诗境中所表现出的知觉的主体——一个敏锐觉察世界之肉本源力量的主体形象。他试图带出每个世界意象的诗意的潜在,于是才有了将沉闷阴晦之气的封闭空间整个绽开的“一声雷鸣”。
其二,特氏总是试图通过词语的隐喻、意象组合的场景试图破入词语背后深度的部分,他试图将诗意的光线投向世界潜在的阴影中。诗歌艺术自身作为一种介质,将潜在的神秘带进一个可见的范围,这就是庞蒂那个关于游泳池的比喻:“当我透过水的厚度看游泳池底的瓷砖时……正是透过水和倒影,正是通过他们,我才看到了它。”[9]64
1958年特氏发表的《途中的秘密》这首诗就具有典型性的表达方式。诗中,第一段和第二段先给出了一组对位的场景和人物,沉睡的人对应行走的人,阳光对应黑夜,但是他们两者皆有缺失:沉睡的人进入不了光线所照射的澄明之境,只是在春秋大梦中安眠;而阳光下的行人却行色匆匆,黑暗已经落在脸上也未察觉,即那潜藏的力量,世界的神秘被他悄然遗忘。显然,对诗人来说,这两种人的生活都不是理想的,特氏要展现的是能够包容两者的第三种生存方式。那么,真正的生存是怎么回事呢?
“世界忽然像被暴雨弄暗。
我站在一间容纳所有瞬间的屋里——
一座蝴蝶博物馆。
阳光恢复了先前的强烈。
它急切的笔涂画着世界。”[1]74
“我”潜入那晦暗的神秘之中,那是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所统合的空间——原初与终极的场域,以有机的、整体的生命力去面向“我”。所以,当回到可见的场域,光线将从那不可见中带来的将是更多的东西。此乃交互的边缘,一边是原始神秘,一边是知觉可感,理性可思的具体;选择,并不是二者择其一,亦非绝对超越二者,而是既身在其中又身在其外。于是,有国内学者对此诗解读时常用的“梦与醒”“日常与未知”的解读[10],固然有其道理,但只有回到知觉的本源处,才得以理解上述的这种“双边对立”的使动因素何在。如此,全诗四段的意象与场景的使用与对位法的使用与全诗内容表达紧密相连。诗自身的创作确实是这些被精细挑选的词汇、句法的组合,是与其肌理、形式、抑扬格所共同开启的一个符号之场域。但是,词语的象征意义,隐喻的延展,形式格律的变化中丰盈的内容,在诗歌中完成,当一次整体的阅读结束之后,这一切人工的构建都会悄然退场——就如读者进入特氏之诗时,尽管大可以对其每一个部分进行孤立的形式拆解或内容分析,但想要真正走进诗人的世界,就必须以非对象性的内在方式面对诗歌,去寻找艺术“内在的灵性化”(animation interne)[9]65。诗境,就是领会艺术的两面:一半是原始之沉默,一半是心灵的发声。这亦是特朗斯特罗姆匠心所在,西方有研究者借助罗伯特·布莱的话去赞扬特氏诗中展现的意象(image)魔力:“他知道意象需要多大的空间来扩展和共振(expand and resonate),他让周围的一切保持安静和宽敞。这首诗变得像一把小提琴。”[11]
写诗,如何不能是一种生存实践或生存美学呢?在此意义上,当代文学与当代法国理论实际上面临同样的任务,即将伦理的责任、对世界的理解与主体自身的实践放在语言的思域中。以诗的形式重塑知觉的身体,在与世界肉身的交互中回过头来重新在世界中醒来;也许就是在特氏的艺术世界中,读者重新如此切近地逼临这一任务——以知觉的方式,向无限的世界投向充满希望的凝视。
四、结 语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总是以绝妙的修辞或独到的意象去表现人与世界之间那微妙而又特殊的感官的触碰,他呈现给读者的是如此具有生命活力的一个充实意义的世界。其诗出色地证明,即使是在纯粹的形式革命、先锋运动此起彼伏的当下艺术界,诗的道路仍然有不同的方式,对生命的体验仍然可以以这般动人的方式来到读者面前。这是一种原始、神秘的体验,也许就如庞蒂所给出的世界的“肉身”:面对沉默的,在不可见的那一处,艺术挺身而出,使世界“那一面”的声音飘然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