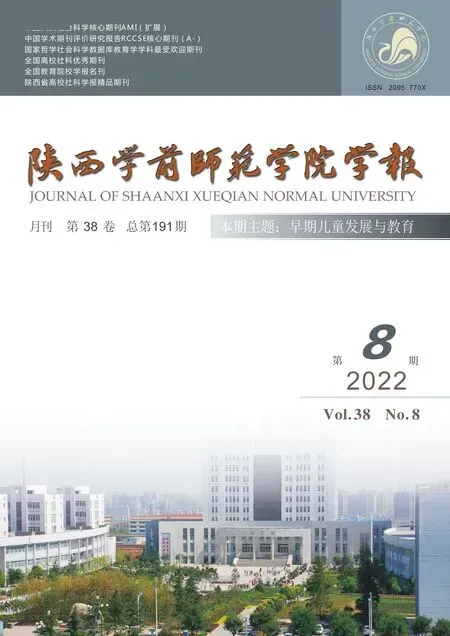儿童科学的悖论破解、内涵明晰及意义阐释
张海欧,张更立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2021 年6 月3 日国务院印发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科学让世界祛魅的能力和显著的生产力优势让其在现代社会中备受关注。人们对于科学的期待转化成了教育中各个阶段的科学教育,以期通过系统的科学教育为科学创新培养人才。在“科教兴国”战略指引下,科学教育已成为教育的重中之重。在高等教育中,科学的概念与内涵是清晰且透彻的,就是指近代以来的数理实验科学,但学前阶段的儿童科学到底是什么?“儿童科学”作为一个经常直接使用的概念,相比其他内涵明确的概念而言,至今却尚未有一个明确公认的界定,这为学前儿童科学的深入研究留置了一片“阴云”。这样一个本质性、基础性的起点问题得不到明确的阐释,那么儿童科学教育就存在迷失的可能。明晰科学与儿童的契合点,厘清儿童科学的内涵及意义,不仅有助于确证儿童科学存在的理论正当性,揭示科学贯穿生命发展的整全性,也能为儿童科学教育定位逻辑起点。
一、儿童有科学吗
“科学作为人类心智发展的最后一步,被视为人类文化最高、最具特色的成就,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最重要的主题。”[1]238显然,对于科学在人类发展中的高度评价与处在生命初期的儿童无法直接关联。但是诸多涵盖“儿童科学”的概念,如“儿童科学经验”“儿童科学教育”早已经成为教育研究中常见的术语。现实生活中,人们质疑儿童科学认识发生的可能,同时又希冀于儿童科学教育的显性成果,致使“儿童科学”像悖论一样存在于生活中及教育里。那么儿童作为能动的主体有科学吗?(以下“儿童的科学”简称为“儿童科学”)
(一)儿童科学悖论的产生
1.科学与儿童的历史疏离:儿童“无”科学
科学进入近代中国的历史背景决定了科学在中华文化中的命运。在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一词,即使偶然出现,也不是指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西方科学在进入我国文化时,背负着救亡图存的使命[2]5。近代中国的落后让国人认识到西方科学的强大,“科学”一词就是在这样一个民族危机时刻,作为强大军事力量的代名词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由于急于寻求这样的力量来拯救国家和民族,来不及考究科学在西方文化中的发生与发展,更无暇顾及科学漫长的发展史及其具体内涵的演变。人们对于科学的崇拜和热情,在本土文化的需求之上形成了对舶来“科学”丰富的认识,从而引发了科学内涵逐渐泛化及其边界渐渐模糊。
科学引入我国的历史背景致使科学与儿童的历史相疏离。具体而言:其一,科学作为巨大的生产力代表,以更为外显的技术外衣进驻中国,因而,从一开始,国人对科学与技术不相区分,技术的实用性甚至让人们更为青睐;其二,科学作为从西方引进的发达技术,最初用于救亡图存的目的,尚无缘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成为人们生活中鲜有的高级文化;其三,科学巨大的生产力效应震撼着国人,致使“科学”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崇高,衍生成为价值评判的意义——“科学的”就是好的、对的。对于如此逻辑进路入驻中华文化的科学而言,似乎与儿童是不可能有交集的。由此,无论是实用性强的技术与儿童个体能力之间的空集,还是作为高级文化的科学与儿童生活的远离,抑或是拥有价值评判意义的科学与儿童天性取向之间的矛盾,都将儿童与科学放置在两个似乎没有交集的范畴里。
科学与儿童在历史中的境遇决定了国人的观念中科学与儿童是没有显著关联的。首先,儿童没有操作科学技术的能力,无法与科学技术产生直接关系;其次,儿童处于远离科学文化的生活中,没有接触科学文化的机会;最后,儿童亦不具备科学所肯定的价值,从而没有与科学产生关系的必要。总而言之,科学进入中华文化时候的光环让科学自觉地远离儿童。
2.科学与儿童的现实亲近:儿童“有”科学
科学始发于个体,从其过程来看,主要由好奇、发问、观察及根据观察结果解释现象等几个阶段组成。刘晓东指出,儿童的科学是儿童对周围环境所具有的一种天生的好奇感,促使儿童对周围环境好奇、发问、观察并对现象进行解释[3]116。儿童像金子般珍贵的好奇心,被科学家、教育者肯定。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认为,“每个人在他们幼年的时候都是科学家,因为每个孩子和科学家一样,对自然满怀好奇和敬畏”。好奇心作为儿童与科学家的共同之处,不仅是科学发生的关键,更是教育者确信儿童科学教育存在的前提。建构主义者曾指出,科学家与儿童都不会简单的使用系统性方法来解决未查明的问题,而是对问题充满疑惑与好奇,进而进一步进行探查[4]5。换言之,科学在儿童对世界的好奇中萌芽,儿童与科学从一开始就有契合的可能。不仅如此,皮亚杰等人的研究表明,儿童早期已经建立了关于物理等不同学科的科学经验[5]120-132。因此,科学在儿童早期已悄然发生。
反观生活,生活世界中的儿童充满了对周围世界的好奇与探索物质世界普遍性的热情。儿童在自己的生活世界里,不仅感受着力量、运动等事物的物理性质,也惊讶于动植物等生命科学的神奇。科学世界像一个充满着神秘物质的宝藏,引发儿童对世界的困惑与好奇。对世界的好奇驱动着儿童在形象的、不具有抽象符号的生活世界中,不断地像科学家一样探索周围世界,摆弄身边的器物,并向周围的人发问。由此,儿童成为人们眼中的“十万个为什么”“小小科学家”或“探索者”等。
正是儿童在生活世界中显现的好奇、好问等,给予人们开展儿童科学教育的信心,成为儿童科学教育实施的着力点。通过设计开放而具有弹性的科学活动、开展STEM活动等,促进儿童科学经验的获得[6]。《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不仅明确了学前教育包含科学领域,还具体阐述了科学教育的目标、内容与要求等。尽管人们尚未就儿童科学的具体内涵达成一致,但人们清楚地知道儿童科学教育的前进方向和最终目的是与抽象的、符号的、近代意义上的数理实验科学接轨,以期实现教育对科学的发展。从生活世界中的自明到理论研究的确证,无不说明儿童有科学。
科学与儿童关系的双重表现:历史的疏离与现实的亲近,让儿童科学更像是一个悖论。儿童与科学的历史疏离沉淀了国人意识中儿童“无”科学的观念,而现实中儿童科学教育又无声地指向儿童“有”科学,使得儿童有没有科学这一命题产生了相悖的结论。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儿童教育尽管明确提出了科学领域,且确定了儿童科学教育的目标与内容,但是就儿童科学是什么尚未达成共识。由此,只有明确儿童科学的内涵才能破解儿童科学的悖论,为儿童科学教育和相关研究驱逐“阴云”。
(二)儿童科学悖论的破解
人们期待明晰儿童科学的具体内涵,为儿童科学教育寻找具体的起点。但是,反观科学内涵本土化的历史过程,源自科学自身内涵的狭隘化理解,反而固化了儿童科学的悖论。也就是说,倘若只是将问题聚焦在儿童思维特征与科学作为高级文化品性之间的矛盾,儿童科学悖论是无法被破解的。因此,只有准确把握科学自身的本质内涵,寻找科学在人类与个体两个层面的统一点,才有可能破除此悖论。
1.“科学”本源的追溯与“儿童科学”的存在
科学进入我国的历史背景,造成了科学在本土化过程中概念的边界异动,进而导致了儿童科学的悖论。因此,作为西方文化的产物,科学只有回到西方语境明确其本源与发生,才能在此基础上从根源寻求儿童与科学的契合点。无论人们如何定义,儿童成长的逻辑与科学的关系都沿着其内在的轨迹向前发展,不会因为人们的定义而改变。因此,儿童有没有科学不是一个本质的追寻,而是一个定义范畴的问题。科学定义范畴的大小,决定着儿童科学有无的可能,更进一步决定儿童科学的内涵边界是什么。
科学,若狭隘地理解为近代以数理实验为标志的西方自然科学,显然,儿童是没有科学的。因为儿童不具备完全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若从科学史的发展理解科学,科学是自由人性发展的必然产物,那儿童具有科学发生的可能。因为儿童较少受到社会文化的浸染,能够保持自由的天性,坚持自我。当从最为广义的哲学视角审视科学时,科学是脱离于母体哲学的自然哲学。“哲学”(philosophy)是从古希腊文中的“爱”(philein)与“智慧”(sophia)演化而来。所谓“爱智慧”,就是热爱智慧并追求智慧。它是一种激情,来源于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7]。同时,又是一种穷根究底地思考人与世界关系的渴望[8]4。这种渴望不仅催促着人们探索宇宙奥秘、洞察人生意义;还驱动着人们为自身提供“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支撑点”。将科学回归到哲学母体生发的自然哲学,科学的发生在人的一生中都是可能的。
从人类生命诞生之日起,人类因对生命无限性的渴望而产生激情,伴随着这种激情的驱使,人类在生存过程中生发追寻普遍性的智慧。当提出普遍性问题时,哲学就产生了[9]6-14。哲学的发生孕育着科学,无论自然哲学还是哲学都是探寻普遍性,不同的是自然哲学将对象锁定在自然万物。科学在哲学母体中的悄然发生以提出普遍性问题为肇始。对儿童来说,当儿童像成人一样寻求物质世界的普遍规律时,儿童的科学便开始了。
2.科学的原初性与儿童的天性契合
科学自身不是致力于另外一个世界,而是这一世界,它最终说出的是我们经历的同样的事情[10]15。也就是说,科学的目的不是致力于创造另外一个世界,也不是为了将人类的发展与个体的发展分流截断,其最终表达的就是人们日常经历的同样的事情。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儿童或成人所经历的共同的事情,如日出日落、生老病死。科学的原初性正是指向对大千世界的普遍性追问,从而与儿童基于天性而生的自由探索行为相契合。
早在婴幼儿时期,儿童就已经出现科学发生的迹象[11]。其中,探索行为表现明显且频繁[12]67。总体而言,儿童早期关于自然现象好奇的复杂程度和深度不亚于成人。不仅如此,儿童在众多科学现象中更多关注的是物理现象,并以此作为基础,继而发展更多的关于自然现象的认识,最终个性化为自己的经验[13]320-325。马修斯的研究表明,儿童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出关于普遍性的哲学问题[14]27-44,就其内容而言,这些哲学问题中很多内容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因而,就普遍性问题与科学发生的原初性本质而言,儿童早期就已经身处科学之中。无论从儿童自身发展的角度,还是从科学发生的逻辑,儿童科学都是存在的。科学存在于我们之中,无论过去或者将来,无论是孩童还是成人。由此可见,儿童一定有其科学,只是儿童的科学是在个体早期发生的、有别于成人科学形态的科学。
二、儿童科学的内涵是什么
儿童科学悖论的破解揭示着儿童科学存在的理论正当性。在科学原初性本质的厘清与儿童科学正当性的逻辑论说中,儿童科学的内涵也逐渐明朗,并在科学内涵的原初性回归中进一步明确。
(一)回归科学原初性:寻求普遍性
在西方语境中,科学源于自然哲学,是人们对自然万物蕴藏的普遍规律的探索。当人们渴求人与世界的普遍规律时,哲学便开始了,而当人们将规律发生的主体聚焦在自然世界中时,科学便开始了。因而,科学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被称为“自然哲学”。科学的发生过程,就是人们利用理性将大量经验连接起来,从而在表面彼此独立和不规则的现象中,寻找它们的共同规律、发现自然的秘密,形成对自然的观念和知识[15]49-51。
但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发生在西方文化而不是东方文化?这是不同文化中不同的人性追求决定的。在近代科学以前,中西方文化中都有原初科学的发迹——人们出于好奇或者生存的需要,探寻着世界的规律。只是在近代以后,文化差异形成的不同人性追求对科学的影响逐渐显现,从而在西方文化中形成了近代意义的数理实验科学,而我国则错失了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的发生。然而,科学原初性本质——探寻物质世界的普遍性——在人类科学的发展史上从未间断。
无论是近代以前的“另类科学”,还是近代以后的数理实验科学,都始终在追寻自然世界的普遍性。因此,科学的内涵不是简单的以数理实验为标志的近代科学,而是包含了“另类科学”与近代科学。也就是说,科学发展的整个过程,都是人类探寻世界规律、寻找世界普遍性的过程。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在自由人性追求的鼓励下,西方文化中的人们突破了从描述性分类的“另类科学”向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的瓶颈,数学、理性和实验促成了精确测量、精准控制的近代科学。对于个体而言,科学也经历了一个从“另类科学”向数理实验科学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抽象思维和数理逻辑扮演关键角色。由此可见,科学在个体的发生和在人类的发生有着共同的要素和相似的逻辑,而个体早期科学发生的状态与人类近代科学之前的“另类科学”样态类似。
首先,自由人性是探寻世界普遍性的起点。虽然不同的文化环境对人性的塑造有所不同,但是相较于成人而言,儿童较少受到文化影响的天性直指人性自由,儿童的自由从精神到行为,从内在到外在,既表现明显也需求强烈。这样的人性起点促使儿童将好奇心投射到对自然万物的了解和探索中。自由不仅是西方文化中促成近代科学的重要精神,也是触发儿童向世界寻求普遍性的关键。
其次,好奇心是儿童科学与成人科学的另一共同要素。无论是人类还是个体,好奇心都是驱使人们走进世界的内动力。自由的人性起点与好奇心相辅相成,共同促成科学的发生。自由提供足够的心理空间容纳人们对世界的好奇,好奇心为人们自由探索世界提供动力。只有自由的精神才有好奇的心理空间,而束缚在樊笼中的精神则是被控制的、被定向的,无法对外界产生好奇。
再次,追寻物质世界的普遍性的目的贯穿科学始终。无论人们采取怎样的方式,“另类科学”的描述、分类与近代科学的数理实验的目的都是探寻世界普遍性,不同的是精确性和由此产生的控制、预测的能力不同。儿童与成人都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探索周围世界,只是由于身心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不同认知水平的探索结果。
最终,人类获得关于这个世界普遍性的知识,是为了解答思想疑惑或解决生存问题。对于儿童来说,生存问题还尚未进入他们的思想,但是他们和成人一样也有着解答思想疑惑的需要和体验。
(二)儿童原初科学的内涵界定
回归科学的原初性内涵,全面理解科学的过程中,科学与儿童的关联逐渐显现。生命与世界的相遇必然引起两者之间的适应和互动,这便触发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儿童向世界走近,科学也在儿童对周围世界的好奇中从生命里展开。儿童正是在对周围世界的好奇促使其发问、观察与解释[16]206。但是,将儿童科学简单描述为好奇心、观察探索等科学关键要素的组合,显然不足以破解儿童科学的悖论,驱逐人们内心的存疑。儿童随意看一看、摸一摸的行为如何评定是科学范畴或者不是科学范畴?儿童科学与成人科学的共性、差异是什么?儿童科学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什么?这些存疑还在继续。
好奇心等科学发生的要素已在儿童科学教育中被明确指出。但是,这些要素之间以怎样的机制表达儿童科学的内涵?“科学在人类发展史上的演进和在个体成长中的发生表明,古代的科学和儿童的科学是有可比之处的。”[16]206根据科学在人类与个体中发生的共同要素与逻辑相似性,可以将儿童科学的内涵界定为:以儿童自身兴趣为出发点,伴随着好奇心的驱使,儿童倾注注意力,进行发问、观察、探索、实验与逻辑运用等行为,最终形成对事物特征的认识或现象的解释的过程。
对于儿童科学内涵的解读,即儿童科学表现和日常行为表现的区分有以下四方面:首先,儿童科学发生的动因是好奇心。尽管儿童对世界的好奇可能无法从始至终显现在儿童科学发生的过程中,但是一定出现过。因为只有好奇的内动力才促使儿童分配注意力,从而牵引儿童关注世界的特征或现象。其次,儿童科学以儿童兴趣为出发点,即儿童的科学是自由的。儿童自我决定科学发生的内容、时间等,既不是迁就他人的目的,也不是在他人的强迫之下进行。因为科学的发生已经表明,只有自由的人性追求才能奠定原初的科学精神。儿童远离社会文化和成人功利取向,本着天性自由的状态正是科学自由而全面发生的最好时机。再次,在儿童科学发生的过程中,儿童的发问、观察、探索过程不是随意的行为,而是凝聚着儿童的注意力,这种发问、观察和探索等行为进入儿童的意识阈,需要儿童身心投入的过程。最后,就儿童科学发生的结果而言,是儿童在发问、观察和探索等过程中给儿童留下经验过程的痕迹。儿童科学发生的结果,无论是微小的还是显著的,都将成为儿童的科学经验,与儿童已有经验建立联接,促使儿童走向事物的更深处。
尽管无法保证儿童科学发生过程中的经验产出,但是对儿童而言,这个过程有内在的目的性。这种内在的目的性即使没有贯穿始终,或者说,没有以强烈的意义散发出来,但是早已融化、沉淀在儿童的生命里,延伸到儿童的成长中。就像亚斯贝尔斯所言:“哲学的本质并不在于对真理的掌握,而在于对真理的探究……哲学就意味着追求。对于哲学来说,问题比答案更重要,并且每个答案本身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17]5儿童科学的目的并非获得真理般可靠的知识,而是注重儿童探索过程中的收获,这种收获是多元、多层次的。在儿童科学的定义中,儿童科学表征的行为界限与其说是模糊,不如说它是包容的、多元的。
儿童科学以最包容的姿态容纳人类发展史上有关科学发展的初级形态和内容,从而注重人类早期科学的发展,跳出了近现代科学成就对科学的狭隘和禁锢。在儿童科学的发生过程中,儿童早期自我中心的特点决定了儿童总是以自己的天性为出发点展开对周围事物的认知[18]116,认识视角的局限留下认识经验的残缺和进步发展的空间;与此同时,儿童与世界浑然一体的起点状态决定了儿童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都夹杂着强烈的主观意愿。随着儿童精神的成熟与独立,主客体关系逐渐建立,泛灵观念日渐退却,儿童的好奇心将其引向更为客观与恒定的世界,为儿童进入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奠定基础。
三、为什么要明晰儿童科学的内涵
通过剖析人类科学发生逻辑与个体科学发生逻辑的相似性和契合点,不仅可以破解儿童科学的悖论,明晰儿童科学的内涵,还能揭示科学发生逻辑的整全性。儿童科学作为儿童科学教育的发生原点,明确其内涵与边界的基础上,不仅为儿童科学教育定位逻辑起点,也为培养儿童科学精神而建构适宜的科学教育提供初始条件。
(一)揭示科学发生逻辑的整全性
科学作为人类最高、最具特色的文化成就,提供着人们对世界恒定的信心。无论个体层面还是人类层面,将科学的发生置于生命中审视,生命的连续性决定了科学发生逻辑的渐变,因而,科学从来都不是断崖式或跳跃式的突现。科学发生的主体是人,无论是作为人类的人还是作为个体的人,科学的发生都是连续的统一体,即便科学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也不能遮蔽内在逻辑的渐变。随着人类心智水平的不断成熟,人类与个体各自遵循内在的规律向前发展,但是,儿童作为时间与空间的交点,不仅演绎着个体科学的发生、发展规律,也蕴藏着人类科学发生发展的特征。基于科学在人类进化中的嬗变,明晰科学对于个体发生的原初内涵,以儿童为个体与人类的交叉点,在个体与人类的发生的双重逻辑之上,揭示科学发生逻辑的整全性。
就科学在人类社会的发生意义而言,不仅要看到近代以来的科学成就,更要关注为近代科学奠基的“另类科学”的意义。虽然我国没有发生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但中华文明中蕴藏了丰富的“另类科学”,这是中华民族在探索宇宙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不能因近代意义的科学没有系统化发生而贬低自己的历史文化,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边缘。科学发生逻辑的整全性,将对科学的审视回归到科学史的长河中,在人类层面凸显“另类科学”像根一样为枝繁叶茂的近代科学供给养分的作用。就科学在个体的发生而言,虽然数理逻辑的心理结构是儿童发展数理实验科学的前提,但是,早期儿童只有在生活世界中获取足够丰富的、具体的科学经验,才有可能形成数理逻辑的心理结构。日常生活不仅是科学发生的本源世界,也是儿童科学发生的原初场域。聚焦儿童科学经验发生的原初场域,关注儿童生活世界中的具体经验,为儿童数理逻辑的心理结构夯实经验基础。
同时,科学发生逻辑的整全性提醒人们全面关注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不能让花繁叶茂遮蔽根的基础地位,并由此为科学教育的功利化敲响警钟。由于人的成长节律规定了以人为发生主体的事物的发展逻辑,因而,科学作为以人为发生主体的探索活动,只有遵循人类生命成长节律,才能长远发展。由此,在科学教育中,不能将科学教育仅仅聚焦在科学的高级成就,更不能仅仅从科学现有的成就向各个阶段的教育进行延伸。这将违背人的成长节律与科学的发生逻辑,从而导致科学成为生命的枷锁,反而束缚人的发展。
(二)定位儿童科学教育的逻辑起点
儿童作为科学发生的主体,是人类精神发生的原初存在,有着与成人不同的心理水平和精神世界。儿童是成人生命的起点,儿童科学也将是成人科学发展的逻辑起点,这是由生命成长的节律对科学发生逻辑的规定决定的。然而,一直以来,人们清楚地知道儿童科学教育的终点是走向抽象的数理实验科学的发展,继而拓展科学为世界祛魅的能力,而不清楚科学教育逻辑起点在哪里。正是因为确定了儿童科学教育的终点而不清楚其起点,儿童科学教育一直接受到更多来自抽象数理实验科学的影响,而忽略了作为起点的儿童科学。如此一来,儿童科学教育起点的迷失导致了人们错误估计科学教育需要的人生距离,进而将儿童推向现代科学的发展阶段。在此心态催生下的科学教育会违背科学发生的规律,破坏儿童科学发生的关键要素(天性自由),也将科学教育过程置于破坏创造性之机械重复的境地。因此,只有明确儿童科学的内涵,儿童科学教育才有一个明确的逻辑起点,从而为儿童科学教育敞明生命的长度和宽度,即儿童科学教育的具体内容与形式既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也要基于科学在不同身心水平的内涵;进而避免儿童科学单向靠近成人科学而远离儿童科学教育生发的逻辑起点——儿童科学,防止成人科学无限向儿童科学延伸,吞没儿童科学的阈限。
早期儿童科学教育的核心不是科学知识的获得,而是通过设置儿童化的科学课程、环境、方法及评价等,提升儿童综合能力[19],促进儿童获得符合孩子本性的生活习惯和基本素养等[16]235。当儿童的好奇心在生活中被周围世界唤醒的时候,儿童主动进行的系列动作和行为,就是寻求打开精神枷锁的过程。当困惑成为儿童自由的绊脚石时,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儿童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现象的解释符合自己的经验思考逻辑,从而打开“思想的结”。儿童科学正是儿童主体能动的探索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初显的科学精神和品质等。
回顾科学发生逻辑与发展历史,反观儿童成长的身心规律,倘若用成人的科学审视、定义儿童的科学,就是将科学在人类文化中的智慧结晶压在儿童的原初科学之上,这对于儿童原初科学来说是“重负”。儿童与生俱来的自由天性为厚植科学精神提供了契机,而科学精神正是科学教育培养的核心。在儿童科学内涵明晰的过程中,科学精神的人性之源也得到敞亮。因而,儿童科学教育作为科学教育的起点阶段,不仅要保护儿童的好奇心,更要尊重儿童的天性,为儿童科学的后续发展积攒生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