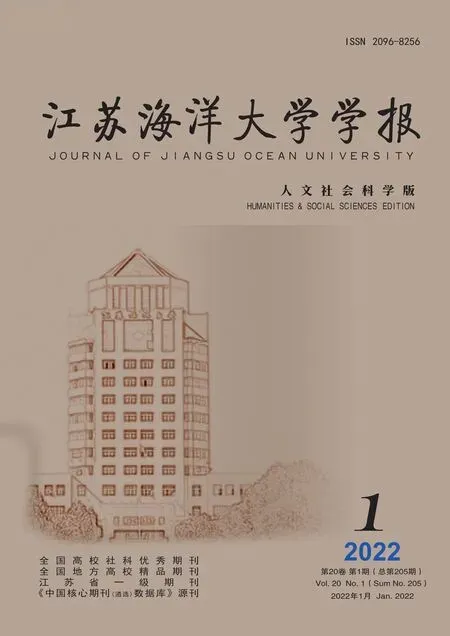从《开天辟地》到《1921》:建党献礼片的创新性表达*
沈玲玲
(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 视觉艺术系,安徽 芜湖 241000)
作为时代的缩影,电影作品有着不可替代的教育功能和艺术价值。在其成长历程中,中国电影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舶来品到具有中国特色电影内涵的多样阶段。从1949年至今,系列关于加强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政策、文件,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指导与保障,促进了电影文化传播,推动了电影事业的发展。建党献礼片重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和发展历程,表现了救国救民、美好生活的初心和使命。百年电影纪录史传播了中国文化,将治国理念进行了艺术化的表达。建党献礼片作为中国电影的特有类型,具备人民性、革命性、自觉性等特征,以具体场景、关键人物、真实事件演绎了党的革命故事,建党献礼片与党的发展紧密相连、相互促进。从《开天辟地》到《1921》,建党献礼片从初心与发展回归于内涵拓展,呈现多元形态,开辟了新阵地。
一、“以史为镜”——建党献礼片的影史书写
中国电影百多年来的发展,离不开党对电影事业的引导与推动,从早期中国电影的诞生、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影视相关机构,党在电影事业的发展中是领导者、推动者的角色,为时代精神的记录、传播提供了理念支撑、形象引领、科学规划。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前,献礼片作为目的明确、组织严谨、计划周详的国家工程被提出来,作为周期性重点创作项目,以其独特的类型风格和专业的创作团队,显示了日益强大的品牌号召力。
(一) 时代发展推动类型融合与创新
长期以来,中国电影的创作类型以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为主体,其中早期的主旋律电影作品强调以宏大场景和历史事实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多维度传播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发生、转向和胜利,使革命底色在人民心中扎根。进入信息时代,碎片化的短视频成为了大众精神消费的主体内容。主旋律电影的宏大叙事因为个性弱化、个体忽视而与社会生活产生了距离,使其在凸显国家意志和集体利益的同时,却对大众审美的引导收效甚微。而中国的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则偏重于大众娱乐消费,唯票房、唯收视率、唯点击率的偏执现象丛生,大众视听接受出现低俗化倾向。随着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的深层次改革和艺术创作格局的更新,传统的三分法已经不能概括当下中国电影的面貌,尤其是政治立场鲜明、红色文化突出、商业投资制作和艺术元素融入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1]。《1921》不仅是具有时代意义的献礼片,更是精彩的商业电影,时代发展逐步模糊了主旋律、商业、艺术电影的分界线,具有工业化的制作模式、商业化的叙事风格、艺术化的视听表现在融合中演变,在变化中提升,以具体的电影作品深化了群众的爱国情怀。
建党献礼片融合了政治、艺术和商业的多元文化,以其特有的方式打造银幕上的中华民族新史诗。近年来的家国、抗疫、脱贫攻坚、全民小康等题材的影片点燃了十四亿中国观众的热情,观众需要电影,产业需要电影。《开天辟地》《1921》这两部影片以红色历史再现了战争年代、传承了优良传统、歌颂了革命精神。
(二) 新旧交替推进文化汇流与认同
中国电影在体制变革中经历了从事业方向到产业布局的调整,建党献礼片从最初的主题设计到如今的创意理念更加注重传者和受者的主体性,注重市场消费规律,实现了从事业组织的模式化到产业发展的类型化转变,逐步呈现出富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需求、深受观众喜爱的风格和类型。1991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执导拍摄的建党七十周年献礼片《开天辟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进程,选择从五四运动切入故事,影片整体创作思路为“以人托史”,展现了基于民族认同的、顺应时代对历史和生活的解释以及不断更新的意识形态话语方式[2]。电影《1921》进入大众视野,在碎片化的信息时代以多条故事线索引燃建党初期的革命火种,以积极正面的红色文化提高大众政治意识,满足了中国故事的正向传播。
(三) 艺术初心回归真实革命历史
《1921》由郑大圣和黄建新联合执导。生于电影世家的郑大圣,其母亲是第四代导演黄蜀芹,她的代表作有《围城》《当代人》《青春万岁》等。郑大圣家学渊源,从小受到很好的艺术熏陶。郑大圣善于讲述个体人物的状态,为影片注入另一种文艺情怀。黄建新导演从《建国大业》开始特别注重商业元素的运用,以对接当下的主流观众。两位导演把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片、文艺片进行了很好的结合,《1921》回归到人物的塑造,回归到故事的讲述,以人为中心来叙事和表情达意,相比《开天辟地》来说,故事更集中、更流畅、更完整,影片与历史是共存状态,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是空间,在这个空间能看到的是过去的抗争、伟大的牺牲以及未来的希望。
《1921》描述了青年时期革命领袖们革命理想形成的过程,影片围绕“开会”展开,重点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背景、议程以及代表们为民族解放传递火种、点燃希望的生动历史故事。影片以“火种联想”为线索,从影片开头的枪火炮火,到李达在阳台上因为一根火柴引发的心灵震动,此时观众看到了他内心世界中的希望之火,再到毛泽东在黑暗中点亮烛光,照亮了整个中国,这是中国寻找崭新革命之路的进程映射,在歌颂英雄的同时回归了初心。
二、“以人为本”——建党献礼片的人物刻画
《开天辟地》和《1921》表现出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与蜕变,突出了从主旋律电影到新主流电影的变化。两部影片对初心与发展价值的终极指向是相同的,都是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这是其可比性之所在。人物刻画是文艺创作的重要任务,是中国英雄形象谱系强化和扩充的重要途径,两部影片通过塑造典型人物为时代传神写照,以具体的人物形象展现了时代精神的文化表征,以人物的外形、动作等元素突出了角色特征。《开天辟地》通过许德珩的敲门、邓中夏的宣讲、李大钊捐出怀表等一系列故事展现了青年一代的热情,通过人物塑造及其关系的建立以及人物行动与性格的刻画还原历史,而革命人物的突显、平凡人物的点缀以及与反派人物的冲突,在献礼片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一) 典型人物的类型划分与性格刻画
1 革命人物的价值引领 《开天辟地》以革命人物视角介绍历史,对革命人物的表达尝试摆脱传统政治历史的话语定式,政治功能意识形态明显,通过影像进行教育宣传,但是观影人大多为固定人群,普及性不强。而《1921》在人物塑造方面,以13位共产党员为主角,剧情主要围绕“开会”而展开,通过故事情节的层层深入,找参会人、找会场、布置会场、代表报到等,虽然部分片段没有深入挖掘,但重要历史细节的精心设计使每个角色的特点突出、功能明确,在个性发展与共同目标的多重表达中形成点面关系,观影人的普及面较广。《1921》对革命人物的刻画体现为在学习中深化思想、在抗争中净化思想、在牺牲中实现升华,以思想改造升华了胜利的价值和意义,人物没有淹没在群像之中,而是通过行为、语言强化了角色性格,折射了内心世界,明晰了道路选择,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在人物心中扎根。
2 平凡人物的点缀烘托 近年来的历史题材影片往往都紧紧围绕主要人物来组织情节、揭示性格、讴歌英雄、阐述哲理,主要人物的平凡出身与其之后的伟大成就形成对照,平凡人物的默默耕耘与主要人物的重要作用形成对照。
一是“生于平凡,终于伟大”。《1921》中由张颂文饰演的何叔衡,只是旧社会的一名穷秀才,当军阀焚烧书籍时,他大声呵斥对方,他的声嘶力竭也十分清晰地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痛和无助传递出来;何叔衡被追杀时,他一路奔向山巅,到山顶后,仰天看了一眼,随后纵身跳下山崖,从容赴死。何叔衡从秀才到革命战士的转变、从平凡人物到革命英雄的转变以及最后英勇牺牲的场景,对观众实现了潜移默化的宣教,整部影片有血有肉,展现了他由一个普通人一步一步成为革命家的过程。
二是“平凡小人物”的点缀。《1921》中,平凡女孩与主要人物李达的对视隐喻着希望。雨过天晴,刚刚搬入新家的李达透过窗户,看到了微笑的小女孩,与小女孩第一次对视。第二次是夜晚,李达划着火柴、吟唱共产主义歌曲的时候,他又看到了小女孩,向她摆了个睡觉的动作,小女孩微笑着回去休息了。第三次是清晨,李达爬到房顶,再次看到了小女孩,小女孩站在窗口跟他打招呼。第四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庆典上,身着新衣服的小女孩,开心地站在一群小孩子中间。寥寥可数的几个镜头,既表现出平凡女孩的天真无邪,也是李达淳朴内心的真实写照。尤其到了片尾,小女孩的形象“跨越”到了新中国,直接上升为“百年回望”的隐喻性形象。
3 反派人物的对比映衬 反派人物的道路选择以及和正面人物的矛盾强化了电影的戏剧性效果,升华了影片的艺术价值、审美格调。角色表达形式的多样化使反派人物更加鲜活,衬托了正面典型的伟大。
一是蜕化变质为反派人物。这类反派的形象暗含双层隐喻,明线是其曾经是怀揣梦想的有志青年,暗线是其渐渐成为走向异端的叛徒。《1921》中隐含着的反派人物陈公博与周佛海,通过细微表情的抓取折射出转型反派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其精致服装、头型、饰品的形象设计突出了其对于享乐生活的向往,与其他一大代表的造型差异反衬出其革命态度、理想追求的模糊与摇摆,让其具有复杂性。其中周佛海因吃冰淇淋拉肚子而让其他代表随便代为投票的细节刻画、陈公博夫妇的风花雪月以及其无法忍受公共住所的态度、周佛海与陈公博携伴侣在上海街头相遇的场景等,都向观众暗示了这两人最终一定会与正确道路渐行渐远,由正面角色蜕化变质为反派并最终走到人民的对立面。
二是始终为反派人物。人物性格的设定不能扁平化,也不能非黑即白呈现二元对立,立体生动的人物形象有助于丰富影片的细节和内涵。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是单线叙述,反派人物形象塑造不够。《开天辟地》中的反派典型代表是徐世昌,影片中他登场后即下令镇压游行的有志青年,枪杀请愿的热血青年代表,其人物性格及反派角色形象未进行多层次处理。而《1921》中的反派人物代表是上海巡捕房第一位华人督察长黄金荣及他的两名手下,作为反派典型,他们为了金钱和地位等利益使用了大量卑鄙手段,疯狂镇压革命者,与影片中的革命者为国为民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影片在这里运用了多线叙事的方式。
(二) 青年演员演绎角色新形象
基于受众的传统视觉经验,建党献礼片在“形”像且“神”似上有较高的要求,不仅要形神具备,还要为影片增加“亮点”“量点”。当下的化妆造型技术叠加数字虚拟制作技术,使角色的外在造型在技术层面上实现了逼真准确,而“神似”则需要演员对历史能够宏观把握,对角色个性和思想能够深入了解,才能做到表演记录和视听呈现的一致性。
1 角色“活化”挖掘内容深度 《开天辟地》对领袖人物和英雄人物的塑造将形似放在首位,如王霙饰演毛泽东、孙滨饰演邓小平、邵宏来饰演陈独秀等。31岁的王霙从22位青年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进入《开天辟地》剧组首次饰演毛泽东,自此王霙作为特型演员专注饰演一个角色,他年轻时饰演青年毛泽东,表现伟人的激情澎湃;中年时饰演中年毛泽东,表现高瞻远瞩的伟人风范,通过自身的年龄成长配合不同阶段的角色饰演。通过特型演员的表演、化妆造型的重塑、道具服装的复原,强化了像似符号的形象性,这是历史剧的传统模式。
《1921》的选角标准不局限于特型演员,在角色定位上“形”似不再是首要标准,其以文献为支持、以史实为依据,确定每个人物的性格甚至是形态动作和语态姿态,同时也找到他们共处一个特殊时代的历史共性,使得这些人物的思想动机、行为方式、道路选择、情感冲突都有了内在的性格支撑,同时也有了鲜明的时代烙印[3]。《1921》导演组强调演员要将角色“活化”,让角色深入人心。比如影片中陈坤饰演的陈独秀,用肢体语言表现陈独秀为了坚持理想表现出的执拗和疯狂;张颂文饰演的何叔衡,人物经典形象分层次表演,演绎了一个旧社会的秀才面对军阀焚烧书籍时所表现出的无奈抗争,参加革命后的满怀梦想,面对敌人追杀时的从容赴死。分层次地去演绎英雄,经典镜头极具感染力。毛泽东的扮演者王仁君通过海量阅读以及与前辈艺术家、导演广泛交流,寻求与毛泽东当时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的契合点,比如刚来到上海时坐上汽车探出头对大城市充满好奇的毛泽东、调侃湖南同乡李达“不吃辣”的毛泽东、和杨开慧不舍道别的毛泽东等,都颇为传神,许多细节都从不同维度塑造了一个更加立体的毛泽东形象,从观众的视角,他就是“真实”的毛泽东。影片《1921》艺术地“活化”了每个人物角色,准确传达出影片的历史深度和思想深度。
2 明星效应增强视觉意象 从特型演员到明星演员,再到流量明星,近年来中国革命家的影视形象塑造路径和方式更为丰富。影片在要求演员神似、形似的同时,也要追求演员的流量,唐国强、保剑锋、刘烨等演员在成名之后饰演过伟人毛泽东,其明星效应拓展了观影人群,观众们已不在意明星们与所扮演的历史人物是否足够形似。
《1921》选用50位年青演员来加盟献礼片,并阶段性发布角色海报,让海报成为象征符号,完成了演员成为明星符号、被符号化的身份建构。从一百年前革命者的奋斗之路到如今中国的富强之路,百年前后的历史情境差异虽然大,但演员要在两者之间实现对接,要穿越到一百年前的历史情境当中去触摸、感受真实历史,用典型的青春肖像向观众展现历史人物故事,激发话题、提升热度,感受当时那种探索精神。影片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体现影片的现实价值,让观影人与历史呈共存状态,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是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观影人看到的是未来的希望。
三、“以影载道”——建党献礼片的视听建构
相较《开天辟地》和《1921》的视听体验,电影制作技术的变革催生了更为丰富的影像呈现,从有声到数字环绕声、从黑白到数字调色,从胶片到数字虚拟影像,建党献礼片以具体直观的视听形式展现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更为专业、更具时代感的电影创作方式激发了新的美学主张和审美形态,扩充了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技术革新、理念创新加速了建党献礼片的成长,多样视角的介入、数字影像的模拟让受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和谐于视听奇观的营造。电影数字技术的发展使电影艺术创作进入了仿真时代的拟像阶段。
(一) 数字特效——新技术真实再现环境音效
《1921》为了表现大上海的现代化风格,影片的摄影及后期制作用3D技术和高帧率技术强调回溯现实的精度,用上万只灯泡,星星点点照亮街道,用绚丽的霓虹灯来凸显上海这颗东方明珠。影片把数字特效呈现的上海与现实中的上海同一镜像,数字特效产生的视觉奇观令人无法分辨出其与真实事物的区别,营造出了最具东方魅力的上海。影片中毛泽东和杨开慧看烟花的情节,为了增强电影的空间感以增强真实感,摄影组采用国际先进的组合灯阵,用整个LED的屏幕,建筑上方打出绚烂的烟花图像,再通过后期制作将烟花绽放的闪烁效果展现出来,最后用数字特效将灯从画面中扣除。
《1921》生动还原、真实再现了时代氛围,将多元的声音交织,例如牢门打开的声音、自行车的铃铛声、奔跑中心脏跳动的声音、有轨电车的滴滴声、舞动红旗的声音、划火柴的声音、人群的呐喊声等声音交织在一起,经过数字调试,使观众沉浸于数字打造的逼真奇观或数字情境。
(二) 运动表意——新设计把控整体叙事节奏
运用各种运动造型表现手段,不仅可以从各种角度连贯而完整地再现一个动作过程的各个方面,也可以将宏大的场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4]4。《1921》中在博文女校阁楼中深夜畅谈的那场戏,摄影机镜头不仅要对群像有刻画,也要对个体进行细节描绘,比如某个人在说话,镜头就需要单独描绘,画面需要有近有远,此时导演将摄影机进行两圈360度的旋转,设计了720度的调度,为了不让画面呆板,摄影机没有停留在一个圆心转一圈,而是有升降的维度,让画面更具动感。
《1921》中,毛泽东在法租界被拦后沿着大街在夜幕中奔跑,奔跑的背景时而是璀璨的烟花,时而是霓虹闪烁的十里洋场,还不时切入他当年离开家乡时的奔跑闪回,回忆父亲的追赶和母亲“不要回来”的愿望,画面以镜头写意,以音乐律动,这一奔跑段落,也是毛泽东内心世界的投射[5]。影片采用蒙太奇式的多时空混剪,时而是在湖南家乡为了反对封建社会的种种压迫被父亲追着跑,时而是在上海标志性建筑外白渡桥上带着理想奔跑,这是看到未来期望的奔跑,体现了不同时空下的思想转变,也让观众看到了毛泽东从一个平凡人逐步成为伟大人物的成长历程。
(三) 符号叙事——新结构明确重点细节指向
《开天辟地》采用的是宏大叙事的线性编织形式,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的视角,准确演绎、全方位呈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过程。而《1921》则采用多线叙事,运用符号叙事创造了电影的想象空间,使影片更富有逻辑性,进而丰富叙事的内涵[6]。《1921》以平凡人物作为角色基础,以李达夫妇为中心人物,组织五湖四海的13位革命志士陆续来到上海的开会地点。影片将六个不同空间里的故事素材集中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电影文本,在时空转换中使平凡走向伟大。影片中多条线索并进,有日本密探叙事线、共产国际代表参会的叙事线、法租界巡捕房的叙事线、陈独秀三次出狱的线索(三进三出表现了五四运动的起起伏伏)以及最后共产党员陆续牺牲的线索,多条线索平行共进,强化了时局的复杂。影片的交叉结构丰富了故事情节,深化了叙事的内涵,支撑起了整部电影的架构。
电影《1921》中,用生活细节来还原历史,在复杂的叙事结构中加入生活中常见的象征性符号,比如在阳台王会悟给李达端上的上海老字号“乔家栅”汤圆、李达进出印刷厂时让观众看到的非遗文化活字印刷术,以及租界石库门等一些传统胡同与法租界欧式建筑的对比。影片通过服装、化妆、道具等去接近和还原历史,自行车、眼镜、汽车、三轮车、街上行人的整体装扮等,都有着强烈的年代感,瞬间将观影人带到1921年的上海。环境和观众产生共鸣,影像符号带领观众根据生活中所积累的储备知识按自己的理解方式诠释这些符号,使虚构的电影世界与现实世界接轨。
(四) 光线色彩——新基调风格的主观渲染
影片创作中,用光线与色彩去塑造人物形象,可以使人物形象更为高大、立体。《1921》中有一个片段是一大代表围桌开会的场景,影片中仅用了一盏煤油灯,就制造出光影的不同层次,光的投射距离与衰减程度使静态的物影和动态的人影呈现出真实的现场,烘托出紧张、凝重的气氛。光影还原了每位代表独特的造型,同时又有了情绪的暗示,使每个人物立体饱满,用光影叙说党史。此外,黄轩饰演的李达在清晨跳出屋顶的老虎窗欣喜欢呼的那场戏中,李达在阁楼上迎接日出,摄影组原先是打算打灯以达到理想拍摄效果,可就在那时太阳升起,大自然明媚的阳光直射营造出来的氛围很诗意、很绚丽,拍摄效果很好。
从《开天辟地》到《1921》,建党献礼片作为一种影视文化产品,塑造了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了时代精神。《1921》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过程,穿越1921到2021百年中的不同历史时期,在建党初期遭遇重重困难时、在革命先辈牺牲时、在和平鸽从天安门广场飞过时,时间在变、环境在变,但建党精神没有变。影片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完成情感表达,其主题是新生、冲破、希望,以青春为基调,以光影艺术为笔触,向百年前的热血青年们献上一曲致敬之歌,为百年后生逢盛世的新时代青年绘制了一幅精神蓝图,以伟大建党精神唤起当代青年人的雄心壮志、责任担当,将建党初心潜移默化为这一代人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