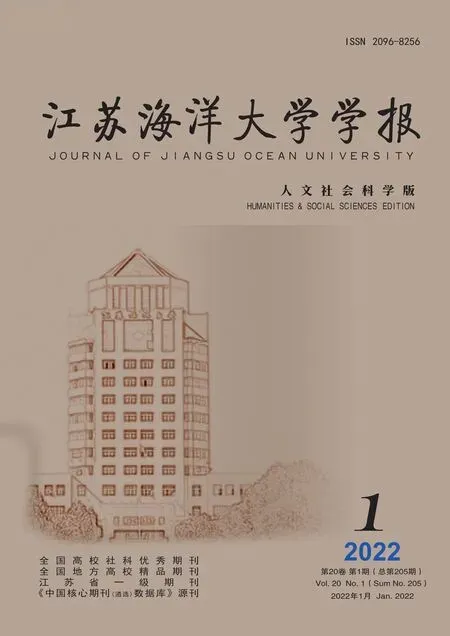《西游记》中的宝物书写及其文化编码*
王一雯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说文》:“宝,珍也。”“宝物”对应物品的世俗价值,多为珍稀之物。明清小说中的宝物书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林林总总的宝贝、兵器不仅频繁出现在神魔小说中,也扩散到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甚至一些世情公案等题材的小说中[1]。龚维英指出,在《西游记》叙事中,宝物占有非常大的比例,展现了丰富的文化意涵[2]。《西游记》中的宝物大都来历非凡,又与儒道佛三教文化紧密相连,这些物品兼具器物、宝物和圣物等多种文化性质。作为世代累积型的作品,《西游记》中的宝物书写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
一、物欲:《西游记》中宝物书写的泛化
欧阳健在《中国神怪小说通史》中提到:“在神怪小说的发展中,‘宝贝’走过了一段由财富的象征到新型武器的道路。宝贝在《西游记》中的频频出现和广泛运用,与《平妖传》之主要依恃咒语做法,遂有了根本性质的不同。”[3]406-407然而事实正好相反,《西游记》中的人物频繁使用宝物进行战斗这一叙事现象,显示了日常器物的宝物化过程。
志怪笔记中,精怪可以变身为美貌女子引诱男子;原始神魔故事中,精怪往往使用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攻击人类,不使用法宝或武器。《西游记》中,作者却频繁地书写宝物,营造了“珠光宝气”的三界形象。西游故事中还经常出现妖魔“盗宝”的情节。比起传统的精怪炼化自己身体某部分的行为,《西游记》中,不论是神仙还是妖魔,大多都拥有自己的兵器或法宝。当兵器除了格斗功能之外还存在其他特殊功能时,就具有了“宝”的特征。这体现了宝物书写模式的进化,以及道教与民间传说对神魔小说书写的影响。
《西游记》中“盗宝”情节很多,如赛太岁盗取观音的紫金铃,独角兕盗取太上老君的金刚琢,黄眉老佛盗取弥勒的金铙、人种袋,金角银角盗取太上老君的紫金葫芦、羊脂玉净瓶、七星宝剑、芭蕉扇和幌金绳等。这些宝物虽然在凡间神通广大,但在仙界只是神仙随身的一般物品,如紫金葫芦是太上老君炼丹时的日常用具、幌金绳是太上老君勒袍的带子等。在仙界,宝物更多地作为寻常器物被使用。
“宝物”之“宝”代表了其珍稀性和世俗的价值,“宝”的特性延伸到一系列日常器物之“用”上。在人间,这些日常器物就成为了神通广大的法宝。它们的制作材料往往极不寻常,宝物材料的神圣性提升了它们的价值。这些材料多来源于混沌初开之时,是上古神物。如玉兔精的兵器是捣药杵:“跑到御花园土地庙里,取出一条碓嘴样的短棍,急转身来乱打行者。”虽然“金箍铁棒有名声,碓嘴短棍无人识”,但“源流非比凡间物,本性生来在上天”[4]1171-1172,捣药杵的珍贵之处在于它的材质来源于天界;又如“宝杖原来名誉大,本是月里梭罗派”[4]273一句,说明沙僧宝杖的材料来源于月中桂树;再如紫金葫芦是混沌初分、女娲补天时昆仑山脚下的神物,来历非凡;而芭蕉扇扇出的火“不是天上火,不是炉中火,也不是山头火,也不是灶底火,乃是五行中自然取出的一点灵光火”[4]440。这类民间常见的器物均被赋予了宝物的色彩,和道教、民间宗教故事互相结合。
除了日用器物的材质被“宝物化”,获宝的过程也提升了物品的价值。《西游记》中常见的“获宝”方式是地位尊贵的仙佛赐予宝物。如猪悟能和沙悟净提到玉帝曾御赐宝物:“名为上宝逊金钯,进与玉皇镇丹阙。因我修成大罗仙,为吾养就长生客。敕封元帅号天蓬,钦赐钉钯为御节”[4]234;“玉皇大帝便加升,亲口封为卷帘将。南天门里我为尊,灵霄殿前吾称上。腰间悬挂虎头牌,手中执定降妖杖”[4]270。“虎头牌”和“降妖杖”都是官方地位的象征。这些被贬或者私逃下界的妖怪可以获得宝物,间接说明了他们原有的地位。
“宝物”是身份的象征。在收服小白龙时,“菩萨上前,把那小龙的项下明珠摘了,将杨柳枝蘸出甘露,往他身上拂了一拂,吹口仙气,喝声叫:‘变!’那龙即变做他原来的马匹毛片”[4]187。宝珠对于龙族来说是身份的象征,“颔下之珠”的典故出于《庄子》,最早的西游故事如《西游记平话》等并没有提及白马。因此,“宝物”书写的泛化现象应流行于明代,呼应着“晚明兴起追新逐奇的社会时尚,新富阶层追逐社会地位,昂贵物品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志”[5]248-252的文化风气。
从宗教仪式角度看,宝物是祭祀的必要物品,具有神圣性,通常是特殊的食物。《西游记》中人们“食用”以及希望食用的东西,几乎都是与“长生不老”相关的仙家至宝,如悟空偷吃的蟠桃和太上老君的仙丹。唐僧的肉身在妖魔世界中也被刻意物化为“宝物”,贯穿于整个叙事过程。
细究《西游记》中取经团队所遇的灾难,前四难是唐僧出世之难,其余七十七难是前往灵山取经遭逢的磨难。各路妖魔的目的多是“吃唐僧肉”以求长生不老。因此,“意象化的唐僧肉是九九八十一难的主要诱因。围绕“吃唐僧肉”,作者叙述了取经人的生存危机,为摆脱生存危机而生死肉搏,寻找外援,智慧脱身”[6]。可以说,“吃唐僧肉”不仅是一个叙事情节,还是《西游记》中最主要的叙事结构。然而在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之前,虽然唐僧曾差点被虎精、熊精、牛精和黄风怪吃掉,甚至沙僧皈依前也曾“一个旋风,奔上岸来,径抢唐僧”[4]268,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唐僧肉“长生不老”的价值。第十三回《陷虎穴金星解厄》中,唐僧被妖怪抓住,其中一怪说:“不可尽用,食其二,留其一可也。”[4]158这说明其根本不知道唐僧的价值。第二十回《黄风岭唐僧有难》里,黄风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锋说道:“今奉大王严命,在山巡逻,要拿几个凡夫去做案酒。”[4]249洞主听说小妖捉到唐僧,只说“我闻得前者有人传说,三藏法师乃大唐奉旨意取经的神僧”,小说没有提及洞主知道唐僧肉有“长生不老”的功效,只说“吃了他不打紧”[4]250,可以“慢慢的自在受用”[4]251,仅暗示吃修行人之肉有好处,并没有明写究竟是什么好处。
在元杂剧《西游记》第十一出中,曾提到取经人九世都在流沙河遇难:
有一僧人,发愿要去西天取经,你怎么能勾过得我这沙河去!那厮九世为僧,被我吃他九遭,九个骷髅尚在我的脖项上。我的愿心,只求得道的人,我吃一百个,诸神不能及。[7]23
吃得道之人是妖怪提升能力的方式之一。世德堂本《西游记》第二十二回写道:“师徒们正看碑文,只听得那浪涌如山,波翻若岭,河当中滑辣的钻出一个妖精,十分凶丑”,“项下骷髅悬九个,手持宝杖甚峥嵘”,“一个是久占流沙界吃人精,一个是秉教迦持修行将”[4]268。故事中却没有强调沙僧为了“长生不老”这一目的吃唐僧肉,更没有说九个骷髅是唐僧,或者九个取经人都是唐僧转世,从文本中我们仅能知道吃取经人对于沙悟净来说相当于普通的吃人。
尸魔出现后,取经团队在西行途中的磨难才转为妖怪欲吃唐僧肉以求长生不老、唐僧被擒后悟空前去解救的模式。第二十四至二十六回的“偷盗人参果”事件成为将唐僧身体宝物化的关键情节节点。《西游记》第二十六回明确提到了服用人参果后“尽是长生不老仙”:
众小仙遂调开桌椅,铺设丹盘,请菩萨坐了上面正席,三老左席,唐僧右席,镇元子前席相陪,各食了一个。有诗为证。诗曰:万寿山中古洞天,人参一熟九千年。灵根现出芽枝损,甘露滋生果叶全。三老喜逢皆旧契,四僧幸遇是前缘。自今会服人参果,尽是长生不老仙。此时菩萨与三老各吃了一个,唐僧始知是仙家宝贝,也吃了一个。悟空三人亦各吃一个,镇元子陪了一个,本观仙众分吃了一个。[4]329
“人参果”事件前唐僧所受的灾难和之后的灾难几乎可以“截然二分”。《西游记》以前期故事中最贵重的“宝物”之一——人参果,渲染和强调了取经过程中最核心的“宝物”——唐僧肉。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首次明确吃唐僧肉能够长生不老:
却说常言有云:“山高必有怪,岭峻却生精。”果然这山上有一个妖精,孙大圣去时,惊动那怪。他在云端里,踏着阴风,看见长老坐在地下,就不胜欢喜道:“造化!造化!几年家人都讲东土的唐和尚取‘大乘’,他本是金蝉子化身,十世修行的原体。有人吃他一块肉,长寿长生。真个今日到了。”[4]332
妖精听闻的信息是“十世修行”使唐僧肉具有让人“长生不老”的功能。这一说法的来源及传播时间不明。在尸魔出现以前,所有妖怪都没有以“吃唐僧肉长生不老”为目标,这显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妖魔消息不灵通。这一情节安排显示了作者的特殊用意,他将唐僧的身体进行了“宝物化”的强调处理。首先,作为“尸魔”,对血肉的渴望使其不满足于仅维持生存或享受口腹之欲的“人肉”,而追求具有“长生不老”功能的“唐僧肉”;其次,该章节照应了唐僧吃“人参果”的情节,“人参果”与“唐僧肉”并置,成为可以“长生不老”的宝贵食物。《西游记》刻意强调“肉身”的宝物化,显示了其宝物书写泛化的特征。
《西游记》故事中,“宝物”经常与宗教仪式及灾难情节相互联结,宝物流动与消耗的过程对应了人情义理的交换。在《西游记》中,妖精举办宴会是为了与宴席的对象进行宝物交换。第十七回《孙大圣大闹黑风山》中,佛衣会为庆生而开,作为宝物的袈裟俨然是宴会的主要角色之一。第三十四回《魔王巧算困心猿》中,金角、银角大王派小妖去压龙山压龙洞,请“母亲”九尾狐妖吃唐僧肉,表面上是二人孝道的体现,实际上他们作为太上老君的道童下界作乱,与妖魔并无任何血缘关系,二怪举办宴会是为了获得寄放在九尾狐妖处的宝物幌金绳。第四十二回《大圣殷勤拜南海》中红孩儿请父亲牛魔王赴宴、第四十三回《黑河妖孽擒僧去》中黑水河鼍龙怪请舅爷赴宴为其暖寿,则主要是与亲人分享有“长生不老”功能的宝物。妖魔模仿人类进行社交,妖魔间的宴席将宝物与人际交往互相结合,突显了宝物在日常社会交际中的重要作用。精怪通过在“宴会”中交换宝物,建立了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成功地模拟了人类社会的社群关系。
将日用物品、身体以及人际社交活动与“宝物”紧密相连的叙事,展现了明人的“好物”风尚,传达出晚明社会中的平民阶层在现实人生中对“物”的痴爱迷醉。
二、得失:宝物的所有权及其权力象征
《西游记》中,宝物的所有权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个体是否拥有宝物,取决于其获得宝物的途径。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宝物之一,这一宝物虽是悟空“自取”,实质却是悟空强迫龙王赠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的猴行者是靠大梵天赐给唐僧的金环锡杖拿妖捉怪,只有单纯的“赠宝”情节;《西游记》中的“龙宫求宝”又与佛经《贤愚经》卷八的《大施抒海品》《佛说大意经》《生经佛说堕珠着海中经》《经律异相》、卷九《入海采珠以济贫苦》等中的入海取如意宝珠之事非常类似,故事只是将“宝珠”改易成“金箍棒”。但与“求宝珠以济贫苦”的高尚目的不同,《西游记》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中,孙悟空是因为个人需要合适的兵器,前往龙宫自取,而龙王不好推辞,只好送宝:
正说处,后面闪过龙婆、龙女道:“大王,观看此圣,决非小可。我们这海藏中,那一块天河定底的神珍铁,这几日霞光艳艳,瑞气腾腾,敢莫是该出现,遇此圣也?”龙王道:“那是大禹治水之时,定江海浅深的一个定子,是一块神铁,能中何用?”……你看他弄神通,丢开解数,打转水晶宫里,唬得老龙王胆战心惊,小龙子魂飞魄散,龟鳖鼋鼍皆缩颈,鱼虾鳌蟹尽藏头。悟空将宝贝执在手中,坐在水晶宫殿上,对龙王笑道:“多谢贤邻厚意。”龙王道:“不敢,不敢!”[4]32
被迫送宝之后,四海龙王甚是不平,商议进表上奏,控诉悟空“欺虐小龙,强坐水宅,索兵器,施法施威,要披挂,骋凶骋势”[4]38。
孙悟空龙宫“求宝”之后,成功获得了如意金箍棒的所有权。与传统“盗宝”故事不同,龙王答应把定海神针当作礼物赠送给悟空,虽然这只是龙王的权宜之计,但名义上金箍棒成为了一件“礼物”。同时,龙王并没有掌握如意金箍棒的真正用法,“金箍棒”在很长的时间里明珠暗投,最终到悟空手中才发挥其真正价值。因此,宝物最终才能归属悟空。
在《西游记》中,悟空曾经数次将妖怪的宝物骗到手中,并试图保留它们,但宝物原来的持有者却执意要将宝物收回。从故事情节上来看,这类情节是为了维持取经团队的实力,以保证取经团队历劫的难度。失去了宝物的精怪会顿时法力尽失,“宝物”是精怪兴风作浪的主要依凭,在某种意义上精怪本身成为了宝物的附庸。这些宝物不是精怪原形的一部分,大多是其配饰,如“菩萨将铃儿套在犼项下”的紫金铃[4]891。值得注意的是,与主人可以制服自己的坐骑不同,宝物不会因为召唤而自动回到主人手中,观音、弥勒、太上老君都曾向孙悟空讨要过宝贝,这说明宝物的所有权往往不可控制:
正行处,猛见路傍闪出一个瞽者,走上前扯住三藏马,道:“和尚,那里去?还我宝贝来!”八戒大惊道:“罢了!这是老妖来讨宝贝了!”行者仔细观看,原来是太上李老君,慌得近前施礼道:“老官儿,那里去?”那老祖急升玉局宝座,在九霄空里伫立,叫:“孙行者,还我宝贝。”
……
“若不是老官儿亲来,我决不与他,既是你这等说,拿去罢。”[4]445
此处,悟空出于人情的考虑而归还宝物。而在与观音的周旋中,悟空往往迫于紧箍咒的“威胁”而归还宝贝:
那菩萨才喝了一声:“孽畜!还不还原,待何时也!”只见那怪打个滚,现了原身,将毛衣抖抖,菩萨骑上。菩萨又望项下一看,不见了三个金铃。菩萨道: “悟空,还我铃来。”行者道:“老孙不知。”菩萨喝道:“你这贼猴!若不是你偷了这铃,莫说一个悟空,就是十个,也不敢近身!快拿出来!”行者笑道:“实不曾见。”菩萨道:“既不曾见,等我念念《紧箍儿咒》。”那行者慌了,只教:“莫念!莫念!铃儿在这里哩!”[4]891
这类情节象征着宝物的不可控性以及宝物主人对其所有权的担忧。在“精怪盗宝”——“悟空得宝”——“悟空还宝”这一过程中,宝物的使用权最终被交还给原来的主人,这些人往往来自仙界或佛界。宝物在遗失与回归复杂过程展现了权力的“不可赠送性”与“不可控制性”。
莫里斯·古德利尔在《礼物之谜》中曾经指出物品的不可赠送性:“那些不能赠与、只可保留的珍贵之物、财富和避邪物,很有可能正是那些体现着最大的想象性权力的物件,因此也就是具有最大的象征性价值的物件。”[7]29这种不能被赠送的、作为保留物品的“圣物”,当然也是一种宝物,但是其价值往往在其象征性,而非其世俗价值。一些“保留”是为了减少“宝物”的流通,而正是它们构成了社会的阶级层级[7]34。《西游记》中对宝物所有权的描写,展现了具有话语权的社会知识阶层在面对阶层变化时的特殊心理。
三、交换:“圣物”与“俗物”的宝物化
《西游记》中,孙悟空一直充当着“抢夺”和“谐谑”宝物的角色,如悟空用秽物假作宝物,冒充三清制作仙药,消解了“宝物”的神圣性;悟空在朱紫国用尿液制造“神药”,以“谐谑”的姿态消解“宝物”的内在价值:
行者道:“药内要用。”沙僧道:“小弟不曾见药内用锅灰。”行者道: “锅灰名为‘百草霜’,能调百病,你不知道。”那呆子真个刮了半盏,又碾细了。行者又将盏子递与他,道:“你再去把我们的马尿等半盏来。”八戒道:“要怎的?”行者道:“要丸药。”[4]859
同样的,《西游记》第四十六回《外道弄强欺正法》中唐僧隔板猜物时,孙悟空将国王放置在柜中的宝物转变为废物:
“我先猜,那柜里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裙。”唐僧道:“不是,不是!柜里是件破烂流丢一口钟。”国王道:“这和尚无礼!敢笑我国中无宝,猜甚么流丢一口钟!”[4]579
这些情节无疑暗含对“宝物”的讥讽,促进了圣物、宝物、俗物、废物之间的流通和转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宝物”的谐谑过程中,故事聚焦于对宝物价值高低的对比和品评。
佛教中,同一类型的法宝也有价值高低。《施设足论》中曾提到“四轮宝”:“金、银、铜、铁,轮应别故。如其次第,胜上中下。逆次能王,领一二三四洲。谓铁轮王王一洲界,铜轮王二,银轮王三;若金轮王,王四洲界。”[8]64又,《阿毘达摩大毘婆沙论》曾说:“此四轮宝亦有差别,王四洲者有金轮宝。”[8]156这一文化因子也体现在《西游记》中。即使是以“出世”为目标的佛教和道教人物,同样关注宝物世俗价值的高低,如孙悟空的紧箍、黑熊精的禁箍以及红孩儿的金箍。传统观点都认为这三者并无区别,实际上这三件宝物在价值上仍然有所区分。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中,如来曾说紧箍儿虽是一样三个,只是功用各有不同。这种价值高低体现在观音对待三个箍的态度上。第四十二回《大圣殷勤拜南海》中,观音提到“这个金箍儿,未曾舍得与人”[4]536,正因“金”的价值更高,因此观音才会一直保留金箍,最后将金箍给予红孩儿,并让他做善财童子。《华严经》卷第六十二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三中提到“善财童子”与金钱、宝物密切相关:
知此童子初入胎时,于其宅内自然而出七宝楼阁,其楼阁下有七伏藏,于其藏上,地自开裂,生七宝牙,所谓:金、银、琉璃、玻璃、真珠、砗磲、玛瑙。善财童子处胎十月,然后诞生,形体支分端正具足;其七大藏,纵广高下各满七肘,从地涌出,光明照耀。复于宅中自然而有五百宝器,种种诸物自然盈满……如是等五百宝器,自然出现。又雨众宝及诸财物,一切库藏悉令充满。以此事故,父母亲属及善相师共呼此儿,名曰:善财。[9]384
《西游记》中,佛界“圣物”在被赋予价值的过程中,也变为了存在价值高低的“宝物”,生发出各种价值比较、物品交换的情节。
“圣物”以“宝物”的形式,在流转中生产“圣”与“俗”的辩证,神圣的宗教象征和具有世俗价值的宝物互相联结。比如,唐僧的袈裟和紫金钵盂这两件宝物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在《取经诗话》中有这样一段话:“罗汉曰:‘师曾两回往西天取经,为佛法未全,常被深沙神作孽,损害性命。今日幸赴此宫,可近前告知天王,乞示佛法前去,免得多难。’法师(玄奘)与猴行者,近前咨告请法。天王赐得隐形帽一事,金锡杖一条,钵盂一只。三件齐全,领讫。”[10]47在世德堂本《西游记》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中,如来吩咐观音:
“但恐善信难行,我与你五件宝贝。”即命阿傩、迦叶,取出锦襕袈裟一领,九环锡杖一根,对菩萨言曰:“这袈裟、锡杖,可与那取经人亲用。若肯坚心来此,穿我的袈裟,免堕轮回;持我的锡杖,不遭毒害。”[4]88
《取经诗话》中没有提到“袈裟”这一宝物,世德堂本《西游记》中出现了“袈裟”和“锡杖”,其价值之高被一再强调,但观音最后却将宝物无偿赠送给取经人,这一情节构成了从“卖宝”到“送宝”的行为转换。故事中“有价”和“无价”对应了“宝物”和“圣物”的价值。袈裟首先以“宝物”的姿态出现,有人甚至以“长生不老”质疑其价格:
菩萨道:“袈裟价值五千两,锡杖价值二千两。”那愚僧笑道:“这两个癞和尚是疯子!是傻子!这两件粗物,就卖得七千两银子?只是除非穿上身长生不老,就得成佛作祖,也值不得这许多!拿了去!卖不成!”[4]146
后来,宰相勒马询问袈裟价格:
菩萨道:“袈裟有好处,有不好处;有要钱处,有不要钱处。”萧瑀道:“何为好?何为不好?”菩萨道:“着了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不遭恶毒之难,不遇虎狼之灾,便是好处;若贪淫乐祸的愚僧,不斋不戒的和尚,毁经谤佛的凡夫,难见我袈裟之面,这便是不好处。”又问道:“何为要钱,不要钱?”菩萨道:“不遵佛法,不敬三宝,强买袈裟、锡杖,定要卖他七千两,这便是要钱;若敬重三宝,见善随喜,皈依我佛,承受得起,我将袈裟、锡杖,情愿送他,与我结个善缘,这便是不要钱。”[4]147
唐太宗同样询问了袈裟的价值,观音在向他描述袈裟“超凡入圣”之妙时,主要渲染其宝贵的世俗价值。当太宗要买两件宝物时,菩萨又坚持“既有德行,贫僧情愿送他,决不要钱”[4]149。整个赠送的过程又将“袈裟”与“圣物”相类比,观音的“卖”与“送”展现了袈裟作为“宝物”与“圣物”,分别对应了“有价”与“无价”的双重特性。
在取经途中,袈裟主要体现了宝物的特征。从第十六回《观音院僧谋宝贝》中黑熊精盗取袈裟想要举办佛衣会到第九十七回《金酬外护遭魔蛰》中寇员外被强盗所杀、唐僧被牵连入狱的一系列情节中,袈裟一直都以“宝物”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出现。在到达灵山后,袈裟复又兼具“圣物”和“宝物”两种意义。作为观音礼物的“袈裟”并没有被用来交换“有字真经”,唐僧选择用紫金钵盂作为交换真经的人事。《取经诗话》中,钵盂是天王所赐;而在《西游记》中,紫金钵盂是唐王所赠。唐僧以“钵盂”交换真经,除了血食祭祀的意义之外,相比象征世俗皇权的“钵盂”,“袈裟”才是不可交换之物。同时,宝物的价值与交换性又与取得有字、无字真经的情节互相关联,作为唐王“礼物”的钵盂是有价并且可以被交换的“宝物”。
第九十八回《猿熟马驯方脱壳》中,佛祖强调“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4]1215。燃灯古佛听说传经之事,则肯定了无字真经的价值:“东土众僧愚迷,不识无字之经,却不枉费了圣僧这场跋涉?”[4]1213由此可知,无字真经的价值甚至超越了有字真经。唐僧取得无字真经是因为没有给予足够的人事。无字真经作为圣物,具有不可交换性,与其等价的是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八十一难”。“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耳。”[4]1215
作为圣物的无字真经对世俗世界是无用的。
在换取有字真经的过程中,三藏赠送紫金钵盂时,特地解释钵盂也与寻常金钱不同,并承诺了日后的谢仪:“弟子委是穷寒路遥,不曾备得人事。这钵盂乃唐王亲手所赐,教弟子持此,沿路化斋。今特奉上,聊表寸心。万望尊者将此收下,待回朝奏上唐王,定有厚谢。只是以有字真经赐下,庶不孤钦差之意,远涉之劳也。”[4]1215唐僧将整个交换过程从神圣的“求取真经”转换为人间世俗公务,将自己定位于唐王“钦差”的身份角色,以彰显取经是一种宝物交换的过程。该情节与当时唐王欲购买观音的宝物前后呼应。但与前文观音最终将取经视为“神圣”任务不同,此处唐僧和诸佛都将这一神圣的取经过程降格。通过交换,“有字真经”成为了世俗的宝物。因此,两位尊者在接受了人事之后,面对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的调笑和谐谑,并不感到羞耻。实际上,这一行为得到了如来的准许,并具有象征意义。
同时,整个取经过程也不只是取经团队四人的交换行为。从唐王的钵盂到唐僧对未来谢礼的承诺,都显示了这是一种整体的交换。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整个氏族以全部的名义来订约,换言之,是让那些塑造着社会的各个群体(家庭、氏族、部族)都卷入其中[7]37。
《西游记》中,圣物被降格成为可交换的宝物,而宝物具有价值的高低,这充分显示了从上到下、从宗教世界到世俗社会中,人们对宝物的追逐与爱好。这种现象表明知识界对民众逐物风尚的深度参与,“物”成为其缓释压力和寻得精神游牧的新出口。晚明知识分子为“合法合理”地占有“物”,弱化了自古以来“物”作为礼器的道德意蕴而偏重其价值,“器物已不再仅仅是礼乐文化的载体或是道德情操的隐喻,更是服务于个体生活的审美依据和物质消费”[11]。
“圣物”“宝物”和“俗物”的互相转化,体现了“神圣——世俗——谐谑”的三重文化特征。《西游记》将“圣物”和“俗物”宝物化的过程,展现了晚明知识界面向现实世俗人生的“沉降”。但这并非知识精英的道德“堕落”,精英和平民阶层与物的“交缠”关系本是整个晚明社会现实的“一体两面”,体现了市民文化的强势崛起[12]。
四、结语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明末如此重视‘物’,观物、用物、论物到不厌精细的地步。”[13]《西游记》中的宝物书写主要表现为三个特征:一是将日常器物、身体以及社会人际关系与宝物相联结,呈现出宝物书写的泛化;二是通过宝物得失之间所有权的转换,暗示了知识界对自身地位及话语权力的担忧;三是将圣物、俗物和宝物相联结,将不可交换之物转化为具有世俗价值的宝物,体现了精英和平民共同的世俗化倾向。
宝物作为一种媒介,沟通了“圣物”与“俗物”,仙界、佛界和人界,展现了晚明的时代风气。宝物交换具有相应的社会意涵。“宝物”的赠送、归还、抢夺、交换和流通作为《西游记》重要的叙事环节,展现了其“仪式化”和“非仪式化”的流通过程。《西游记》中大量的宝物书写,体现了宝物在世俗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价值以及作为宗教礼物的象征意义;宝物对人物身体的“物化”过程,则彰显了明人对包含身体在内的“物”的迷恋,体现了知识界和平民阶层在理想与现实两个方面对物欲及权力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