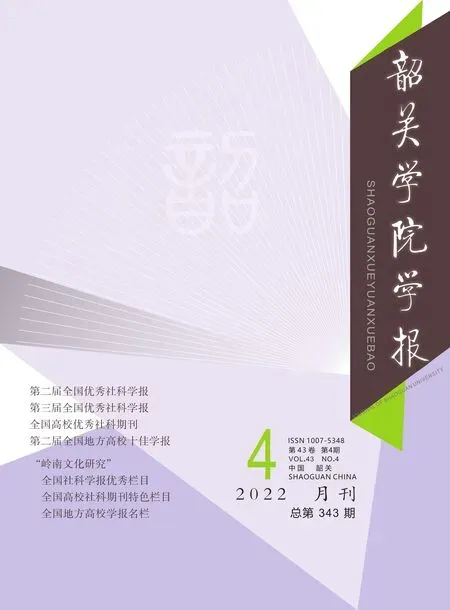试论西方建筑的审美定性
张萍萍
(宿州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美往往具有两种层次:一种是事物自身的自然属性和外部形态;另一种是社会属性和生活内容。建筑,既是人类的物质寓所,也是人类蔽隐世俗的精神空间,兼有了物质与情感的双重属性,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建筑的美学表达、神韵显现需要回归文化本体,让无形的文化和有形的载体串联耦合,从而揭示出其审美尺度、装饰意味、美学品格,追溯隐藏在文化深处的内在动力,为当代建筑发展提供一个可供参照的价值体系。
建筑的审美尺度涉及建筑内部的三维空间(长、宽、高)和外观形构的视觉因素,通过建筑的整体,在人们心中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从而勾联出建筑的审美意象。建筑的审美尺度,在本质上体现为人与建筑的互动关联,是人的大小关系与建筑整体尺寸形成的比例尺度。西方建筑擅长在几何关系、数的结构关系上把握整体形构,具有明显的形体性特征,这种数列关系在西方被艺术家赞誉为“法规”,也就成为了艺术的范本,总体受到希腊建筑、雕塑的影响,尤其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下文简称为“毕式”)数的浸染,“毕式”数的概念是事物生成的原则和组织结构,并不是机械、刻板的公式、序列,而是比例关系的动态韵律,彰显出“毕式”对美学本质的理解。
按照宗白华先生的观点,中西建筑观照方式大异其趣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宇宙”认知的差别。西方讲“时—空”,时间在前,空间在后;中国则是“宇—宙”,“宇”为房屋,常常表达空间,“宙”是“宇”的出入来往,形容时间;中国人认知“宇宙”往往是从浩瀚无垠的无穷空间中返回万物,从万物到自我,达到自己心中的“宇宙”。中国古代的房屋就是自己的世界,从房舍中得到空间思维,从“日落而息”中得到时间概念。这种时空有往有复,有仰有俯,形成“网罗无地于门户,饮吸山川于胸怀”[1]的美学。西方人常常向“宇宙”作无限的追求和遐思,宇宙中“数”的永久定律,一方面形成了和谐的音乐;另一方面创构了建筑形制。弦上的节奏韵律和建筑的众多样式显现为全部宇宙的和谐象征!数变成了美,数成为了宇宙的中心结构,建筑师以建筑表现探索宇宙获得的秘密[2]。
一、西方古典建筑审美尺度探源
一座座雄伟壮观的建筑是人类主观赋予的审美尺度,常常通过建筑的空间、结构、造型、材料等因素诉诸视觉,从而产生美感。建筑的优美不仅是人类积极赋予情感的成果,还是人类审美活动主动参与的结果。赋予美的过程常常需要按照人的尺度进行,从自然的有机体中妙手偶得,仿生地进行建筑创作,这种内在的人心规范,往往是万物的审美尺度。建筑物自然表现这一审美尺度。
在原始社会,人类建造房屋基本上用的是人体丈量法,都是利用手、脚、臂等人体部位丈量土地、梁柱、墙壁,乃至今天,有些设计师如果遗忘了丈量尺,往往也会手脚并用、左右开弓,完成相关尺寸的测算。这种利用人体部位丈量的方法,是世界各民族普遍共有的创造,建筑设计具备了原创性质,并且拓宽了我们对传统建筑设计的认知。建筑中与人类身体活动密切联系的构件,往往是建筑的重要构成或过渡结构。比如,门与窗,门的尺度一般都在两米左右,超过普通人的身高;窗的设立,常常根据用途而有异,宗教建筑的窗户窄狭,居住建筑的窗户则相对宽阔,但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采光与生活的适应。由此可见,建筑的真正尺度,最终都是人体动作与尺寸的映射。
人体美的尺度,在西方文明先驱的古希腊有着悠远的表现,以人体的支撑之力建造成建筑的承重之柱。古希腊发明的三种柱式,即多立克柱式粗大雄壮代表男性阳刚之气;爱奥尼亚柱式复杂多变代表女性阴柔弹性;柯林斯柱式装饰轻巧彰显形态优美纤细,同时根据人体的标准尺寸确立了建筑黄金分割定律(总长部分与较长的部分比例为1:0.618)。古希腊三种柱式,不仅在外观上传达了人体和谐完美性,奠定了西方建筑的总基调,更凸显了人本主义的光辉,透露出深刻的哲学之思,蕴含着人类复杂的思想情感,是对人自身的预设与肯定。宗白华先生曾这样评论希腊一座小神庙的建筑:“这四根石柱由于微妙的数学关系发出音响的清韵,传出少女的幽姿,它的不可模拟的谐和正表达着少女的体态。艺术家把他的梦寐中的爱人永远凝结在这不朽的建筑里,就像印度的夏吉汗为纪念他的美丽的爱妻塔姬建造了那座闻名世界的塔姬后陵墓。”[3]人体尺度寓于建筑之中,建筑成为人类的审美对象,这种关联思维建构起了西方古典建筑与人之间的内在审美尺度,充分印证了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概念,审美尺度变成了本能的、自然的标准单位,人类成为衡量建筑的真正标准。同时,人类须将丰富的情感植入建筑设计之中,建筑美的尺度才能全面彰显。于是,建筑的审美尺度既是可直观观览的物理空间,又蕴含着重要的心理感受。西方建筑往往以向上的超越达到超世的目的,以人的尺度达到接近“神”的高度,人的尺度超越成“神”的尺度。古希腊建筑创立了以人为尺度的大设计观。
二、西方古典建筑的审美核心:神性尺度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经历了与自然的和谐友好和相互抗争的过程,面对不可解释的自然现象(如火山雷电、花开花落等),便开始产生信仰,虽然植物、动物、无生物、人都曾成为信仰的对象,但最普遍的信仰对象则是神,体现为物质层面的和谐安定与精神层面针锋相对的神性,始终贯穿于西方建筑发展之中。
“建筑”在古希腊语本初涵义是指安放众神神像的神圣空间,有宙斯(统筹万物的天神)庙、波塞冬(掌管大海和一切水域)神庙、帕提农神庙(供奉雅典娜女神的最大神殿)等。古希腊自古就有神话统领生活的习俗,神主宰着世界,从个人到集体、从家庭到社会,神成为主宰一切的主体,生活中到处都有祭奠神的空间场域。虽然他们的神性涵义与人性涵义相同,但希腊神庙的精神主导,却弥漫着神光的庇护,流淌着神的精气与灵性[4]55。
无论是古代的建筑营造者还是当代的建筑评论家,都非常赞赏古希腊建筑整体与部分间的比率——黄金分割律。这种黄金分割律的广泛使用,正是源于对人体比例的崇尚和神性尺度的珍视。这些哲学家和建筑师都认为“数”是万物之本,“数”的数量和规律只有神才能创造,数量中的和谐关系体现为最佳的神性。建造于公元前447 年的帕提农神庙在凸显神性上尤为显著,它位于希腊雅典卫城最高处的山峰之上,是雅典卫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之一,这个代表古希腊最高水准的建筑,东西宽31 米,高19 米,遵循希腊人推崇的黄金比例分割律。南北长70 米,东西两端各有8 根、南北两侧各有17 根多立克柱,柱身颀长秀挺,是古希腊建筑中的典范之作。
古希腊神庙是神与人和谐相处的重要场域,这种人性与神性的完美契合,是人衡量建筑审美的重要源泉。随后的古罗马人相信神性力量会将神的定力传达给世人。为此,古罗马建造的体量巨大的建筑往往与其征服世界的声势步调一致,这是对神的无声赞扬,也是神性尺度的物质表达。皇帝或国王是造福人类的人间之“神”,在驱魔保护国家、情感意志传达上彰显了神的旨意,成为人们敬仰膜拜的对象。古罗马建筑的核心永远都是建造豪华宫舍、架设伟岸高桥、广铺宽敞马路。建于公元72-80 年的古斗兽场,是罗马文明的重要标志性建筑,这个容纳9 万人,供奴隶主、贵族、自由民观看斗兽或奴隶角斗的空间,依山而设,观众座位层层升高。见证人与兽之间残酷搏杀的古斗兽场,整个建筑平看为圆形,鸟瞰为椭圆形,采用拱劵技术相互环绕,之间架设柱壁,柱壁依次为多立克柱式、爱奥尼亚柱式、柯林斯柱式,人体之美再次在古罗马建筑上凝结。古罗马斗兽场以庞大、雄伟、壮观著称,在世界建筑史上堪称杰作和奇迹,以至于有人形容斗兽场与罗马同气连枝、共荣共损,罗马颓废了,世界也就意味着萎靡了。字里行间虽然流露着夸张的意味,但总体还是与事实相符的。
中世纪的欧洲始终被神学笼罩和统治,神被装扮成白璧无瑕的圣人,建筑的营建自然也追寻神的尺度,哥特式教堂的广泛兴起,是欧洲建筑史上的大事件。哥特式建筑外观的总体基调是垂直满密的直线,直刺云霄,尖顶、钟塔、山花、飞券、神龛、矢形窗皆为尖状,共同汇聚于钟塔的尖顶,具有动态的升腾之状,透露出对天堂的追寻与向往[4]58。内部结构,整个空间封闭严密,彩色窗户呈现半透明状,饰以神学故事题材,黑暗中透射着迷幻的光影,整体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气息。基督教徒在这里集结、收心,封闭自己,用虔诚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建筑自然具有了宗教寺庙的艺术风格和独立自主的含义,这与希腊神庙的宽大开朗,与神性生活相融、水平方向延展不同,它表达肃穆静心、浪漫升腾,达到摧垮自尊、驯服自信、虔诚修行、祈求恩惠的目的。人的微小与神的崇高、世俗苦难与天堂光辉,形成巨大的反差,使人们对宗教产生恐惧和期望,基督教从此利用建筑,启发心志[5]。
从古希腊神庙、古罗马斗兽场、中世纪哥特建筑,神与人关系的和谐与矛盾,形成了西方古代建筑的总体面貌。总体来看,西方建筑用神的尺度传达神性的伟大,神成了上帝的化身和无与伦比的人格神,祭奠神的庙宇、教堂自然成为西方建筑中等级最高的建筑形制。从此以后,神与上帝成为“完美无瑕”的代名词,同时具有超验恒久的特性,以最好的建筑尺度表达对神或上帝的瞻仰和追慕。
三、回溯与重塑:西方建筑的未来表征
以往人类精神的传递依赖于宗教、哲学及艺术,现在科技将人类带入了技术控制的新生活,人类不再是单纯的自然人[6]。随着欧洲工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的出现,人们原有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科技催生出前所未有的新材料,西方古典建筑在功能、形式、审美意识等方面产生了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危机和困境。于是,为了摆脱古典建筑形式上的束缚,出现了具有明显激进色彩和理想主义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1919 年,格罗皮乌斯在德国魏玛建立了包豪斯学校,它的成立标志着现代设计教育的诞生。在校舍设计上,采用理性的“方盒子”几何造型,无论是外观造型还是内部空间,都割裂了西方古典建筑承续的历史文脉与形态特征。随后这种风格拓展到世界的每个城市,城市变成了具有几何意义的建筑模型,它不再尊崇古典建筑的均衡、对称、和谐的神性理念,但“设计为大众服务”的宗旨却真正得到了全面落实。它在理性与科学基础之上,将工业生产体系介入建筑之中,倡导建筑的机械性、工业性、标准性,具有了独特的历史地位[7]。现代主义建筑的经济实用、功能第一、简单明快、反对装饰等设计观念契合了当时的设计潮流,符合建筑设计的客观规律,形成了“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的大设计观,建筑不再具有神性意义,而是具有了理性的大众思维,是科技与人文相互促进的结果。
现代主义建筑的“功能决定形式”理性观念,随后在美国发展为国际主义风格,真正成为全球推广的统一风格。20 世纪70 年代以后,人们发觉现代主义建筑千篇一律的格调割裂了建筑与历史文化、风俗人情、情感心理的联系,强调功能至上,人们在心理上无法获得“家”的归属性,远离了建筑的审美特征。这些弊病,为后现代主义的出场提供了条件。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罗伯特·文丘里率先对现代主义建筑发起挑战,主张用历史建筑因素和美国的通俗文化来赋予现代建筑以审美性和娱乐性[8],从而推演出后现代主义建筑的非标准、非线性、非统一、非和谐、非完整、不确定、多元化的设计风格,颠覆了几千年来西方古典建筑“和谐美”的设计观念,热衷于主观感受和关注建筑自身,追求旋律、动感、曲面、含混、未完成的未来倾向,逐步走向了世界建筑的壮阔舞台。
建筑,作为多维的生活体验和空间载体,在未来具备了更多的超现实想像。西方建筑从有神性的古希腊神庙到无神性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其演变轨迹是在不断超越基础上呈现出来的。对于它的未来表征,笔者认为应该是具有体验性、超现实、时空感、场所性的精神世界的表达。
体验性建筑的表达,需要在建筑中增加传统的历史文脉与人类情感的认知。这种潜意识的状态常常是杂乱无序、一反常规的奇幻妙境。将人造景观达到舞台表演虚拟布景的水准,叠加和隐藏占据主导地位的功能结构,使之形成一种审美张力。超现实性建筑整体消解了空间表面的人工化技术痕迹,利用电脑程序编码的随机性,打造一种自然本身的有机形态,形成一种非线性的建筑形体,流露出“既熟悉又陌生”的空间场域,使人仿佛脱离了现实世界[9]。时空感建筑则要求建立人与自然、自然与城市的共生关系,在建筑细节中传达比例与尺度,通过戏剧化、想像力、奇异感获得时空与精神世界的互动。场所性建筑就是将建筑“隐匿”,表面上看到的是自然地貌,通过色彩的划分,达到运动、登高、观览的目的,创造出具有自然、激情、符号特性的建筑标识。
西方建筑的未来表征,是全球建筑师探索建筑现实困境与未来幻境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审视人、自然、城市尺度的主观意识和精神价值之路。这种基于经济与科技的非线性形态与超级体验是解决城市光明、新陈代谢、环境友好的必然途径,它是物质现实与精神虚幻达到平衡的最佳可能。
总之,西方古典建筑从古希腊、古罗马体现出人神和谐的比例尺度,哥特式建筑通过装饰语言达到宣传教义拥护宗教的目标,到现代主义建筑对理性与科学的宣扬,再到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回归和通俗文化的重视,西方建筑走在了否定之否定的发展之路上,每一次审美变异的转折,都预示着一种新的审美观的开始。当前它正不断指引着人类的建筑审美意识走向具有超现实、重体验、时空感、场所性的未来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