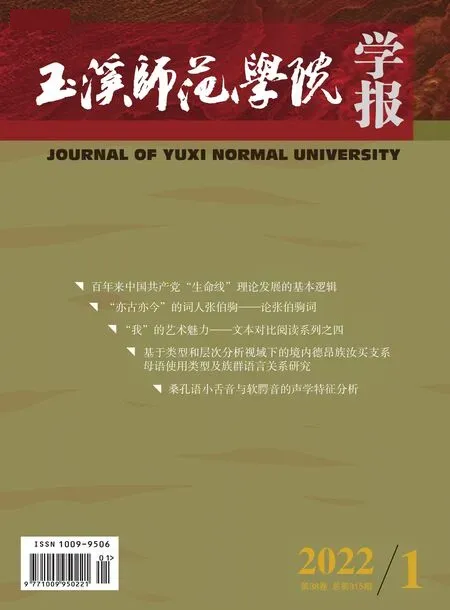“我”的艺术魅力
——文本对比阅读系列之四
石 健
(玉溪师范学院 文学院, 云南 玉溪 653100)
巴金在20 世纪40 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与以往相比数量不多。特别是他自己颇为青睐的短篇集《小人小事》(1)《小人小事》中的五个短篇,分别创作于1942-1945 年间。本文所讨论的这些作品引文,均出自《巴金全集》第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的《小人小事》版本。,一直默默无闻。巴金曾这样评价这部作品:
我在四十年代中出版了几本小说,有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集,短篇集子的标题就叫《小人小事》。我在长篇小说《憩园》里借一位财主的口说:“就是气魄太小!你为什么尽写些小人小事呢?”我其实是欣赏这些小人小事。这一类看不见英雄的小人小事作品大概就是从《还魂草》开始,到《寒夜》才结束。(2)巴金.关于《还魂草》[M]//巴金全集:第1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658.
巴金对于《小人小事》的欣赏,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于我们来讲,一方面,他从“看不见英雄的小人小事”中,提取素材并透视人性,这显然比同一时期主流文学充满宏大话语的英雄叙事更有生活气息,更接地气。另一方面,也是更容易被忽视的,巴金在这些小人小事中,采取了惯用的第一人称叙事手段,不过却自觉地突破了以往过于直白激切的直抒胸臆方式,在艺术上有很大的创获。正是在叙事方面突破自我的努力,使得巴金在1940 年代的创作渐趋含蓄内敛,完成了从招牌式的充满激情的“青春文学”向博大深沉的人生体验类型文学的蜕变。在此意义上,《小人小事》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一、以“我”为主的自我突破
王国维曾说:“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3)王国维.人间词话[M]//民国奇才奇文——王国维卷:晚清的最后一个文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163.这对于巴金在20 世纪40 年代之前的创作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长期以来,提到巴金的小说,就会令人想到“激情”“青春”“朝气”这一类的称谓。这与其作品常常满溢着情感宣泄特征的直抒胸臆密不可分。
巴金本人常常说到,自己并不满于作家的角色,而是想以实际行动介入社会生活,为人类的幸福而奋斗。他又常常说,自己写作不讲究技巧,只是想把心头郁结的情绪抒发出来。回溯巴金文学历程正式的源头,是在法国留学期间,并且受法国文学大师的影响颇深。公然袒露自己灵魂的卢梭和对人间的不公不义高呼“我控诉”的左拉,都是他的精神导师。巴金在20 世纪30 年代的小说写作中,对于万恶的封建家族制度乃至人间的一切丑恶现象,不停发泄着心头的怒火;对于代表着民族希望的青年群体,则不遗余力地鼓舞他们走向反抗的道路。而其作品的最大特色,就是坦诚热情地直抒胸臆,令人易于感受到字里行间的勃勃激情。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激流三部曲》《爱情的三部曲》等作品,像火一样引起了一代代青年读者的强烈共鸣,并引领他们勇敢地走出旧家庭,走向革命的旅程。
与此同时,这些作品亦无一例外地令人感受到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巴金的存在。小说中的叙事者与作者巴金的叙事视角,往往都是高度统一的。人物成为作者的代言人,也就成了巴金小说的题中应有之意。在写作时,“巴金先生同样把自己放进他的小说:他的情绪,他的爱憎,他的思想,他全部的精神生活”(4)李健吾.爱情的三部曲[M]//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7.。如此一来,巴金的作品虽然以无限的热力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但是其清浅直白、一览无余的方式,也招致广泛的诟病。巴金本人对于自己的作品常有敝帚自珍的心态,所以对于他者的批评,常常进行激烈的自我辩护。但是,作为成名很早、创作颇丰的作家,他未必不在意作品的艺术性,对于在艺术领域有所突破的诉求,在抗战开始之后,便在暗自酝酿之中。
作为具有高度责任感、使命感的作家,巴金在抗战时期满怀强烈的忧患意识,这实属必然。在写长篇《火》的同时,他也在撰写中短篇,1942 年4 月中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出版。在序中,巴金如此表白:“我拿笔的时候,我觉得满腹正义的控诉要借我的笔倾吐出来,然而写在纸上的,却是这几篇散漫无力的东西。它们不像控诉,倒像呻吟。我失望地放下了笔。”“放下笔,我又感到窒息,我又感到胸腹充塞。愤恨仍然像烈火似地在我的心里燃烧。似乎我的笔并没有把堆积在我心上的东西吐出一丝一毫。”(5)巴金.《还魂草》序[M]//巴金全集:第1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15.这是典型的巴金风格,这一风格的鲜明标记就是,他总是在有关的创作谈中,为自己对于丑恶现象的控诉力度不够以及没有真正充分抒发内心的愤懑而感到自责。《还魂草》序就体现出他对于控诉暴行、伸张正义、传递愤恨不力的不满和失望。
不过,对于作家的宣言,要保持清醒的认知态度,要结合作品来看,方能有更好的体察。证之于这本小说集的重头戏《还魂草》(1942 年1 月初刊于《文艺杂志》1 卷1 期)就会发现,巴金并没有以太多的笔墨来写战争的残酷,而主要聚焦于对于人性的挖掘,尤其是以女孩子利莎的形象衬托了生活当中一些自私自利者的丑恶,可以说延续书写了鲁迅开创的改造国民性的传统。不过,《还魂草》的艺术风格又未完全脱离以往的表现方式。比如,在第一人称叙事人“我”得了重病之时,少女利莎的出现,意义非同小可:“我又一次接触到孩子的纯洁的心灵了。这比良药还更能够治我的病。我用感激的泪眼望着她。”(6)巴金.还魂草[M]//巴金全集:第1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41.进而,利莎和她的好友秦家凤,简直就是“我”的心灵慰藉——
要是没有利莎这个孩子和她的小姐姐秦家凤,我在病中一定是很寂寞的,或者我的病甚至不会好也说不定,即使病好,也会好得更慢。是她们支持了我的精神,使我能够忍耐这么长久。她们的天真的笑和好心的话便是我这个病人所需要的阳光和温暖。(7)巴金.还魂草[M]//巴金全集:第1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72.
不过,这样的文字显然是颇为矫揉造作的,早期小说那种直白清浅的弊病也是很明显的。在《还魂草》中,虽然没有更多地书写抗战的主旋律,但是字里行间,巴金显然仍以一种过于直截的方式,在弘扬童心和真爱的可贵,这也可以说是陷入了文以载道的窠臼。抗战开始后,其许多作品出现题材单调、艺术匮乏的“差不多”现象。对此,巴金是有所警觉的,对于配合抗战主旋律而写的长篇《火》,他就多次表达过不满,比如在《关于〈火〉》一文中如此写道:
《火》一共三部,全是失败之作。……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考虑得不深,只看到生活的表面,而且写我自己并不熟悉的生活。我动笔时就知道我的笔下不会生产出完美的艺术品。(8)巴金.关于《火》[M]//巴金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230.
巴金在抗战开始以后的文学创作中,注意到了对于生活应开掘得更深等问题。这就是说,他是重视作品的艺术性的,这也是对其所谓“不讲究技巧”之说的有力颠覆。在《还魂草》之后陆续创作的《小人小事》集的几个短篇中,巴金便在积极尝试着突破自我,即既能以作品作为抗战的助力,又注重艺术的打磨。而在艺术性的突破方面,关于巴金惯用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改变,则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从上引《还魂草》中的文字,足以窥见巴金抗战之前的第一人称叙事的主要风格。作为一个以主观抒情方式为文坛所瞩目的作家,巴金是比较喜爱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手法的。这样的叙事,确实比较契合巴金的个性气质,因为从“我”的视角出发来讲述故事可以增强小说的真实感。巴金本人终其一生都强调讲真话,并厌憎一切虚伪之人和现象。所以,其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就强化了文本叙事者无比真诚的特点。此外,“第一人称的叙述特别适合于作心理忏悔,因为人称本身就具有一种独白性,这为叙事主体的直接登场提供了方便”(9)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07.。而自我忏悔恰恰是深受“吾日三省吾身”文化传统影响颇深的巴金念兹在兹的永恒主题。在此意义上,小说家巴金与第一人称叙事更可谓“天作之合”。
可以认为,巴金不满于《还魂草》和《火》的宣言,其实主要是着眼于艺术上的缺欠而发的。从《小人小事》5 个短篇的写作中,可以看到他以第一人称叙事为切入点,进行了艺术上的新探索。这几篇作品,都采用第一人称“我”作为叙事者。而与此前“我”偏爱较为直白的抒情和议论方式迥异,文本呈现出客观、冷峻叙事的显著特点,即“我”往往作为旁观者在小说中隐藏得很深。但这并不等于“我”完全消隐,而是巧妙地融入到文本当中——“我”或者以他人为代言人,或者与人物形成自我指涉,或者以抒情独白方式介入故事的进程。而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在“我”的注视下,或是以独角演出的方式,或是以嘈杂发声的方式,一方面形成众声喧哗的局面,另一方面又与“我”形成了颇富张力的潜在对话关系。总之,由于巧妙地运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者,《小人小事》中的5 篇小说,充满了复调性的特征,别具艺术魅力,为巴金在20 世纪40 年代完成深沉凝练的艺术转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值得深入研究。
结合本系列文章,对比的方法之于《小人小事》的整体解读亦颇为有效。“单篇作品的批评详尽地研究作品的内部构造,提交这方面的报告;但是,仅仅依据这方面的报告很难断定这部作品的地位和价值。因为每一篇作品的价值总是在和其他作品的相互衡量中方可确定。”(10)南帆.文学批评手册——观念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43.在《小人小事》中,《猪与鸡》《女孩与猫》都写到了人与动物的关系,而《兄与弟》《夫与妻》《生与死》则牵涉到家庭伦理。然而,由于对同一主题的书写,巴金利用了不同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使得作品的风韵颇为不同。因此,对于《小人小事》第一人称叙事的妙用,采用比较的方式予以解读,是很好的切入点。
二、巧妙代言与自我指涉
《猪与鸡》的故事,围绕冯太太饲养猪、鸡与邻居发生纠纷而展开。冯因为饲养动物破坏环境卫生,招来邻里的责难,但她毫不示弱地予以还击,且骂人极凶。这一人物,在以前的研究中,常被视为不讲道理的泼妇。但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冯是以“我”的巧妙的代言者身份出现的,这还尚未引起重视。
巴金作为著名的人道主义作家,作品中悲天悯人的色彩极为鲜明。这种爱,是惠及世间万物的。而在《猪与鸡》中,冯太太对猪与鸡的关爱之情便溢于言表。比如,文中出现过她用柔爱的眼光看小猪的场景。另一处细节更令人感动。房东与冯交涉不成,令人踢伤小猪后,冯不但为小猪擦洗身子,还不断地说着安慰它的话。她还说:“我望它,它也眼泪水汪汪地望我,我心里头真难过。畜生跟人是一样,它也有心肠,啥子都懂得,就是讲不出来。”在小猪死了之后,冯“不吵不闹,声音不大,埋着头,寂寞的哭声中夹杂着喃喃的哀诉”(11)巴金.猪与鸡[M]//巴金全集:第1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24.。她对小鸡亦体现出无比的关爱。凡此种种,都体现了冯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女性。
总之,巴金并没有把重心放在批驳冯的缺点上,而是弘扬其满满的爱心。“我”虽然是一个很克制的叙事者,并未过多地参与故事进程,但是在小猪受伤后,对于它的情感,与冯太太的视角是完全合一的——“忽然它睁起眼睛望着我,这是多么痛苦而无力的眼光”(12)巴金.猪与鸡[M]//巴金全集:第1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23.。从传递博大的爱意来讲,冯完全可视为“我”的隐含的代言者。从这一角度来看,《猪与鸡》与巴金的散文名篇《小狗包弟》可谓殊途同归,折射出民胞物与的博爱精神。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宇宙全体,还有其中的万物都有尊严性,它是这种意义上的存在。就是说,自然界的无生物和无机物也都有尊严性。大地、空气、水、岩石、泉、河流、海,这一切都有尊严性。如果人侵犯了它的尊严性,就等于侵犯了我们本身的尊严性。”(13)[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429.伟大的作家,莫不是对万物具有悲悯情怀的人。当代著名作家莫言,自小就对牲畜充满情感。他还曾说过,最讨厌虐待动物的人。巴金通过关爱动物的冯太太这一形象,实际上是在呼唤博爱,传递出用爱塑造国魂的深刻用意。
在《猪与鸡》中,巴金还用对比的方式,来突出冯太太的形象。冯在小猪死后痛不欲生,而周围的人却幸灾乐祸地看热闹。文中出现的孩子形象,更令人震惊无比。男孩王文生时常与冯太太对骂,污言秽语不绝于口。他还想尽一切办法作践孤苦无依的冯太太,而就在这样的时刻,他竟然哼着抗战歌曲,这显然充满讽刺性提出了这样的深刻命题——这样的儿童,能成为救国救民的民族栋梁吗?而“我”的侄儿,无论是在黄鼠狼叼走冯的小鸡令她着急的时候,还是在冯给受伤的猪洗澡的时候,都认为这不过是滑稽有趣的事儿。这两个冷漠无情、心理阴暗的孩子,不由令人想起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所激烈批判过的人物,即那些在封建大家庭中畸形成长起来的晚辈们。显然,这样的人日后成长起来,是难当民族大任的。总之,通过冯与周边人物的强烈对比,体现出巴金在民族危难时刻的诉求——用爱来改变冷漠自私的国民性,以此作为抗战的有效助力。
在《猪与鸡》中,巴金的第一人称叙事,收获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从显性层面来看,“我”对冯不雅的骂人之举,颇不以为然;但是在隐性层面,“我”则与冯的立场颇为一致。比如,冯为自己养猪和鸡辩解时,就隐含着对战时物价飞涨、百姓生活艰难的局面予以控诉。此外从冯的口中,还能让读者领会到政府管理混乱、特权阶层贪赃枉法、富人大发不义之财种种战时丑恶现象。显然,“我”与冯太太除了颇有爱心的共同点,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契合之处。这些,都是巴金巧妙地以冯作为“我”的代言者来完成的。
类似于《猪与鸡》,《女孩与猫》同样出现了人与动物的书写。但是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却不是以人物作为代言者,而是与人物形成了自我指涉的对话关系。故事从黎小姐寻找丢失的小猫凯提写起。她对受伤的凯提关爱有加,为它擦洗身体并敷药。后来,黎还安葬了死去的凯提,并为其树立了墓碑。从这些情节可以看出,黎宛如《猪与鸡》中善待动物的冯太太。不过,“我”对黎的态度却颇为复杂。看到黎给猫订了牛奶时,“我想说:‘这种时候好些人连饭都吃不饱,你还拿牛奶来喂猫!’”但是“我”终究还是不好意思说出来。并且,当黎夸奖猫可爱时,“如果允许我说真话,我要说,可爱的不是凯提,倒是黎小姐的一双灵活的黑眼珠,和她那甜甜的笑容”(14)巴金.女孩与猫[M]//巴金全集:第1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54.。可见,“我”虽然对黎对于猫的宠爱不满,但是似乎对于她很有好感。而当黎说凯提是一只浪漫的猫时,“我”的反应,更值得回味:
她说得那样认真,差一点叫我发笑了。可是我并没有笑,我多看了她一眼,她的表情使人想到她渴望着什么,她缺少着什么。我忽然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什么东西把她和猫连在一起呢?这只猫不就是她的缩影吗?她不是把凯提当作她的小妹妹吗?这个想法太怪,太唐突她了。我不敢说出来。(15)巴金.女孩与猫[M]//巴金全集:第1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55.
这大概暗示:来自繁华都市的娇弱的黎,也如小猫一样,需要时时被人呵护。不过,“我不敢说出来”,究为何意?巴金一向对玩物丧志的青年人取批判态度。如果在早期作品中,黎小姐这样的人物毫无例外会成为他的抨击对象。不过,在《女孩与猫》中,“我”对黎的态度却是暧昧不明的。如果细读,能够看出“我”对黎的理解和同情成分更多,文中多次提及黎的寂寞。那么,黎在颠沛流离的战乱时代,以养猫来慰藉心灵是否就是可以理解的呢?进而,“我”与黎是否存在某些共鸣呢?在巴金笔下,寂寞与孤独是恒久的主题。所以不妨认为,黎小姐这一人物正折射出作者在特定时代的精神困境——在烽火遍地的战争环境中,无法全力实现报效国家的宏愿,但是又不得不在颠沛流离中谋求生存。所以,“我”对于黎小姐,始终不能像巴金在其他作品中所持的批判态度,而是包容有加。
还要注意到,这篇小说写于抗战刚刚结束之后。此时,一方面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内战阴云布满华夏,这使巴金忧心忡忡(16)李存光.巴金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260.。作为一向着眼于全人类幸福的作者,在前路迷茫时刻的孤独无力之感会越发加剧。所以,“我”对待黎小姐的较为暧昧的态度,或许可以折射出巴金当时较为复杂的心态。
此外,“小说里的名字决不是无的放矢的”(17)[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M].卢丽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43.。巴金在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常自称为黎先生,比如《憩园》和《还魂草》。而在《女孩与猫》中,女主人公却把“黎”姓据为己有,“我”的姓氏则成了“李”。尽人皆知的是,巴金的原名为李尧棠。职是之故,“我”与黎小姐,形成了潜在的互为他者的关系,即微妙的自我指涉。这样一来,“我”的一些看似较为复杂的心理,也便可以理解了。
与《猪与鸡》相比,巴金因为重点在于刻画黎小姐,对于关爱动物这一情节并未展开叙述。而猫之死亡,“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由于疏忽而使凯提走失,它因在外流浪时被打伤最终死去。黎对此并未责备“我”,这与“我”对她溺爱猫也未过多指责一样,可见二者的相互包容。虽然“我”认为自己该骂,但并未做出过多的忏悔。而作者/隐含作者对于“我”对猫的罪愆,也许并不宽容。时隔35 年,巴金为小狗包弟因自己的懦弱而被送上解剖台,做了深刻的忏悔: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有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而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18)巴金.小狗包弟[M]//巴金.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146.
民胞物与、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巴金的面影,于焉可见,令人动容!这或许也可以视为对《女孩与猫》中的小猫凯提的一份迟来的歉意吧?
虽然都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者,但是《猪与鸡》与《女孩与猫》不同。前者中的冯太太可以视为“我”的代言人,后者中的黎小姐则是“我”的自我指涉。“我”在《女孩与猫》中,呈现出自我认同的困惑,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国事蜩螗之历史拐点中巴金的真实面影。
三、丰富多彩的复调叙事
正如巴赫金对充满复调性的小说作者的评论:“作品整体会被他构筑成一个大型对话,作者在这里可说是个对话的组织者与参加者。他并不保留做出最后结论的权利,也即是说他会在自己作品中反映出人类生活和人类思想本身的对话本质。”(19)[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巴赫金全集:诗学与访谈.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96.《小人小事》便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复调性,即众声喧哗的叙事方式:第一人称叙事者“我”,虽然基本上是旁观者,但是既会寻找人物作为代言者,又能与人物形成自我指涉,并且还常常扮演一个独立的抒情者,强化了文本的诗意色彩,极大丰富了艺术表现力。而在处理其他人物的时候,有时由一个人物来唱独角戏,其他人物处于辅助性的地位,有时则是许多人物共同发出声音来推动情节的发展。这些人物,与“我”又常常形成潜在的对话关系,这就使《小人小事》的复调性显得格外丰富。
“我”的抒情独白特征,在《女孩与猫》中表现得很明显。比如,黎小姐的很多举止,都引起了“我”诗意化的遐思。再如,在可爱的秋夜,“为了高空那些发光的世界,我居然站了两个钟点”(20)巴金.女孩与猫[M]//巴金全集:第1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48.。不由使读者想起伟大的哲人康德,把心中道德律和头上星空并举的经典化的哲思。在其他篇章中,以旁观者出现的“我”,也经常会以抒情独白的方式,在文本中巧妙地体现出诗与思的融合,大大丰富了艺术表现力。
在《猪与鸡》中,冯太太因为小猪之死而陷入了悲痛之中。此后,她看似恢复了平静,但整个文本却被巨大的空幻之感所萦绕。最后,冯太太离开了给她带来忧伤的院落。虽然再无家畜家禽的喧闹,环境也变得清洁了,“只是我的房间在落雨时仍然漏水,吹大风时仍然掉瓦,飞沙尘”(21)巴金.猪与鸡[M]//巴金全集:第1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26.。如此收篇,看似简洁明快,实有深意存焉。“我”所居住的环境,只有冯这样貌似凶恶之人,尚具有悲悯万物的情怀。而其他人,包括孩子,都冷酷无情。冯太太的离去,使表面的扰攘喧嚣暂告结束,环境似乎得以变好,“我”却有怅然若失之感。并且,此刻才让“我”对自己居所的诸种缺陷有了更深切的体验。这与其说是对只为牟取暴利而不顾及维修房屋的房东的讽刺,毋宁说是“我”的精神家园的沦陷。在颇为含蓄的抒情独白中,“我”对世界的失望和不满跃然纸上。
其他3 篇小说,以家庭关系为背景,“我”介入故事的成分比较小,情节基本都是由其他人物来推动的。但是,“我”的抒情独白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生与死》描写了一幕办丧事的场景。在本文中,丈夫成为唱独角戏的主要人物。他在祭奠逝去的妻子时,口若悬河地说个不停。从他滔滔不绝的语言和对于因找了庸医而延误对妻子及时救治的忏悔,以及涕泪横流哭肿了双眼的举动,似乎可以看出对妻子的一片深情。不过,细读之下却远非如此。比如,他对着妻子遗照喋喋不休地向众人说,自己已经尽心尽力,完全按照妻子生前所吩咐的去做了,似乎把祭奠这一庄严仪式变成了自我辩白的场所。进而,他还向妻子的灵位许下了承诺,要在她死后一年才会再婚。显然,丈夫把祭奠当成了道德作秀的舞台。加之众多冷漠看客七嘴八舌的议论,一场丧礼遂变成了生者尽情表演的盛会。
而“我”在《生与死》中虽然并未过多参与故事,但是短暂的情感体验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烘托作用。“我”与妻子在生前曾有一次交集,即后者爽快地为“我”兑换了钞票,折射出她的善良。当在乌烟瘴气的丧礼上看到妻子的遗照时,“我想到换钱的事,心里也有点不好过,好像谁泼了一盆冷水在我头上似的,我打了一个冷噤,我连忙调转身子”(22)巴金.生与死[M]//巴金全集:第1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63.。这样的抒情独白,就彰显了作为富有同情心的“我”,对妻子死后成为无情的看客们之消费品的感受——“我”既同情一位善良女子的不幸遭遇,又对无力改变无情的世界而感到无奈。
在《兄与弟》中,手足兄弟唐家二哥与五哥因琐事而争吵,甚至发生肢体冲突。后来,工棚倒塌,五哥不幸遇难,二哥懊悔万分。兄弟二人的纷争以及众人在五哥死后的议论,构筑了文本的主线。在众声喧哗之中折射出对兄弟阋于墙的抨击,暗示国民党在抗战中大搞分裂的丑行。此外,小说亦不动声色地呈现了国民自私冷漠的痼弊,以及工厂不顾及工人安危建筑劣质工棚的恶举。
而“我”同样以抒情独白的方式出现。在兄弟吵闹的故事发生之前,文本烘托出极为安静的氛围,为下文做了很好的铺垫,也巧妙暗示了在国难当头应该和谐共存,避免内讧。五哥死后,“我”的感受得以强化。“我”想到了二哥此时的举动——他是梦见了与弟弟不该争吵,还是梦见了如何才能救活弟弟?这不由令人徒增感慨,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惜,于世何补?“我越想越觉得心里不痛快,便下了决心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把月光也关在外面,然后转过身向着我那张成了臭虫的大本营的木床走回去,今晚我或者可以好好地睡一觉罢,我的心太累了。”(23)巴金.兄与弟[M]//巴金全集:第1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41.把月光关在外面,与臭虫在一起才可以缓解心累,睡上好觉,这实在是过于奇特的想法。不过,这样的书写却意味悠长,令人遐想:或许,丑恶的现实与“我”的期望,构成了无法弥合的裂缝;又或许,经历了太多的失望,“我”只能在封闭的世界中去寻求灵魂的安顿。无论怎样,心造的幻影只能令人走向更深的虚妄。总之,《兄与弟》以颇富张力的书写,传递出作者感时忧国的情怀,以及对美好精神家园的强烈渴求。
《夫与妻》中的丈夫,在围观者云集的路上数落妻子不听话,还说她就是欠揍。一位看客则火上浇油,说所有贪玩儿的女人都无好下场。妻子辩称,平时都是自己维持生计,丈夫不但帮不上忙还总乱发脾气,为此她要与他离婚。此时,现场最能掌控话语权的警察发话,斥责妻子不该反抗,并威胁如果二人继续闹下去就把他们带回局里。他还说女人只要主动闹离婚,就不是好东西,就活该招丈夫的打。围观者也劝妻子不要再做声,跟丈夫回去。在种种胁迫下,妻子只有妥协。《夫与妻》以众声喧哗的速写式笔法,在看似不起眼的夫妻矛盾中,折射出无孔不入的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威压,流露出对弱者的无限同情。
巴金依旧把作为抒情独白者的“我”与其他人的反差,鲜明地传递出来。首段以美妙柔和的文字,勾勒出“我”在静谧秋夜的朦胧月光下阅读友人信件的场景:“他们亲切地对我微笑,我的耳边响起了轻微的脚声。好像许多人向着我走过来。怎么,是朋友们的脚声么?难道他们已经到了我的身边?他们会跨过那么远的距离来看我?我感到一阵惊喜。”(24)巴金.夫与妻[M]//巴金全集:第1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42.可是就在此时,屋外传来了男人的责骂以及女人的哭声。这种强烈的对比,有力烘托出世界需要和谐友爱的主题。而在结尾,当“我”准备接续阅读友人的书信时,又听到了女人哭叫的声音。“怎么,那个女人又在吵闹了?我调转身朝门外看,但是除了一片朦胧月色,我什么也看不见。声音不响亮,那些人应该走远了。我站在门口倾听片刻,也没有再听见女人的受了委屈后的哭声。”(25)巴金.夫与妻[M]//巴金全集:第1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47.整个文本戛然而止,却言有尽而意无穷。书信是“我”精神家园的皈依,然而美好感受却一次次被丑恶的的现实所破坏。以寂静的氛围作为结尾,有力地烘托了女性的不幸命运还会延续。作者巧妙的构思于焉可见:开头和结尾出现的友人的书信,不但喻示着友情的可贵,也喻示了人间和谐美好的真情的重要性。“我”对无情的世界深深失望,但是毕竟还有友人的书信,成为“我”心灵的宝贵慰藉。诗意化的描写,传递出“我”的复杂思绪,也彰显了作者对于国民消弭纷争、共建美好家园的诉求。
对于荷尔德林的“人诗意地居住”,海德格尔做了哲人化的阐释:“诗意建造了居住的特别本性。诗意和居住并非相互排斥。相反,诗意和居住同属一起,相互呼唤。”(26)[德]M·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彭富春,译.戴晖,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199.这里,海德格尔把居住和诗意相提并论,大概也体现出营造理想的心灵家园的诉求吧。而在《小人小事》中,巴金直接传递的主题,其实就是爱。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动物之间,都应该和谐相处,这样才能建造理想的家园。
在叙事方面,巴金在众声喧哗的话语中,巧妙地融入“我”的抒情独白,这不啻为喧嚣扰攘的丑恶世界添加了几许亮色。此外,“我”也起到了为文本增添诗意的作用。这样的诗意,不只是叙事层面的,更是生存维度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的妙用,与爱的主题诠释相得益彰,呈现出巴金艺术探索的努力。
“如何选择故事的视角想必是小说家要做的最重要的决定,因为这会从根本上影响读者在情感上和理性上对小说人物及其行为的态度。”(27)[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M].卢丽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30.如果说,创作初期的巴金,并未过多考虑技巧的问题,那么进入1940年代以后,其在艺术上的探索则大大强化。在《小人小事》中,巴金便颇为显著地改变了以往对于第一人称叙事者“我”的使用策略,即剔除了“我”的大量直接的议论和抒情。“我”在文本中的介入更为隐蔽,或是寻找代言者,或是与人物形成自我指涉,或是以抒情独白的面目融入文本。并且,“我”与人物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总之,这样的改变,使得5 篇小说彰显了了多声部复调叙事特征,丰富了艺术表现,扩大了文本张力。这样的努力,与巴金对于自己包括《火》在内的以宣传为特色的抗战作品的不满有很大关系。《小人小事》的出现也是一位以青春激情写作为显著特色的作家,逐步走向蜕变成熟的信号。巴金在此后创作的名篇,包括为人广泛称颂的《憩园》《寒夜》的叙事方式,其实都可从《小人小事》觅得影踪。在此意义上,《小人小事》在巴金的整个创作历程中,具有转捩点的意义,不可轻忽。